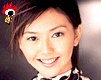一個國際非盲流文集的自序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0月22日 18:18 中評網 | ||||||||
|
《不敢恭維——游學世界看中國》序 丁學良 【釋題】
這些年來,每當我在中國境內境外遇到男女同胞微笑地詢問我"你定居在哪兒?"的時候,我都傻笑著答不上來。幾次"練"下來,終于找到一個頗為合適的應答,就是"我是一個國際非盲流"。"國際非盲流"實乃"國際明流"的避嫌變通說法,因為后者容易被誤聽為"國際名流"。而我尚不具備幾位中國演藝界出國人士(多半為女士)們的長城磚面皮功,在西方當了幾回一流影片的配角演員或四流影片的主角演員,便堅持不懈地在中國人圈子里自譽為"國際名流"。為避免誤解,我只好用拗口的"國際非盲流"替代更為朗朗上口?quot;國際明流"。 我和國內"盲流"人口的差別之處不難羅列。他(她)們是在中國境內流來流去,我則是在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流來流去。他(她)們的流動多半是盲目的,因為不知道哪兒有工打。我在國際間的流動則是明確的,流動前早已從公開出版物上得悉哪個國家的哪間大學或研究所招聘什么職位,研究和教學的條件如何,待遇的菲或厚。要成功地流過去,你得提供自己完備的學術資歷和學術成就的證明,經過國際性的公開競爭,中標受聘。否則,你想流也流不動。 我和國內"盲流"的共同點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走出了出生于斯成長于斯的小村莊,見識了外面的大世界。這個薄薄的小集子里的二十幾篇隨筆和短評,就是我作為一個國際非盲流在地球上時不同地方,對與中國有關聯的問題的雜感、雜想和雜論(但愿不被歸類于雜音)。 這些文字不是理論性的,雖然其中也有微量的理論的鹽分。它們也不是成體系的,雖然從頭到尾一派關切的主線仍隱約可辨(參見本集附錄之一《中國心,全球觀》)。它們不是為專業研究人員而寫的--我的這類專業文章和書籍曾經寫過不少,并且還在寫,用英語和漢語慢慢地寫。但這本小集子里的文章卻是有意識地為普通的中國公民而寫的--只要他(她)們具備大學專科或專科以上的正規或非正規的教育水平,便可大致讀懂。 【洋罪】 對于我以及很多像我這樣的人來說,能用母語中文寫作乃是一種罕有的奢侈(這當然意味看是一種高級享受)。自從1984年8月29日我半明白半糊涂地赴美國求學以來,15年里,能夠用中文寫文章的時間大概不合多于三十分之一。1也就是說,一個月里,難得有一天是在用漢語舞文弄墨。 大部分時間在干什么呢?大約三十分之二十九的時間里,是在受洋罪,名副其實的洋罪--用英文著述和閱讀專業文獻。有些讀者大概也知道,西方學術界有一句俗諺:Publish or Perish,可以譯作"不出版就完蛋"。對于西方學術界混飯吃的袞袞諸公,你手里的飯碗?quot;豆腐渣工程"還是"固若金湯",主要取決于你發表的論文專著知多寡優劣。而你用中文發表的東西,不論在漢語讀者群里獲得過怎樣熱烈的贊美或猛烈的攻擊,基本上不算"學術成果"。所以盡管我有事罵罵咧咧,斥之為"英語霸權主義",2還是得規規矩矩、埋頭苦惱地用英文思考和撰文。你若不想承受英文寫作的蹂躪,那就得主動或被動地下崗,在國外下海賺辛苦錢,或卷起鋪蓋回國來瀟灑地混飯吃。 【留洋】 方才提及,15年前我離國赴美留學是處于"半明白半糊涂"的境界,這絕非虛妄之辭。想當年,本人自上海某某大學某某系畢業后,歷盡周折,全仰賴一位出身于滿清貴族的儒雅恩師之助,才分配來偉大首都做小小的腦力勞動者,在某某學院某某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那個年頭,該學院聲譽正隆,連開小車的司機、管收發郵件的青工、打字機房的文員、往返機場接送外賓的秘書,都大半出身不凡。像我這樣一個三代討飯的赤貧農民的后代,能夠在這樣的研究部門工作,且頗受所里的器重,已經心存感激,真誠地覺著活得充實和富有意義,3故并沒有把心思朝"放洋"上作過多的癡想。 然而人生中偶爾也有歪打正著兒的契機。1984年初春,我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首次全國社會科學中青年優秀學術論文一等獎(詳見本集附錄二)。為著把論文譯成英文向國外推介,我結識了外交系統的一位年輕的老資格翻譯工作者。他十幾歲時便被政府送到倫敦學習語言,英語好到連美國名牌大學的教授都驚嘆不已。某日共進午餐,此兄在神速地結果了我虔誠地奉獻上的三份略有臭味的紅燒腔骨(每份價值二角五分人民幣)之后,摸摸腮幫擦擦手,若無其事地問我?quot;為什么不設法到美國去讀書?"我說到國外留學于我是近乎天方夜譚的事,自己英語不行,且又無特殊背景,很難獲取出國名額的。他說可以自己主動去申請,他過去幾年里,已經鼓動過好幾個人這么干,多數都成功了,其中有黃某某、紀某某等等(多半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后代)。 就這樣,他一手幫助我準備了(包括翻譯)英文的申請資料,逐一發出(共發出6份)。往往返返幾個回合,均遭美國大學的婉言拒絕,原因或是申請期限已過,或是缺乏英文能力的證據。可是這么一嘗試,爭取出國留學的念頭,卻明確地植入心中。 1984年夏初,經我的那位恩師的大力舉薦,和本人所在的學院數位領導的批準,我被遴選為美國匹茲堡大學Presidential Fellowship("大學校長獎學金",該校最高級別的國際獎學金)的第一候選人。在中國官方為該校校長波士瓦(Wesley Posvar)博士訪華舉辦的歡迎宴會上,校長先生略略問了我幾句話,我都半懂非懂。(他肯定對我的回答更加不懂),4就明確地對我說:"下學年開學時在匹茲堡見你!" 所以,我真是有福,既沒有考"托福",也沒有考GRE,就去了美國留學。波士瓦校長是知道我的英語不靈光,但多半是被我的學術簡歷打動了心:能在中國這么大的青年人口群中獲得學術論文一等獎,總不至于在英語上愚不可教! 簡言之,我留學西洋之"半明白"是指我在出國目標上的明白--去攻讀我心儀的"比較現代化"專業。這方面的興趣從1982年底畢業后不久就開始了,那時候的我已經對哲學空談失去了興致,轉和閱讀社會經濟發展的中英文書刊?quot;半糊涂"是指在出國途徑上的糊涂--不知道該怎么聯絡申請。這和90年代的眾多中國欲留學青年很不同,他(她)們是出國途徑明白--明自到可以勝任專業的留學咨詢公司的高級業務骨干,但出國目標糊涂--只要能出國,管它干什么都行。這個時代真開化了! 在匹茲堡大學的近一年時間里,聽到中國留學生傳說波士瓦校長的一些有越經歷。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美國空軍援華抗日"飛虎隊"的飛行員。在福建上空與日本空軍激戰時,座機被擊中,他負傷跳傘,被當地的抗日游擊隊營救。隱匿養傷期間,福建的老百姓常以海參作食物為他滋補。傷愈后,被中國抗日力量的地下交通網輾轉護送到緬甸的美軍部隊。據說戰爭結束后的很多年里,每逢重要的宴會場合,他都要在餐桌上置一盤海參,以忘不忘當年受傷獲救的幸遇。 (據本食客觀察,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不吃海參,因為那玩藝兒看起來很像大毛毛蟲,挺惡心的。) 波士瓦先生戰后讀了哈佛大學的公共行政學的博士學位,在匹茲堡大學校長的位置上坐了至少四分之一個世紀,成為當代美國主要的大學中任期最長的一位校長。5他早就有心要使他管理的大學成為美中兩國教育交流的灘頭陣地。在1980年以前,中國內地的青年很難去成美國,匹茲堡大學就接納了大量香港和臺灣地區的青年。等到中國內地對世界打開大門,匹茲堡大學就成了兩岸三地數百名中國青年學子聚集的重鎮。我去的那年,正值匹茲堡市被評通?quot;全美國最適宜居家的十個城市"之首。犯罪率低,交通便利,"教育和休閑設施齊備,人均收入中等偏上,自然環境優美,物價低廉(巨大的西瓜兩美元一個,雞肉每磅36美分,雞內臟沒人吃,白送你)。以我的"大學校長獎學金"的收入水平,一下子就進入了"小康"階層。 【跳槽】 可我這個人天性不喜歡在一個地方久呆。進了匹茲堡大學不久,接到美國東部幾所名牌大學的邀請去作學術報告。一圈轉下來,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全額獎學金、哈佛大學和福特基金會聯合提供的獎學金,同時對我表現出強烈接納興趣的,還有哥倫比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6順便說一句,麻省理工學院這所以理工著稱于世的大學,其經濟系、哲學和語言科學系以及政治學系和工商管理學院,都是第一流或接近第一流的,與我們國內的那種掛著"大學"的牌子、實為單一專科或單一學系的"理工大學"天差地別。 我獲得哈佛大學和福特基金會的獎學金,多仰賴國際知名政治學家、《中國季刊》的創始人之一、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全力舉薦。普林斯頓大學提供我全額獎學金,則得益于對中國-日本-俄國作比較研究的專家、時任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的饒濟幾(Gilbert Rozman)之熱情介紹。7這二位在此要受我一揖之謝! 經過幾番與國內有關單位的痛苦協商,我選擇了哈佛大學。從1985年8月遷入哈佛北園研究生宿舍Richards Hall,到1993年2月離開哈佛,我在坎布里奇8這個偉大的小城里,作了七個半年頭的臨時居民。其中六年半的時間是作學生,一年是工作兼將我的博士論文修改成專著出版。 每當我回答國內熟人生人的問題--"你在哈佛讀博士花了幾年時間?"提問的人聽了我報的數字后瞪大了眼睛,我總要解釋一番:不到七年拿到哈佛大學社會科學的博士學位,已經不錯了,因為那兒的學位要求非常繁復(參見《談何容易》一文)。1990年所作的一項統計顯示,哈佛大學社會科學系科的學生平均花費8.2年完成博士學位,這其中大部分是美國本國學生,沒有語言障礙。在人類學系和歷史學系,十年以上尚未畢業的老牌研究生并不罕見。9社會學系最長的一位美國學生至少花了14年,以至于有的同學背后稱他為"我們系里的歷史遺產"。 哈佛大學研究生的"窖藏年份"雖不短,比較起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又顯得"青嫩"了。因為哥倫比亞大學基本上沒有年限規約,你只要完成了博士必修課程的學分,通過資格大考,進入作論文的階段(即成為"博士候選人"),就可以離開學校所在地,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邊工作(或邊游蕩)邊寫論文。若論文完成后水平合格,你只要補足所有這些年里的學籍注冊費(約數百美元一年),就可以畢業了。我認識的一位哈佛大學副教授的夫人,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教育學博士,高校后的十幾年里,忙于照料她那可愛的寶貝女兒和參與環保公益活動,論文老是完不了稿。但她每年都把本年度的注冊費存入銀行,單立一個賬號,以期有一日完成了論文,將這筆不少的錢交上去,將一頂博士方帽拿回家。不久前我從她的近鄰兼密友的電子郵件中得知,她的論文"繼續在?quot;。看來她要當跨世紀的博士生了! 【云游】 我在國外選擇的研究領域屬于"比較社會學"和"發展社會學",因此很看重在現實世界里同中尋異、異中索同。到博士學位前后,我利用了多種機會,游學列國--北美、西歐、前蘇聯和中東歐、環太平洋國家及地區、靠近北極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迄今算來,尚缺乏對非洲大陸、拉丁美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感性體驗。準備待到電腦"千年蟲"對航空安全的威脅消失后,再一一這些地方。 我周游列國,實踐的是"行萬里路,讀兩本書,思一件事"的知行哲學。古人有言:"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在那個時代,有心人發憤尚能做到,在科技發達的今天,就難以身體力行了。古時候讀書人云游四海多半騎著頭小毛驢,一天的行程不過數十華里,萬里路行下來,好歹也得十年時光。古時的書籍字大而冊薄,一天讀它三四卷不成問題(根據我少時在家鄉讀明清時代木刻石印繡像小說的經驗測算得出)。萬里路行下來,讀萬卷書的計劃指標也就差不多達到了。而在當今時代,空中航行萬里,連兩頭往返機場的時間算上,也不過兩天辰光。能讀畢兩本書,已屬不易矣。"思一件事",就是反思"在這方面中國如何"?在國外的所見所聞、所學所行、所食所飲,都會本能地或自覺地拿它來與中國的相關事情作比較,發一番有言無言的感慨:"為什么中國不是這樣?"或"為什么外國在這種事情上不像中國那樣?"無言的感慨,多半已和著紅酒綠茶滲入肝腸。有言的感慨,小部分地收在這本小書里。 本集文章大致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談論經濟生活的社會和法律方面,第二部分是介紹"比較現代化"的基礎知識和哈佛的讀書體驗文章,第三部分主要是評判一些文化現象和教育問題,最后是附錄,目的是為讀者提供一些背景信息,以使貫串于本文集諸篇的那一脈關切的主線顯現可辨。近年來我在國內很多大中城市與大學生和大學教師的座談會上,以及與新聞界朋友們的交談中,時常面對相同的一些詢問。但愿本集收錄的幾篇文字,亦有助于回答他(她)們的問題。 這個集子里的絕大多數文章寫于20世紀的最后幾年,也有少數幾篇寫于較早的年間。這次搜集成冊的時候,我作了少量的文字的修正,主要是把報刊式的縮略語改成正規的完整說法。我沒有作觀點實質、立場迥異、幅度巨大的修改,是因為我歷來不贊成不實踐"文章隨時整容主義"--不時地把自己過去的精神產品重新粉刷后推銷給世人,說:"你看我多少年以前就這么英明睿智、高瞻遠矚、洞察一切了!"云云。這么做看起來挺莊嚴,實際上挺無聊。這次在加進一些新的資料和觀感的時候,我多半以腳注和附注的方式,以讓讀者明自各部分文字的大致年齡。 為著使國內讀者對本文集談論的域外人、事、情、景有點直觀印象,我也找了一些照片附上。可惜許多很好的照片已經不在手過了,它們已經散落在天涯四方。還有一些很好的照片從來沒有到過我的手里,拍攝者常常說話不算數,只給我寄回難看的,而截留下好看的。 【鳴謝】 本集子里的隨筆和短論得以發表并集腋成裘出版,要感謝多位先生和女士的鼓勵、支持和協助。這些人有的我有緣結交成友,有的尚無緣熟識。這些人生活和工作在中國境內或境外的諸多地區,經歷各異,地位懸殊,但都關心著中華文化的弘揚和中國人的命運。篇幅所限,我這里只能列出其中的一小部分: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孔憲鐸博士,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常務副院長姚先國教授,北京"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研究員趙曙青先生,上海復旦大學學報前主編王華良編審,《明報》集團主席、馬來西亞聯邦拿督張曉卿先生,《明報》月刊前副總編輯馬勵女士《國際政治經濟評論》編輯部主任邵濱鴻副教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總編輯林載爵教授,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制片人兼總導演時間先生,成都《改革時報》前主編劉恒壽先生,四川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秘書長竇維平先生和科技部部長鐘揚先生,《北京青年報》編輯張向紅女士,四川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文藝部總干事陸佳女士,香港《文匯報》前資深記者孫文彬博士,以及至關重要的人物--本書責任編輯王靜女士。 1999年6月 草于中國最炎熱的大城市(真希望不是北京!) 1.這不是精確的統計數據,而是大而化之的"匡算",有如我國報刊上常有的"國有企業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三分之一盈利";或"我國的國有資產流失平均每天一個億"之類。 2.我一直以為這個詞是屬于我的"智慧產權"旗下的作品,直到1999年11月初在香港聽了一場教育社會學方面的報告,才獲悉早在若干年之前,已經有西方(而且是英語國家)的語言社會學家運用這個詞進行社會批判了!西方一些知識分子的"自我批判"精神有時真令人挺感動的,可惜這樣的人多半進不了政府作大官,否則這個世界上得不公正就會少得多! 3.這不是戲言。直到今天為止,我仍然把那兩年視作我生活中最富有意義的時段。我真愿意舍棄我今天在物質生活方面獲得的一切,以換回那兩年里的那種感覺。人不能純粹生活在感覺之中,但沒有感覺,生活又是什么呢? 4.因為英語的聽和說不行,我在由北京赴紐約的國際航線上,差點"中途變卦"了--在舊金山市機場換機時,我所不太明白,險些錯上了一架不知飛往何方的班機。 5.匹茲堡大學擁有全美國大學校園里最高的建筑物:那幢號稱"大教堂"的主建筑有四十多層。匹茲堡大學的哲學系在美國屬第一流,它的醫學院是美國最早進行心臟移植的醫療中心之一,它的拉丁美洲研究也是極強的。 6.因為要跳槽,我心里充滿了對波士瓦校長的歉意,于是給他寫了一封請求理解的信。遞上去后,做好了承受各種責備的心理準備。誰知道兩天以后,校長的私人助理就告訴我,校長先生同意我轉學,沒有絲毫的責備。"連哈佛大學都錄取了你,證明他當初頒授'校長獎學金'時沒有選錯人?quot;他的助理這么說。 這件事可以說是使我對美國社會里的價值觀念標準有了第一次的親身體驗:跳槽與否不是關鍵,關鍵在于是"跳高槽"還是"跳低槽"。你能跳到高槽上去,不但沒有傷他的面子,反而為他增了面子。 7.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多半都有一個中文名字,有的名字起得十分典雅,如正文剛才提到的兩位,以及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謝和耐(Jacques Gernet)、傅高義(Ezra Vogel)、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年輕一輩的洋學者中,中文名字含義深遠看不多見,但有一位的名字卻起得相當得體:齊慕實(Timothy Cheek,任教于科羅拉多學院的歷史系)。遺憾的是,很多中文翻譯工作者都對此無知,碰上洋人名字就照音調直譯。這真是不尊重洋學者對中華文化(至少是漢字)的尊重,而且也常常造成混淆。但我這樣提醒未必有絲毫用處,當今世界乃"時間就是金錢"的大競技場,很多地方出書時連標點符號都來不及仔細校對,何來閑暇核查洋人的漢號? 8."坎布里奇"的英文名字 Cambridge就是"劍橋",因為哈佛大學的創始者們是英國劍橋大學的畢業生,為著紀念母校,他們就把哈佛大學的所在地命名為"劍橋"。國際上常把劍橋大學和哈佛大學問的學術論戰稱為"老新劍橋之爭"。為著區別兩個劍橋,只好把新大陸上?quot;劍橋鎮"譯作"坎布里奇"。美洲新大陸上很多地名都是從歐洲舊大陸帶過去的,比如"紐約"(New York)的意思實為"新約克"(York"約克"是英國地名)。在美國中部的地圖上,我還見到過Canton(廣州的老英文名),不知是否與咱們的廣州市有歷史淵源? 9.人類學系的博士研究生要熬很多年頭情由可原。按照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要求,做博士論文的資料必須來自學生親自搜集的第一手信息,不能抄用別人的。人類學系的研究生要去美國之外的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呆上幾年,與當地社會的人民同吃同住同活動。為了這種"田野工作"(field work即"實地研?quot;),學生得首先過語言關:你的外語口語不地道,就做不成這種研究。兩到三年的語言訓練,三到四年的實地研究,再加上至少兩年的專業必修課和兩到三年的論文實際寫作時間,可不就是十多年了嗎?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學人 > 丁學良 > 正文 |
|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