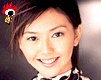轉型社會的法與秩序:俄羅斯現象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0月22日 18:16 中評網 | ||||||||
|
丁學良 引言 轉型社會就是從原來的中央指令型的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眾所周知的包括中國、越南、俄羅斯及東歐。"轉型"最初是一個限定很狹窄的概念,指的是經濟的
中國的轉型從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為止,已經有二十年的時間了。前蘇聯東歐那一大片國家的轉型,迄今也有十年了。套用一句俗話,中國二十年的轉型經驗,以及前蘇聯等許多國家十年的經驗,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顯得很短暫。但是對我們當代的人來講,對于所有關心轉型問題的學者和公民們來說,它們提供的正面的經驗和反面的教訓,仍足以使我們在這個時候能進行一些清醒的總結和判斷。而如果讓總結和判斷能夠具有啟迪的意義,一定要在比較的基礎上作出。如果單看一個國家,它所顯示出來的問題的深度以及問題所蔓延的廣度都會讓你很難把握。從比較的基礎上進行不拘一格、不帶成見的審視,這些問題所包含的現有的意義和潛在的意義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展露。 在今天的報告里,我將特別集中在一個很基本的關節點上,就是轉型社會中的法與"秩序"問題。我們中國人對"秩序"的理解是比較簡單的,通常只是指社會治安、街道上的狀況之類。英文中的"秩序"(order)的含義則深厚得多,強調的是結構化的政治和社會關系(structural relation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我在報告中對"秩序"的使用是基于這個意義上的。以下凡是涉及到重要的概念我將提及乃至使用英文,因為一些重要的概念常常引發很多很深的問題,但很多的中文的翻譯本身是誤導的。對于我們研究法學的人、研究法哲學的人、研究法社會學的人,特別是研究很基本的憲法以及合同法等等的人來講,要精確地理解這些概念本身的含義,應該是一項基本功。 影響巨大的一個概念框架 從1980年代早中期開始,一些深刻的經濟的或社會的變化在前蘇聯和東歐等國家展開。而且,到了這個時期,中國改革的趨勢也越來越深化。在國際社會科學界,學者們力求找到一個新的理論構架,因為所有發生在這些國家的那種種的現象已經超出了原來西方那些成熟的(received)理論構架范圍,那些成熟的理論構架無法解釋從1980年代早中期從這些社會里面出現的日見明顯的經濟現象、文化心理現象、宗教現象和政治現象。在為著應對新的形勢發展而不斷涌現出來的各種理論嘗試中間,有一個概念構架影響最廣泛,很多人都不會生疏,那就是civil society versus the state理論。對civil society的翻譯至少有三種: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這三種翻譯各有長處,但沒有一種是精確和完整的。大家知道,civil是很多重要概念的限制詞或字根:civilized──受過教化的和有教養的、civilization──文明、civility──文明性或文明的狀態。還有密切關聯的諸概念如civil law──民法、 civil court──民事法庭、civilian──文治的或平民的,等等。所有這類文明化了的社會狀態或社會制度,都與法律對人類群體的調節和規約有關。用十九世紀末英國著名法學家John Westlake的名言來概括,就是"沒有一個人類社會可以無法,沒有法就沒有社會"。 但是以上"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三種翻譯都沒有完全把civil中的深層含義揭露出來。versus是指against(對立),一種對立的關系。civil society versus the state(我們暫且將它譯作"公民社會對抗國家" )這個理論框架是強調:在轉型社會里,原來的那個無所不在、無所不管的國家機器在縮減。很多以前由國家自己去干預、自己去做的事情,正在放開。這種放開在有些情況下,是自愿做出的,有些是在形勢的要求下不得不然。這個理論架構的含義是,如果要讓civil society增長,必須要求國家涵蓋的各個領域收縮,國家的力量下降。因為這兩方之間的關系是零和關系,一個強大的無所不在的國家必定意味著civil society是受壓抑的,社會領域里就不可能有常態的civilizing和civilized activity(文明化的活動),比如法治、個人的尊嚴、私有財產的合理保障、社會的和平安定、人民的自由、文化領域的自主、個人的創造活動、新的觀念和新的嘗試辦法層出不窮地涌現出來、非常好的從事上述社會實驗的條件和機會等等。要想有這樣一種社會生活的狀態,前提必須是the state的縮減和衰弱。這就是那個理論構架的基本含義。 這個理論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廣為流傳于東西方,至今已經有15年了。我在1993年寫的一篇論文對這種理解提出了批評。 我當時提出的批評主要著眼于一點,就是這個模式主要是基于英美種族(the Anglo-Saxon的)國家與社會的歷史經驗。在英美種族的國家的歷史經驗中,從來就是一個很小很弱的國家政權面對一個很強大的civil society, 以致于多年里人們研究英美民族的政治,可以不考慮國家機器的地位。換言之,the state可以在分析中不作為一個基本參數。 在英美國家的法律尤其是美國的憲法傳統中,最基本的制度設計考慮的就是如何制約政府的權力, 因此導致了這種把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看成是零和關系的觀念。我認為這種觀念不但不能描述亞洲的情況,甚至不能描述歐洲的很大一部分如德國、拉丁語系國家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近現代史上的經驗。在德國政治哲學和法理學中有一個非常強有力的理論就是"有機國家"論(the organic state), 這個organic state理論講的就是,一個德意志民族像一個人的有機體一樣。在這個民族里,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就同一個有機身體的大腦、心臟和四肢的關系一樣,是不能分割的。用黑格爾當年法哲學的名言來說,身體作為一個有機體只能以整體的方式存在,解剖室里的一具尸體的內臟或肢體只能稱其為實驗品,而不能再稱其為"心臟"或"人手"、"人腿",因為把它們單獨拿下來就再也不能發揮本來的功能了。把一個民族內的國家政權和社會的關系視為互為條件、互相依存、同生同滅的有機整體,在德國等國家里這個思想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所以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理論不能描述和解釋它們。 事過六年了,我現在要對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模式提出第二個批評。多個國家的轉型經驗,尤其是俄羅斯的經驗表明,the state的力量的衰減并不必然導致或幫助civil society的健康發展。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是零和關系,不是此長彼消的正負關系。 在當今的俄羅斯所發生的最深刻的變化中,那些牽涉到法律和秩序的方面,有兩個大趨勢值得我們關注。 "俄羅斯現象" 第一大趨勢是the feudalization of the state,我們中文可以把它翻譯成國家的"封建化"。但是這里必須再次提醒,英文feudalism和feudalization同我們國內理解的"封建主義"的含義不但是不同的,而且在根本上、在基點上是截然相反的。我為此寫了多篇論文,試圖加以辨別澄清,這涉及近代早期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在英語中,feudalization指的是政治或社會結構的分裂、多元、離散的態勢,而在中國的政治教科書里,"封建"一詞講的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個發展階段,并因此成為所有壞東西的代名詞──"封建"、"封建大家長"、"封建專制"、"封建頭腦"、"封建作風"等等。而在英語中,feudalization恰恰是缺乏集權的、不足以高度專制的,因為它沒有一個權力中心,政治權力和公共權威四分五裂,很多權力成為私有物。記住這個關鍵區別,我們也可以把feudalization翻譯成"分封化"。 當今俄羅斯的"封建化"首先指的是在原來的國有社會主義(state-socialism)體制下,被法律和憲法規定為國家財產(國有財產、全民財產、公有財產)的那些財富不再是國有的了,不再是全民的了,不再是公共的了。這個財富的轉手過程并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營化。私有化是拍賣。而"封建化"或"分封化"講的是在當今的俄羅斯,葉利欽這些政治上的當權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為了當選,不斷地通過不那么明確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把原來屬于全民的財富暗暗地轉讓給那些最有權勢的寡頭們。 對原來國有企業的財產,葉利欽他們最初是采取發放民營化券的方法,像配給證一樣,表明對國有財產人人都能分得一份,分到手后可以轉讓。后來采取了更進一步的辦法,讓投資基金會或銀行來接管國有企業。俄羅斯的國有企業大得不得了,一個大型企業幾十萬人,一個城市就是一個企業。當年列寧的名言就是把革命后的俄羅斯變成一個"郵局",像管理郵局一樣地管理俄國的一切公共事務。葉利欽政府對龐大的國有企業要求由銀行或銀行主持的投資基金來接管。這些銀行家和投資基金的主管們并沒有很多資產,政府特許這些人成立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讓他們通過發行債券、股票等等的方式,付出極少的一點錢,也就是象征性地付錢給政府,來"空手道"式地接管國有企業的資產。這種方式的掠奪是"灰色"的,它得以大規模地進行,是因為主政者頒布了法令,用政府行為的方式,使得某些人或集團能夠順利地掠奪全民資產。英文稱呼是"Robber-baron capitalists",即"竊國大盜型資本家"。他們不是小盜,而是"大盜";他們竊的不是一戶、兩戶的私人家,他們竊的是全體人民財產的控制者──國家;他們竊來財產以后,不是藏在山洞里,而是轉手做資本,在所謂的"經濟改革"和"新興市場"中左右局勢。短短的一個稱呼,把他們與別的種類的掠奪者清楚地區別開來。 隨著整個制造業的衰微,俄羅斯目前的主要財源是原材料的開發和出口。 "分封化"的另一種表現形態就是當政集團把原材料的開采經營權和出口貿易權讓給一些權勢集團來壟斷。他們把俄羅斯的自然資源換來的寶貴外匯存到國外不拿回來。像這種通過出口轉移出去的國有資產,據比較保守的估計每年在250億美元左右,從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經有近2000億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時期俄國吸引來的外國投資總數還不到這個大出血數字的十分之一! "分封化"首先是從經濟領域、從公共財富的瓜分起步的。要使這種披著半合法的外衣、經由政府特許的竊取國資行為成為一種常規的、穩定的趨勢,就必須強化既得的利益結構。在原來的公有制的國家里,人們都是低工資、低收入,龐大的國有資產、公共財富都是由這里積累起來的。普通的無權無勢的公民當然對竊國大盜型的資本家很痛恨。所以為了強化他們的政治保護,他們就把那些轉移出去的財產的一部分作為政治資源,再返回俄國,有些作為葉利欽他們參選的政治獻金, 有些則在必要的時候為了選舉而撐托股市,造成一個虛假繁榮的局面,等到選舉過后資產就走掉了,大進大出。被分封了的國有資產成為一個由政治主宰和財經寡頭聯手的權勢集團隨意支配的政治資源。喬治.索羅斯在俄國市場上角力了好幾年,最后感嘆地說:"首先他們是把國家的資產給盜竊了。然后當國家本身變得有價值、成為法統的源泉的時候,他們又把國家給竊取了。" 對重要的地方官員,莫斯科的主政者們采取的辦法也是類似。他們把國家政權的一部分授予地方大員,不要求后者對公眾的交待和負責(public accountability)。他們和地方大員之間的交易就是:后者對他們個人負責,包括在競選的時候提供支持。 還有就是武裝力量的分封化。俄羅斯目前軍隊的狀況非常慘,這些年來保持著全世界軍隊中最高的自殺率和逃亡率。他們自我描述的狀況是:"We are hungry and angry"("我們既饑餓又憤怒")。但是對于那些非常少數的核心軍團,葉利欽不得不抓住。要取得他們的效忠,就要給這些部隊特定地盤的管轄權。軍隊的調撥和軍事資源的分配,不是按照國家的安全和防務利益,而是按照當政者個人的或集團的利益來進行的。 如果我們閱讀歐洲中世紀的歷史便可以看出,俄羅斯目前的狀況非常像歐洲十世紀至十二世紀封建制度的高峰期那種對社會資源的分配狀況。在那個時期,隨著希臘、羅馬古典制度的衰落和北歐蠻族的入侵,原來的公共權威、政治權力和財富被逐漸地瓜分掉了。這種瓜分是在不同的封建主之間進行的,每一個封建主都對他的領地享有最高的權力,封建主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經濟力量、收稅的權力、法事裁判權、武裝力量等等。因此,沒有全國統一的權力、全國統一的法律和秩序,沒有全國統一的稅法和全國統一的軍隊。這種對公共權力的分割現象在二十世紀末期的俄羅斯以一種驚人的規模重現。 在俄羅斯出現的第二個發展趨勢更值得我們研究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人關注,那就是the criminalization of society,即社會的犯罪化。Criminalization至少有兩種主要的含義,一個是由刑法來界定的,意思是某一種行為在以前不被法律界定為犯罪性質,而在新的刑法的條款中被明確定義為刑事犯罪性質。第二種含義更多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也就是我們所使用的含義,是指俄羅斯社會的眾多方面都基本上是以這種或那種犯罪的方式來進行。首先在經濟領域里體現出來的,就是銀行界和金融業。在今天的俄羅斯,百分之70-80的銀行后面都有黑社會在運作,至少與黑社會有關,"黃道"和"黑道"相勾結。幾乎每一個銀行都雇傭全副武裝的私人保安隊,保安隊的人員來源有兩種,一是黑社會組織,一是前克格勃保安部隊和內務部特種部隊。很多黑社會組織都與前克格勃有聯系,又同銀行勾結在一起進行運作。在今天的俄羅斯,在哪個星期里有一個小銀行的人被暗殺了,報紙一般是不會刊登的。要想登報,一定得是中等規模或更大的銀行的人被暗殺才行。在俄羅斯債務執行之類的經濟關系多半不是通過銀行交易,而是通過黑社會組織來實施的。俄語中也創造出了一些很新的詞匯,來描述這種情況。經歷過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我們現在能夠充分地認識到,當一個國家的銀行業、金融市場被黑社會所控制,這意味著什么? 進出口業也是與黑社會勾結在一起。如前所述,現在的俄國能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為了爭奪對原材料開采業的控制,暴力暗殺是基本的手段。這些暗殺和暴力事件盡管造成很多的人命損失,卻極少被破案懲處。 更可怕的是黑社會已經滲透到兩個對國家安全和穩定、對國民利益至關重要的公共領域:軍火貿易和公職競選。在俄羅斯你如果能出得起錢,核武器部件都能買得到,更不用說常規武器了。順便說一句,199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去俄羅斯,開車穿過邊境,沒人管,國家功能的這一重要環節已經處于癱瘓狀態了。國家機器衰落,邊境漏洞百出,軍火走私就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行業。走私猖獗的地步令人發指,軍火走私分子誘騙中亞西亞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主要是婦女)把放射性核原料藏入人身體內偷運過邊境。這樣的人充作了"肉體包裝袋",吸收的放射性元素高過安全標準的幾百倍、幾千倍,很快就會喪命。這種黑道走私實在是殘忍至極。 黑道積極參與全國性和地方性的政府職位的競選,特別是地方選舉。最有權勢的金融財經寡頭們多半擁有"槍桿子"(黑社會勢力)和媒體(主要是電視臺)。在競選過程中,媒體不是公共服務的器具,而是寡頭們操縱輿情的私器。主控黑道的人士也可能以金錢來安排選舉的關節點。 如果你的競選綱領很受民眾擁護,那么對手很可能雇傭黑社會來搞恐嚇,甚至暗殺。對于敢于揭露黑道滲透公共部門行徑的記者,黑道先是恐嚇,然后是暗殺。在俄羅斯很著名的幾位記者都被暗殺了,至今也沒有查出真正的幕后指使者。 對俄國社會的犯罪化,觀察家們的評價是:"在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俄國一樣,有組織的犯罪和大型工商業相互滲透重疊到這種程度,以致于經常無法分清楚,犯罪行為到何處止,合法正當的生意從何處始。" 俄國的國民經濟整體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幾個行業(比如已經提到的銀行界,以及房地產界和消費品市場)里,黑道更是不容爭議的"龍頭老大"。 有那么多著名的黑道人物出馬競選"杜馬"(俄國國會下院)的議員席位,是因為根據俄國憲法,一旦進入"杜馬",就可以獲得赦免權,免于被刑事犯罪法庭起訴和判刑。 "俄羅斯現象"為什么值得關注? 讓我們來作一個簡要的概括。俄羅斯近年來轉型的經驗,揭示了原來的那個"公民社會對抗國家"理論模式的另一個盲點,這是我在1993年寫那篇論文時所沒有看到的。現在應該更加明確地強調:civil society的增長絕對不能看作是國家機構體系衰落的自然必然的后果,二者不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相克相成的方面。對俄羅斯的現象,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法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也在重新思考。純粹從表面上來看,今天的俄羅斯即使不是一個穩定的民主制,也是一個西方式的政體架構,它有多黨制,有定期選舉,有幾乎什么話都可以講的新聞媒體,有了集會、結社的自由,有旅行的自由,等等。但為什么這樣一個國家在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發生了普遍的犯罪化? 1997年底,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的執行主編發表了一篇長篇評論,把俄羅斯的現象稱為democracy without liberties,意即"有民主的形式而沒有自由的內容"。這里的"自由"用的是復數,指的是法律所保障的諸多公民權,諸如個人的安全、財產的權利、公正的司法、基本的社會福利、對少數民族和其它弱勢社群的寬容和保護,等等。對于只有形式民主的政體而缺乏憲法所保障落實的公民權的制度,該主編稱之為"illiberal democracy", 俄羅斯是其中的突出實例。 雖然我們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很多問題引起從上到下很多人的不滿,但中國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在整體效果上仍然要大大地好于俄羅斯,這是國際上多數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的較公正的評論。盡管如此,身為中國學者,我們仍然要對俄羅斯現象進行深思。為什么? 第一個原因,是歷史的類似性(historical parallel)。有些學過比較社會學和比較經濟史的人們知道,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很厚的譯著,Karl Wittfogel的《東方專制主義》。在1981年,還出過一部也非常有趣的譯著,梅洛蒂的《馬克思與第三世界》,是商務印書館出的。 這兩本書都討論了主要來自馬克思,也受到麥克斯.韋伯影響的一個重要概念,英文縮寫是AMP,即"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年和晚年時期的馬克思專門研讀了亞洲和其他一些非西方社會的歷史,他發現西歐歷史發展的圖景基本上不適合亞洲。馬克思對亞洲幾個古老文明中普遍存在的、長期處在中央集權狀態中的生產方式一直找不到一個很好的分析概念,只好用一個地域性的概念"亞細亞生產方式"暫時標示它。而在討論歐洲的社會結構時他用的是分析性的概念,如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根據馬克思等人的研究,最夠格的AMP是中國、印度、埃及,其次是俄羅斯。馬克思等人老早就告誡,在這些地方,政治實體與經濟實體的關系、財產與權力的關系、法律與秩序的性質、個人與集體的關系等等,與歐洲的非常不一樣。歐洲和亞洲走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道路不同,代價不同,時段不同。在麥克斯.韋伯的比較經濟社會史研究中,象中國、埃及、俄羅斯這類有著強韌官僚集權制歷史傳統的國家,一旦官僚體制本身不再發揮社會經濟活動的中心樞紐的作用,如何找到新的制度化的源泉,也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分析上的平行(analytical parallel)。這里的關節點是"規模"與"秩序"之間的關系,中國和俄國都是屬于地球上少數幾個"超級尺寸"的大國。學習過政治哲學和法學的人都知道,在經典的理論中任何一個政治社會(political community)的規模同管理之間都存在著對應的關系。同樣的一套制度,如果它所管理的社會的規模不一樣,它的有效性將會非常的不一樣,即使在其他的方面,條件都相等。先哲們把這一點講得很突出的包括亞里士多德和盧梭,他們傾向于認為在比較小的社會里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法的權威、社會秩序和直接民主。在當代,對規模和秩序的關系作了非常有意思的探討的,包括耶魯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道爾,他和別人合作一本小冊子Size and Democracy(《規模與民主》)。另外,從經濟管理方面對規模和管理之間的關系作出非常好的探討的人有制度經濟學的大師威廉姆森。 在西方有北歐諸小國,如挪威、丹麥、瑞士、冰島、荷蘭等;在東方有新加坡,還有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些社會盡管在文化、種族、政治結構上不同,都表現出高素質的社會管理。這些從另一個方面印證了"規模"作為一個獨立參數的中心意義:規模越大,秩序和它背后的法律制度越難建立;反之亦然。 至少因為以上這兩個原因,我們中國學者要特別關注俄羅斯的轉型經驗,特別應當集中注意力在剛才我們討論過的那兩種發展趨勢上。我們要回過頭來看一看,在經典的法哲學、法社會學方面,有哪些方面的洞見可供我們重新思索和移過來使用。在西歐封建制度的末期至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初期,那時代產生了一個很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叫霍布斯。 他就警告過,人類生活的狀況可能是叢林狀況,大自然狀況(a state of nature),弱肉強食,沒有公共權威,沒有規矩,誰擁有暴力("狠"),誰擁有詭計("毒"),誰就占上風。"人對人象狼對狼那樣"。為了使這種狀況盡快地結束,每一個個人都有必要把他所享有的自由和權力讓渡一部分出來,以形成公共的權威和權力,這就是政治國家,the state。在他看來,要想讓文明社會存在并正常地運轉下去,政治國家實際上是必要的條件,即使政治國家作為唯一的和最高的權力(the sovereign)具有潛在的濫用權力的危險。之后,進一步闡述這方面關系的有黑格爾的法哲學。他講到在西方社會歷史發展的諸多階段上,一定要出現一個普遍意志(the universal will),就是the state. The state對civil society的關系,就是普遍利益對特殊利益的關系。這樣,個人的尊嚴,財產的尊嚴,社會共同體的安定和福祉才能得以維持。在西方的經典中間我們可以找到這些思想,為什么?基本原因之一是在西歐封建制晚期,他們遇到過類似今天俄羅斯現象的情況。引申到今天轉型的條件下,我認為如果泛泛地、一般地提國家的弱化和收縮,是容易誤導的。考慮到國家的力量和功能的多種可能性,應該提另外一個概念:state-rebuilding, 可以譯作"國家機器之重新建構",簡稱之"國家重構"。這個概念強調把政治國家的發展,當作是一個有意識的建構操作,同時又是漸進的過程。 當俄羅斯的轉型剛剛開始時,西方主流學派強調的是怎樣把它的全權國家搞散架。俄羅斯現象提示我們,把國家機器搞散架的代價是非常沉重的。把一個國家機器搞散架是一回事,獲得有實質公民權的民主政體是另一回事。破不等于立。所以在系統轉型(systemic transition)的條件之下,如何實施state-rebuilding這個過程是研究法學、政治學、社會學乃至于經濟學的人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我想強調,在研究轉型社會的學術出版物里,包括西方眾多主流派學者的流傳很廣的著述里,把許多概念過分地簡單化了,簡化到在邏輯上干凈利落,操作方便,而在認識功能上制造出只能看見黑白分明的僵化潛意識,對所有其他的形態視而不見。以前我們慣于使用的是"大政府,小政府","有限政府,無限政府","強國家,弱國家","全權國家","集權國家"這類概念。要想幫助轉型社會順利地轉下去,我們在國家重構的全過程中,必須要對以前的過分兩分法的簡單化概念"對子"進行重估。 State-rebuilding絕不意味著要完整地回到過去。可以這樣講,以前我們把"強弱"作為政府"規模"的一個屬性,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導。以前人們衡量一個政府的強弱,還看它能不能較自如地運用鎮壓的力量。當然,使用強制的力量進行鎮壓(coercion)是國家很基本的一個功能,這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在韋伯的國家理論、甚至在黑格爾的國家理論中都是很重要的。眾所周知,在韋伯的政治社會學里, 國家被定義為壟斷著合法暴力的最高的政治實體。但是,把"暴力壓制"這個功能當作國家強大有效的最重要的指標,實在是一個重大的誤解。 我們在進行state-rebuilding時必須要走出這個固有的誤解。從比較政治社會學的意義來講,一個專權的國家機器,并不必然是一個強韌的國家機器,一個受憲法制約的(constitutionally limited)或有限的國家政權,并不必然是一個不能有所作為的跛腳政權。同理,一個小的國家機器也不一定就是一個弱的國家機器,一個龐大的政府不等于是一個強大的政府。在這里我們要著力分清"硬政府"(hard government)不等于"強組織"(strong organization)。組織指的是組織的能量、適應力和效力。一個專權的政府并不等于一個有效的組織,一個能夠很有效地執行自己法定正常職責和功能的政府,也可能是其它領域里相當"軟"(soft)的一個政府。 加尼福利亞大學伯克萊校區的著名政治學教授Ken Jowitt曾經以古巴為例,說明強硬政府的軟弱腰部。規模很小的古巴,其政府從動員武裝力量、遠征非洲為安哥拉打仗,到多年里抗擊美國霸權主義等,是一個真正的hard state。但在其他重要的公共政策的領域內,如稅收、土地管理、經濟和貿易方面,古巴的政權搞得一團糟。因為它的organization是不行的,其效能遠不足以貫徹實行它自己制定的任務。它的國家機器是一個矛盾的實體:強硬而無能。Jowitt的這個評論同樣也適用于當年的蘇聯──正是這種"遺傳"的性質嚴重影響了今天的俄國,導致出現"分封化"和"犯罪化"兩種趨勢。 在經濟的轉型過程中,一定要很好地注意國家機器的效能問題。一部有效的國家機器應該是規模適中的,目標適中的,權力范圍適中的。它可能不是直接民選的,但也不能任意行事,得要尊重憲法對它的適度規約。1997年的世界銀行年度發展報告,主題就是建立一個"有效政府"。 中國在建立有效政府機構方面的當務之急是什么呢?要逼近這一目標,我們不能不想到對政府有限的資源加以合理配置的問題。為配合傳統的中央指令經濟的模式而設置的政府職能機構,在很多方面已經不必要了,它們的存在對社會來講是個負效益。很多在傳統的指令型經濟結構下不存在的或附帶性存在的活動領域,正在變成政府職能中最供不應求、最值得關注的要點。這樣的背景下國家機器怎樣進行調整,才能實現state-rebuilding的任務?在技術上,我們對此可以嘗試列出一個單子來。 讓我們舉例來說明。上個星期的《南方周末》報道了兩件事情,都是在中國的大西北。一個是寧夏自治區的一個很窮的縣,縣里的頭頭已經把自己九歲的兒子變成"國家干部"了,十一歲的女兒已經是"技術人員"了:他倆的名字已經列進了縣政府的編制里,可以吃"皇糧"了,而這個縣每年都從國家要幾千萬元的救濟款。另外一個例子,是青海的一大片古墓被盜挖,盜墓者們開始是拿著鏟子去挖,后來把大拖拉機開去了,光天化日之下連續作業7-8天,竟然沒有任何人來過問。后來記者問州政府,為什么不管?政府說我們的警力不夠,我們的車又破又爛,汽油又不多,哪能追得上他們呢?他們盜墓的開的都是好車、新車、進口車。 這兩個現實的例子的比較,恰好從一個側面提示我們:中國在轉型時期,state-rebuilding的關鍵部位應該是在什么地方。國家機器(行政部門、司法部門、國防部門等等)在必須花錢的那些環節上無錢可花,基本原因之一是國家機器的雇員在支配有限的國家資源時,可以違背國家機器的目的。只要這種背離組織目標的行為得不到及時和嚴厲的糾正,它們就會逐漸地使國家機器本身癱瘓。因此,我們首先必須對政府的有限資源重新進行合理的配置。在中國僅僅強調政府錢不夠用,這話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包括最為富裕的那些國家,都不會有任何一個政府會說我的錢多得用不完。經濟學之所以存在,法律之所以必需,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社會的資源永遠是相對不充足的。如果一個社會的資源豐富到那種程度,可以不受約束地使用,那還要法做什么?那還要經濟學干嗎?關鍵的問題不僅僅是資源缺乏的問題,更為要害的是如何配置的問題。我這里談的不是空泛的民主制度,而是談有效的國家機器的最低條件。 在傳統的中央指令型經濟體制下,行政部門把很多其他部門對公共事務的調整和管理的功能給同化了,對此,學法律的人大概感受最深。許多應該由法律來調節和管理的領域,在中國卻是通過行政干部的直接干預來對付的,是不會拿到法庭上去的,很多年里也沒有法庭。傳統體制下國家機器職能中最小最弱的部分恰恰是轉型過程中最需要強化的部分,其中很大一塊就是英文中的the judicial,即司法、執法。中國的經濟體制從單一的國有制走向多元所有制的市場經濟,一個一個的行業市場(the sectorial markets)一定是非常快速地分化出來,比如象房地產業、金融業、旅游業、個人服務業(美容、健身、心理咨詢,等等)、資訊業、教育業等等。這樣原來被黨政部門同化了的調節和管理的職能就要部分地分化出來。這個過程在中國已經開始,但還遠遠不夠,遠不足以保障市場經濟作為一個制度而確立,并且具備復生機制(self-perpetuation)。做個宏觀歷史角度的對比,當年韋伯在比較了西方的市場經濟同東方的經濟狀態后,得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結論,諸位可以在他的《經濟與社會》一書中查看細節。韋伯說,如果你看一看從宋朝到清朝前期的中國社會,就會發現當時商業已經非常發達了,財富的運作形式已經很精致了。在同時期的西歐,還是在黑暗的中世紀的陰影下。為什么后來工業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恰恰不是在最善于經商的東方大國中國出現,而是出現于西歐? 當然原因不止一條,但韋伯特別強調:在那個時代的中國,財富的創造、交易、轉讓、繼承多半是一種特許的權利,而不是一種普遍的權利;主政者皇帝和朝廷隨時可以從民間那里拿回來。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個人如果要發財,必須與官府和皇帝有特殊的關系,這樣才能安全地進行財富的積累與轉讓。而現代工業資本主義最基本的條件之一是要使財富的生產、交易、繼承具有長時期的可預測性。沒有可預測性,穩定的、大規模的生產絕不可能,更不要說投資于技術的積累和創新了。那么,長期的經濟環境的可預測性靠什么來保障呢?讓我們看一看迄今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就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示意圖表: 意 指 政 行 法 憲 見 示 策 政 律 法 條 例 ──│──│──│──│──│──│→穩定性、可預測性的程度 - + 在這個表上,公共權威(public authority)的行為被放在一個連續線上進行比較。越靠近右端,可預測度越高(more predictable)。公共權威的表現方式被歸納為六種三組。"行政條例"和"政策"組的可預測性或穩定性居中。因為它們的制定、頒布、修改和廢除需要經過國家機器的相關部門主管官員的集體討論和表決,但不必經過人民代表大會和立法機構的辯論和審核。而"憲法"和"法律"就要通過這樣的程序,費時較長,變更較難,所以社會成員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可以依照它們來調節自己的行為。"指示"和"意見"組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程度最低,因為它們通常不必經過相關部門主管官員們的集體討論和表決,更不必經過立法系統。一個有實權的主管官員就可以發"指示"(通常都是書面的)和"意見"(多半是口頭的),所以,比指示更多變的是意見,不成文的,領導打電話說我有個意見,他說過以后甚至可以賴帳。在我們中國,大部分的社會管理都是在意見至政策的跨度內展開的,隨意性強。隨著中國日益與世界市場接軌和互相依存,我們必需向更高的可預測性方向移動。 在這個歷史性的進步過程中,我們現在做的最多的事情是立法。立法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在過去二十年里立的法多得不得了。以后要進到司法和執法的層次。從中期任務來看,要建立一個高效能的國家機器,最重要的領域就是司法和執法。從遠期目標來看,要建立一個法治的國家,要使民主制從最基層逐步地向上發展,司法和執法都是至關重要的"軟件"系統的基本建設。沒有法治的市場,一定是強盜和騙子橫行的經濟地盤;沒有法治的"民主",也一定是強盜和騙子橫行的政治地盤。 小結 做個小結:在系統轉型的條件下,絕不能認為只要削弱了國家機器或政府的權力,就自然必然地達到civil society的健康發展。要成功和安穩地培育公民社會的生長,一個有效能的國家政權是必不可少的環境條件。在致力于state-rebuilding的過程中,相對于國家機器的其他分支,我們更需要把資源和注意力放在司法和執法方面,而不是行政部門。我們每年都設置很多的部門和辦公室,我們有無數的"辦";有了三、五個"辦"之后,再設立一個"協調辦",三個"協調辦"以后再設立一個"領導小組"。這是不行的。我們必需改變方式,才能保證中國社會的順利轉型,俄羅斯就是教訓。要把原有的在指令型經濟體制下過分擴張的部位裁減下來,把被這些部門耗費的資源轉移到迄今為止尚很弱小、但對中國新興的市場經濟和開放型社會相關的那些部門去。我們即使不擴大中國現有的國家機器的規模,只要對這個體系內部的資源進行重新的配置,當今中國社會里大家都頭痛的問題即使不能獲得完全的解決,也能得到很多的解決。對中國的基層情況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俄羅斯的問題在中國也有部分的存在,我們不能允許它們蔓延到俄羅斯那樣的地步。俄羅斯搞得再糟糕,還能賣自然資源,我們中國可沒有自然資源可賣。希望在座研究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的人都冷靜地思考如何在轉型社會里建立一個高效能的國家機器。如果問你,你希望自己的祖國成為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每個人都能把最美好的情景列出來,民主、自由、公平、富強、法治、生態良性循環、文化繁榮、科技發達,等等。最難的是在有限的時間跨度內,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在面臨著一大堆難題的時候,而且很多歷史問題積累在一起的時候,怎么能找到一個比較可行的切入點,這才是對政治智慧的考驗,是法律設計和制度設計的最關鍵所在。這個任務就落在或至少是部分地落在諸位的手里。 此系作者1999年夏天在北京大學的講演 原刊于《清華社會學評論》,2000年第2期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學人 > 丁學良 > 正文 |
|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