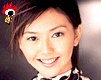訪談丁學良 從世界看中國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0月22日 18:11 南方周末 | ||||||||
|
崔衛平
中國心,全球觀
崔:您作為全國第一屆中青年學術論文一等獎的獲得者,1984年便去了美國,在哈佛從師社會思想大師丹尼爾?貝爾,這中間已經過去二十年。您是否愿意向國人匯報一下,這些年在外頭都學了哪些“先進文化”? 丁:我在國外做的研究——包括從做博士論文開始,一直到現在,始終圍繞一個基本的主題,即中國社會的轉型。你看我這么個人,在中國生,中國長大,在中國受教育,然后又去國外受教育。和很多中國讀書人一樣,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是懷著一顆中國心,就是說你頭等關注的事是中國的問題。但是不應該沉浸于“中國心、中國觀”。什么叫“中國觀”呢?就是僅僅就中國看中國,那種似乎是完全在關注中國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會產生非常狹隘偏頗的結論,很容易誤導別人。所以我提倡的是“中國心、全球觀”、“中國心、世界觀”。你一定要把眼光盡可能地放得開。 崔:世界這么大,您究竟是把中國放在哪一個范圍和角度去比較? 丁:我所關心的是兩個比較的范圍。第一,把中國和東亞國家及地區進行比較。東亞工業化比較成功的案例是1960年代之后的亞洲四小龍,在這之前是日本。亞洲四小龍是隨著日本的起飛而起飛的。比較研究的另外一面是前蘇聯東歐這一塊。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和東亞比較是因為中國和這些國家及地區在歷史、文化甚至人種方面具有很深的共同之處。比如香港、臺灣就是中國人社會,新加坡基本上也是華人社會。從文化角度來講,韓國、日本在國際上也被稱為是“儒教文明”圈子里的。這一方面的比較,使得我對許多觀念、包括出國之前接受的某些“天經地義”的觀念,來了一個大清洗。 崔:如何稱呼您所從事的這種比較研究的學科? 丁:可以稱之為“比較政治社會學”。這門學科最著名的奠基人是馬克斯?韋伯,他一生關注的問題是,為什么資本主義是從歐洲興起,而不是從當初其他條件更好的東亞(特別是中國)開始?研究這種轉型和革命不一樣,轉型包括了繼承在內,是漸進的。我們當然把經濟的轉型看得很重要,但是也把政治和法制的轉型看得很重要。在轉型中,政治和法律具有獨立的巨大作用,它們不是完全被經濟領域所決定的,不純粹是經濟的被動反應。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在法律、政治的層面上(包括行政)產生與之相匹配的(但不是同步的)變化,社會的成功轉型是不可能的。 現代公務員制度保證社會的穩定良性運轉 丁:我覺得我們看問題,一定要擺脫單一因素決定論的思路。它一定要找出一個終結的因素,或者是文化,或者是經濟,或者是政治,再拿這個因素來解釋其他一切方面發生的或者沒有發生的變化。這種思路造成了對于其他方面可能引導變化的動力的排斥。其實有些日本人當年在對待自己文化的態度上,比中國人還要極端。當年大清帝國被英倫三島的幾首鐵船打敗了,在日本引起的震撼不亞于在中國。他們幾十年的爭論所得出的有幾個結論是非常極端的,一是文化決定論。歸于文化怎么辦?因此日本要整個地“脫亞入歐”,脫離亞洲、加入歐洲,因為亞洲代表過去,歐洲代表未來;亞洲代表落后,歐洲代表強大——日本的出路在于徹底拋棄傳統文化,包括儒家文化。更極端的看法是亞洲“人種”也要改造,最極端的認為日本女人要嫁給西洋男人,這樣才能改造日本的種族,實現現代化。 崔:盡管有這樣一些極端的看法,日本人仍然靠自己的力量實現了現代化,同時沒有喪失民族的文化特點。關鍵途徑在哪里? 丁:在哪一方面?關鍵是有一批日本的改革者看準了制度的重要性,在制度上進行了效仿西方的改革。不是找到一個,而是找到一組比較好的、制度性的東西,這對后發展國家來說,是比什么都重要的。當年日本在現代化的時候,把歐洲和北美的一些制度進行比較,發現郵政系統法國好,于是學法國;海軍是英國好,于是學英國;鐵路系統哪兒好?美國好,于是學美國。法律制度學誰?在比較了英美、歐洲大陸的法律之后,用當時日本上層的眼光來看,發現德國的方式比較好。因為德國的法律制度給行政官僚很大的權力,而不給民間很大的權力。在選取制度時,他們是有長遠眼光的。這并不是說,日本的制度選擇是不需要批評的,日本這些年來出了很多消極事態,顯然與當初形成的官商協同制有關。但是總的來講,日本在制度要素的引進方面,是非西方的后發展國家中做得最早、最成功的。 崔:看來我們要對“制度”這個詞“脫敏”。以前一講到制度,就是姓“資”、姓“社”的問題,就是改變“顏色”的問題,其實制度是可以分成若干個方面,若干較細小的制度,在這些方面做一些變革,是馬上可以做起來的。 丁:對,有人覺得在制度改革上,什么事情也不能開口子,不能動,一動就是生死存亡的問題。這種心態很不理性。回到日本人的制度引進,他們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是公務員制度。此前日本的吏制一部分是來自中國的官僚制度,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到了近代,已經不管用了,因為沒有包括經濟、技術和法律方面的知識,是“一部論語治天下”的道德主義。道德主義和理性主義是不一樣的,理性主義是怎樣通過合理的途徑來達到一個理性地確定的目標。日本在引進現代公務員制度時,參照了德國、英國、法國,他們更多地是學了德國。公務員制度強調得是公務員的專業素質,有很明確的與政治家的職能分工。西方國家的公務員在政治上中立,我剛到美國學習時,覺得政治中立很奇怪,在政府機關里上班的人怎么可以在政治上中立呢?后來才知道,公務員政治中立對于一個社會的穩定和有效管理太重要了。 崔:為什么? 丁:按中國人“當官的”這種說法,西方的官分兩種,一種是民選的,叫政客(politician),一種是非民選的,通過考試和任命,叫文官(bureaucrat)。這兩種官員不是一回事。在成熟的民主制下,政客是定期選舉,過幾年就要選一次,因此政客是上臺又下臺的。但是政客的經常上下,不應該影響到非常復雜的現代社會在經濟、民生、國家安全方面管理的延續性、穩定性。公務員則是相對穩定不變的,他們有現代行政管理的專業知識。這在一個農業社會里是不重要的,但是在一個現代社會里是太重要了。你看農業社會,它是24節氣,按節氣來安排生產和社會事務。而現代社會是一個規劃的社會,其中主要的事情都是人決定的,是人安排出來的。這就是“大管理”。在傳統農業社會里,很多東西是不存在的,比如公共衛生系統、公共安全系統、郵政系統、交通系統、國際交往,更沒有航空系統、核能系統。所有這些都需要公務員在總體上協調和管理,他們的職能是執行法律和政策決定之后的社會大管理。一個公務員不能因為他在政治上喜歡哪一個黨、哪一個政客,而影響他對已經決定了的政策的落實,那樣會導致行政癱瘓和社會潰散。 崔:公務員制度保證了一個社會穩定良性地運轉。從比較研究的角度看,有哪些制度化的方法防治公務員在位置上呆很長時間而自身不腐敗? 丁:西方廉政措施里有一項我們可用:公務員每年一次或兩次,要申報有可能發生與公共利益沖突的那些活動。比如,你在政府某部門任職,每年要填一兩個表,申報在你的直系親屬中,有沒有人從事同你分管的這個部門直接相關的利益活動?假如你在稅務部門,那么,你的親屬在私立稅務服務所就業,這個事情一定要申報。假如你是在建筑部,你的親屬開了一家建筑公司,一定要申報。即使你沒有利益上的瓜葛,也要申報。申報才能過第一關。如果你不申報,哪怕你實際上并沒有勾結,你也違反了規則。這種對公務員的制度化控制延伸到公立部門的一切角落,只要是由納稅人的錢資助的公營機構,在里面就職的都要填這張表,以防止利益上的輸送。如果有一天發現你的實際行為和表上填的不一樣,你就要受到反腐敗法的追究。你全部的正式收入及來源,有沒有另外的收入,都屬于填表的范圍。假如你在政府的部局里工作,你的工資每年是四萬英鎊,而實際收入是六萬英鎊,那你的這額外的二萬英鎊是從哪兒來的呢?炒股票也好,稿費也好,都要有文件證據。雖然這樣不能達到對濫用公共職權的“零”控制,但它大大降低了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它有好幾個連鎖環節,譬如每個人每年都要填稅表,如果在填稅表時將自己重要的收入隱瞞,就違反了稅法;追查到額外收入來源時又違反了其它的法,那么好幾個法律就會疊在一起對你處罰。又假使某人不填表,如果他的實際生活和消費已經明顯超過了合法收入所能達到的水平,也會受到法律的追查(尤其在香港和新加坡)。再加上媒體的常規報道,就能夠大大加強對整個政府公務員系統的監督,抑制腐敗大面積的發生。 好的大學是創新之源 崔:在比較研究中,還有什么其他感受深刻的題目? 丁:我很關心的另一個話題就是大學制度。這20年來在世界范圍的綜合評鑒中,亞洲能進入前50名的大學一個也沒有,中國能進入前150名的大學一所也沒有。進入大學排行榜前200名最多的亞洲國家是日本,它的大學制度當年是從歐洲學來的,但后來沒有邁出第二步——仿效美國之長的改造。中國1949年以前的大學制度和日本的來源類似,后來卻改造成了蘇聯式的,與世界大學發展的主流脫了節。從比較研究的視野可以看出,等到新的產業部門越來越以知識創新為前提、國家的綜合實力越來越依賴于“軟力量要素”的時代,原來亞洲從18-19世紀的歐洲引進的大學制度就不夠用了,更不要提蘇聯式的了,必須進行第二步的改革。 崔:這第二步主要體現在什么方面? 丁:這方面美國對亞洲的啟發極大。當今世界上,美國的大學數量最多、辦大學的模式最多樣化,效果相對而言也最好。美國當初在引進了英國、德國的大學制度之后,結合自己國家發展的需要和國際競爭的趨勢,進行了長期的、多元的改革創新,1950年代起取代英國,成為全世界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大學辦得好,太得益于辦學的多樣性。它的大學不是一個以公立大學為主的體系,而是社會多元的財源辦大學,因此葆有活力。美國也有公立大學,但大部分是私立的,最著名的幾所都是私立大學。美國的體制從二戰以后(到1990年代更突出),大學日益成為研究的中心,這種模式對于18-19世紀歐洲式的大學提出了很大的挑戰。我在美國十年,經驗的是美國制度,在香港和澳大利亞十年,經驗的主要是英國制度,所以體會非常深刻。美國大學的優勢到1970年代都不是很明顯,從1970年代之后越來越突出。美國的一流大學重視開創性的研究,而且研究不僅僅局限在象牙塔里,它還重視把研究成果進行“產學結合”,帶動新的產業。它們的研究也不僅僅局限于應用技術,在基礎科學和社會科學上都活躍。所以如果我們把“產學結合”的這個“產業”的概念在社會科學的意義上擴展,那么可以說它對于行政現代化、國家的公共政策、發展戰略、外交政策、國際競爭,都有巨大的助益。這個模式對亞洲來講挑戰太大了!一個國家的大學的創新力不夠,就會壞事,因為大學在現時代,無論從科學角度、技術角度還是制度角度、觀念角度、文化角度,都是整個社會創新的最重要的源頭之一。 崔:大學里的創新思路,如何對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起引導作用? 丁:一個大國的研究型大學所起到的作用,與政府或企業辦的研究所不一樣。不一樣在于,政府自己辦的那些研究所,研究的問題在政策層面上比較具體,偏向于執行的方面。但對于一個國家發展影響最深遠的,是那些開放性問題的獨立研究,這應該是在大學里進行的。比如美國社會里的種族關系,在1960年代激進主義的時代,大學中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認為,美國社會欠少數民族尤其是黑人的太多,因此應該大力扶持少數民族,尤其是黑人。但是那時候也有少部分大學里的研究成果不同意這樣做,指出這樣做的話,可能會有兩個壞處。一是那些非常有能力的白人有可能被歧視,這會在整體上影響美國社會的發展,而且也不公正。第二,更有意思的觀點是,少數民族中那些真有才能的人也不愿意這樣做。他們認為,如果少數民族人升得很快,這些成功不是基于他們能干,而是他們受到了特殊照顧。這樣可能在少數民族中產生一種依賴思想,他們用不著非常努力,因為他們一定會得到特別照顧,這就無意識地鼓勵了懶漢思想。這兩種觀點自1960年代以后一直在爭辯,大部分時候是前一種補償觀占主導,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社會觀念開始轉變——越來越強調以后還是應該對所有的種族用同一個標準去衡量。我自己并不認為這兩種政策哪一個是完美的、應該永遠執行下去,但是我認為美國的研究體制就好在這個地方,它讓多種觀點都能夠發出聲音,雖然有的聲音大,有的小,因此這個國家不會把一條路走絕,它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不會出現那種不顧一切代價、蠻干到底的狀況。這一點值得我們中國人重視。美國研究型大學中,無論是國內公共政策方面,還是外交政策方面的問題,研究項目不是“一刀切”,沒有統一口徑,所以走新路的機會不至于被封閉。 崔:這樣一種開放的大學研究體制,肯定需要同樣是開放的人才引進制度? 丁:要想使大學為社會進步、為國家各領域的發展提供創新的源頭,重要的是大學必須開放地向世界招聘人才。全世界辦得最好的大學都是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好大學本身就應該是全球化的先鋒,只要看看著名大學的背景就知道了。譬如早先的英國牛津、劍橋大學,吸引的師生決不僅是本國的,至少是歐洲各地的,后來又吸引了北美的好師生;德國的洪堡大學、海德堡大學是整個中歐人才的聚集地;美國那些最好的大學的教授和學生更是全球化的。亞洲的大學直到二十世紀快結束時,教員還沒有全球化,學生全球化的也少,這樣就嚴重限制了它們創新的機制。道理很簡單,人只有來自五湖四海,才能把天下最有意思的觀念和設想帶來。人才是互相刺激的,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才產生刺激。這是我最想在中國呼吁推動的事情,就是讓中國資源最豐富的那些大學,在招聘教員的時候全球化。研究型大學還有一個基本的社會責任,就是在觀念方面、公共政策方面、外交戰略方面(也就是“軟力量要素”),成為國家整體利益最好的代言人和推動者,這個角色對后發展的中國來講更重要。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那些應用科學的成果還可以拿錢去買到,但是在開發那些軟力量要素上、在給本國國民提供開放性的思路上,用金錢去買是買不到的。這是中國的大學最應該發揮的公共服務職能。 印度尼西亞的教訓 崔:在您進行現代化比較研究的范圍之內,看到哪些現象是中國要高度警惕的? 丁:我覺得對中國最有直接警示的負面案例,是二十世紀后期的印度尼西亞。印尼在蘇哈托政變成功之后,一直用強制的方法推進工業化現代化,而且也在多年內保持了高速增長,全球許多國家都到印尼投資。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嚴格壓制了社會里的批評聲音,但使得印尼老百姓中的很多人從農業文明前期的漁村,一下子邁進了工業社會的前期。因此在二十多年的統治時期,蘇哈托覺得自己對這個國家貢獻太大了,全國都應該感謝他。但就是在這個高速發展、同時也是在以穩定為目標的二十年里,政府沒有清醒地看到印尼社會積累的那些問題——特權集團的勾結、嚴重的貧富不均和腐敗、金融機構的潰爛,等等。結果在全球化大潮中,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使得印尼在20年里取得的成果在幾個月內幾乎喪失殆盡,緊接著就出現沖突、暴亂,差不多幾天之間跑走了絕大部分外資。這種情況決不能在中國發生。任何發展中國家出現類似狀況,最吃苦的還是普通百姓。 原載《南方周末—閱讀專欄》 2004-3-25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學人 > 正文 |
|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