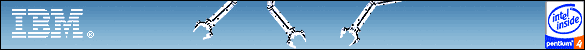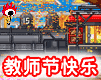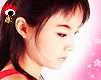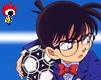| 林毅夫:一個經濟智囊的自助、他助和天助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9月07日 14:32 南風窗 | ||||||||||
|
章敬平 2004年8月17日晚6時許,52歲的林毅夫隨著“中國優秀經濟學大學生夏令營”營員們期待的目光,以他一貫的優雅姿態,雙手有節奏地擺進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萬眾樓。除了著裝上的隨意莊重之別,林的“課堂姿態”和他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朝堂姿態”,并無二致。
過去十數年里,有官方經濟智囊稱謂的林,出任過4屆全國政協委員。 掌聲響起來。40多名來自中國各個大學的營員用大學生們獨有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林的擁戴。營員中鮮有人知曉,10年前,萬眾樓所在的朗潤園一片荒蕪。彼時,這個昔日乾隆皇帝第十七子的府邸,這個道光末年被轉賜于恭親王的皇家園林,里面雜亂地住宿著近50戶北大的、甚至是燕京大學時代留下來的職工家庭。除了門口兩個雄偉的石獅子,朗潤園聞不到一絲書香,看不到一點旺盛的跡象,無情的戰火和歷史的風霜,早將往日王府的繁華淘汰盡凈。 反觀今日修復一新的朗潤園,古樸而有十足帝王氣,已然北京大學最有園林特質的經典建筑。懸在湖心島上蓮蓮荷葉畔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牌匾,業已簡化成CCER,沉淀在中國經濟學人和經濟官員的心目中。10年來,從篳路藍縷間一路走來的這座四進園林,已是中國經濟政策研究的重鎮,一個非官方的經濟決策機構。它不僅將西方經濟學的范式,系統紹介到中國,確立了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準則,推動了中國經濟學與世界的交流,還成為中國領導人信任的一個智庫。身為CCER當之無愧的領導者,從臺灣泅水到大陸的林本人,也在10年的磨練中成為海外矚目的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智囊。 CCER是北京大學一個體制創新的研究機構,觀察人士對它所顯示的勃勃生機的不解,就像臺灣島人不理解林當年為什么來到中國大陸一樣。 回望CCER10年和林的驚人的個人成就,林以為所有這一切,皆來自自助、他助和天助。 自助:勤奮,責任感,以及品格 講演、集體答問、個別釋疑、合影,原定2個小時的講座延長到將近5個小時,林以極大的耐心和寬容事無巨細地滿足了學生們的所有要求。在一個本科生很少見到教授的年代,學生們感動不已。 林說,他只是在盡一個教員的本分,他沒想過要做教育家,如果有幸成為經濟學教育中的大家,那最多是個副產品,就像他成為官方智囊一樣。教育家、經濟學家、官方智囊、社會活動家、名士—在民間人士和傳媒隨意授予的頭銜中,他最喜歡的是經濟學家。 2002年3月8日下午,全國政協會議期間,林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一個全國政協委員誠信問題記者招待會。是次招待會上,林贏得了經濟記者們對于一個本土經濟學大師的普遍贊譽。 招待會開始后大約半個小時,在座的政協委員中,有人已被記者提問了好幾遍,唯有林無人問津。終于,一個女記者打破了林被動的沉默。他笑意盈盈地聽完了她的4個問題,說:感謝你的提問,讓我不再擔心我會像是一籃擺在講臺前的鮮花。嗣后,作為195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第一個在美國攻取經濟學博士學位后歸國的經濟學家,他以西方式的優雅和禮貌,向所有到場的女記者表達了節日的祝福。記者們注意到,林回答4個問題的前后順序是三二四一,該記者所提經濟問題背后的邏輯頓顯清晰明了。 學界認為,林之所以占據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制高點,可能在于他總是把握內部邏輯的一致,以及邏輯推論和經驗事實的一致。 林說,他將經濟學家和職業乃至理聯接在一起,已有25年的歷史。這段歷史在他的人生中,原來是一個極大的偶然。很難想象,若無堅毅的“自助”之心,偶然怎么會成為必然。 1979年夏天,軍銜上尉的臺軍連長林毅夫,從金門游過那一彎淺淺的水來到大陸。在他登岸的福建,林被當作賓客參觀游覽了兩個月。而后,他向大陸官方提出工作的請求。要謀職就得知曉大陸社會,要明了大陸社會最好的方式就是讀書。幾經輾轉,北京大學接受了他。在北京大學經濟系,他開始研習政治經濟學。林與經濟學的偶然因緣肇始于此。 這一年,他27歲。現今,向他討教的很多學生在這個年齡差不多拿到了博士學位。 3年后,林深造于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師從于197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今天的人們除了“機緣巧合”,可能找不出更為恰當的詞句,來描述林是怎么與經濟學大師親密接觸的。彼時,舒氏到北京大學發表演說,林的優雅姿態和同樣優雅的英語口語,使得他成為翻譯的絕佳人選。據稱,講演完畢,舒氏對林表現出溢于言表的欣賞,并以極大的誠意邀請他去美國讀書。于是,林未經申請即幸運地拿到了芝加哥大學的獎學金,進入全球經濟學研究的第一方陣,像臨摹大師畫作的習畫者,悉心揣摩諸多經濟學大師的治學方法。讓關心他的人覺得欣慰的是,借助去美國讀書的“東風”,他在異國他鄉和分散3年的妻兒團聚了。 又4年,舒氏為他戴上了博士帽。接著,林去美國另一所著名大學—耶魯大學,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 據稱,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素以學風嚴謹,淘汰率高著稱。林用4年的時間,拿到了一般學生需5至7年方可拿到的博士學位,且是同時入學的同學中第一個拿到博士學位的人。迄今,林是1970年代后第一位在國際最權威的經濟學學術雜志《美國經濟評論》和《政治經濟學雜志》發表論文的中國大陸經濟學家,也是到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一位。 觀照自己的成就,林并不認為他真的具有出席政協記者招待會的人們眼中的“天分”。他說,他去美國時年屆而立,由于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美國的巨大差距,他在芝大遭遇了別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和困厄。如果不是一個“毅夫”,一個有毅力的人,一切都不可能。他的成就完全得益于超人的努力,而非其他。盡管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支,需要治學者對社會經濟現象的深刻體悟,但悟性替代不了勤奮。 與其相信林的天才,不如相信他的努力。林給他的學生的一個座右銘是“成功等于機遇加上努力,而機遇屬于平常就做好準備的人”,他在跟學生聊天時,曾說過“將軍最大的榮耀是戰死疆場馬革裹尸還,學者最大的榮耀是累死在書桌上”。CCER不像北京大學體制內的其他院系,為了CCER的發展,為了給“海龜”們一張寧靜的書桌,林不得不扮演一個四處化緣者的角色,從事大量的社會活動,為CCER贏得有利的外部環境。但,林并未因此豁免自己在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時間成本,從CCER的網站上可以看出林一個人每年在國內外發表的論文的數量經常是CCER其他同事的數倍。被問及“林是否像傳說的那樣白天忙于社會活動,夜間忙于經濟學論文的寫作”?跟隨他數年的秘書陳曦說:這樣的問題已接近真實的林毅夫了。 今天春天,新華社浙江分社副總編輯張奇志在CCER攻讀《財經》獎學金。他說,在波蘭前總理來CCER的那一天,林上了一整天的課,接待這位歐洲前政要前,林在辦公室草草吃了一個盒飯,然后主持晚上波蘭前總理的講演。次日,林接著講演和上課。張感嘆林的體力非常人可比,他作為學生在臺下聽課都受不了,而林卻總能精力充沛,有條不紊。 林自以為,身為知識分子,他窮其一生而不停歇的動力,離不開擔當社會責任的儒家情懷。1987年,林學成回國。他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后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那時侯,拿到美國著名大學博士學位的人很少,回國的則少之又少。問林為什么會成為“少之又少”的一分子,他談到兩點理由: 首先是立志做一個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家,他看好中國研究經濟學的前景。中國的經濟改革和轉型,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度經濟學的實驗場。 其次,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對中國經濟現象的研究,有助于中國的進步和未來。 事實上,他為什么回國,和他25年前為什么從臺灣來到大陸的理由,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他曾對香港《亞洲周刊》的記者說過,作為昔日臺灣青年的楷模,他泅水到內地的思想轉變,“不是從哪一天開始,而是長期不斷思考的結果”,直接的動機并非臺灣島上猜測的那樣,而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要對中國作貢獻,就要到內地來”。 根據林的自述,他從小就喜歡歷史。少年時代閱讀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屈辱史,便開始思考討論如何使中國富強的話題。這也是1960年代后部分臺灣年輕知識分子的話題。發生在保釣運動、尼克松訪華、中日建交、中美建交諸多事件之后的歷史,促使林意識到中國強盛的希望在大陸。 一個“自助”的人,不但勤奮,對國家有責任感,還應當有獨立的人格。林待人接物,無論達官貴人,還是一般的學生,都是一樣的分寸。《經濟學消息報》總編輯高小勇出身軍旅,曾是文學青年,不但沒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更非經濟學科班出身。但林仍然和高有著很好的友誼,對高身上諸多可貴的品質表示欽慕。高籌辦《經濟學消息報》時,財務困窘,林不僅投資了他的報紙,還為這份報紙積極撰稿。 在美國獲得終身教職的CCER副主任李玲稱,林的品格,與他的胸懷和人生歷練息息相關。林的血脈中流淌的是“六經”的要義,他在臺灣省宜蘭縣讀的小學,誦讀的國文中大多蘊藏著傳統的士大夫情懷,忠于國家,孝于父母,義于友朋,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就在他讀中小學的1960年代,中國大陸正處于傳統文化被革命被當作四舊橫掃的年月。或源于此,有人牽強地解釋為什么同年代的經濟學人中,林是少數沒有遭際道德攻擊的人之一。 林經常出入于廟堂之上,作為中國領導人的智囊之一,他身邊總少不了達官貴人的身影,他們給予CCER的幫助也可謂善莫大焉。林讓人欽佩的是,他沒有像坊間傳言的些許經濟學人那樣,以“客卿”或者“幕僚”自傲,而始終保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 他助:君子不同而和 2004年8月19日,林在北京飛往上海的航班上對我說,不能將CCER的集體成就悉數歸功于他一人,即便是他自己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成就,他也不認為是他一個人的事情。林認為,一個人的成長絕不是一個人的事。他之所以有今天,仰賴的不僅是“自助”,更有“他助”。 林說到人生難以承受感謝之重,一口氣從家人,老師說到朋友和同事們。 今天暑假的“中國優秀經濟學大學生夏令營”就是他大哥林旺松資助的。說到家人的助益,他還提到了自己的二哥和姐姐。據稱,他在臺灣的親屬資助他的非但是金錢,還有精神。2002年5月,林父辭世,臺灣方面考慮到他“叛逃”的歷史,聲稱不放棄對他的追訴,以至林不能赴臺奔喪,盡為人子者的最后孝道。林心靈深處的痛楚一般人難以得知,關注他的人們只能從他接受香港鳳凰衛視專訪時滾滾的眼淚,推測他的苦痛。是他的家人在他最為痛苦的時刻給他以精神支持,對他不能返鄉奔喪表示諒解。 25年來,林一直對北京大學心存感念。在1979年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文革的遺毒還到處彌漫的時候,正是這個中國第一高校接受了他,給了他這樣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繼續深造的機會。倘若沒有前校長吳樹青以難得的擔當,乾坤獨斷地給以支持和勉勵,在1990年代初葉的中國大學探索一個體制創新的CCER,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外部世界的有利,固然舉足輕重,若無內部人士共襄義舉的志同道合,是成不了大事的。林很感謝周其仁、易綱、海聞、張維迎等人,他聲稱,CCER是共同智慧共同努力的共同產物。CCER是一盤棋,他一個人是沒辦法做“局”的,得要好幾個“眼”方可。CCER草創之初,只擁有北京大學地學樓里兩間半格子式的辦公室,從海外歸來的博士們,沒有將條件的艱澀歸咎于他,卻在功成名就時,讓他以主任的名義獨享了不知情者給予CCER的集體榮譽。 領導者和集體成就之間的道理人人都懂,人們詫異的是,林用什么樣的力量將個性差異殊大、治學方法各異的經濟學家們,聚集在一起,做到不同而和的? 接近林毅夫的人們沒有直接回答“不同而和”的秘密,而是間接地敘述他是怎么做到“和而不同”的。 林予人的印象,多是藹藹君子之風,待人接物以謙和為主。可他在學術上卻始終堅持君子和而不同。最典型的事例,莫過于他和故交楊小凱教授的論爭。 2004年7月8日,林在始終充溢著他的微笑的朗潤園內淚流滿面,追悼英年早逝的“論敵”楊小凱。楊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海外華人經濟學家中的翹楚,供職于澳大利亞莫納斯大學,兩年前楊于北京的一次演說中,以一個華人經濟學家的學術和社會使命感,提醒中國注意其后發劣勢。楊認為,西方經濟學家沃森“對后來者的詛咒”的概念,或可在中國發生。他指出,發展中國家有先從技術模仿以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的傾向,但是快速的經濟增長會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建設,而強化了國家機會主義,為長期的經濟增長種下禍根,因此,具有后發劣勢。他認為最好的制度是英美的共和憲政體制,發展中國家必須先完成英美的共和憲政制度的模仿,等完成了制度模仿才來進行技術模仿,這樣才能避免后發劣勢。 楊中學時代因寫作“中國向何處去”被江青定為反革命分子,一生命運坎坷,身世與林一樣離奇。和楊相交將近20余載的林毅夫,對楊所謂的后發劣勢說提出了全面商榷,并指出英美的共和憲政體制,既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甚至也不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且,制度是內生的,也就是在不具備英美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因素的條件下,在中國完成和英美同樣的憲政體制。因此,林主張應該先利用技術上的后發優勢發展經濟,并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調整不適應的制度。 論爭的硝煙尚未散盡,55歲的楊就被癌癥奪命于異國。林哽咽著說,他痛失了一位真摯的朋友,自創辦留美經濟學會與楊相識時始,20年來,楊一直是他學習的榜樣,盡管近些年,他們在學術觀點上時有沖突。然而,公開的學術爭論,并未影響他們的友誼,盡管言辭難免有時相當尖刻。所謂“眾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是也。 林個人追求和而不同,也一樣期待自己領導的組織機構,將“和而不同,不同而和”視為一種需要長期堅持的品格。林主張擯棄狹隘的門戶之見,在CCER的歷史上,迄今還沒上演過黨同伐異的鬧劇。2002年夏天,香港大學教授張五常,另一個海外華人經濟學家中的大師級人物,出乎意料地受邀于CCER。演講的前一天晚上,住在釣魚臺附近的張,反復受到警示,肇始于CCER一博士后的挑戰,他在萬眾樓的演講,有可能變成一次不愉快的毀譽參半的口水戰。少數人擔心的場面并沒有出現,一場經濟學饕餮大餐,最終在友好而獨立的學術氛圍中謝幕。 林的品格中有感恩的一面,正如他常常念叨別人對他的好。回顧朗潤園的歷史,信奉君子和而不同的林說,是那些同而和,不同也和的君子們幫助了他。 天助:感謝200年來最好的時代 林篤信,個人歷史是時代歷史的一部分。他成長為經濟學家的機緣,除了自助,他助,還有天助。所謂“天助”,指的就是這個200年來最好的時代。 結束對夏令營營員的講演,已經是夜晚11時許。走在朗潤園中,林毅夫懇切地說:就CCER而言,她升騰的火焰,是眾人拾柴的結果,就個人而言,經濟學家也罷,官方智囊也罷,無不是時代使然。他感謝這個時代。 林把自己52年的人生歸納成三個階段:他多年來不肯多談的在臺灣的27年,是他人生的第一個階段;從爬上大陸海岸線到從美國學成歸來的8年,是他人生的第二個階段,他從一個臺軍上尉蟬蛻成一個經濟學人;從1988年形成了一個一以貫之的,以經濟中的要素稟賦、政府的發展戰略和企業的自生能力為分析框架的學術思想迄今,是他人生的第三個階段,這是他人生中最有價值的一個階段,是他用西方經濟學研究范式研探中國經濟現象的15年,是他以獨特的視角提出新的發展、轉型理論影響國內外學術界,并以官方或者半官方智囊身份影響中國經濟政策的15年。 林認為,是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大時代提供的素材,讓他在經濟發展理論研究中脫穎而出,成為國內外受人矚目的經濟學家,并為國內決策者所重視而躋身于高層智囊行列。近年來,中國領導人高頻率地聽取過林對經濟政策的意見。除了以中共黨外人士的身份,在2003年兩度出席溫家寶總理主持的“黨外人士經濟形勢座談會”以外,他還參加過中國最近兩任總理的專家問計會。“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林領銜的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與對策建議,也為決策層所采納。 林不愿意過多透露他為中國領導人做智囊的細節。據觀察人士的梳理,他對中國農業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殊大的影響。他在中國農業問題上的研究在國內相當權威,曾擔任發改委“十五”計劃咨詢審議委員會常務理事會成員、中國糧食經濟學會常務理事等職務。2001年圣誕節,江澤民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新階段三農問題座談會,林所作《三農問題與我國農村的未來發展》的報告很受高層看重。此前40天,江澤民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重大問題研究座談會,林出席并作了《當前農民收入問題和未來農村發展思路》的匯報。 林的同事,CCER副主任李玲博士證實,林多年對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和建議在2004年中共中央以農業為主題的“一號文件”中頗有體現。林倡導的“新農村運動”,有望影響中國農村的未來變革。 身處百年來未有之變局,他將自己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對中國時代進程的助益,理解成時代的風云際會。未來倘能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能夠保持政治穩定,并堅持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那么最遲到21世紀30年代,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得益于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國經濟研究在世界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亦將同步提高。 當一個時代的經濟奇跡在中國出現,西方經濟學大師開始頻頻造訪中國。大師紛至沓來的時刻,林和CCER充當了他們和中國經濟決策者和執行者之間的一個橋梁。1998 年夏天,馬丁.費爾丁斯坦所率的美國經濟智囊團進入朗潤園,數位中國經濟官員,和他們坐到了一起。馬丁.費爾丁斯坦,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局長,他和他的經濟學家團隊,打造了美國最大的非官方經濟政策研究機構。 經由林的努力,NBER和CCER開始了交流互訪。6年來,非但央行行長周小川等經濟官員,數度與他們展開對話,江澤民也在國家主席任上接見了馬丁.費爾丁斯坦,耐心聽取了馬氏對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看法。 盡管林的“智囊”和“橋梁”身份為他贏得了榮譽,但他似乎并不在乎,更不會自大地認為自己改變了中國經濟版圖。他對出席“中國優秀經濟學大學生夏令營”的營員們說,中國領導人并不總是聽經濟學家的。多數情況下,經濟智囊們的意見只是在與領導人所思索的問題不謀而合的時候,才會發生作用。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人不尊重專家,正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看中諾獎得主哈耶克的經濟思想,而沒有照著哈氏在信中所寫的那樣去做,政治家對經濟政策的考量比經濟學家的限制條件要多得多。林認為,中國領導人對現實情境的掌握,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他們對政策的制定和把握,總是對照現實條件的需要,而非其他。 林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表示樂觀。他堅持認為,當下中國,是一個空前的好時代,不是民運人士所說最壞的時代,甚至也不是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所說的:“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在對時代好壞的判斷中,林堅持放棄意識形態的評判標準。他認為一些經濟學家,已經從意識形態的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曾經,凡是符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經濟現象和經濟理論,都是對的,現在,凡是符合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經濟現象和理論,就是對的。經濟學家的責任是分析問題,而不應該以主義代替分析。 8月20日,林在上海“世界中國學”論壇上大膽預測:2030年左右,中國經濟規模有望趕上美國。預測經媒體報道后,引來網民反對聲一片,有的甚至是謾罵。CCER有教授為林叫屈,覺得網民們是以臆測替代評論。其實,林說的是經濟規模,而不是人民的幸福指數,因為那時候中國的人口將達到15億,再大的經濟規模,除以15億,幸福指數就可想而知了。 勿論網民,即便是經濟學界的臆測,林也不愿站出來回擊。 據稱,1990年代中后期,林提出國有企業改革“非產權中心論”。在被中央政府高度認同的同時,也遭到了部分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抨擊,認為他是討好意識形態。他的身份的特殊性,確實影響到他的行為和話語。譬如,人們從未在北京大學的官方網站上看到他在臺灣的經歷,他每每說到臺灣地區必稱“臺灣省”。 對于臆測,林只是無可奈何地一笑置之。25年過去了,他一直在被人們臆測,尤其是臺灣島上。他說,他從不否認民主制度的終極價值,可是今天的中國問題,不是簡單的民主制度設計就能了事 。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都會存在著一些經濟社會問題,但不能把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歸罪于沒有進行憲政體制改革。因此,設想一個國家、地區,先用50~100年改革憲政,然后才來發展經濟,這在實際上怎么可能呢? 林援引孔子的話說,五十以學易。最近兩年,常于不經意間背出一段《道德經》或者《金剛經》的林,一直在反思“術”和“道”之間的邏輯關系。他說,思辯“道”“術”關系,有助于他對經濟學之“體”和“用”的理解,常讓他在治學的途路中會心一笑。 問林50歲之后的追求,他說他的追求一以貫之:做個經濟學家,左手經濟政策,右手經濟理論。他最大的樂趣在于徜徉于真實世界的理論創新。從終極目標上說,他希圖以經濟學家的方式,為造就自己的大時代奉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兩個余月前,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福格爾在杭州答記者問時說,林有望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林不認為自己會獲此殊榮,但他對未來一代摘取桂冠擁有信心,這也是他為什么會操辦“中國優秀經濟學大學生夏令營”的原委所在。林對參與夏令營的營員們說,21世紀將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希望他們好生努力。他說這絕不僅僅是一個老師的勸勉,而是中國的時代走向決定的。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學人 > 林毅夫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