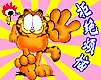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行政刑罰——行政法與刑法的銜接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09日 16:34 中評網 | |||||||||
|
一、問題的提出 行政刑罰并不意味著行政機關把握著刑罰的大權,而是指某種刑罰施予的根據來源于行政法的規(guī)定。也就是說,行政法律對違法者危害行政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達到比較嚴重程度的情形,規(guī)定了刑罰。也就是說,國家對違反行政法規(guī)范所規(guī)定的義務的人,由法院適用刑法總則的規(guī)定,依刑事訴訟程序所實施的制裁[1]。這樣,行政法與刑法就直接掛上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違法或經濟犯罪現象明顯增多。為了維護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發(fā)展,九十年代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先后制定了《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guī)定》、《關于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的犯罪的決定》《關于懲治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的犯罪的決定》《減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犯罪的決定》以及《夫于舞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等。盡管這些決定增設了刑法典原來所沒有的新罪名,如《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guī)定》增設了“欠稅罪”;《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犯罪的決定》增設了“虛報注冊資本罪”、“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虛假發(fā)行股票、公司債券罪”、“謊報財務會計報告罪”、“非法清算公司財產罪”、“提供虛假資產證明文件罪”、“擅自發(fā)行股票、公司債券罪”以及“侵占罪”等多種新罪名。但立法仍趕不上社會的實際需要,因此設立新罪名的一些建議常常見諸報端。如以1995年的《法制日報》為例,有4月20日“建議設立非法侵犯電腦網絡罪”一文,6月1日的“增設證券欺詐罪芻議”一文,6月22日的“談設立拒不償還債務罪”一文,7月27日的“應設立見危不救罪”一文,以及8月10日的“給恐嚇一個‘恐嚇’——增設“恐嚇罪”的建議”一文等。 筆者羅列上述事實只是想說明:盡管我們的立法機關為適應形勢的需要,已大大加快了立法速度,但在滿足打擊犯罪的社會需要方面,仍然有一定距離,表現出某種滯后性。在法治國家“罪刑法定”的前提下,要維護社會經濟秩序,打擊不斷出現的新的危害社會的行為,當然首推修訂刑法典的方法。但修訂刑法典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刑法典更應體現法律穩(wěn)定性的特征;而且刑法典的修改,仍然不可能將現有一切罪行都包羅進去,更何況還會有新的反社會行為的出現,僅靠修改補充刑法典是不夠的。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來修改、補充刑法典的方法。但這仍然不是非常令人滿意的方法。 第三種辦法即通過附屬刑法解決追究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的辦法。附屬刑法,從立法理論而言又稱為“散在型刑事立法方式”,指在行政法中規(guī)定刑罰。這種立法方式又可分為依附性與獨立性兩種。 我國許多行政法律、法規(guī)都在法律責任中規(guī)定了刑事責任,但這些刑法規(guī)范必須依附于刑法典才有意義,所以屬于依附性的散在立法方式[2]。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對刑法典補充作用,緩解了修改刑法典的壓力,但仍有弊端。其一是行政法中刑法規(guī)范與刑法典的規(guī)定不協(xié)調,無法在刑法典中找到相應條款,造成附屬刑事規(guī)范形同虛設;其二是行政法援引刑法條文不確切或不充足,使得有法難依。第三個弊端是行政法中的比照性刑事規(guī)范不合理,例如《野生動物保護法》第37條第2款規(guī)定:“偽造、倒賣特許獵捕證或者允許進出口證明書,情節(jié)嚴重、構成犯罪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的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任。”同樣是倒賣許可證,《煙草專賣法》第39條第2款規(guī)定:“買賣本法規(guī)定的煙草專賣生產企業(yè)許可證、煙草專賣經營許可證等許可證件和準運證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條的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任。”刑法第117條規(guī)定的是投機倒把罪,這與倒賣獵捕證等類推適用刑法第167條即妨害公文、印件、印章罪相去甚遠。 筆者以為這兩項規(guī)定有失衡之嫌,它們實際上都應比照同一刑法規(guī)范類推適用,而不應比照不同的刑法規(guī)范追究法律責任。 二、新的行政刑罰立法方式 那么,在上述三種途徑都不能充分滿足社會打擊犯罪需要的情況下,有沒有更好的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呢?辦法是有的,出路就在于建立行政刑罰制度,即在刑事立法方式上采用獨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獨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即“在經濟行政法規(guī)中設置具有獨立罪名和法定型的刑法規(guī)范”[3]的方法。這里,我們須對與此有關的一些概念如空白刑法、空白犯罪構成、空白罪狀、行政刑罰等略做概括性的說明。 所謂空白刑法,是相對于完備刑法而言的。兩者更確切的說法應是“空白刑法規(guī)范”、“完備刑法規(guī)范”。完備刑法規(guī)范是指對罪名、犯罪的構成要件、罪狀、刑罰等均予以明確規(guī)定的刑法規(guī)范。除了大多數的完備刑法規(guī)范外,還有少部分空白刑法規(guī)范。空白刑法具體表現形式有“空白犯罪構成”和“空白罪狀”。“空白犯罪構成”,指刑法條文中只規(guī)定罪名及其刑罰,而沒有規(guī)定構成要件或構成要件不完整,有待刑法的其它條款或刑法以外的其它法律——主要是行政法規(guī)定的補充來確定犯罪構成要件,所以又稱為“有待補充的犯罪構成”或“援引的犯罪構成”。如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懲治犯罪的補充規(guī)定中,有些就屬于是補充刑法犯罪構成要件的情形。行政法中也有一些法律法規(guī)屬之,如《文物保護法》第31條第2款規(guī)定:“全民所有制博物館、圖書館等單位將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贈送給非全民所有制單位或者個人的,對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的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任”;第3款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非法占有國家保護的文物的,以貪污論處;造成珍貴文物損毀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的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任”;第四款規(guī)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將收藏的國家禁止出口的珍貴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贈與給外國人的,以走私論處“;第五款規(guī)定:“文物工作人員對所管理文物監(jiān)守自盜的,依法從重處罰”。 空白罪狀即刑法條文對犯罪的罪名或犯罪構成特征難以描述,而需參照其他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確定該罪的罪狀。所以以空白罪狀又稱為“參見”罪狀。“空白罪狀”這一概念比“空白犯罪構成”概念大,它實際上涵蓋犯罪構成和罪名。我國刑法上也存在著空白罪狀,如1979年的《刑法》第 116條規(guī)定:違反海關法規(guī),進行走私,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處罰金或沒收財產。該條指明了罪名一走私罪,但犯罪構成特征沒有具體規(guī)定,如若確定犯罪構成特征,需參照海關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guī)。還有一種空白罪狀,是對犯罪的行為特征作了部分描述,如1979年《刑法》129條規(guī)定:“違反保護水產資源法規(guī),在禁漁區(qū)、禁漁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撈水產品,情節(jié)嚴重的,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該規(guī)定雖然描述了非法捕撈水產品罪的一些特征,但何謂禁漁區(qū)、禁漁期、禁用工具或方法,要參照保護水產資源方面的法律、法規(guī)。 總之。我國的空白刑法在立法上均屬于依附性散在型立法方式,行政法中的刑事法律規(guī)范均須依附于刑法典才有實際意義。因而在彌補刑法典之不足、滿足社會秩序需要方面還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采用獨立性、散在型立法方式,直接在行政法的刑事法律規(guī)范中規(guī)定罪名、法定刑,是否可取,是否可彌補現行作法的不足呢?筆者以為是完全可以的。 三、新立法方式的可行性 (一)從立法主體看,無論是通過決定來補充刑法,還是通過行政法律在其中直接規(guī)定罪名和法定刑,主體均是同一的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補充決定”與行政法律并無孰高軌低的問題。 (二)刑法與行政法銜接具有內在性質的基礎。行政處罰與刑罰都是行為人因其違法行為而對國家承擔的法律責任,都是公法上的制裁方法。因此產生出二者的共同之處: 1. 責任的基礎相同 任何違法行為,不論是直接針對自然人和法人,還是針對社會或其正式代表——國家的,都是對統(tǒng)治階級根本利益和國家確認、保護和發(fā)展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侵犯,是不能容許的。因此,“法律責任的實質是統(tǒng)治階級國家對違反法定義務、超越法定權利界限或濫用權利的違法行為所作的法律上的否定評價和譴責,……。”[4]法律責任既然是對違法行為包括犯罪行為所作的法律上的否定性評價和譴責,其存在的基礎以法律明文規(guī)定為限。刑罰是“罪刑法定”,行政處罰亦恪守類似的原則:處罰法定。 2. 施罰主體均為國家權力的擁有者 人類社會曾有過漫長的原始社會,那時一切社會沖突和糾紛都是由當事人自行解決,不存在法律責任。而當國家這個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特殊公共權力產生后,法律責任就出現了。而法律責任的認定和歸結是國家權力運行的具體體現。行政處罰與刑罰的適用過程,正是法律責任認定和歸結的過程,無疑應由形式國家權力的國家機關實施處罰。正所謂“國家追究主義”。 3. 行政處罰與刑罰都不產生責任轉移 在刑法上,“行為只有作為意志的過錯才能歸責于我”[5],所以刑罰只能針對其行為構成犯罪的人,而不能將這種責任轉移給他人。行政處罰,私不強調違法者的主觀過錯狀態(tài),都是行為后果于責任是連在一起的,也不產生責任轉移。這與民事責任不同。 4.行政處罰與刑罰在制止和預防違法行為方面的功用相同 有人認為行政處罰有預防違法的作用,著眼于未來,而刑罰是對犯罪行為的報應,一般著眼于過去[6]。筆者則以為,行政處罰的本質也是制裁,與刑罰只是在制裁的程度上有區(qū)別,應該說二者也都具有預防違法的教育性功用。 關于兩者的區(qū)別,早有學者論及,認為刑事處罰是對殺人越貨、強奸等被認為其自身帶有反社會、反道德的行為課處的,也就是說刑罰針對的是“自然犯”;而行政處罰則是針對“行政犯或法定犯”[7]。當然這種區(qū)分是按照西方自然法理論而作出的說明。在解釋傳統(tǒng)刑法未規(guī)定行政刑罰所針對的犯罪行為方面,僅有部分合理性。實際上,行政刑罰與刑罰的區(qū)別,并非主要取決于“惡”之不同,行政刑罰主要還是順應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需要,為彌補刑法不可避免的滯后性而出現的。 行政法和刑法,作為部門法,具有不同的功用和目的;但作為公法,它們又有著相同的一面:都是保護國家利益的法,也都是由國家機關作為執(zhí)法主體的法。因此,兩者不僅可以并行不悖地存在和發(fā)展,而且可以某種互相銜接的關系存在和發(fā)展。 (三)從國外情況來看,獨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各國廣泛采用的一種刑事立法方式,它能很好地銜接行政處罰和刑罰,[8]并能彌補依附性散在立法方式的上述不足。 如法國“在許多情況下,當事人不履行行政法上義務時,法律規(guī)定刑罰作為制裁,依靠當事人對刑罰的恐懼而自動履行義務。這種制裁以違反行政法義務的行為為對象,不是一般的犯罪行為,稱為行政刑罰,由刑事法院判決”。[9]在日本,行政處罰分為行政刑罰和秩序罰,因而公法責任的追究分成了三部分:一是刑罰,一是行政處罰,行政處罰中的行政刑罰實際上是處于兩者之間的位置。當然日本的行政刑罰同樣在程序上適用刑事訴訟程序,刑罰上也是適用刑法中的死刑、徒刑、監(jiān)禁、罰金等刑名。美國雖然在理論概括上無行政刑罰之名,但是實際作法早已有之。如美國1890年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普查法》等,尤其《普查法》明顯的是行政性的法律,但是其中亦規(guī)定,對官員蓄意和故意提供任何虛假的陳述或報告的,應處以2000元以下的罰金和五年以下的監(jiān)禁,對此由法院按訴訟程序追訴。德國等大陸法系國家亦有此類行政刑罰制度。 四、新立法方式的益處 我國采取這一刑事立法方式其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一)配合刑法典的修改,刑法分則中的罪名將盡量采用“敘明罪狀”,不用或少用“簡單罪狀”、籠統(tǒng)的詞匯,甚至“口袋罪”,無非是期望包羅盡可能大范圍的罪行在刑罰制裁的范圍之內。那么如果采用在行政法中直接規(guī)定罪名、法定刑的方法,則刑法典的精當才有可能。 (二)在行政法中直接規(guī)定罪名、法定刑,比起另行通過“補充決定”更及時、更直觀、更明確。因而更便于“預警”、遵守和操作。 (三)更有利于行政法與刑罰的銜接。因為“刑法在根本上與其說是一種特別法,還不如說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一般的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在社會危害性上是有差別的,但違法行為達到某種嚴重程度,則可能轉為犯罪行為。刑法中有適當的罪名、罪狀,行政法當然可以援引;但刑法如無適當罪名、罪狀,行政法直接規(guī)定罪名、罪狀、法定刑,難道不比等到問題成堆再通過“補充決定”更好?行政機關不再會因為無相應刑法規(guī)范或者相應的刑法規(guī)范無法落實,不得不“以罰代刑”或束手無策。也有利于解決行政處罰中的“軟”與“濫”的問題。解決行政處罰中的“軟”與“濫”的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建立行政刑罰制度,確實有利于克服這兩個問題。因為“軟”的問題有些是由于“以罰代刑”造成的,而“濫”的問題有些是因為缺乏程序制約而引起的。建立行政刑罰制度后,當罰則罰、當刑則刑,而當刑的部分適用嚴格的司法程序,杜絕其間產生的腐敗和不公正。 提出建立我國的行政刑罰制度,可能會有人產生疑問:國際上有“非犯罪化”主張及刑事政策,我們這樣做是否與國際流行作法背道而馳?[10] “非犯罪化”是一種刑事政策思想,其主張是“將某些被認為社會危害不大的犯罪行為排除出犯罪范疇不予刑罰處理”[11]。這種思想有其先進之處,例如提出了刑法經濟觀念,強調刑罰的使用應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了刑法手段最后性的觀念,強調刑罰的嚴厲性、強制性,非到萬不得已不動用刑法等。因而,西方一些國家對這一刑事政策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采用,將某些輕罪劃出犯罪范疇,如有必要則適用行政制裁或民事制裁。那么,這種國際潮流與建立我國行政刑罰制度的建議,在走向上是否呈兩極分化趨勢?筆者以為不是。 首先,中國和西方目前的情況不同。西方的行政處罰從來沒有發(fā)達到我國的程度,刑罰是西方國家制止違法、犯罪的主要手段。所以 19世紀末以來,西方工業(yè)國家每一項新的國家管理活動都伴隨著新的刑事內容。“非犯罪化”正是針對刑罰膨脹而提出的。而我國目前正處在建立新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各種新型犯罪“乘虛”而出,刑法典中沒有規(guī)定,而僅靠行政處罰力度又不夠,建立行政刑罰制度,絕非對刑法的盲目崇拜,而是根據我國具體情況提出的有針對性建議。 其次,制止違法、犯罪,從國家角度講,由法院實施和由行政機關實施并無大的不同。懲戒違法不僅是法院的事,也是行政機關的事,反之亦然。關鍵是何種違法行為歸法院管,何種違法歸行政機關懲戒。在“非犯罪化”思想影響下,許多國家將墮胎、同性戀等排除在犯罪之外,將違警罪非犯罪化,某些原來刑法中既可以判刑又可罰金的行為,改由行政機關罰款處理[12]。而我國建立行政刑罰制度,將原屬行政處罰的較嚴重的違法行為歸由人民法院審判,使限制人身自由期限甚至長于刑罰的行政處罰措施、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上千萬元的行政罰沒,最終溶于行政刑罰制度中。誰能說我國與國際趨勢背道而馳呢? 當然我國要建立行政刑罰制度仍可從“非犯罪化”思想中吸取我們所需要、值得借鑒的養(yǎng)份。例如實施“非犯罪化”的標準之一是“無被害人”說。諸如賭博、同性戀、吸食毒品、色情書畫等行為屬無被害人的犯罪或自愿被害人犯罪,由于不涉及他人,可適用“非犯罪化”。我們設定行政刑罰也可利用這一標準。掌握內容當然可以根據我國國情有所不同,如對許多經濟活動,像違章占地、設攤等行為,雖然對公共利益有所侵害,但由于沒有被害人,可考慮僅以行政處罰,而不納人行政刑罰范圍。“非犯罪化”的其他觀念,如已提到的刑法經濟觀念和刑法手段最后性的觀念,都可以在設定行政刑罰時,作為劃分行政處罰與行政刑罰的標準加以借鑒。(劉莘) 張明楷“行政刑罰辨析”,《中國社會科學》95年第三期,P94-117; 盧建平“論行政刑罰的性質”,浙江大學學報93年第三期。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學人 > 劉莘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