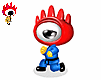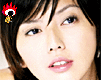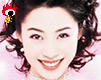| 董輔礽與一個時代的背影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04日 07:37 21世紀經濟報道 | |||||||||
|
本報記者 吳銘 廣州報道 這是一個令人感傷的季節。中年一代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英年早逝之后不久,老一輩經濟學家董輔礽教授也揮手向“這個激動人心的時代”告別。 北京時間7月30日下午3時03分,董輔礽教授因患癌癥醫治無效在美國杜克大學醫療
二三十年的時光,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長程發展而言,幾如白駒過隙,池水微瀾,然而對于那些以各種方式各種姿態參與了這個民族和國家在“文革”后的一段轉折期的人們而言,卻意味著畢生心血的傾注。這個被命名為“改革開放時代”的轉軌期看起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這個轉折期最初的見證者、論證者和推動者卻開始花果凋零了。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年代,經濟學家們主動或被動地站到了這個時代的知識場域的中心地帶,成為社會、媒體乃至政府關注的一個中心。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就是在經濟學家們的辯論、參謀和解釋中展開的。董輔礽是其中一位聲名卓著、成就斐然的參與者。他的辭世,讓人們逐漸看到一個時代的背影。 一個時代的合法性論證 從一個時代轉折到另一個時代,不會沒有任何積累就隨機變化,一蹴而就。董輔礽以及一大批從三十年中國國家建設的曲折中走過來的知識分子,就是時代的轉折從醞釀到拓展的重要社會積累。他們敏銳地感知和把握了時代變化的契機,在混沌中闖蕩出一條此后彰顯于世的理論道路。 1978年9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不久,大局甫定乍暖還寒,董輔礽便率先提出了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革的問題。那是在中國社科院的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上,董輔礽提出了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兩個分離”,即改革國家所有制,實現政企分離;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實現政社分離。這番“離經叛道”的陳詞震驚了當時幾乎所有在場的人。無論他的學生們還是學界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追懷董輔礽的思想貢獻,都首先提起他在所有制改革上的大膽開拓。 在以預見能力為一大成就指標的經濟學界,這種大膽和對此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判斷,無疑也奠定了董輔礽此后在以改革為業的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地位。 1980年,董輔礽提出取消指令性計劃,反對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1981年,他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征求意見時,建議把“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改為“發揮市場調節的積極作用”。后來這個看法被定為“南斯拉夫觀點”而受到批判。那個時代即使有見識要發表,也需要以勇氣做基礎。 董輔礽何以在轉軌期之初就在所有制改革和市場化方面有如此堅定的見解?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劉紀鵬教授認為,董輔礽那一代經濟學家深切地看到了計劃體制的弊病,很自然地就要去尋找新的道路。青年經濟學家巴曙松與董輔礽一樣曾就讀于經濟學界泰斗張培剛門下。在巴曙松看來,盡管董輔礽曾于1950年代留學蘇聯國立經濟學院并獲得副博士學位,接受了正統的蘇聯模式經濟學的教育,但他在武漢大學學習以及留校任教的時候,張培剛正好與幾位留美學生從美國回到武漢大學任教。張培剛是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當時在西方經濟學界已有不小的影響,回國后教的也全部是西方經濟學。從這批老師那里,董輔礽得到了西方經濟學的系統訓練。在此期間,他也曾赴英國留學,對西方經濟發展有所了解。董輔礽很早便對所有制改革與市場化改革有所洞見,這一知識積累極為重要;十年“文革”并沒有截斷這一知識傳承,而后才能夠由對時局的敏銳感知激發出這些先見之明。 董輔礽的多位學生都說,他對自己的這些先見之明看得很平淡,因為他就是這么看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的。今年4月25日,在美治病的董輔礽寫了后來發表于《金融時報》和《經濟界》的《守身為大》一文,認為“守身”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況會有不同的內涵,在改革開放的曲折過程中,改革與保守或反對改革的斗爭異常激烈,每前進一步都有斗爭,有時甚至轉變成政治斗爭。面對這種斗爭,理論工作者是否敢于堅持真理,堅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堅持學術節操的考驗。 董輔礽所要堅持的“真理”,就是要從中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系中開出一個市場經濟體制來。如何開出一個市場國家來,這也是董輔礽和一大批年長的經濟學家如于光遠、蔣一葦、厲以寧、吳敬鏈等等試圖回答的中心問題。青年經濟學家趙曉認為,盡管他們后來在諸如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等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也小有分歧,但在這一代經濟學家群體里,對大方向的共識卻未曾破裂,“在稀缺的時間與生命中,經濟學家已經克盡全力為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并且將在年輕一代經濟學者中薪火相傳。 董輔礽這一代建國前后成長起來而又在改革開放之初站在經濟學界主流與前沿的經濟學家最為重要的理論工作,也就在于論證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合法性。這一論證既包括為具體的轉軌措施出謀劃策,漸次改變中國經濟體制的法則,也包括為漸次轉軌的政策表述提供智力支援,在體制法則嬗變的同時論證經濟體制轉型對于中國國家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合法性,也因此論證改革開放時代的合法性。 如果說董輔礽對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方向早有定見,那么他在20余年的改革過程中保持了充分的理論張力。就所有制的論述而言,從1979年首次區分公有制和公有制實現形式,到1985年的“董氏八寶飯理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的混合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再到1997年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理論,分為共同所有制和公眾所有制,這一層層演變完整地呈現了在社會主義體系內進行市場改革的合法性論證的過程。 而這種“特洛伊木馬”的策略,也是董輔礽這一代從建國初期走過來的經濟學家所特有的論證方式。在下一代或者更年輕一代的經濟學家那里,已經是在一個全新而沒有太多猶豫的基礎上進行論證了。這個經濟學的新時代的到來,正是董輔礽這一代人的戰利品。 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前身后事 盡管國家政經發展大勢與智囊型知識分子包括參知政事的經濟學家之間的關系很難說清道明,盡管政治家們究竟更在乎社會階層的升沉與民眾的意志,還是更在乎理論家的論述,也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但人們還是愿意在國家制度轉型與經濟學家的勞作之間建立密切的聯系。至少作為社會公眾,他們最早感知和說出了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向和方向,而他們的言說也足以代表一種力量強勁的社會意見,更何況他們的意見曾經被國家決策者所采納。于是一般著名的經濟學家都走出了專業領域,成為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成為社會、媒體乃至政府關注的一個中心。 董輔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被公眾和媒體所悼念的。作為在20多年改革開放過程中功績最為顯著的經濟學科中的代表人物,門生、媒體和公眾對董輔礽的追思,顯示重量級的經濟學家享有著其他專業的公共知識分子難以企及的哀榮。在此之前不久,公眾、媒體和門生剛用類似的方式送別了楊小凱。 一位著文悼念董輔礽的經濟學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董輔礽和楊小凱是兩類不同的經濟學家。董輔礽的貢獻不僅是學術的,而且對國家政策方針的制定貢獻良多,這是兩人無法比較的地方;楊小凱的活動則只在于思想學術領域以及與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對話。 換一種說法就是,盡管董輔礽和楊小凱在許多問題上都存在共識,都是經濟學專業背景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但前者更多在體制內,后者在體制外,是“自由漂泊”的知識分子。董輔礽從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時間里,一直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從1998年開始轉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在此期間,董輔礽主持過《期貨交易法》的起草,參與過《證券法》等經濟法律的審議工作。董輔礽的學生葉輔靖回憶,在人大任職期間,他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建言頗多,并多富爍見。這種身份的差異,自然影響到這兩類經濟學家對中國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的合法性的論證,以及各自論證的實際效應。 作為兩類公共知識分子的典型,董輔礽和楊小凱的社會影響模式大不相同。一位學者在接受采訪時說,楊小凱對經濟學后學和媒體知識分子的影響在于其理論的批判魅力,而董輔礽的理論魅力則在于其切入國家制度發展的影響力和解釋力。體制外的學者以其高蹈贏來掌聲,體制內的學者則盡管頗有影響力但也容易因這種影響牽涉利益而引來毀譽(例如股市大辯論之于董輔礽)。他們都有論敵,但學術論敵在其身后一般不再提論戰而惺惺相惜,這時后者由于牽涉利益矛盾而使部分公眾成為論敵,容易在網絡等公共論壇帶來多音喧嘩。 這兩類公共知識分子不同的社會影響模式還在于弟子門生。傳統科考時代的社會階層變動,世家與門生是相當重要的決定因素;在當代市場社會,家族承繼和教育同樣是社會升沉的重要影響因素。經濟學家的公共性和成就在自身的學術成就之外,還可以通過學生的學術傳承和社會活動體現出來。董輔礽指導的學生中,多有經濟社會的領導與骨干,其中有的官至副省長,有的是大型企業的總裁,有的是資本市場著名的弄潮兒。從目前各種媒體發表的董門弟子或關系相近的人士悼念師長的文章來看,多有感念董輔礽教授相與提攜的事跡。這樣先生的學術見解通過弟子群體的努力,可以影響及于后世。而楊小凱則因為在體制外而少有弟子能夠直接影響國家政經運作,其影響更多地通過學說而綿延。 而這些影響力,正是公共知識分子希望在他們念茲在茲的改革事業中看到的。 我們時代的難題 董輔礽逝世的消息最早在主流網站上發布,曾引來眾多網友跟帖懷念,中間對董輔礽的生平事跡也有所爭辯。有經濟學家認為,其實這對于董輔礽先生來說乃是平常之事。他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文集《用辨證的眼光看市場經濟》的封面便有引言說,“市場經濟本身就充滿矛盾,它的運行和發展處處都遵循著辯證法的規則,如不用辨證的眼光來看待,人們很容易出現認識的偏差,只看到一面,看不到另一面。”有矛盾便會有爭辯。 董輔礽最后幾年時間對資本市場的發展關注尤多,這多少與2001年那場關于股市的大辯論有關系。這也是人們在其身后仍然有所爭論的話頭。在吳敬鏈等學者發表對中國股市的嚴厲批評(如“賭場論”)之后,董輔礽與厲以寧、蕭灼基、吳曉求、韓志國舉行記者“懇談會”,全面反擊吳敬璉,并稱“現在股市已經到了很危急的關頭”。現在看來,這場爭論的意義不僅在于求證中國股市究竟是否是賭場,是否應該推倒重來等等問題,而且在于推動市場化進程的經濟學家群體內部的分歧和他們所體驗到的市場社會中的“矛盾”。其中的一個矛盾就是“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董輔礽等認為應該公平對待投資者,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而論戰的另一方面認為認清股市的真相,才能真正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問題是什么是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據葉輔靖解釋,董輔礽認為“不存在投資者利益之外的上市公司利益”,不能把上市公司的利益同投資者的利益對立起來,公司是投資者的公司。不過“矛盾”的地方在于這只是上市公司的宗旨,而現實運作中確有不少公司把公司的利益和投資者的利益對立起來,通過損害投資者來實現公司的利益。這個理想、原則和現實的矛盾,意味著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并不總是和公司的利益相等同。這樣問題也就變得復雜起來。 而在其他的場合,這種市場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以及對這類矛盾的體察和辨析,一直為董輔礽所重視。他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論述中,一直對“社會公平”、“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等議題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據他的學生楊再平回憶,董輔礽在學術研究上的一大遺愿就是將學術思想系統化為《追求公平與效率的統一》。而這其中要處理的一個關鍵“矛盾”就是,理想的市場發展固然可以達至社會公平與均衡,但現實的市場競爭則往往為不公平的力量和追求者所扭曲。理想和現實的矛盾使問題變得復雜難解。這一矛盾在股市中的體現就是,雖然市場按原則上應該保護中小投資者,但現實卻往往相反。 記者向劉紀鵬請教董輔礽何以保持強烈的有關社會公平的問題意識,是否因為他曾經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高級顧問和成員參加1992年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大會、1995年哥本哈根的社會發展大會的經歷,使他對社會均衡發展問題有切身的感悟,還是因為他仍然保留有年輕時投身地下黨工作的社會主義追求。劉紀鵬認為這其實也是董老這一代學者的特點,他們的確對社會公平有一種近乎本能的關注。據葉輔靖回憶,董輔礽在1998年抗洪最緊張的時候,看到圍困在洪水中的農民,總是念叨該怎么辦。 董輔礽為一系列市場社會的“矛盾”開出的辨證藥方是進一步的市場化,通過發展市場來解決這些問題,也即是辨證地看市場,相信市場的作用。但問題是,從董輔礽的大量辨析中可以看出,市場的破壞力量不僅從市場反對者那里來,而且從市場內部產生。就像有些公司會通過損害投資者利益來實現自己的利益一樣。 市場化進程似乎已經一往不復,而我們這個時代的難題也越發清楚起來。市場的敵人正從它的內部產生,歷史并未終結。這也是董輔礽先生留給下一代經濟學家乃至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人的問題。 分子希望在他們念茲在茲的改革)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學人 > 懷念董輔礽 > 正文 |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