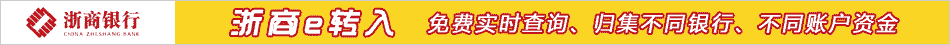任志強王巍劉曉光談企業家啟蒙(實錄)
 “中國金融博物館讀書會(第二十四期)”于2012年12月7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讀書會現場。(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張健 攝)
“中國金融博物館讀書會(第二十四期)”于2012年12月7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讀書會現場。(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張健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金融博物館讀書會(第二十四期)”于2012年12月7日在北京舉行。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任志強,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北京首都創業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劉曉光[微博]談企業家啟蒙。
以下為全部實錄:
劉曉光:今天我做主持人,任志強和王巍做主講人。下面我們邀請主講嘉賓上臺。
首先是華遠地產的董事長,中國金融博物館的主席任志強。
下一位是中國金融博物館的理事長王巍。
大家好,我叫劉曉光,在去年的7月10號,我們三個人做了一次讀書會的首場對話。當時王巍是主持人,我們兩個是嘉賓。從去年的7月10號到今天,有王巍,任志強,于桐我們四個人在意大利參觀的時候做了一個商量,商量這個讀書會的內容和它的目標。后來我們定名為閱讀豐富人生。
在這一年多里一共有52位企業家,學者和官員參加了這個會,他們從自己的視角出發,講影響他們人生脈絡的圖書,一共有12000位書友到達會場,報名超過77000人,微博粉絲超過10萬人。
今天我們做讀書會這樣一個活動,大概用一個小時20分鐘,主要他們倆講我來主持,再留30分鐘大家來提問,我希望大家把問題準備得精彩一點,以顯示我們在座的水平。
讀書會的目的,我們在這一年來概括總結一下,應該是折射人生,一代人的成長,應該是社會的影響,正能量的影響,這里面很多精彩的內容。
我問的第一個問題,什么是啟蒙?為什么要專注社會啟蒙?任志強你來說。
任志強:什么是啟蒙,沒有人知道什么是啟蒙,但是知道把一盆水攪渾了就是啟蒙,如果一盆水什么都不產生,這個水就會臭,把它攪混了,變成了活水,這個水才生命力。
我們覺得太沉悶了,所以我們發起了讀書會,大家來談一談通過讀書怎么來體會社會。我們在專制和壟斷的條件下,會把思想也變得單一。但是這個世界是多元化的,當思想只有一種的時候是進步不了,當思想是多元化的時候才能促進,才能進步。如果是一潭死水,沒有思想的火花,沒有思想的碰撞,這潭死水就不會促進中國的進步。
因此我們在20多期的讀書會中間,既有學者,有官員,有經濟學家,有企業家,有各種各樣的人共同來參與,目的就是從用不同的視角讓大家知道歷史,知道現在,通過對比知道過去,也知道我們可能的未來。書院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建立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們看《1942》,其實和《1962》也差不多。要用這種方法學會獨立思考,要真正的讀一些書,通過書中記錄的各種各樣的不同意見,來反思一下我們現在的沉睡。
我個人覺得,我們用這樣一個大標題,閱讀豐富人生,就是要啟蒙我們現在社會中的所有人不要再沉睡了,該動腦筋想想,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么,最后爭取到什么。
所以在我們讀書會中有的人提出,要知道你從哪來,要到哪去,我們要解決恰恰是這樣一個問題。但是我們讀書會秉承的不是要灌輸你什么思想,而是用各種各樣的多元思想,告訴大家你們自己去判斷,自己去思想,自己去尋找應該走的路。這可能就是我們想通過讀書會用閱讀豐富人生這樣一個命題來告訴大家的,我個人覺得這就是在做中國的啟蒙。
劉曉光:什么叫攪和,啟蒙就是啟蒙。
任志強:在我們讀書會有一個說法,喚醒醒著的人,你不攪和他還睡著。
劉曉光:你就是用攪和來代表啟蒙。任志強講的是思想高度的飛翔,是一種啟蒙過程中提升人的人生價值,同時不同的歷史階段,可能也是有不同的啟蒙的含義。比如說早期的科學民主,中國富強,現代思想觀念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這都是不同歷史階段的啟蒙概念。
王巍你來講一講,為什么辦這個書院,書院建立對啟蒙意味著什么?
王巍:辦書院是對老任的推動,啟蒙者首先自己啟蒙,由于書院出來一年半的時間,任志強從一個地產商,現在變成公眾認可的公知。我首先是解決自己的腦殘,你過去從小長大受的是主流教育,是有思維方法和歷史觀。但后來跟國際接軌,特別跟江湖人打交道的時候,你突然發現你過去的教育可能是錯誤的,是框架里的思維方式,全國步調一致,這是一個非常高度統一的思維模式,這是錯的。
我當時在美國,有一次在圖書館,當時87年,88年,兩個臺灣教授聊天,我和他們正好談得不錯,他提出大陸搞點共同化,于是我就談中國歷史,當時我感覺我對中國歷史非常熟悉,所以從鴉片戰爭,洋務運動,土地戰爭,抗日戰爭,四大戰役等等,講了一個多小時,非常興奮,自己感覺到給臺灣同胞進行一次歷史教育。
當時這兩個臺灣人看了半天,他說兄弟,我看你只補了一部土匪史,這對我沖擊非常大。當然成了是革命領袖,失敗了就是土匪。終于發現我們很多很多知識都不知道,觀念都是錯,所以我說我是腦殘。
好在我們還有一種信念,就是不斷自我修復,不斷地修復腦殘,在這個過程當中,自己修復自己,同時又通過自己努力,把這樣一個真實情節把各種方式教育大家,傳遞給大家,這就是一種啟蒙。絕大多數人都不是文盲,但大部分人都是金融文盲。所以我從金融角度提出,我們搞一個書院,整個啟蒙完全就不是金融了,它變成一個社會、歷史、人生方方面面的互動,我們參與當中更多是自己獲得了教育。
劉曉光:你辦書院,包括任志強,是為了啟蒙。
王巍:首先自己,當然你也可以招來一堆人,很多老部長,很多同志,很多人身居要位,他說你完全顛覆了我們的觀點,因為他們沒有時間上網,上微博,所有都是看領導的眼神,他說什么都對,他已經是真正腦殘了。
劉曉光:有人說會不會像任志強這樣的,王巍這樣的,你們有什么資格啟蒙社會?
王巍:連任志強這樣的都到今天了。
劉曉光:任志強到現在有什么變化?
王巍:我認識他30年,剛認識他時,他高高在上,根本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眼睛是往上看的,當時非常居高臨下的。他跟我談寧波項目的時候才跟我打電話,架式明顯不一樣了。
這幾年明顯地感覺到,他過去是非常軸,以自我為中心,最近喜歡把自己的想法推向周邊,不管聽不聽都推,不管是精華還是垃圾都推。上了微博以后,他應該說表面上是很嚴厲的油煙不進,但實際上是好好學習。原來寫的詩,寫的東西是不堪入目,感覺他差很多。但現在寫的詩特別好,明顯給女粉絲寫的留情萬種。
劉曉光:任志強是從狂野到軸,到提高自己,到會寫詩等等等等,任志強你自己說說,你有什么變化?
任志強:我沒什么變化,我覺得我原來就這樣,就是個努力好學,原來可能學得不夠好,再努力點就學得好點了。但是它就是這么個過程,誰天生下來就會走就會跑,你不也得摔兩個跟頭。但如果說當爺爺知道小孩沒生出來以前的事的時候,這個小孩并不知道。當父親的知道孩子生下來以后的事情的時候,也可能不知道這個孩子長大了以后的事情。你不能用一個階段的情況去看這個問題,要把時間拉長以后去討論這個問題。
我沒看見有誰買我的書,外頭書大家好像不太愿意看,主要是因為王巍寫的序不好,但是我的書寫得很好。我嚴格說起來,是因為上了王巍的當,有一天我在去天津的火車上發了個微博,說我要去天津辦個什么事,他比較壞,他就給我發了信息說,說等你辦完事以后到我的金融博物館去開堂課,于是我就說行。
大家都說微博改變了任志強的性格,我個人覺得我沒什么變化,只是大家有變化。因為在過去的傳說中,都是看媒體報道什么東西,如果媒體報道一個什么東西,就給你塑造一個什么形象,如果媒體說你好,這個人不錯,如果媒體說你壞的時候,就用惡劣的手段扭曲你,于是你出來的形象就是扭曲的形象。
如果是20歲的人是最容易改變的,30歲的時候也可能會改變一些,都6、70歲老頭子了,還改變什么。基本上應該說是當社會處于一個公平和透明的情況下的時候,人們會通過信息的完全對稱了解更真實的情況。所以我們的讀書會的目的,就是想通過各種各樣的書,讓大家從一個側面到另外一個側面,多向去進行比較,而不是單向地說我只看一面,那你完了。
就像我們在文革以前,改革開放以前,大家都知道一個非常偉大的口號叫我們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民,那時候因為我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樣,以為我們是最幸福的。等大門打開以后,發現外面的世界比我們這里更精彩,而且這三分之二的人比我們活得更好。
所以當信息完全透明的時候,人們的思想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因此啟蒙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讓信息完全充分地透明化,讓你知道這邊的東西,那邊的東西,你才能獨立思考,去分析,到底應該信哪邊,什么樣才是最全面。
劉曉光:微博是一個大學校,微博本身你向其他人學習很多東西。你說你沒變化,難道別人的知識對你就沒有用嗎?
任志強:不對,你理解錯了。我善于學習沒變。所以我說從不會走到學會走,到學會跑是個過程,你要拉長了看。但是你能不能學會走,能不能學會跑,要有一個頑強的學習的精神才行。不管歲數多大,繼續往前走,繼續讀書,繼續學習的精神沒變。在你這個精神不變的情況下,你一定會有進步,你要不學就不會有進步。
王巍:老任的學習能力特別強,我認識他30年,原來特別聰明。原來見到雞下蛋都臉紅的人,今天什么人,變化太大了。
劉曉光:我認識任志強是1984年,85年的時候,那時候任志強穿一雙解放鞋,背一個小軍包,那時候很有激情這么一個人。但是后來我們打交道比較多,他來做地產,我來批項目。有一次任志強找我,我說你先出去等會兒,一等四個小時,我給忘了。那時候任志強比現在謙虛,那時候任志強比現在更加熱心,當時我在政府,沒有計算機,買計算機,他就得去買去,實際上他還是有變化的。
任志強:這一屆黨的領導可要求反貪污腐敗,劉曉光是特權的典型,作為政府官員老欺負我們企業家。
王巍:我們回到啟蒙,一方面我們看啟蒙,看起來好像單方向。我們從小接受教育,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勤勞勇敢的民族,中華民族的文明是燦爛的,什么時候從燦爛的文明,領先的文明變成愚昧了。我們一百年前是亞洲最先進的一個現代國家,辛亥革命那時候,中國有那么多的知識分子,民族英雄這么多,怎么突然就走到一個今天看來還需要重新啟蒙,這是大問題,因此啟蒙不是單方向的,我們要了解什么樣的因素導致社會走向愚昧,走向啟蒙的另一個方向,這是更重要的。而這些東西不單單是外面的制度的變化,而是每個人內心當中如何真正啟蒙。
劉曉光:可不可以說那是一種負能量。
王巍:我們如何來發現社會因素,制度性因素,使得我們將來不再重演悲劇,那都是負力量,所以啟蒙是雙方向的,一方面找到面向未來,另一方面如何來阻止惡的發生。這是一個更加嚴肅的問題。
當然在書院這樣的活動中,我們更多的是推動大家來互相交流,互相啟發,但是它不是給出結論的,不是搞意識形態的宣傳,而是要去體會,真正體現個人的自主選擇,讀好書,學高品位的人,慢慢給我們的社會更多的價值觀。
中國企業過去30年,叫野蠻生長,因為我們太窮了,因此我們要革命,這時候是為達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相當的野蠻生長,盡管我們成為大國了。但是今后的30年,10年,中國的企業家是不是應該有些價值觀,這種增長要文明起來。我覺得這是書院的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劉曉光:志強你來回答這個問題,你來評評他。王巍從一個商人到推動民間協會的建立,再到建立金融博物館,他有什么變化?
任志強:他是想當官沒當成,不得不下海了。你是當官當不下去了,不得不下海。
他很牛,海龜,搞了一大堆名堂,最后發現不如我們做實業的更有成就。所以發現需要做一些公益的事情,來為這個社會尋找另外一條恢復民眾權利的路。他一開始就是投機性的,搞基金那時候也是投機性的。
中國在那個時候很多投機性,因為我們是從一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大家都是實驗性的,投機性的多,摸著石頭過河就是讓你投機,不投機怎么能摸著石頭。
王巍:老任說的是他的心路歷程,給社會造了這么多房子,很沒品位,他努力進取,推廣讀書。
劉曉光:有人說你一天晚上一本600多頁的書,厚厚的書就讀下來。
任志強:我一天晚上讀6萬字。
劉曉光:任志強和王巍,這6萬字也好,600頁也好,你們看得懂嗎?
任志強:6萬字在某些人眼里,覺得6萬字是很大很大的一個數。慢慢的一頁人民日報你們知道是多少字嗎?一萬字。你就看6萬版的人民日報你覺得多嗎?你一定不會覺得多。你說6版人民日報你一天讀不下來,不可能吧?我說平均的概念是什么,也可能今天讀得多一些,明天讀得少一些。
比如坐飛機去海南一趟得三個多小時,飛機上你可看的不只6頁人民日報,你可能看20頁人民日報都能看完。但是看書和看人民日報不一樣,看書有個連貫性。
劉曉光:你看6萬字,真看懂了嗎?
任志強:6萬字有時候不行,少了。比如說我看的《1949》,那本書我一晚上就看完了。大概30萬字。
劉曉光:你怎么概括它?
任志強:我當時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把我們過去心中的神像全都打翻。列寧這本書讀了7遍,我們有時候翻譯成怎么辦,有的人翻譯成為什么,這本書我們小時候可能都讀過。但是列寧從那時候開始的神像都被打倒了。高爾基,包括《母親》,《大學》等等,發現不是那么回事,是另外一個人。包括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一直到后來的革命,到斯大林時代,所有的神像都被打亂了。你只看到那些東西,你沒有看到中國戰場上那個形象。
劉曉光:你們倆讀書是不是也是老老實實地讀,不是只看前面,中間和結尾。
王巍:那本書我是一晚上看完了,但是我真認真看,一也就是大概四分之一比較細地看的,那本書非常好,我認為可以更濃縮,精華,因為是女性做的,太細膩。是在俄羅斯農奴的專制制度下,怎么從兩個輪子當中拐出這個道路,它是俄羅斯知識分子思想裂變的過程。
我小時候沒有書,自己看把雜志,這個同志借本雜志,那個借本雜志,基本上就把它一次看完,過去一本好書只給你4個小時,輪著走,這時候你就會非常迅速看書。看書不是眼光這么來回掃,眼角甩掉兩個角,一下就下來了,這是當時的訓練。我斜著看。
劉曉光:看完第一個字看最后一個字,這頁就翻過去了。你們都是想證明自己特聰明,跟別人不一樣,可以對角看。
任志強:因為我堅持了快2、30年,一天不能少于6萬字,我覺得我是屬于比較笨的。
劉曉光:每天都看?
任志強:對。
劉曉光:大家鼓掌。
任志強:我發現很多人讀書比我速度快得多得多。
劉曉光:但是任志強有一個知識咱們學不了,有一天我去他的辦公室,他在寫一篇關于地產的論文,大概也就是4個小時左右,他寫了一萬多字,這個我覺得跟他平時的刻苦,他的積累是相關的。
王巍:主要是有激情,有激情寫情書也能寫6萬字。
劉曉光:你們辦書院,大量的讀書也好,在這個歷史階段,閱讀給我們的是什么?閱讀給你們的是什么?
任志強:閱讀給我們的是快樂。
劉曉光:還有呢?
任志強:知識、經驗、曙光、未來。
王巍:對我來說讀書是一個消遣,因為人生很多的東西都是無效的,不一定讀書有意義,要獲得太多東西。你總得干點事,有人玩兒蛐蛐兒,有人打麻將,有人讀書,不一定讀書一定比麻將高多少。
劉曉光:歷史上叫書中自由黃金屋的概念還是正確的。
我再接著問,在讀的過程中,很多人反應,也看了很多書,但是記不住,或者抓不住重點,或者在實踐中沒有結合起來。就是想問問你們倆讀書的方法,讀書跟實踐,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怎么結合起來。
任志強:王巍看完第一個字,看最后一個字,我沒他那個本事,我一般的都是至少你要把前面的序很好地看了。通常一本書的序,會把的本書里很重要的東西說清楚。然后你根據他這個序提出的幾個部分,你可能需要把書里每一部分的中心找出來。比如說一本書翻開目錄,可能分四個大問題,每個問題主要講什么,可能你的速度就會快。
王巍:我是看書絕不看序,因為你一旦看序,就被寫序的人牽著走。所以每個人的方法是不一樣。就和看一個人一樣,如果這個人20年來一次,你看三天,仔細觀察他,20年再來絕對會忘掉。這個人天天在門前晃一次,晃兩年你絕對記住他。我們讀書也是一樣,慢慢積累。
劉曉光:怎么把書本和實踐結合起來?
王巍:看書是愉快,為什么結合。讀書并不是為了用,讀書是為了消遣。
任志強:我比較笨,我一般一本書從頭讀到尾。
劉曉光:很多人給你們兩個送書,你們倆還老推薦書,你憑什么來推薦書?
任志強:我這個口袋是金融企業協會,我們每次去都拿一口袋的書,因為金融企業里成為了一個讀書的圈子,每個人每次都要推薦一本兩本,這樣的話每個月聚會一次的時候,這么多人都推薦出來書就變成幾十本,或十幾本。
當這個圈子形成以后,你就可以節約大量的時間,有些書可能就不看了,因為被推薦出來的書,可能更能代表這個時代,或者是當時的一些情況。
我確實也帶了幾本書,這幾本書主要推薦的是最新出版的書。以前的書,過去很多書都推薦過了。一本袁偉石先生,一本是馬勇先生的《清亡啟示錄》,這兩個人在我們讀書會坐過一期,涉及到辛亥革命傳統歷史的研究,馬先生和沈教授還做過一次讀書會的嘉賓。在中國的近代史里面,我覺得這兩本書基本上把很重要的問題都說清楚了。
我另外推薦的幾本書,一本叫《讀書毀了我》。據說有兩本,同一個名字,一本是外國人寫的,一本是王強寫的。看了這個書名覺得,是不是他告訴大家別讀書,其實這個王強是個書癡,他用了一些短文,說的這些書中的事,常常是他花了很長時間,看了很多書,然后才寫了一個很短的文。比如我們常常說,任志強就是個憤青,同樣在這本書里,他說魯迅經常把中國的最貧窮的和最腐敗的一面告訴大家,說他詆毀人民。但是書中反映的一面,恰恰是他愛人民。所以這個書值得大家看一看。當然它還說了很多其他的東西。
一本是《民主的限制》。它從另外一個角度討論民主,民主有不同的定義,有的人只從單方面去考慮,就是選舉權的問題,除了選舉權之外,民主還有許多其他的內容。所以廣義的民主和狹義的民主,兩者之間是有爭論的。他對比了三種,四種對于民主的認識來談了一個基礎觀點,我覺得和現在我們大家所追求民主的東西,是有值得一提的。
另外一本紅皮的,書名叫《歡喜》,其實說的都是不歡喜的東西,就是憤青的事的東西,他在指責我們現在社會上的各種抱怨,我們在微博上,和年輕人交流的時候,發現很多人有一肚子的抱怨,埋怨社會,埋怨不公平,這個書恰恰是把抱怨這種病毒做了一種分析,認為最不應該有的就是抱怨,而抱怨通過各種分析告訴你,這種抱怨是表現了這樣一種心態,那種抱怨是表現那種心態,如果我們都換一種心態的話,也許就能尋找到自己應該走的一條路。
這幾本書里有好幾本是中信的,恰恰是因為中信出版社知道我們喜歡讀書以后,每個禮拜就給我寄好幾本,我翻一翻有的書就扔一邊了,包括立志的有些書還是不看的。我們在書店里發現賣書的時候,立志的書可能是銷量最大的,特別是80后,90后,總是希望看立志的書,有些人物傳記涉及到立志的值得一看。如果看一些我們說的這些書,可能你通過了解歷史,了解社會,它同樣在其中代表了,反映了一些人物情況,那時候的立志可能是最好的。
我們過去說胡雪巖和曾國藩,胡雪巖可以不看,曾國藩不可以不看。很多人都想創業,想怎么發財,但是你要看曾國藩你發現曾國藩的書里恰恰是精品。
劉曉光:很多人送你書,特別出版社,他想讓你推薦。
任志強:他們沒有說讓我推薦。
劉曉光:也沒有金錢的關系?
任志強:兩種概念,一個是中信銀行和中信出版社中間有一個優質客戶的關系,按優質客戶就給你送。我想在座的在中信銀行辦的銀行卡,進入他那個級別都會給你送書。
我是因為我的幾本書,有幾本是中信出版社出的,你記錄在案了,他就把新書給你送書,我享受的是作者被送書的待遇。我推薦的不是他送給我的書都推薦,我是選擇我認為好的書才推薦。
劉曉光:王巍說說,你在推薦的時候,主要推薦哪一類書?
王巍:我不是優質客戶,老任得到書我也得到了,也是中信直接送的,包括機械工業出版社等等也經常送一些書。我個人很少推薦書,但是我是知道,如果這個讀書人非常認真,很注重自己的名譽,他會很認真推薦。所以為什么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邀請嘉賓推薦書,因為他要為自己的名譽負責,所有這些書都集中在一個微博上,叫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里面,現在超過十萬粉絲了。
劉曉光:你們書院應該有商業價值了。所以我要警告你們倆,不要隨便推薦書,推薦的時候,就應該是確實是好書,有意義的書,這你們兩個同意嗎?
任志強:你沒找到我們推薦的書是不好的書吧。我們要對我們的書院負責任,我們不會瞎推薦書的。
劉曉光:這就好,為了你不會瞎推薦書,為了這里面沒有金錢的利益,大家鼓掌。
時間過得很快,下一個問題我想問你們倆,現在中國建立一些公益平臺很多,但是在社會中有些不理解,也有一些負面的聲音,詆毀的聲音,本來是好事,面對這樣的質疑聲,你們怎么理解,怎么看?
王巍: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是這樣,你做一個事情大家不理解也很正常,因為不可能大家都來理解,因為立場觀點都不一樣,但最主要是內心里你有一個基本的原則,你堅持走下去,慢慢社會會理解。你重要的不是來判斷動機,而是看過程和結果。我們做了一年半,起了很多正面的影響。
長期以來中國在一種不開放的環境下容易產生陰謀論,所有的東西都是陰謀。即使我們看到十八大以后,中央一系列反腐的態度,這樣一個好事情,大家都說都是假的,沒有希望,絕望了,根本不可能,都是騙子,走了一批貪官,還會來一批貪官。這是一個長期社會缺乏信任感形成的。我們不能改變大家的認識,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由于這樣的批評對我們是有鞭策的,是一種約束,使我們保持警惕,繼續不斷往前走,我相信總有一天社會會相信,重要是我們自己相信我們自己堅持這條道路,這是我個人的理解。
任志強:中國在相當一段時間,處于一個完全是假話的環境之中。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我們聽到的東西,或者是樹立起來的正規形象的東西,和反面形象的東西都顛倒了。因此在這個社會相當一段時間里,說什么都沒有人信。你說好的他就說是壞的。比如說紅十字會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是最美好的,突然發現里面有個腐敗的,就不好了。所以你現在做好事也會有人攻擊你,他認為是假的。
我們中國金融博物館完全是公益的,在座的有很多參加過多次讀書會的人,但是在微博上,在媒體中都有,對中國金融博物館的公益性表示質疑。比如說買我們的光盤要花錢,30塊錢,雖然30塊錢在大街上買一個假的盤可能10塊錢就夠了,為什么賣這么貴。我們配置了最好的設備壓制這個光盤,因為我們不能像音像有那么大的量,我們有版權號。這樣成本就大大提高了。但是知識是不能用錢衡量的,我們覺得我們只用一個成本價,而且要用一定的金錢來支持這個讀書會的公益行動。但是很多人認為你就是變相賣你的盤,就是為了賺錢。這點錢和我們投入的設備相比,和我們付出相比,差得太遠太遠。
王巍:所以我們內心是很不平衡的,包括做博物館也一樣,本來在天津做博物館是不要錢的,但是因為在市中心,所以我們象征性地要10塊錢門票,連電費都不夠,你一旦要錢大家開始攻擊。其實從我內心來說,我覺得中國應該改變一個觀念,像這樣的事情應該付錢,憑什么知識不收錢,我是民間博物館,我們自己來花精力,時間,費用來支持這個博物館,大家應該覺得到博物館花錢,或者參觀買一些書花錢,是一種榮耀,并不是一種恥辱。
劉曉光:你的博物館不會是為了賺錢的吧?
王巍:從做第一個博物館沒有想,當時是自己業余的,因為我自己有生意,生意不賺錢不會干這個。有第一個大家就忽悠我做第二個,于是第三,現在好幾個都在談。我是沒有精力,我們過去三年參與社會,我們非常幸運,我們沒想到有今天的財富。人生兩部分,一部分是掙錢,一部分是花錢。做公益,都是花錢的方式,這都是人生的一種表達。這就是一個中國會需要一大批人,不管在書院,博物館,各個方面,包括阿拉善,還有奧林匹克,都不是為了掙錢,是要表達這一代企業家正在調整,獲得初步成功之后,應該為社會做些哪些貢獻,來改變中國企業界這樣一種野蠻生長狀態。
任志強:我相信這個社會會改變的,偉大是熬出來的,要把假話的世界變成真話的世界要有個過程。但是經過這段痛苦以后,更多的人會支持你,贊成你這樣一種公益事業。我們相信他們這些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的,最后他們看到的結果一定是更多的人會相信,我們這個金融博物館是真正在做公益。我們既不是僅僅讓企業家來參與,也不僅僅讓經濟學家來參與,也不僅僅讓歷史學家來參與,而是讓大家一起來參與,這種選擇權交給你,你愿意聽這期也可以,聽下一期也可以,但是怎么選擇是你自己決定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真正讓大家充分認識的一個公益事業。
劉曉光:在歷史的長河中,在今天的歷史階段,在中國社會這個情況下,我們還需要多長時間?
任志強:如果有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地方開更多的讀書會,也許我們的速度就會快一點。如果有更多的政府,給予博物館或者公益事業更多的支持,可能我們普及的速度就更快一點,受眾的人群會更多一點。如果我們一次報名5000到7000人參加,但是我們的場地只能提供4、500人,如果有十個這樣的場館,或者更大的場館,也許我們的受眾人群就會迅速擴大。所以我們在有限的情況下做一些支持社會,支持中國改革的事情。
劉曉光:讀書會的目的或者作用,它也是一種社會的正能量的影響,或者是啟蒙,它可以產生這種思想,可以產生新的眼光和新的價值觀。所以現在我們真是需要更多的人,需要我們的企業家,其他人,共同來創造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平臺。
辦書院辦了將近50多場,這個讀書會中任志強最讓你高興的是什么?
任志強:最讓我高興的,就是有那么多人愿意來參加這個讀書會,我們先來的人可能有座位坐,中間來的人坐不到正規的座位,只能坐小板凳,為這個我們專門做了一些小板凳。再后來的人,沒有小板凳坐,我們一個人發一個小墊子要坐在地上。再來晚的人,就得站著。但是整個會場的情緒非常好,他們非常自覺,哪怕坐在地下坐了兩個小時,基本上沒有人去走動,底下自我交流說話都沒有。就是他認可這樣一個公益行為,對公益行為表示支持,他也信服臺上嘉賓講的這些東西,因此他們覺得這些東西可以給他們更多的收獲和更多的啟發,這個就是我們感覺到高興的。
劉曉光:觀眾的熱情和不斷的激勵是你最高興的事。
任志強:我們不是為自己去做這個事,我們請的嘉賓要真講什么東西,我們在小會議室里自己就可以享受了,我們不用到現場去陪著大家一起聽。但是我們更愿意看到的是,有更多的讀者和書友愿意來參加我們的活動,還有我們有那么多的志愿者,努力在做各種各樣的公益付出,幫大家服務。因為有的志愿者在外面,聽不到里面說什么,他們默默的犧牲,實際上就是讓我們的事業能影響更多的人。
劉曉光:王巍,最讓你高興的是什么?
王巍:我一聽到很多書院都在學習我們,而且我們的志愿者,包括我們秘書長不斷被人挖走,我就很高興,因為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來讀書。再一個我在微博上看表揚中國金融博物館我就很高興,因為批評太多了。
劉曉光:當你們書院辦了以后,全國有多少這樣的書院辦起來?
王巍:我覺得越來越多,前天我聽到一個總編輯跟我談,他關注我們很長時間,發現我們發展很快,今天中國已經到了這個時代,大家都開始學習,自我啟蒙,趕上這個時代了,所以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中國書院一個迅速的增長,而且老任來拿了一個獎在上海,社會服務獎。
劉曉光:在辦書院的過程中,讓你們倆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巍:有很多女粉絲為老仁要自殺,為了見老任一面?
劉曉光:確有此事?
任志強:我不知道。
劉曉光:王巍,你病了也有很多人來看你。
王巍:我幾乎沒有什么病,我一直在工作,我都沒有機會得病。
劉曉光:你們在辦這個書院,你們有什么希望?有什么愿景?
任志強:我們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最初我們并不是說兩個人商量好了,一定要把這個事怎么辦,一開始是試一試的辦法,辦一期,辦兩期,但是突然發現這個驢套了磨以后就下不來了,于是我們希望把它辦得越來越好。因為我們在辦的過程中,有更多的人不斷在問,你們下一期什么時候開始,下一期什么人來,很多人愿意把這個東西看成是自己生活的必需品,它不是打麻將。
在我們感動的時候也發現,在500人左右的人里,每次大概有30人左右是外地飛來的,有的是從深圳專門飛過來參加,從蘭州,從云南,從青島,從各地都有。這些外地人他能從這么遠的地方到北京來,有的坐火車,有的坐飛機,專門來聽。這反而讓我們覺得我們不能不把它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