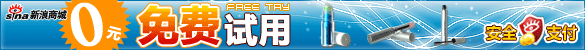|
周其仁:重新界定產權之路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2日 15:58 新浪財經
2008年1月12日,第十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為“中國改革三十年:評價與展望”。新浪財經對此次盛會進行全程同步報道。以下是北大CCER教授,經濟學家周其仁的精彩演講。 周其仁:謝謝。這場改革開放對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這個改革開放不是突然的一天從天上掉下來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醞釀了很長的時間。 陳志武教授的題目是改革開放160年,可能他要講更長遠的歷史淵源,我就想講得近一點,我自己比較關注兩個事件,給后來的改革開放都有重要的聯系,一個是在和平時期中國發生了較大規模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饑荒,其中第一個被報告到國務院的是河南的信陽地區,這個地區有850人,包括當年的地委書記被查辦,而且饑荒不僅僅發生在河南,這個事件引起了中央嚴重的反應,我看到的記錄就是在河南信陽事件在中央政局討論以后,囑托周恩來總理緊急起草了農村經濟政策的12條,這12條第一次提出要允許農民保留少量的自留地,這是劃下的第一道線,這道線沒有講執行的時間多長,也沒有講這是什么樣的權利安排,因為當時的情況等不及,有這樣的細致的安排,當時這個饑荒不僅僅是發生在河南的信陽。也在61年前后全國發生了很大的包產到戶,當時叫借地,安徽大概40%的生產隊也搞了包產到戶,當時也不叫包產到戶,叫“救命田”。這些事情當然可能是有很多的偶然的現象了,但它背后有很多的道理,當時來不及總結。這是我所知道的,跟后來的改革開放有關聯的一個事件。 第二個事件發生在1962年,發生在寶安縣,那一年由于各種各樣的謠言,說英國女皇要怎么樣,香港要開放,就在寶安這個地方,其中10萬人口意圖偷渡逃港,從廣東62個市縣全國12個省區聚集過去的,都是偷渡跑港,變成當年很大的一個事件,也是周恩來總理親自處理,分發疏散人口,據現在我看到的資料當時大概有約6萬人逃過去,其中4萬8千人大概被遣返回來,加上這里沒有出去的人當地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安頓,嚴格了出境的制度,同時也在62年就在寶安也做了很積極的反映,當時提出了叫利用香港建設寶安,把邊境的貿易活動活躍自由市場,活躍民生,活躍買賣,這個政策也是被當時的情況逼出來的,這兩個事件當然跟后來變化有關。但今天來看,僅僅有局部地區的自發的反應,不足以釀出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改革開放還要等待其他的條件,其中一個條件就是文化大革命,為什么文化大革命從反面籌備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因為它把過去的體制錯誤,擴張到了頂點,引起了很多的人對整個問題的重新的思考。因為任何的體制下,經濟會出錯誤,有人會說假話,但是在什么條件下,會發生到這么嚴重的地步呢?我們一直在宣傳我們的優越性,但為什么我們的人們要往資產階級的香港跑呢?這種問題,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很少有人會想到這個層次,這就是鄧小平最重要的總結,認識不到位,就有很大的問題。1978年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因為這一年發生了思想解放的運動,發生了對過去體制的重新的思考,不是思想家的思考,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解放運動,雖然發生在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個別政策比如說對包產到戶還是下了禁令,但是這一場全會和在他之前進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思想路線糾正了整個國家看待體制,看待制度,看待政策的思想方法,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的時候講過,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前進,就要亡黨亡國,這個思想路線是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因為從這個層面你才會去想,我們選的社會主義,我們選的公有制,我們選的計劃經濟,這個都是手段,講到底,要滿足人民的日益增長的文化和經濟的要求,要滿足發展生產力不能把它倒過來,用前人寫過的東西,本本的東西,蘇聯做過的東西,變成我們自己選擇我們體制的一種桎梏,選錯了要改過來,要聽從實踐的經驗,任何體制不管邏輯講得多么的透徹,做的效果不好就要調整,這個思想我相信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所有今天最重要的一個思想根源,所以我們今天還是把改革開放定成1978年開始,我們來看78年我剛才講的兩個事件完全做了不同的處理,不但自留地,因為后來形勢一好又開始折騰,又開始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包產到戶也得到了合法的承認,其實鄧小平在60年就講過,包產到戶能多打糧,不合法,讓它合法起來,但是60年沒有這個政治條件,要到1978年以后才有這個政治條件,逐步的從局部的包產到戶變成席卷全國的包產到戶,包產到戶我一會兒要將它的意義,它的意義就是劃出一條權利,我這個題目叫做界定產權,中國界定產權有社會性意義的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就是從包產到戶開始的。是集體的公有制,但是可以劃一道權利界限,使用歸你,種什么歸你,產品歸你,這個事情本本上沒有講過,但是實踐做得通就要把它做下去,給它寫到本本上去,這是78年以后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開放,開放也不是一天來的,78年的開放就我所知,也跟77年寶安第二次大規模的逃港集結人口有關,當時在廣東主政的是一位席同志,他去調查的時候,發現很多農民跑過去了,跑過去的農民的收入一兩年寄回來的錢就可以在老家蓋房子,這是很大的一個事情,席同志也不能接受,但是好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有一個實事求是,仔細找當地的干部問說過去干什么?說過去就是打工,說為什么打工可以掙這么多錢,甚至今天你可以去訪問羅芳村,靠香港邊境,香港對面也有一個羅芳村,是由我們這邊的羅芳村跑過去的人建起來的,但是收入相差100倍,后來我們就想能不能把門打開,你過去打工,讓香港的企業開到境內來,這就是最早開放的由來,廣東第一線的同志提出這個構想,向中央匯報,得到鄧小平的同意,當時用的什么名字,叫加工區,自由加工區,是臺灣搞過的,當時廣東的報告是叫自由貿易區,鄧小平聽了以后說就叫特區,因為共產黨在陜甘寧搞的就是特區,特區就是這么來的,這些事件歷史上發生過,包產到戶也好,自留地也好,農民的小自由也好,逃港也好都發生過,但是如果思想認識路線不同,后果就完全不同,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是逼出來,后來換到實事求是的路線上來,只要能夠容納生產線的發展,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好處,我們思想可以調過來,不要動不動就去遏制有生命力的生產形式,組織方式,全力界定形式,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 所以很多人批評華盛頓共識,我也看到過,認為改革開放是華盛頓共識的結果,這個是錯誤的,沒有這會事情,那個時候中國人絕大多數人不大關心華盛頓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們說了一些什么,我們的問題是要把飯吃飽,要把這個國家的經濟持續下去,而過去的教條阻礙了我們的手腳,就是這么一個簡單的問題,所以調整過來以后局面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個界定權利變成了一個席卷整個國家的改革運動,在我看來整個改革開放就是權利的重新界定,第一個層次我們的所有權全部要歸國家和集體,個人在里面是什么地位?什么權益呢?不清楚,搞了好多年,問題在這個層次,改革開放找到一個方法,集體的所有權是可以通過承包和界定出去的,清清楚楚的界定到個人,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層次,2002年立了一部法;第二個層次,這個層次不是可以使用,也可以轉讓,很多人討論市場經濟價格機制起主導作用?有人喊價有人還價,喊價是一個權利,還價也是一個權利,如果我們的企業沒有喊價權和還價權,所謂教科書上寫的市場價格從何而來?中國第二個層次就啟動了這個層次,你要使用權還有轉讓權,定價權,喊價權和還價權,中國資源的配置就不再生活在蘇聯教科書的那一套范疇,看不見的手開始起作用,直到最后寫入中央的改革文件,基本上要以市場價格手段來配置資源。 第三個層次,在中國社會當中,界定了創業權,很多人說創業不就是賺錢嗎?聽起來不好聽,可是市場經濟賺錢你要滿足別人的需要,我們過去高喊口號就是對人民的需要不聞不問,生產憑計劃,看上級的命令,不是看人民的需要,創業權是要對人民有反應,你不做反應賺不到錢,這一條東西對中國生產力的解放,我們從各個階層人看到了新型的企業家,如果沒有這個改革,陳志雄就不能去養魚,這是1980年廣東的一個農民看到市場這么缺魚,又有水,組織起來養魚,供應市場,立刻就劈天蓋地,資本主義,剝削,這個是高層領導干預了討論這件事,鄧小平干預了瓜子事件,蕪湖的人民今天是很自豪的,說《鄧選》里面三次出現蕪湖,就是傻子瓜子,那個人我做過調查的,文化程度很低,脾氣很壞,急了就踢工人,踢工人不可以,但是組織企業可以,你看我們改革開放就把這個界定清楚了,沒有這個東西,怎么會有后面的局面怎么會有這么多的產品送到世界上去,柳傳志可以搞PC,這是創業權的結果,他是計算所的一個工作人員,只能按照國家方法的科研基金做科研題目,改革開放使他變成了國內最大的PC的供應的商。馬化騰是年輕人吧!把全國的QQ好幾億人搞進去了,這個事情過去多少年就是認為不可以,犯了天條,然后還有馬云,還有溫州企業家,是通過重新界定創業權才有市場定基,才有今天這么多的服務和商品。 第四個層次就是各種來路的權利可以放到一個合約里面來,可以在市場的基礎上組織工廠,斯大林時候的工廠是絕對排斥市場的,我們今天的股份制是以市場為基礎來組織公司,不同權利放到一起,怎么互相保護利益,怎么互相不侵犯利益,怎么組織更大的生產力,這是中國第四個層次,就是不斷的重新界定權利,從僵化的教條當中走出來,從實際出發,至于這個權利界定到哪一步,再往哪一步界定,繼續實踐,先試再做再討論再炒,最后把穩定的東西變成法律,變成長久生活依存的一個章程,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改革開放,對于這四個層次的產權界定到今天為止都有不同認識,這個沒有關系,不同人就是有不同認識的,人就是有不同認識的一種動物,但是有一點重新界定產權和原來含含糊糊的大公有制之間使中國的經濟勢力發生了完全不同的變化,這一點我相信看到的人越來越多。由于有四個曾經的權利界定,中國今天的主要特征還不光是高速增長,是開放情況下的高速增長,我們過去也是高速增長,計劃時代蘇聯的數字也是很離譜的,問題你不開放,你不知道那個質量是什么,開放你沒那么容易造假,出口商品對方海關要檢查,中國今天高速增長不是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的高速增長,是放在世界舞臺上來看的高速增長,這個高速增長很多解釋,不少西方經濟學家說中國就是勞動力太便宜,我一直不同意這個解釋,勞動力便宜是一個要素,要素不會自動變成產品,要素要變成產品要經過組織和制度,中國高速增長或者開放下高度增長,真正的經驗是,真正的秘訣是什么東西呢?就是大幅度通過改革開放降低制度和組織的成本,這樣我們廉價勞動力才開始發揮作用,中國的工人技術人員企業家和地方和整個國家才能發力,才能在世界上占有更大的份額,當然這一場重新界定產權,就像剛才林毅夫講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哪一個領域里面問題嚴重了先動一動,過不下去了先改一改,所以我們的權利的界定是不夠普遍的,權利和權利之間的平衡關系構成未來改革的一個難點,如果看將來,我相信我們現在可以提出這樣的目標,要是有普遍的產權,不是哪一方面的權利,界定到所有的資源配置上去,我們現在講環境污染,環境污染就是在公共地方,對企業來說排放有好處,排放污染物的代價是大家去承擔而不是企業自身,所以環境問題在我看來是一個權利界定的問題,用什么準則來界定,來界定得清楚,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最困難的問題是中國改革當中已經提出來,所有權利當中有一種權利背后帶著合法的暴力,這個東西是一個社會當中最難對付的一個問題,任何一個社會要獨立國防要有秩序一定要有強制力,一定要有合法暴力,但是這個合法的暴力怎么能夠在軌道上運行呢?怎么能夠不出圈呢?怎么能夠不被濫用呢?怎么能夠不再這一次重新界定權利的過程當中可以循規蹈矩了,這是我們改革開放30年來到今天沒有解決的問題,也要留待未來解決。這個問題超出了純粹經濟學的范疇,但是我所知道的優秀的經濟學家同樣關心這個問題,比如說楊小凱臨去世之前一直關心這個問題,我讀了他很多臨死之前的那些文章、筆記、講話,中心就關心這個問題,我自己在國內做這個調查做得比較多,看來看去其他問題都好解決,就是這個問題有特別大的難度,當然總的思路有了,就是法治,這個法治不是說一些人寫一部法去統治別人,而是所有的人要服從同樣的準則,是用同樣的準則管住所有的人,今天上午幾位前輩特別是吳敬璉老師都講到了這個層次,茅于軾老師講到了這個層次,我相信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很重大的任務,中國要屹立于世界,沒有強大的國家是不行的,但是國家強大,尤其像今天財政力量這么好,政府部門你想要他不驕傲都很困難,因為成績就是好啊,在這種情況下,帶有強制力量在我們整個資源的權利重新界定過程當中,怎么能夠規范走上軌道,這是包括經濟學家在內要共同努力來探索的。 最后我想說,30年告訴我們實踐是第一位的。理論是第二位的。經濟學是在第二位理論當中的一個分支,我們要學習前輩當中對這個過程當中做出貢獻的一些優秀的人,比如說我們的很多經濟學家,我們上午的三位經濟學家,我們老師那一輩的經濟學家,也包括香港的一些教授,他們都從科學的角度闡釋現象,界定道理,把基本的經濟規律來做探索,我想在未來的改革開放還有很多難題等著,現在的麻煩是我們已經遠離了饑荒,中國雖然現在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重新發生59到61年那樣的大饑荒的可能性是幾乎等于零的,因為今天的制度是不可逆的消除了發生那種事件的體制基礎。同時國際競爭呢,中國在國際當中的表現,你要看GDP的增長,要看總量的增長,國際上現在比得過我們的沒有幾個國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確實有一個動力不足的問題,從我所知道的知識來說,繼續改收益會非常大,從局部的漸進的權利的界定變成普遍的權利的界定,變成盡最大的可能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要擴大經濟自由,據我所知對經濟增長還可以發生革命性的影響,會把中國比較可靠的從中低收入引向中等收入甚至引向高收入國家,但是動力在什么地方?過去是危機推動改革,這個動力已經衰竭了,新的動力在什么地方?這可能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尤其是我們在座的年輕的朋友要面對的問題。謝謝各位。
【 新浪財經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