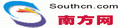南方周末:聚焦精英移民海外潮

作者:閻靖靖(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在讀博士)
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已成為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軍,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移民輸出國。
高端群體、龐大數量和趨勢化發展構成了不容忽視的問題:中國正在經歷全球化的新階段。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撒落著無數璀璨的明珠,貝勞就是其中的一顆……”這句18年前的電影《大撒把》中演員葛優謀劃移民路線圖的經典臺詞,如今已由喜劇幾乎變成現實。
想移民么?現在,你不再需要乘上前往西伯利亞的火車,穿越廣闊的俄羅斯,到巴黎等待夏季觀光團,再伺機前往貝勞,然后以貝勞為跳板前往美國。
你只需要準備一張35萬美元以上的存折,在五星級酒店的會議廳里,由熱情的中介小姐引導你,在挨著太平洋,同樣浩瀚的加勒比海地區,無數撒落的璀璨明珠之間,使勁圈中其中的一小顆——圣基茨和尼維斯聯邦。這個絕大多數中國人聞所未聞的小國,如今竟已成為眾多新富階層的移民目標之一。
這個將電影變成現實的場景,只是眼下眾多移民推介會的一幕。在眾多更高端的推介會上,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和香港,才是主流重頭戲。
過去十年,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各界精英、富商通過技術移民或投資移民的渠道,獲取他國永久居民權(以下簡稱PR)或國籍。在他們看來,優質教育、清潔空氣、安全食品、資產轉移、安全感,都將在移民的彼岸得到。
各種數據表明,自上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兩撥移民潮以來,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三撥移民高潮在進入新世紀的十年中已成愈發洶涌之勢。不同于第一撥混雜偷渡客的底層勞工和第二撥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高端群體、龐大數量和趨勢化發展構成了不容忽視和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是否正在經歷社會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
北京買房,不如移民?
中國社科院 《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
2010年4月北京車展上,一則移民廣告打得相當煽情:在北京買房?不如移民吧!
這條廣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潛臺詞是:在二套房購買門檻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環以內一手房價每平方米均價仍死守3萬元時,仍未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美國,已開始推行EB-5類簽證,吸引各國有錢人入籍,最低投資50萬美元(約人民幣342萬),即有資格申請美國綠卡。“理論上,居住二環以內的北京人民都具備了移民美國的條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機構協會會長齊立新笑說。
其協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到美國投資移民的EB-5類簽證的中國申報人數已經翻了一番,從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過1000人。中國再次掀起投資移民海外的熱潮。
2008年一宗移民美國拒簽案讓大眾對中國富人的美國夢與財力嘆為觀止。彼時,147名富豪組團投資,每人欲出50萬美元,集資7350萬美元,打算投入到美國費城會議中心的擴建中,以此辦理投資移民。申請因涉及人數眾多,有違移民法之嫌,全部遭拒。
這并沒澆冷富人們的移民熱情。美國國務院最新公布資料顯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聯邦財政年度獲批的EB5類簽證移民總數,已從2008財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來自中國。齊立新說,投資移民成功率高的國家分別為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其規定投資門檻分別為40萬加元(約235萬人民幣),80萬澳元(約454萬人民幣),150萬新元(約962萬人民幣)。
此外,申請難度最高的歐洲,近兩年仍頻頻有富裕家庭關注。在荷蘭一家移民機構任律師助理的黃馨(化名)說,中國富人已成為他們最優質的客戶,每年他們都會提供免費往返機票和酒店住宿,邀請中國富商赴荷考察投資項目。
加拿大移民局數據顯示:2009年,加國投資移民全球目標人數為2055人,中國大陸的名額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資起步價40萬加元(約235萬人民幣)計算,僅2009年,即使只按“門檻標準”計算,從中國流向加拿大的財富至少23.5億元人民幣,相當于一座世博會中國館。
事實上的財富轉移遠遠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請移民加拿大時,馬舒辦理的是技術移民,盡管身為廣州某公司高管的他彼時資產已達上千萬。“投資移民門檻很高,不是說你口袋有三百多萬就能移民加國了,還必須雇用一定數量的當地雇員,每年有一定銷售和利潤額度。”
在相對少數的投資移民之外,技術移民是一個更為龐大的群體。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機構協會會長齊立新告訴本報記者,近十年申請各國技術移民的數量與投資移民相比,大約為20∶1。
這意味著,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體面、收入頗豐的中國中產精英同時向加拿大移民局遞交移民申請。不僅僅是加拿大,過去十年,隨著各移民接收國政策的放開,中國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與財富精英大量入籍澳大利亞、新加坡、美國。如今,對于幾乎所有一線城市中產階級而言,一個集體感受是,每個人身邊都有起碼一個朋友正在或已經辦理了移民。
馬舒學的是國際貿易,加國駐香港的移民官專門為他設了一場長達一小時的英語面試,申請順利通過。他的履歷是中國典型的中產精英:畢業于某名校,三十出頭即擔任廣州某文化公司高管,有豐富的國際合作經驗,后獨立創業經商。
“分數有可能達標的人才基本素質為碩士以上學歷、精通英語,3-5年以上工作經驗,”馬舒說,“就是中國的中堅分子。”
馬舒只是龐大的“中堅分子”群體中的一個。據統計,2009年度,中國移民加拿大共2.5萬人;移民美國約6.5萬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亞約1.6萬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異軍突起的中北美小國也同時在吸納大量中國大陸移民。
2007年,中國社科院發布《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的同時,中國流失的精英數量也居世界之首。
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流出海外的78.5萬青年才俊,相當于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他們在尋求什么?
優質的教育,健康的環境,安全的食品,規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對移民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1992年葛優、徐帆主演的《大撒把》熱播時,馬舒已經大學畢業工作了三年。這部移民題材電影反映了上世紀90年代初的移民熱潮,彼時,移到哪是次要的,移出去才是關鍵。
馬舒并沒陷入那撥移民狂躁癥之中。由于工作的關系,馬舒常在國外出差,熟知1978年以來大批偷渡出境的同胞,在海外維生本領仍是賣苦力,這批處于社會底層的群體至今仍占所有華人華僑的絕大多數。1990年代初期沖出去的同齡人,也遠未過上光鮮的生活。一名定居歐洲的朋友,工科博士,彼時做著一家雜貨鋪的老板兼店員,每天最復雜的腦力勞動是計算一雙人字拖加兩罐卡布其諾等于多少英鎊。
拘謹、沉默、沒有宗教信仰、畏懼諫言、不參與公共事務,這些骨子里揮之不去的集體氣質加深了黃、白兩個世界的隔膜。
馬舒的理想是逐漸做到公司高管,而不是出國做超市店員。干了幾年,馬舒獨立出來單干,順風順水的生意突然敗于一場糊里糊涂的官司。2001年,馬舒辦理了赴加技術移民。
尋求安全感、為孩子謀求優質教育,是所有受訪者移民的前兩條理由。其中一名受訪者是身家數億的溫州商人,與本報記者第一次見面的場合,竟然是在他中學同學的家中。盡管在中東經商多年,他身上仍未散去溫商特有的熟人社會處事風格。
2009年,他開始將中東的生意轉移至美國,通過投資一座中美貿易城,投資移民。他坦言越來越不喜歡每周有四天時間得在外應酬、打點各路官員、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時間留給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為身份量級的標識。他們將之稱為“抄捷徑”,即用過去20年里迅速積累的財富,支付轉型期的中國所付的或忽略的代價:規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稅點、低遺產征稅、健康的空氣、安全的食品、免簽多國護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齡人中,許多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父輩、親友偷渡歐洲,有的為了入籍還加入法國外籍軍團,“現在輪到我想出去了,”他說,“但已經跟他們那批移民不一樣,我們有了更多選擇。”
另一個低調得近乎隱秘的移民群體常人無法輕易接近。公開資料顯示:加拿大的多倫多和魁北克是華人富豪移民的首選地。而在澳大利亞,華人富豪的首選地是悉尼與墨爾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已經明確將吸引華人富豪作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據。而對于這些新富階層來說,財產的安全則是他們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過去幾年也成為國內富豪青睞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遺產稅,令該國對國內富豪的吸引力加大。與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對移民沒有居住時間的限制,因此許多獲得新加坡綠卡的中國富豪仍可以持續在國內經營企業,這點也對國內業務存續的企業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許多國內富豪都在新加坡烏節路(屬于商務中心)購買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購買別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這一群體在技術移民印象中,封閉而光鮮,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他們從不參與任何華人社團活動,全都住在當地高端社區,有的甚至把名字都改了。一位移民律師在接受采訪時透露,他曾被中國某部門要求配合調查他的一名客戶,據說此人出境后,被查涉嫌挪用上億公款,這位律師拒絕了:“保護客戶的隱私是律師的義務。”
為了子女的未來
他們中的大多數需要褪去在國內“成功人士”的光環,回歸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們更多著眼于自己子女的未來。
在技術移民的世界里,他們首先得適應謀生的艱辛與社會地位的落差。各國在制定技術移民政策時,都將本國急缺的人才類型作為優先考慮對象,如澳大利亞、加拿大青睞IT工程師和會計師。
但由于兩國各大公司只認可本國及北美的工作履歷,大多數來自中國的技術移民都無緣從事原先的職業。
剛到加拿大時,馬舒的謀職底線是“先當個經理,也是可以的”。以他在國內的公司高管背景,“無論如何不算過分”。
當看到一位在國內做IT工程師的朋友,在加國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餐館服務生,三天后還因表現笨手笨腳被開除時,馬舒“心都涼透了”。
三個多月后,他終于在一家電訊公司謀到銷售國際長途電話的工作。這名快40歲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輕一起競爭業績,每拉到一個顧客,獎勵2加元,如果足夠勤奮,一個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幣5191.28元)。
沒人知道他曾打理過資產上千萬的公司,也沒人在乎。每次面試時,面試官的態度禮貌而堅決,“雖然你在中國的工作履歷很吸引人,但對不起,這不算數。”
受過高等教育,在國內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教養良好,地位體面,收入可觀,這是中國技術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頭即赴美讀MASTER、PHD,畢業后留美工作的留學型移民,他們移民時年齡已在30~40歲,選擇余地與競爭力都較小。
馬舒身邊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學老師,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術骨干,到加拿大后,他們成了卡車司機、超市貨柜員、收銀員;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術,表現頗受認可,卻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歲時,重返大學,現在正讀大一。
和普通大眾想象中不同,大量技術移民在國外的生活雖然平穩卻遠不如國內光鮮。在遙遠的異國他鄉,他們中的大多數需要褪去在國內“成功人士”的光環,回歸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們更多著眼于自己子女的未來,他們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夠在異國延續自己在國內的成功。“犧牲我一個,幸福后來人。”一位已經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術移民如此總結。
也不是每個中國技術移民都想得開。2005年,讓加拿大移民圈內轟動的兩起事件,一是湖北省前理科狀元讀完博士后,只在一家工廠找到一份體力工,跳樓自殺;另一名中國博士在被公司辭退后,跳橋身亡。
馬舒覺得,這都是讓中國的教育給害的,“尊卑貴賤意識太深”,“生而平等的價值觀已經滲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在馬舒印象中,在餐館遇到對服務生大聲呵斥的基本都是中國人,“加拿大人很詫異,為什么要這么做呢?”
盡管謀生艱難,盡管這兩年澳、加開始收緊技術移民政策,申請移民的中國公民不減反增。美國移民局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大陸共有4萬人加入美國籍,移居其他國家的移民總數也在4萬左右;在新加坡,華人總數約占全國人口75%。
馬舒至今保存著2001年初到加拿大的一份報紙,上面刊登著當時的加拿大總督(相當于中國公安部長),多用了15000加元(約10萬人民幣)裝修辦公室,被媒體曝光,道歉無果,只好引咎辭職。
雖然一度從事藍領工作,馬舒與朋友從未感到尊嚴因此受到損害,住房價格合理,多倫多居民曾一度抗議當地樓市被大量涌入的中國富人炒高;重新念大學的朋友,享受加國政府的教育補貼,每月2000加元足以支付學費及一家三口的生活費。“你現在能理解我不后悔移民的理由了吧?”他說。
中國繞不開?
他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時可以是一名中國人。
在越來越多的技術移民家庭中,至少一名家庭成員保持中國國籍,以便給自己留條就業機會。這一現象很像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香港掀起的移民高潮,人們把男主人保持香港籍的現象稱為“太空家庭”,太太在國外照顧孩子,先生們繼續在香港工作、做生意。
彼時的香港,一方面在許多人眼中政治前途不明,一方面隨著經濟的高速起飛,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與利潤空間,這些正是社會已平穩發展了幾十年,各領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國家所缺乏的。
馬舒重新開始操起老本行,做國際貿易,最初開始的生意還是與中國相關,即將國內的重型機械銷往海外。
馬舒承認,如果是想做生意,賺錢,中國是繞不開的天堂。
李兆,普美藝術品有限公司總經理,2008年移民加拿大,獲取永久居留權后,仍然生活在北京。這位留學法國五年的28歲年輕人開車前總習慣性地將ARMANI西裝脫下,掛在車后座,扣上安全帶,才啟動車子。
移民是他“長遠布局的戰略”,他堅信,與國際合作伙伴交往時,自己身上的歐洲氣息與加國身份能拉近雙方的距離與談判的砝碼。并且,這樣的想法已得到越來越多致力于發展為跨國企業的商人的認同。
在他所知道的投資移民中,放棄中國國籍是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要么是全身而退出國養老,要么是嫁人,相夫教子去了”。絕大多數只是需要獲取PR,兩者之間只是政治權利上的差異,卻能保證自己以中國公民的身份在國內暢通無阻地做生意。
“獲取PR,是為了讓自己更自由,”李兆說,“對于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個人來說,這點至關重要。”相比中國護照的13個免簽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免簽數量分別為125、120、130、122和110。
凌霄君,2007年投資移民新加坡,夫人孩子都遷居獅城,自己在上海繼續生意。“在新加坡,生意有15%的利潤,已經很讓人歡欣鼓舞了,可拿回中國呢?太一般了。”“這就是中國的好處,”移民對他來說,是給自己留條后路。
在這些投資移民的商業邏輯中,個人身份與對中國的認同問題已經剝離開來,祖國不僅僅只是有著高度文化認同與依賴的政治概念,更是一座奶牛牧場,他們喜歡喝牛奶,并不意味著樂意和奶牛過一輩子,而是把牛奶擠出來,帶走,同時,奶牛場也受益。這樣有什么不好?
孫多菲,美國留學生,綠卡持有者,2007年回國與姐姐開創第五大道奢侈品網購站,低于國內專營店的價格使生意很快紅火起來。2008年,孫多菲干脆把哈佛畢業的丈夫王征也叫了回來。
在波士頓,王征是一家公司的建筑工程師,小老板也是個中國人,五十多歲才爬到合伙人的位置,他覺得自己再這么呆下去,“閉上眼睛就能想到自己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的樣子。”
回國后,在正處于急速上升期的建筑業中,王征很快成為一家兩千人規模的公司的副總,年薪是波士頓的兩倍。“回到中國,你會覺得整個人生都彪悍起來了,”孫多菲說,“那是30年走完人家100年的路的速度。”
對于已拿到美國等國家國籍的王征們而言,仍然實行單一國際制的中國國籍法越來越成為國際化生活的障礙。
國務院僑辦專家咨詢委員錢江告訴本報記者,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是在1950年代的萬隆會議上由周恩來總理向東南亞各國承諾過的,以避免東南亞的華人華僑陷入雙重政治效忠的尷尬和危險。近幾年,多有商界、文化節、知識界高層人士通過與中央高層見面的渠道呼吁實施雙重國籍,這一問題也數次被高層討論,但很快否決,“在身份證問題、戶籍問題、遷徙自由問題等一系列身份界限沒有解決之前,承認雙重國籍,仍會帶來新的,甚至是更大的不公平”。
一位已移民澳大利亞的學者則認為,中國實施雙重國籍,是國際趨勢,目前全球一半以上國家承認或默認雙重國籍,韓國、印度等在轉型期一度流失大量精英人才的國家也已開始默認雙重國籍,吸引精英回巢,站在全球化人才流動、合作的角度考慮,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糾結了兩年之后,馬舒終于決定加入加拿大國籍,經常在國際間飛行的他需要更實際的安全感,作為加國公民能享受到極其重視與完善的外事保護,另一方面,每次回中國,他又不得不到中國領事館排隊,作為一名外國人申請簽證。
他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時可以是一名中國人。
(文中馬舒、凌霄君為化名)
>南方周末同日相關報道:
網友評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