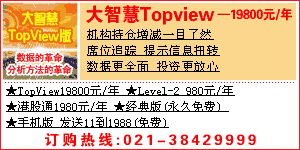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爭奪沉默的資產 聚焦農村土地財產權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30日 21:24 中國經營報
在合法與“非法”的搖擺之間,農村土地的財產權是繞不過的問題。 爭奪 “沉默的資產” 作者:李樂 李玉蘭從未想到,她會和農民對簿公堂,而且自己還坐在被告席上。 但是,這一切在2007年夏天還是變成了現實。在此之前,身為畫家的她,并不覺得法律是自己的“必修課”。讓她坐上被告席的,是她兩年前在北京宋莊從農民手中購買的一座院子,花費4.5萬元。彼時的她從未想到,兩年后這4.5萬元要面臨著打水漂的危險。 北京的宋莊,因為近年來“畫家們”的聚集,被習慣地稱為“畫家村”。在這里,面臨著與李玉蘭相似命運的人不在少數。原因很簡單,畫家們購買的是在“農村集體土地”上建造的房屋,而這類房屋的“流轉”與“交易”向來是“法律禁區”。任何試圖沖破這一“禁區”的“嘗試”,都可以被法律判為無效。 一切緣于土地。在中國土地并非農民財產,因此,農民雖然可以建房使用,但卻無權轉讓。長久以來,這成為了一片“無聲的財產”。然而,在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維系這片“無聲財產”的城鄉二元土地制度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于是,一場爭奪早已在暗中風起云涌,宋莊畫家村只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 四年靜默 從北京繁華的國貿中心,向東南沿京沈高速公路駛向東南方向,不到40分鐘,一塊標有宋莊的“界碑”便會進入視野。四年前,身為“藝術從業者”的李玉蘭和丈夫譚小勛來到這里,開始書寫自己在藝術生涯中的新履歷。 那時的宋莊,在圈內已經小有名氣。1994年,隨著大批畫家聚集的圓明園開始改造,方力鈞、岳敏君、劉煒、楊少斌等一批“畫界大腕”,開始遷居到通州宋莊,他們看中了這里農民自家的院子,于是掏錢買下,并且自掏腰包投入改造,將一個個破敗的農家院,改造成頗具個性的工作室。 李玉蘭便是步這些大腕的后塵來到宋莊的。2002年時,她因為自己看中的一套農家院而結識了當地村民馬海濤。他是這套院子的主人,按照村里人的說法,這套院子是馬海濤的父親“傳下來”的,而他祖上三代都是宋莊村民,這個院子的宅基地便是繼承而來。 “當時我們看這個院子面積合適,風水也不錯,很適合做工作室。”李玉蘭回憶說,彼時,到宋莊落戶的藝術從業者已經越來越多,整體氛圍也已越來越好,所以李玉蘭當即決意買下這個院子,而馬海濤則已有新的宅基地另蓋住所,到此,雙方一拍即合,用李玉蘭丈夫譚小勛的話說,當時雙方合作的態度“相當愉快”。 4.5萬元是雙方幾經討價還價之后,最終商定的價格。當地村民告訴記者,在“出售”給李玉蘭夫婦之前,馬海濤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不在這個院落中居住,雙方買賣時,這個院落已經稍顯破敗,“房子嘛,沒個人氣兒不行。”一位當地村民在鞋底上敲了幾下旱煙,向前來尋訪的記者說道。 北房5間,西廂房三間,還有整個院子。這是李玉蘭和譚小勛支付4.5萬元金額的內容。為了保證日后“不惹亂子”,李玉蘭和馬海濤像在城里買房一樣,雙方簽署了“購房協議”,并請村干部充當“保人”。 事后不久,李玉蘭拿到了土地使用證,以及房屋買賣協議。她發現,土地使用證上沒有自己的名字,而只是在“變更欄”中注明,“房屋出售給李玉蘭使用”。當時,因為這一點,她還曾向村干部咨詢此事,得到的答復是,“因為農村宅基地按規定不能流轉,所以在變更欄注明就可以了”。 在宋莊安家的“畫家們”境遇大抵如此。記者在宋莊走訪了多位“藝術工作者”,他們房產的購置證明,都是通過在變更欄中注記。“當時沒有人覺得這有什么問題。”1997年便在宋莊“安家”的孫永誠告訴記者,大多數人認定沒有風險的原因在于,變更欄的注記是由村委會以官方的身份做出的。 李玉蘭們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行為實際上是在“爭奪”一筆“無聲的財產”——在《土地管理法》維系的城鄉二元土地制度中,農民所使用的集體土地,雖未獲得“農民財產”的身份,卻始終為村民占有使用,而這種獨特的土地所有制,恰恰成了李玉蘭們日后遭遇的“伏筆所在”。 “東窗事發” “一審是完全敗訴,我接這個案子的時候,已經是二審了。”說這話的是陳旭,北京京倫律師事務所知名的房地產維權律師。此時,已經是2007年12月,而李玉蘭在一年以前,已經被馬海濤告上法庭,而馬海濤的訴訟主張十分簡單,就是要回房子,結果李玉蘭一審敗訴。 一切都在李玉蘭的預料之外。在平靜地在自己買下的農家院中度過了4年時光后,2006年12月18日,馬海濤與他的妻子董秀梅共同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2002年雙方簽訂的協議,并要求李玉蘭夫婦歸還已經使用了四年的房產。 這四年間,李玉蘭夫婦為改造這個院子,已經陸續投入了近12萬元。而家在河北的她,也已賣掉了自己在老家的房產,打算在北京宋莊徹底定居,一旦馬海濤的訴訟請求成立,不僅12萬元的改造投入將無法收回,而且,李玉蘭夫婦還面對著無家可歸的境遇。 然而,這一切并不能成為支持她繼續擁有這個院落的理由。陳旭告訴記者,馬海濤的院落是在農村宅基地上建立,按照現行《土地管理法》以及國務院的一系列條例、規定、通知,宅基地只能繼承而不能流轉,“因為宅基地農民只有使用的權利,而沒有處置的權利。”他說。 農民對宅基地失去處置的權利,還要追溯到1962年。國土資源部一位官員告訴記者,在建國初期,農村宅基地還屬于農民的個人財產,農民擁有“處置”、“抵押”、“占有”的權利,但是,1962年以后,新中國進行了土地管理制度的規范工作,彼時,農村所有土地均被收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農民對宅基地只有占有、使用的權利,不再擁有“處置”的權利。 然而,恰恰是這次使農民失去財產處置權的制度調整,給馬海濤提供了機會,因為馬海濤與李玉蘭進行了一次法律并不認可的交易。 李玉蘭向記者回憶,在庭審現場,她向法官出示了2002年在土地使用證變更欄上獲得的“注記”,以及與馬海濤簽訂的協議,但最終主審法官告訴她,包括政府注記在內,這些“文件”都不具備法律效力,因為這些文件協議都是建立在違反土地管理法及相關規定基礎上的,因此,協議一律無效。 就在李玉蘭訴訟的過程中,國務院與國土資源部先后兩次下發文件,并召開國務院常務工作會議,強調現行土地制度沒有任何松動的可能,農民仍然不具備宅基地及集體土地的“實質財產權”。 “鎮里面對這個事其實很重視。”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因為畫家的到來,宋莊被北京市確定為文化創意產業基地,如果畫家們集體離開,對經濟沒有好的影響,所以,鎮政府和法院達成過私下協議,在中央政府明確對農村集體土地、宅基地的態度之前,不進行判決。”他透露。 但恰是在此期間,國務院、國土資源部文件、精神相繼下發,使法院不得不啟動判決程序,按照“宅基地不是農民財產而無權處置”的原則,繼續維護現行法律,李玉蘭與馬海濤的交易無效。 制度爭奪 在宅基地仍然屬于財產的1962年以前的年代,馬海濤還未出生。至今,生在農村、長在農村的他,似乎也并不清楚“財產”這個法律概念的真實含義。但是,他眼看著的情景是,晚“賣”一天,就可以賣出更高的價錢,現在的宋莊,更多的“村民們”在注視著馬海濤和他曾經房產的最終命運,他們在考慮,“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從曾經的土地上得到更多”。 宋莊鎮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在與農民的溝通中發現,雖然不明確“財產”的法律概念,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村民開始明了在地價飛漲的背景下,自己手中的土地可以為自己帶來收益。 “很多村民就跟我講,旁邊的一個鎮,去年高速公路建設征地,一畝地的征地補償,就相當于他們‘賣掉’一個院子價錢的5~6倍,這種對比太強烈了。”他說。按照他的說法,恰是這種明確的對比,教會了農民“財產”的實際概念,“他們的邏輯很簡單,既然要回來能賣更多的錢,那就要回來。” 這位中國最基層的政府官員最為擔心的,并不是農民“奪回”土地的行為可能對本鄉鎮經濟所產生的影響,而是他們“奪回”土地之后,究竟能如何處置這些土地。他曾和不少宋莊的村民探討過這個問題,得到的大部分答復是“重新賣掉”,或者是要求原先的購買者,按照現在的價格,給予自己補償。 記者了解到,在處置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宋莊鎮政府及各級村委會曾考慮過一個“普遍合法”的方案,這個方案是,先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回這些宅基地,然后成立公司,并以村民持有的宅基地計算,讓村民入股,然后由這家公司統一將房屋租給畫家使用,產生收益,而后向村民股東分成。 陳旭告訴記者,這個方案已經規避了現有法律制度的一些限制,是合法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將土地出租用以經營是合法的,鄉鎮企業其實就是這個搞法。” 記者了解到,鎮政府、村委會的一些工作人員,曾就此問題與畫家們進行過溝通,基本得到了支持,但在村民那里,這樣的方案最終被否決。 “我不交。”在一個斜陽夕照的冬日下午,村民孫玉玲對記者直言不諱,“掙了錢能真按現在的說法分給我們嗎?還不是大隊的人拿的好處多,上次把我家一塊菜地做集體蔬菜種植,去年的分紅到今年還沒給呢。”這位農村婦女話語雖然直接,但確實暴露了中國基層政權存在的種種問題。 財產難局 “我很不同意你這個觀點。”當記者就農民是否真正有能力行使財產權提出質疑的時候,經濟學家鐘偉反駁道。“我講的是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經濟學所做的研究,絕不深入私人生活領域,我只研究土地這種財產權是不是應該歸還給農民,而不研究歸還之后的結果會怎么樣。” 在恢復農村土地財產權方面,他是一個激進主義者。在他看來,農民理應享有土地的財產權利,最終要體現的就是“處置”的權利。鐘偉的觀點代表了絕大多數學界的看法,周其仁、茅于軾、江平等“權威學者”始終都強烈主張“把農民的土地還給農民”。 對于中國農民是否具備行使好財產權的素質與能力,顯然不在他們的研究范疇。但是,畫家村僅僅是“冰山一角”,當全國數量巨大的農村集體土地,都要具備財產權而可以由農民自行處置并流轉的時候,可能產生的效果將不再是一個“經濟學不研究的范疇”。 記者了解到,像畫家村這樣的集體土地或宅基地流轉問題,政府實際早已考慮多年,并已開始準備在天津、重慶等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進行試點,但這仍不意味著政策的放開。天津濱海新區管委會一位官員明確告訴記者,即便試點流轉工作開始,也絕對不是農民自身主導下的完全自由流轉。 “肯定還是要有政府指標管理,不能說農民想把地賣給誰就賣給誰。”這位官員透露,他的擔心恰是在于農民是否有能力鑒別決定最佳的“購買者”,而即便如此,天津的土地改革流轉方案也進行了大量的修改,“基本的精神還是政府控制下的流轉,自由是相對的,只是取消了原來農村集體土地要轉變為建設用地,一定要通過征地這個環節。”他強調。 顯然,政府考慮的是比法理公平與學理公平更重要的現實問題。作為中國——這個復雜社會機器的管理者,他們不得不對“自由流轉”的后果做好“最壞的準備”和“最好的工作”。 “印度和北非一些國家遵從西方經濟學家土地私有化的藥方,最終的結果是,農民在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下,最終導致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對記者表示。 而在他看來,中國農民的社會保障同樣處在不甚健全的環境下,“一旦允許土地流轉,一旦農民遇到大病或其他超出現有保障或自身能力不能解決的問題,賣地幾乎就成為了唯一的選擇,而此時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日后如何生活,顯然將成為政府需要面臨的一大難題。在仇保興看來,印度與北非國家大城市周邊存在的規模龐大、缺乏公共飲水和基本衛生條件的貧民窟,與其激進的土地私有化流轉政策直接相關,而這恰是中國政府官員最為擔心的未來,也是賦予農民土地應有財產權最大的難局所在。
【 新浪財經吧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