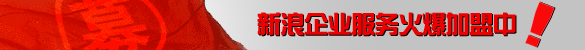遲到的婚紗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6月18日 18:08 經濟觀察報 | |||||||||
|
采寫:劉小萌 口述:張玲 采訪地點:北京市東城區豆腐池一 我出身在一個資本家家庭,與共和國同齡。上小學三年級,迎接少先隊十年大慶,要選代表上人民大會堂,還有毛主席接見,聽說這消息,別提多振奮了。同學們都以為會選
我記得那個場景特清楚,回家時我爸正挨那兒坐著。在這之前,人民大會堂剛建完還沒開放的時候,組織工商業人士參觀,我爸也興沖沖地去了。回來以后還給我講呢,里面怎么怎么好,穿的釘子鞋,怕把地板碰壞了,干脆就提了著鞋,光著腳走了一圈,特新鮮。我當時還說:“好不容易有這么一個機會,怎么不讓我去。”等到我告訴他“去人民大會堂沒有我,說我出身不好”時,我爸看著我笑著說:“沒關系,長大當上勞動模范就能進去。” 1967年我在中學鬧串聯回來,學校說要“復課鬧革命”,接著給畢業生辦學習班,動員上山下鄉。我是66屆初中畢業生,最后報名去了內蒙土默特左旗,那是1968年9月。 插隊第一年,國家發給生活安家費,我們知青小組買供應糧吃,一起勞動,還沒有顯出什么差別。可到第二年生活費沒了,吃什么呀?吃你頭一年掙的工分。我呢?干到第一年的5月份就病倒了。下鄉前我受過一種刺激,精神狀態不是太正常,到現在也不能說完全恢復了,這刺激大概一生都得留在心里頭。當時我躺了十多天,知青對我很照顧,但再照顧,你不出去勞動,工分沒有啊?她分給你點工分那不可能啊。 正好是那段時間,有一次我去看場院,從外邊回來,碰上了李剛小他媽,也就是我后來的婆婆。當時村里那些好心人,對我們知青可好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給我們送去。對別人家送的吃的,我們都痛快地收下了,唯獨這一次,剛小他媽煮的十個雞蛋,家里的知青說什么也不收。我從外邊回來,她兜著雞蛋正怏怏地往回走,碰上我了,就跟我說:“張玲,我送了點雞蛋他們沒要,給你吧。”知青為什么不收她的雞蛋?她名聲不好,也就是作風有問題,沒人愛搭理她。我當時正在困難的時候,也顧不了那許多,就收下了。 從我們下鄉之后,剛小就一直幫助我們,他是漢民,那個村里蒙民比較多。我們遇到什么事比如煙筒堵了,炕冒煙了,他都來幫忙。有時別人老遠的看著,他不在乎,走過來關心地問問,跟我們沒有什么界限。他祖輩是從山西過去的,好像內蒙那邊的漢人大部分都是從山西過去的,解放以后還有一部分貧民是政府給遷過去的。我們去的時候也是這樣,蒙人是雙份自留地,漢人都是一份。 他媽看見我要了她的東西,乘我看場的時候,就讓她的女兒給我送烙餅啊、餡餅啊,當時真是救濟了我。她這個人雖說作風有問題,但是挺熱心、也挺能干,再說剛小,69年10月份,我倆的婚事兒就定了。我們那個地方的女知青,5月份就有結婚的,但她不是我們公社的。我們村就我一個與農民結婚的。 我決定在農村“扎根”,有多方面的考慮:一個是下鄉前精神受到過刺激,留下了后遺癥。開始時我特能干,后來連鋤頭把兒都拿不住了。那件事對我影響太大了,如果我是一個正常人,本來身體又好,可能就是另外一條人生道路了。但是在當時情況下,既喪失了勞動能力,又沒有經濟來源,只有走這條路。我覺得既然決定留在農村,就要找個歲數合適的。剛小和我的年歲差不多,他是村里最好的勞動力,生活上有依靠。他不是貧農,是中農出身,按說中農也可以參軍,但比貧下中農還是費點事啊,可他沒有參軍要求,我覺得這點也很合適。再有一個,無論是他們家還是我們家,都有一些扯不清的麻煩事,我家是成份不好,而他媽的作風問題對他也是一個很大的包袱。我想,我們倆應該甩掉包袱,靠自己去建立一種新生活。 從決定這件終身大事到操辦婚事,前后也就是一個多月的時間。婚禮的頭天晚上,我一個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場。那時,我的心情很復雜,因為這是在沒有出路條件下做出的選擇,這一輩子就得留在農村了,今后面臨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樣子,沒法想像。我覺得,就是一個火坑也得往里跳,確實也沒別的路。 婚后十幾天,就發現剛小有賭博的惡習。當面數落他,他不承認,過后依然故我。因為他屢教不改,我氣得自殺過,一瓶安眠藥,才吃掉了4片,剩下的96片我一口氣全吞了下去。慢慢的就兩腿發軟,動也動不了了。幸虧被及時搶救,才保住了命。這以后,我也不想死了,何況還有了孩子。 第一個孩子是在70年冬天出生的,農村過月子有吃一百個雞蛋的說法,但我一個雞蛋也沒吃過,頭幾天就是喝點紅糖水,接著一些天吃細面條。冬天坐月子可把我凍慘了。結婚時,我住的還是剛小家的舊偏房,第二年我們蓋了新房,當然是土坯的。內蒙的冬天特冷,北風呼嘯,遍地積雪,夜晚溫度足有零下三四十度。新房坐落村東,更感到風頭的強勁。 熬過這年冬天,心里忽然產生回北京探親的強烈愿望。下鄉一年多,時間不算太長,但經過結婚、生育等人生的大事,我已從天真無邪的城市少女變成了每日圍著灶臺轉的農家婦女,對過去的生活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覺。在“廣闊天地”的磨礪下,我已經脫胎成另外一個人,一個連我自己都時時感到陌生的人。 當我提出帶孩子回京時,卻遭到剛小家一致的反對,他們不了解我的心,擔心我一去不復返。在我的一再堅持下,他們最終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是把孩子扣下了。即便這樣,我還是毅然離家踏上返京的路程。 從村子到火車站有十幾里路,為了趕十點多鐘的火車,我起了個大清早,一路上,眼前不時浮現孩子紅撲撲的笑臉,腿上像灌滿了鉛般的沉重。在車站排隊買票,從隊尾到隊頭,足足排了四五次,每次輪到賣票窗口,都拿不出勇氣來掏錢買票。前面是望眼欲穿的家,后面是牽腸掛肚的孩子,一般難以割舍的親情,猶如兩只無形的大手撕扯著我的心……南去北京的火車在小站只停留一二分種就啟動了,望著漸行漸遠的火車,我不禁嚎啕大哭,站上的人們都困惑地看著我,但是又有誰能洞悉我內心的苦痛呢?從上午到下午,我在車站外的土坡后足足哭了半天,淚流干了,心里好受了一些。當我拖著沉重的雙腿回到村里時,已是深夜。回到家,發現婆婆把孩子抱到他們屋子去了,我那屋他們也占了。可是我沒回城增加了他們對我的信任。他們當時的心情是:你走了,也就不回來了。看到我回來,他們了解張玲了。 71年秋天有了點收成,我帶著孩子回了趟家。那些年,我媽自己承受著種種苦難不說,不知為這個破碎的家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淚,她把所有的情感都傾注在幾個孩子上。“文革”前,我們就像一群無憂無慮的小雞,受到母親精心呵護,只有到下鄉離家,人各一方,特別是自己也身為人母之后,才真正意識到母愛的博大。 后來的日子逐漸好了一點。婚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幫助剛小改掉賭博的習慣,原以為我這心血沒有白費,結果卻發現他根本沒改,老是為他擔著心。他有時輸了錢,心情不好,回來就跟我吵,弄得我膽戰心驚的。我們的生活是挺困難,可有時候也改善一下。孩子有病了,吃點面條,我說你就坐下來高高興興地吃,哎呦,又吵得翻了天,沒有一天安定日子。按當地習慣,過年吃年飯,全家人圍坐一起烤旺火,吃餃子。一步一步安排的好好的,誰知他又去賭了。 知青找了當地的農民,絕對是有差異。如果剛小不耍錢,其他的事我都能處理好,換了別人不知道能不能?婚姻問題我反復想過,跟農民結婚當然有積極的一面,你有一些新的東西,他沒看到過,通過婚姻他了解了,可是深層的東西不會因為這個改變吧。從大的方面說,農村更不會因為你找了農村的青年有什么改變。 二 我在農村一直生活到79年,上邊終于發話,要給我們這些在農村扎根多年的老知青安排工作。以前,我想都不敢這事,因為在農村結了婚,還有了二個孩子,老大是70年出生的,老二是72年冬天出生的,除了帶孩子,還要喂豬、做飯、伺候公婆、男人,天天如此,和其他農婦沒有兩樣。這次忽然說要給安排工作,還說是最后一次,如果不走以后國家就不管分配了。這就像天上掉下了餡餅,意外之喜,說什么也不能錯過。那時我的身體也是不太好,還是借了一輛自行車,跑了老遠的路,去領指標、填表。 80年5月我到廠子報的到。一同報到的有12個北京女知青,差不多都是在在農村結婚多年的。一直到88年把戶口轉回北京,我在這個“大集體”整整干了8年。“大集體”的待遇跟國營單位絕對不一樣,白手起家,自負盈虧,頭三個月都開不了支,生產、管理沒有一點“王法”,整個一個“土”政策。 說是進了廠子,連個穩定的住處都沒有,上哪兒施工就住哪兒,臨時搭個帳篷。任務主要是維修鐵路,也就是篩石頭,清篩,把土篩出來再把石頭擱回去。鋪設新鐵路的活也干過,從抬土、抬石頭到鋪鋼軌,那鋼軌多沉呀,好多人抬一根,還有那洋灰枕,女的跟男的、個高的跟個低的,大家一個樣,多沉呀。我的腰就是那會兒壓壞的。我們一個個的腰都是這樣,腰椎受強壓,關節受損。內蒙的冬天可冷呢,沒錢買棉鞋,都張著嘴了,拿鐵絲拿繩湊合勒一勒,腳指頭凍的一直麻著,摸著沒感覺,跟“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玉榮白毛風天遭的罪沒什么兩樣。 就這樣,在線路上干了兩年,定期回家去看看,總算有了點工資,比在農村好過些。在農村一直就沒錢,年終分紅,也就10塊8塊的。 我的戶口從農村出來后落在呼市吉寧段,屬大集體戶口。人家不是說孩子隨母親嗎?但孩子的戶口沒上來,派出所不給辦,說哺乳時期隨母親,年齡一大就不符合轉戶口的條件。80、81兩年,我在線路上跑,還顧不上孩子戶口的事,當時孩子就跟我住帳篷,都上學了。82年以后開始安定下來,就想著法把孩子戶口從農村弄出來。我想了個轍,要求辦離婚手續。這在當地早有先例,有的是真離婚,有的是假離婚。離婚證的條件是:所有財產歸男方,孩子歸女方。就這么寫的。我就要那兩孩子。孩子歸我了,當然得給他們上戶口。 看別人辦的挺容易,到我這可難了。公社管事的是剛小的親戚,他不給辦,說剛小有賭的毛病,離了婚只有打光棍。我跟他說這是假離婚,為的是給孩子上戶口。他還是不聽。后來我找了一桶奶子,托村民政給他寫了一封信,講明原由,總算給辦了。廠子里我們一共8個知青,我是最后一個辦成的。孩子的戶口給上了,糧食關系又不給上,又費了好多周折,求人送禮,才辦成糧食關系。當時糧食關系還是挺重要的。因為我們還沒有獨立戶口,只好把孩子戶口也上到集體戶口上。 辦完孩子戶口,接下來該考慮剛小的問題。我帶孩子出來之后,剛小也不愿在村里呆著了,出來找事干。過了一段時間,有些正式工開始在鐵路旁邊蓋小房,路邊有的是空地,沒人管。我們也順勢蓋了一間小房。有住處了,這才又想著給剛小弄戶口。有好多國營廠子,對知青照顧特好,想方設法給他們的農村配偶安排工作,至少是個臨時工。我們那兒可沒這好事,幾個知青都“是后娘生的”。廠子對他們自己的子女很照顧,但這幫子知青是沒辦法帶進來的,就事事卡你。我們曾要求跟男人對換,我們留在家里,讓男的出來干活,上面就是不同意。 我們原來考慮過去靜坐、去臥軌,想來想去,覺得這樣做不妥,才決定一起給國務院寫信。后來回到北京,我為住房的事還給北京市委寫過信。 給國務院的信發出沒多久,上邊就批準給農村配偶上戶口。我是在82年辦的假離婚,后來給剛小上了戶口也沒再辦復婚。當初開那個離婚證只是為了給孩子上戶口,在戶口本上我們還是兩口子。把剛小戶口從農村轉出來,主要是讓他心里踏實,沒有多大的實際好處。我當時還留了個心眼,說咱們不如兩邊干,這邊掙著錢,那邊自留地留著,多好的事啊!我的腦瓜還是比較靈活的。他不行啊,看見人家戶口都轉了,他也得上啊!其實他一上戶口,自留地也沒了。戶口是上了,工作不給解決呀,都是自己干,后來就想著做點小買賣,收雞蛋賣雞蛋,在廠子邊上開了一個小雜貨鋪。 84年以后,我們生活基本上比較平穩了,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剛小買賣做的紅火一時,殺羊賣肉,誰也賣不過他。買肉餡的顧客來了,他白給你鉸,別人的羊肉半天賣不出去,他的羊肉一會兒就出去了。他做買賣在行,人也好,又能干。85年正好鐵路沿線改造,在我們搭小棚的地方蓋起兩幢樓房,我們作為拆遷戶第一次住進了樓房。現在那兒還有我們兩居室呢。如果當初你沒在那蓋房,拆遷也沒你的戲。我們自己有了房子,戶口才遷到了一塊兒。 三 88年我把自己和孩子的戶口辦回北京,主要是為孩子的前途著想。剛小的戶口不好辦,就先那么拖著。那會兒兩孩子都大了,如果初二插班的話,學校還能收,到了初三就不收了。 為了轉戶口必須先有接收單位,沒有接收單位只好辦假接收,如果沒有接收單位他不給你落戶口。我開了證明,費了好長時間,找了一個假接收單位,總算把戶口落下了。接著趕快安排孩子上學。兒子從沒離開過我,原來擔心他不能適應這里的生活,沒想到他上學還混的不錯,學校挺重視他,升旗還讓他去,這孩子特老實,很快入了個團,學習成績越來越好,我就塌實了。 女兒轉到女一中,也就是我的母校。老師都特好,過去教過我的老師挺幫忙,本來插班是要交錢的,我這兒什么都沒有,大家出于同情心,就把孩子給收下了。 把子女安頓好以后,就決定回內蒙。我是90年過完年回去的,在北京一呆2年多。我在北京辦的是假接收,自己和兒女的戶口雖然辦回來了,我卻成了不折不扣的失業者。回去后我就是養病,躺了一年,身體弱,一直怕風。好在剛小很能干,他做買賣,我在家里料理,幫他剔個羊肉。他弄來雞蛋,我幫著賣。孩子們都不在身邊,我就專心對付他。那幾年,是我生活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到92年我們就沒有欠帳了,還斷斷續續攢了些錢。我從來沒見過存折,那時有了第一個存折,3000塊錢,挺高興,他也沒去賭。 93年的買賣不太好做,買東西的人少了。買賣總是開始時好做,越做下去越賺不上多少錢了,剛小的干勁也就差了。我說:實在不好做,咱們門前擺個車攤,這歲數也大了,你想下去收雞蛋,就跑一回,不愿意跑,就在這兒修個車,你有力氣,這也能干啊,還能跟大伙接觸。我給他想了這么一個碴兒,他不干。 一次,有人來買雞蛋,我一看,哪兒還有雞蛋?他根本就沒收回來,兩個簍子都空著,車也在那兒,就是人沒了。哎呀,我的心里“咯噔”一驚,就知道不對碴。對他好賭這點,我特別敏感。一個是買賣不太好做,就有點兒放松。再一個,我們當時幫他叔伯兄弟找了個媳婦,這叔伯兄弟的父母都死了,是我給張羅的這事,辦的挺好的,還給他出了1000塊錢。誰知這媳婦呆了10天就跑了,人家說是“放鷹”的 。剛小受不了這個刺激。人在強刺激下,意志又沒了,就像吸毒的復吸,剛小又落入賭博的深淵。從此,買賣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95年我正在北京看病,他來北京看看,臨走時將歷年積攢和子女掙的一萬多元錢都拿走了,說是要“做大買賣”。那年頭,一萬元可不是個小數,“萬元戶”還是個很值得羨慕的稱號呢?可沒過多久,就傳來噩耗,說剛小腦溢血突然病逝了。他回去后,據說買賣進行得不順利,心情自然不好,加上經常酗酒,身體里潛在的病狀一下子爆發了。剛小的喪事是在村子里辦的,兒女怕加重我的病,沒讓我回去,他們回去辦的喪事。說實在的,剛小應該算是個不錯的男人,一表人才,能干,勤快,心眼靈,待朋友真誠,如果不是陷入賭博泥潭難以自拔的話,恐怕不會是這么一種結局。 四 剛小一死,我完全沒了經濟來源,再加上沒有一個穩定的住處,這段日子對我真是“雪上加霜”。原來我爸有一個院子,剛解放就上交了,剩下三間北房也被人給占了。后來又落實回來,兩間由我哥哥住著,剩下那間算是我們的,可是又被我媽單位換走了。等于我們住著公房,原來那間私房也要不回來,這中間的關系特別亂。那間公房到底有多大?說起來嚇你一跳,也就是8平米的一間小耳房。我媽已經70多歲,我只能擠在她的單人床上一起睡。我媽本來身體不好,再加上不得休息,身體狀況就更差了。我看總這么下去不是辦法,就只身到小湯山療養院照顧一個癌癥病人,臨時找個寄身的去處。以后,病人去世,小湯山不能再留住,我又去給親戚帶孩子,過著“打游擊”的生活。 我的這些困難,被我以前的校友田小野知道了,“文革”中她也是在土旗插隊。98年初我們集體返鄉途中,她帶著深切的同情傾聽了我這些年的坎坷經歷,在當年5月22日《中國婦女報》發表的長篇報道《嫁給農民的女知青》中,專門寫了我的遭遇,文中寫到:“如今張玲戶口回到了北京,但在北京她卻沒有一張屬于自己的床”。報道發表后被多家報刊轉載,引起許多有過知青經歷的人的關注。一位素昧平生的老知青趙昌明幾經周折找到我,對我的處境表示關切。 不久,昌明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對方也是老三屆,同病相憐,很容易就坐到一起,但是沒有談成,據說是嫌我身體不好,后來昌明才告訴我實情,對方是因為我沒有工作。前面說到,我在88年把戶口轉回北京時不得不辭掉了工作,從此失業。我這人不懂政策,但總有個疑問:國家讓我們戶口回北京,本意是為了解決我們的困難,既然這樣,為什么又要制造新的難題呢? 回過頭再提與吳春海結婚的事 。春海60年生人,整整小我10歲。他小時候得過腦膜炎,留下后遺癥,腦筋不如常人,過去干過臨時工,燒鍋爐需要上崗技術證,春海干不了,只能做鍋爐工的助手,推煤。這是力氣活,春海最不惜的就是力氣,但還是干不長。不是因為他自己捅了漏子,就是老實巴交的被人欺負。他父母生前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把自己10多米的住房指標留給了他。好在他弟弟春明很照顧他,春海得以衣食無憂。 昌明給我介紹春海,女兒不大滿意,嫌他沒有工作。我說既然提了,就去看看,這樣就約了日子見面。春海家住什剎海前井胡同,我家住鼓樓大街豆腐池不遠,離北海都不遠,我們就上北海溜達。我一個人說呀說,春海只會一聲接一聲的“嗯”。就說這歲數,我說你是59年的,我比你大10歲呢。他說,那他們怎么說比我大9歲呀。我說:“那你覺得怎么樣?”他說:“無所謂。”他特愛說“無所謂”。我問:“你會做飯啊?” 他說:“會做飯。”我說:“走,上你家瞧瞧去。”我這人就是,辦事從來就不帶拖拉的。他特高興,就領我去了。 進了大門,穿過一條狹窄的通道,就是他的家。外間接出的廚房,完全遮擋了屋內的陽光,白天在里面也需要開燈。我說:“哎呀,住窯洞來了。”再一看床上鋪的被褥,別提多么臟。那些天,我因為照顧家里病人特別累,進屋休息,沒多會竟打起盹來了。一會兒功夫,春海就把飯做好了。蒸的米飯,炒了兩個菜,一個是青椒肉絲,一個肉片豆角,飯菜可口。真沒想到,春海還有這么一手,我對他的生活能力徹底放心了。心里說,這人不用別人怎么幫他,頂多收拾收拾屋子就行了。 和春海的事最初沒跟兒子提起,只是說:“我給你們找了個做飯的吳叔叔”。當時兒子和兒媳剛來北京,孩子很小,兒媳不會做飯,吳叔叔天天過來給他們做飯,一來二去,很快熟了。兒子的心特善,他不在乎別人怎么看,總是說這個人不錯。春海天天過來給做飯、買菜、換煤氣,家里這攤事他全包了,你想這一家人回來吃飯,挺重要的事。因為我弄這一攤事兒弄不了,身體不太好。后來兒媳婦學會做飯了,不用他幫了,而是做好以后說:“讓吳叔叔過來吃飯吧。”他們對“吳叔叔”的印象就是樸實、勤快。過了子女這一關,我和春海的事就算定下來了。 我和春海住到一起,也沒辦結婚登記。我覺得這不過是個手續,沒多大實際意義,再說,交300多元辦手續,也舍不得。另外,擔心這樣會影響春海申請最低補助。左思右想,還是一切從簡吧。我們的事引起許多熟悉和不熟悉的知青的關心。田小野、張援等人希望給我舉辦一個特殊的婚禮,并在小野的知青網站上發了一個通知。反映之強烈出乎意料。 2001年1月7日,新世紀的第一個星期日。這天下起罕見的大雪,城里道路泥濘,交通阻塞,我真擔心婚禮的冷落。畢竟,在答應要來的賓客中,幾乎沒有我們的親屬。沒想到,那么多朋友冒雪趕來參加我們的“世紀婚禮”。 回想過去大半輩子,的確是受了不少苦,但沉浸在歡快的婚禮進行曲和賓客的笑語中,我一時又覺得自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許多人的經歷盡管比我還坎坷,但他們也曾受到過如此誠摯深厚的關愛么?婚禮上,我高興地告訴來賓:我這一輩子,第一次穿200多元的紅衣服,第一次涂胭脂抹口紅,第一次見到這么多人參加我的婚禮,做夢都沒有想到會這么熱鬧!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
|
不支持Flash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國內財經 > 正文 |
|
不支持Flash
|
| 熱 點 專 題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市黑馬:今日牛股! |
| Excel服務器功能強大 |
| 戒煙讓男人暴富項目! |
| 韓國親子裝2.5折供貨 |
| 1000元小店狂賺錢 |
| 聯手上市公司賺大錢 |
| 一萬元投入 月賺十萬 |
| 18歲少女開店狂賺! |
| 99個精品項目(賺) |
| 治帕金森—已刻不容緩 |
| 夏治哮喘氣管炎好時機 |
| 痛風治療新突破(圖)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Ⅱ型糖尿病之新療法 |
| 高血壓!有了新發現!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