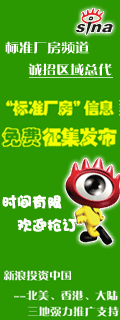|
本報記者 姚峰 張鳳安
溫州 杭州 上海報道
溫州模式是什么?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是一個謎一般的問題。
從1980年代初到現在,對溫州模式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平息,與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相伴而生。
從某種意義上講,溫州模式作為一種“術語”的出現是必然的。當所有人都試圖“摸著石頭過河”尋找富裕的路徑時,任何方法論上的成功都難免被善意地上升為一種世界觀,于是,一種在溫州被驗證的路徑就很容易被固化成模式,機械的理解并崇尚也就無法逃脫。
爭論也正源于此。
但爭論者是否都走進了溫州的深處?是否將溫州模式放在歷史的背景中考察?從溫州模式肇始之初,外界對溫州單一的、非此即彼的判斷就相伴而生,而在種種的言詞間,跳動著對溫州和對溫州模式的刻板印象。
從1980年代溫州第一任市委書記袁芳烈,到如今大力推行招商引資的現任市委書記王建滿,看似思路、手法迥異,但這背后的“推手”,卻是殊途同歸。
也許,真實的溫州模式一直在被誤讀;也或許,從來就沒有什么溫州模式。
“我沒有推翻溫州模式”
3月31日這天,溫州市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接受了劉奇辭去溫州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的請求,同時任命邵占維為溫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代理市長。
邵占維曾經長期擔任寧波港務局局長。很多人的判斷是,邵占維之前的工作經歷將對正在建設的溫州石化基地大有裨益,而基于寧波與溫州不同的發展路徑,邵占維的到來,會與大力推行“騰籠換鳥”計劃的溫州市委書記王建滿一起,共同促進溫州模式的發展和革新。
溫州為什么要“騰籠換鳥”,王建滿說:“我們必須要打破溫州經濟以小取勝、以多取勝、以價取勝、以量取勝的老格局,換來新的產業、新的體制和新的增長方式。”
王建滿選擇的路徑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2005年初,從杭州蕭山轉戰溫州,履新3個月后的王建滿在溫州燒起了“一把火”。他率領溫州官員前往上海、嘉興、杭州考察。
“正好是108人,我們笑稱108將”,王建滿回憶起去年的這個行動,感慨頗深。他說,這次考察主要是統一認識,解決溫州招商引資的“該不該、要不要、能不能、對不對”的問題。
返回溫州當天,王建滿召開“千人大會”。他在會上首次大張旗鼓地向外界公布了他醫治溫州經濟的猛藥——招商引資。從四面八方趕來的與會者,多數都被王建滿的一席話搞懵了。
招商引資,對于全國任何城市、任何一屆政府來講,也許都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話題。但是一位溫州官員稱,這在溫州“史無前例,完全是破天荒”。
在王建滿之前,溫州政府主流的觀點一直是:不缺少資金的溫州沒有必要引進外資,而資本本身就帶有擴張性,溫州資金的大量外流是正常現象。也正因此,溫州不論從政府還是到企業,對于招商引資都沒有興趣,甚至沒有類似“招商局”的部門,只有一個被閑置的“開放辦”。
一時間,王建滿被視為溫州模式的終結者。然而王建滿卻并不這么看,他說:“我沒有推翻溫州模式。”
說到這里,他向記者舉了一個例子,“西湖很美,但依然要和錢塘江連通,這樣西湖水就活了,才能持續她的美麗”。在王建滿看來,民營經濟是溫州的發展優勢,但是不是只要民營經濟就夠了呢?
相反,王建滿認為自己是在完善、發展溫州模式。“我們的招商引資注重結構調整,溫州豐厚的民資并不意味著就可以把結構調整過來,所以,有錢不一定能把結構調整好,我們溫州的招商引資,錢、量不是主攻目標,而是要解決溫州粗放式增長方式的問題”。
從來都不是“小政府”
對王建滿的質疑多數基于這樣一個判斷,溫州經濟有95%是由民營經濟構成,溫州經濟完全依靠民間力量推動,數年來政府一直被認為是“無為而治”。
“溫州正處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期。”他解釋說,一是產業發展難以為繼,二是要素難以為繼,三是環境承載難以為繼。而要改變這種境況,“政府應該有所作為,不‘騰籠換鳥’的話,溫州經濟就沒有出路。”
而至于政府有為或無為,王建滿認為并非溫州模式的特點。他說:“要基于溫州發展的歷史階段,政府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為。”
有學者認為,從溫州1980年代的第一任市委書記袁芳烈開始,溫州政府變成了一個小政府、弱政府,更多的人將溫州政府的無為而治歸結為溫州模式的核心特點。
但袁芳烈說,說溫州政府是無為而治,這是貶低、不對的。我把烏紗帽掛在褲腰帶上頂風做事,這是最大的有為。
無為還是有為,一切基于時機。從這點來看,袁芳烈與王建滿的觀點是一致的。
今年已經76歲的袁芳烈精神依然矍鑠,說話聲音洪亮,思路清晰,記憶力驚人的好。而每每談起溫州模式,說到當年的改革過程,他語速極快,許多施政例子隨手拈來,恍如昨日。
袁芳烈認為,所有對溫州模式的解讀都忽視了一個歷史細節:溫州模式發軔之初的一場同樣來自政府的變革。用袁芳烈的話說就是“民主整頓吏治”。
“當年省委派我去,就是為了徹底解決溫州的領導班子問題、組織問題。”袁芳烈這樣回憶他當年南下溫州的使命。這位當時浙江省最年輕的副省長甫到溫州后才發現,情況比想象中更糟。
袁芳烈回憶說:“當時溫州有兩套領導班子:溫州地委和溫州市委,都歸省委管,誰也不服誰。”而擺在袁芳烈面前的最大問題就是地市合并,必然牽涉到精簡多余的人。問題是機關干部都去考慮這個問題,誰還考慮工作?
經過袁芳烈大刀闊斧地“民主整頓吏治”,建立起穩定、精干的溫州干部隊伍,為接下來順利推行溫州模式提供了強力的政府保證。袁問道:“你說這是有為還是無為?”
歷史和現實開了個玩笑。至今絕大多數研究溫州模式、忽視了這個細節,也使得溫州模式“無為而治”得以流傳。袁芳烈反問:“不發展叫什么溫州模式?什么叫大政府什么叫小政府?溫州模式不是一成不變的。”
他感慨:“無為也是為,甚至無為比為更加需要勇氣和魄力。”
溫州模式:鏡像與拯救
被誤讀的何止是政府的角色。
多少年來,各樣的言語構成了誤讀溫州的兩端:“神化” 和“妖魔化”。神化者以為溫州人有點石成金之妙,妖魔化者以為溫州人是毒蛇猛獸。
一個如炒房團、炒煤團,譽之者以為是順資本意志而動的明智之舉,激活了當地的市場神經;毀之者譏之為市場經濟的蝗蟲,亂了一方的安寧,須先拿下而后快。
處于溫州模式中的溫州人,也難免被誤讀。只要是溫州人,一律被視為富豪。
而顯然并非真相。王建滿說:“溫州的文成、泰順、永嘉、平陽等縣,還有一些鄉鎮經濟仍欠發達。我們做了一個統計,發現整個溫州還有139個鄉鎮的人均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在所有對溫州模式單一的非此即彼的判斷中,溫州模式已經不屬于溫州。
溫州模式只是活在鏡像中。從這點,溫州模式一直處于他者的視界中,而由此,如果要對溫州模式進行拯救,力量也來自與溫州之外的他者。
這也正是王建滿的困境。
從袁芳烈時期便開始參與溫州模式發展,其后曾經擔任溫州市發改委主任、溫州市委政研室主任的馬津龍認為,溫州經濟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改革的先發優勢,但這只是體制外的改革優勢。
他說,現在像溫州這樣的市場化領先地區,凡是可以依靠底層力量推動、老百姓能夠做的微觀領域的制度創新基本上都已經完成。當改革深入到體制內階段時,變遷已經不可能自動完成,“它需要政府采取主動”。
但與王建滿不同,馬所說的“政府采取主動”是指,現在溫州的先發優勢不再,凡是可以靠底層力量推動的制度創新,在溫州已經完成。現在溫州遇到的創新,不是地方政府能左右,而是需要國家層面去推動。
馬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金融創新,一個是投融資體制。溫州現在的民間資金達到2800多億,怎樣利用起這些民間資金,政府遲遲拿不出個辦法。
拿金融創新來說,溫州市2002年底爭取到了國家的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但是三年時間快過去了,除了對浮動利率進行改革之外,民間銀行等鮮有成果。
一位溫州市的官員感慨:“如果不給豐厚的溫州民間資本一條正確出路的話,炒房團、炒煤團的故事還會繼續發生。”
顯然,要拯救所謂的“溫州模式”,不能只靠溫州,更大的力量來自于溫州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