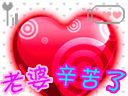|
文/羽良
2005年12月17日,四川省廣元市政府新聞辦公室發布了一條引人注目的消息。即日起,廣元市第一家民間小額貸款公司正式向海內外招標。其實,對于一直關注國內民間金融發展的人來說,“廣元試點”并非突如其來。早在2005年2月,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就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上表示,要“放松借貸管制,促進社會資金融通”。到了10月份,吳曉靈更是
向外界透露了央行對“社會資金融通”的政策方針:鼓勵民間資本成立小額貸款公司,原則是“只貸不存”。最終,在得到央行、銀監會和四川省政府等多個部門批準后,廣元成為計劃中的西部五省試點的“破題”城市。
廣元試點,破題之舉的尷尬
“廣元試點”的出臺,至少在名義上,為困擾中國金融體制多年的“地下信貸如何轉正”的問題提供了一次真正的解決契機。然而,就在媒體報道“廣元試點”的當天,筆者和北京一位從事投融資生意多年的朋友提及此事,問他做為“圈里人”的看法。沒想到朋友一搖頭,說道:“叫好不叫座,恐怕搞不起來。包括信貸業務在內,地下金融走向地上,最大的經營風險不是別的,而是要服從目前的政策監管。”
不服從政策監管,又何談“轉正”之說?這聽上去多少有些滑稽。這位朋友對此進一步做了解釋。他說,地下金融的模式有很多種,類似“廣元試點”這樣以中小民營企業為對象提供短期融資的業務,地下錢莊、合會這樣的地下金融組織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但是,地下金融的企業融資服務呈現出的是市場高度分割、交易信息高度黑箱化,貸款條件大多是不符合現行法律法規的“灰色契約”,而對融資企業的風險監控手段則是以數家連坐、一損俱損的方式為主。
以目前了解到的模式來說,地下錢莊、合會這樣的地下信貸組織,其所提供融資服務的對象非常集中,往往是建立在親緣、血緣這種“熟人社會”基礎之上。服務對象的平均規模為一家錢莊或者合會,對應著十幾家固定的企業。為了降低資金風險,一家企業需要資金找到錢莊或者合會融資時,除了要支付超出正規金融機構利率的利息外,除融資企業以外的另外那些家企業亦自動承擔資金擔保的風險。假如融資企業出現惡意騙貸或者惡意損害提供融資方的情況,其他那些企業要為融資企業帶來的壞賬買單。
事實上,除了上述企業層面的“連坐”,自然少不了對責任人“道德風險”的控制手段。“非常簡單,一旦出現企業所有者騙貸或者惡意損貸的情況,那么他就只能從當地迅速逃離,并且要保證自己能夠永遠不再回來。否則,沒人能保證他的安全。”朋友解釋說。
當然,錢莊、合會這樣的地下信貸組織絕非僅僅靠嚴酷的事后懲罰措施控制自身放貸的風險。僅就筆者了解的情況來看,國內各個地下金融活動發達的地區,都會根據其當地人員結構、企業特點、資金使用方式,發展出各自頗為不同的貸款風險評估和控制方法。這些經驗性的,甚至有點兒“土”的控制風險手段,一方面顯示出國內地下金融從業者某些天生的經營創造性,另一方面,這些不夠合規甚至很多不夠合法的“地下規則”,也足以說明對于這些地下金融組織來說,“最大的經營風險是要服從政策監管”。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一下“廣元試點”的政策,“小額貸款公司注冊資本不得低于500萬人民幣。不得吸納社會存款,其發放的主要是信用貸款,單戶貸款額不超過其注冊資本的2%,貸款期限不超過1年。具體的貸款利率將由公司與借款人雙方私下協商,但不能超過央行同期基準利率的4倍。由于小額貸款公司目前不屬于金融機構,將由人民銀行對其實施非審慎性監管。”此外,據報道,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廣元市,每年有1.7億元人民幣的發展資金缺口。
這意味著,無論誰接下“廣元試點”的頭標,其服務對象都將是當地農業經濟特征明顯的中小企業,這與國內地下金融組織以參與制造業企業經營活動的總體趨勢并不相符。換句話說,農業產業的企業利潤低,且對于“廣元試點”而言,貸款公司開展業務在某種程度上還帶有了些許對“三農”的政策扶持色彩。
果然,原本從12月17日到26日的招標時間,被延長到2005年12月30日。即便如此,也是看客多,真正報名的寥寥無幾。
中小民營企業融資困局
“廣元試點”的背后,是困擾中國經濟多時的民營經濟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饑渴”。那么,中國的民營經濟融資領域到底有多“饑渴”?根據2001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助理教授Kellee Tsai的一項研究(Beyond Banks: The Local Logic of Informal Finance an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China),自建國以來到1998年,國有銀行的貸款只有0.4%流向了私有部門。在其研究樣本所選擇的1996-1997年,甚至有88%的民營企業根本無法從正式的金融部門貸到一分錢。
無獨有偶,2005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和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聯合調研編寫的《中國中小企業金融制度報告》發布,報告顯示的情況并不令人樂觀。以國有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信貸體系,對中小企業的市場開放雖然較以前有所提高,但開放的領域基本上局限于短期信貸業務。這些企業的中長期貸款需求并沒有得到滿足。
此外,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做大的民營名牌企業在信貸市場上已經獲得了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同樣的待遇,甚至在很多地方,這類民營企業已經成為當地信貸市場的搶手貨。而對于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因為信用等級過低、缺乏可抵押資產、財務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幾乎無法從銀行部門獲得貸款。國內信用擔保機構在幫助中小企業獲得貸款方面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9月末,報告所取樣本地區平均有76%的樣本企業沒有和任何擔保機構建立過信用擔保關系。樣本企業中擔保貸款余額僅占到全部貸款余額的6%。
在正規的外部融資渠道不暢的情況下,大多數民營中小企業都要求助于其他融資方式。在Kellee Tsai的研究中,1999年有90.5%的民營企業要靠“自籌”的方式來解決融資需要。而在央行的報告中,溫州地區小型企業通過向親友借款和內部集資方式融資的分別為68.6%和45.7%,中型企業這個比例為45.8%和41%。
早在20世紀30年代,英國議員邁克米蘭便曾向英國國會提交過一份關于當時英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調查報告。并在報告中提出了中小企業融資的“金融缺口”問題,即企業外援性資本需求低于一定規模時,便難以在資本市場上融到資金。時至今日,“金融缺口”的問題依然在世界各國存在。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博士后研究員劉明興的介紹,在美國小企業的融資結構中,股本融資平均占49.63%,債務融資平均為50.37%,債務融資由金融機構的貸款(26.66%)和非金融機構、個人、政府的信用(23.71%)構成。在小企業從金融機構獲得的貸款中,有抵押的貸款占91.94%。商業銀行貸款在小企業融資結構中的比重為18.75%,其中有抵押的貸款占91.99%。
而在國內,根據央行的調查,目前國內中小企業融資需求在200萬元人民幣以下的時候,很難得到銀行貸款。這其中的原因多種多樣,首要的問題是國內中小企業大多缺乏足夠的不動產作為貸款抵押,這是與美國的情況截然不同之處。而信用擔保作為解決中小企業缺乏抵押品進行貸款的主要方法,并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相比之下,日本作為成功建立起信用擔保制度的國家,有著諸多中國可以學習借鑒的地方。目前,中國全國1000多家信用擔保機構,不僅存在著基金規模小、放大倍率低的硬件缺陷。更本質的問題在于,國內的信用擔保體系缺乏一個具體有效的政策環境支持。按照JICA的建議總結,中國目前的信用擔保機構存在著缺乏嚴格區分、缺乏全國性整合、未形成統一的信用擔保制度、缺乏再擔保制度四大缺陷。同時,不僅沒有考慮通過制定相應的社會政策,推進信用擔保體系的完善和深入,甚至為具體法規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管理辦法》也尚未出臺。
缺乏可用于貸款抵押的資產,信用擔保體系乏力,加上眾所周知的國有金融信貸機構對金融資源的壟斷以及長期以來對中小型民營企業的信貸歧視。致使國內的中小民營企業不得不依靠非正規的(地下)金融手段獲取急需的資金。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為這些中小企業提供資金的非正規金融機構長期以來得不到法律上的確認和規范,以至于始終難以建立起有效的中小企業金融監管秩序。由此造成的惡果便是,非法集資等金融詐騙案件時有發生。更為嚴重的是,司法界定上的空白帶來的企業“灰色”融資行為,為民營企業家增加了巨大的法律風險。2003年下半年發生的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及其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便是這類風險的典型案例。
在缺乏最高人民法院對刑法中有關“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條款司法解釋的情況下,河北省徐水縣人民法院做出了孫大午及其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名成立的判罰。案件發生前后,國內多位法律和經濟學專家相繼撰文指出,孫大午的行為客觀上可視為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最終判決的差強人意,除了現行司法體制本身的一些缺陷影響了判決的結果之外,企業民間融資行為立法不足,監管不力的尷尬被孫大午案徹底暴露出來。更進一步來看,孫大午及其集團公司在整個兒融資過程中那些頗具創造性和極佳操作性的融資手段,完全可以視為一種積極的企業金融創新。可惜,這種自發秩序下的創新產物也最終被無情扼殺。
地下信貸轉正之路如何走?
2005年9月,由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李建軍主持的《中國地下金融規模與宏觀經濟影響研究》(以下簡稱《研究》)課題報告正式發布。作為國內第一份全面研究中國地下金融成因、現狀,并對總體規模和宏觀經濟影響進行實證計量的報告,《研究》對國內地下信貸規模做出了一個謹慎的估算:截至2003年,國內地下信貸規模總計7462.4億元人民幣,占當年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4.7%,達到當年GDP的6.4%。
盡管《研究》的作者們得出的結論是政府可以通過控制信貸和利率政策,來間接控制地下信貸的規模。但與成熟的金融體制所不同的是,這種間接控制顯得相當被動,政府和中央銀行對近7500億人民幣的貸款缺乏實質性的監管能力。近年來,媒體對諸如“標會”惡意“倒會”等以地下信貸機構為幌子出現的金融犯罪做了大量報道。如何將地下信貸乃至整個地下金融產業轉入地上,成為關心中國經濟的人近年來的一大討論熱點。
其實,中國的地下信貸組織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和市場環境,相比歐美發達國家,與東亞近鄰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省等地區都更為接近。回顧日韓兩國和中國臺灣省的地下信貸組織轉型歷史,不難發現,其實除了已經開始進行的“廣元試點”這樣的政策新設型模式之外,還有一條更市場化的轉正道路。
根據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員Pairault博士的研究。中國臺灣省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民間合會雖然不是當時臺灣中小企業主要的融資渠道,但是卻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影響最大。對當時的小企業主來說,召集或加入合會是獲得貸款的一個草根策略,合會不僅提供了足以滿足資金周轉需求的短期小額貸款,而且可以使這個人獲得合會的擔保。日本殖民政府于1916年在臺灣頒布《合會儲蓄公司法》標志著合會儲蓄公司走向正規化,并被納入中央銀行的管理范疇。
到了1948年,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地區頒布了《合會儲蓄業管理規則》。根據這項規則,七家私有合會儲蓄公司獲準在島內按照規定的經營范圍和地區劃分運營。只有“國有”合會儲蓄公司才可以在全島經營合會業務。到了1956年,一項關于使用會員抽簽方式決定當期會金歸屬的決定,給臺灣地區合會儲蓄公司的未來發展帶來了根本性的轉折。因為這一方式不僅有利于降低競標所帶來的高額成本,以杜絕出現博傻一樣的借貸欺詐,更有利于將合會儲蓄公司由信貸機構轉變為儲蓄機構。也正是由于后一個轉變,合會儲蓄公司扮演的發放貸款的角色,使得它最終于1976年被臺灣國民黨政府升級為銀行。此后,臺灣又經歷了中小企業銀行組建合會,帶來了合會行為銀行化直至1995年合會業務自然消亡。
在回顧了臺灣地區的合會發展史后,Pairault博士認為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省的歷史經驗證明,一國(地區)的持續經濟發展絕不僅僅依賴于標準金融理論所單純強調的“現代金融部門深化”,而可能更多地依賴于其固有的“傳統的”、“民間的”和“非正規”金融體系。應該說,這樣一個結論有著相當大的政策啟發性。而且,改革開放以來地下信貸活動最為活躍的地區——浙江溫州,其自身地下金融部門的發展歷史,便在很大程度上與臺灣地區合會史相吻合。這一點,無論是在海外學者如Kellee Tsai的研究中,還是國內官方機構對溫州地下信貸活動進行的案例調查中,都得到了一些驗證。
當然,地下信貸組織的轉正之路絕非照搬任何現成的經驗案例就能一蹴而就。而尚未轉正的國內地下信貸組織對于中國的金融體系而言,到底能不能成為熊彼特意義上的“創造性破壞”,人們也將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