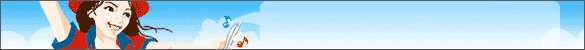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一個目睹曹文莊被帶走“協助調查”整個經過的知情人士描述這事件,用的形容詞是“錯愕”,從2006年1月15日過后,他和曹文莊接連在年底中國藥學會和藥監局舉辦的總結會上碰頭。“他是個喜歡烘托氣氛的人,一旦興致來了就很活躍。看得出那幾天他心情很不錯,在中國藥學會舉辦的聯歡會上他還自告奮勇地上臺表演了詩朗誦,他說話很有感染力。”
讓該知情者覺得錯愕的主要原因是,“從以前到現在,很多人看好曹文莊,他年輕,
才40多歲就當了藥監局注冊司司長”。
可是在1月12日,曹文莊出席了在北京郊區寬溝召開的“2006年全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工作會議”,“按照流程,晚飯后接著開會,才剛做完第一個報告,有人低著身子走到曹文莊、盧愛英、王國榮等數位司局級干部以及3位藥品注冊司的處級干部旁邊,然后他們紛紛起身離開,大約共有7人。直到散會時候聽到說法,曹文莊他們是被紀檢監察機關帶走的,大家一下子議論紛紛,畢竟帶走的是國家藥監督核心部門注冊司司長和助理巡視員、原注冊司化藥處處長、國家藥典委員會秘書長等最敏感幾個部門的工作人員,最主要的,他們負責的工作都和新藥審批有直接關系”。
直到目前所能確認的進一步消息是,就在2月15日左右,國家已經正式委派原北京市藥監局一位副局長接任曹文莊的職務,而截止到記者發稿,還沒有相關檢查部門對這一事件做最后定性的通報。
記者 蔡崇達
注冊司司長:越來越絕對的權力
“以前我們的工作完全是規定框好的,就一個復查的工作流程,沒有太多空間,談不上能有什么巨大的開拓,就求個本職工作做好。”2月17日下午,目前在香港任職的、曹文莊前任,國家藥監局注冊司前司長張世臣在電話里對記者這么說。根據他的介紹,“1985年開始實施的《藥品管理法》規定,新藥審批在國家一級,仿制藥品及保健藥品的審批在省一級”。而當時的仿制藥品未列入新藥大都在地方審批,中國自己研發的新藥數目從來就較少,所以國家藥監局注冊司在張世臣任職時候,權力確實僅在于一年批準100個項目左右的新藥的復核工作。
注冊司司長的職務管轄范圍和權力在曹文莊任內有了一定改變。中國醫藥工業總公司原總工程師、中國化學工業協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俞觀文在醫藥系統工作近50年,他給記者分析了整個過程:“1996年4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各省級衛生行政部門要對已經批準生產的藥品進行清理整頓,在清理整頓期間暫停批準仿制已有批準文號的藥品及保健藥品。所以,藥品審評從那時候開始已經是國家一級審評。”
“不過這個通知在實施時候遇到困難,當時之所以推出這個規定有個目的,此前由于仿制藥品及保健藥品的審批在省一級,各省都有較多藥廠,甚至有些地方大部分縣都有,有時候一個地方經濟支柱就來自藥廠,而藥廠利潤來自藥品銷售,所以出現一種受歡迎的藥物,各藥廠就齊擁而上。這些藥絕大部分是仿制藥,仿制藥的審批權如果在地方,各省會因照顧地方經濟大開綠燈。據2000年對全國進行調查,有15個省(區、市)在國辦發14號文件下發后仍批準了710個藥品。”俞觀文說,“這就造成藥品低水平重復生產,同品種競相仿制,徘徊在低水平地搶時間和低價格上,獲利模式是那種薄利低水平重復,根本沒有藥廠有精力和能力進行新藥研發,長期下去中國藥品根本上不去。”
改變是在2002年,喜歡寫文章的曹文莊曾在2002年的總結中提到,“為了嚴格藥品審批,確保人民用藥安全有效,修訂的《藥品管理法》第29、31、33、39條明確了新藥、仿制藥品、進口藥品都必須由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審批,取消了地方批藥的權力”。而曹文莊也正是在這一年正式接任藥監局注冊司司長。
俞觀文認為,之所以在這個改革時刻選擇曹文莊,在于“當時大家普遍看好曹文莊。曹文莊1984年從黑龍江省商學院中藥系畢業后進中國藥學會工作,因為能寫文章,做事認真一直受關注,1988年他調入原國家醫藥管理局工作,任秘書。從一個副局長秘書到接任局長的秘書,后來任辦公室主任、人事勞動司司長。1998年成立藥監局后,他任藥監局人事司司長、辦公室主任,2002年任命他為注冊司司長。應當說當時藥監局對他有充分期望”。事實上,藥監局在1998年從醫藥局到獨立的部級單位改造重組后,包括對藥品的生產、經營、流通等管轄權已經分割出去,最有價值的權力就在新藥注冊。“而這也是藥監局作為監督部門一個起監督作用的重要手段。”俞觀文說。
“當時曹文莊的任務應該很明確,就是通過對藥品注冊審批的管理,改變中國藥品低水平惡性競爭,提高藥廠科研能力,促進中國藥業真正發展。所以可以理解,為什么在藥品審批權集中上交到國家藥監局注冊司的同時,也緊接著出臺的《藥品管理法實施辦法》,對新藥的定義和審批流程重新梳理。這次梳理可以說也是為注冊司更有力量去掌握局勢。”俞觀文說。
曹文莊在2003年6月曾經對《醫藥經濟報》詳細分析過按新規定國家藥監督局注冊司集中的權力是:“1.生產新藥或者已有國家標準的藥品,須經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并發給批準文號,藥品生產企業在取得藥品批準文號后,方可生產該藥品。2.研制新藥,必須按照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規定,如實報送研制方法、質量指標、藥理及毒理試驗結果等有關資料和樣品,經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后,方可進行臨床試驗。完成臨床試驗并通過審批的新藥,由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發給新藥證書。3.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組織藥學、醫學和其他技術人員,對新藥進行審評。”
“也就是說,一方面新藥從準備申請審批到審批生產的全過程都要經過國家藥監局注冊司的批準,每個環節的標準都交給注冊司。另一方面,即使是已經批準過的藥,也要全部重新由國家藥監局注冊司審核,周期是5年一次,注冊司可以在重新審核時候,重新掂量這種藥是否有繼續生產的必要。注冊司的權力于是得到強化,比如說,福建、江蘇生產同一類藥品主要成分是一樣的,但他們以前生產的標準由于是地方審批是不一樣的,要定福建的標準那江蘇的許多廠就要改造,這需要花費成本,需要改造時間,需要重新審核,而福建的廠就可以在競爭對手缺席的情況下擴大經營。再比如說,同一種藥福建和江蘇同時有廠提出申請,越早審批通過越早搶占市場,在注冊司的工作流程下,誰能先審批通過誰就搶了先機。可以這么說,藥監局強化注冊司的權力是可以理解的,1998年改組后,藥監局最大的權力本來就只在于新藥注冊,國家這樣的調整就是寄希望通過新藥注冊監管醫藥行業,促使這個行業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新藥注冊:藥廠壓力的尋租出口
與此同時,藥廠的壓力和不良競爭卻越演越烈。“中國醫藥有個最基礎的問題就是藥廠太多,太小,龐大的美國市場上只有約200家流通企業,大的供應商不到10家;而中國有17000家流通企業、6700家生產企業。”中國醫藥企業競爭力研究課題組專家委主任、北京康派特醫藥經濟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磊對記者說。
“藥廠多造成的問題在于,中小藥廠為了求生存,會在低水平的藥品上競爭激烈。舉個數據,跨國制藥公司科研開發費占銷售額的15%~20%,銷售利潤率在20%左右;而我國醫藥企業因為科研開發費僅為銷售額的1%,銷售利潤率只有7%~8%。而且中國所有藥廠的產值加起來還不如美國一家大藥廠,根本就沒有辦法競爭。”俞觀文說。
2000年開始,國家藥監局開始推行GMP。“所謂GMP說得通俗些,就是在藥廠的規模和生產能力上提高門檻,GMP認證花費高昂,單個車間通過認證就需要800萬~1500萬的資本投入。這個舉措當時想的是一石二鳥,關掉大量中小藥廠,讓大藥廠更能贏利,有足夠的資金投入科研、升級,另一個是保障藥品安全。”李磊分析說。
但是中國的實際情況是,藥廠絕不是通過提高門檻能關掉的。“我國的藥廠分布有個背景,從1959年開始,按計劃經濟那種平均的原則,開始在各省分別建立作用類似的化學制藥工業。1979改革開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開始對藥品需求增多,許多省又開始鼓勵興辦藥廠,而且許多藥廠是地方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資金的,是地方經濟命脈,關掉一個藥廠意味著背后一個地方經濟的虧損。”俞觀文說
在那種背景下,很多地方選擇的是,由政府出面向銀行貸款讓地方的藥企得以改造。“所以最終推行GMP的結果是,全國7000多家藥廠淘汰了將近1500家,可通過GMP認證之后的40%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但是GMP改造后由于對生產規模的強制要求,每家藥廠生產能力擴大了3倍,產生的過剩產能達到2000多個億。”李磊對記者說,“為順利過關,很多企業是不惜血本,勒緊腰帶湊集資金進行GMP改造。全國醫藥企業為通過GMP花費了1400億元,大部分藥企背上了巨額銀行貸款,比如三九醫藥公司就向銀行借有數百億。”李磊表示,成倍的產能擴張、巨大的財務壓力都需要擴大產品營銷緩解,而在國內需求穩定和出口有限的情況下,市場原本出現的低效、低價競爭更加激烈。
“與此同時,從1997年起至2003年底,國家14次大幅度降低藥品價格,工業利潤不斷削弱;而醫用原料漲價和‘治超’導致的運輸成本激增等各方面因素,也使得不少通過GMP認證的企業在市場上感覺步履維艱。而這時候,國家發改委為貫徹減輕群眾負擔對一些常用藥給予硬性定價,逼得許多企業開始尋找出路。”李磊說。
當時很多藥企不約而同打起了新藥的主意。因為一方面國家為了鼓勵新藥研發,新藥價格國家沒有控制可以自由定價;另一方面新藥因為生產的廠家少可能更好銷售。“這本來是藥監局所期望達到的效果,可在當時低水平競爭和產業底子本來落后情況下,中國藥廠根本沒有足夠實力和國外藥企在真正的新藥上直接競爭。”而且以前的政策也讓企業有了鉆空子的機會,在審批權還沒有統一上交到國家前,藥監局為加大管理力度擴大自己審批監督范圍,規定國內上市的藥品定義為新藥外,改變給藥途徑和增加適應癥的這類嚴格意義上的仿制藥按新藥管理,到了2002年修改規定后這一條還是被保留了下來,“這給了仿制藥可以當作新藥審批的空間”。
時任藥監局局長的鄭筱萸在出席全國藥品注冊工作座談會時曾指出過這種現象:“不具備研制新藥能力的企業轉向仿制尋找出路,而擬仿制申請要求簡單,不需做技術工作,有的單位一次報來十幾甚至二十幾個擬仿制申請表,他們抱著批下來哪個做哪個的心理。”還有相當企業試圖通過加個成分,注冊個新藥品,然后就轉身變成定價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新藥牟利。比如人人皆知的阿司匹林,每片僅0.03元,不少醫院已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價藥“巴米爾”,每10片6.3元,其成分也就是單一的阿司匹林,而價格一下子漲了20倍。
這樣幾乎所有權力都集中到負責新藥審批的注冊司上。而新藥審批在統一到注冊司后大概有三個主要流程,一報給注冊司底下的審評中心。審評中心負責審評材料提交的格式和方式,然后上交給注冊司,注冊司再從自己的專家團里組織相關專家論證,是否有批新藥的必要,以及工藝上是否達到安全。如果不通過就打回,通過了就重新提交到注冊司,注冊司在專家研究的基礎上審批是進入一級臨床、二級臨床、三級臨床或者可以直接生產。如果要進入一級臨床,就到各個地方藥監局指定臨床基地,通過了一級再返回到下一級,只有全部通過然后才能生產。
“由于臨床基地大部分是在地方,所以藥企和他們的關系一般比較好,最關鍵的把握還在于注冊司組織的專家團以及它的審批意見,在這種背景下,即使是新藥也是同類競爭,你通不通過,以及以怎樣的速度通過就關系重大了。比如同一個產品,甲是直接進入生產,乙是進入一級臨床,等乙最終可以生產的時候,甲早就占據市場了。”李磊對記者分析說。而事實上即使按規定,新藥審批也確實可以給企業方便的彈性,“一是暫時手續不全,爭取提前通過,之后再一一補齊;二是產品尚處于臨床試驗階段時,就把許多本應該依照不同時間段按部就班的手續全部辦妥,待臨床試驗剛一通過,產品就能夠立即推向市場。這中間,就給了一些單位運作的可能。”
對這種現象,當時鄭筱萸還特別提出工作指示:“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注冊司要繼續下大力氣采取措施予以控制。”而這就是剛上任的曹文莊面對的狀況。
“標準”背后的隱晦空間
從2002年到2003年發生了什么?據中醫藥在線2004年2月20日的數據,2003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共受理各類藥品注冊申請17000多份,全年共審批新藥注冊申請6806份,比上年增加128.5%。其中,批準新藥臨床研究申請4222份,比上年增加346.3%;批準生產申請1351份,比上年增加66.4%。而這些申請大部分是2003年下半年通過的。
這種現象的出現,按俞觀文的分析是,“當時國家正掀起法治風,落實到藥監局就是要以法治藥。我記得當時鄭筱萸局長在貫徹中央精神的時候解釋過,所謂以法治藥就是國家規定的就要嚴格執行,國家沒規定的就不能辦”。
“有一個令人窘迫的事實,藥監局審批新藥依據的精神其實是沒有寫入法律的。從一開始的醫藥管理局到藥監局,當時新藥審批有個默認的規矩,就是一般同一種新藥批準不超過3家。當時隨著藥廠的壓力增加,時常有各地領導到處運作。等到了2003年下半年,大量藥廠開始反彈。”俞觀文說。所以就出現了一種情況,本來各省藥廠沒有具體的方向分工,生產的藥品大部分類似,以前可以控制只給3家,到那時候,你要是批了一個就上百家甚至千家企業全部要批。
“失守的同時也造成了另一次同質競爭,結果最終還是在營銷上競爭,而且這些藥大部分國家并沒有強制定價,所以就出現了各種用回扣、折扣甚至不法的方式推銷。在這種情況下,注冊司對藥廠的存亡興衰也越加顯得舉足輕重,因為同質化,同類產品你讓誰先過,誰就先贏利,后面等一大批都過了一起競爭的時候,營銷成本肯定要提高,銷售肯定要下降。”俞觀文說。
“到了后來藥企競爭開始非理性化,許多小藥廠干脆砸鍋賣鐵就為了搞個新藥,這樣的生死關口,一個新藥及審批的快速與否,關系到的是一個廠幾千職工一個地方向銀行的上百萬貸款和這個地方靠藥廠的納稅和經濟拉動,它們拿出幾萬甚至幾十萬審批就不需要考慮了。”張光在哈爾濱一家藥企新藥注冊部門工作,他告訴記者,“我們廠后來干脆請一個審批公司代理,在北京北海附近,有大批代理審批的人,我們用超過十萬元的價格和他們簽了一個協議,協議中寫到,乙方(代理方)一定要保證新藥審批通過,并且最好是盡快通過。有的甚至規定具體時間,按時間收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