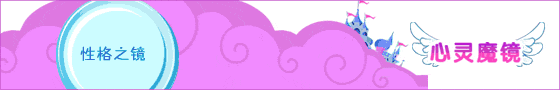回首分稅制:基層政府收入不平等加劇地區差距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1月10日 07:35 21世紀經濟報道 | ||||||||||||
|
中國的分稅制,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是一個不斷尋求完善的成長過程。 1994年建立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帶有強烈的制度創新性質。這次改革,初步理順了中央與地方之間主要是中央與省級之間的財力分配關系,大大淡化了政府與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控制,為政府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正確發揮調節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職能作用創造了條件。
但“一個體制的改革,一個制度的建立,剛剛建好就說它偉大得不得了,說它成功得不得了,影響大得不得了,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因為沒有經過實踐檢驗。但作為一個財政制度,經過10年的檢驗,現在回過頭看是可以給它做一點評價的。……” 10年過后,再回首。當年在政府果斷出手力挽狂瀾之后,中國平穩度過了亞太金融危機并進入持續發展的繁榮期。分稅制也在10年中漸漸顯出它的力不從心,甚至是某些弊端。比如對地方財政運轉的不良影響,比如轉移支付制度的不規范和隨之而來的鄉鎮財政困窘,比如在當前過多的政府層級下地方與中央之間事權與財權的博弈…… 一系列的變化似乎是某種改革的征兆或者先聲,最近,對分稅制的質疑和探討已經上升到國家的層面,健全公共財政體制,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責任,進一步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民族地區的財政支持已經成為現時的迫切之需。 或許,是到了一個檢討和深思的時候了,作為一個具有過渡性質的財政制度,分稅制的歷史使命將會持續多久? 從本期起,我們將推出分稅制十年的系列報道,敬請垂注。 ——編者 本報記者 孫雷 北京報道 1994年2月8日,農歷臘月三十,北京,七、八級間九級的大風。 窗外,北風呼嘯,壓得人透不過氣來。而此時,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項懷誠,則一直在財政部大樓里焦急不安地等待著那個關鍵時刻、關鍵數字的到來。許多天來,他常常失眠。 終于,一月份稅收數字報上來了——一月環比稅收增長61%。“我當時高興得無法形容。”在回顧那段難忘往事的時候,項懷誠內心的激動仍然難于掩飾。 61%,一個普普通通的數字。但它卻使得那些參與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人們在那一刻,“可以喘一口氣了”。對于新中國55年財政史來說,成敗榮辱,苦辣酸甜,這個數字意味著太多太多…… 分稅制前夜 時間推回到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斯時,中央財政陷入尷尬。 1980年代以后,中國出現持續性的高速經濟增長。1980年─1990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率為9.5%。 但是,經濟的高速增長并沒有帶動和促進國家財力的同步增長。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落后于稅源的增長速度。從1979年到1993年,我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有數據顯示,從1979年財政收入在GDP的比重為28.4%,到1993年已經下降到12.6%,大體上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還要多。 而另一方面,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也由1979年的46.8%下降為1993年的31.6%,中央財政的收支必須依靠地方財政的收入上解才能平衡。 由于中央財政收入嚴重不足,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甚至發生過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借錢”并且借而不還的事。1980年代中期“能源交通基金”,1989年的“預算調節基金”,都是為了維持中央財政正常運轉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實行“分灶吃飯”剛過一年,中央就連續兩年向地方“借款”,以維持支出的需要,以后的年度中,又宣布不僅“借款”不歸還了,還要把這一塊財力打進基數,即成為固定的(年年重復的)體制調整措施。到1980年代中期,中央在無奈之下推出“能源交通基金”,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10%(整體約100多億),來補充中央財政的不足。1989更加捉襟見肘,又出臺了 “預算調節基金”,同樣的口徑增收5%。而且當時每年財政會議之前,總要千方百計地出臺一些收費措施。 有專家分析,“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國是極其罕見的,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央政府調控能力的弱化和中央財政的被動局面,宏觀政策意圖的貫徹難以得到充分的財力保證。” 這是1993年,分稅制改革前夜。 上半年的一些指標發出警示,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全線吃緊:整個財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徑也僅僅持平;工商稅收140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12%,去掉出口退稅10%,僅比上年同期增長1.4%。而1993年上半年GDP增長達到14%,比1992年12.8%高出不少。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比例嚴重失衡。 稅收增幅小,開支卻大幅增長。幾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急呼缺錢:糧食收購財政虧損性補貼資金不到位;重點建設資金不到位,很多重點建設卡著脖子,如鐵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進度,重點建設資金上半年至少要撥付全年的40%,而1993上半年為19.5%,差了將近一半;重點生產企業和重點出口企業缺乏流動資金。而此時,需要由中央財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沒有地方能擠出錢來。 從前財政部在困難時向銀行借錢的法子現在也不靈了,因為當時分管銀行的朱镕基副總理已嚴正宣布,財政再困難也不能到銀行透支。當時已經到了不借錢連工資都發不出去的境地。 1993年7月23日,當時正值全國財政、稅務工作會議召開,朱镕基副總理來到會場,對所有參加會議的人員拋出一句典型的朱式警語:“在現行體制下,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現在不改革,中央財政的日子過不下去了,(如果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中央財政)就會垮臺!” 1994年1月1日,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在艱難時世中誕生。 從“財政包干”到“分稅制” 如果說中央財政的難以為繼直接催生了分稅制的降生的話,具有過渡性質的“財政包干”制與“條塊分割”地按照行政隸屬關系控制企業的舊體制相結合所造成的重重積弊,則是分稅制改革不得不改的更深層次的原因。 行政性分權的“財政包干”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主要財政模式,其要點是“劃分收支,分級包干”,并根據不同地區的情況,采取六種不同形式(收入遞增包干、總額分成、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上解額遞增包、定額上解、定額補助)。 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后,雄心勃勃地決定在中國建立一套完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作為其基礎的財政制度,從1950-1952年、1969-1970年在全國實行統收統支體制。其余年份則實行小有改動的分類分成或總額分成。80年代改革開放之后則開始實行“包干制”——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與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國企承包制一脈相承:“承包”是那時的改革主調。 “作為一種過渡性的財政制度,財政包干制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教授分析指出,這種體制在改革開放前期發揮了在傳統體制上打開漸進改革突破口,為后續許多方面改革提供操作空間的作用,同時擴大了地方政府財權,調動了地方政府理財和發展地區經濟的積極性。在“多勞多得”的刺激下,廣東、浙江等沿海地區經濟迅速崛起。 但另一方面,包干制與“條塊分割”地按照行政隸屬關系控制企業的舊體制相結合所造成的弊端也在日益顯露。 它相當程度上導致始終伴隨這一時期經濟發展,并且十分突出的重復建設、結構失調、地區封鎖、資源配置扭曲等問題,對于1993年的嚴重經濟過熱,包干制可謂難辭其咎。 專家指出,一方面,這種中央地方“分灶吃飯”的體制給予了地方政府投資權和財政收入處置權的擴大,使得地方政府投資動機空前高漲,而另一方面,“條塊分割”地按照行政隸屬關系控制企業的舊體制,又使得按照行政級別排隊的企業領導、各級官僚包括中央主管部委,更多地形成了各自局部化的利益共同體,而更多致力于憑借或依附與行政權力來增加局部利益,也極易形成明顯的互相攀比,而對企業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包盈不包虧”更進一步促成了不計后果的盲目開發和重復建,與此同時,中國的行政體制又不能對地方政府的行為有任何有效的制約,政府主導的投資過熱最終引發1993年的經濟過熱。 這一機制同時還刺激了生產流通的地區封鎖、地方保護主義,阻礙全國統一市場形成。當年“羊毛大戰”、“棉花大戰”、“桑蠶大戰”等此起彼伏,大有諸侯經濟之勢,包干制的“效應”不容忽視。 在地方各種形式的財政大包干中,關于收支基數、上繳或補貼數額都是通過中央與地方一對一的談判達成的,缺乏透明度,交易成本相當高。這種“討價還價”式的談判在以各種方式不斷延續,而每年年中和年終的財政工作會議,使討價還價達到高潮。 鑒于包干制的種種弊端,早在1980年代,中央就曾有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實行分稅制的意向,因為國外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證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分稅制所構筑的財稅管理體制將直接沖擊和破壞這種“條塊分割”的行政隸屬關系而使中央地方的財稅體制走向健康和自治。 這一考慮最早始于1986年。那年,決策層曾在國家機關和研究單位中安排了規模甚大、為時很長的“價格、稅收、財政”配套改革方案的設計工作,擬于1987年初出臺。該方案是一種力求理順價格信號并實行財政“分稅制”的思路。 但是,由于當時社會經濟環境沒有要求實施分稅制的動因,也不具備實施分稅制所要求的市場經濟財稅體制,特別是與宏觀層次配套改革相呼應的企業改革路子尚不清楚,同時又遭到了幾個省的強烈反對,因為這直接觸及到了地方的利益,結果,1986年底傳出消息:改革方案胎死腹中。 1990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建議》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間,有計劃地實施分稅制。鑒于當時的狀況還要不斷完善財政包干制,同年,財政部提出了“分稅包干”的體制方案。 1992年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后,分稅制再次被提出。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要逐步實行稅利分流和分稅制”。同年,中央選擇遼寧等九個省、市、區進行分稅制試點。 1993年,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分稅制改革被正式寫進《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稅制改革是這十個問題里的第四部分第18條。在分稅制改革的歷程上,十四屆三中全會“一錘定音”。 “共贏”三原則 從包干制到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這種變革直接關系到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調整。圍繞著分稅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央與地方的博弈貫穿始終。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分稅制改革既確保增加中央財力,又不損害地方利益?方案設計者絞盡腦汁。 1993年4月底,分稅制改革方案小組成立。在6、7、8三個月里,方案小組先后做了40多套方案,處理了幾十萬個數據,做了數千張表格。 據本報了解,方案的第一輪評估集中在中央層面,焦點則集中在有關增值稅方案的設計上,其中,增值稅共享、稅收基數返還和系數返還成為方案成敗的關鍵點。之所以如此看重增值稅,原因就在于,作為穩定的稅收來源,它將是稅制改革后最大的稅種,占整個稅收比重的43.7%,占流轉稅的75%。 反復討論的結果,“共贏”三原則得以最終確定:承認地方稅收基數全部返還,中央與地方按照75:25的比例分享增長增值稅,按照10.3系數返還辦法激勵地方增收。核心原則是“保地方利益,中央財政取之有度”。 同時,正是由于當時宏觀經濟形勢的處于經濟過熱時期,正在加大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力度,因此,最終采取了生產型增值稅而非消費型增值稅這樣一種形式,也為今日的增值稅轉型埋下了伏筆。 據說分稅制的主要推動者朱镕基曾對河北省委及財政廳的同志聲稱:這種改革是非常溫和的改革,地方既得利益沒有損害,而且退回去的不是“死面”,而是一塊“發面”,但是后來的過程已證明,因為牽涉到錯綜復雜的地方利益,真正要說服地方支持中央的這個方案卻絕非易事。 從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兩個多月的時間,朱镕基帶領60多人的大隊人馬,包括了體改辦、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及銀行等部門的同志,飛遍17個省、市、自治區,從南向北,第一站是海口,最后一站是河北,開始了大規模的調研、解釋、征求意見和談判工作。 在朱镕基開始他的這次“走南闖北”之前,一些地方便已對方案發出了強烈的“反對”信號。一些發達省份不同意搞分稅制,擔心會嚴重削弱其自身的經濟實力。而欠發達地區也提出異議,因為這些省份均為“煙酒財政”,長期靠“小煙”、“小酒”支撐,當時已經決定對小煙、小酒征收消費稅,按照分稅制的設計,消費稅增量100%歸中央。顯而易見,這些地區是“吃虧”的。新疆則提出,作為貧困地區,他們希望增加增值稅、消費稅的分成比例。 在這兩個月里,中央原定的分稅制方案在地方政府的強烈要求下不得不作出一系列調整、妥協與讓步。但實行全國統一分稅制改革的大原則,始終沒有動搖。 過渡性的財政制度? 分稅制改革的成效無疑是明顯的。如今,分稅制已經實行了整整10年,這是我國建國以來所實行的最穩定的一個財政體制。 1994年-2003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7.4%,其中,中央收入增長16.1%,地方收入增長19.3%。10年間,我國財政實力不斷增強,財政收入從分稅制改革前的5000多億元增加到如今的2萬多億,全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3年的18.6%。同時,2003年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54.6%,比1993年的39%提高了15.6個百分點。 “1994年建立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帶有強烈的制度創新性質。這次改革,初步理順了中央與地方之間主要是中央與省級之間的財力分配關系,大大淡化了政府與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控制,為政府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正確發揮調節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職能作用創造了條件。”賈康教授對分稅制改革給予了充分肯定。 “1994年分稅制改革是基于當時的歷史條件而搭起的一個制度框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它還需要不斷地完善。”一位長期從事財稅工作的官員這樣說。 中國的分稅制,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是一個不斷尋求完善的成長過程。 “中央財政收入規模的壯大,增強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財政部預算司司長張弘力在談到分稅制取得的成效時說。 “必須看到,該體制為種種條件所制約,帶有過渡色彩,留下不少問題。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問題趨于明朗化,對地方財政運轉的不良影響日漸突出。”在充分肯定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制度創新性的同時,賈康教授也談到了分稅制改革在完善中需要正視的問題。 在他看來,1994年的分稅制重新界定了中央、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和事權范圍,以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明確各級政府的責、權、錢,但當時還不能確定省以下政府之間的財力分配框架。而由于省以下體制改革的深化近年來并未取得明顯進展,財權與事權的劃分出現了相背離的局面。省以下政府層層向上集中資金,基本事權卻有所下移,特別是縣、鄉兩級政府,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基層政府財政困難。 分稅已定,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級政府只能在省內分稅發揮靈活性。部分省、市財政也打著“加強宏觀,中觀調控”的旗號,紛紛采取不同手段,集中一塊財力,形成了財權層層集中,事權紛紛下移的背反格局。 省級財政“二次”集中財力、市級財政“三級”集中財力,基層政府的財政困難進一步加劇,地方財政缺錢只能向當地企業和居民收費、攤派和集資。十年分稅,爭項目、爭資金、跑貸款、忙舉債幾乎成了基層政府的必然之舉。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層級過多,大大降低了收入劃分的可行性。我國現行稅種有28個,和其他國家比,為數不算少。但問題是,我國目前有五級政府,是世界上主要國家中政府層級最多的國家。過多的政府層級使得中國不可能像國外那樣完整地按稅種劃分收入,而只能加大共享收入。但同時,一味擴大共享部分又會反過來影響分稅分級財政基本框架的穩定。五級政府的架構,使分稅制在收入劃分方面難以真正實行,甚至可以說,不具備最低限度的可行性。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研究所楊之剛教授也認為,分稅制實施以來,中央財政已經具備充裕的財政自給能力,征收的收入除了滿足本級支出外,有相當一部分可以用于對地方政府實施轉移支付。雖然中央財政具備了向地方財政實施大規模轉移支付的財力基礎,但直至目前為止,轉移支付仍存在很多問題,地區差距的存在,導致基層政府收入來源的不平等;在轉移支付制度不規范的條件下,基層政府收入的不平等反過來又加劇了地區間的差距。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國內財經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