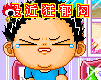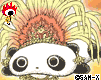中國城市化進入青春期 房地產是否套牢中國人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0月08日 14:16 新周刊 |
|
在民權意識尚未覺醒和成型的空白期,城市差不多已經定型了,市民對城市的設想和權益保護是缺席的,只有歷史會給大建設時期留下定論。 文/胡赳赳 “15”這個數字對2004年的中國人來說有絕佳的寓意:房地產市場發展15個年頭了; 如果此時要購房,那么總房款大約會是你年薪的15倍。人們并未意識到高昂房價背后的民權缺失,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披露,民權意識相對城市開發來說有30年的滯后期,2004年,滯后期演進到一半,正好又是一個15年。吳志強教授是上海同濟大學建筑與規劃學院院長,他在向《新周刊》拋出他的雙“S”曲線理論時,并未忘記從城市的角度喚醒人們疲憊的記憶:“一言以蔽之,城市是誰的?是市民的。不是官員的,更不是開發商的。” 雙“S”曲線理論形象地描述了一個“盛世危言”的場景:城市的大發展是一個“S”形,它從一個較低的平臺上啟動,然后進入高速發展期,最后趨于緩和定型,進入較高的平臺穩定期;民權意識的發展也是一個“S”形,也是由較低的平臺覺醒,進入快速覺悟階段,然后進入較高的平臺穩定期。 吳志強教授的研究表明,民權意識的發展較之城市開發建設的發展有30年的滯后性,30年的時間大約也是一個新型城市發展的關鍵期,這個時候盛行的是大軸線的規劃、大廣場的建設以及此伏彼起的大拆大建。 也就是說,在民權意識尚未覺醒和成形的空白期,城市差不多已經定型了,市民對城市的設想和權益保護是缺席的,只有歷史會給大建設時期留下定論。 現在,正是民權意識滯后的第15年,城市開發建設的關鍵年限也行進到一半,學者們認為,2003年諸多拆遷、房產糾紛案件的發生,正從普適角度反映了民權的缺席。在央視《今日說法》節目2003年的年終盤點“年度十大說法”中,涉及到房地產法規、維權與個案的事件就占了三席。 被房地產套牢的中國人,將2003年稱之為“拆遷維權年”。 誰的城市? 城市化是人類最偉大的事件之一,一個不斷增高的亞洲戴著“通俗城市”的面具在舞蹈,這既是一場偉大的實驗,同時也不乏痛苦的感覺。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進入了“青春期”。 有學者表示,回顧中國城市化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體現的是超強的國家意志,以大廣場、寬馬路、火柴盒式的建筑為特征,體現的是集權的建筑;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后,計劃經濟時代的配給制和市場化的商品交易先后出現,在不完全的自由市場和雙軌制度下,城市呈現的是膠著的狀態,在集權與市場之間擺渡;而第三個階段則以2003年為原點,在居住利益上爆發的維權事件,以及對城市規劃的空前關注,可以看作是民權意識的覺醒,這使得房地產市場回歸到市民本體成為可能。 在城市化的游戲規則中,開發商是重要的一個角色,學者丁東為此總結出“四方博弈”的結論:“城市開發建設是四方利益博弈的結果。官方、開發商、民間再加上傳媒及公共知識分子構成了博弈的四方。” 在四股力量中,官方是各方的調適平衡者;媒體則是監督者和評判者,但媒體本身有自己的多重特性,作為多方博弈的一個平臺,一方面受官方輿論導向的左右,還要接受開發商的廣告,另一方面要為百姓代言,傳遞知識分子的民間話語。故此,媒體作為城市化進程中的第四種力量卻被削弱了。而民間的力量因為缺少與官方和開發商等利益集團對話的途徑在博弈中處于弱勢地位。所以,剩下來的事情,只是兩方博弈,演變成官方和開發商的“二人轉”。 民間和傳媒的兩股勢力雖正在覺醒,但遠未形成氣候,未建構起有效的制衡平臺。在城市化的共謀中的缺失,被很多公共知識分子認作是“自身的尷尬”。 自身的尷尬來源于著名的“囚徒困境”。在四方博弈中,民間力量/代言者顯然具有與對方陣營官員/開發商的信息不對稱,在這種情況下,選擇“共謀城市”還是“放棄城市”就成為一個悖論。共謀城市是集體理性在起作用,而放棄城市是個體理性在起作用,在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較量中,顯然,放棄城市所付出的代價最少。居住在北京的丁東干脆直言:“我越來越不喜歡北京了。” 但城市有它的合謀者,在廣州做過樓市記者的董海斌到北京后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兩年后,他成為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戰略中心總經理。業界傳來消息證實,最近,他出任公司在北京順義區開發的某大型樓盤項目的總經理。 房地產在中國吸納了無數資金和人才的涌入,像董海斌這樣投身其中的并不在少數,他的主要工作是與政府主管部門、銀行和媒體“打交道”,這使他在朋友們面前常常顯得精疲力竭,作為既得利益的一方,他扮演著“開發商”這樣的角色。盡管迄今他并未購買私人住宅,但這是他的城市。 張寶全則是北京知名開發商,曾以“會吃的房子”的裝置藝術而名噪上一屆深圳住交會,在北京開發商隊伍中,他是公認的將房地產與文化形態結合得最好的人。他透露苦衷說:“開發商只有1/10的時間用來考慮怎樣蓋房子,9/10的時間都是用來協調各種關系、辦理各種手續、跑各個部門。”他表示,如果開發商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建筑本體的營造,那將會誕生好的城市建筑,而不是相反。 民眾的“地”位 當房地產行業以“居住改變中國”的姿態進入大眾的體驗空間時,這個行業的“影響力”就開始爆發了。 環境藝術家米丘認為,城市化發展及房地產行業的輻射力和影響面已經使之左右著民眾的生態。米丘表示,幾乎所有的城市人、所有的行業都在談論或是“直接進入”房地產,這是一個特別特殊的現象,這種規模、這種速度、這種集中釋放在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西方社會也未曾出現過。米丘能感受到房地產行業所帶來的影響,越來越多的開發商找他“直接進入”房地產創意和設計領域,這在前幾年則是沒有的。 每個人都變得與房地產行業有關,政府成了“地主”,房地產開發商成了城市運營商,市民成為業主,藝術家成為商用的環境藝術家。 “人人都在談論房地產!”一位藝術評論家有所感嘆地說,凡是吃飯聚到一起,好像永恒的話題就是房子、房子、房子。 北京大學一位中年女教師在餐桌上給朋友傳授她的“生意經”:她在清華大學附近交首付款買了一處房產,然而將新房裝修布置后租給韓國的兩個留學生住。 業主楊先生在杭州擁有一處兩居室的房子,又在上海購得了一處,他每個月的開支有一半投入到付房款的月供上,在找到一個更合適的工作前,他不得不選擇“炒更”。 城市的民眾被迫選擇了過一種“壓力”下的生活,最大的壓力就來源于“住房”問題,“你吃了嗎”的問候語被快速切換成“你買房了嗎”的語境。“安居樂業”的田園式圖景在都市里很難看到,大多數人是在職場上奮斗和打拼,尤其是在京、滬、廣等一線城市,居住成為“大不易”的事情。 除了樓盤的售價讓一般民眾身受“供樓”之苦外,房屋的質量也是一大問題。在北京樓市記者圈內,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買房子都是坑(陷阱),只不過有的坑大,有的坑小,就看你跳不跳。這句話起因于一位做過十年樓市報道的資深記者,以他的經驗和判斷,在買房時也遭遇到一件令他難堪的事:交房的時候他發現,買的單元房內竟然沒有下水通道。 越來越多的拆遷、物業、房屋買賣糾紛事件的發生是有其原因的,一方面人們維權意識和居住要求在提高,從簡單的受眾變成了參與者和市場主導者;另一方面,城市發展和房地產行業模式進入了一個相對固定和成型的階段,而人們對這個過早形成的現狀是不滿的。 盡管人們在為房地產現狀的不滿而喋喋不休,但同時,卻又因購買了某種代表生活方式的樓盤而沾沾自喜。這就是民眾的地位,雖然不能“我的地盤我做主”,但是作為消費者的苦辣酸甜都領略過。 即便是買到了稱心如意的房子,就意味著一切OK么?實際上你只有70年的產權。學者朱學勤表示,他在倫敦見到過一張為期999年產權的房契,他感到無比震撼,一個只有70年產權期限的城市發展如何能與之相提并論?房地產只有70年的命脈,這意味著,城市化的發展,將會以70年為一個周期輪番上演拆遷與建設的工地游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忽視了一個城市的歷史傳承和悠久根基。 知識界的發難 對于城市的開發建設,文化學者朱大可有他的哲學思考:“實際上中國多數城市建設都是權力、資本角力、合作和妥協的場所。權力美學以高、大、全的美學特征出現,表現在建筑上就是我高故我在、我大故我在。與國家主義美學相對應的是人本個人美學,我們應該提倡個人美學,以小街區對抗大馬路,以人的身高尺度來規劃人與建筑的關系。工業主義的哲學就是水泥化,全面覆蓋,以水泥顛覆土地。” 以水泥為基本建筑材料的房地產行業顯然更加具有商品的屬性,商品的特性之一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萬科的王石曾經表白說:“超過15%的利潤我不賺。”考慮到萬科是房地產行業杰出品牌的地位,如果反過來理解,那么房地產行業到底存在多大的利潤以及自由度可以依理推之。 具有強大吸附功能的房地產建筑,也許是個人所購買的最昂貴的商品,這件商品卻決定了個體的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他住在這個商品里面,感受到的也許是另外一種心境。 一位有過買房經驗和入住體驗的學者說:“小區草坪設計好了,房間格局是格式化的,你能夠做的不過是裝裝修擺擺家具。哪一天,等你搬出去的時候,你存在的所有信息立即歸零。就像電腦的格式化或是刷新,留不下你的任何痕跡。所以說,現代人沒有‘家’,只有‘公寓’;不是歸宿地,而是暫住地。不像以前的老家,等幾十年過后回去,還能找到自己的過去。工業時代的人們更有理由懷念舊的民居。” 城市的景觀和風貌正是由建筑支撐起來的龐大體系。然而,“千城一面”的局面的形成正是與大量建筑的毫無生氣、嚴重雷同、大量批發有關。 法國著名藝術策展人侯翰如對此有一個很好的注解,他說,亞洲城市等于拼湊城市,規劃跟著建設走。侯翰如認為,一個城市的活力并不在于規劃的合理性,而在于解決緊急問題的能力。就該問題他曾于去年在威尼斯雙年展上策劃名為“緊急地帶”的藝術展。同樣不滿的還有城市規劃方面的專家,近期在廣州南沙舉行的一個業界論壇上,有學者發問:“貪污犯罪會判刑,劣質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是不是犯罪?該判多少年?” 廣州市規劃局副局長李紅衛在一番難言之隱的解釋后,為難地告訴大家:“規劃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從規劃到實施一般要5到10年的過程,中間變數太大。”以廣州為例,李紅衛說目前的狀況并非當時的規劃和初衷。變數來源于哪里?官員的更替、資金的壓力等等因素都是導致城市廢墟化的制度原因。 從城市化的游戲規則來看,無法去指責某一個階層或群體,每個人都可以從利益的角度去看城市化,但關鍵是,要在一個多方博弈的規則下去探討問題。 最差的博弈情形是官、商之間的“對弈”,把城市居民利益放置在一邊。以南沙為例,愛國實業家霍英東先生原本有把南沙建成粵港“9+2”重鎮的籌劃,但一直遭遇時任番禺區委書記梁柏楠的“卡位”,致使霍先生建設家鄉的良好意愿屢屢被扭曲。 房地產套牢中國人,這確乎是一個讓人“抓狂”的命題:一方面是中國城市建設“青春期”的到來,舉世無匹的城市化進程和房地產建設熱火朝天;另一方面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和大量復制使不斷膨脹的城市同步感受到不安。正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實驗”和“痛苦的感覺”在市民心中的雙重作用,使得被“套牢”的心態日益彰顯。 如果我們以未來的眼光來評判現在的時刻,在2050年回望2004的當下中國,“城市大躍進”式的房地產建設將留下什么是個巨大的問號:留下的是GDP的一些貢獻值,是開發商的利潤,還是幾十年揮之不去的遺憾?可惜的是,這種荒謬感在幾十年后才會被人們普遍體會到。 我們期待著,進入雙“S”曲線中后期的多方博弈,隨著民權意識的覺醒和新鮮勢力的加入,進入良性博弈——專家提醒說,只要博弈的任何一方使壞力,結果就不會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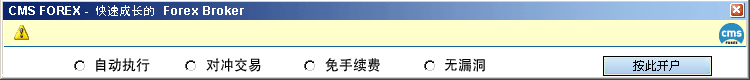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國內財經 > 行業專題--房地產業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