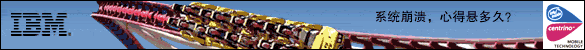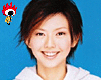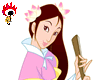|
茅于軾
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一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愿望。然而作為經濟學一個重要分支的發展經濟學在它產生后的幾十年內卻建樹甚少。究其原因,是因為在發展經濟學中將制度和技術這兩個推動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因素,當做完全是經濟原因之外的因素所規定的,因而不去研究經濟規律如何作用于制度變遷和技術創新。美國歷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斯
首先發現,制度變遷之動力存在于新制度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增加產出,使許多人得益;制度變遷的阻力則在于變遷需要付出成本,當成本很高時改變制度就很不容易,尤其是此項成本如何在社會成員之間分配時,當每個人都希望別人去承擔改變制度的風險或犧牲而自己坐享其成,則制度變遷將不可能發生。諾斯的理論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因為他提出了一個分析性原理。但是后人很少能用定量的實證方法來驗證這一理論。我國從一九五二年組織農業合作社,經過了高級社、公社,到七十年代末又解體為家庭承包的制度變遷,為驗證諾斯的理論提供了一個機會。這一工作為林毅夫在《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一書中的幾篇重要論文所完成。
最近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林毅夫的這本書。該書收集了他從一九八八年四月以來在具有世界影響的《政治經濟學雜志》(美)、《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美)、《美國經濟評論》(美)、《發展經濟學》(美)、《發展經濟學雜志》(英)等刊物上發表的九篇論文,以及另一篇尚未發表但具有總結性的新作“李約瑟之謎:工業革命為什么沒有發源于中國”。對于熟悉國際文獻的經濟學家而言,林毅夫的論文在短短兩三年內大量問世早已引起了注意,他的學術思想已經產生了影響,但對大多數國內的經濟學家,他們沒有機會方便地了解國際學術動態,上海三聯書店出的這本書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諾斯理論的背后是假定人都是從自利出發來作決策的。一個好的制度是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生產,整個社會欣欣向榮;一個壞的制度是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欺騙、爭奪,去瓜分別人創造出來的財富。我國從一九五二年起中央引導農民成立互助組、初級社,以后又成立公社,三年災荒以后又調整為隊為基礎,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出現了家庭承包責任制。這一段歷史很好地說明了制度演變和個人利益的相互關系。在公社制以前,集體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業生產一直呈上升趨勢。可是一九五八年組織人民公社,農業生產立即遭到空前大倒退,造成餓死幾千萬人的大悲劇。對這種現象雖然已有了種種解釋,如自然災害,規模不當,管理不善(如吃飯不要錢),但缺乏以事實為依據的科學解釋。對此,林在“集體化與中國一九五九——一九六一的農業危機”一文中通過對統計資料的分析作出了答復。四十年來農業成災面積、減產程度、動力排灌所占面積等的統計,清楚地說明自然災害說是極難自圓其說的。而規模和管理也未能說明公社制和合作社的本質區別。林在研究中發現,關鍵的問題在自愿或強迫。在農民有權選擇加入或不加入合作社,尤其是有退社自由的情況下,農業制度的改變不可能引起嚴重危機。因為如果合作生產制不如單干,部分農民會退社,社的規模會自動縮小甚至解散;如果合作制更優越,農戶會自動要求加入,生產隊還可以拒絕勞動不好的農戶入社。而在公社制下既不允許農民退社,又不允許公社解散,農民和公社都不再有選擇的機會。此時農民對自己失去了自我制約的條件,勞動、分配都產生“不撈白不撈”的思想,而且這種行為沒有任何后顧之憂,表現再差也仍是公社社員。用林毅夫的話,在自愿入社情況下是農戶與生產隊之間的多次博弈,雙方可隨著情況變化選擇對策,所以農戶和生產隊都有自我制約的必要。公社制下變為一次性博弈,任何破壞協議的行為都沒有可供選擇的對策來對付。林的這一研究結論對我國今后農業制度演變的政策設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其實,自由選擇是整個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經濟之所以有活力,能以效率較高的經濟活動代替效率較低的活動,從根本上說,是由于當事各方有選擇的機會。政府應減少對企業的干預也正是這一緣故。政府的作用不是限制行為當事人的各種選擇方案,而是協助他們能作出更好的選擇,并保證市場規則的嚴格遵守。因為維持市場規則需要市場之外的第三方面居高臨下的參與。
經濟學研究人的經濟行為規律。它的基本前提是:人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有理性的生物。在有市場和價格起作用的時候,人的行為受價格信息的影響,價格起了指揮棒的作用。這一推論在市場經濟國家已得到無數觀察資料的支持。但是在中國,改革之前價格不起指揮棒的作用。例如在農村中土地和勞動是不許買賣的,當然無所謂價格。各種農產品的價格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因為大部分農產品不是光用錢就可以買賣的。于是就發生了一個帶根本性的理論問題:生活在計劃經濟國家的人是不是追求自利的人?如果是的話,他們的行為受什么信息的支配?這個問題在西方十分成熟的經濟學中也還沒有充分討論過。它的主要困難在于缺少了價格這個可以定量的參數,就很難用經濟數理統計,亦即經濟計量學的方法得出科學的結論。土地和勞動雖然沒有價格來定量地描述其稀缺性,林毅夫用三十年內人均耕地的數字看出了二者相對稀缺性的變化,又將改良種子的科研經費視為以節約土地為目的的投入。由于各省市人均土地的變化相差極為懸殊,用于改良種子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極不相同,于是就可用經濟計量學檢驗二者的變化是否存在相關性。林得到的結論是農民和農業部門負責分配資金和人力的干部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追求經濟利益這一規律的。中國農業技術進步是沿著節約最稀缺的生產要素的道路發展的。在林之前有希克斯、速水、拉坦、賓斯旺格等人證實了技術發展的道路是節約稀缺要素,但必須有用價格來衡量稀缺性的市場存在。林的研究將他們的結論推廣到了沒有價格信號的條件下,這一結論依然成立。林又比較了投資于不同種類農作物的品種改善所用的資金,進一步證實投入的資源與產品的市場規模有關,市場越大或種植面積越大的作物,投入的資源越多。
現代經濟理論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具有相當堅實的邏輯基礎,因此應用經濟學理論作政策設計時,理應是相當有把握的。可是事實卻未必。一個主要原因是當幾個因素同時產生作用時,很難分清他們的主次。如果誤將次要因素當作了主要因素來用,政策就會發生偏差。這里有一個重要例子。中國農業在一九七八——一九八四年間的迅速增長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即提高農產品價格,和從生產隊所有制改變為家庭承包責任制。一九八四年以后農業生產增長減緩,尤其是糧棉生產減少。于是不少人重新提出了農業集體化的問題。集體化可以擴大生產規模,從而有效地利用大型農具,組織灌溉,連片殺蟲。但集體化就要放棄家庭承包。從經濟理論來看,激勵機制的改善與生產規模合理擴大都可以提高產出。但二者不可得兼,因此存在何者的作用更為重要的問題。這聯系到七十年代末的增產是提價的作用還是家庭承包的作用為主。如果主要是提價的作用,則放棄家庭承包搞集體化顯然是合理的。林在“中國的農村改革與農業增長”一文中用生產函數法對此作了答復。這一研究結論肯定了家庭承包在增產中的重要作用。
這一切決不意味著擴大生產規模的利益不值得追求。我國的人均耕地已經很少,戶均僅0.55公頃,這一點地又因土地細分而進一步變小。林毅夫在“中國改革后決定農業投資與農民住房建設的因素”一文中,用計量方法證明了在江蘇泰縣和句容縣戶均耕地少于三分之一公頃時,存在著極明顯的增大土地規模的經濟效益。但正如前面提到的林的另一個重要結論,規模耕作必須通過自愿的道路,合作化或土地買賣是自愿基礎上擴大規模的主要途徑。
林的這幾篇論文無一不是巧妙地解決了有些概念難于量化的困難,從而使計量的方法可以用來對經濟理論作科學的檢驗。林毅夫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用監督費用來衡量農業生產制度優劣的一個因素。家庭承包制不需要監督,干活是為自己干,所以監督費用幾乎為零。反過來如果對社員勞動監督越困難,則改成家庭承包制所得的利益越大,推廣承包制的速度應該越快。林巧妙地發現,隊的規模越大,種植業對畜牧業的比例越高,則監督越困難。以上三個參數(規模、比例、速度)都是可以定量的,于是經濟計量學的方法就有了用武之地。結果證明了林提出的關于監督費用與制度關系的理論假定。
在該書最后一篇文章中討論了何以有燦爛古代文明的中國沒有發生開創現代文明的工業革命的問題。工業革命是以一系列科技發明為特征的。中國古代不但有發達的哲學和科學萌芽,有當時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的政府,而且也有眾多的科技創新。作者認為這些科技都是能工巧匠憑經驗積累而碰巧發明的,而不是一批專門人才刻意鉆研的結果。十八世紀以來現代技術大量出現是由于逐漸培養了一批以科學技術為職業的階層,他們了解前人的科學理論并能系統地組織前人的理論,通過專門的試驗和糾錯,尋求出為特定目標的提高生產率的新方法。基于這一假定,作者將完全基于個人經驗對某一工藝方法所作的各種知識組合視為一隨機事件,這種組合所能達到的生產率則為一隨機變量,它具有正態分布。當所達到的生產率碰巧比目前流行的生產率高,這種知識和經驗的組合就成為技術創新。這個理論解釋了何以中國在十七世紀之前與其它文明古國相比有數目多得多的科技發明,這是人口眾多,偶然發明機會相應增多的緣故。工業革命以后科技發明的規律起了變化,人多不再有優勢。他的理論使我想起一例佐證。中國在公元七八世紀的唐朝就已有了雕板印刷術,但活字印刷則是一○四一——一○四八年間宋代的畢升所發明。這樣一個小小的概念進步競花了三百年的時間。相比之下,現代黑白電視之進步為彩色電視,要克服的技術困難何止千百倍,然而它只花了十三年時間(一九四一——一九五四)。造成這一差別的原因正如林文所說,前者是“碰巧”發現,后者是有組織研究的結果。林進一步分析,何以中國人中最有才智的人沒有沿鉆研技術的道路發展而陷入了八股文,浩繁的文獻加上激烈的競爭耗盡了知識分子的心智。這個假設用來解釋中國科技發展受阻顯然是十分有力的。但我認為歷代統治者打擊商人的政策不能不說也是一個原因,它使得從商致富并攀登到社會上層的道路變得此路不通,只剩下通過科舉當官的一條路可以成為人上之人。秦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于洛陽,把他們的致富基礎——和當地百姓的聯系從根上切斷。漢高祖也干過類似的事。秦漢時征到邊疆去服兵役的七種人(稱為七科謫)包括逃犯、贅婿、商人以及三代內經過商的商人后裔。漢武帝時派楊可去征大商賈的財產稅,稱楊可告緡,使大部商賈破產。此種政策一直變著花樣沿襲至今。解放以來對工商資本家出身的子弟在升學、參軍、提干、出國等方面有一系列歧視性規定。文革時將全國集市幾乎一掃而光;抄“資本家”的家,分他們的浮財。至今從商致富的人還經常成為敲詐勒索的對象,而且此種行為常能得到許多人的支持,干得理直氣壯。在這種環境下商人能去從政,而且當官之后仍能代表商人利益來影響政策的可能性確乎微乎其微。這成為現在從商者老怕政策變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雖然這本書基本上討論農業問題,但對不熟悉農業的讀者而言一樣讀來饒然有味。因為作者所用的經濟學方法帶有普遍意義,他對問題的機智處理常令人叫絕。特別是這些研究都是針對開放改革以后農業中發生的變化,它關系到我們每一個人。不是嗎?餐桌上的副食更豐富了,水果、點心、飲料不論是數量或質量都上升了幾倍。這一切好象是從地底下鉆出來的。一個發生在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多的大國中這樣一個變化,其意義無論如何估計也不會過高。這本書把我們在親身經歷的變化中,從知其然引導到了知其所以然。
(《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林毅夫著,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一年三月版,7.3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