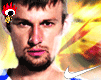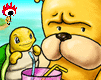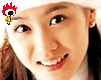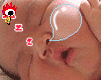| 平實以致遠 茅于軾先生的生平與學術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6月11日 16:14 中評網 何帆 | |||||||||
|
何帆 那還是七年前,我剛剛跨進大學校門的時候。有一天我在學校的圖書館里亂翻,無意中找到茅于軾先生的《擇優分配原理》一書。這是一本引人入勝但我卻無法一口氣讀完的書,因為書里用的是數理工具,討論的又是經濟學的微言大義。盡管茅于軾先生行文洗練、深入淺出,但我仍費了不少勁才把這本書啃完。對于當年的我來說,這次閱讀是一次神奇的
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最讓人激動的經歷莫過于在多年之后,能夠結識自己當年曾追隨過的思想先驅。兩年前我在天則經濟研究所里終于認識了茅先生,此后,每次在天則所遇見這位矍鑠而慈樣的老人,心中總會生出崇敬和親切之感。 在北京東南的方莊小區,一幢幢高樓叢生林立。天則經濟研究所,這家蜚聲中外的民間研究所,就設在這里的一幢公寓樓里。從外表看,這里普普通通甚至還有幾分簡陋。但這卻是中國經濟學界星光大放送的地方。天則所的成員包括茅于軾、張曙光、盛洪、樊綱、劉世錦、張宇燕、唐壽寧、張平等一批中國社科院的知名學者,茅于軾先生則是天則所的現任所長和創始人之-。除此之外,茅先生還身兼亞洲開發銀行注冊顧問、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廣州外語外貿大學和山東礦業大學的兼職教授等職務。曾被美國Marquis世界名人錄和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選為1993一1994年度世界名人。 但是,這些榮耀并不足以體現出茅先生的價值。在我看來,日后如果會有一本記載中國經濟學發展歷史的著作,那么其中的許多篇章都會提到茅先生的名字。因為,除了他自己在學術上的重要貢獻,他還一直不遺余力地從事引介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和國際化的事業,這些工作更是澤被后學、功德無量。 一 茅先生1929年生于江蘇南京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參加辛亥革命。他的父親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聞名的橋梁專家茅以升先生便是茅于軾的二伯父。茅于軾的母親陳景湘女士也出身書香門第,她的父親陳吟詩是清末的舉人,三哥陳章曾任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后又任南京工學院教授。 茅于軾的父親茅以新處世正直,公而無私。他把自己的畢生默默奉獻給了我國的鐵路建設事業。大學畢業之后,茅以新負笈美國,在普渡大學獲得鐵路機車碩士學位。回國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贛鐵路和粵漢鐵路的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抗戰爆發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廣西柳州組建柳江機器廠,到1944年日軍進犯湘桂時,又負責工廠向貴州的疏散。茅于軾的童年,也便在這連天烽火中轉輾于桂、黔、川等地,他曾在6個小學、7個中學就讀。抗戰時期生活艱苦,一家人清貧度日,常常吃不飽肚子,衣服也是補了又補,時事的艱難反而使茅家的四兄妹更加成熟和自律。他們敬重父母、互相友愛,那種樂觀而融洽的家庭氣氛仿佛成了他們借以驅散寒夜的火種。父親工作繁忙,母親也有操持不完的家務事,茅于軾和他的弟弟妹妹們不僅幫著母親做家務,還非常自覺的堅持學習,連放假的時候也不松勁兒。長輩的榜樣便是好的激勵,當年茅家的四個孩子,現在都已成長為杰出的學者;茅于軾先生是海內外知名的經濟學家,他的兩個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妹妹茅于蘭是北京師范學校的副教授。 抗戰之后,茅于軾考入了父親當年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當時他深受父親的影響,志向也是要獻身祖國的鐵路建設事業。于是,大學畢業之后,他便到了東北齊齊哈爾鐵路局工作,當過火車司機,還當過工程師,后來又調入鐵道科學院。那時候,他恰當風華正茂,渴望大展宏圖。不幸的是一場“文化大革命”風云突變,茅于軾一家也受到沖擊。領導里一位自視為革命的街道積極分子。為了立功邀獎、誣陷他們家是資本家,引來紅衛兵到茅家翻箱倒柜,大打出手。后來,年已七十歲的茅以新先生被發配到甘肅省邊界的一個地方燒鍋爐,茅于軾自己在鐵道科學院也被劃為右派。從此,許多重要課題與他無緣,他的科研成果無處發表,已經出版的書還要把作者的名字改成筆名。但在那個混亂的年代里,茅先生仍做了許多很有價值的科研工作,他用控制論原理討論機車牽引熱工動態性能;用概率論作了機車牽引熱工試驗的誤差分析,建立了鐵路道口事故的概率論模型;還應用變分法推導了列車牽引中的能量方程。但在這時期,茅先生的研究仍然局限在鐵道工程學的領域之內,對于經濟學,他井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失注。 二 1975年,中央打算修建一條青藏鐵路。這條鐵路起自格爾木,計劃通到拉薩,全長1200多公里。為此組織了一批專家對這條鐵路的設計作技術經濟評價。茅先生也參加了這項工作。正是這次經歷使他對經濟學發生了興趣。當時,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仍在忙著從《資本論》中尋章摘句,為政策的變幻做出種種政治上的詮釋。茅先生以一個講求實事求是的工程師的眼光,很快認識到經濟學是要研究資源的約束條件下求得效益最大化的問題。他深厚的數學修養更使他-下子領悟到,經濟學的本質在數學上就是數學規劃問題。非常巧合的是,就在這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給了線性規劃的創始人,蘇聯經濟學家康托羅維奇等人。茅先生在那個閉塞的學術環境里,從一開始就抓住了經濟研究的世界前沿問題,這卻是他當時所不知曉的。在此后的幾年里,他一個人潛心構造他的經濟學世界,終于在1979年導出了擇優分配原理。1981年,茅先生參加了美國經濟學家克萊因在頤和園舉辦的計量經濟學研討班,到這時,他才正式地接觸到了現代經濟學。此后,他進一步地閱讀西方經濟文獻,并和自己的想法參祥印證,更加堅定和完善了原先的構思。直到1985年,茅先生應《走向未來叢書》之邀,才寫成《擇優分配原理》-書,回首遙望,距離當年的思想萌芽已有十年之久。此時茅先生也已調人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從此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去思考經濟問題。“十年磨一劍,劍光照人寒”。茅先生的這本書深受歡迎,先后印行7萬余冊,現早已脫銷,據說不久仍要再版,青年經濟學家張維迎87年曾在《中國:發展與改革》上撰文評介此書,稱這是“一本真正的原著而不是評著,作者是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而不是以第三人稱的筆法寫作”。 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討論的核心問題便是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擇憂分配原理就是想直接探討什么是配置資源的最佳原則。微觀經濟理論認為,最優分配要使配置到各個領域的資源能有一個統一的邊際收益。從理論上講,實現最優配置有兩種方式:一是由一個計劃者事先計算出統一邊際收益的數值,再按這個計算結果制訂計劃,調配社會資源。問題在于,復雜經濟系統中邊際收益的調整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現實中沒有任何一個計劃者能求出全社會各種資源的統一邊際收益。理想狀態中的計劃經濟神話不過是一種“計算機烏托邦”。事實上,計劃者總是誤把平均收益當成是邊際收益,創造出許多拍腦瓜式的、一刀切式的比例關系,用以指導國民經濟建設,結果堵塞了資源向更有效的配置調整的渠道,造成了我們熟知的浪費和低效率。看來,只有另一種辦法,即走市場經濟之路才行得通。因為,按照擇優分配原理,無論我們是從哪一種初始分配出發,追求自利的市場參與者總會充分利用價格信號,不斷作微量調整,將邊際效益低的投入改用于邊際效益更高的領域。由于普遍存在邊際收益遞減公理,最后-切投入的邊際收益都會趨于-致,從而達到了最佳分配。從學術貢獻來看,茅于軾先生的擇優分配原理把微觀經濟理論直接建立在數學規劃的基礎上,使經濟分析的前提條件和邏輯推理都表述得更為清晰,同時也把微觀經濟學的制度背景從隱含表述為明顯。1990年,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邀請茅先生前去講述微觀經濟學,就是由于看中了他建立的這一特殊的學科結構。從現實應用來看,茅先生的這-原理對我們觀察經濟現象和制訂經濟政策都有很重要的啟發。茅先生自己也曾用這一理論得到過不少有意義的結論。1986年,他在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時,曾注意到美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差異很大,最窮的州和最富的州人均相差幾達一倍。美國是一個人口流動相當自由的國家,何以較窮州的人口不遷向富州,而使各州的人均收入趨于-致?茅先生翻檢了有關的歷史記錄,發現各州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是大體一致的。應用擇優分配原理,可以對這一現象做出解釋:原來,影響人們遷移的原因在于各地之間人均收入增長速度的差異,人口的自由流動最終會使各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趨同。這一結論對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也有很大的啟示。也就是說,我們不應不顧客觀規律地強求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整齊劃一,而是應以消除地區間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為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歸根結底要靠更靈活、自由的市場機制。 從茅先生對擇優分配原理的研究可以看出他治學的特點,他總是力圖把最基本的原理徹底弄清吃透,發掘簡單定理背后的深刻寓意,再用長久思考得來的道理去分析實際問題。茅先生稱,他的信念是:“經濟理論必須逐條地都可還原為經濟現象。一切經濟現象也必定有相應的理論可以解釋”。本著這樣的信念,他曾以在美國的點滴感受為素材,寫了一系列隨筆,用經濟學的原理為普通讀者說明市場經濟的運作,后來,這些文章又編成一本書,取名《生活中的經濟學一對美國市場的考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書里既介紹了價格與資源配置、通貨膨脹、外部效應、國際貿易等基本理論,還討論了市場經濟的文化、法律及道德背景。這本書旨在引導讀者自我思考,體會出自己能掌握的經濟學來,這本書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茅先生的隨筆從此也-發而不可收拾,在《南方周末》、《經濟學消息報》等報刊上,都可以經常讀到茅先生的新作。一本新的隨筆集《誰妨礙了我們致富》,也已交給四川文化出版社,大約今年年底之前就可面世。茅先生在教學生的時候,也不忘引導他們用經濟學去回答日常生活中-些基本的問題。去年他在北大演講時,給學生們出了八道經濟學問題。例如:交換是否等價?投機饒的錢是創造出的財富還是別人口袋中的錢?為什么窮國和富國的工人同工不同酬?這些問題我們幾乎每天都會遇到,但實際上卻很不容易回答,里面包含的理論都是相當尖端的。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也用茅先生的這幾道題測測自己的經濟學功底。 三 伴隨著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人們的道德水平出現了大幅度的滑坡。舊有的傳統倫理經過文革的沖擊早已七零八落,而極左的所謂共產主義道德又面臨著災難性的信仰危機,一時間自私和欺詐的行為四處蔓延,公眾對社會公德的冷漠態度和暴力等惡性事件的滋生正破壞著我們這個社會的健康發展。茅于軾先生早在1986年前后就開始關注這些問題。十年來,他在國內外發表一系列討論道德與經濟的文章,并于1989年完成了《新經濟體制下的道德觀》一書。這是他嘔心泣血的一部力作,但卻幾經周折,遲遲未能發表,直到今年,才將多次修改后的文稿交給了廣州出版社。我在1994年曾從他那里索得此書的一份拷貝,有幸先睹為快。我想這是一本值得向每一位讀者推薦的佳作。它一路娓娓道來,宛如茅先生平日里那低緩而清晰的江南普遍話。書中主要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參考了大量倫理學方面的著作,把人類道德倫理學方面的著作,把人類道德倫理的起源和演變一一用經濟理論加以剖析,能使人對感覺無所適從的道德難題豁然開朗。茅先生把道德釋為自私的人們尋求互利而規定的社會規則。在人們的相互交往中,能使大家都得利的最佳途徑便是自愿條件下的交換。但交換成為一種制度卻只是這二、三百年之內的事情。自然經濟條件下物質貧乏,個人間的逐利行為常會掉進零和對局的困境,克已復禮、重義輕利才成為道德的基石。農業社會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維持家庭倫理就等于維護社會秩序,因而等級制又成了傳統倫理的核心。市場經濟下交換能得以最完善有效的保護,交換將帶來每個人利益的增加,因為它促使每個人都發揮其比較優勢。經濟的發展要求人們在觀念上更新、揚棄傳統道德、重建市場經濟下的新道德體制。另一方面,新道德體制的成長也需要盡快確立自由、平等的市場機制。 我很擔心我的這一段并不精彩的轉達會使讀者誤以為茅先生的書中都是些干巴巴的說理。事實上,他引經據典,旁證博引,更為可貴的是,還從報紙上摘引了大量改革中發生的新聞,用這些實例使一個個鮮明深刻的觀點躍然紙上,初讀此書,就覺得茅先生針砭時弊的雜文筆法讀來特別暢快淋漓。好書耐讀。當我又讀過幾遍之后,已能漸漸品出茅先生悲天憫人的情懷。這是一位堪稱“社會良心”的學者對人間冷暖的深切關懷。我相信這本書能使頭腦混亂的讀者思路通暢,能使內心不安的讀者心靈安寧。 四 在我的同學中,許多人知道茅于軾這個名字都是從讀他和湯敏主編的《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開始的。可以毫不夸張他說,這套書已成為國內經濟學研究生必讀的參考書。在已經出版的兩冊中,收入了楊小凱、錢穎-、田國強、陳平、易綱、鄒綱、王建業等一批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成員的論文,介紹了企業理論、交易費用經濟學、非線性經濟學、對策論等經濟學新興領域,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影響深遠。茅先生為這套書的編輯和出版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他從1987年就擔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國內聯絡員,協助學會在國內普及現代經濟學理論,出版過許多圖書雜志,其中比較流行的除《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之外,還有一套《市場經濟學普及叢書》。從1988年起,茅先生還一直擔任學會刊物《中國經濟評論》(在美國用英文出版)的顧問編輯。 茅先生有那種典型的望之淵默、即之也溫的長者風范。他和許多青年經濟學家都保持著半師半友的密切往來,在青年學者中威望甚高。我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那次是楊小凱回國其間到天則所做報告,他一進門,顧不上和眾人握手,就滿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師”。當年楊小凱的第一本著作拿給茅先生看,茅先生把書中的每一個定理,每一個公式仔細做了推導。在那本書中楊小凱的思想還只是初步成型,茅先生便看出他的不凡。在此后的許多場合,茅先生總是不忘為楊小凱的思想做宣傳和贊揚。他看到年輕人發表了好的文章,常會親自去信討論問題,也以此表示鼓勵。他和盛洪的交往便是這樣開始的。茅先生在1989年的《中國:發展與改革》上看到盛洪的一篇《中國經濟需要制度創新》,非常欣賞文中的見解,便去信和盛洪切磋,他還謙遜地說,“盛洪是我學習制度經濟學的老師”。對于青年學者的成長,茅老師總是鼎力相肋,呵護有加。當年,宋國青從地質系畢業,被分到西安的地質局。茅先生深知這是對人才的埋沒,他親自找到當時的教育部副部長周麟,拍著胸脯為宋國青打保票,說他一定是個經濟學家的好料子。由于茅先生和許多熱心人的奔波,宋國青最后才又被調回北京。張維迎、平新喬、栗樹和、梁天征,……,在茅先生的這些青年朋友背后,也許還有著更多類似的佳話…… 五 1993年,茅先生和盛洪、張曙光、唐壽寧等,與從事文化事業的大象公司共同創辦了天則經濟研究所。“天則”這-名字,取自《詩經》的詩句“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意指自然之規則。這-名稱表露出天則經濟學家對制度經濟學的共同愛好。研究所創辦之初,是由盛洪擔任所長,盛洪在1993年秋天去了美國芝加哥大學作訪問學者,茅先生便承擔起所長的擔子,從此一直干到現在。天則所在這兩年多來做出的成績是驕人的,如第一批關于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已先后完成,舉辦了60多次天則雙周論壇,編輯出版了《中國經濟學1994》等。此外,他們還走出象牙塔,致力于將經濟學“產業化”,完成了亞洲開發銀行、福特基金會和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委托的多個項目,在國內也完成了“廣西玉柴機器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發展戰略”、“西安金融中心地位與城市發展模式”、“天津電解銅廠改組設計與論證”等咨詢、研究項目。由于這些學術研究和咨詢活動的成功,也由于天則所為中國新生的民間研究所的代表和旗幟,它已吸引了許多中外媒體的追蹤報導。美國《時代》周刊1995年6月采訪了盛洪和茅于軾,《商業中國》在1995年6月曾在報道中介紹過天則所,敏感的香港新聞界更是領先一步,在1994年10的《中國時報周刊》中,就有一篇關于天則所的專訪。在國內,《經濟學消息報》和《長江經濟導報》幾乎每一期都有關于天則所活動的消息。 臨到這篇稿子快寫完時,我才想到自己還沒有想妥一個結尾。為此我又撥通了茅先生家里的電話,請他談談他的心愿。他說“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國能富起來!”關于中國的經濟學,他希望能走出一條和西方的主流經濟學不一樣的道路。他把這個希望寄托在年輕一代的經濟學工作者身上,叮囑他們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并且要努力發揮自己的創造性。 讓我們和茅先生一起,為中國經濟的未來和中國經濟學的未來祝福。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國內財經 > 茅于軾 > 正文 |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