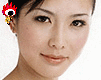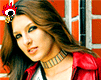| 《經濟》:怒江大壩突然擱置幕后的民間力量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5月20日 16:15 《經濟》雜志 | ||||||||||
|
 本刊記者 曹海東 張朋 本期封面上的幾個人物,由近到遠的前三位分別是:民間環保組織“云南大眾流域”的負責人于曉剛;云南省政協委員、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戴抗;“云南大眾流域”客座研
“云南大眾流域”是通過發出種種聲音反對在怒江上建設大壩的中堅民間組織之一,于曉剛是其組織者;戴抗則是在今年2月份的云南省政協九屆二次會議上發言質詢怒江工程的人,他的這次發言被評價為“(針對怒江工程)云南省地方政府內部的第一次出現的不同聲音”。實際上,戴抗的態度直接受到了反對怒江工程的民間環保人士的強烈影響。 在反對怒江大壩工程的民間力量中,最核心的力量是北京的“綠家園”和“云南大眾流域”這兩個民間環保組織,而前者的負責人汪永晨可以說是整個事件的始作甬者、靈魂人物。 因為汪永晨的“綠家園”、于曉剛的“云南大眾流域”這些NGO(非政府組織)的呼吁和推動,中央領導人批示,暫時擱置了一度如箭在弦的怒江大壩工程。 民間組織的活動和聲音極大地影響了中央政府的決策,這在中國還是第一次。這是一個標志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其實,關于怒江流域是否應該開發水電、怒江上是否應該建大壩,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經濟》也并不認為環保NGO們從生態保護的角度出發反對工程上馬的觀點就一定“正確”。《經濟》之所以關注此事件,并認定這一事件的意義,只是因為它是中國NGO發展歷程中的一件大事,更重要的,它折射了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次重要躍升。 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傳統社會”是一個由“全能政府”決策一切、包辦一切、負責一切的社會。一個開放、多元的現代社會則應該是一個NGO充分活躍、發揮巨大作用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政府與NGO保持順暢的溝通、交流與具有建設性的協調、互動。這是一個中國目前正致力追求的社會。中國的社會轉型正在艱難行進中。 這個事件本身涉及的范域也許是局促的,但它喻示的未來圖景卻是十分宏大的。 (一) 在怒江問題上,純粹的民間組織質疑并最終改變了政府的決策,這是一個飛躍,在中國的社會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怒江的民間保衛戰 文/本刊見習記者 曹海東 2004年2月18日下午三點,從怒江丙中洛到貢山的路上,十幾個人默默地走著,每個人的情緒都非常低落,十幾分鐘里沒有一句話,山路上只有怒江水在一旁咆哮而過。 忽然一個人的手機響起來了,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被吸引了過去。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她的臉色開始慢慢轉變:從憂色到歡喜。在掛掉電話的一剎那,她突然大叫: “中央批示了,怒江不用修水電站了!” 隨后,聲音慢慢低落了下來:“怎么為了保護一個怒江這么難呢?” 她開始掩面大哭! 她——汪永晨,50歲,民間環保組織“綠家園”的負責人。她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 寂靜的大峽谷開始沸騰起來,來自北京和云南的十幾名環保志愿者和專家學者,第一次開始開懷大笑,一直壓抑在大峽谷中的凝重憂慮在一剎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蹤,興奮的聲音在峽谷中激蕩——“我們勝利了!” “對這類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且有環保方面不同意見的大型水電工程,應慎重研究、科學決策。”這句中央領導人的批示使得爭論了半年的怒江十三級水壩終于暫時擱置起來了。中國民間環保NGO(非政府組織)的力量第一次在與一個大壩的斗爭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我想這在中國環保史上,中國環保NGO(非政府組織)史上,都是第一次,都值得濃墨重彩地寫一筆。”一位民間環保NGO人士自豪地說。 誰要建怒江大壩 怒江、瀾滄江、金沙江三條大河在滇西北麗江地區、迪慶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行政區內并流而行,人們稱之為“三江并流區”。2003年7月3日,“三江并流”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批準為世界自然遺產。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傳來另外一條消息——怒江要修水電站,而且是兩庫十三級! 2003年8月12日至14日,國家發展與改委員會在北京主持召開《怒江中下游水電規劃報告》審查會。會議通過了怒江中下游兩庫十三級梯級(松塔、丙中洛、馬吉、鹿馬登、福貢、碧江、亞碧羅、瀘水、六庫、石頭寨、賽格、巖桑樹和光坡)開發方案,全級總裝機容量2132萬千瓦,年發電量為1029.6億千瓦時。 該《報告》認為,怒江干流中下游河段全長742千米,天然落差1578米,水能資源十分豐富,是我國重要的水電基地之一。與另外12大水電基地相比,其技術可開發容量居第6位,待開發的可開發容量居第2位。 如果建成,經濟效益顯而易見,比三峽工程規模1820萬千瓦還要大,是三峽年發電量(846.8億千瓦時)的1.215倍,而工程靜態總投資才896.46億元。 2004年4月12日,云南,昆明。 雖然在“114”電話查詢臺上登記了中國華電集團云南怒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的具體地址,可是真正找起來卻很難,因為根本沒有這個公司的牌子。最終一個門衛告訴記者,該公司在“云南電力集團水電建設有限公司”的三樓、四樓辦公。 華電集團云南怒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建新見到《經濟》雜志的第一句話就是:網絡等媒體上流傳的消息很多都是不準確的,目前怒江整個開發從宏觀層面上還在按照國家政策,按法定程序認真地進行施工準備。 張建新告訴《經濟》, “早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怒江開發)已經開始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根據他的了解,在上個世紀80年代全國能源普查的時候,1989年怒江流域的水電開發已經進入當時的普查范圍,規劃了相應的梯級。 《經濟》記者所拿到能源部水電開發司1991年編制的《中國水力資源圖集》關于“云南省大中型水電站位置圖”中,怒江流域設計了6個電站,總裝機容量為1090萬千瓦。 1999年,國家發改委“根據我國的能源現狀,根據有關人大代表的呼吁,決定用合乎程序的辦法對怒江進行開發”。于是撥出一定的資金,由水利水電規劃總院牽頭,用招標的方式確定了兩家設計單位——北京勘測設計研究院、華東勘測設計研究院,由這兩家設計院對怒江中下游的云南境內的水電進行規劃。 最終,“提出的方案就是‘兩庫十三級’”!因此,張建新認為怒江流域的水電開發的規劃“并不是現在才想起來的”。 據張建新的介紹,華電集團參與到怒江流域水電開發中來是在2003年春節后。當時華電集團總經理賀恭與云南省主要領導交換了意見,從整個水電開發的形式——“水火并舉,優先發展水電”著眼,特別是怒江上游已經建有水電站的前提下,才決定開發怒江水電的。 “當時云南很多老領導都同意怒江水電開發,再說賀恭在云南呆了那么久(張建新稱賀恭在云南工作長達14年之久,曾擔任云南省電力局副局長),參與了云南省第一個百萬千瓦水電站漫灣電站的建設,非常熟悉云南的情況。”2003年3月14日,華電集團與云南省政府簽署了《關于促進云南電力發展的合作意向書》,云南省政府支持華電集團開發云南電力資源,支持怒江開發。 隨后,2003年6月14日,云南華電怒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組建,7月10日正式注冊。“我也就是云南華電怒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成立后才調過來的。”張建新說。 本來按照規劃,2003年內將開工建設六庫電站,同時啟動馬吉、碧江、亞碧羅、瀘水、賽格和巖桑樹電站的設計工作。但是因為隨之而來的一連串“輿論攻勢”——專家辯論、民間力量的參與、公眾要求知道真相,所有的設想開始擱淺,到2004年便有了中央領導的批示。 怒江州外宣辦科長楊宏斌為難地告訴《經濟》說,“專家有專家的說法,媒體有媒體的說法,現在只要提到怒江水電開發我就頭痛,一撥一撥記者來!” 不過,張建新似乎比較樂觀,“現在不是還沒有掛牌嗎,等六庫電站環(保)評(估)下來,我們就掛牌!” 怒江保衛戰第一槍 “綠家園”負責人汪永晨很清楚地記得,她是在2003年8月16日獲知云南怒江州要修建十三級水壩的。 當時汪在南水北調的丹江口采訪,途中忽然接到在環保總局的一個朋友電話,朋友急匆匆地告訴汪永晨,怒江要修十三級水電站了。 “以前我對水壩關注得并不多,2001年去泰國的時候,遇到當地的一個反壩村,至此我開始覺得反壩是環保的一項內容,但是從內心來說依然覺得與中國沒有多大關系,可就在聽到怒江的時候,我的心頭一震。”汪永晨說。 環保總局的朋友告訴她怒江是中國最后的生態江之一時,汪說從那一刻起,覺得這輩子反水壩的生涯要開始了。 “我的朋友說,他在國家發改委開會,孤軍奮戰,‘環保總局一定要守住’,并且非常急需她幫忙找一些熟悉怒江的專家學者,他要反擊!” 汪現在要為這位環保總局的朋友輸送“援軍”。在丹江口船上亂糟糟的環境,一個個名字閃過汪永晨的腦海,忽然“何大明”這個名字蹦了出來。 何大明,云南大學教授,云南大學亞洲國際河流中心主任,著名河流專家。汪永晨10年前認識何大明,但是后來一直沒有聯系過。2003年7月汪去云南采訪時碰到云南的一個朋友,談到修水庫事情的時候,獲知何大明有關于怒江的大量、詳細的資料。 沒有猶豫,何大明的電話馬上就被汪永晨送到她環保總局的朋友手中。 如此,就有了何大明在2003年9月3日,由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在北京市主持召開的“怒江流域水電開發活動生態環境保護問題專家座談會”上對怒江建壩的激烈抗議。而何大明的這些言論后來成為國家環保總局以及北京的專家們向怒江“發難”的基礎。何大明成為最先反對開發怒江、呼吁“為子孫保留一條生態江”的專家,也是站出來反對怒江建壩的惟一的云南當地專家。 就此,也挑起了全國關于對于怒江大壩的爭論。 2004年3月下旬,《經濟》雜志聯系過云南大學亞洲國際河流中心,希望通過何大明了解當時“北京會議”的情況。該中心的一位人士稱,何現在可能不會接受記者采訪,“太多媒體采訪了”。而記者從其他渠道獲知,云南有關方面曾專門找過何大明“談話”。 2003年9月份北京這個會議汪永晨也列席參加,“當時我叫了綠家園記者沙龍十幾家媒體的記者前去”,由于這場會議請來的專家大多數是反對建壩的,所以局面呈現“一面倒”。 環保NGO人士、環保官員都稱這次會議是“打響怒江保衛戰的第一槍”。 在云南本地,同樣有一個環保NGO——“云南大眾流域”在密切注視著怒江流域的水電開發,他們一度甚至促成了云南政府內部的第一個不同聲音的出現。 2004年4月14日,“云南大眾流域”負責人于曉剛在昆明接受《經濟》雜志采訪時說,在2003年初,他們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怒江要建水電站,不過當時只是風言風語,很難確定。隨著消息明朗,在香港樂施會和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于曉剛反復提出,怒江作為生態江應該保護。 “直到2003年7月份,‘三江并流’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批準為世界自然遺產,我的心才放下來,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事態急轉,8月份便聽說《怒江中下游水電規劃報告》審查會舉行。太驚訝了,他們怎么能這樣呢?”直到現在,于曉剛對于去年發生的一幕幕都感覺費解。 眼看著怒江水電開發逐漸浮出水面,綠家園、大眾流域、自然之友等環保NGO的急迫之情與日俱增,他們通過講座、論壇(比如記者沙龍、水之聲論壇)等形式開始積極宣傳怒江大壩的相關事宜。汪永晨、沈孝輝(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委員、多家環保NGO成員)也不斷替環保總局的一些官員呼吁、“打氣”,希望他們能夠挺住。 隨后全國的多家媒體開始報道怒江問題,“很多都是綠家園的記者沙龍的記者”。華電集團云南怒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建新稱,也就是因為輿論的影響,怒江十三級水電站開始拖了,“并由此影響到六庫電站”。 爭取民間的話語權 2003年10月25日,綠家園組織發起了一項很有影響力的行動。在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62位科學、文化藝術、新聞、民間環保界的人士聯合簽名,反對怒江大壩。 “當時,副會長郁鈞劍提出請保留最后的生態河。郁說,目前在世界上保持原始生態的江河幾乎沒有了,在中國也剩兩條:雅魯藏布江和怒江。可是最近怒江流域也要進行水電開發了,為此我們心急如焚。” 汪永晨聽到這話后馬上靈機一動,可以利用這些知名人士的影響力來保護怒江。 于是她找到一張紙,就用鉛筆請當時正在開會的各位“名人”聯合簽名呼吁:請保留最后的生態江——怒江。 2004年4月9日晚,在汪永晨的家中,《經濟》雜志記者見到了這份聯名呼吁信。“第一個是張抗抗、第二個是……”這張普通紙上的鉛筆簽名后來通過媒體的傳播,引起了很大的輿論效應。 汪說,也正是這份簽名給很多人惹了一些麻煩。“別人都反駁我們這些簽名的人,‘你知道當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名苦,多么難嗎?’” 華電集團云南怒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建新對這種簽名就比較反感,“你問問他們對怒江了解多少?怎么能對情況不甚了了就說東道西呢?”怒江州委宣傳部部長段斌稱,這些專家學者是脫離實際,憑想象說話,“極端片面地理解環保”。 曾經到過怒江州徒步旅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的一位博士后也對《經濟》表示過這種態度:“抽象地說,我也擁護環保。可是我到了怒江一看才知道,當地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原始、多閉塞、多貧困。怒江搞水電開發可能是他們通往現代社會的唯一通道了。搞環保也應該問一句:誰需要這樣的‘環境’?是衣食無憂的北京人,還是當地老百姓?” 也許是當地人更能感同身受,在云南省環保局分別于2003年9月29日、10月10日召開的兩次研討會上,對于“保留一條原生態河流”問題,云南的專家出現了“一邊倒”——開發。 2003年10月1日,“云南大眾流域”開始對怒江流域進行考察。“那次考察就是要獲得真實的情況!”于曉剛說,“我們希望能以NGO的名義說服當地政府。” “我們把漫灣電站建成后給老百姓帶來的苦難告訴當地政府,我們贈送他們《世界水壩委員會公民指南》,我們與沿途各縣領導交流,希望他們能夠了解水壩建成后在移民、泥石流、生態方面造成的損害!” “我非常驚訝的是,當地很多政府官員竟然說他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他們很驚訝我們提出的想法!”于對此非常感慨。 也正是這個時候,國家環保總局前來怒江調研,云南省政府有關領導陪同。“我們已經聯系好了環保總局的官員,希望向他們表達一個環保民間機構的想法,但是他們臨時回昆明,我們只好在半路等著,眼睜睜看著車子從我們的身旁走過!”于回憶說。 2003年11月,“第三屆中美環境論壇”在北京舉行,這是一次盛會,與會者全部是民間環保組織——包括綠家園、自然之友、綠島、地球村等。據參加論壇的人士講,凡是當時在全國比較活躍的NGO都參加了,200人左右。而最后的議題在綠家園等組織的扭轉下,轉向了如何保護中國最后的生態江——怒江。 “該想的招兒都想了,甚至準備讓自然之友搞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北京辦公室的電話,我們輪流給其打電話,希望‘煩’他們,引起對怒江的注意。”汪永晨說。 據了解,這次會議在環保NGO內部也有激烈的爭論。有人稱如果不修水壩、電站,當地老百姓究竟怎么脫貧,怎么致富?而很多NGO人士激烈反駁:電站建成之后,給老百姓的用電可能比城里還昂貴,移民土地都沒有了,怎么生產? 不管怎么說,“這次會議讓環保NGO對水壩說‘不’的聲音被廣泛傳播”。 同時,中國環保NGO在國際社會贏得了支持。 2003年11月底,世界河流與人民反壩會議在泰國舉行,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參加的有綠家園、自然之友、綠島、云南大眾流域等。 在這會議上,中國民間環保NGO為宣傳保護怒江在眾多場合奔走游說。最終60多個國家的NGO以大會的名義聯合為保護怒江簽名,此聯合簽名最后遞交給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此專門回信,稱其“關注怒江”。 隨后,泰國的80多個民間NGO也就怒江問題聯合寫信,并遞交給了中國駐泰國使館。因為怒江的下游流經泰國。 2004年3月26日-29日,環保NGO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綠家園志愿者的四位代表在韓國濟州島參加了第五屆聯合國公民社論壇,這是為聯合國環境署第八屆部長環境論壇舉辦的。 會上,綠家園代表作了《情系怒江》的專題講演。會議期間,各國代表紛紛簽名表示支持保留最后的生態江河怒江。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托普費爾看了怒江的照片后,提筆寫下:“多美的江啊!水一直是全世界人民最重要的需求。”聯合國亞太地區執行主任索拉塔也在“情系怒江”攝影展首日封上簽名,并專門觀看了“情系怒江”網上的照片。 2004年4月9日晚,在汪永晨家中,記者看到了那些首日封上的簽名,“當時我們還義賣了很多怒江攝影展的照片,很多國家代表非常喜歡這些照片。” 9天怒江之行 2004年2月16日至24日,來自北京和云南的20名新聞工作者、環保志愿者和專家學者,一起走進怒江,進行了為期9天的采風和考察。 之所以有此次考察,一是受了《大壩經濟學》作者麥卡利的影響,二是針對支持怒江大壩上馬的人的指責——環保人士連怒江都沒有去過。 此次考察全程路線設置由云南大眾流域負責,基本按照十三級水電站規劃的路線進行的,不過進入怒江流域的時候,他們的身份卻是“旅游者”。汪永晨、沈孝輝等其他環保NGO的人員都說,這是萬不得已的做法,“如果不這樣,我們的報道、節目很可能要夭折。” “我們是和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在斗爭,如果我們以記者的身份前去,他們會找到媒體單位阻撓節目報道的播出、刊載,這在以前怒江的追蹤報道中,我們是經常遇到的。” 在9天的采訪考察中,他們跋山涉水走村串寨,了解到許多真實的情況,大批關于怒江兩岸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報道出現在媒體上。 很多聽眾、讀者紛紛專門詢問有關怒江的情況,“這讓我們很感動!” 云南大眾流域的于音說,有時候大伙9點還在車上,10點就要在電臺上直播,“很刺激!” 怒江的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給他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怒江22個民族多樣的生活方式就將失去賴以生存的根基;沒有豐富的傳統文化,怒江兩岸自然生態的多樣性,也將難以留存。 2004年4月16日下午,伴著淅淅瀝瀝的小雨,踏著泥濘的小路,經過十多分鐘的攀行,《經濟》雜志記者踏入了怒族集聚地——怒江福貢縣匹河鄉瓦娃村,匹河鄉黨委書記彭虎生說,這里有十三級水電站中一個電站的選址。 村里正在召開會議,大伙在村公所的門前,嘰嘰喳喳地討論著——很多話不好理解。 “我們都喜歡開會的時候喝酒,你別介意啊!”38歲普大益懷著歉意說。普大益是瓦娃村的醫生。 指著不遠處,普大益說,“自從開始打洞(注:設計院勘測)那天起,我們就提心吊膽!” 根據國家電力公司北京勘測設計研究院和華東勘測設計研究院所完成的怒江中下游水電規劃報告推薦的開發方案,十三級水電站建成,水庫移民安置人口為48979人,是三峽電站(約110余萬人)的4.89%。 普大益和他的鄉親們擔心的就是這個移民。 望著窗外的綿綿細雨,普大益心事重重。“我們是最小的世界(注:怒族村),誰也不妨礙誰,誰也不侵擾誰,平平淡淡地生活,吃得飽穿得暖,我們能說得清什么時間下雨,什么時間天晴,我們有自己的生活、風俗、節日,搬了怎么辦呢?” 直爽的村主任桑益普說:“我自己不想搬,但又不是我們說了算!” “從我出生,我就在這里,我也不知道這里是什么時候有的。窮就窮在這里,富也就富在這里,不是嗎?”普大益的目光灼人,“不過,國家如果確實要我們搬,我們也無法違背政策。” 2004年2月18日,這或許是任何一個為怒江付出勞動的環保NGO都能記住的時間,就在這一天中央領導人對怒江做出了批示,這個批示消除了志愿者的顧慮,他們放心的恢復成記者的身份,開始光明正大的采訪。 也就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們籌劃回京后的攝影展,“要讓更多的人了解怒江!”。 “當時每個人都拍了很多照片,本來我們說趕路的時候不拍照的,可是確實太被周圍的景色、老百姓的生活吸引了,幾乎無法克制。” 從2月25日至3月21日,這些環保志愿者沒日沒夜地開始籌備北京怒江攝影展。 沒有錢自己先墊,汪永晨把家里的存折都用上了。沒有時間就拼命地擠時間。 3月14日是世界江河日,“情系怒江”的中英文網站做出來了。3月21日“情系怒江”攝影展終于正式開幕。單是場地就輾轉了好幾個地方才好不容易確定下來。展地在北京站附近的郵局。 “這么大的展覽就是林業局出面搞也要花很長時間,沒想到這么快就搞好了!” 國家林業局高級工程師沈孝輝說。 3月31日這天,一位年過花甲的老人上午來參觀了一趟攝影展,下午又帶著自己的老伴再次前來參觀,并希望環保志愿者們組織去怒江時帶上他們。中國探險協會的王方辰在攝影展后留言:“獨有的江,獨有的民族,獨有的資源,留住它的原有風貌,為了今后。看了它才知道什么是原生環境!” 3月下旬在攝影展上,《經濟》雜志記者碰到沈孝輝,他說要用鏡頭記錄一個坐在輪椅上白發蒼蒼的老人——她是那么仔細地看著每一張照片。 北京“上書”與云南質詢 在云南怒江流域考察期間,沈孝輝就開始醞釀寫作自己的提案,他想在全國兩會期間將自己的議案找途徑提交上去。在返京途中,經過環保志愿者反復討論,兩份提案脫胎而出。 兩會期間,沈孝輝終于成功地將議案提交給了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這個渠道來自于全國政協委員梁從誡。梁告訴沈孝輝說,“我的提案我沒有報,把你的提案全報上去了!”在沈孝輝那間擁擠的房間內的昏暗燈光下,沈說,他聽到這個話真的很感動。 這兩份議案是沉甸甸的。一份為《保護天然大河怒江,停止水電梯級開發》,一份為《關于分類規劃江河流域,協調生態保護與經濟開發的提案》。 在提案《保護天然大河怒江,停止水電梯級開發》中,沈提議:必須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否決《怒江中下游水電規劃》。 而在云南同樣有一種力量開始滋生。 2004年2月13日,云南省政協九屆二次會議上,省政協委員、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戴抗,代表民盟云南省委在民主黨派、無黨派界別聯組會議上發言,對怒江流域的開發提出質詢,認為水電開發應與整個流域的可持續發展統籌起來,未經統籌規劃的水電開發,將會對怒江流域的生態和社會帶來巨大影響。 “這是第一次在云南省地方政府內部出現的不同聲音!”有人評價說。 據參加此次會議的人士說,當時省委有關領導很尷尬,一位省委領導當即表態說:“可持續發展重點在發展、生存與生態,重點在生存!”這個表態讓當時很多與會者很難接受。 而在這次會議后一周,云南省領導即進京學習中央的“科學發展觀”。 這次會議的發言于2月14日出現在《云南政協報》一份影響并不大的《經濟周刊》上,全部的書面發言直到2004年3月31日才在《云南政協報》上出現。 2004年4月13日,戴抗接受《經濟》雜志記者采訪時說,這個提案是在環保組織云南大眾流域的影響下形成的,“專家被很多人認為是一面之詞,可是無黨派人士可以發言,可以質詢政府,也應該得到政府的關注!” 據了解,云南大眾流域內部本身就有很多民盟人士,水之聲論壇民盟也經常參加。云南大眾流域的黃光成在提案形成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黃光成對怒江有10多年的研究,他在我們怒江的調研中相當于軍師。”戴抗說。 直到現在戴抗還記得發言結束之后,于曉剛興奮地對她說,他們民間組織的聲音終于可以通過民盟來發出了。戴抗說,“他們環保NGO非常執著,于曉剛、黃光成,一見面就講怒江,講水壩!” 拖在勝利背后的陰影 2004年2月份中央領導的批文,讓每個關注怒江環保的人都感到一種欣慰,但是這個勝利有一個拖得很長的陰影——貧困,當地政府時時提起的話題灼痛著每個人。 2004年4月15日,怒江州委宣傳部部長段斌這樣形容怒江的貧困:怒江是100%的貧困,是刻骨入髓的貧困。 2003年9月29日,怒江州委書記解毅在怒江開發與環境保護專家研討會上,作了《中共怒江州委、州人民政府關于怒江開發與環境保護的意見》的報告。在該報告中,解毅用數字描述怒江州的貧困情況:在怒江州49.2萬人口中,2002年年末,還有22萬人處于貧困線下,占農業人口的50%以上,年人均純收入在560元以下的極端貧困人口有7萬人,年人均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絕對貧困人口有13萬。 華電集團云南怒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建新激動地告訴《經濟》雜志說,貧窮與美麗我們選擇什么?我們怎樣與全國人民一道奔小康?我們不能光著屁股搞環保。他還想不通的是,自己搞了30多年水電,經歷了那么多水電工程,怎么一下子在怒江就成為“不保護環境的人”了? 怒江州外宣辦科長楊宏斌也傾訴著他們的難處,宣傳部每年只有8萬元辦公經費。“怒江州每年一個多億財政收入的概念是什么?不要說北京,還不到昆明一個村公所一年的收入!而今年,怒江州已經建州50年了!” 在解毅的《意見》中稱,2002年怒江州地方財政收入1.05億元,財政自給率僅為14.7%。2003年上半年,全州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13.1%,經濟增長幅度僅為5.9%。從1953年建州到1995年,國家對怒江州的投入累計9.7億元,占云南總投入的不到1%。 怒江州委宣傳部部長段斌的一個邏輯是,只要水電開發了,老百姓就可以搬遷,也就可以脫貧,同時有了錢,有了錢什么就好做,可以搞旅游,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淹沒了谷底以后,以前山腰中的風景就可以形成新的旅游景觀。據《怒江報》2003年10月22日報道,2003年1至7月份,怒江州全州接待國內游客26.23萬人次,海外游客524人次,旅游收入9825萬元。 段斌甚至認為,十三級水電站的建成其實是有利于環境保護的。他的理由是水電站的建成可以搬遷移民,從而退耕還林。而對于搬遷移民的補償,怎么搬,目前只有大體的說法,還沒有明確的方案。 據了解,怒江州境內有怒江、瀾滄江、獨龍江三大干流及其183條一級支流,水資源總量達955.91億立方米,可開發的裝機容量占全省可開發量的19.9%。 地方政府毫不懷疑一個判斷:水電開發可以脫貧,水電開發是怒江的最好出路,“全州各族人民齊心開發!” 環保NGO在近一年的時間里東奔西走,發起各種活動,讓怒江州“處境很難”。怒江州外宣辦科長楊宏斌說,現在他們很被動,上面要求“少說多做”。對“多做”的解釋就是積極向中央反映怒江的實際情況,爭取得到支持。段斌也稱,目前狀況下,上級要求怎么辦,他們就怎么辦。 云南大眾流域負責人于曉剛說,當地政府稱,既然環保組織反對水電站的興建,就應該找出解決當地老百姓貧困生活的解決方案。“你們政府可是拿納稅人的錢,替老百姓著想這是本職工作,怎么能讓一個民間的環保NGO來解決?”于曉剛對這種說辭非常生氣。 但是即使如此,于曉剛他們還是積極為怒江尋求項目,幫助怒江當地百姓。綠家園負責人汪永晨告訴《經濟》,他們也在積極地籌備錢,“起碼給當地小學建一些圖書室”。為此,汪與她的同伴們到處義賣照片,到處游說,尋求國外基金,“我們都快成乞丐了!” 剛上場的新生社會力量 作為一支新生的社會力量,在保護怒江行動中,中國民間環保NGO表現出了讓人欽佩的意志,展示了不容忽視的生命力,有理由相信,將來他們在中國社會中將有越來越大影響力。 但目前中國民間環保組織還一直在夾縫中游走,步履蹣跚,聲音微弱。 去年在云南召開的幾次環保專家會議,昆明云南大眾流域作為民間環保組織要求列席參加,得到的答復卻是,首先要讓他們明確立場:反對還是贊成怒江水電工程。如果反對,連列席的機會都沒有。于曉剛感慨,與政府打交道太難了。 沈孝輝認為,中國民間環保組織經過20世紀90年代末期到21世紀初期這個階段,已經有了質的提高和量的發展,政府應該給環保NGO應有的地位。“政府應該和NGO溝通、協調,政府應該認識到民間的力量!” “當環保NGO還沒有興起的時候,政府老是在說公眾環境意識怎么這么差;當NGO真正發展起來了以后,又害怕與政府作對,以致無法控制。其實這種擔心是多余的。政府應該學會怎么引導民間環保力量的發展,讓其成為一支推動環保發展的力量,而不是做一些徒勞地擔憂!” 令NGO感動的是,他們越來越不孤獨了,公眾開始越來越多地認識到環保的重要,“這比十幾年以前要好多了!” “我發覺我們的公眾是最可愛的。”公眾的聲援、支持,一直是環保NGO們最大的鼓勵。對此沈孝輝一直感激在心,沈從世界反壩會議回來后,在北京圖書館做了一個關于水壩的報告,當時有位50多歲的老同志參加會議后,馬上提筆給中央領導寫信反映怒江的情況。 對于怒江十三級水電站,一位云南專家對沈說,“我是學者,關鍵的時候還會投反對票的,你需要什么,我給你提供炮彈!”沈的《怒江十問》,也就是在這樣支持背景下產生的。 盡管怒江大壩暫時處于停滯狀態,但是對于民間環保NGO們來說,這只是個階段性的勝利,他們面對的是比他們強大的多的利益集團,怒江依然充滿變數。 2004年年初,怒江州州委五屆六次全會提出怒江發展的戰略目標:兩個國家級基地(水電基地、有色金屬基地)、一個世界品牌(三江并流旅游區)。 華電集團張建新也認為,六庫電站的環境評估報告估計還會批復的。 “不管怎么說,這在中國環保發展史上還是第一次,以前中國的環保NGO都只是停留在‘教育’的階段,觀鳥、種樹、揀垃圾,就這‘老三樣’,現在在怒江問題上卻可以影響政府決策!這是一種飛躍!”一位觀察人士評價認為。 2004年4月9日,夜色沉沉,汪永晨家中。對于怒江的前景,汪依然堅定自己的信念,她的神情有一些悲壯。 “即使怒江上最終還是建了十三級水電站,我們還是要告訴公眾,告訴子孫,曾經的怒江是一個什么樣子!”
|
|
|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國內財經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