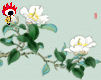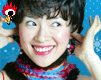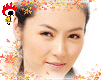| 溫州模式:第二次交鋒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4月18日 16:40 經濟觀察報 | |||||||||
|
-本報首席記者 仲偉志 記者 劉明娟 施春華 溫州報道 在物質至上主義興起的1990年代中葉,“香三年,臭三年”的溫州模式終于從“充滿爭議”變成“充分肯定”,一座普通的城市成為一個時代的信仰。然而現在,一連幾個月,由于GDP等增長業(yè)績在浙江省內相對下滑,以及一些學者與媒體的質疑,溫州模式似乎又進入到“否定之否定”的階段,再次充滿爭議。
一些曾經為溫州模式著迷、并為之極力辯護的人士哀嘆,繼蘇南模式敗落之后,溫州模式也將壽終正寢。還有人說,因所有制問題而一度衰微的蘇南模式,經過一段時間調整,已經重新超越溫州模式——蘇州經濟的成長就是最好的答案。 那么我們究竟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當舊的模式解體,有什么新的可以替代嗎?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說,公眾的迷惘情緒令人驚訝。 每當人類遇到從未經驗過的事物時,雖然他們并不能完全理解,卻往往搜索枯腸,要為這未知的現象厘定一個名目。但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面對中國區(qū)域發(fā)展中最富有戲劇性的溫州經濟社會變遷,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正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惑與焦慮之中。 “唱衰”溫州 在浙江省11個省轄市的GDP排名中,“杭甬溫”長期占據三甲位置,優(yōu)勢難以撼動。但是2002年的統(tǒng)計結果出來后,溫州的GDP出人意表地滑落到浙江省第七位,進入2003年更是每況愈下,上半年名列全省倒數第二,7、8月份則連續(xù)兩月倒數第一。消息傳出,輿論驚覺不安,華南與華東一些媒體開始連續(xù)報道,慨嘆并反思溫州的“衰落”,風潮綿延至今。 溫州市政府辦公廳一位官員告訴我們,許多媒體在2004年的報道中依然使用了2003年9月份之前的數據,有失公允。實際上,2003年,溫州GDP全年達到1220億元,增長14.8%,是6年來的最高水平,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5.7個百分點,其財政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標都快于GDP的增速,名列浙江前茅。 “溫州GDP的基數比較大,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要有10億元的增量。”溫州市市長劉奇在杭州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從具體的數字看,溫州經濟發(fā)展的絕對速度仍是高速的,并沒有像外面說得那么差。” 2003年,在浙江區(qū)域經濟的傳統(tǒng)“三強”中,杭州GDP增長15%,寧波增長15.3%。杭州灣兩岸地區(qū)的增長速度都比溫州稍高,這其實反映了區(qū)域經濟發(fā)展“比較優(yōu)勢”的客觀變化。而衢州和麗水GDP基數小,增速超過溫州也在情理之中。溫州市發(fā)展計劃委員會的一位處長說。 劉奇,這位曾經在衢州擔任巨化集團公司董事長的溫州市長,到任一年后已經可以隨口羅列出一系列數字:溫州市民每百戶擁有汽車13.5輛、電腦64臺、移 動電話?含小靈通?185.8只、鋼琴6臺,擁有比例遠遠高于全國許多城市。這些數字不是更能準確反映溫州居民真實的生活水準嗎?他說。的確,看著這位山東人像他的前任錢興中一樣極力為溫州辯解,真是一個令人感佩的鏡頭。 但是人們似乎難以擺脫那些固有的觀察問題的方向與牽引力。進入2004年1月份,在杭州、湖州、紹興三市工業(yè)總產值增幅達20%以上的情況下,溫州居然下降了1.9%。于是,人們對溫州經濟的運行態(tài)勢和劉奇市長的自我辯護滿腹狐疑。——對不同層面現象的觀察往往容易得出混亂的結論,那么,未來的溫州究竟會有一個什么樣的演變趨勢?溫州模式是否真是每況愈下? 一些來自浙江省內的學者,首先為“唱衰”溫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史晉川教授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史晉川,1957年生,經濟學博士,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浙江省政府經濟建設咨詢委員會委員,長期推崇溫州模式。不過,自從1999年開始承擔教育部首批社會科學重大研究項目——“溫州模式研究”之后,在調查過程中,他逐漸觀察到溫州經濟存在的諸多問題,開始發(fā)出體制危險預警。2003年,他運用歷史制度分析框架闡述溫州經濟,斷言溫州模式將在此后一至兩代人的時間內徹底瓦解。 兩代人與一張“網” 眾所周知,一連十多年,與浙江其他地區(qū)的工業(yè)化進程相比,溫州的制造業(yè)結構演變相對緩慢,基本局限于傳統(tǒng)勞動密集型行業(yè),例如皮革制品、服裝、塑料制品和打火機等,盡管其專業(yè)化分工程度與營銷網絡世無其匹,但增長勢頭已明顯放緩。在2003年,大多數傳統(tǒng)行業(yè)的增長速度低于全市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的平均增長速度,這直接導致了同期溫州GDP增速相對下滑。 史晉川教授據此指出,20多年來溫州的兩代創(chuàng)業(yè)者大多固守在勞動密集型行業(yè),以致溫州的制造業(yè)演變過程出現了“代際鎖定”現象。他發(fā)現,在溫州兩代人之間存在高度相同的交易方式,他們成長的區(qū)域性商業(yè)文化背景相同,擁有的“地方知識”相同,了解的生產技術知識相同,依賴的市場網絡也基本相同。 不過,多數媒體記者將史晉川所說的“代際鎖定”誤寫為“待機鎖定”,將一個原本很有價值的制度分析概念敷衍為一種個人化的膚淺體驗。 這樣的路徑依賴在溫州的確極為普遍,以致被稱為“溫州新生代”、“美女企業(yè)家”的挺宇集團總經理潘佩聰在北京投資文化產業(yè)的時候,許多人都連連搖頭。潘佩聰18歲從父親手中接手生產閥門和儀器儀表的挺宇集團,對傳媒行業(yè)一直有濃厚興趣。她甚至與日本最大的一家電視臺合作,投拍專題紀錄片,自己身兼制片與策劃,而且經常親任主持。她是那種很少能跳出“代際鎖定”的溫州企業(yè)家之一。 那些“絕大多數”們跳不出“代際鎖定”,而外面的資本似乎也很難進得去。史晉川手中的數字表明,作為中國沿海開放的14個城市之一,溫州的外向型經濟步伐同樣極其緩慢,幾乎沒有吸引到真正的外資。溫州的“三資”企業(yè)產值占全市工業(yè)產值比重近10%左右,約為浙江全省平均水平的1/2。2003年1至8月份,溫州引進外資只有區(qū)區(qū)0.8億美元,只有寧波的1/10、杭州的1/5,其外貿出口總額也只有寧波的1/4、杭州的1/3。 “不要說國外投資者,就是國內的民營企業(yè)家,也很少會去溫州投資辦企業(yè)。”史晉川說,“公共權力與私營經濟兩者不斷地相互滲透,形成了一張‘不可觸摸的網’,阻礙了溫州經濟社會的對外開放。”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地方官員出于種種動機——其中并不排斥幫助親友謀求自身經濟改善的動機——默許并支持了私營經濟的成長,并且冒了很大的政治風險。史晉川教授并不否認,公共部門這種行為方式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但他同時指出,政府官員介入具體交易方式,不僅造成了政府在對待溫州人與非溫州人時產權保護的不公平,事實上也造成了溫州區(qū)域內產權保護的“親疏”,導致了民間資本的大量外流。 有一個數據似乎可以支持史晉川的觀點——2003年,浙江省11個省轄市的固定資產投資大都在35-80%之間,溫州卻不足20%。同時,據新聞媒體報道,“溫州炒房團”到外地炒房的資金高達300-1000億人民幣。溫州市統(tǒng)計局的一份分析報告也指出,“資本過分輸出,必然導致當地經濟的衰退”。 一般認為,溫州企業(yè)的外遷與民間資本的外流,多與溫州當地資源(尤其是土地)的制約有關,也與企業(yè)在擴張中不能得到更為完善的要素市場支持有關,但史晉川教授認為,“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是溫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 史晉川說,他在省委黨校講課時也曾闡述過這一看法,得到了溫州市原副市長楊秀珠(時任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的高度認同,認為史教授這一看法是“入木三分”。幾個月后,由于涉及腐敗問題的經濟案件曝光,楊秀珠攜家人逃亡美國,迄未歸案。在這里,楊秀珠成為一個隱喻。 溫州模式:是馬格里布,還是熱那亞? 經濟發(fā)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是那些有效率的經濟制度。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溫州人的自組織是一種擺脫了大共同體束縛、具有獨立人格并自己對自己負責的人們建立的“市民社會”,這個被稱為“中國猶太人”的社會群體應該是小農中國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教科書。 溫州的進步歷代無雙,為什么當新的世紀剛剛開始,溫州模式卻幾乎要在挽歌中落幕? 史晉川教授借用歷史制度分析闡述有關溫州經濟和溫州人經濟,指出了溫州模式衰落的內在必然性。 所謂歷史制度分析,是新制度經濟學家將歷史經驗方法與主流經濟學的博弈論方法結合出的一種經濟史學框架。其代表性人物阿夫納·格雷夫以此研究10-14世紀地中海地區(qū)馬格里布商人和熱那亞商人的交易方式,闡述了不同的合約執(zhí)行機制的形成及其基礎。史晉川從中發(fā)現了溫州人的影子。 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體主義的穆斯林移民,他們形成了一種有利于無限次重復博弈的封閉聯盟,在從事遠距離貿易時,聯盟成員只選擇內部人作為貿易代理人。這是一種典型的人格化交易機制,一旦有某個貿易代理人出現欺詐行為,整個聯盟就會對其作出集體性的、永久和徹底的懲罰。阿夫納·格雷夫稱之為“多邊聲譽機制”和“多邊懲罰機制”,它不僅與政府無關,恰恰是缺乏政府的產物。 熱那亞商人信奉的則是新教拉丁地區(qū)的個人主義。他們在從事遠距離貿易時,不排斥在非熱那亞人中雇傭代理人,他們通過創(chuàng)立“社區(qū)責任制”以及類似法庭組織的仲裁機構,來保證跨時空的陌生人之間的交易合約有效執(zhí)行。阿夫納·格雷夫稱之為“雙邊聲譽機制”和“雙邊懲罰機制”。 史晉川認為,與馬格里布商人的人格化機制相比,熱那亞的非人格化交易機制在貿易擴張中更有效率,熱那亞商人從事海洋貿易的歷史也比馬格里布商人更長久。此后,在地中海地區(qū)貿易活動中勝出的是威尼斯商人,因為他們的交易方式更接近現代市場經濟。 (下轉07版) 現在讓我們來描述溫州人——老大生產服裝,老二生產布料,老三生產紐扣,妹妹負責市場銷售,外地人進來無從插手,即使進來也沒有任何競爭力;子承父業(yè),交易方式和營銷網絡也承襲了下來;溫州本地雖然缺少外來投資,但溫州人卻通過大規(guī)模的移民方式來撒開國內和國外的生意網,從事的依然是傳統(tǒng)行業(yè)——他們與馬格里布商人何其相像? 改革開放之初,溫州以外的地區(qū)不敢與溫州人一樣大膽而廣泛地從事市場交易活動,溫州人的商貿活動甚至還會受到外地人的歧視,所以,溫州人只有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來從事商貿活動,逐步導致一種“路徑依賴”,一方面使得溫州人能以較低的成本進入傳統(tǒng)勞動密集型行業(yè),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溫州人進入新的行業(yè)。因為進入一個新的行業(yè),就意味著進入一個以非溫州人為主的分工體系和市場網絡,必將承擔更大的機會成本和經營風險。 史晉川教授認為,溫州對人格化交易的“路徑依賴”,已嚴重影響溫州區(qū)域經濟的競爭力以及區(qū)域經濟的健康發(fā)展。他說,一個在改革初期和中期確立先發(fā)優(yōu)勢的地區(qū),倘若不能夠與時俱進,進一步開拓新的體制優(yōu)勢,就不可能順利完成從初級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變,也不能很好地完成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 現在讓我們來描述溫州人——老大生產服裝,老二生產布料,老三生產紐扣,妹妹負責市場銷售,外地人進來無從插手,即使進來也沒有任何競爭力;子承父業(yè),交易方式和營銷網絡也承襲了下來;溫州本地雖然缺少外來投資,但溫州人卻通過大規(guī)模的移民方式來撒開國內和國外的生意網,從事的依然是傳統(tǒng)行業(yè)——他們與馬格里布商人何其相像? 改革開放之初,溫州以外的地區(qū)不敢與溫州人一樣大膽而廣泛地從事市場交易活動,溫州人的商貿活動甚至還會受到外地人的歧視,所以,溫州人只有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來從事商貿活動,逐步導致一種“路徑依賴”,一方面使得溫州人能以較低的成本進入傳統(tǒng)勞動密集型行業(yè),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溫州人進入新的行業(yè)。因為進入一個新的行業(yè),就意味著進入一個以非溫州人為主的分工體系和市場網絡,必將承擔更大的機會成本和經營風險。 史晉川教授認為,溫州對人格化交易的“路徑依賴”,已嚴重影響溫州區(qū)域經濟的競爭力以及區(qū)域經濟的健康發(fā)展。他說,一個在改革初期和中期確立先發(fā)優(yōu)勢的地區(qū),倘若不能夠與時俱進,進一步開拓新的體制優(yōu)勢,就不可能順利完成從初級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變,也不能很好地完成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 反擊與“挺溫” 史晉川等人的學理研究,以及媒體大量關于溫州GDP下降、企業(yè)外遷、資金外流的報道,給溫州帶來了極大壓力。 溫州市書記李強認為,這些輿論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qū)——追求最高收益是資本的共同屬性,無論是跨國流動還是在國內流動,本質是一樣的,而溫州人通過資本對外擴張,說明已經進入資本經營階段。“本地企業(yè)到外地投資辦廠,我們認為是好事——因為溫州人掙到錢了,溫州的土地資源卻節(jié)省下了。”他說,“我們都很熟悉日本從國外買資源填海以備后用的事,對于資源少的溫州,道理是一樣的。” 這位市委書記強調,溫州資本是外擴而不是外逃。 媒體的熱情似乎僅僅在于向人們揭示一個煊赫城市的沒落,地方政府官員自然不會坐視。據說他們本來想低調應對,原以為書記與市長的解釋足以抵擋,但沒有想到從浙江省兩會到全國兩會,以及各種各樣的場合,溫州官員走到哪里都被窮追猛問。同時,一個又一個問題往往也令他們備感困惑,啞然無言。 在這種情況下,理論不能繼續(xù)缺席。 其實在媒體與政府之間,學者早已在進行即時和充滿智力性的討論。連續(xù)幾個月來,作為溫州最有名的本土思想家之一,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在全國各地奔走講學,平均兩天一堂課,內容只有一個:溫州模式從來就沒有衰落。洪振寧說,我們不是意氣用事,我們認為對溫州模式的新一輪“唱衰”將導致我們的社會在發(fā)展理念上更加混亂與不成熟。 溫州向來訥于言而敏于行,在別人的爭論中出名,在自己的不爭論中發(fā)展,它只是擁有歷史追授的榮譽。但是現在,對溫州前景的思考,已經變成溫州乃至浙江經濟學者的一項集體性功課。在“唱衰”者的對面,“挺溫”者大有人在。這座山間水湄的浙南名城,無意當中又一次成為爭論的焦點。 浙江大學教授羅衛(wèi)東說:“事實上,關于溫州模式的爭論,至今為止我們都沒有能夠在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上做出回答,比如溫州的經濟績效到底該如何來衡量?衡量溫州區(qū)域經濟和溫州人經濟,其結果有多大差異?如何評價溫州經濟績效的長期變化?溫州與同類地區(qū)的比較到底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再比如在經濟績效和要素、制度約束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這些問題的研究關系到對溫州模式的正確判斷。” 羅衛(wèi)東不同意史晉川就溫州模式所做的比附。他認為,溫州模式既不同于馬格里布模式,也不同于熱那亞模式。根據歷史記載,馬格里布商人的貿易是被埃及人強行終止,從此融入猶太社群,而非經商效率低下而衰亡,而熱那亞人的遠洋貿易更多的是在馬格里布商人退出以后才崛起。也就是說,并不存在兩種商業(yè)模式之間直接競爭的歷史階段,而且經濟進化也不是決定論的。 問題是,溫州人是“類馬格里布商人”嗎?羅衛(wèi)東說,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判斷。阿夫納·格雷夫的調查發(fā)現,馬格里布商人群體是一個人數有限、邊界明確的團體,信息傳遞比較便捷,這是其聲譽和集體懲罰機制行之有效的前提。而熱那亞人在1200年至1300年之間,人口從3萬人增長到10萬人——“數萬人的社會,只能采用個人主義的商業(yè)文化,何況溫州這樣數百萬人的社會,如何來建立和實施基于聲譽和集體懲罰的商業(yè)模式?”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曙光也認為史晉川的觀察“存在著某些含混、牽強和片面之處”。他說,由于伊斯蘭教的背景和約束,馬格里布商人內部是沒有競爭的,而溫州商人由于地域關系,也形成了一個“海外生意網”,其間也會出現某些類似于人格化交易的情形,但地域約束大大弱于宗教約束,溫州人之間的競爭有目共睹,很難形成真正的人格化交易。 與此同時,張曙光先生反駁了目前社會上針對溫州的一些流行觀點: 溫州發(fā)生“代際鎖定”了嗎?——產業(yè)結構演變其實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從傳統(tǒng)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向資本密集型產業(yè)或高新技術產業(yè)轉變,另一個則是在傳統(tǒng)產業(yè)范圍內,從低技術向高技術、從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發(fā)展。溫州作為一個地市級經濟體,第一個方向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很明顯,溫州擯棄了第一個方向而取第二個方向,這是市場的選擇而非政府的選擇。現在,溫州的服裝、皮鞋已經擁有自己的品牌,打火機也裝上了電子機心,依然能夠占據并擴大這個輕工消費品市場,因此,斷言溫州“代際鎖定”為時尚早。 溫州外向型經濟步伐緩慢嗎?——首先,溫州與寧波、杭州的出口沒有可比性,這里不僅有出口結構的問題,也有原產地的問題。此外,如果說引資多少是外向型經濟的重要指標,那么,對外投資也是外向型經濟的重要指標。溫州引進資本少,但輸出資本多,就此而論,溫州外向型經濟發(fā)展并不慢。至于溫州資本外流對于溫州和全國究竟是好是壞,是福是禍,恐怕不能簡單下結論。 ——對于這個問題,溫州上下正滿腹委屈。市委書記李強說,如果中國企業(yè)到國外投資被稱為“走出去”,而溫州資本在國內跨省、跨地流動,就被稱之為“外逃”,這是很不正常的。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則說,溫州資本在很多時候做著與李嘉誠同樣的事情,卻往往得不到公正的評價。 溫州有一張“不可觸摸的網”并因此造成了產權保護上的不公平嗎?——實際上,所謂人格化交易方式,目前仍是中國市場交易的一種基本方式,溫州不可能例外,它并非內生于溫州本土文化。如果公共權力不是一種被公民監(jiān)督和法律約束的有限權力,如果社會資源仍是以政府配置為主,那么,我們就很難切斷政商之間那條灰色的利益輸送渠道。 溫州GDP相對下滑說明了什么?——一般來說,發(fā)達地區(qū)是人口流入地區(qū),不發(fā)達地區(qū)是人口流出地區(qū),地區(qū)GNP通常沒有計算,而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GDP,發(fā)達地區(qū)是夸大了,不發(fā)達地區(qū)卻被縮小了。但是,溫州的情況則相反。作為發(fā)達地區(qū),溫州既是資本流出地區(qū),也是人口流出地區(qū),流入80萬人,流出140萬人,凈流出60萬人。這樣,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GDP是縮小的,如果按照實際人口計算,溫州的GDP肯定比現在大得多。如果計算溫州的GNP(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國民在全球所產出的財富),那可能是中國最高的地區(qū)之一。 “美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如中國快,難道我們就能說美國經濟衰落了?”杭州商學院副院長張仁壽說,“假如溫州市和浙江省其他地區(qū)的統(tǒng)計數字都是真實可靠和可比的,我認為,溫州經濟目前的走勢基本面是正常的、健康的。” 洪振寧則表示,溫州GDP排名下滑不足為怪,這是溫州10年持續(xù)高增長之后的合理調整。這位身材瘦小、閱歷復雜的學者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們:“如果一定認為溫州模式出了問題,問題的根源也不在這里。溫州存在的問題,其實是中國的改革不夠深入、不夠到位的問題。解決溫州問題不應該就溫州說溫州,要解決整體性的問題。” 溫州問題是中國問題 盡管這次爭論已經超越了十幾年前那場姓資姓社的交鋒,具有明顯的實證色彩,其理論含義日益豐富,但是,由于溫州模式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地理經濟名詞,對于中國而言,它的坐標意義遠遠超過它的經濟價值。所以,對溫州模式的再認識和再評價,更應該擯棄一些似是而非的口水。 馬津龍,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員,溫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與洪振寧以及另外一位學者并稱溫州模式研究“三駕馬車”。這位在當地屬于“教父”級的人物,同樣馬不停蹄地四處講學。他對我們說,憑借溫州的地理位置與資源稟賦,它本來不可能在中國經濟發(fā)展中擁有如此顯赫的位置,只因為在改革方式上存在著與全國的時間差和“制度差”,方才有“奇跡”的發(fā)生。 但是產生奇跡的黃金時代結束了,溫州人的優(yōu)勢已經不再是溫州當地經濟發(fā)展的優(yōu)勢。馬津龍說,溫州改革的先發(fā)優(yōu)勢,只是體制外改革的優(yōu)勢。現在,像溫州這樣的市場化領先地區(qū),凡是可以依靠底層力量推動、老百姓能夠做的微觀領域的制度創(chuàng)新基本上都已經完成。當改革深入到體制內階段時,變遷已經不可能自動完成。 杭州商學院副院長張仁壽說,現在,溫州模式遇到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私人產品”的生產問題或者所謂技術創(chuàng)新問題,而是“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問題。這個“公共產品”,并非指現在溫州市政府正在推行的意在優(yōu)化服務的“效能革命”,而是政府體制的改革與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創(chuàng)新。 比如,早在1986年,“中國農民第一城”——蒼南縣龍港鎮(zhèn)就提出與平陽縣鰲江鎮(zhèn)合并設市的設想。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也是一種公共產品。但是18年過去了,規(guī)劃文本不知做了多少,由于兩鎮(zhèn)合并必然要調整行政建制與管轄范圍,影響到一些地方與部門利益,溫州地方政府一直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改變現狀,以致這座中國農民自己創(chuàng)造的“城市”至今鎮(zhèn)不像鎮(zhèn)、縣不像縣、市不像市。 龍港鎮(zhèn)的鎮(zhèn)長對我們說,與整個溫州一樣,“農民城”的先發(fā)優(yōu)勢也已經逐步喪失殆盡,多年來依靠民間經濟力量推動的龍港,正面臨衰退的危險。 再如:溫州曾經有過20多年前利率改革的一馬當先,但時至今日,溫州仍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間銀行;溫州曾經有過十幾年前王均瑤包機的驚世駭俗,但均瑤集團進一步參股航空公司卻發(fā)生在武漢;溫州民間資本在全國范圍炒房,但在溫州本市的80多個行業(yè)中,只有41個允許民營企業(yè)進入。 ——這一切讓馬津龍傷感:改革先發(fā)優(yōu)勢的弱化,以及制度創(chuàng)新的匱乏,反映在發(fā)展上就有一個“時間滯差”,它將在近幾年凸顯出來。如果沒有改革的全面推進,溫州注定要向原來的位置回歸,但是,許多制度變遷的確不是地方政府所能推動的。 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的經濟學研究員盛世豪指出,區(qū)域制度創(chuàng)新空間畢竟十分有限,而且,區(qū)域之間的制度差異也將越來越小。無論你是否愿意,無論你是主動還是被動,從此之后,任何一個區(qū)域的制度變遷都將只是宏觀體制變遷的一個支流。 正如杭州商學院副院長張仁壽所說,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開放性系統(tǒng),它不可能率先在一個地區(qū)范圍內完整建立起來,如果沒有全國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的相應配套推進,溫州推進經濟改革的難度會不斷增加。 從這個意義上講,溫州實際上是率先遭遇了其他地區(qū)即將全面遭遇的另一種失衡問題。于是我們說,溫州GDP的相對下滑,不僅向溫州當地政府發(fā)出了值得重視的信號,而且歷史性地提出了一個嚴肅的課題:在我們的經濟發(fā)展中,必須及時配套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的改革。 |
| 首頁 ● 新聞 ● 體育 ● 娛樂 ● 游戲 ● 郵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點卡 ● 天氣 ● 答疑 ● 交友 ● 導航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國內財經 > 溫州炒房團南征北戰(zhàn) > 正文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