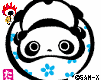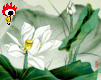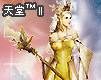| 南方周末:解密溫州商會 娘家、伙伴與情報站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4月15日 11:46 南方周末 | ||||||||||
|
溫州商會在夾縫中滋生,然后頑強地壯大并蔓延到全國各地,成為溫州商人征戰(zhàn)商場的利器,成為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粘合劑”,這種力量如何在轉軌時代發(fā)揮作用? 本報記者余力實習 生肖華 3月24日,萬里歸來探親的陳克平在溫州市柳市鎮(zhèn)旭光村忙到凌晨兩點,圓滿解決了
陳克平是新疆喀什市陳氏實業(yè)董事長。看起來,41歲的他就像村子里的大家長。實際上,一年的絕大部分日子里,他都在新疆扮演著類似的角色——不同之處僅僅在于,那里的“家族”由數百遠離鄉(xiāng)土的溫州商人組成。 他的名片另一面,印著“新疆浙江企業(yè)聯(lián)合會溫州商會會長”的頭銜。 像他這樣的“溫州家長”,全國已有近80個,活躍在除北京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qū)。他們率領數目龐大的“家族”成員,作為170萬溫州在外創(chuàng)業(yè)者的中堅力量,承載著數以千億元計的商品和資本流動。 這些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xiàn)的異地溫州商會,主要由民間自發(fā)組成,獲得了廣泛的合法性,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扮演著日趨重要的角色,被眾多觀察者期許為中國社會中的“第三種力量”。 石頭縫里生長的大樹 1995年8月28日,昆明溫州總商會獲準成立,這一天后來成了每個在滇溫州人的節(jié)日。 “那天放了焰火,在昆明的溫州人一夜狂歡。”現(xiàn)任會長,也是十幾個發(fā)起人之一的張國光對那天的興奮記憶猶新。回憶起一年多的籌備過程,他感慨說“做了無數的‘思想工作’”。 當時,昆明的溫州商人已達3萬有余,在商業(yè)領域已頗具影響力。但“這些在外漂泊創(chuàng)業(yè)的溫州人沒有一個自己的‘家’,困難不知找誰解決,煩惱不知向誰訴說,受了委屈更是舉目無親,眼淚只能往自己肚里流”,漸漸萌發(fā)出聯(lián)合起來保護自己的念頭,于是向昆明市民政局申請成立商會。 未曾料到,申請遭遇了極大的障礙———當時的社團登記管理條例不鼓勵成立異地商會和同鄉(xiāng)會性質的民間社團;一些部門擔心溫州人成為幫派,擾亂市場;同時,對經濟組織政治化的擔憂始終存在。 此后整整一年多,發(fā)起者們四處奔走,反復闡明溫州人只是商人,組織起來只是有利于更好管理,更好地經營,甚至舉出北京“浙江村”的例證;溫州市經協(xié)辦也專門派人赴昆明游說。 多方努力之下,民政局終于允許登記。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合法登記的異地民間商會。 同年10月8日,西安成立浙南工貿協(xié)會(后變更為西安溫州商會)。到1996年底,異地溫州商會已達6個。 盡管先例已漸次出現(xiàn),但隨后的商會成立之路并沒有順理成章地平坦起來。在大連的溫州人就付出了5年多的漫長努力,廣州溫州商會也經歷了近4年的籌備期,分別在2002年成立。 到2004年,據最新統(tǒng)計,已經成立的異地溫州商會達74個,另有6個正在籌建之中。而此時,對于異地商會的政策閘門并未徹底打開。“溫州人的務實靈活,在商會成立的過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xiàn)。”一位政府官員說。 “務實靈活”,主要體現(xiàn)在各地溫州商會對“婆婆”的選擇上。 根據相關政策,這種異地商會均采取“雙婆婆”制———由所在地政府和溫州政府相關部門共同主管。溫州市經協(xié)辦受市政府委托成為一方“婆婆”,而所在地的另一方“婆婆”則并無具體規(guī)定。 出于可以想見的原因,后者往往對商會能否獲準登記至關重要。也正因如此,各地溫州人找到的“婆婆”面貌不一。 在昆明,這一角色由市經委扮演;隨后成立的其他商會中,這方“婆婆”或是當地經協(xié)辦,或是統(tǒng)戰(zhàn)部、工商聯(lián)、招商引資局等。“誰當‘婆婆’都沒關系,只要我們能夠登記。”一位會長坦言。 娘家、伙伴與情報站 “我們有娘家了”,這是異地商會成立后,當地溫州人的第一反應。 對于家族觀念極重的溫州人而言,“娘家”意味著安全、信任與溫暖。小到夫妻吵架,大到巨額合同糾紛,他們都習慣性地找商會出面。 另一方面,溫州人極重面子,“做生意以做人為主,人品最重要。一旦失去信用,在圈子里立不住腳,再做事情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一位溫州老人說。商會因此也具有了自我管理的功能。對于逾矩的人來說,在商會內部進行通報,比政府給予嚴厲處罰還要難受。 但與傳統(tǒng)家族或宗族不一樣的是,聯(lián)接會員的紐帶,主要是利益。“我們溫州人成立商會,第一是掙錢,第二是掙錢,第三還是掙錢。”廣州溫州商會會長劉劍坦言。 要實現(xiàn)這樣的目標,最有效的途徑顯然是與政府合作,以盡可能低的成本獲得資源。“成為政府最好的伙伴”是每個商會的理想。 但這樣的伙伴關系能否建立,最終仍取決于雙方是否有可平等交換的資源。溫州商會的底氣恰恰來源于此:精明的企業(yè)家群落和強大的民間融資平臺,能有效將政府手中的土地、政策、項目等資源轉化為現(xiàn)實產出。資源和資本的交換,使雙方各得其所——政府得到GDP、稅收、就業(yè),而企業(yè)家得到利潤。 至于溫州民間資本的存量,從數百億到數千億,各種版本的數據都在坊間流傳。但對于許多溫州商人來說,統(tǒng)計數字并無意義,“溫州人現(xiàn)在根本不缺錢,就缺值得花錢的項目。只要是好項目,不愁找不到錢。”數億資金通過合股的方式在數日內聚集,已是并不鮮見的溫州故事。 各有所求之下,異地商會自然而然成為當地政府與溫州資本之間的通道。2001年的統(tǒng)計數據表明,當年到溫州的1000多個外地招商團,大部分經由商會安排。 沈陽溫州商會會長胡定海介紹,商會成立后,與沈陽市政府共同組織了幾次大規(guī)模的赴溫招商團,幾年時間里,引回的資金從數十億一路上升到200多億———在此之前,溫州人在沈陽投資鮮有過億。 如此大規(guī)模的資本流動,如何保證安全回報?溫州商人顯然并沒有過于擔心,這得益于他們龐大而靈敏的情報系統(tǒng)———“與境外投資者相比,我們的優(yōu)勢是遍布全國的溫州商會”。一位溫州人透露,他首次到新疆投資時,從下飛機到簽下7000萬的購并合同,不過寥寥數天。在如此短的時間里作出決策,有賴于當地商會提供了全面信息,甚至包括合作伙伴的為人與喜好。 好會長=成功的商會 在四川,溫州商會會長何必獎是個德高望重的“大家長”。 在1萬多人的商會里,“他的發(fā)言權無人置疑”。去年四川各地溫州商會在成都召開年會,上百萬元的會議經費,“我只在辦公室里用了20分鐘,打了6個電話”就籌集完畢。 這種影響力的取得,來自于所有會員的敬服而非權力。他任會長的近6年時間里,四川省溫州商會從瀕于癱瘓成為省內影響最大的民間組織。 一個好會長是成功運作的商會的共同特征,這已成為政府、企業(yè)和商會的共識。 這樣的現(xiàn)象根源于溫州商會的組織形式。 實際上,現(xiàn)今的溫州商會并非橫空出世。早在1906年溫州商務分會就已成立,宗旨是“保衛(wèi)商業(yè)、開通商情”,經費“由商家自行樂輸,就貿易之大小,助捐費之多寡”;商會會長由“勤奮得力為眾商所信服推重者”擔任。 90多年之后,溫州商會依然延續(xù)了清朝時的基本模式。 商會由普通會員、理事會員和副會長、會長組成。會費按照不同級別,多寡不同,如新疆溫州商會,普通會員年費100元,副會長為5000元,常務副會長1萬元,會長則達5萬元。除會費之外,經費可由會員捐贈補充,原則完全沿襲近百年前的“自行樂輸”。 會長采取民主選舉的制度:理事會員提出數名候選人,得到兩個“婆婆”認可后,由理事會員公開選舉。 選舉時需公開辯論、采用不記名投票,競爭往往異常激烈,一些地方的候選人擁躉甚至訴諸武力。原因無他:溫州人極重在“圈子”里的地位,當選會長說明同行認可自己的地位;商會會長可以方便地聯(lián)絡當地官員,建立私人關系;同時,會長本人的企業(yè)在交易過程中更容易獲得信任,也容易得到銀行貸款。 當選會長,意味著承擔起溫州人“高級公關代表”的角色,但同時意味著大量金錢與時間的付出。昆明溫州總商會會長張國光每年1/3的時間用于參加各種會議;接待、陪同政府官員;出席大大小小溫州企業(yè)的剪彩儀式;以及處理各種糾紛。“很多時候,副會長可以不出席,但會長必須出現(xiàn)。”張國光無奈地說。沈陽溫州商會會長胡定海則每年為商會自掏腰包幾十萬元,“做會長的,這些錢應該掏得起,而且必須要掏,否則沒有人看重你。” 這樣的現(xiàn)實,使得溫州商會的會長呈現(xiàn)出兩極分化,用何必獎的話來說,“一個好的會長是把所有會員的無形資產聚集在一起,使之增值,然后由大家共享;一個壞的會長則是把大家的無形資產放到自己或家族的錢袋里”。但實際上,好壞主要取決于個人自律,商會除了改選,并無其他制度約束后者。 何必獎之所以贏得如此威望,在于他從未“利用會長的頭銜為自己征過一塊地,要過一項特殊優(yōu)惠”。于他而言“人活著,除了掙錢之外,總得做點對大家有利的事情”,從別人的認同中,他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但對于大部分人來說,物質的付出總要有物質的回報,在溫州商會不長的歷史里,不乏因會長的自利行為而分崩離析的例證。 都是贏家 溫州人大規(guī)模背井離鄉(xiāng)出外謀生,始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最初的身份大多是小商販、油漆工、理發(fā)師、修鞋匠、裁縫等,干的往往是最苦最累的當地人不愿干的活。眾多溫州商會會長的第一個腳印即始于此。 1980年代初,溫州家庭加工業(yè)開始興起,數以十萬計具有逐利和冒險基因的異地溫州人成為溫州產品的天然銷售者,大規(guī)模的財富積累故事因此在中國各地上演。異地的成功故事激勵著更多人外出,散布各地的溫州人逐漸形成群落,從中下階層上升為當地商業(yè)生態(tài)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1990年代中期,溫州本地的原始積累已完成,資本開始出現(xiàn)向外擴張的需求;而異地溫州人的營商模式已開始從個體商販向商圈經營轉換,溫州店逐漸擴張成溫州村、溫州街、溫州商貿城,“工廠+專業(yè)市場”的溫州模式開始向外克隆。 更復雜的經營需要更高級的組織形式。商會成為現(xiàn)實需要——除了保護自身權益,眾多已完成原始積累的異地溫州人更迫切的需求是組織起來,集體性地獲取信息和資源,以降低成本和風險,更大程度地實現(xiàn)“掙錢的快樂”。 此時,溫州市政府成為商人們的堅定同盟者:他們毫不猶豫地協(xié)助游說異地政府,甚至提出“先發(fā)展,后質量”的思路,加快促成異地溫州商會的建會。沈陽的溫州商會就是在當時溫州市副市長林培云的建議下成立,而南昌溫州商會則是溫州市市長帶隊的考察團直接向江西省副省長請示后,異常順利地得到了批示——2002年8月1日請示,8月3日成立。 如此堅定的姿態(tài),無疑是出于這樣的事實和預期:分散各地的溫州人銷售了40%的溫州產品;“百萬大軍”化整為零,解決了全市1/5人口的就業(yè)問題。再者,異地商會可以民間方式組織、管理在外溫州人,承擔部分政府職能,同時形成龐大的蜂巢狀信息和銷售網絡,延伸溫州經濟的外延。 與溫州相比,異地政府起初的態(tài)度頗為猶疑:國家政策并不鼓勵,突破需要承擔風險。但隨著溫州民間資本對外擴張加速,異地政府對資本輸入的強烈渴求迅速消解了原先的猶疑。甚至在清理整頓民間社團審批的1999年,沈陽溫州商會也因當地政府的特批而得以成立。 為回報政府的信任,各地溫州商會無一例外地恪守“不談政治”的原則。如此,“民間推動、政府承認(默認)、避免‘抗上’”的合作方式成為三方默契,自發(fā)生成的民間商會事實上已被官方公開接受。 三方的利益趨同實現(xiàn)了罕見的多贏:商會成立并開始運作后,云南、四川、新疆、遼寧等地從2001年起獲得的溫州資金均以百億元計,新增的就業(yè)崗位以數十萬計;2002年在外溫州人創(chuàng)造的GDP相當于溫州市的GDP,年終匯回溫州的存款達100多億元。 但是,隨著溫州資本的大規(guī)模外流,舊有的利益平衡逐漸被打破,溫州市政府的態(tài)度漸漸發(fā)生了微妙變化:去年,某位會長帶領一個政府代表團回溫州招商,一貫熱情接待的溫州市政府這次只是“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官,說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話”。 頗為有趣的是,這一兩年來,出于對資金外流影響本地經濟的擔心,溫州一些地市政府開始向異地溫州人進行“反向招商”,希望資金回流。 這種現(xiàn)象被解讀為政府的尷尬,有會長直言不諱地說,“現(xiàn)在的溫州政府最頭疼的就是兩件事———電荒和資本外遷。”但他對此不以為然,“要吸引資金,必須要有資源和優(yōu)惠政策,比如西部一些地方免費提供土地。這樣的政策在溫州顯然不現(xiàn)實,而資源匱乏更是溫州的胎里毛病。”在他看來,資本必然要趨利而去,政府其實也不必過于擔憂———大部分外流資本的收益最終仍會回到家鄉(xiāng)。 制度瓶頸 “溫州商會不是烏合之眾,也并非精英組合,但仍在發(fā)生作用。”這是一個溫州人對商會的評價。 可以觀察到的現(xiàn)實是,仍有新的商會不斷成立,仍有新的會員不斷加入。在大部分商會內部,爭斗與合作一如既往在發(fā)生,“沒有矛盾就不是商會了”。 但對于制度學派的觀察人士而言,恰恰是那些贏得眾多稱許的成功商會,隱含著更本質的危機。四川省溫州總商會,因何必獎的正直公正而井然有序,但何目前最為煩憂的事情是選擇合格的接班人,他仍擔心這樣一個“優(yōu)秀商會”可能因他的離任而改變——顯然,他并沒有留下與他的個人威望媲美的制度遺產。 而胡定海領軍的沈陽商會,爭取到當地政府的極大善待,政府各部門為溫州人特設“綠色通道”———“溫州人的事情不過夜”,而同在當地的諸暨、福州、四川、閩南等異地商會會員則沒有這么幸運。 在新疆,多位商會領導人向記者強調,“這里的投資環(huán)境是全國最好的”。他們的感受顯然發(fā)自內心,但這與眾多權威機構的評析明顯相悖。也許,對于溫州投資者的盛情相待、特事特辦,恰恰在分析人士眼中成為投資環(huán)境不佳的表現(xiàn)。 所有稱職的商會會長,或多或少都與當地高層官員建立了私人情誼。好會長出于公心,讓這樣的私人資源惠及商會普通會員,也不過是將受惠范圍由過去的以血緣為紐帶的小家族擴展到以地緣為紐帶的“溫州人大家族”。非溫州人依然是排斥的對象,曾有沒有自己的商會的外地人試圖加入溫州商會,但是遭到拒絕,理由是“不會說溫州話”。 “先行政策半步”是溫州商人的致勝之道,溫州商人的“務實靈活”和無規(guī)則,極大地契合了這個轉軌時代的特征,并因此獲得了巨大成功。 另一面,眾多的溫州人習慣于游刃于體制內外的窄縫之間,也許已經失去了對更合理制度的主動要求。 現(xiàn)實與理想的距離也許常常只在一指之間。溫州商人們出于自利動機,撬開了異地商會登記的閘門,眾多后來者隨之涌入———僅在昆明,就出現(xiàn)了湛江總商會、福建總商會、潮汕總商會、浙江企業(yè)聯(lián)合會、工商聯(lián)莆田商會、工商聯(lián)晉江商會等異地商會,在西部的陜西、青海、甘肅、新疆,異地商會也不再是諱言的詞匯。最新的消息是,新疆自己的在外企業(yè)也已提出成立異地商會的申請。 制度化的安排也開始出現(xiàn)———2003年7月,云南省宣布,支持個體、私營企業(yè)在云南省發(fā)起組建異地商會,由省民政廳進行登記并對其年度檢查實行隨到隨檢。 這樣的個別事件能否成為經常性安排?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郁建興教授稱現(xiàn)在還沒有答案,而他更關心的問題是:“溫州商會能否促使政府一視同仁地在轄區(qū)內保護私有產權,進而獲得更廣泛的認可?”
|
| 首頁 ● 新聞 ● 體育 ● 娛樂 ● 游戲 ● 郵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點卡 ● 天氣 ● 答疑 ● 交友 ● 導航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國內財經 > 溫州炒房團南征北戰(zhàn) > 正文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lián)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