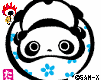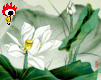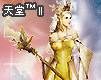| 南張樓沒有答案--一個城鄉等值化試驗的現實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4月15日 08:58 南方周末 | |||||||||
|
為了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農民是應該進入城市,還是應該留在土地上? 從1990年開始,山東青州一個叫南張樓的自然村所發生的變化,給我們提供了與當前大部分農村不同的解決方案。 作為山東省和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一個合作項目,德國人把享譽世界的土地整理
“巴伐利亞經驗”在南張樓村經歷了15年實踐,部分地達到了最初的目標,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與中國農村的現實發生碰撞。 比如,很有意思的一個事實是:南張樓確實實現了把村民留在農村,但更多是通過大力興辦非農產業,這一切恰恰是在違背“巴伐利亞試驗”初衷的背景下完成的。 現在的南張樓肯定不是德國專家理想中的中國新農村的范本,但它也顯著區別于中國農村大批農民進城打工的常態,某種意義上,它是德國經驗與中國現實互相作用又互相妥協的一個結合體。無論尷尬多些還是收益多些,這沉甸甸的15年,是中國人為“三農”命題求解的一次獨特實踐,南張樓的意義更是超越了一個4000人的村落本身。 □本報見習記者 徐楠 3月22日,約根.維爾克到達山東省青州市(濰坊下屬的縣級市)南張樓村。 這個63歲的德國人是漢斯.賽德爾基金會中國—蒙古處處長,在山東省外辦他有個雅號叫做“德國白求恩”。下了車,和以往一樣,頭一個迎上來的還是留著寸頭、腳蹬布鞋的袁祥生。他們相識15年了。 維爾克的中國之行也有差不多30次了。這15年,他們一直在為南張樓村的“城鄉等值化”試驗而奔忙。這是何等感慨系之的一段合作,就如同共同參與了一個孩子的培養,眼看著他一點點成長起來——盡管并不完全是當初期待的模樣。 從巴伐利亞州到山東省 1987年,山東省和德國巴伐利亞州締結友好省州關系,巴州和賽德爾基金會共同確立了一系列援建項目。帶著為項目選點的使命,維爾克第一次來到青州市南張樓村,這個4000人口的大村,除了大片農田和一個冒著黑煙的磚窯,幾乎什么都沒有。矮胖的村支書袁祥生在前面帶路,高大的維爾克跟著他趟過村里的爛泥土路,走過成片的垃圾堆,穿過村民驚奇的目光。 橫七豎八的農舍、坑坑洼洼的地塊,這些景象在北方村莊里,再常見不過了。 那一年,袁祥生41歲,已經在南張樓做了14年村支書。 項目的名稱是“中德土地整理與農村發展合作試驗區”。維爾克的背后,是德國巴伐利亞州享譽世界的土地整理經驗。50年前的德國面臨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問題,農業凋敝,交通落后,自然環境和基礎設施惡化,城鄉差別越來越大。維爾克說,這就是今天中國的現實,德國已經走了彎路,希望中國不要再走。 賽德爾基金會想在中國山東做成這件事。 1990年,一個農業職業教育中心首先在山東平度建起,村莊實驗作為其子項目來立項,基金會聘請的聯絡負責人常駐平度。袁燕那年剛8歲,現在她已經在村委會辦公室工作:“選咱村是因為典型啊——六條:不靠城,不靠海,不靠大廠子,不靠大路,沒礦,人多地少。”她說的這些都是袁祥生后來的總結。 就在那一年,4名德國人進村住了一個月。他們分別是土地整理、水利和建筑方面的專家,還有當時巴伐利亞州土地整理司的司長馬格爾。他們的任務是幫助南張樓制定長期發展規劃。 村里按照基金會的要求組織分組討論。“婦女組要拖拉機;學生組要求改善學校條件;工業組要新設備、要接受培訓;老年組要求整修道路,改造房屋……”袁祥生每組討論都參加了,代表們提的全是“要錢的事”。 “無償的資金援助”,這是村里人當時對項目的本能理解。 “德國人聽了咱討論的那些要求,也不表態,只是笑,估摸聽出全是在要錢。”事后大家猜度著。 最后形成的《南張樓村發展規劃》實際上是張藍圖,把村子劃成了四個區片:大田、教育、工業區和公共設施,總的原則是:同類的功能要連片。規劃不涉及定量目標,也不提資金的事,項目通過論證后,基金會承諾需要花多少錢就撥多少。 從那以后,村中大會小會必談項目的進展情況。 首先是土地削高、填洼、整平、劃方,每個基本“方”東西向300米、南北向350米,當季的糧食一打下來,就重新分了地。田間主要道路硬化了,寬的地方能開小汽車,大田比以前整齊了,播種機、收割機可以沿直線開過去。 接著就是修路。“以前下雨天根本出不去人!全是爛泥。”不滿20歲的袁樂依然清楚地記得兒時的景象。 房屋之間的“胡同”也全部重新整修,路面正中間挖一凹槽,用來排水。 幼兒園和初中的舊房子徹底扒掉了,在規劃中的教育區重建起來。小學校來了德國客人,人家在黑板上寫下一行德文,翻譯朗聲念出來:“南張樓的小朋友,你們好!”1994到1995年,基金會分批選送小學教師到上海、阜陽等地去培訓。中學新建了圖畫室、微機室、勞技室等等。幼兒園和小學的桌子設計成半個橢圓的形狀,拼起來孩子們就能圍成一圈;中學的桌子做成梯形桌面,幾張桌子能拼出個封閉的形狀,是大家圍坐討論的空間。 幼兒園以南蓋了長廊、亭子和小型雕塑,整片區域被劃定為“村民休閑用地”。 1989年6月,袁祥生第一次赴德考察。后來他向基金會主動提出選派年輕人到德國留學。1992年,袁普亮和袁東升開始在慕尼黑歌德學院學習德語。1996年,又去了袁普華和張敏。此外,德方每年資助幾個青年到平度、上海、阜陽等地去接受職業教育。 2000年,“南張樓文化中心”落成,這是一座禮堂,全村共有1013戶,這里有1013個座位。但歐式立柱和歐式色調使它呈現出很不“中國”的風貌,被德國專家說成是“建筑垃圾”。 2002年,民俗博物館在文化中心北側落成,這是袁祥生去巴伐利亞農村考察時的學習成果。挑角飛檐的兩重院落,完全是中國古典建筑風格。展品從村民手中收集,每件上面都用橡皮膏粘個小條,寫上捐贈人的名字。本以為德國人會對此滿意,沒想到馬格爾又急了:“這是規劃好的休閑用地,怎么能隨便占用?” 1990年制定的區片規劃,如今已經基本完成。賽德爾基金會前后投入約450萬元人民幣。2000年,南張樓項目在46國國際農村發展研討會上被專門介紹。2002年,中德建交35周年大型紀念活動在北京舉行,安排南張樓派出了一個代表團,講解和翻譯全由該村村民來擔任。這件事在人們的眼里,被看作是賽德爾基金會極為滿意的象征。 “副業”出名的南張樓 “外村的姑娘說給南張樓的人家,男方哪怕是腿腳不太利索,哪怕長得孬點,都能將就——關鍵他們村里副業多。”相鄰的郭集村村民張秀說。 三月的鄉間滿眼是油綠的麥田,南張樓成了小島,被包圍在中間。 油綠色中間,往往只有幾個稀疏的人影,很多時候一個人也看不到。 張云珍白天的時間就守在自家的美容美發店里,她說:“坡上(農田里)的事現在不咋費工夫,有時半個月也不到坡上去一趟。麥子一春三水(澆三次水)就夠了,一畝地花個半天功夫,俺家三畝地,一半天也就完了。收的時候專門有人開收割機,一畝三四十元錢租上,就都打下來了。” 所以,她的丈夫袁可貴從機械廠下班回來,就能坐在屋里安閑地翻翻《齊魯周刊》,晚上踏踏實實看電視。南張樓的廠子每年放秋假和麥假,各二十天,除此之外沒有公休日。這里工廠的工作時間是上午7時30分到11時30分,下午12時30分到4時,余下點時間,留給人們去照看自家的田地。 上班累了,生意忙了,經濟上有底氣了,農活就被包出去做了。趕上農忙季節,有三四百名外村人在南張樓替人收麥子。 中午11時30分,村里的三家飯館開門營業了。都是家庭經營,父親算賬,兒子下廚,閨女端盤子。客人有不少是來村里談生意的,也有很多跟袁長海家一樣——兩口子都在廠里上班,中午從飯館炒菜帶回去。 下午2時一過飯館就關門,店主一家人該跑買賣的跑買賣,該下地的下地。 南張樓目前的經濟總量里,農業約占40%。一般村民家庭平均至少從事兩項“副業”:上班、種地、開店或者經辦企業,選擇多了,生活的底色就變了。 眼下還有約100名村民在國外務工,村子的人口保持在4000左右,沒有青壯年勞動力大規模外流。維爾克認為:“項目是成功的。” 但很多南張樓人認為,改善生活并使他們留在農村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德國人的試驗,而是“副業”的興旺。不難發現:賽德爾基金會所做的文章,始終緊緊圍繞“土地”。曾擔任村干部的袁崇武說:“看起來他們是更重視教育和群眾福利,對工業上的事好像不咋感興趣。”然而,工業是這里最出名的“副業”。離開了它,南張樓的變遷恐怕要失去一層最堅實的地基。 借助外力的同時,南張樓沒有停止過產業結構調整的自身努力。袁祥生說:“咱兩國工業水平差距太大,他們的工業咱還達不到,咱的工業他們也搞不來!” 1970年代的一孔磚窯和一個油坊,是南張樓最早的“工業”。磚窯被德國專家堅決叫停了,因為嚴重污染環境。1984年村里建立了石油機械廠,選派16個年輕人出去學技術,面向東營油田加工石油機械。后來有了織布廠、化肥廠、飼料廠,因為臨近壽光蔬菜集散中心、周邊蔬菜大棚的種植面積很廣,村集體又做起塑料農膜回收造粒。前前后后加起來,現在共有七八十家企業。 目前南張樓村固定資產由1990年代初的幾百萬元,增加到現在的五六千萬元,年人均純收入接近5000元。村子西邊辟出了一片150畝左右的“開發區”,基本相當于土地整理帶來的耕地面積增量。往后村里新辦的民營廠子會從那里冒出來。 袁祥生去溫州考察的次數最多,他認準了搞民營企業的路子,因此2001年村集體企業全面改為民營時他絲毫沒猶豫。“村里不背那個擔子了!”縣級公路經過南張樓的路段,左右兩邊平房小院整齊劃一,塑料造粒機械24小時不停轉。 就是這七八十家企業,從根本上改變了村民的生活,它們使80%左右的非農業人口成為可能,使青年在農村的職業選擇成為可能。這個數字,還會不斷增長。 村子依然是4000來人的規模。在賽德爾基金會的幫助下,村里不再為交通、文教犯愁,南張樓也以文教中心和集貿中心的功能幅射周邊的自然村。缺少了土地整理后的高效率耕作,“副業”的興旺同樣是不可想象的。人們留在這里,幾成是因為有了平整的道路和整齊的農田,幾成是因為闖世界辦廠子帶來了經濟收益和生存空間?沒人想過這問題。這個村莊的15年有太多記憶,它還來不及細細梳理。 “厲害”的“袁村長” 為了陪同維爾克,袁祥生這些天就住在青州。 他熟悉這里,不亞于熟悉南張樓。這個莊戶人曾是青州市市委委員和濰坊市人大代表。村里到青州不到30公里,到濰坊84公里,他的圓口布鞋無數次在清晨踏進市政府大樓,在那里他豎起耳朵聽著各種各樣的項目信息、投資信息、企業信息。 1987年,德方要搞農村項目的消息就是這樣被他聽到的,他決心抓住這個機會。第二年他的拉達車跑了51趟濟南。后來省政府的門衛都知道:“青州那個胖子又來了,不用登記。” 進入進一步的考察論證時,德方要求中方提供一幅村莊、土地全貌的空中照片,和兩幅帶比例尺和高程的村莊田地地圖。袁祥生也不知道這些東西怎么弄法,但他當即表態:“一年時間沒問題!”德方專家說,巴州的一個村子搞這三幅圖要3年時間。袁祥生憋了個大紅臉:“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年時間保證完成。”馬格爾當場豎起大拇指。 經過與德方專家的多次接觸,袁祥生慢慢明白了:德國人理想中的農村,是安守鄉土的,是自足的、寧靜的。然而對中國農村的事情,他早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不就是戶口本的皮皮顏色不一樣嗎?咱莊戶人哪點比城里人差?我就不信這個邪!” 袁祥生倒是希望村民走出去。村里對考出大學生的家庭給予一次性的物質獎勵;袁祥生親自去給初中生演講,鼓勵他們“出去闖闖”。在南張樓初中念過書的劉建強大學畢業后到青州市當了記者,回想起初中生活,他第一個想起袁祥生的演講。 1992年一個華人從阿根廷回村探親,這讓袁祥生冒出了新想法。雙方達成合作意向:安排村民到阿根廷務工,合作創辦華生農場。誰也沒料到這個開端有多重要。那個時候農村最響亮的口號還是“離土不離鄉”,可袁祥生已經在大會小會上說:“出去一個富裕一戶!” 什么辦法都用上了。不少青年人先以商務考察簽證出國,再轉為勞工簽證。 南張樓的很多人家都并排掛著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出國打工的多了,咱得看看他在啥地方”。 后來有人說:論境外勞務輸出,南張樓在青州搞得最早,等別的村都開始張羅,他們出去的頭一批人已經往回返了。袁長海1996年出國,5年后從美國回來,蓋了新房結了婚,又資助家里搞了個自營的奶牛養殖場,他說:“這幾年我愛玩,花得兇,拿回來近20萬人民幣吧,在村里不算多的。” 機械廠、織布廠、塑料廠,直到現在的奶牛養殖,南張樓搞什么,周邊村子就跟著學什么,但它總能快一步,出國打工回來的人“腦子活,見世面廣,做起買賣反應也快”。 袁祥生說:德國人對這些是一知半解的,“有些事沒告訴他們”。 村黨委會召開的時候總是天剛擦黑。村委會小樓里燈光雪亮,袁祥生站在大幅的巴州風景圖片前面,講他在國外的鄉村見聞:“一戶就老兩口,看不見邊的大田全用機器耕,得空了倆人就騎馬進山去。人家那山呀、路呀,干凈得像洗過似的。”婦女主任鄭慶彬很久以后還記得這些話。 當初搞項目時,有人嫌道路規劃砍了自家的樹,有人嫌公共用地擠占了自家的院子,袁祥生一句話:路照修!誰家不樂意就隔過去,最后誰也受不了下雨天堆在自家門前的爛泥。德國專家再來時,只看到平平展展的大路和胡同。他們感慨:這是“人與人之間緊密聯系的情感和友誼”。袁祥生還是不吭氣,翹著二郎腿抽他的煙。 維爾克把項目獲得的成功評價首先歸功于“袁村長”:“他很厲害——大家談規劃的時候他說起一些想法,我們只是聽一聽,等到再來的時候,已經變成現實。” 德國的風和中國的空氣 清晨,袁祥生散步歸來,坐在賓館大堂等著維爾克。 與德國人打了15年交道,架也吵過,臉也翻過,這個敦實而狡黠的山東人,最終還是擺了張合影照片在自己的案頭,上邊印著“珍貴的友誼”。 1993年巴伐利亞州州長來訪時,村里正在為中學配備桌凳。用于教師辦公桌椅的5萬元已經到位,要求按照德方提供的圖紙制作。為了趕在州長來時裝備好,袁祥生拍板買了40張三屜桌代替,后來項目負責人把錢要了回去,那一次袁祥生火了:“我不用你的錢也能把中學建起來!我不陪你了!”事后他又后悔——人家按要求辦事,于理不虧。 很多時候,他不得不心服口服。1993年給幼兒園做桌椅,德方項目負責人“為一顆釘子釘在哪,都能和木工一起研究幾個小時”。費解歸費解,用了六七年后,買來的桌子都快散架了;可他們指導制作的桌子,至今都沒有變形。 小學音體美教師是基金會組織培訓的重點對象。一人一個圖畫本,每天的功課是“發揮想象力”畫各種東西。四方形的蘋果,或者長著翅膀的魚——都是黑板上的示范。 回村后,“學以致用”的具體做法是給學生布置命題作文——《二十年后的我》、《四十年后的學校》、《五十年后的我們村》。學生們的作文本中,寫得最多的是:“四十年以后,我們的學校一定變得更現代化、更美,有很多高級的設施。” 袁珊珊今年讀高三,袁華在平度念職業教育,他們對自己初中時勞技培訓的回憶,都只是幾節木工課,“畢竟還要中考嘛”。 對于村莊發展規劃討論會,普通村民沒有興趣。“一般村民?你拽他來都不來,來了也坐不下去——開這會又沒啥經濟效益。”當年的大隊干部袁崇武說。 幾乎沒人記得德國人印的問卷調查表上都列了些啥問題,“問咱滿意不滿意,讓畫勾那咱就畫勾唄。” “德國人為啥來?咱沒詳細問,但總覺得吃不透那個精神。” “是不是要挖什么礦?在咱這里提煉啥東西?” 各種各樣的議論在村民中流傳,時間久了也就慢慢平淡了。 論證規劃的一個月,是德國專家在村里停留時間最長的一次。再往后,每次最多三兩天。田間匆匆的走訪、辦公室里長長的會談,對村民來說,項目漸漸隱退到生活的背景之中,德國客人的形象模糊了。 今年20歲的袁偉說:“要是沒人提起來,差不多都忘了有這項目了。” 國土資源部土地整理中心的副書記徐雪林說:“土地整理這方面,群眾參與得還很不夠。” 開發區沿路的一排小樓使德國專家相當不滿,然而對于村民來說,住在那里就是富裕的象征。他們說:“那些在開發區蓋新房的,都在青州城里買了樓呢!”建筑式樣的否定是容易的,有關“先進”和“落后”的價值標尺卻極難改變。 民俗博物館建成了,袁崇武負責拿鑰匙,他經常在里面獨坐一天。有村民說:“俺的名字還在那磁盤子上貼著呢,有啥看頭?再說,俺家門頭(雜貨店)上忙著哩。”小推車、老油燈、村史陳列,還有走廊側墻上“二十四孝”故事的刻畫玻璃磚,只好蒙塵。在村里,博物館是最地道的中國仿古建筑,也是最孤獨的建筑。 張云珍夫婦已經把兒子送到青州的親戚家去讀初中,他們還是覺得那樣孩子才能有大出息。“現在看咱日子也不孬,城里有的咱這也有,可你想想:啥好東西不都是先到城里,然后才到咱莊里的嗎?” 德國人帶來的沖擊是風,而南張樓落腳的這塊土地,是它的空氣。 |
| 首頁 ● 新聞 ● 體育 ● 娛樂 ● 游戲 ● 郵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點卡 ● 天氣 ● 答疑 ● 交友 ● 導航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國內財經 > 關注“三農”問題 > 正文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