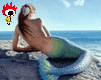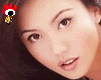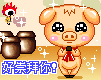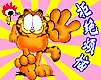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村莊民主與全球化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31日 16:50 中評網 | |||||||||
|
姚洋 《讀書》最近連續刊載兩篇關于村莊民主和全球化的文章(溫鐵軍等:《怎樣的全球化?》,2001年第8期,張鳴:《熱鬧中的冷想》,2000年第3期),其共同點是對村莊民主和全球化表示出深度的懷疑。本文的目的是對這些懷疑做出回應,澄清一些事實和觀念,以利更深入的討論。
溫鐵軍和張鳴似乎特別欣賞中國古代以鄉紳之治為特征的精英政治。鐵軍說:“傳統社會中自有精英產生的一套機制,當需要解釋鄉規民約的時候,社會精英會自然產生作用,不需要的時候沒必要以昂貴的成本來維持。”(溫鐵軍,第3頁)但是,精英政治對于中國鄉村決不是一貼良藥。這并不僅僅是因為它以犧牲平民的利益為代價,而且也因為它在現階段農村的不可行性。 鐵軍和張鳴懷疑村莊民主的一個共同理由是,民主是外來的正式制度,對于中國這樣擁有深厚的鄉村自治傳統和千百萬分散的小農的國度未必適用。“承認和尊重鄉村自治,無疑是中國的古代制度的一種傳統。”(張鳴,第16頁)果真是這樣嗎?如果鄉村自治僅僅指的是官不下縣,這種說法可能是正確的。但是,一個真正的自治體應該有自己的法律和執法機構,但古代鄉村并不具有這種自由。朝廷雖然不向鄉村派官吏,但其法律卻具有普遍性,村莊也不可能成為阻止它侵入的壁壘。溫鐵軍和張鳴將政府行政等同于國家是錯誤的。國家是由政體、法律、行政等多方面構成的,所謂官不下縣僅僅是就行政而言,而不適用于國家的法律以及其它方面。張鳴認為計劃經濟將小農強行綁在國家的“行政列車”上,從而破壞了農村的自組織能力,言下之意是古代國家對農民是放任自流的。我雖是歷史學的外行,但也耳聞中國古代強制性人口遷移和編村制度對鄉村的破壞。中國古代的鄉村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浪漫。所謂鄉村自治,不過是鄉紳之治,或用現代的話語來說,是精英政治。在許多情況下,一個鄉村就像一個中世紀歐洲的城堡,平民與鄉紳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佃戶-地主經濟關系之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哪有一點浪漫可言?中國古代鄉村的自組織能力的源泉逃不脫宗族勢力、傳統倫理、經濟依附乃至地痞政治的范圍。秦暉和蘇文在《田園詩與狂想曲》一書中發現,關中在解放時沒有多少地主,但惡霸不少。這些惡霸橫行鄉里,既是統治者所利用的統治工具,又是魚肉百姓的地痞。同樣,在外人看來,禹作敏的大邱莊可謂秩序井然,殊不知,在這個封建土圍子里,禹作敏父子做盡了壞事。 如果中國傳統還有任何可以為現時所用的話,大概只能是尊重權威、長幼有序的傳統倫理了。但這樣的倫理還存在于中國鄉村嗎?答案是否定的。經過半個世紀、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巨變,傳統倫理已經喪失殆盡。一個例子是家庭的核心化。一般人的印象是,中國農村還保持著大家庭的格局,但筆者所參與的數項調查發現,三、四口人的核心家庭占據著農村的主導地位。大家庭的瓦解使得社會關系原子化,傳統的垂直倫理讓位給了新型的平面關系。年輕一點兒的人的交往圈子早已超出了村莊的范圍,商業關系對他們來說比地緣和血緣關系更重要,盡管后兩者時常被他們利用來作為商業關系的起點。中國鄉村正在商業化和移民的沖擊下在社會層面走向分裂。在筆者最近參與的一項涉及華北、蘇南、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各一個村莊的調查中,我們發現,農村中的社會分層已經完全擺脫了血緣和地緣關系,而以收入作為最主要的分水嶺(劉一皋,王曉毅,姚洋:《村莊內外》,河北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在這樣的情況下,回歸傳統倫理已經失去了組織和動員基礎。 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傳統的鄉紳之治是以鄉紳之知識優勢面對文盲和半文盲對知識階層的尊敬為支撐點的。在以文盲為主的古代,有文化的鄉紳成為統治者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平民對知識的景仰又給了他們統治的權威。當今的中國農村,教育水平固然不高,但教育的分布卻非常地平均化(部分原因是高學歷者進城的緣故),從而使得基于知識優勢的統治成為不可能。劉紹棠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可以用稿費買下北京的一座四合院,現在恐怕連莫言也做不到。原因很簡單,擁有知識的人增加了,知識的相對價值自然就下降了。這是好事,因為知識的平民化正是一個社會進步的標志。 正如鐵軍和張鳴所指出的,古代的鄉紳之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鄉紳的道德感召力。但是,這種道德感召力又是產生于他們的知識優勢或作為村莊長者的權威。正因為此,目前的農村精英們并不具有這種道德感召力。所謂精英,就是那些在村莊政治、經濟或社會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人。在當前的中國農村,這樣的人只可能是兩類人,一類是村莊的富有者,一類是和上級政府關系密切者。他們沒有了古代精英的知識優勢,也沒有因地緣和血緣關系所賦予的權威,因此不可能對其他村民構成道德上的楷模。 中國農村過去沒有脫離國家的介入,今天更是被納入了國家的軌道。計劃經濟時代自不待言,農村改革之后仍然如此,國家在土地制度、計劃生育、稅收、教育等等方面都介入極深;更重要的是,國家法律已經不再遷就宗法制度,而將管轄范圍擴展到農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農民也正在逐漸接受這樣的事實,并積極地利用之(在浙南一個村子里,我們發現,村民已經自覺地運用法律手段來要求罷免他們認為不稱職的村委會)。那種將國家撤出鄉村、使其實現自治的想法是極不切實際的。實現鄉村自組織能力只能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進行。這并不是因為現有的制度無法改變,而是因為它代表了正確的方向,因此沒有必要改變。沒有一個現代國家允許小單位的地方自治;同時,國家法律的深入使得農民個體得到國家的保護,和古代的宗法統治相比,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原生的東西不一定就是自然的東西,至少,它可能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相反,外來的東西不一定都是破壞鄉村自組織能力的。民主是外來的,但卻是建立鄉村自組織能力的一種手段。要說明這個問題,讓我們先撩去籠罩在民主之上的迷霧。 在某些語境下,民主被賦予了道德的力量,但民主的的確確和道德無關,它只不過是公民自愿組成我們稱之為“社會”或“國家”的團體所必需的手段。在一個利益分散的社會里,除了民主,沒有其它可以使人們長期和平相處的政治框架。在這里,抽象的論述可能是無益的,中國的現實也許更能說明問題。在沿海地區的農村,外來人口俱增,在許多地方已經超過了當地的人口數量。但是,這些外來人口是二等公民,他們受到來自經濟、社會和政治各方面的壓迫,而現有的制度架構又沒有為他們提供必要的申述和保護途徑。這種情況如果持續下去,沖突就不可避免。民主對于移民來說不再是抽象的權利,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同時,也只有民主,潛在的暴力沖突才能被和平的討論和對公共管理職務的競爭所消化。 就民主是一種組織手段而言,它往往被賦予過多的責任。比如,許多人認為民主可以消除官員的腐敗,同時也應該促進經濟增長;如果沒有觀察到這些成績,他們就會認為民主是沒有用的。民主單獨不能消除腐敗,在這方面,法治的作用更明顯。民主的矛盾在于,它是公民組成社會的政治基礎,因此必不可少;但是,我們又無法將其發揮到極至,事事由全民公決來決定,而只能采納代議制來解決問題。代議制度賦予官員自由裁量權,從而使腐敗成為可能。此時,法治作為民主的補充物就顯得非常重要。我在這里不想把話題引向民主和法治的關系問題,而只想提醒讀者,不要把法治的失敗錯誤地歸罪于民主的失敗。同樣,那種認為民主應該促進經濟增長的看法也是錯誤的。世界范圍內的經驗表明,民主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確定的關系;在理論上,我們也無法找到民主必然促進或阻礙經濟增長的理由。民主只是公民自愿組成社會所必需的工具,而不是為經濟增長而設計的制度條件。 當我們撩去籠罩在民主之上的迷霧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只關注民主在社會組織方面的作用,這就是我為什么說民主可以成為構建中國農村自組織能力的工具的原因。前面說過,國家的介入已經成為中國農村的現實,精英政治已經失去了政治基礎;同時,道德感召力和知識優勢的喪失使得新精英們失去了被民眾所認同的權威。在這種情況下,民主作為建立權威的替代制度可以是有效的。一些民選的村委會干部之所以敢于公開和村黨支部叫板,和他們所認定的合法性有很大關系。一般而言,在海選的情況下,能夠當選村干部的人一定是村里的能人,或我們所說的精英。在選舉的條件下,他們因此獲得雙重的權威:一方面是產生于他們的群眾基礎的自然權威,另一方面是來自制度對這種權威的保障。因此,從本質上說,民主和自然秩序對鄉村所產生的效果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民主為秩序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并將村莊納入到國家體系中來。無論我們怎樣地不愿意,中國農村還是在經歷著快速的商業化,傳統的農村社區正在解體,鄉村自治只能是對古代的浪漫遐想而已。 鐵軍和張鳴都強調民主的成本和民主的效果問題。關于成本問題,我們必然區分兩種成本,一種是目前的村莊選舉的成本,一種是大范圍民主的成本。后一種成本的確很高,但是,如果民主是解決一個國家政治認同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為此而付出成本是可以接受的,更何況,通過精心的設計,民主的成本是可以降低的(比如,英式民主的成本就比美式民主的成本低)。關于村莊選舉的成本,我們很難說它很高。一個村莊的人數頂多不過三、四千人,三年一次的選舉決不會產生很大的成本。村委會的運作成本也是較低的,集體資產較少的村子只有三、五個干部,集體資產較多的村子干部較多,但他們負擔著村莊管理和資產經營的雙重任務,因此很難說人太多。溫鐵軍和張鳴二人認為村莊民主的成本高,可能是因為許多地方對民主選舉不積極,選舉似乎成了多此一舉。但是,鐵軍自己的觀察已經為這種現象做了一個很好的注腳:“(集體)財產的多少,財產的存在形式,和人們對選舉的參與程度是高度相關的。”(溫鐵軍,第4頁)在集體財產較少的村莊,人們參與選舉的積極性不高,但這與選舉的制度成本無關,而是與人們能從選舉中獲得的收益相關。對于這樣的村莊,一個降低成本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如果村民認為誰當選無所謂,外人不必強迫他們去選舉。美國大選時的參選率總是在50%左右徘徊,但沒有人懷疑美國民主的真實性。那些不投票的人對選舉結果不關心(或認為選舉的收益低于他們所付出的成本),他們不參加投票不會影響民主的運作(至于張鳴以共產黨解放區的選舉動員來反證民主成本之高,似有牽強之嫌。共產黨在解放區搞選舉,為的是顯示她在政治和道義兩方面優于國民黨的一黨專制,而選舉的政治動員顯然也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這里的問題不是參選率的高低,而是是否賦予了民眾選舉的權利。給不給他們權利是原則問題,用不著這些權利是他們的私人選擇問題。如果沒有選舉制度,那些發達村莊的民眾豈不失去了一種有效的村莊治理方式嗎? 民主當然也有缺陷。在象印度這樣多種族、多語言、且歷史上不存在一個民族國家的國家,民主可能是保證她的和平存在的必然政治選擇,但是,這樣的國家的民主也導致了她在許多時候的不可治理性:由于利益的過分分散和制肘,她的政府無法進行有效的決策。同時,許多人的理性棄權也可能給利益集團操縱國家以可乘之機。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因噎廢食不是最好的選擇。對于民主的上述缺陷,我們可以做的是加強法治并建立新的國民的政治認同。這個話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范疇,需專門的文章加以討論。 最后,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村民選舉。村民選舉是一個試驗,是一個學習過程,同時,也是一種示范。在目前的政治結構下,以村莊為單位的孤島式民主肯定會出現許多問題。研究者因此應該進行仔細的分析,認清哪些問題是民主自身產生的,哪些是由于外在的限制產生的,只有這樣才能對癥下藥。我個人認為,村莊民主所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來自村民自身,而是來自外在的政治結構。將目前村莊民主所遇到的問題歸罪于民主之與傳統的不協調,表面上看是試圖揭示深層原因,實則是掩蓋了主要矛盾。產生這種傾向的主要原因,我以為,是幾位論者對感性知覺的過分依賴。這不僅表現在他們對民主的看法上,而且表現在他們對全球化的看法上。 鐵軍等根據對印度喀拉拉邦的考察引發了對全球化的討論。他們的觀點以劉健芝的話最有代表性:“當中國的燈泡進入印度市場,帶來的壓力就是讓印度勞工的工資降低。這實際上就是把所有勞工價格一致化,使他們的生存條件同一化到最低、最受剝削的程度。”(溫鐵軍等,第8頁)我不知道劉健芝的“同一化”指的是誰的同一化。我所知道的是,當中國的燈泡出口到印度之后,中國生產燈泡的工人的境況改善了。難道是中國的工人剝削了印度的工人不成?印度的人地關系比中國還緊張,但工人的工資卻比中國工人的工資高,而素質又比中國工人的低,這是印度的問題之所在。這是一個獨特的國度。一方面,她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另一方面,她又長期實行著類似于社會主義計劃的經濟政策。其中一項主要內容是對國內工業的保護,它導致了國內企業的高成本和在國際市場上的低競爭力。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暗自竊喜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轉變,使得中國的產品在印度這樣的國家也能具有競爭力。要素價格的同一化是一個經濟體系走向效率的表現。印度工人的高工資所反映的是她對勞動力以外的其它資源價值的低估,因此必然產生浪費。當然,市場產生非人性的東西,但解決的辦法不是閉關自守,而是積極的應對。 鐵軍認為,全球化只是資本單一要素的全球化,“單純強調資本全球化的背后,隱含的是反對勞動力和土地要素的全球化。”(溫鐵軍等,第9頁)這一判斷有兩個問題。第一,勞動力不能自由地跨國流動的確是一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涉及民族國家的主權和文化遺產問題,要解決是極端困難的。如果中俄邊界開放,中國人大量涌入俄羅斯,以中國人的勤勞,定能在俄國扎根;但是,這樣一來,俄國就不再是俄國了。作為一個民族實體的俄羅斯必然對此做出反應,其后果不堪設想。即使是像美國這樣的大熔爐,大量低成本工人的涌入也會降低當地的生活水準,從而導致沖突。人口的跨國流動意味著一個民族國家的嬗變甚至瓦解,因此理所當然地要受到接受者的抵制。第二,盡管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土地流動不過是勞動力流動的表現),但產品和資本的流動已經足以抵消它在經濟方面的負作用。以一個農民為例。如果他可以在市場上出賣他的產品并自由地租入或租出土地(相當于資本),則他是否能夠出賣他的勞動力或雇傭他人對他的生產不會產生影響。比如,如果他想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話,他租入土地以利用他的富余勞動力可以起到和出賣勞動力同樣的結果;相反,如果他想雇人,則他可以租出土地。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情形是一樣的。比如,中國的人力資源豐富,充分利用這些人力資源的一個辦法是輸出勞務,另一個辦法是進口資本,只要國際產品市場是開放的,兩個辦法的效果就是一樣的。 那么,資本的進入會想鐵軍等人所認為的那樣,將勞工的生存條件壓低到“最低、最受剝削的程度,”并“同時也把所有自然資源的價格壓低,變成資本的收益”嗎?答案是否定的。讓我們還是用農民的例子來做說明。假設一戶農民原本有兩個勞動力,四畝地,每畝地的凈收益為每年400元,則每個勞動力每年的收入為800元。假設種地是這戶農民的唯一收入來源。那么,要使這戶農民放棄種地遷入城市,則他們每人在城市的收入至少應該也達到每年800元(考慮到搬遷的經濟和心理成本,實際收入應該高于此數)。我們因此可以認為,這戶農民每個勞動力的價格是每年800元。現在,假設天上掉餡餅,這戶農民的土地突然增加了四畝。那么,他家每個勞動力每年的收入變成了1600元,即他們的價格上升了一倍。土地對于農民來說是資本,資本的增加提高、而不是降低勞動力的價格;這是因為,資本(土地)是勞動力的互補生產要素,資本的增加提高勞動力的生產率。一個國家的情形要比我們這個農戶的例子復雜得多,但實質是一樣的。在其它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只可能提高勞動力的價格,而不會降低它。 那么,怎樣解釋深圳勞工工資十多年毫無實質性增長呢?這個板子決不能打在外資身上,我們應該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這個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中國有幾乎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這些勞工的境地是不是因為外資的進入而變壞了呢?顯然不是,因為否則的話我們又如何解釋內地農民向沿海地區源源不斷的流動呢?(有誰會自愿去受苦呢?)這些農民留在原籍雖然閑散,但生活未必好,這是每個做農村研究的人都清楚的事實。他們到了沿海地區之后,境遇雖然沒有我們所期望的那樣好,但總比他們在家閑著好。我這里沒有提倡對勞工在沿海地區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視而不見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認為國家需要做許多事情(參見拙作《社會排斥和經濟歧視》,載《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3期),其中之一正是村莊民主,不僅僅是對本地人的民主,而且也是對外來人口的民主。 至于外來資本的進入是否會壓低自然資源價格并變成資本的收益的問題,我們要做具體分析。從資源的開發增加全球資源供給,從而壓低世界價格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給上述問題一個肯定的答案。但是,即使是這樣,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以下三點。第一,資源的國際價格的降低對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包括資本的輸出國。第二,資源的開采增加就業;同時,如果外資不進入,本國可能無力開采。第三,說到底,對資源的開采是一個主權國家可以控制的事情。也許,一個發展中國家更看重眼前利益,因此急于開采自然資源。但這樣一來,我們也就無法怪罪外資了。對自然資源的開采使本國和外來資本共同受益,不存在外資獨占的問題。如果真有問題的話,是發展中國家的眼界問題。 鐵軍等人還擔心資本流動會導致法西斯化。從理論上講,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總是會有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外資問題挑起民族和種族問題的。但是,仔細分析一下,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可能性不大,至少不會比人口流動所帶來的可能性大。前面說過,外資進入有利于本地工人,因此,法西斯化缺乏群眾基礎。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由于對日本的巨額貿易逆差而不得不將包括西爾斯大廈這樣的房地產賣給日本人,一些人因此強烈要求美國政府予以干預。然而,這種呼聲并沒有得到多少響應。原因是,日資的進入非但沒有傷害美國,而且還有利于美國經濟的增長。至今,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外資最多的國家,我們卻沒有觀察到它的法西斯化。相反,在外國移民大量涌入的德國,特別是經濟蕭條的東德地區,法西斯勢力發展得非常迅速。原因在于,外國移民壓低了當地的工資,搶了當地人的飯碗(當然,德國法西斯的遺毒也可能是一個原因)。盡管人們還可以就上述判斷進行爭論,但是,資本不會比移民更容易導致法西斯主義是可以肯定的。 黃平關于全球化正在對民族國家產生沖擊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種沖擊的后果是好是壞還是可以討論的。首先我們應該看到,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沖擊不僅僅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而且也是針對發達國家的。這是一個全球問題。我們沒有必要以一個弱者的面目出現,以消極的反全球化的態度來對待這個問題;相反,我們應該積極地加入世界性的討論,成為各種規則的制定者。其次,民族國家的松動可能在一個國家內部造成一定的緊張,但卻可能成為維護世界持久和平的一種重要力量。比如,黃平提到跨國公司正在造就一批沒有國界的中產階級,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民族國家松動的表現,但是,這批人的存在也造成了利益的跨國界分布,從而降低了國與國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鐵軍和張鳴等人對鄉村精英政治的向往來自于他們對中國古代鄉村浪漫而模糊的認識。北大哲學系一位教授在前不久提出建立儒家人文保護區的設想,提議在曲阜、西安等地建立儒家文化的示范區,并視其成就推而廣之。這位教授糊涂得可愛。鐵軍等人的精英政治主張沒有達到教授的水平,但也是一個脫離中國現時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幻想。他們對全球化的看法更是意氣多于分析。關于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已經有許多實證的分析和計算,我們的討論應該是基于這些分析和計算的結果來展開。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被意氣遮蔽了理性的眼睛,民眾需要的是冷靜的分析,而不是意氣的發泄。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姚洋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