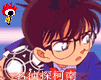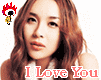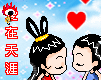| 經濟學:書架上藏著的輝煌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27日 14:54 中評網 | |||||||||
|
張 軍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80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后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
古典體系 眾所周知,至少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等等。而在1750-1870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則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于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后人對于什么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當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羅賓斯,《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那么,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這部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的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后的馬歇爾那里轉換成了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范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后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 O’Brien)在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的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 M. 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后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在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而且沒有繼承斯密的關于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后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 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余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后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余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么,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布勞格,“古典經濟學”,載《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1 卷,第480頁)。 作為剩余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里學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余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 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做的這樣的高度評價: “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方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么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于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采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余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轉引自熊彼特,《從馬克思到凱恩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頁)。 不過,提起“作為剩余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 Sraffa)所做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 von Neumann)一樣僅靠3 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余產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們今天干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英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我每次走在劍橋的古老學院的臺階上,心靈都無不為之震撼。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A. Pigou)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后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 A. Marshall)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 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于法國的瓦爾拉(M. Walras)、古諾(A. Cournot)、德國的屠能(J. Thunen)和英國的杰文思(W. 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范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為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記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并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后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熊彼特語)。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并大力傳播的。凱恩斯(J. M. Keynes)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事實上,他經常去倫敦在政府財政部掛職,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由著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帕廷金(D. Patinkin)等人撰寫的凱恩斯的條目就長達34頁。 凱恩斯是在馬克思逝世的那一年即1883年出生的。他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于他的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的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于《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 “在《通論》中, 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并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坂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后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于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哪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夸大了。’”(“約翰.梅納得.凱恩斯”,《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第383頁)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自己還在傾心于《貨幣論》的寫作。頁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意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這是作為經濟學搖籃的劍橋在3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這個俱樂部里,除了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F. Ramsey)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 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 Robinson)、以及后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 Meade)。 提起拉姆齊,他杰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后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并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于鮑莫爾(W. 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后,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 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的理論而被授予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金。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26歲的拉姆齊悲壯的謝世使劍橋失去了一位知識巨匠,使哲學界失去了一位思想家。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是劍橋學術俱樂部的唯一一位女性。她和卡恩是昔日的同窗(不在一個班)和后來的親密的同事。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她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 Kaldor)和卡萊斯基(M. 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后她致力于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后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于凱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在經濟學家的心目中,她也許是一個沒有獲得諾獎的真正的得主。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想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并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過去的十年來,無論在倫敦經濟學院那著名的“經濟學家書店”,或者是在擔綱“英國政治和經濟科學圖書館”的萊昂.羅賓斯大樓內,抑或是在其他我去過的大學,我總是喜歡駐足在高大的書架前瀏覽五彩繽紛的經濟學著作。在滬上嘉華苑我新搬入的寓所里總算有了一個自己的“工作間”,面對喧鬧的“嘉里不夜城”,聽聽鋼琴,翻翻經濟學,算是我唯一的奢侈了。電腦旁放著的兩本經濟學至今還沒有擺上書架。一本是科爾內(J. Kornai)教授親筆簽名的《短缺經濟學》的珍藏本,另一本則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記念本。這是為了紀念《經濟學》出版50周年而出版并由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中國代表處的一個朋友今年7月贈寄給我的。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氏的這本《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 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么。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并不知道”。 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于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的《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那里他領教了漢森(A. Hanson)、列昂惕夫(W. Leontief)、熊彼特和著名的數理經濟學家威爾遜(E. Wilson)等著名教授的風采。更重要的是,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后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M. Friedman)、施蒂格勒(G. Stigler)這兩位后來先后于1976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F. Knight)和維恩那(J. 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后經西蒙斯(H. Simons)和德累克特(A. 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能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 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于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 Wallis)等,雖然更忠實于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采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 (O. 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杰出的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并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 舒爾茨(T.W. Schultz),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于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 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到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于“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終囿于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做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后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并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做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 G. Lewis) 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年)和加里.貝克爾(G. Becker)關于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年)是早期的兩個例子”(里德,“芝加哥學派”,《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1卷,第454頁)。貝克爾由于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 F. Modigliani) 和米勒(M. Miller)1958 年關于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后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 Lucas) 所領導的經濟系里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于1990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后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于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后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于后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 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斯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里,真實世界總是趨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這其實不正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嗎? 毫無疑問,“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不僅僅是因為在迄今為止的44位經濟學諾獎得主中芝大占有最多的比重,更重要的是,芝加哥的經濟學思潮及其延伸以其與眾不同的特征和風格成了當代主流經濟學的主要基礎。 書架上擱著的成就 的確,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從“古典的”到“新古典的”,從劍橋的“學派”到芝加哥的“學派”,她的發展和成型歷程還只有3百多年。在眾多社會科學的分支當中實屬“小弟弟”。但經濟學發展之驚人速度令不少學科望塵莫及。在我看來,經濟學在今天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我們再也無須通讀它的“歷史”來成為今天的經濟學家。事實上,即使就最近100年來的經濟學思想之演進,我們知道的經濟學家的名字也早已并遠遠超出了我們對他們的作品的了解。這看起來可能并不是一種我們今天的可悲,而更是榮幸。經濟學家熊彼特曾經以隱喻的方式表達過他對上個世紀的經濟學的看法:“我們可能喜愛、仰慕佩魯吉諾筆下的一位婦人,因為我們認識到她完美地體現了她 那個時代的思想和情感,然而我們也同樣意識到我們與她的距離已是多么遙遠”(熊彼特,《從馬克思到凱恩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5頁)。 我不知道在過去的300年出版了多少經濟學的著作、共創辦過多少專業雜志。但我相信,經濟學的文獻現在占據著任何一家圖書館的很大相當大的一部分書架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我們事實上還擁有了經濟學的專業圖書館。我們把這些事實用來描述經濟學在過去幾百年來的成功標志也許并不嫌過。當然,經濟學辭典的出現應是另一個必要的標志了。在目前世界上被認為最具權威的經濟學大辭典《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該辭典的前身于1894年問世,現收入2000多個詞條、4000多頁,由34個國家近1000位著名經濟學家和當時在世的13 位中的12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著共同編纂而成)中,把經濟學的圖書館和專業雜志的出現專列為詞目,令我贊不絕口,個中原因便不言自喻了。 據說,直到17世紀,經濟文獻還只是個人的收集品。甚至在18世紀也不是所有的經濟學家都依賴這些收集的文獻,如馬爾薩斯和李嘉圖。即使斯密的《國富論》也只引用了大約100位作者的文獻。然而到了19世紀,沒有經濟學文獻的圖書館似乎已經不可想象了。沒有倫敦大英博物館的文獻,馬克思要展示其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的能力是極其困難的。斯特奇斯在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是撰寫的“經濟學的圖書館和文獻使用”的條目里提到(《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2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5頁),在1901年英國的私人收藏家福克斯韋爾出賣的他一生搜集的藏書成了后來倫敦大學圖書館戈德史密斯藏書的基礎,而1929年賣給哈佛商學院的藏書則成了哈佛貝克圖書館的重要藏書來源。1896年在倫敦經濟學院建立起了現在著名的“英國政治和經濟科學圖書館”。在20 世紀的歐美,政府部門和相關組織也往往成為經濟學圖書館發展的重要來源,這包括1913年的美國商務部圖書館,英國貿易部圖書館,設在日內瓦的國際勞工組織圖書館以及巴黎的商工會圖書館等。另外,始建于1914年的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圖書館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圖書館,而且它的編目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被認為是傳統的經濟學文獻編輯方法的頂峰。 經濟學和經濟研究的快速成長必然要求更快捷的學術交流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顯然需要要改變傳統的著書立說的方式。在17-18世紀的經濟學家那里,我們幾乎看不到他們的研究論文。實際上,第一個經濟學的專業雜志是1886年才創辦的,它就是哈佛的《經濟學季刊》。1911年,《美國經濟評論》的誕生使美國最終確立了它在經濟研究上的學術中心的地位。從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發展程序上來說,這些專業的權威雜志的陸續創辦更加使經濟研究的活動變成一種比較獨立的學術活動,甚至經濟學研究的論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一個基本上由學科本身和研究者內部的結構來決定的問題了。 總之,在17、18世紀,擁有大量的藏書和文獻方能使一個人成為經濟學家變得可能,亞當. 斯密曾經風趣地說,我并不講究穿著,但我在買書上卻是個“花花公子”。的確,據《亞當。斯密傳》的作者約翰.雷的考證,斯密的藏書大約為2800卷(《亞當。斯密傳》,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493頁)。可是在19世紀末,即使象埃奇沃思(F. Edgeworth)這樣的大經濟學家也根本離不開圖書館的經濟文獻的書架來從事研究工作了。毫無疑問,從那時以來,書架上擺著的數不盡的經濟文獻的確成為人們從事經濟研究的基礎,但我們從書架上看到的更可能是數百年來經濟學所取得的輝煌之成就。面對這些浩如煙海的文獻和非凡的成就,要試圖說明誰是重要的,或者誰是更重要的人物可能已經沒有了意義。盡管我們在上面必須得提到或渲染一些“大人物”,但本文想力圖展示的其實并不是這些人物,而是數百年來經濟學在這些人物背后所經歷的激動人心的時代。 1999年12月4日于滬上嘉華苑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張軍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