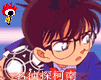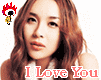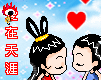| 走近“經濟研究”?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27日 14:49 中評網 | |||||||||
|
張 軍 如果有人說,研究經濟的職業人士也不一定都真的理解經濟研究的過程,他肯定會被認為是在口吐狂言。不過,下面這段話多少會讓我們冷靜: “實際上,我們的確可以從評閱送交刊物發表的原稿中,看出作者在研究方法論方
這是我最近讀到的出現在《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論》(英文原名Research Methodology in Applied Economics;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一書“導言”中的一段話。這部由美國作者唐。埃斯里奇(Don Ethridge)撰寫的經濟學研究生的教科書,其目的是對經濟研究的方法論的程序化方面做出深入的“研究”和敘述。但它顯然也是一部研究“經濟研究”的學術著作。由于我近年來對經濟研究的程序化過程頗為關注,因此這部著作成了今年以來吸引我的為數不多的學術著作之一。 我雖然從事經濟研究多年,可是我想我們大多數人至今還只是這一課題的學生而不是它的權威。我從來不認為諸如“什么是研究?”以及“如何做研究?”這樣的問題是故弄玄虛。事實上,猶如作者所說:“‘研究’這一術語會激起人們對一些活動的想象,而對大多數一般人來說,這種想象或者說是不完整的或者說是錯誤地得到的。這是因為,恰巧有一些專業化活動正是這樣的。按照許多人的想象,忙碌于實驗室的那些人,身邊到處是試管,化合物和正在研究的物體;而在圖書館里,他們則被掩沒于堆積如山的文獻中。雖然這兩種活動正確地代表了一些研究方式,但他們都不能完整地提供經濟研究過程的圖景。”(第16頁)我記得倫敦大學的研究生在注冊時都會領到一本關于如何做研究以及如何撰寫科學論文的手冊,其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很多年之前我就聽說,美國經濟學會的經濟學研究生教育委員會曾對經濟學研究生教育缺乏對學生在從事經濟研究的程序化和研究能力的培養深表擔憂,并強調指出,如何欣賞經濟學研究論文,如何組織和從事經濟學研究,是完成研究生學業和將來從事學術活動的基本要素。 不過,這個話題不僅僅與美國的研究生有關。這部著作與從事經濟研究的“我們”也有相當的意義。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可謂披荊斬棘。自然,不少人對這一艱難發展的過程有很多的解釋,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還是概念的沖突。我們傳統上理解的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是不同的。特別是,我們所理解的經濟研究在方法論的程序化方面與現代經濟研究是有相當距離的,這還不包括我們對現代經濟學還存在著的一時還難以澄清的許許多多的誤解。近年來我的腦子里常在反省著一個問題:在我們的刊物所發表的數不盡的文章中,即使是“研究”經濟的,有多少(包括我自己的)可以算作經濟“研究”的呢?我所以反思這樣一個問題,是因為我認為“研究”這一概念有時侯在我們這里好象已經被濫用到了完全喪失其含義的程度。事實上,“研究”這一概念的濫用正在使我們大學的經濟學研究生教育受到更嚴重的損害。對這一問題的更加清醒的認識會在閱讀了這部著作對科學的經濟研究程序和制度規則的“研究”之后很快得到。 我不想把埃斯里奇在書中對“經濟研究”給出的定義在這里復述出來,因為我覺得這樣做無法將我對作者原義的理解表達出來。我寧可把我的解釋熔進原作者的定義中,但我將使用原作者所有的“關鍵詞”。于是可以這樣來定義“經濟研究”:經濟研究是尋求對經濟事件,現象或經濟諸現象之關系的可靠的解釋,而可靠的解釋只有在一個有計劃的設計得當的并且科學細致的理性程序中才是可能的。這種程序遵從了科學界和學術界的某種公認的規則(我綜合了作者第2章和第3章的主要論點)。也許,人們對這一定義所可能產生的唯一疑問是,經濟學研究為什么要對研究的程序作出類似自然科學般的要求,這樣的要求很容易喚起人們對經濟學是不是“科學”的爭論的回憶。自然,社會科學研究的是人以及那些本身不能受控的,或不能在實驗室進行實驗觀察的現象。但是,正如埃斯里奇所提到的那樣,其實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別可能僅僅在程度而已。而且,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經濟學家為了找到替代實驗室的方法已經發展了更為復雜的多變量概念和計量分析的技術來研究社會經濟現象。更為重要的是,一些人由于經濟學不能利用傳統的實驗室或者由于它的研究領域所限而將其排斥在“科學”范疇之外,其實他們只是根據特定的方法而不是根據方法論(即研究的程序和遵從的規則)來給科學下定義的。所以,從經濟學所積累的知識基礎,它的描述性知識和程序方面看,它當然是一門科學(這是我對第3章前半部分論述的小結)。 可以見得,這樣定義的經濟研究,作為一種具有嚴格規范和研究程序的科學探索活動,顯然是受到實證主義,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影響的。雖然并非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全然信奉純實證主義哲學,但源于自然科學的邏輯實證主義哲學自從19世紀末馬歇爾時代以來確實已發展成為經濟研究的主要的哲學基礎,其影響力至少在本世紀60年代之前是獨一無二的。在此之后,一股實用主義而非實證主義思潮開始對經濟研究產生一定的影響。不過,由于實用主義者的主要興趣是“解決”問題而不是“解釋”問題,因此,實用主義者并不太關注規則性知識的增長,而僅根據概念在解決現實問題中的實用性來評價理論。與實證主義哲學在經濟研究的專業基礎問題上的持久的影響力相比,這種實用主義的影響還主要局限在“非專業基礎問題”的研究方面,包括專題研究,應用研究和對策研究。 談論實用主義,我不得不提到中國經濟學界近兩年出現的一些值得擔憂的傾向。可以說,也許受制度主義經濟思潮的影響(制度學派被認為帶有某種實用主義的哲學基礎),以一種膚淺而又極端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實用主義”正成為一些學人用來呼喚“為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的衣缽。更有甚者,有的人竟把十幾年來成長起來的中國新生代經濟學用“屠龍術”做了幾乎全盤的否定。甚至,還對經濟學家做了這樣的譏諷:“一些據說曾轟動一時的中國經濟學家,在紙上縱馬弛聘之時游刃有余,而一將理論用之于實踐則一觸即潰,凡‘下海’者大多殺羽而歸,偏偏是那些未入流的準文盲在商海中如魚得水。”“實用主義”的邏輯在某些學者那里發展到如此極端乃至荒唐的地步,我只能感到失望。更讓我失望的是,類似這樣的言論在今天居然能夠贏得不少的轟動和喝彩,這只能是一種可悲了。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水平雖然在改革開放以來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但整體來說在國際上還是相當落后的。我特別認為,原因主要是“經濟研究”還不被作為一種嚴格遵循科學程序和規則的尋求知識增長的系統過程。“研究”的程序化還不被廣泛接受。結果,實證性的研究難以受到真正的重視,要么用實用主義取代實證主義,要么把實用主義庸俗化,嚴重影響了經濟研究水平的提高。在這種局面下,我們的大量對策研究的憑空想象和粗制濫造就肯定不可避免了。不過,要使這種局面有所改變,我們大家所要努力的不是什么“將經濟學重新引回到道德的,政治的道路,為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而是腳踏實地地樹立經濟研究中的制度規范,提倡并鼓勵經濟研究中的的邏輯經驗主義精神,健全經濟學家的理論素養。實際上,我從埃斯里奇的這本著作(特別是第四章)中得到的一個認識是,對經驗主義的依賴并不完全排斥實用主義。以計量經濟學來說,它的發展為在經濟研究中不僅使用數據檢驗理論假說的有效性同時也為政策研究和建議奠定基礎提供了可能,從而它不僅代表了一個興旺的研究領域,實際上也構成了每個經濟學家的基本分析訓練的一個必要知識和技術。因此,正如埃斯里奇所說的那樣,“計量經濟學包括經驗數據和計量,這使計量經濟學更具有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性質,并使它不再僅僅是數理經濟學的抽象邏輯。”(第80頁)可是,如果把實用主義“庸俗化”,甚至徹底排斥邏輯實證主義,那么對我們經濟學和經濟研究水平的提高確實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危害。好的,現在我們應該重新回到埃斯里奇的“研究”中去,探詢他所指的經濟研究的程序化過程。 那么,研究的程序化是指什么呢?埃斯里奇實際上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從第5章到最后的第10章),也就是在書中的第2篇和第3篇做了全面的“研究”。研究的程序包括研究計劃的設計(第5章的內容),研究性問題的提出和表述(第6章的內容),文獻的檢索,評論和參考文獻的注明(第7章的內容),概念框架和理論假說的建立與邏輯檢驗(第8章的內容),經驗方法和檢驗程序(第9章的內容)以及研究論文的寫作(第10章的內容)。接下來讓我主要針對第6章關于研究性問題和第8與第9章關于概念框架和理論檢驗的問題做一些評論,因為我認為這些東西對于我們在經濟研究中澄清一些方法論上存在的誤解是有重要意義的。 埃斯里奇把研究性問題與決策性問題作了區分,因為研究性問題需要的是認識,描述和解釋,一句話,是知識;而決策性問題則需要知道采取什么行動。他說,“我們所有人都面臨決策問題和行動問題,問題在于,對于行動或要做的事情,要在不同的路線之間進行選擇。研究可能提供知識和規則,但它不能做出決策和執行決策。”(第112頁)在基礎的專業學術研究中保持研究性問題與決策性問題的距離并不是說決策問題不重要,而是希望作為決策問題之基礎的知識或信息盡可能保持中立和客觀。事實上,在政策制定和行動決策中遇到的問題往往并不是基礎研究中的問題,也就是說,不是專業內提出的問題。這使得經濟研究的結果大多數往往僅對專業內的同行感興趣,而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正因為這樣,除了專業基礎研究之外,我們還需要專題研究和對策研究。對后者來說,研究性問題與決策性問題被聯系在了一起。不過,遺憾的是,埃斯里奇的書是一本談論經濟研究方法論的著作,這個問題好象特別由研究性問題所提出,因而對決策性問題沒有展開討論。 研究決策性問題確實是非常難的一項工作,其主要的困難在于,研究性問題的結果并不總是能為決策性問題的研究提供直接的幫助。就其性質而言,決策性問題常常迫在眉睫,這與專業研究本質上是累積性的發展過程形成一對矛盾。在經濟研究方面,這種矛盾可能表現為,一方面經濟學家常常基于已有的理論知識對政府的政策持批評性意見,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又在重大的政策選擇問題上爭執不盡。有很多原因使我相信這對矛盾不會消失,只會發展,正因為如此,經濟研究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才被格式化了。在一些公共決策問題上,當經濟學家經常因之被抱怨,被批評和被懷疑的時候,我正好看到了一種方式,一種經濟研究影響公共政策的方式(這使我想到了經濟研究文獻中所謂的“摩菲定理* )。遺憾的是,這種方式(至少在職業經濟學家之外)好象還沒有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更廣泛的認同。 凱恩斯說過,經濟學是一門按照模型進行思維的科學。這句話點出了概念框架在經濟研究中的重要性。這也是埃斯里奇的第8章所研究的問題。他把經濟研究中的“概念”定義為“對一個或更多關系進行思想的邏輯結構。“(第145頁)他說,“概念化針對問題而不是目標或方法。它純碎是概念性的,即不考慮經驗證據或數據,它的主要功能是形成有意義的假設并為其正當性提供思想基礎,進而,這些假設還要經受檢驗。”(第146頁)顯然,概念化的主要功能是幫助研究者形成理論“假說”,即形成有待經驗檢驗的嘗試性斷言。假說是概念框架中邏輯推理產生的結果,根據我的理解和經驗,這個邏輯推理的主要方式是盡量導出可檢驗的命題來(最常見的檢驗是統計檢驗)。埃斯里奇轉引的古德和哈特(Goode and Hatt)在《社會研究的方法》(1952)中的一段話也闡明了相同的含義:“演繹的系統闡述,。。。構造出一個假設;如果得到證實,它就成為未來理論結構的一部分。因而,十分清楚,假設與理論之間的關系的確非常密切。。。雖然兩者決不可能完全分開是一個事實,但是,將它們視為科學增進知識的方式的兩個方面卻是有益的。理論闡述的是事實之間的邏輯關系。如果這一關系有效,根據這個理論,則可以演繹出應該是真實的其他命題(假設)。。。假設期待的是,命題可以通過檢驗來決定它的正確性。”(第153頁) 定性的假設,無論是預定假說,診斷假說,一般都把“邏輯一致性”作為其合理性的檢驗標準。為了便于經驗檢驗,埃斯里奇基于他人的研究提出,定量的理論假說則應該具備下列的一般特征,即,假說必須用術語做出具體的陳述;必須具備可利用的或可生成的數據;必須構建得足以運用分析的技術以及必須有一個概念的基礎。 對于概念化(理論的構造)的實施程序,埃斯里奇在書中認為至少應包括以下步驟:領會與你的研究有關的研究文獻;把問題盡可能壓縮到最簡單最有條理的程度;確定可應用的經濟理論;用一個基本模型開始分析的概念化過程;將分析模型的分析擴大到問題的其他方面;從概念分析中發展出有關的和可檢驗的理論假說,并盡量按邏輯順序給出。 既然概念化的過程往往始于模型,那么一般來說,理論模型的建立是經濟研究工作中最難也是最充滿想象力的工作。對經濟學家來說,模型的建立全部或部分地來自于現有的經濟理論,常常是為了解釋特定的問題而對現有的理論做出某種改造。模型可以是理論的,也可以是經驗的,但往往是借助于數學公式加以表示。這產生了一種使得經濟學家確實難以抵擋的誘惑,即如果不能數理化就稱其不存在。埃斯里奇在書中借用布雷邁爾在其論文“農業經濟學中的科學原則和實踐”中的一段話表達了對數理模型的基本看法:“數學方法的使用不能替代嚴謹的理論闡述。。。相反,它本身要求對其組成的結構做出更準確的理解。”(第165頁) 在經濟研究中,概念化過程之后的工作就是檢驗假說的工作。埃斯里奇在第9章做了分析。埃斯里奇提到,在經驗檢驗方法的發展歷史上,19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穆勒做出了重大貢獻。穆勒對實驗設計進行了形式化,特別是,穆勒提出的“一致方法”和“差別方法”對實驗科學和實地科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不過,穆勒的實驗方法的原則在今天僅被視為“相關”關系的證據而不被當作因果性結論。經濟學研究的幸運之處在于,隨著20世紀初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采用,將穆勒的“差別方法”的思想發展了。統計技術,特別是回歸分析的廣泛應用,使經濟研究在“受控實驗”不可能的前提下找到了一個“控制”不同變量的手段。計量經濟學的發展更是極大地推動了經驗手段的進步。不過,經驗觀察和統計/計量技術僅能幫助我們建立和確認經濟變量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聯系或存在相關性,而因果關系的證據只能來自于概念和理論模型的推理。 我相信,許多經濟學同行都會對這一理論框架的構建方式表示認同,而且我們很容易在歐美經濟學期刊上發表的大量的經濟研究論文中找到這一研究范式的影子。這也是為什么作者在該書的每一章末尾都建議讀者從近期經濟學雜志中選擇并仔細閱讀論文的理由。事實上,至少我的個人體會是,經常閱讀(真正的)經濟研究論文是掌握研究規范和改善研究水平的有益途徑(我想提及的是,在《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最后附有一篇博士論文的典型范例,值得研讀),因為,每一篇經濟研究的好論文都成為我“走近”經濟研究的新起點。 至此,埃斯里奇的這本著作我已經基本讀完了,但有關“經濟研究”的話題還有很多。我記得1995年我從美國訪學回來后曾與《經濟學消息報》的主編高小勇先生商討,決定在“消息報”上開辟一個欄目,專門為讀者就如何做經濟學研究提供探討的陣地。為此我還寫了按語,其中提到了克魯格曼發表在《美國經濟學家》雜志上的文章“我是怎樣做研究工作的”。這一文章的具體內容我已基本忘卻,但現在仍能記起他總結的“研究之規則”:1. Listen to the gentiles; 2. Question the question; 3. Dare to be silly; 4. Simplify, simplify.我想,在經濟學說史上,這四個規則的每一條是都可以講出許多故事來的。我平常喜歡通讀很多學問家(特別是從事自然科學的大師)的自傳,因為我發現往往從這些傳記中我們才能真正領略到他們身上的科學精神和治學的經驗。治學本身是一門更大的學問。在復旦大學的校園里豎立著一塊刻著復旦校訓的大理石,它上面的文字精煉地記述了中國傳統的治學精神和學問思想--“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它似乎以更簡化了的(借用克魯格曼的第四條)結構也表達了同樣精髓的思想。不過,我們今天真正需要的是“行動”。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張軍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