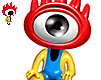| 憲政建設:中國改革的新階段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25日 17:28 中評網 | |||||||||
|
趙 曉 “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個個體都有其自身的運動規律,和執法者施加的規則不是一回事。如果他們能夠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類社會的博弈就會如行云流水,結局圓滿。但如果兩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結果將苦不堪言,社會在任何時候均會陷入高度的混亂之中。”
------亞當.斯密(1759) 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 一、憲政建設的內涵遠遠高于“修憲”: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理解“修憲”與憲政 修憲成為經濟學家無不重視制度及制度變遷。這是因為,“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演進的誣蔑破綻經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道格拉斯.C.諾斯)。 這樣說吧,一個社會的資源條件好比說土地啊,礦產啊都是給定的,與此同時技術也是給定的,按理說,這個時候,這些條件將決定生產的最大可能性邊界,或者說經濟發展的機會了。其實不然,因為這些生產要素狀況以及技術狀況能否得到發揮,完完全全地要取決于制度約束,而在通常的情況下,制度通常都會制約資源和技術的最大限度的發揮,使經濟增長達不到潛在增長率水平,嚴重者甚至“鎖定”于長期停滯的悲哀增長路徑。 二戰后的發展經濟學家只重視資金的積累和技術進步等通常的經濟發展條件,卻忽視了制度對經濟增長的約束。所以,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失敗得一塌糊涂。后來的經濟學家就聰明多了。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的經濟學家,言必稱制度,中國的經濟改革也完全建立在相信制度變遷能夠消除對經濟增長的技術和其他生產條件約束的假設上。 中國改革開放證明了制度創新的神奇。“山還是那座山,梁還是那張梁”,資源和技術約束并沒有變化,但因為有了制度創新,生產力便神奇地呼喚出來,1980-2000年間,中國實現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長,超過日本和韓國在高速增年年代的記錄。而擺在中國人前頭的仍然是進一步的制度創新,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張維迎教授放言,如果將遍布于中國社會的消除一舉管制,中國的經濟增長決不止于“七上八下”(指年均增長7%-8%),每年至少增長30%。誠哉斯言! 制度的變革顯而見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但是,制度變革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究竟如何才能確保制度變革的成功呢? 早年,遍讀諸子百家時曾經讀到過孫中山“知難行易”四個大字。中山先生對制度創新有一解。在他看來,其中的關鍵是人的思想認識問題,人的思想認識變了,則行為將變化,行為變則天下大變。因此困難的并不是行為的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從這樣的角度講,規則的變化也罷,世界的變化完全也罷,完全取決于思想的變化。 更簡言之,以“知能行易”的觀點看制度變遷,就是人心的變化在前,制度的變化在后,人心的變化困難,制度的變化容易。 在少不更事的我看來,這種觀點嚴重違背了物質決定意識的原理,具有濃厚的唯心主義色彩。豈能接受?!所以,很久以來,盡管我知道“知難行易”是貫穿中山先生一生的重大思想,是他對于民族文化的新的貢獻,卻從未放到心里去,也沒有太將這一思想當一回事。 但是,當我認真學習了《圣經》,尤其是結合對制度經濟學的認識讀了《圣經》中著名的“腓利門書”時,我卻有了豁然開朗的感覺,感覺到中山先生思想的深刻和精妙。再聯想到中山先生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我便知道了中山先生的制度變革思想或許是來自《圣經》。 讓我們先重溫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集大成者是道格拉斯.C.諾斯,其著作《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英文版,1990;中文版,1994)第一次構建了一個制度分析的框架,成為任何研究制度及制度變遷的基礎。如何理解“制度”?在書中,諾斯下過一個定義:“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諾斯這樣說,在我們聽來未免還是顯得抽象。不妨更通俗地來理解,好比說你要到某個陌生的地方去,你必定需要一張地圖,或者知道大致的方向,而你要和陌生的人打交道,你對于如何處理你們之間的關系,哪些是該做的,哪些是不該做的,你們倆得有個共同的“譜”,這個“譜”可能法律、規章、可能是行政命令,可能是你們彼此的合同,可能是風俗習慣,可能是國際慣例,可能是約定俗成的“潛規則”,還可能是任何心照不宣的東西,這個“譜”如同你的行為指南,你的人生“地圖”,沒有它你寸步難行。 對制度認識的一個誤區是以為只有正規制度(法律文書、紅頭文件)才是制度,忽視了制度其實是一套復雜的體系,是一整套制度結構,是任何對人們行為構成約束的東西。諾斯說“制度包括人類用來決定人們相互關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約”,它可能是正規的,也可能是非正規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諾斯認識到非正規規則是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認識非常重要。否則,我們將永遠無法明白:對于沒有文字的原始社會,以及缺乏成文規則( 沒有“憲政”,也沒有“紅頭文件”)的部落,你卻不可視其為野蠻民族,認為制度從來沒有君臨其上。 事實上,沒有制度就沒有社會,因為人們要靠制度來減少人和人之間行為的不確定性。所以諾斯強調說:“制度在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相互作用的穩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想象外星人被拋到地球,或者你突然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因為對制度的陌生和無知,必定會出現手足無籌、動輒得咎的情形。 制度是相對穩定的,否則不足以起到降臨不確定性的效用,但是,制度又是變遷的。無論是習俗,行為規則,行為規范還是法律以及人們之間的合約,制度始終處于演進之中。 是什么導致了制度變遷呢?按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制度變遷的一大動力來自于相對價格的變化。譬如,諾斯等證明,歐洲的農奴制度在黑死病后,因為奴隸變得稀缺,價格升高,奴隸主為避免奴隸逃跑而得以改變成自由雇工制度。制度變革的另一大動力來自于不同制度之間的競爭(在這一點上制度經濟學家們的認識頗類似于文明史學家湯因比所指出的文明演進的“挑戰-應戰”模式)。由于競爭壓力的存在,在停滯經濟中的政治企業家將被迫效仿那些更為成功的政策,從而廢除無效制度-----存在于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計劃經濟制度是因為與市場經濟制度競爭失敗而改弦更轍的。鄧小平說過一句很老實的話,中國必須改革,因為中國周邊的國家和地區都發展起來了,老百姓一比就會有問題,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可見全球制度競爭的壓力是中國制度變遷極其重要的動力來源。 這樣說,好象我們已經很理解制度變遷了。其實不然,我們對制度變遷仍然知之甚少。在青木昌彥等關于制度的最新研究中,認識到制度的可實施性(制度創新是否有效)是困難所在,并將制度概括為一種博弈均衡,但卻發現制度均衡可能有多重解(經濟學家有時也稱之為“共時性問題”)。 研究制度變遷的一大困惑就在于,盡管正規制約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決定的影響而在一夜之間發生變化,但是,在考慮政策時,內含著習俗、傳統和行為準則的非正規制約可能更多地是不受影響的。因此,可能出現的一個情況就是,一個國家引進了新的正規制度,但非正規的制度卻制約著正規制度的作用效果,甚至與正規制度發生激烈的沖突,最終導致正規規則的失敗。我們可以舉巴列維伊朗的事例,當時巴列維致力于伊朗的現代化,為此引入了一系列新的正規制度,然而,伊朗社會非正規制度的惰性極強,兩者的沖突的結果是巴列維的倉皇逃竄,以及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全面復辟。 諾斯以此總結了世界上為什么有些國家會變富,而另外一些國家則鎖定在貧窮之路上。原因就在于“理性人模型的說法會很容易地使我們誤入歧途。行動者常常根據不完全信息行事,且他們常常通過想象處理所獲得的信息,這樣就有可能導致無效的路徑。政治和經濟市場中存在的交易費用會導致無效的產權。但是,當行動者企圖理解他們所面對問題的復雜性時,他們的不完全的主觀主義模型會導致這類產權的持續存在。”將諾斯的話翻譯成人人能聽懂的大白話就是:經濟學家常假設人是理性的,又是擁有足夠信息的,其實現實中的人們既不是那么聰明,也常常缺乏足夠的信息,因此他們總是憑借著腦中的一知半見行事,其行為好比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你當然不可想象他們一定能夠一路順風,諸如無效產權的長期存在并沒有什么奇怪的,經濟陷于長期停滯也沒有什么奇怪。 這樣的話,可想而知,讓人們一齊變得更聰明一些,讓人們一齊擁有一些新的信息并接受之便是制度創新成功的關鍵。 這樣,我們就又回到了我們前邊“知難行易”的討論。我們發現:原來中山先生的思想與現代制度經濟學居然是絲絲入扣地暗合! 歸根結蒂,無論我們所要取消的制度,還是要創立的制度,均有其取消和確立的理由,而理由的根本無非在于取消舊的制度、創立新的制度能夠改良人生,帶來更多的社會福利。假設正規制度依舊,而每個人的人生能夠得到改良,社會福利能得增進,那么制度實際上就成為死的東西,取消與不取消,確立與不確立都無關緊要。這翻譯成諾斯式的語言來說,就是制度的精神應重于形式,非正規的規則更重于正式規則。換形式,不換精神,正式規則雖變,非正式規則不變(有中國歷史學者近年來用“潛規則”概括之),則在平等自由制度下所發生的不平等、不自由的束縛,可能比在獨裁專制制度下所發生的還要多。換精神而暫留形式,則在奴隸制度之形式下,主奴亦能相親相愛,誼同兄弟,情若家人,主奴身份形同虛設,并且猶如身體長大了衣服遲早得換一樣,形式最終也將隨精神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因此,制度創新成功的關鍵是改變制度中的人的共同信念,所謂變人心即變規則,變規則即變天下。如青木昌彥所講的:“新制度的出現只有當參與人的決策規則在新的條件下相互一致,其概要表征導致的各人的信念系統相互趨同時才能實現。” 有人說,二十世紀是個沒太有出息的世紀。因為二十世紀缺乏自己的思想,而是做了19世紀思想的試驗場。二十世紀的確將19世紀的各種“主義”行了個遍。但是,有些制度變遷并沒有取得成功,有些制度付出了過高的成本,有些制度創新至今仍在痛苦的變遷中。總體而言, “革命”的遺產成為二十世紀的一大鮮明特色。但是,制度經濟學的反思卻是:制度變遷從來都是邊際演變的,正規制度的表面上的變化并不足以帶來真正的變革。現實與理想的反差無疑值得我們深思。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趙曉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