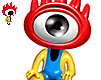|
鐘 偉
在東亞奇跡遭受金融危機的重創之后,人們開始重新反思所謂“東亞模式”,激烈批評者稱此模式不過是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拙劣復制品,熱烈鼓吹者則堅持“東亞奇跡既非虛構,亦未終結”。在亞洲仍為自身的成就和挫敗頗感茫茫然之際,美國“新經濟”已經締造了驚人景氣,歐盟11國也進行了人類有史以來發行區域貨幣的嘗試,所謂
“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這樣的論斷再度顯得遙不可及。一種稱之為“日本病”的東西正使得亞洲經濟黯淡起來。
日本病的病癥之一是重視后發優勢(Backwardness Advantages)。在西歐產生現代工業文明以來的幾個世紀中,亞洲一直處于世界體系的邊緣、半邊緣狀態,因此亞洲國家和地區幾乎毫無例外地有一種緊迫感,即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試圖通過植入西方市場經濟的架構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現代化。這種思使得亞洲國家不必要象歐美先行者那樣,經過無數次市場的起落和崩潰、無數爾虞我詐的案例及其處理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場運作框架,通過“后發優勢”亞洲國家可以迅速追趕上先行者,歐美國家花費了數個世紀才使得人均收入超過了2000美元,而很多亞洲國家用了不足50年時間就達到了。但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這種思路也有致命缺陷:1、“拿來”會產生排異反應,西方市場架構中的契約、信用和個人負責精神碰到“亞洲價值觀”就變形,從而導致淮橘北枳,例如西方商業銀行制蛻變為日本銀企勾結的主銀行制;西方股份制蛻變為日本法人交叉持股制等等,這些變形都被掩蓋在“具有本國特色”的借口之下。2“拿來”會使亞洲缺乏創意,模仿和學習西方較之獨立摸索當然省事,但習慣于此則可能產生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等方面的貧乏,換言之,因為你有了游泳教練并學會了游泳,反倒使得你根本就沒有留意原本可以乘舟而渡的便捷了!3、趕超到接近先行者時,作為后來者突然會陷入到“無航標”的茫然之中。這在80年代的日本尤為突出,當年美、歐、日幾成三足鼎立之勢時,日本迅速地迷失在無榜樣的困惑中。亞洲國家在看到所謂“后發優勢”的同時,是否可以時刻提醒自己這其實就隱含著“后發劣勢”(Backwardness Disadvantages)呢?
日本病的病癥之二是突出產業政策。歐美市場經濟的制度架構有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兩方面,宏觀層面大致是政府對有關競爭、行業準入等法律框架的完善,提供適當的公共產品以彌補市場失靈(Market Externality);微觀層面則是私人部門進行交易的秩序。但日本在兩者間插入了一個中觀的東西:產業政策,即政府可以引導資源注入特定的產業部門,迅速造就所謂的“支柱產業”。盡管產業政策(Industry Policy)已經被視為經濟學誤區,但日本等亞洲國家至今仍對此津津樂道。產業政策在亞洲垂而不死折射出市場機制始終在亞洲得不到根本尊重。1、如果產業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也就是說政府有預見未來新興產業的方向,此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嚴格優于市場機制,市場經濟就是多余的,如果產業政策是失敗的,那么政府就沒有任何必要搞產業政策。2、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展本身就表明,市場機制是“看不見的手”。我們似乎始終不能理解風險的本質乃是事先的不確定性。曾有這樣的笑話,說既然股票等證券資產的總體收益率比銀行貸款還高3個百分點,那么只要從銀行貸款炒股票不就可以進行套利了嗎?這種說法顯然忽視了這3個點的利差是高風險下集體理性的事后結果,作為個體投資者的投資既可能獲利頗豐也可能傾家蕩產。產業政策的荒謬性也恰恰在于政府忽視了新興產業的涌現,是私人部門在所有可能的方向進行各種形式創新后,在市場機制的大潮撇去失敗者足跡的“事后”結果。凡患此病癥的亞洲國家,在有跡可循的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時往往是比較成功的,但再邁向技術或知識密集型產業時便手足無措。當一個故事尚未開始時,誰知道其結局?當一種產業政策被執行時,卻誰都不為其失敗負責,至今沒有誰為日本80年代中后期大力扶持模擬技術、忽視即將到來的數字時代的失敗負責,更沒有誰為締造了當年韓國經濟奇跡的、而今資不抵債的超級財閥的崩潰負責。
日本病的病癥之三是政府隱含擔保和企業預算軟約束。所謂隱含擔保(Implicit Governmental Guarantee)是指政府對金融機構的放貸損失提供不言自明的擔保,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得益于金融機構大量的資金扶持,至今一些日本的金融元老,不僅沒有考慮政府指定銀行向某些產業優先貸款的作法本身,使得銀行業幾乎淪為“第二財政”,并導致銀行貸款質量的持續惡化。反而認為,低利率有助于銀行緩解其支付存款利息的壓力;甚或認為如果日本政府當年如果能拿出10萬億日元來借助銀行,就不會象今天這樣需要至少支付30萬億日元來實施"金融大爆炸法案"(The Big Bang)了。所謂預算軟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按照短缺經濟學之父科爾奈的總結,大體含有兩個特點,一是事后政企間可就財務狀況重新協商,就是企業賠了掙了都可以和政府再商量;二是政企之間有密切的行政聯系,就是企業領導階層兼有行政領導色彩。既然大藏省的官員退休后到企業人職被稱為“神仙下凡”,既然部分企業可以源源不斷地得到主銀行的融資,既然銀行也在政府隱含擔保下不擔心死無葬身之地,那么非常自然地,政府、銀行和企業通過隱含擔保和預算軟約束被捆綁在一起,俱榮俱損。由是觀之,亞洲金融危機暴露的并不是金融問題,而是政府管理的問題;反觀兩年來險象環生的亞洲經濟,危機給我們的最大教訓恰恰是我們也許根本沒有從中得到教訓!
“日本病”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是政府對“看不見的手”和對個人創新的懷疑,是借用傳統文化和道德回避市場機制可能帶來的深層次微觀基礎的演化。換言之,我們希望免費享用市場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的好處,但不想付出交織的繁榮(投資加速或曰重復投資)和衰退(企業的兼并和重組)的代價。我們希望亞洲經濟可以和歐美媲美,但卻生怕淹沒在金錢的汪洋之中,這一切如日本金融學家竹內宏所聲稱的那樣:老一代精英以其勤勉、集體至上和拋棄個人私利造就了戰后的新日本,而現在的精英們卻深信新古典經濟學,毫無羞恥感,為了私利私欲而葬送了整個國家。不幸的是亞洲的竹內宏們沒有看到:純柏拉圖式的集體模仿、集體創新制在造就日本奇跡的同時也將“日本病”深植其中。最悲劇性的現象并不是新精英們的個人主義,而是沒有政府官員、銀行或企業,必須為10年之久的泡沫經濟負責,似乎也沒有亞洲各國政府官員為本國遭受的危機負責;而是裙帶風盛行、貪污腐化驚人幕布后的精神荒蕪。日本病使得我再度想起這樣一句話:如果你讓它負起各種各樣的全部責任,那么結果恰恰是完全不負責任。
在亞洲得“日本病”的并不僅僅是日本,也涵蓋了很多其它經濟體。令人不安的是,中國經濟成長所帶有的“日本病”色彩在被涂抹開來,連“創新”這樣千差萬別、箐蕪俱存、主要由私人部門進行的事情也被冠以“工程”之名。跡象之一是政府動用私人部門資源,注入效率低下的國有經濟部門的趨勢有所強化,但舊企業的虧損乃至破產和新企業的崛起和壯大正是市場機制這枚硬幣的兩面;跡象之二是化解銀行不良貸款和建立社會保障機制進程緩慢的同時,以口號帶項目,以項目耗資金、以資金出速度、以速度回避漸進改革中沉淀問題的苗頭有所抬頭;跡象之三是仍然對經濟成長速度主要取決于市場機制缺乏信任,對政府決定增長卻寄托不切合實際的厚望;跡象之四是金融信用和國企集團的信用正被隱含的國家信用所取代。在重新審視日本病時,我們更深切地感受到,對待市場經濟只可能有實事求是一種態度,而不能虛與委蛇,所有的特色是在市場沖刷后仍不改的特色,而不是事前用油氈布密密裹來生怕市場沖擊的古董。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