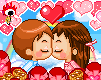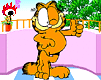| 傳染病的全球化與防治傳染病的國際合作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22日 18:16 中評網 | |||||||||
|
內容提要:從全球化的視野來看, SAR S預示著傳染病和新興傳染病的全球化。回顧人類歷史,我們會發現,傳染病對人口數量、經濟增長、技術演進、宗教、國家建設、王朝興衰甚至文明的滅絕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最近20多年來,由于全球人口流動的加劇、病毒出現了抗藥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原因,過去已經控制的疾病如霍亂、鼠疫等開始重新出現或擴大傳播范圍。一些新的傳染病如艾滋病(HIV/AIDS)、埃博拉病毒、軍團病、禽流感和SARS等紛紛出現。本文將簡要回顧最近20多年來傳染病和新興傳染病全球化的原因和影響,并
關鍵詞:傳染病 國際合作 公共產品 一、 引言 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忽然讓人們感受到疾病對健康、經濟增長甚至社會秩序的威脅。正如威廉姆.麥可尼在《瘟疫與人》中警告的那樣:“才智、知識和組織都無法改變人們在面對寄生性生物入侵時的脆弱無助,自從人類出現,傳染性疾病便隨之出現,什么時候人類還存在,傳染病就存在。傳染病過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會是影響人類歷史的一個最基礎的決定因素。”[①] SARS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較大的影響,對旅游、交通、餐飲等服務行業的沖擊尤其嚴重,2003年上半年第三產業僅增長0.8%。由于近五年中國新增就業的70%左右是通過第三產業吸納的,特別是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和社會服務業,已經成為下崗職工、農民工和隱性就業的主渠道,因此,SARS沖擊使得中國所面對的就業形勢更加嚴峻。SARS還暴露出來中國公共衛生體系存在的問題。中國曾經被稱為發展中國家公共衛生的樣板,但是近20年來,中國的公共衛生體系已經成為可持續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軟肋”:70%的人口(44%的城市人口和90%的農村人口)未參加醫療保險、過去10年醫療費用增長了大約8-10倍、政府支出中衛生所占比例低于中等國家的平均水平。SARS進一步提醒我們問題的嚴重性:由于中國缺乏應對傳染病的基層衛生組織,將放大疫情爆發之后對社會和經濟的沖擊;疾病帶來貧窮,也將加劇貧富分化。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公共衛生體制的潛在問題將帶來巨大的隱患。[②] SARS也是一次全球性的危機。在短短半年時間之內,SARS疫情已經擴散到19個國家和地區,由于發病地區是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因此更是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傳染病專家赫斯蒂芬.莫爾斯說:“SARS表明我們未來可能會遇到什么。使病原體傳染大量人口并擴散到全球各地的條件近年來不斷發展,而且還會繼續發展。”[③]從全球化的視野來看, SAR S預示著傳染病和新興傳染病的全球化,這一問題將給國家安全和國際政治帶來了新的挑戰。回顧人類歷史,我們會發現,傳染病對人口數量、經濟增長、技術演進、宗教、國家建設、王朝興衰甚至文明的滅絕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到20世紀中期,歷史上曾經是被認為是絕癥的天花、肺結核、鼠疫等已經被人類消滅或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是,最近20多年來傳染病似乎正在卷土重來。1992年美國的醫學協會(Institute of Medicine,IOM)發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響的報告《新興的傳染病:微生物對美國健康的威脅》。其中提到,由于全球人口流動的加劇、病毒出現了抗藥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原因,過去已經控制的疾病如霍亂、鼠疫、瘧疾、肺結核和白喉等開始重新出現或擴大傳播范圍。一些新的傳染病如艾滋病(HIV/AIDS)、埃博拉病毒、軍團病、禽流感和SARS等紛紛出現。[④]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在過去20多年內至少出現了30多種新的傳染病。 本文將簡要回顧最近20多年來傳染病和新興傳染病全球化的原因和影響,并對從經濟增長、人口和移民、國防以及政府效率等四個方面分析傳染病全球化對國家能力和國際關系的影響。由于傳染病已經成為一種全球問題,防治傳染病也迫切需要全球合作。本文對防治傳染病的歷史過程進行了簡短的介紹,并根據公共產品的理論框架,提出了加強全球合作的具體建議。 二、 傳染病的全球化 歷史學家們發現,在大部分有記載的歷史中都找不到人類社會持續進步、后人的生活水平會比前人更高的觀念。這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瘟疫的爆發。瘟疫使得人口數量無法持續增加,生產效率難以有效提高。大規模的瘟疫爆發甚至影響到歷史的演進,瘟疫影響到戰爭的勝負、王朝的興衰和文明的滅絕。公元542年鼠疫爆發于地中海地區,并持續了五六十年,史籍上所稱的這次“查士丁尼瘟疫”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東羅馬帝國的衰落。14-17世紀,黑死病肆虐歐洲長達300多年。1348-1349年,在短短的兩年時間之內黑死病幾乎傳遍歐洲,有1/3以上的歐洲人口死于這場猝然降臨的災難。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和鋼鐵》一書中談到,正是病菌而非槍炮幫助了歐洲人征服美洲。由于缺乏畜養家畜的經歷,美洲人從來沒有接觸過許多由動物帶給人類的病原體,對這些疾病完全沒有抵抗能力。歐洲人給美洲帶來的是一連串的瘟疫:1518-1526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發麻疹,1546年斑疹傷寒、1558-1559年流感。據估計,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帶來的疾病。如果說瘟疫毀滅了瑪雅文明,可以說一點也不過分。[⑤] 19世紀以來尤其是到二戰之后,隨著細菌學、流行病學的發展、公共健康體系逐漸完善,歷史上曾經是橫行一時、被認為是絕癥的天花、肺結核、鼠疫等已經被人類消滅或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是,一些跡象表明,21世紀傳染病可能會卷土重來。 首先,即使傳染病在發達國家已經得到了相當有效的控制,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傳染病仍然在為害人類的健康。每年全球死亡人口中大約有1/4是死于傳染病。歐洲每年死于傳染病的人口僅占總死亡人數的5%,但是在非洲,60%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于染上了傳染病。世界衛生組織把艾滋病、腹瀉、肺結核、瘧疾和呼吸道疾病(如肺炎)列為5種主要的傳染病,死于這5種疾病的人數占死于傳染病的總人數的90%以上。在發展中國家,死于這5種疾病的人口比例是發達國家的13倍。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發展中國家的傳染病將隨著商品和人員的跨國界流動傳播到發達國家。 其次,過去已經控制的疾病如霍亂、鼠疫、瘧疾、肺結核和白喉等開始重新出現。1993年世界衛生組織就曾經宣布肺結核成了全球危機,因為肺結核的發病率不斷上升,而且因為病毒對原有的藥品產生抵抗能力,導致病人死亡比例持續增加。連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無法幸免于難。1953年美國的肺結核病例為84300起,到1984年減少為22200起,但是從這以后肺結核病例開始以每年14%的速度不斷增加。原有的一些傳染病如瘧疾、登革熱傳播的范圍大大擴大。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由傳染性病毒和細菌感染的癌癥病人人數不斷增加。世界衛生組織估計15%的新增癌癥病人受到傳染病菌感染。 再次,一些“新”的傳染病粉墨登場:最著名的當屬艾滋病(HIV/AIDS)。2001年全世界共有大約3360多萬艾滋病人,每年都會有560萬人感染艾滋病,相當于每天有一萬六千多人被感染。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1/5到1/4的成年人為艾滋病人;1976年出現的埃博拉病毒不斷肆虐剛果、加蓬、烏干達等非洲國家,這種致命病毒的感染者死亡率達到50-90%。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美國影片《恐怖地帶》更是將這種可怕的怪病渲染得讓人不寒而栗;1976年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在費城一家旅館聚會,1個月之后就有221名與會代表和當地居民得了一種酷似肺炎的病,后來被稱為軍團病。致病的元兇是嗜肺軍團菌,主要寄生在中央空調的冷卻水和管道系統中,可經通風口無聲無息地入侵建筑物內的每個房間;1997年香港發現一名男童死于本來是家禽才得的禽流感。這場禽流感導致18人感染,6人死亡。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在過去20多年內至少出現了30多種新的傳染病。 美國醫學協會(IOM)提出了導致傳染病卷土重來的主要原因:[⑥](1)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傳染病也隨之周游列國。攜帶病菌的病人從一個國家到達另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時間往往比傳染病的潛伏期還要短。頻繁的人口流動使得傳統的隔離方式根本無法生效,也使得一國爆發的傳染病會迅速地傳播到其他地區;(2)我們消費越來越多的加工食品,這些食品可能來自遙遠的他鄉甚至異國。在種植、采摘、加工、包裝、運輸、儲存和銷售等各個環節如果出現污染,都可能導致傳染病傳播。瘋牛病和口蹄疫是非常著名的例子。而在美國,近年來接連發生通過食品傳播的傳染病。污染源包括快餐店的漢堡包、學生餐中的草莓、牛肉肉餡、冷凍的肉塊、早餐麥片等等;(3)人口結構的變化和城市化。發達國家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老年人對疾病的免疫能力下降,更容易被病毒擊潰。城市化導致人口居住過度集中,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現的貧民窟,衛生條件極端糟糕,成為城市中被遺忘的角落,但是也是病菌最容易藏身的地方;(4)戰爭和自然災害是瘟疫的催化劑。戰爭過后瘟神接踵而至,大災過后必有疫情。在戰爭和自然災害中流離失所的難民會進入城市或逃往其他國家,加速了傳染病的傳播;(5)農業灌溉、砍伐森林、砍伐完森林重新植樹造林、都改變了攜帶病菌的昆蟲和動物的生活習性。很多傳染病的爆發都是因為生物習性的改變,比如瘧疾的傳播范圍超越了熱帶地區就是因為帶菌的蚊子活動范圍擴大了;(6)靜脈注射和不安全的性生活;(7)微生物本身也有進化過程,進化機制使得它們能夠適應新的寄主細胞或找到新的物種作為寄主,它們會生產毒素,它們會破壞人們的免疫系統,它們會對藥物和抗生素產生抵抗能力,而人們大量使用殺蟲劑、抗生素,加速了病毒抵抗能力的發展;(7)永遠都有冒險精神的人們進入熱帶雨林和其他人跡罕至的地方,并帶回了很多人類原本未曾接觸過的病菌;(8)20世紀中期人類對抗傳染病取得的勝利使得大家變得麻痹大意,原有的防治傳染病的系統逐漸衰落,公共健康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心血管病和癌癥等“現代病”,疫苗的提供沒有跟上,財政支持不夠,人員培訓和公眾教育都落伍了。 從這些原因可以看出,傳染病正在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全球問題。正如美國醫學協會(IOM)在1997年的一份報告所指出的,“區分國內健康問題和國際健康問題正在失去其意義,并且常常會產生誤導”。[⑦]傳染病的全球化,使得其對國家安全和國際關系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防治傳染病全球化,依賴于各國之間深入和有效的合作。SARS的突然爆發,更加提醒國際社會要加強公共衛生領域的國際合作。從防治SARS的過程可以看出,政府之間及時通報疫情、協調進行防疫管理,全球的科學院進行有效的合作研究,及時通報研究進展等,都對有效防治SARS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三、 傳染病全球化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談到,國家的核心職能是為了防止其公民受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劫掠,獲得安全感。從國際政治理論的傳統來看,現實主義的國家安全觀主要強調國家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基本上忽視了傳染病對人類安全的巨大影響。事實上,每年死于傳染病的人數遠遠超過死于戰爭的人數。傳染病將通過影響經濟增長、人口流動、國防和政府治理等四個方面影響到國家能力。 從歷史上來看,傳染病對國家安全和國際政治的影響不容忽視。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就曾經談到,公元前430年至427年在雅典發生的瘟疫徹底改變了希臘政治的格局。這次重大傳染病造成的后果非常慘重,它使得雅典軍隊的生力軍1/4死亡,瘟疫繼續在南部希臘肆虐,導致了城邦人口的1/4死亡。雅典本來是和斯巴達同時稱雄的那個古希臘城邦國,素有稱霸整個希臘半島的雄心,但是受到瘟疫影響,從此衰落下去。西歐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新興民族國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和黑死病有關。從中國歷史也能看得出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比如中國歷史上瘟疫集中爆發的兩個時期,即東漢末年和明末清初,均為戰亂和社會動蕩的時期。據估計,明代萬歷和崇禎二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三省人口死亡總數至少達到了l000萬人以上。在遭受鼠疫侵襲之后,北京城墻上,平均每三個垛口才有一個羸弱的士兵守衛。事實上,李自成進入北京城乃是不攻而克的。后來,清兵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乘虛而入。 遺憾的是,傳統的現實主義國家安全觀基本上忽視了傳染病對國家安全的深刻影響,而是片面地關注國家間的戰爭、各國軍事力量對比等等。正如Richard Ullman指出的,“片面地從軍事方面定義國家安全帶來了對現實的深刻誤解。這種誤解使得國家僅僅考慮軍事威脅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或許更為致命的威脅”。[⑧]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為健康投資》提供的資料,1990年死于傳染病的全球死亡人數達1669萬,占總體死亡人數的34.4%,而死于戰爭的人數僅為32萬,占0.64%。死于傳染病的人數是死于戰爭人數的50多倍。[⑨]傳染病、全球環境惡化、國際移民等隨著全球化出現的新問題都對國家安全和國際政治提出了新的挑戰,并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國家安全概念。 一國的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取決于能否實現如下幾項基本使命:(1)維護國家的基本存在,即最起碼地要保有可有效運轉的政府、司法、軍隊等,以及維護領土完整等;(2)保護公民免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對人身安全的侵害,這其中也包括保護公民免受傳染病對生命健康的侵害;(3)維護經濟繁榮和穩定;(4)有效的政府治理。傳染病將通過影響經濟增長、人口流動、國防和政府治理等四個方面影響到國家能力。[⑩] 經濟增長:傳染病帶來人口死亡和健康狀況惡化,這直接減少了勞動力的有效供給;傳染病也使得患病的勞動力生產效率下降;受到疾病影響,人均收入減少,中低層家庭的收入減少尤為嚴重,這導致居民戶尤其是貧困家庭減少儲蓄、減少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比如兒童被迫輟學);傳染病的另一個結果是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經驗研究表明,淪為貧困的人口大多是因為疾病原因,傳染病的爆發將擴大貧困人口的數量,增加一國反貧困的難度;傳染病對各個經濟行業的影響是不均勻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旅游、餐飲、交通等服務業受到的打擊最為嚴重。由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旅游、餐飲、交通等服務業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所以當這些行業受到打擊之后,又導致一國失業狀況惡化。由于以上幾方面的原因,傳染病可能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根據Cuddington的一項研究,僅僅艾滋病就可能使得坦桑尼亞的GDP減少15-25%。[11]在無法有效控制的情況下,傳染病所影響到的并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而可能是某個區域內所有鄰近的國家,這將對全球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帶來更為負面的影響。 人口數量和人口流動:在人類還沒有擺脫馬爾薩斯陷阱之前,傳染病幾乎是控制人口數量增長、保持人口與資源平衡關系的工具。大規模的傳染病過后,人口將大量死亡,對國家的實力甚至社會秩序均帶來巨大沖擊。目前,傳染病和人口數量的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為了彌補傳染病流行期間家庭成員死亡帶來的損失,發展中國家的家庭可能會增加生育量以減少風險,結果是傳染病之后人口數量反而會增加,而這又進一步導致了世界環境的惡化、世界人口的貧困化。傳染病會帶來人口在國內和國際間的流動,并對區域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關系帶來直接的影響:首先,由于某些地區受到傳染病的嚴重打擊,當地人口銳減,而外來人口又不愿意遷入,會造成當地經濟的凋敝,比如巴西和哥倫比亞的某些農村地區、泰國和緬甸交界的地區,都由于瘧疾流行而無法開發。受到傳染病襲擊的地區會發生人口外流,有時候這種人口流動的范圍是在一國國境之內,但是跨國界的人口外流也越來越多。比如印度1994年爆發瘟疫,以及1995年扎伊爾爆發埃博拉病毒的時候,均發生了大規模移民現象。外流的人口可能攜帶著病菌并導致傳染病流行范圍的擴大,由于人口外流的方向往往是由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由窮國流向富國,也會對流入地區和流入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影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發達國家已經無法在傳染病的海洋中成為幸存的安全島。 國防:戰爭總是和傳染病相聯系。戰爭能夠幫助傳播疾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軍隊的行程,流感隨之在全球范圍內爆發并導致大約4000萬人口死亡。直到20世紀,在歷次戰爭中死于瘟疫的士兵幾乎都比死于敵手的士兵更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作戰的效率和士氣。在很多時候,軍隊是被病菌而非敵人打敗的。在歷史上這樣的事件包括我們曾經談到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李自成進入北京等等。疾病甚至能打破像拿破侖這樣的軍事奇才。當時受法國控制的海地爆發黑奴起義。拿破侖派兵前往鎮壓。在法軍到達多米尼加數日后,黃熱病流行摧毀了這支精銳部隊,2.7萬人喪生,甚至包括法軍的統帥。拿破侖對此束手無策,不得不將當時法國占領的路易斯安那拱手賣給美國。和傳染病全球化緊密相連的新問題是,最近出現了生物恐怖主義。和常規武器、核武器、化學武器等相比,細菌武器的成本最低。美國疾病防治中心已經確定了十余種可能被恐怖份子利用的病菌,這些病菌攜帶方便,可引發包括天花、炭疽熱等多種傳染病,能夠導致大規模人口死亡,且防治甚為困難。 政府治理:傳染病帶來的人口死亡、疾病和社會恐慌給政府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傳染病過后留下的貧窮、貧富分化、大規模人口流動等也增加了政府的負擔。傳染病做為突發的危機事件,將對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提出挑戰:(1)危機是復雜系統的突變,而不是一系列事件按照線性的時間順序先后發生。極端地講,危機在事前幾乎是無法預測和預防的,在現實中,決策者從來不會看到明確的事前警告:有關危機的信息可能早已經淹沒在其他無數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到萬不得已,下級部門也不會故意危言聳聽。此外,危機在發生的過程中也幾乎是無法控制的。危機的進展充滿了不確定性,而這些不確定性是和危機的背景,即爆發危機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有關的。(2)在現代社會中,決策日益多元化、媒體和公共輿論介入政治決策、越來越多的危機成為全球性問題,危機的爆發影響到公眾對政府的信心,危機的處理涉及到資源的重新分配,這些都使得危機變得更加政治化。比如SARS期間WHO和國外媒體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中國政府采取的措施。總之,成功處理危機的關鍵在于建立政府的公信力。增加政府公信力的做法包括:信息透明化、決策公開化、增加政府之外利益相關者的參與,等等。如果政府無法成功地應對傳染病的挑戰,就可能會導致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損害,在極端的情況下可能會成為“失敗國家”。失敗國家的出現將對國際關系產生新的挑戰,因為傳統上國際關系的發展都是通過各國政府之間的交往實現的,如果有的國家連政府都不復存在,國際關系的腳手架將如何搭建? 四、 防治傳染病的國際合作:一個簡短的歷史 《舊約.利未記》中就已經有了關于傳染性皮膚病、麻風病的診斷和處理、如何隔離和清潔病人、禁止吃血、禁止吃野地的死物、保持個人清潔等戒律的記載。《詩經.小雅.節南山》中說“天方薦疾,喪亂弘多”,《呂氏春秋》中說“癘疾,氣不和之疾”,均談到物候反常、寒暑錯位,易于導致瘟疫。但是,這些早期的記載只是人們在對瘟疫的病因、傳染渠道和治療方法根本不知情的時候朦朦朧朧地感受到的一些經驗。明末清初,“天作瘟疫、朝發夕死”。當時的一位名醫吳有性在《瘟疫論》中仰天長嘆:“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 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人們在驚恐之余幾乎嘗試了各種能夠想到的古怪乃至殘忍的治療方法。當“黑死病”在歐洲各地蔓延時,人們使用通便劑、放血療法、燒灼淋巴腫塊、甚至用尿洗澡等辦法試圖阻止疫情的蔓延。由于有效防止傳染病的醫藥和治療技術還沒有被發現,從中世紀直到19世紀中期和20世紀初,惟一有效的治療傳染病的方法可能要屬隔離。1377年意大利的拉古薩港規定來自鼠疫區的人必須在港外指定地點停留40天,如果沒有發病才準許入港。在隨后的幾百年中,地中海沿岸隔離傳染病人已經成為人們司空見慣的事情。隔離政策影響了國家之間的貨物和人員的正常流動,可能會引發國家之間的矛盾,因此,有效的隔離政策依賴于國家間的合作。各國均認識到,國際間的合作對于防止傳染病很關鍵:各國所實行的限制性的隔離政策必須統一,這樣才能防止不公平的貿易限制;各國之間要互通信息,報告疫情,共同建立防范傳染病的早期預警體系。 到了19世紀后期,各國之間關于防治傳染病的合作進一步加深。1851年,由于霍亂在歐洲多次爆發,引起各國的恐慌,因此在法國巴黎召開了首屆國際衛生大會。這次會議統一規定了對到達歐洲港口的船只進行檢查和隔離的措施。此后,國際衛生大會多次在歐洲和美國召開。在此期間,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公共衛生政策的勃興,人類在和瘟神抗爭的過程中才算看到了隧道盡頭的一線光芒。19世紀防治傳染病的幾個里程碑式的事件包括:公共衛生運動的興起、流行病學的成型和細菌學的出現。 中世紀歐洲的衛生條件是如今的人們難以想像的。城市里面堆積著垃圾和糞便,尤其是在貧民窟中,人口擁擠而居住條件惡劣。這使得瘟疫很容易泛濫成災。城市里面各個階級比鄰而居,當瘟疫襲來的時候,富人也無法逃之夭夭。在Edwin Chadwick的推動下,英國在1848年制度了《公共衛生法案》,設立國家衛生委員會,重視都市的排水系統,修建了許多下水道,并開始定期收取垃圾。改善公共衛生條件的很多做法,如改善飲用水的衛生條件,在城市規劃中減少人口居住過度集中、防止居所過于潮濕或通風不好,加強對食品安全的管理,消滅蚊子等,對防治傳染病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以至于研究人口歷史的一位權威Thomas McKeown認為,營養和衛生條件的改善對現代人口增長的貢獻遠遠大于臨床醫學。 傳染病存在一定的潛伏期,一般在1-14天,但是在這種現象被人們認識到之前,人們很難找到疾病的真正起因和兩周之后的爆發之間的聯系。如果沒有掌握大量的數據并做比較分析,人們也很難找到疾病的傳染渠道。只有當統計學方法進步之后,人們才有可能對流行病進行科學的研究。被譽為“流行病學之父”的Pierre Charles Alexandre Louis便是一位法國統計學家。他用統計方法證明放血不是有效的治療方法,并研究過肺結核和傷寒。他的大批學生如William Farr,William Guy,William Budd,Oliver Wendell Holmes, George Shattuck,Jr.等進一步發展了他的研究方法,并組織了倫敦統計學會和美國統計學會。 細菌學和抗生素的出現更為人們所熟知。1865年法國微生物學家路易斯-巴斯德發現,他稱之為“病毒”的微生物是傳染病的病因。1876年Robert Koch區分了不同的微生物以及它們所導致的疾病,開創了疾病的細菌理論。1928年亞歷山大-弗萊明發明了青霉素,1940年青霉素被生產出來并開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廣泛使用。青霉素的問世使得肺炎、淋病等很多傳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治愈。二戰之后,人們在和傳染病的斗爭中取得了轉折性的勝利。過去的一些致命的疾病如肺結核和傷寒熱可以使用抗生素治療,而曾經奪去無數兒童生命的小兒麻痹癥、百日咳、白喉等可以通過注射疫苗的方式預防。人們的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兒童死亡率急劇下降。 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從20世紀初期開始,國際間關于傳染病防治的合作由單純的隔離政策轉變為加強公共健康政策的合作。在20世紀初期出現了幾個國際衛生組織,如1907年12個歐洲國家在羅馬建立的國際公共衛生辦公室(OIHP)。世界衛生組織(WHO)也是在這一時期成立的。世界衛生組織的起源始自一戰之后建立的國際聯盟。在國際聯盟的憲章中,第23條規定國際聯盟的成員國“將努力采取措施,加強對疾病防治和控制的合作”。隨后,國際聯盟成立了健康委員會,健康委員會進行了許多開拓性的公共衛生政策合作,比如定期發布關于傳染病病情的報告,在成員國之間定期通過電報交流信息,改善有關傳染病的統計方法和數據搜集,在各國開展對多種傳染病的田野調查和人口統計等。 隨著國際聯盟的解體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國際間關于傳染病防治的合作被迫中斷。二戰之后,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衛生組織的呼聲很高,1945年4月在聯合國的會議上,盡管美國和英國的代表不同意將衛生健康方面的問題列入議題,但是中國和巴西的代表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國際衛生組織并得到了大多數成員國的贊成。1948年4月,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成立。隨后,之前的一些專門性或地方性的國際衛生組織陸續被納入世界衛生組織的體系之內,比如早在1902年就成立的泛美衛生局(PASB)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美洲分部,反結核病聯盟、反性病聯盟等非政府組織也和世界衛生組織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 從世界衛生組織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是國際間關于傳染病防治進行合作的黃金時期。世界衛生組織成功地完成了消滅天花、小兒麻痹等項目,極大地鼓舞了人類戰勝傳染病的信心。天花在歷史上是最令人生畏的傳染病之一。在20世紀初期可以說每一個國家都經受過天花的肆虐。直到1967年,仍然有大約1000-1500萬人口患天花,其中大約有200萬天花病人不治身亡,另有數百萬病人因天花而殘廢。1967年1月1日,世界衛生組織發動了消除天花計劃。最開始的計劃是通過對各國的全體國民進行免疫,后來發現目標過于宏大,而且在有的地方因宗教信仰等原因而受到因抵觸。后來,世界衛生組織改進了做法,改為對發生疫情的地區迅速隔離并進行免疫。世界衛生組織在消滅天花項目中較好地實現了統一領導和項目靈活性相結合,整個項目有統一的標準、由國際醫療隊進行獨立的評審和鑒定,但是具體負責執行項目的行政管理體系則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到1977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天花已經被消滅。受此鼓舞,世界衛生組織先后又開展了消滅小兒麻痹癥、瘧疾等疾病的計劃。[12] 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世界衛生組織意識到消滅單獨一種傳染病的局限性,逐漸將工作的重點放在全面促進全球公共健康的合作方面。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對于健康的重要性有了認識,形成了一個多層次的全球公共健康合作框架。 1980年之后,世界銀行也開始關注公共健康。1993年, 世界銀行發表了《世界發展報告:為健康投資》,之后世界銀行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成為公共健康的最大資金提供者。世界銀行在報告中強調,單純依靠市場經濟無法提供公共健康的最佳水平,根據經驗觀察,只有10%的資金被用于控制和治療占全球疾病負擔90%以上的疾病。世界銀行認為,為了更有效地提供適宜的公共健康服務,必須發揮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積極性,并根據不同的項目選擇合適的融資方式。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世界銀行在提供向發展中國家的貸款的時候可以提出貸款條件,這樣便能夠引導各國政府重視公共衛生問題,制定更有效的健康、營養和人口政策。 由于貿易和傳染病傳播之間的密切關系,WTO也越來越多地成為公共衛生全球合作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在GATT中就已經規定,締約方可以采取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以保護國民生命和健康,前提是這些措施不得對其他成員構成貿易歧視或貿易限制。在烏拉圭回合中,各締約方達成了《實施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協議》,規定成員方為了保護人類、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可以采取相關的措施,比如所有的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和程序,特別是最終產品標準;工序和生產方法;檢測、檢驗、出證和審批程序;各種檢疫處理;有關統計方法、抽樣程序和風險評估方法的規定;與食品安全直接有關的包裝和標簽要求等。《實施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協議》規定各締約方必須以科學為依據實施有關動植物衛生的措施,并應該以相應的國際標準為依據。比如食品法典委員會對食物添加劑、殺蟲劑殘余、食物標簽要求、產品成分、對食物加工技術的建議、對食物生產的檢驗技術的建議等提出了一系列詳細的規定。世界衛生組織的其他內容,比如TRIPs,貿易和環境等都可能對公共衛生帶來深刻影響。圍繞TRIPs和藥品的爭議是本輪多哈回合的焦點議題之一。發展中國家提出,由于發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制藥企業的利益,對藥品的專利保護過于苛刻,妨礙了發展中國家得到可以支付得起的藥品,而這些藥品本來可以拯救上千萬人口的生命和健康。[13]由于世界貿易組織所包括的內容日益廣泛,而且自1995年以來建立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更是強化了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成員方的約束力,所以世界貿易組織將在全球公共衛生合作中地位更加突出。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和世界衛生組織有很長的合作歷史。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這兩個國際組織就可以共同制定相關的措施。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制定的國際民用航空協定規定,各成員方“同意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霍亂、流行性斑疹傷寒、天花、黃熱病、瘟疫和其他成員方認可的傳染性疾病通過航空途徑的傳播”。協定規定了必須要遵守的標準,其附件9規定了“推薦的做法”。ICAO的很多規定參照了WHO的標準,比如航空器上的除蟲、在機場和在飛機上提供安全的食物和水、對垃圾、廢水和其他危險物品的處置、對黃熱病的鑒定等。 除了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之外,非政府組織的積極介入也是推動全球公共衛生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力量。這些非政府組織沒有政治約束,具有更多的靈活性,資金來源獨立,因此能夠彌補公共衛生中的一些被長期忽視的領域。比較著名的基金會包括Wellcome Trust,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 開放社會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等等。英國的Wellcome Trust是全球最大的醫藥慈善機構,其最主要的項目是人類基因組的研究,他們也長期關注發展中國家的麻疹和糖尿病等疾病。[14]蓋茨基金會資產達218億美元,主要致力于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疾病防治。比如其發動的兒童免疫計劃,主要幫助消滅兒童時期經常易患的疾病如呼吸道疾病、腹瀉等。這一計劃在發展中國家非常急需,但是發達國家很難意識到其重要性,因為在發達國家兒童免疫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開放社會研究所是著名的金融家索羅斯設立的一家基金會,他們和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哈佛大學醫學院共同開展關于已經具有抗藥性的肺結核的治療方法的研究項目。另外還有一些非政府組織,如最早由法國醫生成立的“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s,簡稱MSF)專門為遭受戰亂、流行病和自然災害的人們提供醫療援助。1999年MSF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美國普世救濟合作社(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lief Everywhere,簡稱CARE)不僅為遭受災害的人群提供醫療幫助,而且參與了關于公共衛生的基礎設施如水井、兒童免疫等項目。 五、 全球公共衛生的合作:一個初步的分析框架 傳染病的全球化需要各國政府做出迅速和有效的反應。應對傳染病全球化的政策包括三個方面:首先,在國家層面上,各國政府需要改善其公共衛生體系,建立危機預警和應對機制;其次,在國際層面上,各國之間需要加強政策協調、確立相應的組織機構、規則和慣例促進國際間的合作;最后,在全球的層面上,除了各國政府的努力之外,必須調動所有相關的資源和力量,尤其是包括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共同防范傳染病的全球化。 本節試圖從公共產品概念出發,提供一個關于全球公共衛生提供的分析框架。[15]盡管公共衛生在國內政策層面上也涉及公共產品概念,因為單獨依靠市場力量和私人提供無法實現公共衛生服務的最佳提供水平,不過我們將更加側重公共衛生的國際合作。 公共產品的嚴格定義是薩繆爾森1954年提出來的。按照他的定義,純粹的公共產品是指這樣的物品,即每個個人消費這種物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物品的消費減少。經濟學家一般認為,私人產品的提供應該通過市場上的供求機制,但是公共產品的提供常常需要政府介入。因此,辨別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性質對于政府決策來說非常重要。簡單地說,公共產品需要具備消費上的非競爭性(nonrivalry)和供給上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消費上的非競爭性是指當一種商品或服務在增加一個消費者時,其邊際成本為零,即一個消費者對此商品或服務的消費不會對其他消費者帶來任何影響。比如,一位觀眾在家中收看《新聞聯播》不會影響到任何一位其他觀眾收看同樣的節目。供給上的非競爭性是指公共產品的提供者無法或很難排除不付費的消費者。比如公民納稅的目的之一是建立國防力量保護自己的安全,但是當軍隊在戰爭時期行使保衛國家的職責時,很難區分他們所保護的公民是否已經依法納稅。 根據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和供給上的非排他性這兩個標準,我們可以將涉及公共衛生的各種服務劃分為如下幾種類型: 純粹的公共產品:純粹的公共產品同時滿足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和供給上的非排他性這兩個標準。發現并傳播一種新興傳染病的治療方法屬于純粹的公共產品,因為一國采用這種治療方法不會妨礙其他國家采用同樣治療方法的療效,同時,在一個信息化時代,將有關的信息通過比如互聯網途徑傳播到其他國家幾乎不費任何成本,所以當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被發現之后,只有其基本的原理被公布于眾,其在國際范圍內的傳播通常是無法排他的。純粹公共產品的提供會遇到所謂的“搭便車”問題,即每個國家都只愿意做公共產品的消費者,而不愿意做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解決“搭便車”問題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可能獲得最大收益的國家,或是最有經濟實力的國家預期其他國家一定會觀望,所以只能主動地承擔“領導者”的角色,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并無奈地容許其他國家“搭便車”;另一種辦法是在國際組織的協調下,由各國達成集體行動,一起承擔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不過,如果協調成本和監督成本高昂,或缺乏懲罰違約者的有效機制,這種集體行動是難以維持的。 準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是指那些可能只滿足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和供給上的非排他性這兩個標準之一,或是只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和供給上的非排他性的產品或服務。比如,對邊防線和出入境的檢查就只具有部分的非競爭性,因為在給定資源條件下,隨著邊防線的長度增加或是出入境檢查點的增加,增加檢查的邊際成本為正。在公布治療技術的時候也可能會有部分的排他性,比如治療技術的擁有者可以提供收費的方式將不交費者排除在外,但是仍然不能排除通過交費獲得治療技術的消費者隨之將此技術傳播給未交費的其他消費者。對于具有部分競爭性的公共產品,更容易通過國際稅收的方式,將有限的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最優配置。對于具有部分排他性的產品,更容易激發私人提供的積極性。 俱樂部產品:俱樂部產品的特征是具有部分的競爭性,即在非擁擠的情況下對該產品或服務的消費是非競爭的,但是當消費者過于擁擠之后便出現了競爭性,同時,可以較為方便地將非付費者排除在外。對于俱樂部產品來說,可以通過征收相應的“會員費”,補償由于擁擠出現的成本。在公共衛生的國際合作中,諸如一些先進的醫院和診所會接納來自外國的病人、當通過互聯網咨詢有關技術的人數過多時每個咨詢者能夠獲得的時間就會減少等等,均反映出俱樂部產品的特性。對于俱樂部產品來說,征收“會員費”可以很方便地將外部性內部化,所以效率問題并不是主要的考慮。俱樂部產品引起的關注主要是公平問題,因為如果有的國家因為付不起“會員費”而被遺棄在俱樂部的門外,對于全球公共衛生可能會帶來挑戰。但是這可以通過某種轉移支付的方式加以解決,比如富國增加對窮國的援助,以支持窮國在付費之后加入俱樂部。總之,為了效率,付費是必須的,為了公平,轉移支付也是必須的,這兩個問題需要通過不同的方式分別加以解決。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俱樂部產品由于其特性,并不適合所有的國家都參與,因此在很多情況下,需要在某個地區之內加強各國間的合作,成立規模適當的“俱樂部”。 聯合產品:聯合產品是指一種活動的結果是產生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產品或服務,這些產品或服務具有部分的公共產品特性。公共衛生中的很多服務可以歸為此類。比如,當一國發布關于傳染病的預警和疫情信息時,對于該國來說,能夠使得其更為迅速準確地了解疫情并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但是,疫情的公布也使得其他國家能夠有所準備,所以對于其他國家而言,這種疫情的公布有具有部分公共產品特征。又比如,一國的醫院加強對科研的投入,能夠提供本國的醫療水平,但是由此帶來的醫療技術中的創新和進步又便利了其他國家,使得他們能夠更快地學習到最為先進的醫療技術。聯合產品一方面給提供該產品的國家帶來了具體的私人產品的利益,另一方面有給其他國家帶來了部分的公共產品的利益。因此在鼓勵此類產品的提供時,關鍵一點在于能否強化此類產品的私人產品特性,這樣才能夠增加一國主動提供此類產品的積極性。換言之,應該盡量使得此類產品中的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成為互補,這樣才能在提高一國國家福利的同時又能夠讓更多的國家雨露均沾。 私人產品:私人產品具有完全的競爭性和排他性。比如絕大多數的藥品和疫苗屬于此類產品,診斷檢查也基本上屬于此類范疇,有些公共衛生服務比如消滅攜帶病菌的蚊子,盡管在一國之內屬于公共產品,但在國家之間屬于私人產品,因為這對其他國家幾乎不會帶來什么影響。私人產品應該由市場機制來提供,但是條件是市場機制必須是充分競爭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國家的過度干預實際上破壞了醫療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市場競爭,導致市場失效,而這種失效有可能進一步成為政府干預的理由。此外,發達國家制藥公司要求的過度的專利權保護也損害了市場上的充分競爭。 根據我們對公共衛生中的國際合作的分析,主要的啟示是:(1)必須根據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公共衛生服務,制定適宜的政策,政策的靈活性往往是成功的關鍵;(2)效率問題和公平問題都很重要,但是需要通過不同的機制解決。 六、 進一步的建議 中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往往注重在傳統的安全領域開展合作,相對忽視了非傳統的國家安全問題。因此,在SARS爆發之初,中國對國際合作的態度是消極和被動的,并沒有及時與有關的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溝通信息、開展合作。由于疫情的發展,以及中國政府在危機初期應對措施的失誤(如對疫情的隱瞞),引起了國際輿論和周邊國家的不滿,這種外在的壓力使得中國政府不得不迅速調整戰略,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一方面,中國政府積極配合世界衛生組織,安排有關的專家組到廣東、北京等地考察,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加強了和周邊國家的溝通和合作。2003年4月溫家寶總理出席在泰國召開的東盟與中國首腦SARS特別峰會。這次峰會達成了《中國與東盟領導人特別會議聯合聲明》,此后東亞地區開始統一規劃、協調政策,共同抵抗SARS。中國副總理吳儀在世界衛生組織第56屆年會上坦誠地承認中國在SARS危機初期存在政策失誤并強調中國愿意程度在預防突發性疾病方面的責任。這些努力得到了國際上的理解和贊賞。 展望未來,SARS危機提醒我們,必須重視在非傳統國家安全,包括傳染病防治方面的國際合作。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在加強傳染病防治的國際合作方面必須要注意以下幾方面問題: 這次SARS危機使得世界衛生組織認識到自身工作的被動性,也為其職權的擴張創造了條件。在隨后的第56屆世界衛生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授權決議,今后世界衛生組織無需得到其成員國提交的健康威脅報告就可以在其認為必要的時候對這一國家進行干預,同時決議還規定即使未經成員國邀請,世界衛生組織也可以派員展開實地調查。[16]世界衛生組織職能的擴張對于進一步加強公共衛生的國際合作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與此同時,應對意識到,一個以世界衛生組織為中心的全球公共衛生合作框架也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從世界衛生組織消除天花、小兒麻痹癥等成功經驗可以看出,公共衛生的國際合作既需要統一的領導,又需要靈活性。如果世界衛生組織蛻變為龐大的官僚機構,對于促進公共衛生的全球合作反而會帶來負面的影響;[17]其次,世界衛生組織做為一個專門的國際組織,在解決公共衛生這樣一個綜合性問題的時候,會遇到很多捉襟見肘的困難。導致公共衛生危機的原因,以及傳染病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其中涉及進出口、城市規劃、人口流動、產業政策、科研體系、知識產權保護、社區建設等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原因,而當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政府合作的時候,對口的單位往往只是衛生部,而和比如國內的貿易、產業和計劃部門很少溝通。再次,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國際機構對于公共安全的規定有時候是互相沖突的。比如1991年秘魯爆發霍亂,其貿易伙伴國限制從秘魯進口的食品甚至一般商品,導致秘魯損失7.7億美元。秘魯因此向GATT起訴,要求GATT保護其出口,而對其出口的限制正是和世界衛生組織聯系密切的泛美健康辦公室(PAHO)規定的。 地區性的公共衛生合作應該和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合作并駕齊驅。世界衛生組織關注的是全球范圍內的公共健康,對于地區性的傳染病或是公共衛生隱患常常缺乏專門的知識和人才。由于相鄰的國家和地區之間人口和商品流通最為頻繁密集,區域內的各國在體制、傳統和文化方面均具有相似性,鄰國之間的同伴壓力(peer pressure)更有助于提高本地區各國加強公共衛生建設的積極性,地區之間存在著安全、經濟、文化交流等全方位的合作,公共衛生的合作能夠通過“議題關聯”推動各國在其他領域的合作,因此地區性的公共衛生合作顯得越來越重要。在東亞地區,中國日益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穩定器,地區間的各種議題的合作均離不開中國的積極參與,加強和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公共衛生合作,在各個方面均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對于防治傳染病以及應對各種危機事件都是極其重要的。從國外的經驗看,活躍的民間組織往往是政府在遇到緊急問題時的堅強后盾和最及時的幫手。日本阪神大地震,最先趕到現場并發揮作用的就是民間組織。東亞金融危機之后,在民間組織的動員之下,韓國人紛紛捐出自己的首飾和戒指。在美國,民間組織不僅組織消除了肆虐美國的黃熱病,而且研究出了小兒麻痹癥疫苗。在SARS期間,政府幾乎完全承受了抵抗SARS的壓力,國內的民間組織沒有發育,無法發揮作用;由于缺乏散財以濟天下的傳統和機制,富人和企業在SARS危機中表現得格外安靜,國內非政府組織的缺位使得中國政府難以充分發揮國際上的各種非政府組織的援助力量。SARS危機給我們的警示是:政府在應對風險的時候,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在政府的能力難以達到的領域,需要社會各種民間力量的支持。在一個風險層出不窮的現代社會,永遠不要試圖讓政治高于災害和風險。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何帆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