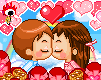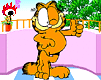| 饑餓 不平等與社會福利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22日 17:50 中評網 | |||||||||
|
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一位來自發展中世界的經濟學家。他就是現正執教于英國劍橋大學的印度教授阿麻泰.K.森(Amartya K. Sen)。這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自設立以來,第一次授予一位亞洲人。 森教授1933年出生于原屬印度的孟加拉。他至今仍是一位印度公民。1953年他畢業于加爾各答的總統學院,1959年獲得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后,他在印度、英國和美國的
森曾任國際經濟學會、印度經濟學會、美國經濟學會的主席。他是英國科學院、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和美國哲學學會的成員。森編著了20多本書,并發表了200多篇論文。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1970)、《論經濟不平等》(1973)、《貧窮與饑荒》(1981)、《選擇、福利及測量》(1982)、《資源、價值與發展》(1984)、《論倫理學與經濟學》(1987)等。 饑餓、不平等、社會福利,這就是一位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講述的故事。 免于饑餓的權利 在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期內,人生都是短促而艱難的。就在一、二百年前,地球上的絕大多數人口仍生存在饑餓狀態,而在中國,許多30歲以上的人都留有鮮明的對饑餓的記憶。誠然,在一段相當短的時間內,世界農業生產和糧食供給量都有了突飛猛進的提高,但營養不良、饑餓乃至大規模的饑荒在這個世界上卻仍未絕跡。 目睹上百萬的人口死于猝然降臨的饑荒,人們不禁會問,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觸目驚心的悲劇發生?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之所以會有饑荒和饑餓,自然是由于食物匱乏。事實上,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開始,經濟學家們主要關心的也是世界人口數量與糧食供應量的平衡。 森提出的問題是:饑荒真的是源于糧食供應量不足嗎?或者,如果我們提高糧食產量,就能從此消弭饑餓現象嗎?盡管有許多饑荒確實發生于糧食產量下降之后,但有些饑荒卻是發生在糧食產量的高峰時期,比如1974年的孟加拉饑荒就是一例。 看來,真正的問題并非糧食的總供給量是否充足,而在于個人和家庭能否及時地獲得食物。當個人免于饑餓的權利被剝奪之后,即使糧食豐收,對他仍是無濟于事。因此,森提出,為了理解饑餓,我們必須首先理解人們的權利(entitlement)。所謂權利,指的是一個人通過其所能夠享有的合法渠道獲得的商品束(commodity bundle)的集合。權利又可分為“稟賦權利”(endowment)和“交換權利”(exchange entitlement mapping)。前者是指一個人的初始所有權,比如,他所擁有的土地、自身的勞動力等。后者是指一個人利用自己的稟賦從事生產并與他人交換所能獲得的商品束。當一個人的權利集合中缺乏足夠數量的食物時,他就不免會有饑餓之虞。這既可能是由于他的稟賦權利發生了變化(比如失去了土地或由于疾病失去了勞動能力),也可能是由于他的交換權利發生了變化(比如由于勞動工資下降、食物價格上升、失業或其所生產的產品價格下降,導致他無法通過交換獲得包括足夠數量食品的商品束)。 一個人免于饑餓的權利來源于:(1)政治體系。這要看政府能否提供明確的產權保護。(2)經濟體系。這取決于微觀上有充分競爭的市場秩序,宏觀上能維持穩定的經濟環境。(3)社會體系。比如家庭內部的分工、傳統觀念中對交換權利和互惠權利的規定,都會影響到權利的分配,并決定著不同的群體在面對饑餓和饑荒時的不同命運(比如婦女的社會地位往往決定了她們在饑荒中處境猶為悲慘)。 1943年約有300萬人死于孟加拉饑荒。當時年僅9歲的森是這場饑荒的幸存者之一。31年之后,孟加拉地區再次爆發饑荒,435萬人口淪為饑民。森對這次饑荒的調查,成為他寫作《貧窮與饑荒》一書的直接動機。他發現,當1974年饑荒爆發的時候,卻正是孟加拉糧食產量的高峰時期。1974年孟加拉糧食產量比前一年增長13%,人均糧食產量增長5.3%。對受災人口的統計表明,饑荒時期受害猶烈的是工人,尤其是農業工人,即稟賦權利中僅有勞動力而需要出賣勞動力換取口糧的人口。1974年左右,發生了一系列最不利于這部分人口的變化:第一,工資水平與糧食價格的交換比率急劇下降。第二,農業工人的就業機會減少。這兩個變化部分地歸因于1974年饑荒到來之前發生的一次大洪水,但事實上,在洪水之前,這兩種變化便已經出現。森指出,正是這兩個因素,從根本上解釋了孟加拉饑荒的起因。 森用以解釋饑荒的思路被稱為“權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繼《貧窮與饑荒》之后,出現了大批以“權利方法”研究饑荒和饑餓問題的文獻。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對中國1959-1961年大饑荒的研究。從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1)1959-1961年大饑荒的直接導因之一雖然是糧食減產,但這主要是由于中央計劃者的失誤所致,并非所謂自然災害。(2)其次,分配制度的變化也是導致饑荒的另一主要原因。以工業化為導向的大躍進運動,引起非農勞動力和城市人口的劇增,國家要求農村提供的糧食數量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3)在這次饑荒中也能看出不同人群在饑荒中受到的不同影響,農村地區的人口受災程度遠較城市人口嚴重,這似可歸因于農民免于饑餓的權利在“人民公社”運動中受到了剝奪(禁止自留地、征集口糧、在短期開放的農村集市上糧價狂漲、禁止農民逃荒等)。(4)計劃體制時期嚴重的官僚主義導致對饑荒的反應遲鈍。比如當1959年死亡人口急劇上升的時候,中國的糧食出口量卻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從森和其他研究者的工作我們可以再一次看出經濟學工具在分析現實問題時的力度。我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經濟學強調以一般均衡方法研究經濟系統,注重考察各種變量之間的互動關系。從這一角度,我們便可以看出,只是比較總人口數量與總糧食產量之間的關系盡管直觀,但卻是非常有缺陷的。為了更好地分析和預測饑荒,就必須對經濟系統的運作做深入的分析,為了更好地預防和杜絕饑荒,就必須保證經濟系統運轉良好。(2)經濟學研究個人在約束條件下的理性選擇,這個約束條件從廣義上講應包括個體決策的制度環境,這便凸現出制度分析在經濟學中的重要性。我想順便指出,熟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讀者也許已經發現,森關于免于饑餓權利的分析方法,與馬克思對工人階級由于在生產關系中處于不利地位而淪入貧困的分析思路非常相似。并不奇怪的是,馬克思早已被公認為制度經濟學的先驅。 經濟不平等的經濟學分析 經濟學圈子之外的人們可能會感到很吃驚:現代經濟學竟然幾乎與經濟不平等問題無緣。就連所謂的福利經濟學,也一直對這一問題視若無睹。 翻開福利經濟學的教科書,我們會讀到,福利經濟學的“核心命題”討論的是完全競爭與帕累托最優的關系。一向被經濟學家們奉為理想境界的帕累托最優狀態,是指若想增進社會中某一些人的福利,除非減少另外一些人的福利,換言之,在帕累托最優狀態下,我們已經無法設想一種能增進社會福利的政策,但又不損害任何一個人的原有利益。帕累托最優狀態并不考慮福利的分配。比如,若在幾個人中間分一塊面包,那么任何一種初始分配都是帕累托最優,哪怕是一人獨占而其他人都餓肚子,這是因為,按照帕累托最優原則,即使要求那個獨占面包的人給他的同伴分一塊面包屑,也會使他的利益受損。難怪,當森在寫作《論經濟不平等》一書的時候,不無感嘆地說:“就衡量經濟不平等問題而言,福利經濟學的皇家大道,通向的卻是荒涼山野。” 為什么要關注經濟不平等問題,或者說何以比較平等的收入分配是更可取的?至少,這里有兩個原因:第一,懸殊的收入不平等會導致效率的缺失。第二,收入不平等會造成公平的缺失。經濟學家如馬歇爾、庇古等關心的主要是前者,哲學家如羅爾斯關心的則主要是后者。森強調,全面地分析經濟不平等問題,應將這兩個方面都考慮進去。 森在書中考察了對經濟不平等的各種測量方法,其中既包括由統計學中而來的范圍、相對均值偏差、方差系數等,又包括常用的基尼系數,還包括泰爾(Theil)、道登(Dalton)、阿特金森(Atkinson)等人提出的測量方法。他發現這些測量方法雖各有短長,但卻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它們過份地追求完備性而忽略了經濟不平等問題本來就是模糊的、多面的、充滿了矛盾的、既是實證的又是規范的。總之,統計讓現實削足適履了。 森認為,當一個概念是模糊的,但這種模糊卻又很有意義時,我們應該做的是,尋找對這一概念的精確表述,同時在這一表述中又保留原有的模糊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既著手推動研究的精密化,又不損害問題的現實性。森的研究思路是,要綜合各種測量方法,對經濟不平等問題做出全面的分析,但并不追求完整的排序。 森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放松假設的條件下仍然能證明,比較平等的收入分配會導致更高的社會福利水平。傳統的福利經濟學是通過社會福利函數的嚴格凸性(strict concavity)來證明這一點的。但問題在于,原有的社會福利函數是通過個人效用函數的加總求得的,我將在稍后的部分談到,這種加總在邏輯上是很成問題的,而且嚴格凸性的假定也過于苛刻。森的貢獻在于,他證明了:首先,假定社會福利函數F是收入分配的函數,而非個人效用函數的函數,這樣便可以避開個人效用的加總問題,同時,這一社會福利函數F也不必是嚴格凸性,只要它是對稱的、嚴格擬凸的,就可以滿足:若有相同總收入條件下的兩種收入分配狀態x和y,如果y較x更為平等,則F(y)>F(x),也就是說收入分配為y時的社會福利大于收入分配為x時的社會福利。如果不能判定y較x更為平等,那么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收入分配為y時的社會福利小于或等于收入分配為x時的社會福利(嚴格的表述和證明可參見Dasgupta、Sen和Starret1973年發表于《經濟理論雜志》上的論文《關于不平等的測量》,或參見Sen《論經濟不平等》一書的第三章)。 森還進一步證明了,即使考慮到人口的變動、平均收入水平的變化、價格的變動,這一定理仍然成立。森的最后結論是:當導致完備性排序的各種測量方法綜合之后,它們所反映出的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也必定是準排序(quasi-ordering,指滿足傳遞性而不滿足完備性)的。因此,我們無法使用任何一種唯一的指標測量不平等問題,而是應將諸種測量方法綜合考慮。比如,他舉例說,在考察各國之間收入分配程度的時候,盡管我們可以明確地指出,英國的收入分配比印度更平等,而印度又比墨西哥更平等,但印度與美國、印度與斯里蘭卡的關系卻是無法排序的。以基尼系數和對數形式的標準方差來衡量,印度的收入分配比斯里蘭卡平等,但若以方差系數來衡量,則不及斯里蘭卡。以基尼系數和方差系數來衡量,印度的收入分配不及美國平等,但若以對數形式的標準方差來衡量,則又優于美國。森的這一思想對以后測量不平等、貧窮和實際國民收入等都很有影響。以測量貧窮問題為例,他反對但以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來衡量貧窮的程度,而是主張同時考慮進貧困人口的平均收入、資源在貧困人口中的分配等因素,建立更完備的一套指標體系。 森在這本書中還討論了與經濟不平等問題相關的分配原則問題,即理想的收入分配應該是基于“需要”(need)還是“應得”(desert)。用中國人熟悉的話說,應該是“按需分配”還是“按勞分配”。有趣的是,森更主張“按需分配”。他反對以“按勞分配”為最終原則的理由是:(1)如果說“按勞分配”更可取是因為“按勞分配”提高了工作積極性,那么最終的結果只是總產量的提高,假如我們不考慮總產量的分配,那么即使總產量提高,也并不一定意味著社會福利的增進。(2)如果說“按勞分配”是因為“多勞多得”,那么我們已忽視了人類能力的不平等和個人的基本需求。他尤其注意到“按需分配”原則在中國大躍進和文革時期的實踐。森認為,“按需分配”下可能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是人們不合作,即都希望別人多干自己不干,最后將是誰也不干,這就是典型的“囚徒悖論”。另一種結果則是人們合作,即在相信別人會干的情況下自己也干,最后將是社會福利的極大提高。當時,森已經看到,大躍進的失敗源于“囚徒悖論”。但他卻似乎相信“文化大革命”會導致合作的結果,因為合作的前提是通過宣傳和灌輸建立人們彼此合作的信念,而這似乎正是“文化大革命”要做的事情。森引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讀到此處,不知各位讀者有何感想,是感慨學者的真誠和天真,還是歷史的復雜與無情? 1997年,《論經濟不平等》一書又出了增訂版,這個版本中收錄了詹姆斯.福斯特(James Foster)和森合寫的一篇很長的附錄《<論經濟不平等>發表之后:四分之一世紀的回顧》,這篇附錄對二十多年來由森所引發的有關經濟不平等、貧窮問題、福利經濟學問題,做了詳盡的評論,但遺憾的是,他們不再提“文化大革命”了。 集體選擇的困境 每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總是授予經濟學某一領域的學科帶頭人。森獲獎的領域是福利經濟學,或更準確地說,是集體選擇理論。集體選擇理論(或稱社會選擇理論)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有著高度的現實性,因為這是我們據以評判經濟政策優劣、政治制度得失的基礎。同時,這一問題對智力又是個極大的挑戰,因為它思辨性和技巧性都很強,因此,無怪乎集體選擇理論吸引了諸多經濟學大師的興趣,在已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中,阿羅、布坎南、維克瑞、海薩尼等對此都有過專門的研究。 集體選擇理論的思想源頭可追溯至兩百多年前的歐洲思想家們如博達(Borda)、孔德特(Condorcet)、邊泌(Bentham)等,但其現代版本卻是自阿羅關于“不可能定理”的著名研究而始的。阿羅1951年出版了《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一書。他指出,公認的集體選擇規則應該能夠滿足四個公理式的前提。但給定這四個公理式的前提,我們又將無法確定集體選擇的結果必定是基于集體內部所有個人的偏好之上的。阿羅“不可能定理”試圖說明,個人偏好是無法加總的。而這將意味著所有根據社會福利函數(或曰社會利益)所做出的政策判斷其實在邏輯上都是經不起推敲的。 阿羅“不可能定理”所要求的四個公理式前提分別是:(1)集體選擇應是在所有可能設想到的個人偏好順序上建立起來的,即社會福利函數的域是非限定的。(2)如果每個個體都偏好x而不是y,則集體選擇的結果也應是x優于y,這被稱為帕累托原則。(3)不存在與社會偏好不一致的個體,阿羅稱此為非獨裁者條件。(4)對(x,y)的社會排序只能建立在個人對(x,y)的排序信息之上,即集體選擇的結果與其它因素無關。阿羅1951年提出的對“不可能定理”的證明,后來被布勞(Brau)指出是有漏洞的,阿羅在1963年又對原著作了修改。森1979年發表于《經濟雜志》的《個人效用與公共判斷:福利經濟學錯在何處》也提出了對“不可能定理”的一種推理式的證明。 由阿羅“不可能定理”所激發的一個問題是:能否,或者如何找到一種集體選擇機制,并據此合乎邏輯地推導出社會福利?這可以說是40多年來集體選擇理論發展的一條主線。 阿羅自己曾提出,如果能對個人偏好加以限定,則多數同意原則便可以成為一種可行的集體選擇機制。多數同意原則可以滿足其余三種公理式前提,唯獨與第一條公理式前提沖突:如果個人偏好完全自由,則多數同意原則可能會導致“投票循環”悖論。阿羅指出,只要選舉人的偏好都是“單峰偏好”,就可以避免“投票循環”。森則認為,多數同意原則在政治領域或許可行,比如從幾個候選人中選主席,從幾個備選議案中選最佳方案,但在經濟領域中,涉及的商品選擇成千上萬,“單峰偏好”的限定極難滿足。更重要的是,多數同意原則僅適于“判斷”的加總,而不適于“利益”的加總,因為個人的利益之間往往存在直接的沖突。還舉分面包為例,如果僅依據多數同意原則,我們甚至可以贊同這樣一種結果:多數人舉手同意,從最窮的那個人手中瓜分面包。在現實中,這種分配原則顯然是無法為人接受的。 森所做的許多重要工作都與集體選擇理論有關,他在多篇論文中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不同思路。比如放松對社會偏好完備性和傳遞性的嚴格限制、擴展集體選擇機制隱含的“信息”基礎、考察人際比較問題等等。其中,他最引人注目的貢獻是將自由與權利原則引進了對社會福利的研究。1970年森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很短的論文《帕累托式自由的不可能性》,引發了后來的大量研究。在這不足10頁篇幅的短文中,森證明了被經濟學家一向奉為圭臬的帕累托最優原則,其實是與現代社會公認的個人自由原則相沖突的。 森講了一個有趣的小故事。假定有兩位先生,他們對《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部小說有著很大的意見分歧。假定有三種社會狀態:即A先生讀而B先生不讀(x),B先生讀而A先生不讀(y),兩個人都不讀(z)。A先生是一個衛道士。他希望最好是誰也不讀,其次是寧可他自己讀也不愿讓B先生讀后中毒,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只有B一個人讀,因此,他的偏好順序是z>x>y。B先生則是個“思想開放”的人,他最希望人人都能欣賞這部小說,尤其是愿意看到像A先生這樣的衛道士也放下架子讀《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其次,要是A實在不情愿,他愿意自己讀,他最不能接受的是這部小說被查禁,誰也讀不成。B的偏好順序為x>y>z。按照個人自由的原則,若先在(x,z)這兩種狀態中選擇,則z要優于x。因為在x狀態下,想讀的人讀不成,不想讀的人卻偏要讀,對AB兩位先生來說,都是極不情愿的。然后再在(y,z)兩種狀態中比較,則y又要優于z,因為在y狀態下,不想讀的人就不讀,想讀的人就讀,互不干涉,皆大歡喜。所以,按照個人自由原則來考慮,y要優于x,但是如果遵循帕累托最優原則,結果恰恰相反,因為根據x>y>z和z>x>y這兩組個人偏好順序,我們會得出x>y,因為在這兩組排序中x都排在y前。森這則故事的寓意是:帕累托最優原則與個人自由原則是不相容的。因此,要么放棄個人最優原則來成全帕累托最優原則,要么放棄帕累托最優原則來弘揚個人自由原則。在森看來,后一條道路才是可行的。 盡管半個世紀以來,集體選擇理論的文獻越積越厚,盡管有像森這樣兼有仁者之胸懷與智者之頭腦的導師指引方向,但是,坦率地講,至今為止集體選擇理論仍在蛹中掙扎。盡管還有其它種種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似乎要算在阿羅之后,集體選擇理論并沒有再提出具有挑戰性和震撼力的問題。我個人的比較消極的預測是,如果這種局面沒有改觀,恐怕集體選擇理論最后只能成為經濟學家們興致勃勃地借以消磨時間和腦漿的猜謎游戲。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何帆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