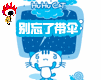| 試論儒家思想對中國伊斯蘭教的影響和滲透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09日 15:25 中評網 | |||||||||
|
1984年10月 伊斯蘭教自唐初入華,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土地上扎根、傳播、發展。在回、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吉克、塔塔爾、烏茲別克、東鄉、撒拉、保安等10個民族中,有著廣泛的影響。逐漸形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變成一種中國的伊斯蘭教。因此,她也必然受中國封建社會經
一、如何接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和滲透 中國伊斯蘭教如何接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和滲透,是生吞活剝,照搬照抄,還是消化,改造為我所用呢?這從明清之際的中國伊斯蘭教漢文譯著中,可以窺見一斑。 明末清初,在中國伊斯蘭教界產生了一批宣揚教義的漢文譯著。比較重要的有:王岱輿的《正教真詮》、《清真大學》、《希真正答》,張中的《歸真總義》,馬注的《清真指南》,劉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天方至圣實錄》,以及咸豐同治年間藍煦的《天方正學》,馬德新的《四典要會》、《大化總歸》等。這些譯著的作者,一般都從小攻讀儒經,是“懷西方(指阿拉伯地區)之學問,習東土之儒書”的“回儒”,有些人甚至是儒、釋、道、回“四教兼通”的宗教學者。為了宣傳教義,他們將“天方經語略以漢字譯之,并注釋其義焉,證集儒書所云,俾得互相理會,知回、儒兩教道本同源,初無二理。”1 以世界觀為例。中國伊斯蘭教學者吸收了周敦頤、朱熹等人關于萬物統一于五行,五行統一于陰陽,陰陽統一于太極,太極本無極的觀點,并將這種觀點與伊斯蘭教“認主獨一”的教義結合起來,用“太極說”為宣傳“認主獨一”服務。他們稱無極為“萬物之原種”,太極是“萬性之原果”,在這二者之前,他們安排了一個“造化之原主”,這就是“真一”,又叫“真宰”。他們說:“真一有萬殊之理,而后無極有萬殊之命,太極有萬殊之性,兩儀有萬殊之形。”2 “真宰無形,而顯有太極,太極判而陰陽分,陰陽分而天地成,天地成而萬物生,天地萬物備,而真宰之妙用貫徹乎其中。”3 乍看起來,中國伊斯蘭教學者的“真一說”與理學家們的“太極說”似有不同。細加對照,則可以發現二者在以下三個方面是一致的:首先,二者都被說成是萬事萬物的總根源,造化天地人物的本體。朱熹稱太極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匯之根柢也。”4劉智說真一“至清至靜,無方所,無形似,不牽于陰陽,不屬于造化,是天地人物之本原也。一切理氣,皆從此本然而出。”5其次,二者都被說成是超時空的永恒存在,普遍存在,而一切事物的生滅、動靜,都是它們作用的結果。朱熹說太極本身無動靜,無始終,但因為包含動靜之理,因此氣有動靜。氣的動靜互相聯系著,無靜不能動,無動不能靜。陰靜之中已有陽動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靜之根。一動一靜,循環不已,化生出五行及天地萬物。劉智等人說真一的時間性是“前無始,后無終”,空間性是“大無外,細無內”,“無方所,無遐邇”。真一也是“無動無靜”,但又非不動不靜,而是“動靜不常”,含有動靜之理。“先天之造化,起于一理之動;后天之造化,起于一氣之動。以理氣之動靜,喻真宰之隱顯,乃神其造化之機,申其妙用流行之自也。”1所謂“動靜不常”,不是講此時動,彼時靜,這邊動,那邊靜,有動和靜這兩個極端;而是指時起時息,“動亦靜,靜亦動,絕無止息”,動靜不已,動靜無端,循環往復,從而造化出天地萬物來。“萬物無以為生,而生于理氣之動靜;萬物無以為化,而化于真宰之隱顯。故曰其生生之本也。”2第三,二者都被說成具有道德屬性;是至善的,完美無缺的。朱熹說:“事事物物,皆有個極,是道理極至。蔣元進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先生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個表德。”3太極是萬事萬物的典型,萬事萬物的形成和發展便以太極為歸宿。劉智等人也說真一是“至知也,至能也,至全也,至善也。”4真宰是萬事萬物的典型,它造化了天地萬物和人類,天地萬物和人類的形成、發展也都要以真宰為歸宿。“一切理氣,皆從此本然而出。所謂盡人合天者,和于此也;所謂歸根復命者,復于此也。是一切理氣之所資始,亦一切理氣之所歸宿。”5“無一物之不化者,實無一物之不歸。此足征大化之流行,而信歸真之非偶。”6 因此,所謂“真一說”與“太極說”,從實質內容上講,沒有什么原則性的區別,同屬于客觀唯心主義的范疇。區別只在于,伊斯蘭教學者們將“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的基本信仰,與理學家們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太極說巧妙地結合起來,用真一取代了太極,將太極降到本于真一的從屬地位。其實,劉智們所說的“太極”已不是朱熹們所說的“太極”,它們所說的“真一”才是朱熹們所說的那個“太極”。 從這些漢文譯著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在認識論上、在人性論上以及在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觀念上,都有儒家思想影響的痕跡,這里就不多贅述了。總之,僅僅通過上舉本體論的例子,我們便不難發現,中國的回族伊斯蘭教學者們并非生吞活剝地照搬儒家的思想和概念,而是把這些儒家的東西接受下來,經過消化、理解和改造,使之與伊斯蘭教思想相融合,成為一種特殊的中國伊斯蘭教的思想,從而為宣傳自己的伊斯蘭教義服務。那種認為中國伊斯蘭教學者簡單襲用了儒家某些概念的說法,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 二、接受儒家思想影響的范圍和程度 儒家思想對中國伊斯蘭教的影響不僅范圍廣,而且程度深;不僅限于漢文譯著,而且深入到清真寺中,深入到教民對教義理解上。這一點,以回族清真寺中所懸漢字匾聯尤為明顯。 眾所周知,伊斯蘭教的基本宗教職責是所謂“天命五功”,即念(誦清真言)、禮(禮拜)、齋(齋戒)、課(納天課)、朝(朝覲天房)。涉及“五功”的漢文匾聯很多,反映出回族穆斯林對這些“天命五功”的理解和認識。如: 天命不敢違道,完五功方見獨一真光;人心猶宜盡理,通三乘得開百年暗幔。7 須實踐五功,天心大可見矣;莫分言三乘,吾道一以貫之。8 上舉兩聯頗有趣。其上聯意思相近,均言實踐天命五功之意義。其下聯則意思相左:前者強調“三乘”的重要性,認為通過人心的修持,達到“通三乘”的境界,即可“開百年暗幔”,超凡入圣;后者則明言反對“分言三乘”,強調“吾道一以貫之”。這表明兩聯的作者分屬不同的教派。上舉第一聯從其文中強調“三乘”來分析,作者當系屬既主張教乘修持又主張道乘修持的門宦教派無疑。三乘,又稱三程,是中國伊斯蘭教神秘論者和部分學者,依據蘇非派修煉道路宣稱認識和接近真主的三個過程和三個等級。包括(1)教乘,指一般穆斯林通過“五功”等修身途徑,認識和接近真主。(2)道乘,指通過清、廉、保、養、念等功修,棄絕塵事,嚴守教規,晝夜堅持,躬行實效,通過七種障礙,去接近真主。(3)真乘,指通過明心盡性等修煉步驟,達到“渾然無我、心不納物、唯獨一主”及性與天道合一的境界。認為達教乘者,可以涉世;達道乘者,可以忘世;達真乘者,可以出世稱圣。三乘學說,本是蘇非派的思想,在正統派伊斯蘭教義中并不存在。但在中國古代回族學者所寫的漢文伊斯蘭教譯著中,這三乘學說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人甚至強調伊斯蘭教之所以至貴,就在于講明了和履行著常道、中道、至道這三乘。可見三乘說在部分回族穆斯林思想中影響頗深。究其原因,一是蘇非派思想的輸入和影響;另一則是中國理學家所倡明心、凈性、修身、養性等功夫的影響和滲透。上舉第一聯正要人們尤須注意去人欲,存天理,修行辦道,明心養性,以通三乘,與主合一,“開百年暗幔”,充分反映了蘇非派思想、伊斯蘭教的正統派思想與中國理學家思想合而為一的事實。 上舉第二聯的作者是賽來菲耶教派,賽來菲耶教派是新興教派伊合瓦尼中分化出的一個小教派,教義與伊合瓦尼大體相同,只是在儀式上主張禮拜時抬三次手,故被人誤稱為“三抬教派”。他們受阿拉伯國家瓦哈比派影響,以天命五功為頭等重要的事清,主張必須遵行。他們反對門宦制度,反對修行辦道,反對“三乘說”。 因此,新王寺聯中明確標榜“遵經”,但即便如此,其受儒家影響的痕跡仍清晰可見。“吾道一以貫之”語出《論語.衛靈公》,其中的“一”原作一向、始終解。新王寺聯的作者將這句孔子語錄搬將過來,既反對了三乘說,又強調了所謂的“正教貴一”,即伊斯蘭教認主獨一的一神論思想,可謂是一箭雙雕,巧妙之極。這當然不是他的發明,劉智就明確講過:“理會得一之為一,則通篇之義不求解訓而自能了達矣”;“經義通篇,只以一字貫之。”[1]而劉智則眾所周知是確實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著名回族學者。 再看專為禮拜者寫的對聯有: 爾來禮拜乎?須摩著心頭,干過多少罪行,由此處鞠躬叩首;誰是講經者?必破除情面,說些警嚇話語,好叫人入耳悚神。[2] 入此門,登此殿,莫朦混,禮了拜去;洗其心,滌其慮,須仔細,做起功來。[3] 這兩聯亦很有趣。上一聯前半聯講的是禮拜,使人感到禮拜的目的是要向真主作懺悔,以求得主的饒恕;后半聯是對講經者而言的,要講“瓦爾茲”的阿訇們多講些危言聳聽的警嚇話語,好叫人們入耳悚神,多來禮拜。下一聯的前半聯也是講禮拜,強調的是“莫朦混”;后半聯講禮拜時要注意的三件事:一是“洗心”、二是“滌慮”、三是“仔細”認真。這三條實際上講的無非是一個道理,即擺脫人間一切情欲思慮,一心向主,認真嚴肅地完成天命五功。這正是理學家們強調的清心養性。在清真寺匾聯中,關于洗心、滌慮的修養內容很多。如寧夏同心清真大寺寺門上懸磚匾三方,中為“清真大寺”,左右分別為“洗心”、“忍耐”。山西太原東米市南牛肉巷清真大寺,昔名“清修寺”,寺內中心建“省心樓”一座,“省心樓”三字傳系明代嚴嵩所書。福建泉州清凈寺,明萬歷年間重修時曾將樓北左側居房改作“洗心亭”。北京三里河清真寺水房名曰“規潔室”;望月樓上有匾文曰“喚醒樓”,表示喚醒世人迷途之意。北京牛街禮拜寺南講堂名“闡一堂”,表示系闡述獨一真主之室;沐浴室顏曰“滌慮處”,蓋謂沐浴者不僅須潔身,尤須潔心之意。從上舉種種匾聯文中,不難嗅出儒家所謂明心、凈性的味道。甘肅西道堂更有聯云:“把齋貴清心上地,拜主須養性中天”,不特將把齋、禮拜與清心養性直接聯系在一起,甚至認為把齋貴在清心,拜主必須養性。理學家的清心、養性,成為穆斯林履行宗教功課齋戒、禮拜所刻意追求的目標和境界。對伊斯蘭教義的這種理解,應是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結果。 北京東四清真寺殿前南側有個《圣贊碑》,碑陰刻有阿拉伯文、漢文兩種文字。阿拉伯文是Bismi allah al-rahim,又稱“太思米葉”,意譯為“奉普慈特慈安拉之名”。漢文是四個大字:“理本無極”。眾所周知,“理”是宋代理學家朱熹哲學思想體系中的基本范疇。它的直接來源之一,便是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太極圖說》云:“無極而太極。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按朱熹的注說,無極而太極,即是指“無形而有理”,也就是說,太極無形無象,不可言說,故稱“無極”。東四清真寺《圣贊碑》碑陰漢文的作者,顯然深得其中三昧,故而干脆將周敦頤那句“太極本無極”,直接改作“理本無極”四字,置于阿拉伯文“太思米葉”的下面,充分加以肯定,從而表明他完全同意朱熹所代表的宋明理學家那套客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 吳文良先生所編《泉州宗教石刻》一書照片部分第20頁圖59,是福建泉州通淮門大街清真寺大門的一張珍貴照片。從這張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有兩方橫匾赫然懸于寺門之上。上面一方匾曰:“萬殊一本”;下面一方匾曰:“三畏四箴”。顯然,這又是儒家的東西。萬殊即萬物,均有所本,本于什么呢?理學家說本于理,本于太極,本于無極;穆斯林學者說本于真一。名異實同,已如上述,不復贅。“三畏四箴”,即孔子的“三畏四勿”。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4]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5] 回族穆斯林將孔子的“三畏四勿”作為箴言,懸于日夜出入的清真寺大門之上,表明他們是樂于接受儒家思想并愿意以此指導自己實際行動的吧? 在贊頌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方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儒家的影響。請看下面兩副對聯: 本真誠以立圣行,成己成仁,允矣道全德備;體大公而遵主命,善心善世,洵哉仁精義熟。[6] 惟道無名,看懷德畏威,西域久垂聲教;以誠立愿,喜父慈子孝,中華遞衍薪傳。[7] 我們知道,誠、仁、義、道、德、慈、孝等,都是中國儒家哲學思想體系中的一些概念和封建倫理道德標準。就以“誠”來說吧。周敦頤在闡述其立誠學說時曾說:“誠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8]他又說;“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9]他認為萬物所開始的“乾元”,是誠的本源,而這種誠又是仁、義、理、智、信五常的根本,是圣人為圣的根本。顯然,這個誠絕非指人與人之間誠實無欺的品質,而是《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那種神秘的精神境界。上舉兩副清真寺聯中的“本真誠以立圣行”和“以誠立愿”的誠,都正是周敦頤所講的那種表示神秘精神的境界。因為“誠者圣人之本”,所以寺聯贊穆罕默德是“本真誠以立圣行”。請注意,這里在“誠”字前還特意加了一個“真”字。何謂“真誠”?周敦頤不是講“‘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么?寺聯中之“真”正是周氏所講這種“誠之源”的“乾元”,也即是穆斯林所講的“真一”。又因為“誠,五常之本”,所以源于“真一”之“誠”作為立圣行之本的穆罕默德,可以“體大公而遵主命”,“成己成仁”、“善心善世”,是一位“道全德備”、“仁精義熟”的大圣人;所以“以誠立愿”的伊斯蘭教,可以做到“父慈子孝”,令人“懷德畏威”,不僅在“西域久垂聲教”,而且能在“中華遞衍薪傳”。由此可知,回族穆斯林在贊頌自己的圣人和崇信的宗教時,也是從儒家的角度出發的。 回族穆斯林還將儒家“致知格物”的認識論和“克己”功夫,運用到對齋戒的理解上。請看下面這副對聯: 開之謂言解,解微、解妙、解一本誠,是大人致知學問;齋之取意齊,齊身、齊心、齊七情欲,正君子克己功夫。[10] 從上下聯的第一個字看,可推知,這副對聯均是在開齋節大典時闡述開齋節會禮意義的作品,它反映了作者的認識論和修養觀。上聯講要本著周敦頤所謂的那種唯心主義的“誠”,去理解去認識真一的微妙和真一本身,才是朱老夫子所講的那種大人致知學問。下聯講封齋的目的就在于齊身、齊心、齊七情欲,這正符合孔老夫子所講的那種君子克己功夫。縱觀全聯,無非是講述一個道理,即朱熹所說的“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11],只不過帶有一些伊斯蘭教的色彩罷了。 這一類匾聯,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限于篇幅,還是就此打住吧。僅從上述,我們已不難看出,回族穆斯林接受儒家的影響和滲透,范圍很廣,程度頗深。他們從儒家的角度,用儒家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自己世代信奉的伊斯蘭教;用儒家的概念,用儒家的語言,去表述和贊頌自己的宗教和圣人。合肥張廣健曾為青海西寧東關大寺寺門寫過這樣一副對聯: “清凈明心,義通釋旨;真實進德,理合儒宗。” 宋明理學是融會儒、釋、道諸家之說的儒家。張廣健所撰此聯明言,以“清真”自詡的中國伊斯蘭教,“義通釋旨”,“理合儒宗”。這正說明我國回族同胞所信奉的中國伊斯蘭教,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和滲透了。 歷代為回族清真寺書寫漢字匾聯、碑文者甚多,其中有朱元璋、康熙、雍正等歷代最高統治者及其手下的官僚大臣,也有歷代知名的學者文人。目前我們所知年代最久的匾聯,當推太原清真古寺的兩方匾:一系北宋邵雍所書“道見知洪”,一系南宋朱熹所書“百世好教”。中國伊斯蘭教不僅一再得到歷代封建帝王的賞識,而且得到了象邵雍、朱熹這類道學家、理學家們的褒贊和高度評價,使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看出它接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程度之深了。 三、接受儒家思想影響始于何時? 有人認為,中國伊斯蘭教接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和滲透,最初始于清代的馬注(1640-1711)和劉智(約1660-1739);后來又有人說王岱輿(約1570-1660)的作品中也有儒家的東西。總之,時間約在清代初年。 在搜集整理《中國伊斯蘭教參考資料選編(1911-1949年)》時,我們發現了一些新資料,可知所謂“回回附儒以行”絕非始于王岱輿、馬注、劉智三氏。如福建泉州清凈寺萬歷三十七年(1609)重修碑,文中對儒、釋、凈(即伊斯蘭)三教進行比較后,得出“說者謂儒道如日中天,釋道如月照地,余謂凈教亦然”的結論,其作者李光縉亦自稱“儒林門人”。又如西安化覺寺所存的創建清真寺碑,碑文落款系唐代“賜進士及第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王鉷撰篆”。但據中外名家考證,此碑是明代人假托唐王鉷名義而刻。陳垣先生曾指出:“碑文語義,純是宋明以后語,與唐人語絕不類。”[12]白壽彝教授也曾指出:“碑文所謂‘事天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不越乎吾心之敬而已矣’,所謂‘寡欲以養心’,都是宋明理學家底話頭,唐人是說不出的。”[13]碑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西域圣人謨罕默德,生于孔子之后,居天方之國,其去中國圣人之州之地不知其幾也。譯語矛盾,而道合符節者,何也?其心一,其道同也。 顯然,這是在強調伊斯蘭教與儒家思想相結合。故白壽彝教授指出:“我疑惑碑文的作者是一個外教人。即使是本教人,也是一個儒化甚深的,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人。”[14] 山東濟南清真南大寺有一碑銘,名為《來復銘》,作者是明嘉靖七年(1528)該寺世襲掌教陳思。銘文全篇僅155個字,宣傳的是伊斯蘭教基本教義,而其所用主要的理論根據竟是北宋理學家張載關于天道心性的定義:“繇太虛有天之名,繇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按白先生的話說,陳思當“也是一個儒化甚深的,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人”了。 據上舉三例,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斷:中國伊斯蘭教接受儒家思想影響和滲透,由來已久,至遲在明中葉便開始了。 大家知道,元、明之交,是中國回回民族開始形成之際。根據上面的推斷,我們說,在回族形成伊始,回族穆斯林的學者們就已經在摸索“回回附儒以行”的道路,主動接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和滲透,用儒家的思想去看待、解釋、宣傳伊斯蘭教的教義了。 四、接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幾點原因 造成中國伊斯蘭教接受儒家思想影響和滲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我以為有以下幾點為最主要: 第一、伊斯蘭教發展變化的必然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實踐告訴我們,一切事物都在發展變化,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說教,不過是表達了取得政權的地主階級世代維持自家統治的主觀愿望而已。作為一種上層建筑,宗教是一定社會的產物。社會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總在不斷地發展變化著,那么反映這些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宗教,也必然要相應地發生改變。伊斯蘭教是公元7世紀阿拉伯地區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產物。隨著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經濟、文化的交流,伊斯蘭教從唐朝初年開始傳入中國。無論是經濟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都有所不同。特別是在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經過一千數百年的漫長歲月,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傳播、發展,在很多少數民族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逐漸形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它也必然要受到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的制約,受到中國古老的封建文化的影響和滲透,從而帶有中國的某些風格和特點。伊斯蘭教的這種發展變化,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第二、接受儒家思想影響和滲透的必要性。做為一種外來宗教的意識形態,為了在中國站住腳,必須要與中國本土的思想意識相融合。如上所說,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與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情況是分不開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自有它的特殊性,以封建宗法制度為核心的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而支持這一社會制度的主要思想支柱,正是大力宣揚三綱五常的儒家思想。宋元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后期。在這個時期中,由于社會政治條件的改變,中國的封建主義不斷從思想意識的各個方面得到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也更趨于強化。伴隨著這種政治上、思想上集權統治的強化,隋唐時期儒、道、佛三教鼎立的局面打破了,道、佛兩教形式上走向衰微,它們的宗教精神滲透到儒家思想的內部,形成為以儒家為中心的三教會同的新局面。宋明理學就是這樣一種以孔子為招牌,大量吸收了佛教、道教宗教世界觀和宗教實踐的新儒學。這種新儒學因得到宋元明清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的賞識而被捧上了天,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不可一世。凡是外來文化,如果不受儒家的歡迎,在中國就根本不能存在。象摩尼教、火祆教、景教、婆羅門教,都曾一度流入中國,但也均很快就被淹沒不傳,除了留下一塊大秦景教碑和一些殘破不全的墓碑石可供考證外,其他遺跡已很難尋見。恰在此時前后傳入中國,并依靠家庭父傳子受、循人口自然繁殖而緩慢發展起來的伊斯蘭教,明代末期已顯現出衰敗的趨勢:教內人宗教知識淺薄,宗教信仰發生動搖的現象已有所發生;教外人由不了解進而至于猜忌、排斥,火藥味已經很濃。伊斯蘭教若再不適應環境,主動向儒家思想靠攏,盡可能接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和滲透,盡可能多地用儒家語言將自己的教義裝扮起來,要想在中國歲長代久地生存下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三、接受儒家思想影響和滲透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思想基礎,另一個是群眾基礎。 伊斯蘭教教義與儒家思想相通或相似之處,為二者的結合提供了穩定的思想基礎。有回回諺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15]表明伊斯蘭教對儒家思想的態度是十分肯定的,二者的思想體系是相通的。從世界觀上說,二者同屬于唯心主義范疇。從這種世界觀出發,二者觀察和認識社會的方法論也基本上是一致的。二者都反對出世,都看重今世,因此也就都很重視人生倫理道德的修養及對現行封建秩序的維系。儒家鼓吹“小不忍則亂大謀”,伊斯蘭教強調“順從”、“堅忍”;儒家主張“中庸之道”,認為“過猶不及”,伊斯蘭教主張“正路”(又譯“中正之道”),反對“過分”。凡此種種,二者的主張都趨于一致。 此外,同一切事物一樣,儒家學說也在不斷地發展變化。漢代董仲舒的儒學與孔孟為代表的儒學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是已經神學化了的儒學。到了宋代,朱熹等理學家們進一步吸收佛、道兩教的宗教世界觀和宗教實踐,使儒學進一步宗教化。這種宗教化的宋明理學,提出了種種神學主張,如提倡涵養靜修,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致力于“天理人欲之辨”,要人們“存天理,去人欲”等等。這些主張很容易得到同是宗教神學的中國伊斯蘭教的贊同和響應。 上述這些基本思想的相通和一致,使中國伊斯蘭教自覺接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和滲透有了比較可靠的思想基礎。 唐宋以來,中國穆斯林世代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影響,為中國伊斯蘭教接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和滲透打下了群眾基礎。自唐初穆斯林來華,歷經唐宋元明四朝,中國穆斯林積極認真地學習古老的漢族文化,世代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涌現出一大批學習、研究、宣傳儒家文化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和詩人。長期以來,儒家的那套唯心主義世界觀、認識論、人性論、道德觀,不僅為中國回族穆斯林的上層人士所接受,而且也對廣大回族穆斯林群眾發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緊緊地束縛和禁錮著他們的思想。雖然確也出現過李贄那樣勇于向傳統封建文化和封建禮教挑戰的先進分子,但那畢竟是極少數;而且這極少數激進分子的思想,既非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一般地說,也不會成為支配廣大群眾的思想。正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指出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樣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16]人們所處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決定了他們擺脫不掉儒家那套說教對自己思想的影響。這種影響程度是如此之深,使他們不能不用儒家的眼光去看待、去理解自己世代所信奉的宗教。這樣,用儒家思想與伊斯蘭教義相結合的方式去宣傳教義,既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又是能為廣大穆斯林群眾易于接受的事情了。 五、一點希望 儒家思想的影響和滲透,給中國伊斯蘭教注入了新鮮血液,使中國伊斯蘭教學術界呈現出一片生機。一批回族穆斯林學者用儒家的語言、儒家的思想系統地研究、整理、總結伊斯蘭教義,完整地構造了中國伊斯蘭教的思想體系,寫出了一批帶有中國獨特風格的伊斯蘭教漢字碑文、匾聯和作品,在中國回族穆斯林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這些與中國封建主義哲學相結合的宗教作品中,有比較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有比較精密的分析問題的邏輯性,有啟發人們進一步尋求正確答案的眾多哲學問題,有優美的文筆、不拘一格的藝術形式。因此,可以說這些富于哲理性的著作,豐富了我國哲學史、思想史、民族史、宗教史,從而成為我國的文化寶庫中的一批珍品;無疑,這也是中國回族穆斯林在中國文化與阿拉伯文化相互交流方面做出的一種極寶貴的貢獻。這些作品以及他們的作者,理應在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縱觀現在諸大家所撰的這類著作,對各族穆斯林(包括回、維吾爾等10個民族)學者及其作品竟無一提及。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遺憾!沒有對中國伊斯蘭教學者的哲學思想進行系統深入地研究和給予適當的評價,我們的哲學史、思想是就很難說是完全的,很難冠以“中國的”名目。須知,這是涉及到10個兄弟民族、一千三四百萬人民的哲學思想啊!為此,懇切吁請從事于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專家學者們,補上這一不容忽視的重要內容,使我們撰寫的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名副其實吧! (原載《中國哲學史研究》1985年第3期) 附注1:2002年11月27日與吳云貴、金宜久、周燮藩一起去香港城市大學,應張信剛校長邀請,參加“中國與東南亞地區伊斯蘭研討會”,并在最后一天的中文專場上作了最后一名發言者。當時我就是以這篇文章與會的。2003年8月初,收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所寄《九州學林》2003.秋季創刊號一冊。這是一個學報刊物,其前身是海外的《九州學刊》和上海的《學術集林》;由香港城市大學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發行;主編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鄭培凱教授。我的這篇論文即發表在該刊的第313-329頁。發表前,我曾對其中一些字句作了技術性修改。 (2003年8月3日) 附注2:香港印尼研究學社主辦的刊物《印尼焦點》2003年11月15日(半年刊)第13期“學術景觀”欄第68-73頁,轉載了本文。轉載時,編者將論文題目改為“中國伊斯蘭教如何接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和滲透”,并加了一個編者按如下:“香港城市大學于2002年11月28日-12月1日,在香港舉行中國與東南亞地區伊斯蘭研討會。中國社會科學院馮今源教授應邀在會上發表關于中國伊斯蘭教和儒家思想相互影響問題的講話。講話受到廣大與會者的關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03年將這篇講話收入《九州學林》的學術刊物里。經本刊顧問黃麗嫣教授的聯系,中國文化中心2003同意我學社在本刊將其全文發表,對他們的信任和支持,謹此深表謝意。”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馮今源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