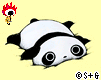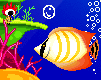| 《來復(fù)銘》析[1]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09日 15:13 中評(píng)網(wǎng) | |||||||||
|
1947年6月號(hào)《月華》雜志,曾載奚利福先生的舊作《教門金石文》跋尾第二十七《來復(fù)銘》一文。文中,奚先生全文披露了山東濟(jì)南清真南大寺的一塊明代石刻的銘文《來復(fù)銘》。這篇銘文篇幅雖小,卻是我國伊斯蘭教史上一份承上啟下的珍貴資料。該文發(fā)表后,未見有對(duì)這篇銘文深入研究的文章,這是十分令人遺憾的。本文擬對(duì)《來復(fù)銘》銘文進(jìn)行一些嘗試性的初步探討,并對(duì)我國伊斯蘭教自覺接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和滲透所形成的中國伊斯蘭教哲學(xué)思想,以及這種思想在中國哲學(xué)史、思想史所占的地位,表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來復(fù)銘》作為中國清真寺的一篇碑文,有其許多獨(dú)特之處,而首先引人注目的便是它的作者。查目前所知明代以前的一些清真寺碑文,它們的作者多為教外人。有的是教外的學(xué)者:如元至正十年的泉州《重修清凈寺碑記》的作者,是著《清源郡志》二十卷的三山吳鑒,明萬歷三十七年泉州《重修清凈寺碑記》的作者,是自稱“儒林門人”的李光縉。有的是教外官僚,如唐天寶元年長安《創(chuàng)建清真寺碑記》的作者,據(jù)碑文中稱系當(dāng)時(shí)的“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王鉷;明正統(tǒng)十二年北京《敕賜清真寺興造碑記》的作者,是“戶部尚書、翰林院學(xué)士”陳循。有的碑文雖系教內(nèi)人所撰,但一般是教內(nèi)之官僚:如元至正八年定州《重建禮拜寺記》的作者,是“承務(wù)郎、真定路安喜縣尹兼管諸軍奧魯”楊受益;元至正十年廣州《重建懷圣寺碑記》的作者,是“奉議大夫、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jīng)歷”郭嘉;明嘉靖二十八年福州《重建清真寺記》的作者,是“賜進(jìn)士第、朝列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左參議”米榮。清真寺的掌教阿訇親自撰寫清真寺漢字碑文,明以前極少。然而我們所要加以分析的這篇《來復(fù)銘》,碑末鐫刻的卻分明是“本寺掌教陳思沐手著”[2]。這在中國伊斯蘭教史上是僅見的。 掌教阿訇們一般不撰寫寺碑文,自有其原因在。從主觀上講,他們可能認(rèn)為由教內(nèi)外的官僚、學(xué)者出面撰寫碑文,比自己親自撰寫會(huì)產(chǎn)生更好的社會(huì)影響。也就是說,在伊斯蘭教剛剛傳入中國而立足未穩(wěn),尚未受到中國社會(huì)上的普遍認(rèn)識(shí)之際,請(qǐng)一些社會(huì)上有影響的官僚或?qū)W者名流為本教樹碑立傳,有利于伊斯蘭教社會(huì)地位的鞏固和提高。從客觀上講,那時(shí)的掌教阿訇們,無論是漢文化水平,還是伊斯蘭教知識(shí)水平,可能都未達(dá)到親自撰寫漢字碑文的程度。上舉各碑文中關(guān)于伊斯蘭教的知識(shí),反映出當(dāng)時(shí)為碑文作者提供這些知識(shí)的掌教阿訇的水平并不是很高的。 但是,《來復(fù)銘》的作者陳思卻是一位掌教,而且是一個(gè)在全國較有名氣的大寺——山東濟(jì)南清真南大寺的世襲掌教。據(jù)奚利福先生考證:陳思的先人陳英,在明初曾三次出使西域,供職光祿寺,后退隱濟(jì)南。宣德元年(1426),陳英推薦木鐸作濟(jì)南南大寺的掌教。陳英在當(dāng)?shù)啬滤沽种械牡匚缓陀绊懀纱丝梢娨话摺Uy(tǒng)元年(1436),在位十年的木鐸又薦陳英之子陳禮主持掌教事,是為陳氏家族第一代掌教。陳禮在位五十二年,其子陳璽于弘治戊甲(1488)領(lǐng)有禮部札付,住持該寺,是為陳氏第二代掌教。陳璽在位十九年,于正德十二年(1517)卒,其弟陳瑩繼位,亦領(lǐng)有禮部札付,是為陳氏第三位掌教。陳思即此陳瑩之后。《來復(fù)銘》碑刻石于明嘉靖七年(1528),距陳瑩繼掌教位的時(shí)間為十一年,這可能正是陳思接任濟(jì)南清真南大寺掌教的時(shí)間吧?按明制,凡清真寺住持必須申請(qǐng)領(lǐng)取禮部發(fā)給的札付,以為憑據(jù)。其初次領(lǐng)取或再度換取的手續(xù)非常繁難,絕非易事。陳思的伯父陳璽始領(lǐng)札付,父陳瑩繼領(lǐng)札付,是經(jīng)官方正式承認(rèn)的清真寺掌教,非尋常阿訇可比。他們能順利地領(lǐng)取札付,恐怕與其祖陳英“明初三使西域,供職光祿寺”的歷史不無關(guān)系。而領(lǐng)有禮部札付的掌教,又“冠帶榮身,仍準(zhǔn)免差徭”[3],儼然一政府官員,非常尊貴威嚴(yán)。這就告訴我們,陳思出身于一個(gè)在當(dāng)?shù)睾苡袆?shì)力、很有影響的家庭,他的先人都曾是這一方舉足輕重的人物。陳思要書寫碑文,似乎無需再轉(zhuǎn)借他人的威望,他本人的出身足以使他具有這種資格。另外,他少承家學(xué),又生長于孔夫子的故鄉(xiāng)山東,不僅具有較深的宗教知識(shí),而且對(duì)中國傳統(tǒng)文化儒家思想也當(dāng)有較好的了解,從而使他具備了書寫漢文伊斯蘭教碑銘的文化條件。 伊斯蘭教自唐入華以后,迄明中葉止,不甚盛行于世。推究其因,主要在于伊斯蘭教人本身不重視對(duì)教義的學(xué)習(xí)、研究、宣傳所致。《古蘭經(jīng)》、“圣訓(xùn)”等從無漢譯,只憑家庭父子口傳心受。因此,不僅教外人不了解,即使教內(nèi)人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沿其跡,不得其真性”;“雖其先守教之家,今亦掉臂而叛去”(萬歷三十七年《重修清凈寺碑記》)。面對(duì)這種宗教信仰動(dòng)搖的現(xiàn)象,一些宗教學(xué)者會(huì)感到學(xué)習(xí)、研究和宣傳教義的必要性,從而開始了這方面的實(shí)踐活動(dòng)。《來復(fù)銘》便是這種實(shí)踐活動(dòng)的一篇代表作。 二 我們?cè)谏厦嬉呀?jīng)介紹了《來復(fù)銘》碑文的作者,下面介紹它的主要精神。《來復(fù)銘》全文一百五十五個(gè)字,原文“共九行,足行十九字,字大如拳,書法不甚佳”。現(xiàn)抄錄如下: 無極太極,兩儀五行,元于無聲,始于無形。皇降衰彝,錫命吾人,與生俱生,與形俱形。仁人合道,理器相成。圣愚異稟,予賦維均。是故心為郛廓,性為形體。繇太虛,有天之名;繇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存心與性,以事其天;慎修厥身,以俟此命;主敬窮理,以養(yǎng)此性;戒慎恐懼,以體此道;不愧屋漏,以事此心。斯與造物為徒矣。不爾,天顧畀之,人顧棄之[4],其將何以復(fù)帝者之命? 《來復(fù)銘》的全文只有如此一點(diǎn)。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銘文通篇談儒,字面上未涉伊斯蘭教一詞一句,這可能是長期以來它未能引起我國伊斯蘭教學(xué)界中人重視的原因之一吧?但這恰恰是其主要特色及應(yīng)著意強(qiáng)調(diào)和深入研究之處。從中我們可以品味出我國早期回族穆斯林學(xué)者是如何摸索探求“回回附儒以行”的道路,如何自覺接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duì)伊斯蘭教之影響和滲透的。 還是讓我們就銘文進(jìn)行一些具體的分析吧。 《來復(fù)銘》全文可分為兩大段:從“無極”句至“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為第一段,主要綜述作者對(duì)我國古代哲學(xué)方面的一些基本概念(天、道、理、心、性)的總看法;從“存心與性”至最后為第二段,講的是認(rèn)識(shí)論和道德修養(yǎng)方法。中間有一段話,給“天”、“道”、“心”、“性”下了明確的定義:“繇太虛,有天之名;繇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這段話承上啟下,既是上文的概括,又是下文的起因,在文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自明。然而這段很重要的話,卻偏偏不是銘文作者自創(chuàng),而是宋代著名唯物主義理學(xué)家張載所著《正蒙.太和篇》中的一段原文,代表了張載的基本哲學(xué)思想。因此,為了準(zhǔn)確地把握《來復(fù)銘》的思想內(nèi)容,有必要花費(fèi)一些筆墨,先將張載的這段話及其基本哲學(xué)思想搞清,進(jìn)而找出《來復(fù)銘》吸收張載思想的具體內(nèi)容、程度和原因。 (一) 在宇宙觀方面,借助張載的觀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造物主的實(shí)有。 “繇太虛,有天之名;繇氣化,有道之名”。這是張載的宇宙觀,是他為對(duì)抗魏、晉以來“以無為本”或“以心為本”的唯心主義本體論,提出的以氣為本的唯物主義元?dú)獗倔w論。 什么是天?天是虛無的,還是實(shí)有的?為了回答這個(gè)問題,張載提出了一個(gè)表示物質(zhì)特性的范疇“太虛”。“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太和篇》)太虛是一種無形的、極細(xì)致的物質(zhì)“氣”。它不是人們的眼、耳等感覺器官可以直接掌握的,但它卻是實(shí)有的。它的存在,絕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世界的本原只有一個(gè),就是太虛,就是氣。氣是一種運(yùn)動(dòng)著的物質(zhì),總是在不斷地變化著:“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yáng)未嘗止息……此虛實(shí)動(dòng)靜之機(jī),陰陽剛?cè)嶂肌!?《太和篇》)在張載看來,世界上的一切現(xiàn)象,包括萬物的生滅成毀、人的生死存亡,都是氣的聚散變化:“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太和篇》)氣聚時(shí),就是有形可見(離明得施)的東西;氣散時(shí),就是無形而不可見的東西。氣聚是暫時(shí)的,所以叫做“客”;氣散后又怎能斷然說氣不存在了呢? 因此,張載認(rèn)為,世界萬物是客觀存在,只有明(明顯)和幽(隱蔽)的區(qū)別,而沒有有和無的區(qū)別,更不能將客觀存在的萬物說成是出于虛無。他說:“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shí)所謂有無混一之常。”(《太和篇》)如果在理論上主張有生于無,就等于承認(rèn)在有之前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現(xiàn)實(shí)世界是由不存在的“無”中生出的,這就必然把物質(zhì)看作是第二性的,而把非物質(zhì)的虛無看做是第一性的,精神性的本體(體)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萬物(用)就必然隔絕,這就叫“體用殊絕”。這對(duì)于道教“有生于無”的唯心主義本體論是有力的駁斥。 張載對(duì)于佛教以心為本的唯心主義本體論也進(jìn)行了抨擊:“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太和篇》)如果將天地萬物看作主觀意識(shí)所顯現(xiàn)的假象,就會(huì)將萬物與太虛割開,以虛空本性為真實(shí),以天地萬物為虛妄,把天人割裂開來,人不依靠大自然而存在,人對(duì)大自然也不起作用,就會(huì)陷入佛教所謂“見病”的錯(cuò)誤。 在張載看來,“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太和篇》)氣的聚合與分散,如同冰的凝固和融解。冰雖融成水,但作為物質(zhì)它依然還存在;氣雖散于太虛,它也同樣是客觀存在的物質(zhì)。懂得太虛就是氣的道理,就會(huì)明白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虛無。據(jù)此,張載明確地給“天”下了一個(gè)定義:“繇太虛,有天之名。”天并不是虛無,而是實(shí)有;并不是精神性的,而是物質(zhì)性的。氣有清有濁,太虛是氣之清者,天就是由這種清的氣太虛構(gòu)成的。 對(duì)于“道”的看法,張載與唯心主義本體論者也根本不同。他認(rèn)為,“道”并不是脫離一切物質(zhì)而單獨(dú)存在的精神性創(chuàng)世本體。世界的本原只有一個(gè),那就是太虛、氣。人的構(gòu)成與萬物的構(gòu)成,都源于氣的變化。“游氣紛擾,合而成質(zhì)者,生人物之散殊。”(《太和篇》)氣的變化,張載稱之為“氣化”,而這種氣化過程,張載就稱之為“道”。這就是“繇氣化,有道之名”。在這里,道有規(guī)律的意思,即是指氣運(yùn)行變化的自然規(guī)律。“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張子語錄》)“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動(dòng)物篇》)他是主張道不離氣的:道不離氣而單獨(dú)存在,道就是氣化的過程,道就是氣的道。氣是物質(zhì),氣化是物質(zhì)的運(yùn)動(dòng)變化的過程,那么道正是指物質(zhì)運(yùn)動(dòng)變化的自然規(guī)律。這是一種很重要的唯物主義本體論的哲學(xué)體系。 由于歷史的局限,張載的樸素唯物主義不可能全面說明世界發(fā)展變化的復(fù)雜性、多樣性。他說:“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于氣而已。”“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cè)為神。”(《神化篇》)張載把高遠(yuǎn)莫測(cè)、精致微妙而不可說明的某些現(xiàn)象,叫作“神”,說神是“天德”,是天之本體。他認(rèn)為,清的氣是太虛,它毫無滯礙,所以叫它“神”(無礙故神);濁的氣有滯礙,滯礙則成為有形的、具體之物(濁則礙,礙則形)。也就是說,世界雖都是由氣構(gòu)成,但是氣有清濁,“清極則神”,“萬物形色,神之糟粕”,“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太和篇》)他把神的地位看得超出萬物之上,認(rèn)為神具有“虛明照鑒”的作用;萬物都是神化的糟粕。顯然,這里的“神”已不再是指物質(zhì)的神妙的變化,而是一種精神作用了。既然“清極而神”,精神是至清的氣,當(dāng)然是永存不滅的,這就給有神論的靈魂不死說留下了后路。這是張載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不徹底之處。 現(xiàn)在讓我們先回到對(duì)《來復(fù)銘》的分析上來,看一看它的作者 —— 一位世襲的伊斯蘭教掌教,為什么要引用張載關(guān)于“天”、“道”的定義?具有宗教世界觀的人,在宣傳自己的世界觀時(shí),引用的卻是唯物主義者的觀點(diǎn),這不是很發(fā)人沉思么? 從《來復(fù)銘》全文來看,無論從其篇幅的大小,使用的概念,寫作的結(jié)構(gòu)上看,都很象周敦頤的那篇《太極圖說》。但如細(xì)加分析,便知二者之不同。 《太極圖說》在南宋以后,逐漸成為宋明理學(xué)的經(jīng)典文獻(xiàn)。所謂宋明理學(xué)的正宗,是程朱理學(xué)。按照程朱理學(xué)的觀點(diǎn),宇宙的本原是“理”,又稱“太極”。他們認(rèn)為,萬物統(tǒng)一于金、木、水、火、土這“五行”,五行統(tǒng)一于陰陽二氣(兩儀),陰陽統(tǒng)一于太極,無形而有理的太極是萬物之本。這就是《太極圖說》中的那句話:“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朱熹把話講得更直截: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朱文公文集》卷70) 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朱子語類》卷1) 可見,“理”或“太極”是程朱理學(xué)的最高范疇,它不生不滅,無始無終,先天先地,生天地萬物,是一種精神性的本體,屬于黑格爾的絕對(duì)觀念一類的范疇。追根溯源,《太極圖說》所搭起來的這種程朱理學(xué)宇宙起源的架子,可以說是從道教“有生于無”那里來的。 《來復(fù)銘》并未取此說。它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講:“無極太極,兩儀五行,元于無聲,始于無形”。這是表明,無極太極同兩儀五行一樣,都是有始的,不是無限的,因此它不是萬物的本原。“道”和“理”也都不是創(chuàng)造萬物的本原:“仁人合道,理器相成”。道是由“仁”與人相合的產(chǎn)物,道是人的道,道離不開人。理也非先天先地,而是與器(物)相輔相成的。理不離器而獨(dú)存。在《來復(fù)銘》的作者看來,在無極太極之前,有一個(gè)最高最強(qiáng)的存在,“無聲”、“無形”的創(chuàng)世者,這就是那位“降衰彝”并“錫命吾人”的“皇”,也就是吾人應(yīng)歸復(fù)其命的“帝”。無極太極、兩儀五行,都是以這個(gè)皇為始;人類社會(huì)的等級(jí)次第(衰),典章制度(彝),都由這個(gè)皇所降;甚至人們的性命,也是由這個(gè)皇所賜予。皇者,天也。天者,太虛也。“繇太虛,有天之名”。太虛者,實(shí)有者也。張載所謂“太虛”,不是一種無聲無形、耳目不可直接掌握而又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實(shí)有本體么?《來復(fù)銘》中所講的“皇”,也正是這樣的實(shí)有。 但是,從《來復(fù)銘》的字里行間又可以發(fā)現(xiàn),它所講的“皇”與張載所講的“太虛”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張載講太虛,強(qiáng)調(diào)“太虛即氣”,太虛是物質(zhì)性的氣。《來復(fù)銘》講皇,則強(qiáng)調(diào)它是“天”,是人格化的“帝”。“降衰彝”的“降”字,“錫命吾人”的“錫”字,“予賦維均”的“予”字,都向人們表明,這個(gè)皇是有意志、有知覺、有能力、有目的的。它造就了人類,造就了人類社會(huì),并按照自己的意志降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彝倫典章給人,人們只能俯首貼耳地順從它的安排。這種超自然體中的人格化的最高主宰,正是典型的宗教觀念——神。 現(xiàn)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來復(fù)銘》引用張載關(guān)于太虛的概念,并不是為了強(qiáng)調(diào)萬物本原的物質(zhì)性,而僅僅是借助于這個(gè)概念,強(qiáng)調(diào)它所講的那位宇宙主宰的實(shí)有性。它為人們塑造的是一個(gè)無形無聲、無始無終,卻又有知覺、有能力的人格化的造物主;這位造物主的存在,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而非虛無縹緲的。 《來復(fù)銘》在這里正是宣揚(yáng)了伊斯蘭教的一個(gè)最基本的教義——認(rèn)主獨(dú)一。 伊斯蘭教的教義,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是信仰;二是行為。認(rèn)主獨(dú)一,是伊斯蘭教信仰的基礎(chǔ)。認(rèn)主獨(dú)一的阿拉伯文音譯是“討希德”,意為信仰真主的獨(dú)一無偶。就是說,要通過對(duì)真主的本體、創(chuàng)造及其為萬物之歸宿等問題的研究而肯定真主的獨(dú)一。《古蘭經(jīng)》第112章《忠誠(以赫拉斯)》,又稱《篤信章》或《認(rèn)一章》(音譯為“討希德章”)。全章僅4節(jié),但據(jù)傳穆罕默德曾說,《篤信章》居《古蘭經(jīng)》三分之一的地位。為什么這短短的4節(jié)經(jīng)文,地位卻如此重要呢?原因就在于這一章不講其他,專講認(rèn)主。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你說:他是真主,是獨(dú)一的主;真主是萬物所仰賴的;他沒有生產(chǎn),也沒有被生產(chǎn);沒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敵。1 《來復(fù)銘》中所講的“皇”,正是伊斯蘭教所信仰的獨(dú)一無偶的真主安拉。 按照伊斯蘭教哲學(xué),將可知之物分為三大類:本來當(dāng)無的、本來當(dāng)有的、本來可有的。所謂“本來當(dāng)無的”,就是其本體自然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會(huì)有的事物。所謂“本來當(dāng)有的”,就是其本體自然存在的,而且從根本上說必然存在,永恒存在,不能不有的。所謂“本來可有的”,是指介乎當(dāng)有和當(dāng)無者之間,其本體原不自然存在,將來也不會(huì)自然消滅,而是因被創(chuàng)造而存在,因無繼續(xù)存在的原因而歸于消滅的,是依著一定的原因而可有可無的。 伊斯蘭教否認(rèn)“有生于無”的觀點(diǎn)。他們認(rèn)為: 凡本來當(dāng)無者,不可變?yōu)椤坝小钡摹R驗(yàn)椤盁o”是本來當(dāng)無者的本質(zhì)所原有的常德,倘若可以變?yōu)椤坝小钡模闶欠穸ㄆ浔举|(zhì)所原有的常德,結(jié)果顯然是否定其本質(zhì)。所以本來當(dāng)無者,現(xiàn)在不有,將來不能有,從前也斷乎不曾有,甚至理性也不能相象其有的本質(zhì),猶如我們所指示的一樣。總之,意識(shí)外沒有這種事物,意識(shí)內(nèi)也沒有這種事物。2 伊斯蘭教認(rèn)為,宇宙間的天地萬物以及人類,都屬于“本來可有者”。他們無因不有,無因不無,都是有始的。那么,始于何處呢?既然“無”不是“有”的本質(zhì),無不能生有,那么萬有的發(fā)生必定都始于“有”,即宇宙萬物及人類統(tǒng)統(tǒng)都需要一個(gè)實(shí)有的創(chuàng)造者。這個(gè)創(chuàng)造者,既不是整個(gè)宇宙萬物的本體,也不是宇宙萬物中的任何一物;它不屬于本來可有的宇宙萬物,而是在宇宙萬物本質(zhì)之外的、獨(dú)一無偶的“本來當(dāng)有者”。這個(gè)本來當(dāng)有者,就是安拉。在伊斯蘭教看來,宇宙萬物這些“本來可有者”的實(shí)有性,便是“本來當(dāng)有者”安拉實(shí)有的證明。“因?yàn)楸緛砜捎姓撸荒茏杂校亟琛小诒緛懋?dāng)有者”3伊斯蘭教是非常強(qiáng)調(diào)安拉的實(shí)有性的。 凡在大地上的,都要?dú)纾晃ㄓ心愕闹鞯谋倔w,具有尊嚴(yán)與大德,將永恒存在。4 惟真主的存在是當(dāng)然的,惟真主的德性是完美的,惟真主是造物者。5 伊斯蘭教所強(qiáng)調(diào)的真主安拉這種實(shí)有性,正是《來復(fù)銘》作者直接引用張載觀點(diǎn)的重要 原因。張載關(guān)于否認(rèn)有生于無、承認(rèn)世界本原太虛實(shí)有的觀點(diǎn),關(guān)于“清極而神”的觀點(diǎn),正好可以為《來復(fù)銘》作者接過來,作為強(qiáng)調(diào)他信仰的造物主安拉確為實(shí)有的論據(jù)。 當(dāng)然,同其他任何宗教一樣,作為伊斯蘭教宗教觀念的最高主宰神安拉,盡管被說成是全知全能、至慈至仁的人格化的實(shí)有,但歸根結(jié)蒂,它仍然是一種精神性的本體,而絕非是物質(zhì)性的實(shí)體。因此,《來復(fù)銘》中所講的造物主“皇”,與張載講的“太虛”又是根本不同的。 世界是創(chuàng)造的,還是從來就有的?精神與自然界二者究竟誰是本原?對(duì)這個(gè)問題的不同回答,使哲學(xué)家們分成了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大陣營。恩格斯指出:“凡是斷定精神對(duì)自然界說來是本原的,從而歸根到底以某種方式承認(rèn)創(chuàng)世說的人(在哲學(xué)家那里,例如黑格爾那里,創(chuàng)世說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還要混亂而荒唐的形式),組成唯心主義陣營。凡是認(rèn)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于唯物主義的各種學(xué)派”[5]。《來復(fù)銘》中盡管引用了張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某些概念,但并不能以此推出它的宇宙觀也是唯物主義元?dú)獗倔w論的結(jié)論;相反,它所反映出來的,恰恰是“歸根到底以某種方式承認(rèn)創(chuàng)世說”的唯心主義宗教宇宙觀。 (二) 在人性論和認(rèn)識(shí)論方面,基本上吸收了張載的觀點(diǎn)。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這是張載力圖用唯物主義的觀點(diǎn)去說明人性問題。 我國古代不少唯物論者,都力圖用物質(zhì)的原因、唯物主義的觀點(diǎn)去解釋人性問題。漢代王充是這樣,南北朝范縝也是這樣。但是由于科學(xué)知識(shí),特別是生理學(xué)知識(shí)的貧乏,他們不了解人的思維能力是大腦活動(dòng)的結(jié)果,往往用生理的、身體的原因去說明人的善惡智愚、貧賤富貴。更由于他們階級(jí)的局限,不了解人的社會(huì)性,不明白認(rèn)識(shí)來源于社會(huì)實(shí)踐的道理,不懂得社會(huì)上“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jí)社會(huì)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jí)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jí)的人性”[6]。他們講的都是自然的人,生理的人的人性,而不講社會(huì)關(guān)系總和的人的人性。因此,他們雖然力圖用物質(zhì)的原因、唯物主義的觀點(diǎn)去解決人性問題,但總是事與愿違,到頭來只能得到唯心主義的結(jié)論。張載也不例外,他同樣是沿著這條貌似唯物主義而實(shí)質(zhì)上是唯心主義的路線發(fā)展,形成自己唯心主義人性論的。 張載的人性論,主要有以下兩個(gè)方面的內(nèi)容: 人性永存的觀點(diǎn)。張載從其元?dú)獗倔w論出發(fā),認(rèn)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物質(zhì)“氣”構(gòu)成的;由于氣有清有濁,所以產(chǎn)生了萬殊的人和物。如同天得氣之清者,地得氣之濁者一樣,人得氣之清者,物得氣之濁者。在人之中,得氣之最清者為圣人,得氣之濁者為一般人,得氣之最濁者為惡人。性是人的本質(zhì),它是由太虛之清氣經(jīng)過氣化過程與一般的氣相配合而產(chǎn)生的,這就叫“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是物質(zhì),它只有聚散,沒有生滅;“聚亦吾體,散亦吾體”。(《太和篇》)氣聚而成為人之形體,固然是存在的;人死后氣散入太空,但它依然是存在的。這是講物質(zhì)不滅,是正確的。但他接下來便說:“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太和篇》)認(rèn)為人性也是氣,不隨人的生死而存亡,即人性不依賴于人的形體而獨(dú)立存在,人生以前有此性,人死后此性依然存在。顯然,這種人死性存的觀點(diǎn)是唯心主義的。這是張載繼承了我國古代唯物主義哲學(xué)家用生理現(xiàn)象去說明人性的錯(cuò)誤觀點(diǎn)而得出的錯(cuò)誤結(jié)論。 “天地之性”和“氣質(zhì)之性”的觀點(diǎn)。張載提出:“形而后有氣質(zhì)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誠明篇》)這里,他把性分為兩種,一種是“氣質(zhì)之性”,另一種是“天地之性”。每個(gè)人在其有了生命而成為一具體存在后,則必有其具體化之條件,此種條件稱為“氣質(zhì)”。而“氣質(zhì)”本身具有的一種性,就是“氣質(zhì)之性”。這種氣質(zhì)之性是與每個(gè)人的生理?xiàng)l件、身體特點(diǎn)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的。由于人們的生理?xiàng)l件、身體特點(diǎn)千差萬別,所以人們所稟的氣質(zhì)之性也就各不相同。氣質(zhì)之性是后天的,有善有惡的。在人未成形之前,早已具有“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出于氣,有天地之氣,便有天地之性。“天性,乾坤、陰陽也”,“性即天道也”。(《乾稱篇》)天地之性是人與萬物共同的本性。“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誠明篇》)不僅我有此性,別人也有此性;不僅人有此性,任何一物都有此性。“性于人無不善”。(《誠明篇》)天地之性,既是天地之氣固有的,是天道,當(dāng)然是先天的、至善的、完美無缺的。氣質(zhì)之性源出于天地之性,但它是惡的根源,障蔽了天地之性的正常發(fā)展,所以說“故氣質(zhì)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誠明篇》)即君子并不將氣質(zhì)之性算作是真正的人性,天地之性才是真正的人性。氣質(zhì)惡的人,因其天地之性被障蔽,所以為惡。人們?nèi)缒軟_破氣質(zhì)之限制,克服了氣質(zhì)之性,省悟并歸于秉自天道之“性”,就叫做“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這樣,張載的人性論終于背離了自己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從而陷入了徹底的唯心主義。 受這種人性論的影響,張載的認(rèn)識(shí)論也走上了唯心主義的歧途。 張載給“心”這個(gè)哲學(xué)范疇下了一個(gè)新的定義:“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就是說,人的本性,再加上知覺的作用,就會(huì)產(chǎn)生人的心理活動(dòng),這就叫“心”。可知,張載所謂“心”,既具有知覺的性質(zhì),是人們主觀認(rèn)識(shí)世界的能力;同時(shí)又具有“性”的性質(zhì),受所具人性的制約。 人們的“心”既然受“性”的制約,而性又分為氣質(zhì)之性和天地之性兩種,那么人的知識(shí)也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見聞之知”,一種是“德性所知”。張載說:“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大心篇》)見聞之知,是靠“物交”,即通過耳目等感覺器官感受外物而獲得的;德性所知與見聞之知不同,它不靠耳目的見聞去獲得。“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誠明篇》)耳聞目見的是“聞見小知”,是淺薄的,不足道的;德性所知,是天德良知,誠明所知,是先天的,從天地之性稟賦得來的,是明曉“天道”(天的根本法則)的良知、真知,這才是最高深的知識(shí),最根本的道理。 什么人具有德性所知呢?張載說:“圣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圣人“有天德,然后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天道篇》);圣人“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神化篇》)。圣人周知萬物,可以把天地間的根本道理一言而盡,甚至達(dá)到窮神知化的程度,這是因?yàn)樗麄兩衲芡ㄌ欤c天為一,具有天德的緣故。 那么,人們是否可以象圣人那樣也具有德性所知呢?張載認(rèn)為是可以的,他相信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可知的。辦法就是要進(jìn)行“成德之學(xué)”。張載說:“如氣質(zhì)惡者,學(xué)即能移……但學(xué)至于成性,則氣無由勝。”(《張子全書》卷五《理窟.氣質(zhì)篇》)學(xué)習(xí),可以使人越過氣質(zhì)之限制,移去氣質(zhì)之惡性,恢復(fù)天地之性。但是,這種“學(xué)”要靠自覺。如果不是自覺地學(xué),僅停留在無理性基礎(chǔ)的信仰上,是不能稱作好學(xué)的。所以張載說:“篤信不好學(xué),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中正篇》)僅有虔誠的信仰而不進(jìn)行理性的“成德之學(xué)”,充其量不過是個(gè)善人信士而已,是不能成為圣人的。張載所謂的“學(xué)”,有“窮理”的意思:“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誠明篇》)若要實(shí)現(xiàn)“盡性”,就要依恃“窮理”的活動(dòng);反之,如能達(dá)到“盡性”的程度,也必能作到“窮理”。但是張載所講的“學(xué)”,主要講“自悟”和“盡心”。“學(xué)貴自悟,守舊無功”;“為學(xué)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zhì);不爾,卒無所發(fā)明,不得見圣人之奧”[7]。所謂“自悟”、“發(fā)明”云云,都是就理性的覺醒而言。人如能自覺進(jìn)行內(nèi)心自省的功夫,變化自已的氣質(zhì),恢復(fù)天地之性,就可以心如朗照,周知萬物之本;否則,仍不能洞見圣人之奧妙。“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圣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大心篇》)不必借助于耳聞目見,更不為聞見所束縛,只憑主觀的直覺的“盡心”,就可以象圣人那樣“知性知天”。讀經(jīng)雖也屬重要的學(xué)習(xí):“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8]但是與這種“自悟”、“盡心”的修行功夫相比,讀經(jīng)便不是主要的了。道德理性的顯用,天德良知的獲得,不僅不源于耳聞目見的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也不必依賴經(jīng)籍。所以張載說:“凡經(jīng)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識(shí)字者,何害為善?”[9] 基于這種典型的唯心主義認(rèn)識(shí)論,張載大力宣揚(yáng)安于天命的思想。他認(rèn)為,人一生的命運(yùn),無論富貴貧賤,都是由乾父坤母即天地所安排的。“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西銘》)把人能享受富貴福澤,說成是上天的照顧;遭逢貧賤苦難,也是上天給予鍛煉成長的機(jī)會(huì)。要人們順天安命,生時(shí)規(guī)規(guī)矩矩,順天行事;死時(shí)服服帖帖,安寧而歸。至此,張載已滑入了唯心主義的宿命論之中。 《來復(fù)銘》基本上吸收了張載的人性論和認(rèn)識(shí)論觀點(diǎn),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大談心性問題。 在人性論方面,《來復(fù)銘》直接引用了張載給“性”下的定義:“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這表明,第一,性既然是“合虛與氣”而有,那么,氣為實(shí)有,為永恒常存者,性也必然是實(shí)有的、永恒長存的,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也不隨人的生死而存亡;第二,氣有清濁,故性也必有二端,如張載所謂的“氣質(zhì)之性”和“天地之性”。《來復(fù)銘》稱“圣愚異稟,予賦維均”。就是說,造物主給予人們的天性(賦)肯定都是均等的、相同的,都是先天至善、完美無缺的;但是,由于人們后天所稟受的氣質(zhì)不同,所以產(chǎn)生了圣和愚的差別。 《來復(fù)銘》中還有一句話:“仁人合道”。查“仁”一詞,在孔子以前就已得到廣泛的應(yīng)用。據(jù)《周易.說卦》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將“仁”作為立人道的主要因素。故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卷八上說:“仁,親也。從人,從二(臣鉉等曰,仁者兼愛,故從二)。如鄰切。”從孔子開始,正式將“仁”作為一種哲學(xué)范疇提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fù)禮為仁。一日克己復(fù)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來復(fù)銘》中的“仁”,正可作“克己復(fù)禮”解。“仁人合道”,就是說,人如果能自覺地約檢自己,時(shí)時(shí)處處警誡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反于禮中,作到了“仁”,就合于人道了。克己復(fù)禮而成仁的過程,就是“戒慎恐懼,以體此道”的過程,就是存性養(yǎng)性、反觀自省的過程。而這種過程,不正是張載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嗎? 在認(rèn)識(shí)論方面,《來復(fù)銘》也承襲了張載的觀點(diǎn)。它直接引用“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的定義,就意味著它同意將人的認(rèn)識(shí)分為“見聞之知”和“德性所知”兩類。“降衰彝”并“錫命吾人”的造物主“皇”,既是無聲無形的,當(dāng)然是“不萌于見聞”的德性所知。如何充分發(fā)揮“心”的知覺作用,認(rèn)識(shí)造物主,進(jìn)而“復(fù)帝者之命”,正是《來復(fù)銘》所要闡述的主旨所在。 在《來復(fù)銘》的作者看來,造物主不僅是應(yīng)該認(rèn)識(shí)的,而且是可以認(rèn)識(shí)的。認(rèn)識(shí)的方法就是要象圣人那樣,“與造物為徒”。“徒”者,同一類之謂也。“與造物為徒”,就是張載所謂的“與天為一”之意。只要作到“與造物為徒”,就會(huì)象圣人那樣“具備天德”,縱使一字不識(shí),也能“窮神知化”,認(rèn)識(shí)造物主,將天地之道一言而盡。為此,《來復(fù)銘》開列了一整套“自悟”、“盡心”的方法: 存心與性,以事其天;慎修厥身,以俟此命;主敬窮理,以養(yǎng)此性;戒慎恐懼,以體此道;不愧屋漏,以事此心。 這些存心性、慎修身、主敬、窮理等手段,目的都是為改變氣質(zhì),恢復(fù)天性,體會(huì)正道,從而認(rèn)主。而這些修養(yǎng)功夫,須自覺地進(jìn)行。最后一句“不愧屋漏”,語出《詩經(jīng).大雅.抑》“不愧于屋漏”句。屋漏,指“室內(nèi)西北隅安藏神主,人所不見之處也。”(《中文大辭典.尸部》)在人所不見之處,也能盡心功修,做到無愧,這當(dāng)然是在強(qiáng)調(diào)人們進(jìn)行道德修養(yǎng)的自覺性。凡是這樣去做的人,就是“斯與造物為徒矣”。“不爾,天顧畀之,人顧棄之,其將何以復(fù)帝者之命?”否則,不自覺地修身養(yǎng)性,只會(huì)遭到上天的拋棄,這樣的人將以什么去歸主復(fù)命呢?《來復(fù)銘》以“復(fù)命”句作結(jié),將這篇以四言為主的韻體銘文的思想推向高潮,便戛然而止,從而點(diǎn)明了銘文的“來復(fù)”主題,最終完成了它的神秘主義的認(rèn)識(shí)論。這種認(rèn)識(shí)論及前述人性論,包括其中表現(xiàn)出來的順天安命思想,確實(shí)與張載的觀點(diǎn)是合拍的,毫無二致的。 《來復(fù)銘》的這種思想,是符合伊斯蘭教關(guān)于行為方面的教義的。 在伊斯蘭教的歷史上,曾出現(xiàn)過宿命論與自由論的爭論。宿命論者主張前定說;自由論者否認(rèn)前定說,主張意志自由說。公元9世紀(jì),以伊瑪目艾什耳里為代表的正統(tǒng)派穆斯林,在研究古代希臘哲學(xué)的基礎(chǔ)上,建立了自己的伊斯蘭經(jīng)學(xué)“凱拉目”。他們傳播著這樣一段“圣訓(xùn)”: 我的教民中,有兩等人已經(jīng)喪失了正教的福分:宿命派與自由派[10]。 實(shí)際上,“凱拉目”教義中,既吸收了前定說,也吸收了意志自由說,將這兩種相反的信條調(diào)和到一起,提出了前定與自由合一論。這種正統(tǒng)派伊斯蘭經(jīng)學(xué)認(rèn)為,有兩條原理是人類幸福的基礎(chǔ)和人類行為的綱領(lǐng):“(一)人類借其意志與能力以謀其幸福的媒介。(二)真主的能力,為萬物的歸宿,且有妨礙人類執(zhí)行意志的作用,對(duì)于人謀所不及的事,除真主外任何物都不能襄助人類”。[11]這就是說,第一,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由人的營謀與自由發(fā)出的,真主安拉的全知全能并沒有奪去人類自由的作用,它賦予人類的生存里也不含有對(duì)人類行為的強(qiáng)迫。人類為善為智,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人類為惡為愚,也要由自己去負(fù)責(zé)。因?yàn)檎嬷髟谠旎f物時(shí),使萬物間都互有區(qū)別,而人與其余一切動(dòng)物的區(qū)別就在于:人類是有思想的,是依其思想而自由行為的。第二,前定法則也是存在的。人類是真主造化的,人的本性是真主稟賦的。真主是全知全能的,他的知覺貫徹一切,知道人類將來要自由地做什么事,知道某種行為在某時(shí)發(fā)生;這種行為是善的,將受善報(bào),那種行為是惡的,將受惡報(bào)。 這種伊斯蘭經(jīng)學(xué)認(rèn)為,真主所賦予人的本性是善的,是應(yīng)當(dāng)謹(jǐn)守的;但是,由于后天的原因,受耳聞目見的蒙蔽,變了心,所以就變了性。 你應(yīng)當(dāng)趨向正教,[并謹(jǐn)守]真主所賦予人的本性。[12] 每一個(gè)人,生來都有向善的本能,后來他的父親母親才使他變成猶太教徒,或基督教徒,或火祆教徒。[13] 你們聽著,人體內(nèi)有一塊肉,當(dāng)此肉善時(shí)全身皆善,它惡時(shí)全身皆惡,它就是心。(《布哈里圣訓(xùn)實(shí)錄精華》[埃及]穆斯塔發(fā).本.穆罕默德艾瑪熱編,寶文安、買買提.賽來譯,第23頁。) 因此,人們應(yīng)該謹(jǐn)守天命五功,加強(qiáng)心性的修養(yǎng)。“有一般人因具有精確的學(xué)問,又能不斷的作精神的鍛煉,所以曾達(dá)到心君泰然,惑疑云散的境地。”[14]穆罕默德就是這樣的圣人。他雖目不識(shí)丁,但因堅(jiān)守伊斯蘭教信仰,又注意理性的修養(yǎng),終于享受到真主放射在其心中光輝的“特典”,從而心如朗照,洞察天地萬物。圣人可以作到,其他人也應(yīng)能作到。因?yàn)椤叭巳说谋倔w都有下列的三種尊榮:(一)受造于真主;(二)同屬人類,毫無差別;(三)具有同樣的本能,都可以達(dá)到真主所為人類預(yù)備之完美的最高等級(jí)”。[15] 總之,正統(tǒng)派伊斯蘭經(jīng)學(xué)認(rèn)為世界上沒有不可知的事物,只有尚未知的事物。即使萬物的本質(zhì),真主的本體,也都是可知的。但是,一般的人還不能知,只有始終信主、拜主而又有理性修養(yǎng)的“圣人”才有資格發(fā)見真主的本體。因此,人們應(yīng)該注重自己內(nèi)心的修養(yǎng),謹(jǐn)守天命五功,勤修現(xiàn)世的完善,以獲來世的善報(bào)。這樣,才能取得真主的喜悅,才能歸真復(fù)命。 《來復(fù)銘》宣傳的思想,不正是這種正統(tǒng)派伊斯蘭經(jīng)學(xué)的教義嗎?它名為“來復(fù)”,也正表明它是一篇宣傳伊斯蘭教義的典型作品。 按伊斯蘭教“五功”中的禮功,分為“一日五禮”、“七日一聚禮”、“一年兩會(huì)禮”三種。每日的五番“乃瑪孜”,可在任何一清潔的處所進(jìn)行;但七日一次的聚禮,一年兩次的會(huì)禮,則必須在禮拜寺中舉行。中國伊斯蘭教對(duì)主麻日的聚禮是很重視的。他們認(rèn)為,每日五番“乃瑪孜”,失而可補(bǔ);每周一次的主麻日聚禮失而不可補(bǔ)。聚禮意義重大。劉智在其所著《禮拜條例》中說:“天地之?dāng)?shù),七日來復(fù)。吾人七日一聚禮焉。蓋以省滌七日之衍,又以征來復(fù)之義也。”為什么這樣說呢?因?yàn)樵谝了固m教看來,天體是按土、日、月、火、水、木、金這七星周而復(fù)始運(yùn)行的,故七日為一周。在這七日中,金曜日(即星期五,伊斯蘭教稱主麻日)最貴重:人于這一天行善,善功百倍;犯過失,過亦百倍。所以,在這一天舉行穆斯林的集體聚禮,斂眾歸一,既可省滌七日當(dāng)中每個(gè)人所犯過失,又可以使大家都能斂聚天性,以歸真主,用以報(bào)答真主安拉的“化成之恩”。濟(jì)南清真南大寺樹立的這塊《來復(fù)銘》碑,以“來復(fù)”為名,以“復(fù)帝者之命”作結(jié),不正是在向人們強(qiáng)調(diào)來禮拜寺參加這種聚禮的重要性嗎? 總而言之,伊斯蘭教“以認(rèn)主為宗旨,以敬事為功夫,以復(fù)命為究竟”(《建修胡太師祖佳城記》)。這正是《來復(fù)銘》全文闡述的思想,只不過是披上了一襲張載的“理”服罷了。 三《來復(fù)銘》的意義何在? 第一,《來復(fù)銘》撰刻于明嘉靖七年,其作者陳思是一位世襲的伊斯蘭教掌教,其內(nèi)容是用宋明理學(xué)家的語言簡明概括地闡述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這些就足以使它在中國伊斯蘭教史上占一席重要的地位。 查目前我們所見的中國伊斯蘭教漢文教義作品,公認(rèn)最早而又有影響的,一是張時(shí)中的《歸真總義》,脫稿于明崇禎十三年(1640);一是王岱輿的《正教真詮》,初次刻版于明崇禎十五年(1642)。此外,據(jù)白壽彝先生考,更早的伊斯蘭教漢文作品有四種:一是明天啟五年(1625)進(jìn)士張忻(字靜之)的《清真教考》,《天方至圣實(shí)錄》卷20收有崇禎甲戌(1634)張忻所作本書的自序,“這是現(xiàn)在可考的最早的伊斯蘭撰述的序”;[16]二是萬歷四十四年(1616)進(jìn)士詹應(yīng)鵬(字翀南)的《群書匯輯釋疑》,《天方至圣實(shí)錄》卷20收有詹應(yīng)鵬于崇禎丙子(1636)所作本書的跋語;三是《省迷真原》;四是《證主默解》。最后兩書,時(shí)間、作者、內(nèi)容均不詳,約當(dāng)與《正教真詮》相去不遠(yuǎn),是王岱輿時(shí)代的作品,王氏曾親眼目睹,并在其著作中給予過尖銳批評(píng)。[17]前四書均比《來復(fù)銘》晚:《歸真總義》晚112年,《正教真詮》晚114年,《清真教考.自序》晚106年,《群書匯輯釋疑.跋》晚108年。據(jù)此,說《來復(fù)銘》是迄今為止所能見到的伊斯蘭教穆斯林用漢文介紹教義的最早作品,是不算過分的。[18] 《來復(fù)銘》雖系碑文,但就其內(nèi)容而言,遠(yuǎn)非一般清真寺碑文可比。它既不象其它碑文那樣去敘述寺的修建時(shí)間、人物、過程,也沒有泛泛地概述那些關(guān)于穆罕默德如何“生而神靈”的伊斯蘭神話。它全文旨在簡明概括地介紹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來復(fù)銘》雖非書本而刊行于世,但作為掌教撰寫的教義作品而樹于禮拜寺中,不正是一種特殊的經(jīng)堂教育“讀本”么?查我國伊斯蘭教經(jīng)堂教育的創(chuàng)始人胡登洲生于嘉靖元年(1522),《來復(fù)銘》刻石成文時(shí),胡登洲僅為一七齡童。他創(chuàng)經(jīng)堂教育的時(shí)間,起碼要晚《來復(fù)銘》四分之一世紀(jì)。 如果說,唐代杜環(huán)所撰《經(jīng)行記》作為伊斯蘭教最早的華文記錄,而在中國伊斯蘭教史“應(yīng)該大書特書”(白壽彝語)的話;那么,《來復(fù)銘》作為掌教撰寫的最早漢文教義作品,在中國伊斯蘭教歷史上不同樣也是十分珍貴的嗎? 第二,中國伊斯蘭教史的研究方面,有許多方面有待加強(qiáng)。如:信奉伊斯蘭教的十個(gè)民族的信教史、西北地區(qū)門宦史、經(jīng)堂教育史等等,都體現(xiàn)著伊斯蘭教的中國特色,應(yīng)該深入挖掘資料,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研究。此外,還有體現(xiàn)中國伊斯蘭教特點(diǎn)的重要一環(huán),便是中國伊斯蘭教的哲學(xué)思想史。我國伊斯蘭教的宗教學(xué)者們,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努力,將伊斯蘭教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形成了一整套中國伊斯蘭教的哲學(xué)思想。這既是我國哲學(xué)史上的一份寶貴遺產(chǎn),也是世界伊斯蘭文化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那么,這種“附儒以行”的中國伊斯蘭教哲學(xué),究竟是怎樣一步步形成的?最初的結(jié)合始于何時(shí)?結(jié)合的程度如何?都是必須研究的。過去,人們通常講“回回附儒以行”始于馬注、劉智;后來,人們又講王岱輿的作品中也有儒家的色彩。現(xiàn)在,當(dāng)我們讀到《來復(fù)銘》時(shí),就會(huì)意識(shí)到這種“附儒以行”的嘗試早在明代中葉即已開始了。元代是伊斯蘭教大規(guī)模入華期,明代是回回民族正式形成期。在回族形成伊始,回族穆斯林便開始摸索如何用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說明伊斯蘭教義的道路,便開始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去豐富、發(fā)展、充實(shí)伊斯蘭教義的實(shí)踐了。《來復(fù)銘》就是中國文化與阿拉伯文化相互交流的最初結(jié)晶之一。《來復(fù)銘》所開的這種中阿文化交流的先河,被后來的王岱輿、馬注、劉智、馬德新諸公繼續(xù)開拓,終于形成了中國伊斯蘭教的一整套回回經(jīng)學(xué)思想。在那些著名的“漢克它卜”中表現(xiàn)出來的關(guān)于宇宙起源、心性、來復(fù)等思想,我們不是可以從《來復(fù)銘》中就看到其萌芽了么? 第三,在中國封建社會(huì)走下坡路的宋明之際,伴隨著中央集權(quán)政治制度的加強(qiáng),出現(xiàn)了一個(gè)各家思想大交流、大融合的局面。宋明理學(xué)就是當(dāng)時(shí)儒、道、佛三教合流的產(chǎn)物。《來復(fù)銘》的出現(xiàn)說明,在這場各家思想合流的過程中,伊斯蘭教學(xué)者也以其獨(dú)特的哲學(xué)思想?yún)⒓舆M(jìn)來,成為中國哲學(xué)思維發(fā)展的一個(gè)組成部分,從而豐富了中國哲學(xué)史和思想史的內(nèi)容。然而,歷來研究中國哲學(xué)史和中國思想史的專家學(xué)者們,在其長達(dá)數(shù)十萬、數(shù)百萬言的著作中,對(duì)中國伊斯蘭教學(xué)者們那套具有獨(dú)特風(fēng)格的哲學(xué)思想?yún)s未涉及一字一句,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令人感到遺憾的事情。隨著我國伊斯蘭學(xué)術(shù)研究的深入開展,特別是對(duì)《來復(fù)銘》等一類碑文及王岱輿、劉智等眾多中國回族穆斯林學(xué)者所撰漢文譯著的深入研究,我國哲學(xué)史和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這段空白,是該填補(bǔ)的時(shí)候了。 更多精彩評(píng)論,更多傳媒視點(diǎn),更多傳媒人風(fēng)采,盡在新浪財(cái)經(jīng)新評(píng)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cái)經(jīng)新評(píng)談頻道。 |
| 新浪首頁 > 財(cái)經(jīng)縱橫 > 經(jīng)濟(jì)時(shí)評(píng) > 馮今源 > 正文 |
|
| ||||
| 熱 點(diǎn) 專 題 | ||||
| ||||
|
|
新浪網(wǎng)財(cái)經(jīng)縱橫網(wǎng)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píng)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wù) | 聯(lián)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wǎng)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huì)員注冊(cè) | 產(chǎn)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