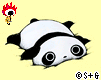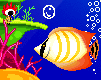| 現代社會中的個人權利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09日 14:25 中評網 | |||||||||
|
一、我們有多少權利? 我們身處的時代是一個權利訴求泛濫的時代。對比于一個世紀以前的人類,我們擁有更多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權,以及更多聞所未聞的權利伸張。如果像政治學耆宿張佛泉先生所言:“諸自由即諸權利”,則今天的社會應該可以說是一個自由呼聲最高、權利意識最強的社會。當然,權利意識及權利訴求并不等于實際存在的權利保障,所以權利訴求高漲并不
我們到底有多少“權利”已經醒來?又有多少“權利”依然沉睡呢?憲法中規定的基本人權大概是每個人最清楚意識到的基本權利,這包括:人身自由、居住遷徙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秘密通訊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直接以權利為名之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請愿訴愿權、參政權、國民教育權等。憲法未曾以自由或權利形容,而解釋上經常被納入權利保障范圍者還包括社會福利保險、健康醫療、文化藝術發展、以及弱勢團體(如婦女、原住民、殘障者)之特別待遇。這些權利規定得并不明確,但是已提供了一個足以發揮充分想象的空間,使學理上的辨析與司法上的解釋產生不少有意思的爭論。 爭論往往不在于“我們有哪些權利”,而是出現在“權利碰上了權利”。我們可以舉幾個較顯著的例子來說明這種權利訴求的困境。 首先,我們都熟悉一個新聞媒體上常用的口號:“人民有知的權利”。所謂“知的權利”并不是憲法所明文保障的國民教育權,而是指“人民有被告知種種關于公共事務如何發展”的權利。憲法上沒有這種權利的規定,理論上這可能屬于言論出版自由及人民參政權的某種結合與擴大解釋。但是不管它的法源何在,新聞工作人員以此為尚方寶劍,扛起攝影機及麥克風深入各種人們想要了解的事件領域中 ── 不管是立法院的議事堂還是兇殺案被害人家中的浴室,他們“負責地”做起“第一手的報導”,務使您“知的權利”沒有受損。可是另一方面,不滿自己整天被追蹤報導的“公共人物”也有話說,他(她)們認為自己的“隱私權”受到侵害。政治人物及影視明星固然抱怨自己私生活無端曝光,車禍或命案的死者家屬也常怒斥媒體對被害人禿鷹式獵攝所造成的二度傷害。然則我們“知的權利”與“隱私權”的分際何在呢? 其次,“發展權”和“環境權”的爭議也是一個眾人耳熟能詳的沖突。主張開發土地、增進地方繁榮、創造就業機會的人認為經濟發展是人民應有的權利,而主張保護自然環境、防止公害擴散、實踐世代正義的人則認為人們擁有享受青山綠水、干凈空氣的起碼權利。他們并不僅僅視自己的主張為一種“意見”,而是宣稱這些主張屬于“權利” ── 屬于一種法律未曾明文規定,但是其基礎無可置疑的自然權利或基本權利。 再以日前臺北市喧騰一時的“廢娼事件”為例。主張廢除公娼的市府官員及民間人士認為每一個人都有不容侵犯的身體尊嚴,因此娼妓制度的存在是現代國家的恥辱,政府應該以公權力鏟除此一違反基本人權的剝削體制。相反地,反對廢娼人士在他(她)們所列舉的種種對抗理由中,也包含了權利的訴求 ── 女性應有自由從事性交易工作以謀生計的權利、獨居男性應有合法滿足性需求之權利、以及女性應有透過性交易開發自身情欲空間、顛覆家庭制度束縛的權利。這個爭議體現的不只是傳統社會主義反異化論對抗自由主義色情寬容論或后現代主義情欲自主論的矛盾,一旦加上了“權利”兩個字,它們也是權利訴求沖突的典型事件。 依著同樣的角度觀察,我們還可以看到許多充滿矛盾沖突的社會爭議。譬如政府為了減少社會成本所強力實施的戴安全帽政策,面臨的是機車族抗議政府過度介入人身幸福安危自主的原則;少數族群為了保護文化資產所要求的使用母語之權利,面臨的是多數族群為了建立溝通可能性而強制實施的國語政策;學生要求圖書館全年開放的權利對上職員要求周休二日的權利;醫師號稱保障病人權益而不釋出處方箋對上藥師基于同一理由所主張的調劑權……。這些權利訴求已經遠超過十七、十八世紀西方思想家所建立的天賦人權范疇,也與憲法所規定的基本人權沒有直接必然的關系,但是并不妨礙人們振振有辭地稱之為權利。 權利訴求似乎依著一個邏輯在不斷地復制:只要在我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冠以權利之名,它就立刻成為一種我本來應該享有的東西。防止我完成這種心愿的障礙,同時也侵犯了我固有的權利。如果這個推測沒錯,那么我們可能還得面對更多(或甚至無止境)的權利要求。學童接受國民教育的權利可能會擴充為人人都有接受完整大學教育的權利;婦女擺脫家奴地位的權利可能會發展成要求國家負擔育幼、養老等照顧工作的權利;而一個人因各種不利條件無法找到適當婚姻對象的主觀挫折,則可能轉化為要求政府扮演超級媒人,以滿足感情安頓的制度性權利實踐體系。這并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傳統權利觀念由消極不受侵犯蛻變為積極要求他方協助實現,以及現代政府日益擴大職能的客觀發展,已經為這種權利訴求泛濫的政治社會奠立了相當基礎。如果人們在口蹄疫的沖擊中可以喊出“我們有吃豬肉的權利”,并且要求政府官員為了老百姓吃不到衛生的豬肉下臺,那么要求人人擁有自己的住屋或享有“轟轟烈烈談一次戀愛”的權利,大概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 二、什么是個人權利? 權利訴求的快速繁衍自然使稍具反省能力的人感到困惑與不安。如果權利伸張只是每個人主觀欲望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權利論述將會迅速失去其正當性與吸引力。在輕易賦予一項主張“權利”之名以前,我們必須思考“憑著什么理由,或是在什么條件下,一件事情才成為我的權利?”這種思考與反省指向政治社會哲學的關懷,而權利的觀念史研究則有助于我們厘清一些問題。 在目前國內僅有的一本關于自由與權利的精心著作中,張佛泉曾經指出:" right " 之原始意義為“直”(straight)。“直”原本為物理現象中的一個描述,如“直線”、“直角”。但是用在道德或政治領域中,right 同樣有“直”或“尺度”之義。他說: 吾人以“權利”譯 right 一字,早已成為法律名詞,欲想改正,已極困難。但吾人必須切記,“賴它”之原義為“直”、為“是”、為“尺度”、為“理應”," human rights " 為“人直”、為“人之理應有者”。(注一) 張佛泉注意到“權利”與“正直”、“尺度”之原始淵源,但是他并沒有解釋一個關鍵性問題:為什么客觀性的“尺度”概念會演變成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主觀性的“擁有”主張?換言之,right 如果原本指涉“直、正確、應當”,那么 human right 就是“人之應當(成為之樣態)”或“人之應當從事者”,為什么它會轉變成“人之理應『有』者”呢?從客觀性的尺度衡量(人應當行其所當行)到主觀性的欲求主張(我擁有……之權利),這個轉變其實正是整個問題關鍵所在。 我們試著從西方學者對“權利”觀念的研究來挖掘更多信息,也許可以補足張佛泉的不足。理查德?達格(Richard Dagger)在一篇探溯“權利”概念起源的文章中告訴我們,“權利”確實與“正直”息息相關。英文的 right 、德文的 recht 、法文的 droit、意大利文的 diritto 等,都源自古拉丁文的 rectus 及 directum。rectus 是“正直、筆直”(straight),directum 有“精確”之意,兩者都與“正確、正直的標準”有關。rectus 可以進一步上溯至古希臘文的相關字眼 orektos,或梵文 riju,同樣也都有“直”或“正直”之意涵。因此毫無疑問地,今人所使用的“權利”一詞,在字源上原本為“正直、應當”之意。將 person 與 right 聯結在一起,表達的是“我應當做件事,因為這是正確的”,它不是現代人所說的“我可以做這件事,因為我有權利這么做”。(注二) 然而這種古典意義的“人直”,又是如何轉變成現代意義的“人權”呢?達格認為這里涉及社會秩序的重大轉變。在古代社會(一直到中世紀末期為止),辨識一個人的方法是認清他在社會中所居處的地位或扮演的角色,而那個人應該做什么行為也與其身分地位相關。“人直”表達的不過是說:“我應當這么做,因為我的地位或角色要求我這么做”。無怪乎 right 與尺寸或標準的意義不可分開,因為每個人正確的為人之道就在社會階層所規定的行為模式之中。君王有君王的 right,封建騎士有封建騎士的 right,它們的表現方式不同,但都依附于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階層體系。 近代社會秩序的劇烈轉變預示了 right 觀念的流變。當封建階層與地位關系逐漸崩解消逝,一個人應當做什么事就不再依附其社會地位,而是奠基于他“身為一個人”的單純角色上。人與人不再嚴格區分階級、文化、種族、性別,而日漸形成無分軒輊的人類。單純的人類是平等的,因此人們享有的自然權利也是平等的。過去一個人依其身分地位而有種種社會實踐上的“權利義務”,今天則每個人都在普遍人性尊嚴的原則下享有一體適用的基本權利。“權利”的詞眼留存了下來,其內涵卻與古典意義南轅北轍。(注三) 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觀察這種社會秩序的轉變,同樣可以找出許多印證達格理論的記述。柏拉圖的《理想國》描繪了一個體現正義原則的城邦,其中每個人依其所屬階層“各盡其職、各安其位”。這里他關切的是人人是否實現其真正的利益,而不是什么自由選擇的權利。正義(justice)與各人實踐其內在的“善”(good)有關,與近代人所強調的“尊重我的權利”沒有關聯。誠如艾文(Terence Irwin)所言: 柏拉圖的道德學說與亞里士多德的一樣,都不曾賦予個人所謂權利。……他的“愛”的理論容不下康德式的“視人為人的尊重”;基于同一理由,他的“正義”理論也輕忽了權利的論述。……由于柏拉圖看不出一個自主而能選擇的人有什么特別價值,因此當個人自由與一個人的(真正)利益相沖突時,他沒有理由去尊重個體的自由。(注四) 西方人真正開始產生權利意識是在中世紀末期到近代初期,約略從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文獻上比較顯著的記載是十七世紀霍布斯的《利維坦》一書,因為這本書不僅開啟了近代政治哲學原子論、契約論、主權論的討論,同時對“權利”語言也有一個革命性的定義。霍布斯說: 著作家一般稱之為自然權利的,就是每一個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 ── 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 ── 的自由。因此,這種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斷和理性認為最適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談論這一問題的人雖然往往把權(ius)與律(lex)混為一談,但卻應當加以區別。因為權(RIGHT)在于做或者不做的自由,而律(LAW)則決定并約束人們采取其中之一。所以律與權的區別就像義務與自由的區別一樣,兩者在同一事物中是不相一致的。(注五) 當霍布斯把“權利”與“法則”分開,他的思想反映的正是 right 由“客觀行為標準”轉變為“個人擁有的自由”之劇變。此一發展并不局限于霍布斯一個人,從稍早的格老秀士、到之后的史賓諾莎、洛克等等,西方政治思想越來越擺脫以良善生活或德性為中心的論述,而朝向權利理論發展。權利不再是封建秩序中每個人行為的正當尺度,而是個人自由的法律保障。個人權利的范圍也從早期的“生命、自由、財產”逐步擴增為包括工作、福利、婚姻、教育,乃至于同性戀、環保、以及多元文化的承認與尊重。從一個角度看,這種“只因我們是人,所以理應享有種種權利”的信念確實是近代人類文明得以突飛猛進的因素之一。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今天權利訴求不斷繁衍以致泛濫的可能根源。那么,我們該如何面對權利的擴充與沖突呢? 三、如何證成權利? 當代西方哲學家看待權利意識的繁衍往往有不同的感受。比較自由開放的人認為權利是我們最重要的觀念,現代政治社會的成立就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個人權利,因此權利越多越好。比較保守嚴肅的人則認為現代權利觀念根本是無中生有的產物,由于它欠缺社會基礎,實際上只是空泛的口號;而由于空泛的口號被當成真理來實踐,因此現代社會秩序崩解、道德淪喪。我們姑且以自由派的德沃肯(Ronald Dworkin)與保守派的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為例,說明哲學家如何愛憎分明地看待個人權利。 德沃肯是當代著名的自由主義健將,也是權利哲學的倡導者之一。他認為權利是個個體化的概念,恰好與集體性的目標有所區隔。一個人擁有權利,表示他能享有某種機會或資源以促進其利益。這種政治權利絕對不能為了增進集體的福祉而被打折扣,所以衡量權利多寡的方式,往往就是看它能對抗多少集體性目標的壓力。權利是人類生活中的“王牌”(trumps),人們之所以擁有權利,并不是因為出身高低或是才能多寡,而僅僅因為他們是“人” ── 是一種具有安排生命計劃的能力以及實現公道的人類(simply as human beings with the capacity to make plans and give justice)。(注六)從這種定義方式看,我們可以確定德沃肯的權利觀念是典型的現代權利觀念:權利是個體選擇生活方式的保障,而人之擁有權利是由于其為普遍平等的人類。 抑有進者,德沃肯主張權利具有某種“自然”屬性。所謂“自然”,并不是指涉近代初期契約論者所假設的自然狀態,而是肯定其保障個人選擇的根本意義。權利的自然性說明了它們不是人為立法規定或假設性契約的產物。權利雖然經由人們立法建構而成形,但是立法建構皆有所本,不是任意創制發明所可比擬。在這個地方,德沃肯提出了著名的“建構模式”。他說:人類的道德直覺與道德理論之間必須有一種均衡的連結方式。“自然模式”假定正義原則乃是客觀存在的道德事實,人們只需要去發現這些原則就可完成道德理論。“建構模式”則主張正義的直覺并不是什么獨立存在的道德原則的線索,而是一個有待建構的理論之規約性特質。我們發展一個道德理論,就宛如雕刻家先找到一些事先發掘到的骨骸,將之拼湊成有限的參考架構后,再著手雕出符合骨架的動物模型。由于骨骸的規定性有限,因此模型無所謂必然的對錯,甚至這個模型所表現的動物也可能根本不存在。在這種道德理論中,重要的是建構工作上的一貫性,凡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假定,就不能當做合理的權利學說之基礎。準此說法,權利的本質是自然的(因為“權利保障個體選擇的重要性”不容懷疑),但是其證成方式則是建構的(我們不能坐待“發現”權利,而是主動去論證一個權利哲學的體系)。(注七)。 很顯然地,德沃肯不只相信個人權利存在,并且有把握證明其存在。相反地,麥金泰爾認為個人權利根本不存在,而所有試圖證成權利的嘗試也都必歸于失敗。麥金泰爾以研究古典哲學見長,他提醒我們“權利”概念一直到中世紀末期才開始出現。權利既然如此晚出,則任何號稱權利為普遍人性訴求之說法都不啻濫開空頭支票。現代人相信我們擁有天賦、自然的權利,其實質效果就像古代人相信女巫及獨角獸的存在一樣。二十世紀的思想家有時會訴諸“道德直覺”以作為“自然權利”存在的依稀證據,但是麥金泰爾說:當一個道德哲學家必須引進“直覺”概念時,多半表示其論證已山窮水盡了。他以嘲諷的語氣評論德沃肯的理論: 德沃肯承認這些所謂自然權利的存在無法證明,但又辯稱即使一個敘述無法被證明,也不表示那個敘述就不真實。這種說法當然沒錯,但是別忘了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策略去辯護獨角獸與女巫的真實性。(注八) 麥金泰爾之所以根本對權利理論嗤之以鼻,乃是因為他相信古典哲學的目的論學說。目的論(teleology)主張萬物皆有其內在預定的自然本性,凡是順應其本性充分發展以臻完善者,即屬該事物的最佳狀態。就人類而言,目的論主張人以追求靈魂之美善為幸福生活的標的,而靈魂美善與否又表現于一個人是否具備種種德性并實踐之,譬如勇敢、節制、慷慨、和善等等。因此,一個人應該成為怎樣的人是有一定尺度可以衡量的,幸福的人生不是個體任意選擇變換的人生,而是努力學習成為一個有德者的歷煉。在麥金泰爾看來,近代權利哲學高漲,肇因于啟蒙運動放棄了目的論的假定,誤信人人可以設定自己想要呈現的人生。其結果是倫理價值相對化、虛無化,而社會上則充斥著無法共量的權利囈語。如果人類還存著救贖的期望,就必須斷然悔悟,重建古典哲學及中世紀宗教信仰所開啟的另一種道德體系。 我們生存在德沃肯和麥金泰爾所共同生活的時代,或多或少也參雜著德沃肯與麥金泰爾截然不同的判斷與建議。從一個方面來講,我們都珍惜近代文明所預設的個人自由,以及政治社會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時而感到現代社會價值過于相對化,五花八門的權利宣稱可能會使一個社會找不到判斷是非對錯的基本準繩。如果為了使生活秩序過得比較單純質樸,而考慮恢復古代的倫理教育,我們會擔心自己目前享有的自主性與生活方式的選擇將歸于消滅。而且社會經濟的發展似乎也不容許我們倒轉時空,重新建立所謂目的論式的德性秩序。反過來講,權利意識由近代自然權利觀念演進成今天的普遍基本人權,再由基本人權朝向無所不包的人權挺進,越來越暴露出其論證基礎的任意性與貧困性。我們似乎到了必須小心反省權利意義與權利范圍的時候。 “個人權利”確實屬于近代以降的產物,所謂“普遍而平等的基本人權”在本質上也確實近似一種信仰,而不是禁得起歷史或社會哲學檢驗的真理。但是權利觀念助長了近代文明的發展,奠立了自由民主社會的意識形態基礎。從其結果上看,依然是利大于弊。當權利意識增長到各種權利訴求沖突難解之時,訴諸近代初期的自然權利論或本世紀初的普遍人權論都無濟于事。比較可行的仲裁方式或許是運用具備溝通討論性質的民主機制,也就是所謂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審議式民主強調一個議題所關涉的人群必須有充分表達意見、進行理性溝通的機會,它不預設議題必須遵循的方向,只在意該議題應該得到公開且自由的討論。因此審議式民主并不必然有利于任何一種爭執的立場 ── 不管是廢娼或反廢娼、戴安全帽或不戴安全帽、有權墮胎或無權墮胎……,但是經過各方人馬淋漓盡致的表達與溝通之后,它至少比較可能使其決策在爭議者心中享有正當性。它所預設的重要前提是爭取權利訴求的人不能把自己的訴求當成永不退讓的天賦權利,從而在民主程序之后仍然不承認民主決策的效力。當然這整個假定是極難落實的,因為不僅民主社會中的成員多半自私自利,而且傳統自由主義的信念也仍然堅持某些基本人權或自由必須超越于民主程序之上 ── 不管是什么樣的民主程序。可是堅持特定價值不也正是我們意識到權利沖突的起點嗎?在民主程序之前,一個堅持色情書刊必須得到合法販售權利的自由主義者,與一個堅持政府必須查緝以保障公民身心健康的保守主義者,究竟有什么道德份量上的先天差別?除了民主程序之外,我們難道有什么更好的仲裁方式?在一個重要意義上,民主程序可能正是自由主義堅持自由價值的必然結果。當越來越多的自由權利被開發出來并形成對立沖突之局,民主審議就成了不得不然的調節機制,因為我們面對的再也不是簡單的自由派或保守派之別,而是不同自命為自由派的自由主義價值之別。這種困境的內在意義,恐怕才是現代社會中所有提倡個人權利的行動者,所必須深思的課題。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江宜樺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