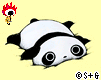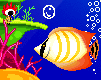| ąąš■įVįA┼eūCž¤(z©”)╚╬éĆ(g©©)ąį╗»čąŠ┐ų«│§▓Į ĪĪĪĪ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Ļ08į┬04╚š 11:18 ųąįuŠW(w©Żng) | |||||||||
|
ĪĪĪĪĪČąąš■Ę©īW(xu©”)蹊┐ĪĘ1998─ĻĄ┌3Ų┌▌dėąę╗Ų¬░Ė└²čąŠ┐šō╬─Ż¼Ņ}×ķŻ║ĪČ▀`Ę©ąą×ķ─▄ʱ═ŲČ©Ī¬Ī¬ī”ę╗Ų╣½░▓ąąš■┘rāö░Ė╝■Ą─Ęų╬÷ĪĘĪŻ┤╦╬─╦∙╔µąąš■░Ė╝■ęčė╔ųžæc╩ąųą╝ē╚╦├±Ę©į║īÅĮY(ji©”)ĪŻ╚╗Č°Ż¼Å─ū„×ķĘ©į║▓├┼ą╗∙ĄA(ch©│)Ą─═Ų└Ēųą┐╔ęį░l(f©Ī)¼F(xi©żn)Ż¼ī”įō░ĖīÅ└ĒĮY(ji©”)╣¹Š▀ėąøQČ©ąįū„ė├Ą─ę╗éĆ(g©©)ųžę¬Ę©┬╔å¢Ņ}Ż¼╝┤ąąš■įVįA┼eūCž¤(z©”)╚╬å¢Ņ}Ż¼▓ó╬┤Ą├ĄĮ│õĘųĻU░l(f©Ī)ĪŻæ]╝░Į³─ĻüĒŻ¼į┌Ī░ąąš■įVįA┼eūCž¤(z©”)╚╬Ī▒Ņ}ė“└’Ż¼ĀÄšōŅHČÓŻ¼[1] ╣╩▒Š╬─ćLįćęįįō░Ė└²×ķĘų╬÷ī”Ž¾Ż¼╠Į╦„ę╗Ślī”▀@ę╗Ņ}ė“Ą─éĆ(g©©)ąį╗»čąŠ┐┬ĘÅĮĪŻ
ĪĪĪĪ░Ė└²ę²│÷å¢Ņ}Ż║šlžō(f©┤)┼eūCž¤(z©”)╚╬ ĪĪĪĪ░ĖŪķ║åĮķ ę“├±╩┬é∙äš(w©┤)╝m╝ŖŻ¼┤Õ├±£½─│▒╗ę╗┼╔│÷╦∙é„åŠĪŻį┌£½─│ĄĮ┼╔│÷╦∙Įė╩▄įāå¢ų«Ģr(sh©¬)Ż¼┼Ń═¼ŲõŪ░═∙Ą─ń█╩ÕĄ╚║“ė┌═ŌĪŻ╝s╩«ĘųńŖ║¾Ż¼┼╔│÷╦∙Š»åT│÷üĒå¢ń█╩ÕŻ║Ī░─ŃųČā║╩Ūʱėą▓ĪŻ┐Ī▒ń█╩ÕļS╝┤╚ļā╚(n©©i)Ż¼ęŖ£½─│Ī░ėę╩ųūźūĪę╬ūėĄ─▀ģŻ¼ū¾╩ų░l(f©Ī)ČČŻ¼─ś╔½▐D(zhu©Żn)ŪÓŻ¼č█Š”░l(f©Ī)ŃČŻ¼║¶╬³└¦ļyŻ¼šf▓╗│÷įÆüĒĪŻĪ▒ų«║¾Ż¼£½─│į┌╦══∙ßt(y©®)į║ōīŠ╚═Šųą╦└═÷ĪŻį┌╔Ų║¾╠Ä└ĒųąŻ¼┼╔│÷╦∙╦∙ī┘─│┐h╣½░▓Šųęį£½─│į°╗╝─I▓Ī×ķė╔Ż¼šJ(r©©n)Č©£½─│ŽĄ─I▓Ī░l(f©Ī)ū„╦└═÷Ż¼╣½░▓ÖC(j©®)ĻP(gu©Īn)ī”┤╦▓╗žō(f©┤)╚╬║╬ž¤(z©”)╚╬ĪŻ£½╝ęī┘ę╗į┘ę¬Ū¾▀M(j©¼n)ąą╩¼ÖzŻ¼┐╔┐h╣½░▓Šų▓╗Ą½╬┤ėĶęį╩¼Öz║═Ę©ßt(y©®)ĶbČ©Ż¼Č°ŪꞤ(z©”)│╔£½╝ęī┘īó╩¼¾w╦═Üøāx^╗╗»ĪŻ╗╗»ų«║¾Ż¼£½╝ęī┘Ž“ųžæc╩ą╣½░▓Šų╔ĻšłÅ═(f©┤)ūhŻ¼╩ą╣½░▓ŠųÅ═(f©┤)ūh║¾šJ(r©©n)×ķŻ║┐h╣½░▓Šųį┌╬┤▀M(j©¼n)ąą╩¼ÖzĪóĘ©ßt(y©®)ĶbČ©Ą─ŪķørŽ┬Ż¼šJ(r©©n)Č©£½ŽĄ─I▓Ī╦└═÷ę└ō■(j©┤)▓╗ūŃŻ╗Ą½┼╔│÷╦∙ī”£½ę└Ę©é„åŠ╩Ū║ŽĘ©Ą─Ż¼š{(di©żo)▓ķųąę▓╬┤░l(f©Ī)¼F(xi©żn)┼╔│÷╦∙Š»åTėą▀`Ę©ąą×ķŻ¼ę▓¤oūCō■(j©┤)ūCīŹ(sh©¬)£½╩Ū┼╔│÷╦∙Š»åTܬ┤“ų┬╦└ĪŻ╣╩Ė∙ō■(j©┤)ĪČųą╚A╚╦├±╣▓║═ć°ć°╝ę┘rāöĘ©ĪĘĄ─ėąĻP(gu©Īn)ęÄ(gu©®)Č©Ż¼ŠS│ų┐h╣½░▓Šųī”£½Ą─╦└═÷▓╗žō(f©┤)┘rāöž¤(z©”)╚╬Ą─øQČ©ĪŻ£½╝ęī┘▓╗Ę■Ż¼ęį£½╦└Ū░░YĀŅĘ¹║ŽļŖŠ»╣„ļŖō¶║¾Ą─╠žš„Īó╣½░▓ÖC(j©®)ĻP(gu©Īn)¤oūCō■(j©┤)ūCīŹ(sh©¬)£½Ą─╦└═÷▓╗╩Ū┼╔│÷╦∙Š»åTąą×ķ╦∙ų┬×ķė╔Ż¼Ž“ųžæc╩ąųą╝ē╚╦├±Ę©į║╠ßŲąąš■įVįAŻ¼šłŪ¾╣½░▓ÖC(j©®)ĻP(gu©Īn)┬─ąąĘ©Č©┬Üž¤(z©”)Īó▓ķŪÕ£½╦└═÷Ą─šµŽÓ▓óĮoėĶ┘rāöĪŻ ĪĪĪĪĘ©╣┘Ą─═Ų└Ē║═╠Äų├[2] Ę©╣┘Ą─ĮY(ji©”)šōąįęŌęŖ×ķŻ¼Ī░╣½░▓ÖC(j©®)ĻP(gu©Īn)æ¬(y©®ng)ū├Ūķ│ąō·(d©Īn)ę╗Č©Ą─┘rāöž¤(z©”)╚╬Ī▒Ż¼└Ēė╔Ė┼└©╚ńŽ┬Ż║ ĪĪĪĪ1.╣½░▓ÖC(j©®)ĻP(gu©Īn)▀`Ę©ąąš■ų┬╩╣£½╦└═÷Ą─┐╔─▄ąįĄ─═ŲČ©ĪŻ£½╦└ė┌╣½░▓ÖC(j©®)ĻP(gu©Īn)ł╠(zh©¬)Ę©Ą─╠žČ©Łh(hu©ón)Š│Ż¼│²╣½░▓╚╦åT║═╦└š▀═ŌŻ¼¤oĄ┌╚²╚╦į┌ł÷Ż¼▓ķŪÕ╦└ę“Ą─╬©ę╗═ŠÅĮ╩Ū▀M(j©¼n)ąą╩¼Öz║═Ę©ßt(y©®)ĶbČ©Ż¼▓╗─▄å╬æ{£½╦└Ū░Ą─ĘNĘN░YĀŅĪŻĄ½╩ŪŻ¼╣½░▓ÖC(j©®)ĻP(gu©Īn)¤oęĢ£½╝ęī┘Ą─ę╗į┘ę¬Ū¾║═Ę©Č©┬Üž¤(z©”)Ż¼╬┤▀M(j©¼n)ąą╩¼ÖzŠ═ž¤(z©”)│╔īó╩¼¾w╦═Üøāx^╗╗»ĪŻ▀@ę╗³c(di©Żn)▒Ē├„┤µį┌╣½░▓ÖC(j©®)ĻP(gu©Īn)▀`Ę©ąąš■ų┬╩╣£½╦└═÷Ą─┐╔─▄ąįŻ╗ ĪĪĪĪ2.╣½░▓ÖC(j©®)ĻP(gu©Īn)žō(f©┤)ō·(d©Īn)┼eūCž¤(z©”)╚╬Ż¼╬┤║▄║├┬─ąą╝┤öĪįVĪŻĪ░ĪČųą╚A╚╦├±╣▓║═ć°ąąš■įVįAĘ©ĪĘĄ┌32Śl├„┤_ęÄ(gu©®)Č©Ż¼ąąš■įVįAųąĄ─┼eūCž¤(z©”)╚╬ė╔▒╗Ėµąąš■ÖC(j©®)ĻP(gu©Īn)│ąō·(d©Īn)ĪŻĪ▒į┌ąąš■ł╠(zh©¬)Ę©ųąŻ¼╣½├±║═ąąš■ÖC(j©®)ĻP(gu©Īn)Ą─Ę©┬╔Ąž╬╗Ī░▓╗ŲĮĄ╚Ī▒Ż¼£½ę“║╬Č°╦└Ż¼įŁĖµ¤oĘ©╠ß╣®ūCō■(j©┤)Ż¼Ī░ų╗─▄┐┐▒╗Ėµ┼eūCĪ▒ĪŻČ°▒╗Ėµ┼e▓╗│÷£½Ī░▓╗╩Ūę“╣½░▓ÖC(j©®)ĻP(gu©Īn)╣żū„╚╦åT▀`Ę©ąąš■ąą×ķų┬╦└Ą─ūCō■(j©┤)Ż¼╣╩æ¬(y©®ng)│ąō·(d©Īn)öĪįVž¤(z©”)╚╬Ī▒Ż╗ 3.▓╗┼┼│²£½ų«╦└▓óĘŪė╔╣½░▓ÖC(j©®)ĻP(gu©Īn)▀`Ę©ąąš■╦∙ų┬Ą─┐╔─▄ąįĪŻ╣½░▓ÖC(j©®)ĻP(gu©Īn)ī”£½Ą─╦└═÷▓╗─▄ū„│÷║Ž└ĒĮŌßīŻ¼ę▓▓╗─▄ūC├„£½Ą─╦└═÷ĘŪ╣½░▓ÖC(j©®)ĻP(gu©Īn)▀`Ę©ąą×ķ╦∙ų┬Ż¼ę“┤╦┐╔ęį═ŲČ©Ųõ┤µį┌▀`Ę©ąą×ķŻ¼Ą½ę▓▓╗─▄ÖC(j©®)ąĄĄž═ŲČ©£½ų«╦└═Ļ╚½│÷ė┌╣½░▓ÖC(j©®)ĻP(gu©Īn)Ą─▀`Ę©ąą×ķŻ╗ ĪĪĪĪ4.╗∙ė┌š■▓▀ąį┐╝æ]Ż¼ž¤(z©”)│╔╣½░▓ÖC(j©®)ĻP(gu©Īn)žō(f©┤)ō·(d©Īn)▓┐Ęų┘rāöž¤(z©”)╚╬ĪŻ£½Ą─╦└ę“ęč¤oĘ©▓ķŪÕŻ¼╝╚┐╔─▄╩Ū╣½░▓ÖC(j©®)ĻP(gu©Īn)▀`Ę©ąąš■ų┬╦└Ż¼ę▓▓╗┼┼│²£½ūį╔Ē═╗░l(f©Ī)ąį╝▓▓Ī░l(f©Ī)ū„įņ│╔╦└═÷Ą─┐╔─▄ąįĪŻ╦∙ęįŻ¼┼ą┴Ņ╣½░▓ÖC(j©®)ĻP(gu©Īn)ī”£½Ą─╦└═÷Ī░│ąō·(d©Īn)╚½▓┐┘rāöž¤(z©”)╚╬╗“š▀═Ļ╚½▓╗│ąō·(d©Īn)┘rāöž¤(z©”)╚╬Ż¼Č╝╩Ū▓╗└¹ė┌▒Żūo(h©┤)╣½├±Ą─║ŽĘ©ÖÓ(qu©ón)굯¼ŠS│ų╔ńĢ■(hu©¼)░▓Č©Ż¼š{(di©żo)╠Ä║├Ī«╣┘Ī»├±ĻP(gu©Īn)ŽĄĄ─ĪŻĪ▒┐╔ģóššĪČć°╝ę┘rāöĘ©ĪĘĄ┌27ŚlęÄ(gu©®)Č©Ī░ū├Ūķ╠Ä└ĒĪ▒Ż¼ė╔╣½░▓ÖC(j©®)ĻP(gu©Īn)│ąō·(d©Īn)ę╗Č©┘rāöž¤(z©”)╚╬ĪŻ ĪĪĪĪĖ∙ō■(j©┤)▀@ą®└Ēė╔Ż¼Ę©╣┘ų„│ųįŁĖµ║═▒╗Ėµ▀_(d©ó)│╔┘rāöģf(xi©”)ūhĪŻ[3] ĪĪĪĪšlžō(f©┤)┼eūCž¤(z©”)╚╬ Ķbė┌įŁĖµĄ─įVįAšłŪ¾Ż¼░Ė╝■Ą─ĮKśOąįĀÄūh³c(di©Żn)į┌ė┌Ż¼╣½░▓ÖC(j©®)ĻP(gu©Īn)æ¬(y©®ng)ʱ│ąō·(d©Īn)┘rāö┴xäš(w©┤)ĪŻ┐╔╩ŪŻ¼▀@éĆ(g©©)Ę©┬╔å¢Ņ}Ą─ĮŌøQę└┘ćė┌ę╗éĆ(g©©)╩┬īŹ(sh©¬)šJ(r©©n)Č©Ż¼╝┤£½─│╩ŪʱŽĄ╣½░▓ÖC(j©®)ĻP(gu©Īn)Ą─▀`Ę©╣½äš(w©┤)ąą×ķų┬╦└ĪŻ×ķ│╬ŪÕ┤╦╩┬īŹ(sh©¬)╔ŽĄ─ę╔å¢Ż¼Ę©╣┘ąĶę¬ć·└@ā╔éĆ(g©©)ĘĮ├µĄ─╚¶Ė╔ūCō■(j©┤)Ż║Ųõę╗Ż¼╣½░▓ÖC(j©®)ĻP(gu©Īn)ėąø]ėąį┌ł╠(zh©¬)ąą┬Üäš(w©┤)▀^│╠ųąīŹ(sh©¬)╩®▀`Ę©ąą×ķŻ╗ŲõČ■Ż¼╚¶┤░Ė╩Ū┐ŽČ©Ą─Ż¼▀`Ę©ąą×ķ╩Ūʱī¦(d©Żo)ų┬£½╦└═÷Ą─ų▒ĮėįŁę“ĪŻė╔ė┌£½╩¼¾węč╗╗»Ż¼Ę©į║¤oĘ©ę└ō■(j©┤)Ę©Č©┬ÜÖÓ(qu©ón)ūįąąš{(di©żo)╚ĪŽÓĻP(gu©Īn)ūCō■(j©┤)ĪŻ[4] ė┌╩ŪŻ¼å¢Ņ}▐D(zhu©Żn)╗»×ķŻ¼įVįAā╔įņ«ö(d©Īng)╩┬╚╦Š┐Š╣──ę╗ĘĮ▒žĒÜ╠ß│÷│õūŃĄ─ūCō■(j©┤)ęįšfĘ■Ę©╣┘ų¦│ųŲõų„ÅłŻ¼Ę±ätŻ¼įōĘĮ«ö(d©Īng)╩┬╚╦Š═ę¬│ąō·(d©Īn)ūŅĮKöĪįVĄ─║¾╣¹ĪŻ▀@ęÓ╝┤╬ęéā═©│Ż╦∙└ĒĮŌĄ─┼eūCž¤(z©”)╚╬Ą─Ęų┼õå¢Ņ}ĪŻ ĪĪĪĪĘ©╣┘į┌▒Š░ĖųąĄ─▀xō±╩Ū░č┼eūCž¤(z©”)╚╬┼õų├ĄĮąąš■ÖC(j©®)ĻP(gu©Īn)ę╗ĘĮŻ¼ų„ę¬└Ēė╔ėąā╔éĆ(g©©)Ż║Ųõę╗Ż¼ĪČąąš■įVįAĘ©ĪĘĄ─├„┤_ęÄ(gu©®)Č©Ż╗ŲõČ■Ż¼ąąš■ÖC(j©®)ĻP(gu©Īn)┼c╣½├±į┌ąąš■╣▄└ĒųąĄ─Ąž╬╗▓╗ŲĮĄ╚Ż¼£½Ą─╦└ę“ų╗ėą▒╗Ėµ▓┼─▄╠ß╣®ĪŻĢ║Ūę▓╗šōĪČąąš■įVįAĘ©ĪĘĄ┌32ŚlęÄ(gu©®)Č©į┌┴óĘ©╝╝ąg(sh©┤)╔ŽĄ─╚▒Ž▌ĪŻ[5] Š═Ą┌Č■éĆ(g©©)└Ēė╔Č°čįŻ¼ąąš■ÖC(j©®)ĻP(gu©Īn)┼c╣½├±į┌ąąš■╣▄└ĒųąĄ─Ąž╬╗▓╗ŲĮĄ╚Š▀ėąŽÓ«ö(d©Īng)│╠Č╚Ą─Ųš▒ķąįŻ¼╚ń╣¹ė╔┤╦═Ųšō▒╗Ėµžō(f©┤)┼eūCž¤(z©”)╚╬Ż¼▀@ę╗┼õų├įŁätžM▓╗│╔×ķĮ^ī”Ą─Ż┐ßśī”ąąš■┘rāöįVįAųąĄ─┼eūCž¤(z©”)╚╬å¢Ņ}Ż¼ėą▓╗╔┘īW(xu©”)š▀šJ(r©©n)×ķįŁĖµæ¬(y©®ng)žō(f©┤)ō·(d©Īn)ōp║”╩┬īŹ(sh©¬)Ą─┼eūCž¤(z©”)╚╬Ż¼░³└©ōp║”╩┬īŹ(sh©¬)Ą─┤µį┌Īóōp║”ė╔▒╗Ėµ▀`Ę©╣½äš(w©┤)ę²ŲĪóōp║”Ą─│╠Č╚Ą╚ĪŻ[6] ūŅĖ▀╚╦├±Ę©į║ę▓į┌ĪČĻP(gu©Īn)ė┌īÅ└Ēąąš■┘rāö░Ė╝■Ą─╚¶Ė╔ęÄ(gu©®)Č©ĪĘųąū„│÷ęÄ(gu©®)Č©Ż¼Ī░įŁĖµį┌ąąš■┘rāöįVįAųąī”ūį╝║Ą─ų„Åł│ąō·(d©Īn)┼eūCž¤(z©”)╚╬ĪŻ▒╗ĖµėąÖÓ(qu©ón)╠ß╣®▓╗ėĶ┘rāö╗“š▀£p╔┘┘rāö?sh©┤)─ö?sh©┤)Ņ~ĘĮ├µĄ─ūCō■(j©┤)ĪŻĪ▒Ė∙ō■(j©┤)1999─Ļ11į┬24╚š═©▀^Ą─ĪČūŅĖ▀╚╦├±Ę©į║ĻP(gu©Īn)ė┌ł╠(zh©¬)ąąĪ┤ųą╚A╚╦├±╣▓║═ć°ąąš■įVįAĘ©ĪĄ╚¶Ė╔å¢Ņ}Ą─ĮŌßīĪĘ(ęįŽ┬║åĘQĪČ╚¶Ė╔ĮŌßīĪĘ)Ą┌27ŚlĄ┌3ĒŚ(xi©żng)ęÄ(gu©®)Č©Ż¼į┌ę╗▓ó╠ßŲĄ─ąąš■┘rāöįVįAųąŻ¼[7]įŁĖµ▒žĒÜ│ąō·(d©Īn)┼eūCž¤(z©”)╚╬Ż¼ūC├„ę“╩▄▒╗įVąą×ķŪų║”Č°įņ│╔ōp╩¦Ą─╩┬īŹ(sh©¬)ĪŻę▓Š═╩ŪšfŻ¼Ė∙ō■(j©┤)īW(xu©”)└Ē║═ūŅĖ▀ÖÓ(qu©ón)═■Ą─╦ŠĘ©ĮŌßīŻ¼▒Š░ĖĄ─įŁĖµæ¬(y©®ng)ī”Ę©į║╦∙ąĶꬥ─╔Ž╩÷ā╔ĘĮ├µūCō■(j©┤)žō(f©┤)ō·(d©Īn)┼eūCž¤(z©”)╚╬ĪŻ╚ń║╬šf├„īW(xu©”)└ĒĪó╦ŠĘ©ĮŌßī┼c▒Š░ĖīÅ┼ąīŹ(sh©¬)█`Ą─▀@ę╗├¼Č▄─žŻ┐į┌┼eūCž¤(z©”)╚╬å¢Ņ}╔ŽŻ¼īW(xu©”)└ĒĪó╦ŠĘ©ĮŌßī║═▒Š░ĖĄ─īÅ┼ąīŹ(sh©¬)█`╩ŪʱČ╝ėąųĄĄ├Özėæų«╠Ä─žŻ┐ ĪĪĪĪĪ░┼eūCž¤(z©”)╚╬Ī▒├„╬·╗»Ż║ę╗éĆ(g©©)ĮĶĶbĄ─ĘĮĘ© ĪĪĪĪ╩▓├┤╩Ū┼eūCž¤(z©”)╚╬ ĪČąąš■įVįAĘ©ĪĘ║═ūŅĖ▀╚╦├±Ę©į║╦ŠĘ©ĮŌßīī”┤╦Č╝ø]ėąū„│÷├„┤_Ą─ĮńČ©Ż¼─┐Ū░īW(xu©”)ąg(sh©┤)╬─½I(xi©żn)ųąūŅ×ķŽĄĮy(t©»ng)ĄžėĶęį╠ĮėæĄ─Ż¼«ö(d©Īng)ī┘Ė▀╝ę韎╚╔·Ą─ĪČšōąąš■įVįA┼eūCž¤(z©”)╚╬ĪĘę╗╬─ĪŻ[8] įō╬─į┌蹊┐ėó├└Ę©ŽĄć°╝ę║═Ą┬ć°Ą─┼eūCž¤(z©”)╚╬ĘųŅÉ└ĒšōĄ─╗∙ĄA(ch©│)╔ŽŻ¼╠ß│÷Ī░═Ļš¹Ą─┼eūCž¤(z©”)╚╬ė╔═Ų▀M(j©¼n)ž¤(z©”)╚╬║═šfĘ■ž¤(z©”)╚╬śŗ(g©░u)│╔Ī▒Ą─Į©ūhĪŻ▀@ĘNę²▀M(j©¼n)ūCō■(j©┤)Ę©▌^×ķ░l(f©Ī)▀_(d©ó)Ą─ėó├└Ę©ŽĄć°╝ęĘųŅÉ└ĒšōĄ─ĘĮĘ©Ż¼ī”ė┌╠Į╦„┼c░l(f©Ī)š╣╬ęć°Ą─ūCō■(j©┤)ęÄ(gu©®)ätė╚Ųõ╩Ū┼eūCž¤(z©”)╚╬Ęų┼õęÄ(gu©®)ätŻ¼ęŌ┴xųž┤¾ĪŻ[9] ĪĪĪĪĖ∙ō■(j©┤)ėó├└Ę©ūCō■(j©┤)ęÄ(gu©®)ätŻ¼į┌├┐ę╗éĆ(g©©)░Ė╝■ųąŻ¼ßśī”├┐ę╗éĆ(g©©)ĀÄūh³c(di©Żn)(issue)Č╝┤µį┌ų°į┌╣”─▄╔ŽŽÓ╗źĻP(gu©Īn)┬ō(li©ón)Ą─įVšłž¤(z©”)╚╬(a pleading burden)Īó╠ßūCž¤(z©”)╚╬(a production burden)║═šfĘ■ž¤(z©”)╚╬(a persuasion burden)ĪŻ ĪĪĪĪįVšłž¤(z©”)╚╬ę▓ĘQū„═źīÅŪ░ž¤(z©”)╚╬Ż¼╩ŪųĖ¤ošō──ę╗ĘĮ«ö(d©Īng)╩┬╚╦Ż¼Č╝▒žĒÜį┌ŽÓæ¬(y©®ng)Ą─ŲįVĢ°Īó╣½įVĢ°Īó┤▐q╗“┐╣▐qųąŻ¼ĮĶų·ę╗Č©Ą─ūCō■(j©┤)╠ß│÷įVįAų„ÅłŻ¼ęį╩╣Ųõ│╔×ķ░Ė╝■Ą─ĀÄūh³c(di©Żn)ĪŻ«ö(d©Īng)╩┬╚╦┐╔ęį║åČ╠├„░ūĄž╠ß│÷╗“ą▐Ė─ŲõšłŪ¾║═▐qūo(h©┤)Ż¼ęį┬─ąąįVšłž¤(z©”)╚╬Ż¼Ųõ─┐Ą─į┌ė┌╩╣įVįAų„ÅłŠ▀ėąšµš²Ą─ęŌ┴x║═┤_Č©ąįĪŻė╔ė┌įVšłž¤(z©”)╚╬Ą─ųžę¬ąį▌^╚§Ż¼│÷¼F(xi©żn)Ą─å¢Ņ}ę▓▌^╔┘Ż¼╦∙ęįŻ¼ėó├└Ę©īW(xu©”)š▀ę╗░Ń▓╗ėĶ▀^ČÓėæšōĪŻ ĪĪĪĪ╠ßūCž¤(z©”)╚╬║═šfĘ■ž¤(z©”)╚╬Ą─║Ž│╔╝┤╦∙ų^Ą─┼eūCž¤(z©”)╚╬(burden of proof)ĪŻšfĘ■ž¤(z©”)╚╬ęÓĘQĘ©Č©ž¤(z©”)╚╬Īó╣╠Č©ž¤(z©”)╚╬Ż¼žō(f©┤)ėą┤╦ĒŚ(xi©żng)ž¤(z©”)╚╬Ą─«ö(d©Īng)╩┬╚╦▒žĒÜ╠ß╣®ūCō■(j©┤)ęį╩╣╩┬īŹ(sh©¬)▓├Č©š▀▀_(d©ó)ĄĮŽÓ«ö(d©Īng)?sh©┤)─┤_ą┼│╠Č╚Ż¼Ę±ätŻ¼╦¹īóį┌─│éĆ(g©©)ĀÄūh³c(di©Żn)╔ŽöĪįVĪŻ╦∙ęįŻ¼į┌─│ĘNęŌ┴x╔ŽšfŻ¼žō(f©┤)ėąšfĘ■ž¤(z©”)╚╬Ą─«ö(d©Īng)╩┬╚╦ę¬│ąō·(d©Īn)Ī░ø]ėąšfĘ■Ą─’L(f©źng)ļU(xi©Żn)Ī▒(risk of nonpersuasion)ĪŻčįŲõ×ķĪ░Ę©Č©ž¤(z©”)╚╬Ī▒Ż¼╩Ūę“?y©żn)ķ╦³╚ĪøQė┌īŹ(sh©¬)¾wĘ©Ą─ęÄ(gu©®)Č©Ż╗čįŲõ×ķĪ░╣╠Č©ž¤(z©”)╚╬Ī▒Ż¼╩Ūę“?y©żn)ķ╦³į┌įVįA▀^│╠ųąę╗░Ń▓╗Ą├▐D(zhu©Żn)ęŲĪŻ[10] ĪĪĪĪ╠ßūCž¤(z©”)╚╬ę▓ĘQū„═Ų▀M(j©¼n)ž¤(z©”)╚╬Ż¼╩ŪųĖę╗ĘĮ«ö(d©Īng)╩┬╚╦▒žĒÜŠ═╠žČ©ĀÄūh³c(di©Żn)╠ß│÷│õūŃūCō■(j©┤)Ż¼Å─Č°┐╔ęįę¬Ū¾Ę©╣┘īóįōĀÄūh³c(di©Żn)Į╗ĖČ┼ŃīÅłF(tu©ón)ū„│÷▓├öÓĪŻ╝┘╚ńžō(f©┤)ėą╠ßūCž¤(z©”)╚╬Ą─«ö(d©Īng)╩┬╚╦ī”╝╚ėąūCō■(j©┤)(¤ošō╩Ūūį╝║╠ß│÷Ą─▀Ć╩Ūī”ĘĮ╠ß│÷Ą─)┬Āų«╚╬ų«Ż¼Č°╝╚ėąūCō■(j©┤)ėų¤oĘ©╩╣Ę©╣┘ĖąėXĄĮę╗éĆ(g©©)└ĒąįĄ─┼ŃīÅåTĢ■(hu©¼)ū„│÷ėą└¹ė┌įō«ö(d©Īng)╩┬╚╦Ą─╩┬īŹ(sh©¬)šJ(r©©n)Č©Ż¼Ę©╣┘Š═Ģ■(hu©¼)▓╗Įø(j©®ng)▀^┼ŃīÅłF(tu©ón)ų▒Įėū„│÷▓╗└¹ė┌įōĘĮ«ö(d©Īng)╩┬╚╦Ą─╝┤Ģr(sh©¬)▓├Č©(peremptory ruling)ĪŻ╝┘╚ńžō(f©┤)ėą╠ßūCž¤(z©”)╚╬Ą─«ö(d©Īng)╩┬╚╦šJ(r©©n)šµŽ“Ę©═ź╠ß╣®ėąĻP(gu©Īn)Ą─ūCō■(j©┤)Ż¼╦¹▓╗āH┐╔ęįĪ░═©▀^Ę©╣┘▀@ę╗ĻP(gu©Īn)Ī▒(passing the judge)Ż¼ūī┼ŃīÅłF(tu©ón)üĒ┐╝▓ņŲõūCō■(j©┤)╝░ŽÓæ¬(y©®ng)╩┬īŹ(sh©¬)ų„ÅłŻ¼Č°Ūęį┌ŲõūCō■(j©┤)▀_(d©ó)ĄĮę╗Č©ś╦(bi©Īo)£╩(zh©│n)ų«║¾Ż¼▀Ć┐╔ęį░č╠ßūCž¤(z©”)╚╬▐D(zhu©Żn)╝▐Įoī”ĘĮ«ö(d©Īng)╩┬╚╦ĪŻ▀@Š═ęŌ╬Čų°ī”ĘĮ«ö(d©Īng)╩┬╚╦▒žĒÜžō(f©┤)ž¤(z©”)╠ß│÷Ę┤ūCŻ¼Ę±ätŻ¼╦¹īó│ą╩▄Ę©╣┘ų▒Įėū„│÷Ą─▓╗└¹Ą─╝┤Ģr(sh©¬)▓├Č©ĪŻ ĪĪĪĪėó├└Ę©ŽĄĘ©į║īÅ└ĒĄ─═©│ŻŪķør╩Ū┼ŃīÅųŲŻ¼ę“┤╦Ż¼╠ßūCž¤(z©”)╚╬╩ŪʱęčĮø(j©®ng)┬─ąą═∙═∙ė╔Ę©╣┘?z©©ng)QČ©Ż¼šfĘ■ž¤(z©”)╚╬╩ŪʱęčĮø(j©®ng)┬─ąąätė╔┼ŃīÅłF(tu©ón)øQČ©ĪŻōQčįų«Ż¼«ö(d©Īng)╩┬╚╦▒žĒÜ║▄║├┬─ąą╠ßūCž¤(z©”)╚╬Ż¼╠ß╣®│õūŃūCō■(j©┤)Ż¼ęįĘ└ų╣Ę©╣┘Š▄Į^░č╩┬īŹ(sh©¬)ĀÄūh³c(di©Żn)Į╗ĖČ┼ŃīÅłF(tu©ón)Č°ū„│÷ų▒Įė▓├Č©Ż╗Č°įĮ▀^▀@ę╗šŽĄKų«║¾Ż¼╦¹▀Ć▒žĒÜųö(j©½n)╔„╠Ä└Ē║├ŲõšfĘ■ž¤(z©”)╚╬Ż¼Ę±ätŻ¼╚į╚╗┐╔─▄į┌─│╩┬īŹ(sh©¬)ĀÄūh³c(di©Żn)╔ŽöĪįVŻ¼ę“?y©żn)ķ┼ŃīÅłF(tu©ón)┐╔─▄▓╗ŽÓą┼╦¹Ą─ūC╚╦ūCčįĪó╗“š▀▓╗įĖĄ├│÷▒ž╚╗Ą─═ŲöÓĪó╗“š▀šJ(r©©n)×ķŽÓĘ┤ūCō■(j©┤)╩╣Ą├ę╔墫a(ch©Żn)╔·┴╦ĪŻ[11] ĪĪĪĪ┼eūCž¤(z©”)╚╬Ą─Ęųō·(d©Īn) šfĘ■ž¤(z©”)╚╬║═╠ßūCž¤(z©”)╚╬Ą─ĘųŅÉĮ^ĘŪ╝ā┤ŌīW(xu©”)└ĒęŌ┴x╔ŽĄ─Ż¼╦³éāČ╝ę²░l(f©Ī)▓╗═¼įVįA▀^│╠ųąĄ─ž¤(z©”)╚╬Ęųō·(d©Īn)å¢Ņ}║═ž¤(z©”)╚╬ĮŌ│²ś╦(bi©Īo)£╩(zh©│n)å¢Ņ}Ż¼Č╝ī¦(d©Żo)ų┬▓╗═¼Ą─įVįAĮY(ji©”)╣¹ĪŻ ĪĪĪĪĖ∙ō■(j©┤)ėó├└Ę©ūCō■(j©┤)ęÄ(gu©®)ätŻ¼į┌ą╠╩┬įVįAųąŻ¼┼cĘĖū’ėąĻP(gu©Īn)Ą─╩┬īŹ(sh©¬)ę╗░ŃČ╝ė╔Öz┐ž╣┘žō(f©┤)ž¤(z©”)šfĘ■┼ŃīÅłF(tu©ón)Ż¼╝┤šfĘ■ž¤(z©”)╚╬ė╔┐žĘĮ│ąō·(d©Īn)Ż¼ŲõĮŌ│²Ą─Śl╝■╩Ū┐žĘĮ╦∙╠ß│÷Ą─ūCō■(j©┤)▀_(d©ó)ĄĮĪ░┼┼│²║Ž└Ēæčę╔Ī▒(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Ą─ś╦(bi©Īo)£╩(zh©│n)ĪŻį┌├±╩┬įVįAųą(ūóęŌėó├└Ę©ŽĄąąš■╝m╝ŖĄ─ĮŌøQ═©▀^├±╩┬įVįA│╠ą“üĒ═Ļ│╔)Ż¼┼eūCž¤(z©”)╚╬Ęų┼õęÄ(gu©®)ätĄ──Ż║²ąįĖ³┤¾ĪŻßśī”╚╬║╬╠žČ©ĀÄūh³c(di©Żn)Ą─┼eūCž¤(z©”)╚╬Ż¼│²ĘŪųŲČ©Ę©├„┤_ęÄ(gu©®)Č©Ż¼ø]ėąŽ╚Č©Ąžė╔įŁĖµ▀Ć╩Ū▒╗Ėµ│ąō·(d©Īn)ĪŻ─Ū├┤Ż¼ėó├└Ę©ŽĄĄ─Ę©╣┘╩ŪĖ∙ō■(j©┤)╩▓├┤üĒĘų┼õŽÓæ¬(y©®ng)Ą─ž¤(z©”)╚╬─žŻ┐ėąīW(xu©”)š▀ųĖ│÷Ż¼┼eūCž¤(z©”)╚╬Ą─┼õų├═Ļ╚½╩Ūę╗éĆ(g©©)į┌▓╗═¼Ūķą╬ųą╗∙ė┌Įø(j©®ng)“×(y©żn)Ą─š■▓▀║═╣½š²å¢Ņ}ĪŻ[12] ┴ĒėąīW(xu©”)š▀ät░čąĶę¬┐╝┴┐Ą─ę“╦žŠ▀¾w╗»Ż¼░³└©Ż║▒Ń└¹Śl╝■Ż╗ā╔įņ«ö(d©Īng)╩┬╚╦½@Ą├ūCō■(j©┤)Ą─ŽÓī”╚▌ęū│╠Č╚Ż╗šlŲŲē─┴╦Ę©┬╔ĻP(gu©Īn)ŽĄ¼F(xi©żn)ĀŅŻ╗į┌Š═╩┬īŹ(sh©¬)ĀÄūh³c(di©Żn)╚▒Ę”įVšłĪó╠ßūC║═šfĘ■Ą─ŪķørŽ┬Ż¼╩▓├┤┐╔─▄╩Ū╩┬īŹ(sh©¬)šµŽÓŻ╗«ö(d©Īng)╩┬╚╦╦∙ę└┘ćĄ─ĘŪ═¼ę╗░ŃĄ─ÖÓ(qu©ón)└¹šłŪ¾Ż╗ų„Åł╩Ūʱȩąį▒Ē╩÷Ą─▀Ć╩Ū┐ŽČ©ąį▒Ē╩÷Ą─Ż╗ėąĻP(gu©Īn)╩┬ĒŚ(xi©żng)╩Ūʱę²ŲųŲČ©Ę©ęÄ(gu©®)ät╗“ę╗░ŃęÄ(gu©®)ätĄ─└²═ŌŻ╗Ą╚Ą╚ĪŻ[13] ĪĪĪĪĪ░═ŲČ©Ī▒╩ŪĘų┼õ┼eūCž¤(z©”)╚╬Ą─┴Ēę╗╠ž╩Ōę└ō■(j©┤)ĪŻį┌ėó├└Ę©ŽĄć°╝ęŻ¼═ŲČ©ę╗į~Ą─▀\(y©┤n)ė├┐╔Ęų×ķā╔┤¾ŅÉŻ║▓╗╚▌Ę┤±gĄ─═ŲČ©(irrebuttable presumption)Ż╗┐╔Ę┤±gĄ─═ŲČ©(rebuttable presumption)ĪŻ║¾š▀ėųėą╩┬īŹ(sh©¬)═ŲČ©(presumption of fact)║═Ę©┬╔═ŲČ©(presumption of law)ā╔ĘNŪķą╬ĪŻį┌ėó├└Ę©īW(xu©”)š▀┐┤üĒŻ¼▓╗╚▌Ę┤±gĄ─═ŲČ©īŹ(sh©¬)ļH╔Ž╩Ūę╗ĒŚ(xi©żng)īŹ(sh©¬)¾wĘ©ęÄ(gu©®)ätŻ¼╝┤═ŲČ©Ą─Ūķą╬╩ŪĮ^ī”Ą─Ż¼¤ošō«ö(d©Īng)╩┬╚╦ū„│÷į§śėĄ─Ę┤±gŻ╗╚ńĪ░╚╬║╬╚╦Č╝ų¬ĢįĘ©┬╔Ī▒Ą─═ŲČ©Ż¼╝┤╩╣«ö(d©Īng)╩┬╚╦ūC├„Ųõ▓╗ų¬ĢįėąĻP(gu©Īn)Ą─Ę©┬╔Ż¼ę▓¤oØ·(j©¼)ė┌╩┬ĪŻ╩┬īŹ(sh©¬)═ŲČ©╩ŪĖ∙ō■(j©┤)▀ē▌ŗĪóĮø(j©®ng)“×(y©żn)Īó│ŻūR(sh©¬)║═ī”╔w╚╗ąįĄ─įu╣└Ż¼Å─ę╗éĆ(g©©)╩┬īŹ(sh©¬)ūCō■(j©┤)═ŲöÓ│÷┴Ēę╗éĆ(g©©)╩┬īŹ(sh©¬)Ą─┤µį┌Ż╗╦³▓óĘŪĘ©┬╔ęÄ(gu©®)Č©Ą─═ŲČ©Ż¼┼ŃīÅłF(tu©ón)╗“Ę©╣┘┐╔ęįū„┤╦═ŲČ©ę▓┐╔ęį▓╗ū„Ż╗▓╗▀^Ż¼ę╗éĆ(g©©)ÅŖ(qi©óng)ėą┴”Ą─╩┬īŹ(sh©¬)═ŲČ©┐╔ęįę²Ų┼eūCž¤(z©”)╚╬Ą─▐D(zhu©Żn)ęŲĪŻĘ©┬╔═ŲČ©╩ŪųĖ«ö(d©Īng)ę╗éĆ(g©©)╗∙ĄA(ch©│)╩┬īŹ(sh©¬)Ą├ęį┤_Č©Ģr(sh©¬)Ż¼į┌Ę©┬╔╔Ž╝┘įO(sh©©)═ŲČ©╩┬īŹ(sh©¬)▒ž╚╗┤µį┌Ż¼│²ĘŪėąŽÓĘ┤Ą─Ę┤±gūCō■(j©┤)Ż╗╚ńĪ░╦ŠĘ©ąą×ķ║═│╠ą“ęį╝░Ųõ╦¹š■Ė«ąą×ķ║═│╠ą“ęčĮø(j©®ng)Ą├ĄĮš²│ŻĄ─Īó║ŽĘ©Ą─ł╠(zh©¬)ąąĪ▒Š═╩Ūę╗éĆ(g©©)╣½šJ(r©©n)Ą─Ę©┬╔═ŲČ©Ż╗Ę©┬╔═ŲČ©Ą─ū„ė├į┌ė┌▐D(zhu©Żn)ęŲ╠ßūCž¤(z©”)╚╬Ż¼į┌śOéĆ(g©©)äeŪķą╬ųąŻ¼ę▓ėąų·ė┌▐D(zhu©Żn)ęŲšfĘ■ž¤(z©”)╚╬ĪŻ[14] ĪĪĪĪ┼eūCž¤(z©”)╚╬Ą─ĮŌ│²ś╦(bi©Īo)£╩(zh©│n) «ö(d©Īng)╩┬╚╦┬─ąą╠ßūCž¤(z©”)╚╬ų«║¾Ż¼▓ó▓╗ę╗Č©Š═─▄░čįōž¤(z©”)╚╬▐D(zhu©Żn)ęŲĮoī”ĘĮĪŻę▓Š═╩ŪšfŻ¼╚ń╣¹ę╗ĘĮ«ö(d©Īng)╩┬╚╦╠ß│÷│õūŃ(sufficient)ūCō■(j©┤)Ż¼įĮ▀^Ę©╣┘ĄĮ▀_(d©ó)┼ŃīÅłF(tu©ón)Ż¼ī”ĘĮ«ö(d©Īng)╩┬╚╦╝┤▒Ń▓╗╠ß│÷Ę┤ūCę▓▓╗ę╗Č©į┌─│╩┬īŹ(sh©¬)ĀÄūh³c(di©Żn)╔Žūįäė(d©░ng)öĪįVĪŻų╗ėą«ö(d©Īng)ūCō■(j©┤)▀_(d©ó)ĄĮĪ░ėą┴”║═┴Ņ╚╦ą┼Ę■Ī▒(cogent and compelling)Ą─│╠Č╚Ż¼▓óē║Ą╣ąįĄž╩╣ī”ĘĮ«ö(d©Īng)╩┬╚╦ų├ė┌┐╔─▄Ą─Ę©╣┘╝┤Ģr(sh©¬)▓├Č©ų«Ž┬Ż¼ī”ĘĮ«ö(d©Īng)╩┬╚╦▓╗╠ß│÷Ę┤ūCŠ═Ģ■(hu©¼)ūįäė(d©░ng)öĪįVĢr(sh©¬)Ż¼╠ßūCž¤(z©”)╚╬▓┼Ą├ĄĮ▐D(zhu©Żn)ęŲĪŻ[15] «ö(d©Īng)╚╗Ż¼╠ßūCž¤(z©”)╚╬Ą─▐D(zhu©Żn)ęŲ▀Ć┐╔─▄ę“═ŲČ©Ą─ą¦╣¹╦∙ų┬ĪŻ ĪĪĪĪį┌▓╗═¼Ą─įVįA▀^│╠ųąŻ¼šfĘ■ž¤(z©”)╚╬ĮŌ│²ś╦(bi©Īo)£╩(zh©│n)ėą▌^┤¾▓Ņ«ÉĪŻ├±╩┬įVįAĄ─ś╦(bi©Īo)£╩(zh©│n)╩ŪĪ░ā×(y©Łu)ä▌ūCō■(j©┤)Ī▒(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Ż¼╝┤╩┬īŹ(sh©¬)┐╔─▄╩Ū▀@śėĄ─Ż¼ūCō■(j©┤)╦∙Ę┤ė│Ą─╩┬īŹ(sh©¬)░l(f©Ī)╔·╔w╚╗ąį▓╗Ą═ė┌51%Ż¼ūCō■(j©┤)Ą─šµīŹ(sh©¬)┐╔─▄ąį┤¾ė┌╠ō╝┘┐╔─▄ąįĪŻą╠╩┬įVįAĄ─ś╦(bi©Īo)£╩(zh©│n)╩ŪĪ░┼┼│²║Ž└Ēæčę╔Ą─ūCō■(j©┤)Ī▒Ż¼╝┤╩┬īŹ(sh©¬)Äū║§┐ŽČ©╩Ū▀@śėĄ─Ż¼┐╔─▄ąįę▓įS│¼▀^90%ĪŻĮķė┌ā╔š▀ų«ķgĄ─ś╦(bi©Īo)£╩(zh©│n)╩ŪĪ░├„’@║═┴Ņ╚╦ą┼Ę■Ą─ūCō■(j©┤)Ī▒(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Ż¼╝┤╩┬īŹ(sh©¬)║▄┤¾┐╔─▄╩Ū▀@śėĄ─Ż¼įōś╦(bi©Īo)£╩(zh©│n)▀mė├ė┌─│ą®├±╩┬░Ė╝■Ą──│ą®╠ž╩ŌĀÄūh³c(di©Żn)ĪŻ[16] ĪĪĪĪĮĶĶb└ĒšōĄ─╝┘įO(sh©©)▀mė├Ż║ę╗éĆ(g©©)įć“×(y©żn) ĪĪĪĪ║åå╬╣┤└š¤oęįĖF▒Mėó├└Ę©ŽĄ┼eūCęÄ(gu©®)ät╝░Ųõ└ĒšōĄ─╝Ü(x©¼)╬óų«╠ÄŻ¼Ė³ļyęį╔µ╝░į┌ęÄ(gu©®)ät╝░└Ēšō▒│║¾▓óśŗ(g©░u)│╔Ųõ╗∙ĄA(ch©│)Ą─žSĖ╗Ą─Ę©┬╔īŹ(sh©¬)█`┼cé„Įy(t©»ng)Ż╗ęį╔ŽĖ┼╩÷ę▓═¼Ģr(sh©¬)ūŃęįūī╬ęéāÅŖ(qi©óng)┴ęĖą╩▄▀@ą®ęÄ(gu©®)ät╝░└Ēšō═¼ī”┐╣ųŲ┼c┼ŃīÅųŲįVįA│╠ą“Ą─¬Ü(d©▓)╠žī”æ¬(y©®ng)ąįĪŻę▓įSŻ¼šJ(r©©n)ų¬Ą─╚▒Ž▌ĪóęÄ(gu©®)ät╝░Ųõ└Ēšō╔·ķLŪķŠ│Ą─╠ž╩ŌąįŻ¼╩╝ĮK╩Ū╬ęéāĮĶ╦¹╔Įų«╩»╣źė±Ģr(sh©¬)╦∙├µ┼RĄ─ā╔éĆ(g©©)ļyŅ}ĪŻ▓╗▀^Ż¼▒Šų°╠Į╦„░l(f©Ī)š╣ų«┬Ęį┌▓╗öÓįć“×(y©żn)ųąčė╔ņĄ─└Ē─ŅŻ¼╬ęéā▓╗Ę┴į┌░Ė└²ųą▀M(j©¼n)ąą╝┘įO(sh©©)Ą─└Ēšō▀mė├Ż¼ęį╩╣ÖzėæĄ─╣żū„į┌Ė³×ķŠ▀¾wĄ─īė├µ╔Žš╣ķ_ĪŻ ī”▒Š░Ė▀M(j©¼n)ąąĘų╬÷ų«Ū░Ż¼ėą▒žę¬║åå╬šf├„╠ßūCž¤(z©”)╚╬ĪóšfĘ■ž¤(z©”)╚╬į┌╬ęć°╦∙Š▀ėąĄ─ęŌ┴xĪŻį┌ę╗éĆ(g©©)Ī░ĘŪ┼ŃīÅųŲĪ▒ [17]Ą─ąąš■įVįA│╠ą“ųąŻ¼╬ęéāĄ─Ę©╣┘╝╚╩Ū╩┬īŹ(sh©¬)å¢Ņ}Ą─▓├Č©š▀Ż¼ėų╩ŪĘ©┬╔å¢Ņ}Ą─▓├Č©š▀ĪŻš¦┐┤ŲüĒŻ¼ī”ė┌ėó├└Ę©ŽĄć°╝ęČ°čįū„ė├├„’@Ą─╠ßūCž¤(z©”)╚╬║═šfĘ■ž¤(z©”)╚╬ų«ĘųŻ¼╦Ų║§ĮĶĶbĄ─ŅA(y©┤)Ų┌╣”ą¦▓╗┤¾ĪŻ╣Pš▀ģsšJ(r©©n)×ķŲõęŌ┴xų┴╔┘┐╔ęį¾w¼F(xi©żn)į┌ā╔éĆ(g©©)ĘĮ├µĪŻŲõę╗Ż¼░č┼eūCž¤(z©”)╚╬ŚlĘų┐|╬÷Ż¼┐╔ęį▌^×ķ├„░ūĄž┤_Č©Ė„ĘĮ«ö(d©Īng)╩┬╚╦ŽÓæ¬(y©®ng)Ą─ūCō■(j©┤)ž¤(z©”)╚╬Ż¼▒▄├Ōž¤(z©”)╚╬Ą─Ų¼├µå╬ę╗╗»āAŽ“ĪŻ[18] ŲõČ■Ż¼░┤šš╠ßūCž¤(z©”)╚╬║═šfĘ■ž¤(z©”)╚╬Ą─įŁüĒęŌ┴xŻ¼ę▓įS┐╔ęįśŗ(g©░u)Žļę╗éĆ(g©©)═źīÅ─Ż╩ĮĪŻį┌Ę©═źš{(di©żo)▓ķļAČ╬Ż¼įŁĖµ║═▒╗ĖµČ╝▒žĒÜ×ķėą└¹ė┌ūį╝║Ą─╩┬īŹ(sh©¬)┬─ąą╠ßūCž¤(z©”)╚╬Ż¼Ę±ätŻ¼¤oĘ©▒ŻšŽĘ©╣┘ū„│÷ėą└¹Ą─╩┬īŹ(sh©¬)šJ(r©©n)Č©ĪŻ«ö(d©Īng)ę╗ĘĮ«ö(d©Īng)╩┬╚╦Š═─│éĆ(g©©)ĀÄūh³c(di©Żn)╠ß╣®ėą┴”║═┴Ņ╚╦ą┼Ę■Ą─ūCō■(j©┤)Ż¼Č°┴Ēę╗ĘĮ«ö(d©Īng)╩┬╚╦ø]ėąī”┤╦╠ß│÷Ę┤±gūCō■(j©┤)Ģr(sh©¬)Ż¼Ę©═ź┐╔ęįšJ(r©©n)Č©įōĀÄūh³c(di©Żn)ęč¤oąĶ▀M(j©¼n)ąąĘ©═ź▐qšōĪŻ«ö(d©Īng)ļpĘĮ«ö(d©Īng)╩┬╚╦Č╝ęčĮø(j©®ng)┬─ąą╠ßūCž¤(z©”)╚╬Ż¼Ūęø]ėąę╗ĘĮ╠ß│÷Ą─ūCō■(j©┤)Š▀ėąē║Ą╣ąįū„ė├Ģr(sh©¬)Ż¼īÅ└ĒŠ═┐╔ęį▀M(j©¼n)╚ļĘ©═ź▐qšōļAČ╬ĪŻĮø(j©®ng)▀^ŽÓ╗ź┘|(zh©¼)ūC▐qšōŻ¼Ę©═źūŅĮKį┌ū„│÷╩┬īŹ(sh©¬)šJ(r©©n)Č©ų«Ū░Ż¼┐╝æ]žō(f©┤)ėąšfĘ■ž¤(z©”)╚╬Ą─«ö(d©Īng)╩┬╚╦╩ŪʱęčĮø(j©®ng)▀_(d©ó)ĄĮšfĘ■Ą─ś╦(bi©Īo)£╩(zh©│n)ĪŻ Ė∙ō■(j©┤)ĪČć°╝ę┘rāöĘ©ĪĘĄ─ęÄ(gu©®)Č©Ż¼Ę©╣┘į┌┤_Č©ąąš■┘rāöž¤(z©”)╚╬Ģr(sh©¬)ąĶę¬┐╝æ]ęįŽ┬śŗ(g©░u)│╔ę¬╝■Ż║Ę©Č©Ą─┬Üäš(w©┤)ąą×ķų„¾wŻ╗┬Üäš(w©┤)▀`Ę©ąą×ķŻ╗ōp║”╩┬īŹ(sh©¬)Ż╗▀`Ę©ąą×ķ┼cōp║”╩┬īŹ(sh©¬)ų«ķgĄ─ę“╣¹ĻP(gu©Īn)ŽĄĪŻÅ─▒Š░Ė░l(f©Ī)╔·Įø(j©®ng)▀^║═ļpĘĮ«ö(d©Īng)╩┬╚╦Ą─ĀÄł╠(zh©¬)Ūķør┐┤Ż¼┼╔│÷╦∙╝░ŲõŠ»åT╩Ū▀mĖ±Ą─ąą×ķų„¾wĪó┼╔│÷╦∙╝░ŲõŠ»åT╩Ūį┌ł╠(zh©¬)ąąé„åŠ┬Üäš(w©┤)ų«Ģr(sh©¬)Īó£½▒╗é„åŠ║¾╦└═÷Ż¼▀@ą®╩Ū║┴¤o«ÉūhĄ─╩┬īŹ(sh©¬)ĪŻę“Č°Ż¼š²╚ń╔Ž╬─╦∙╩÷Ż¼ĀÄūh³c(di©Żn)╝»ųąį┌╣½░▓ÖC(j©®)ĻP(gu©Īn)ėąø]ėąīŹ(sh©¬)╩®▀`Ę©ąą×ķĪó▀`Ę©ąą×ķ(╚¶ėąĄ─įÆ)╩Ūʱų▒Įėī¦(d©Żo)ų┬£½Ą─╦└═÷ĪŻ ėąĘ±▀`Ę©ąą×ķ įŁĖµšJ(r©©n)×ķėą▀`Ę©ąą×ķĄ─└Ēė╔╩ŪŻ¼£½╦└Ū░░YĀŅĘ¹║ŽļŖŠ»╣„ļŖō¶║¾╠žš„Ż╗Č°▒╗Ėµ▓╗│ąšJ(r©©n)┼╔│÷╦∙Š»åTėą▀`Ę©ąą×ķĪŻßśī”▀@éĆ(g©©)ĀÄūh³c(di©Żn)Ż¼æ¬(y©®ng)įōė╔šlžō(f©┤)ō·(d©Īn)šfĘ■ž¤(z©”)╚╬─žŻ┐┤_īŹ(sh©¬)Ż¼š²╚ń▒Š░ĖĘ©╣┘╦∙čįŻ¼╣½░▓ÖC(j©®)ĻP(gu©Īn)Ą─ł╠(zh©¬)Ę©Łh(hu©ón)Š│╩Ū╠ž╩ŌĄ─Ż¼│²╣½░▓╚╦åT║═╦└š▀═ŌŻ¼¤oĄ┌╚²╚╦į┌ł÷ĪŻ╚ń╣¹ę¬įŁĖµ╠ß│÷ĘŪ│Ż┤_ĶÅĄ─▀`Ę©ąą×ķūCō■(j©┤)Ż¼ī”įŁĖµ╩Ū▓╗╣½ŲĮĄ─ĪŻ┐╔╩ŪŻ¼▀@éĆ(g©©)ī”░Ė╝■╠ž╩ŌŪķŠ│Ą─š■▓▀ąį┐╝æ]Ī¬Ī¬ų¦│ųė╔▒╗Ėµžō(f©┤)ō·(d©Īn)┼eūCž¤(z©”)╚╬Ż¼▀Ć▓╗ūŃęįē║Ą╣┴Ē═Ōę╗éĆ(g©©)╗∙ė┌ę╗░Ń│Ż└ĒĄ─┐╝æ]Ż¼Č°║¾š▀ätų¦│ųė╔įŁĖµžō(f©┤)ō·(d©Īn)┼eūCž¤(z©”)╚╬ĪŻ ĪĪĪĪ╬ęéāų¬Ą└Ż¼ūCō■(j©┤)╩Ū╝╚═∙░l(f©Ī)╔·ų«╩┬īŹ(sh©¬)į┌«ö(d©Īng)Ģr(sh©¬)ŪķŠ│ųą┴¶Ž┬Ą─║██EŻ¼æ{ĮĶ▀@ą®║██EŻ¼╬ęéā┐╔ęį═ŲöÓ╩┬īŹ(sh©¬)░l(f©Ī)╔·Ą─╔w╚╗ąįĪŻ«ö(d©Īng)ę╗ĘĮų„Åł?zh©¬)žČ©╩┬ī?sh©¬)░l(f©Ī)╔·▀^Ż¼Č°┴Ēę╗ĘĮų„Åłø]ėą░l(f©Ī)╔·Ģr(sh©¬)Ż¼╝┘╚ńūī║¾š▀╠ß╣®Ī░╩┬īŹ(sh©¬)ø]ėą░l(f©Ī)╔·Ī▒Ą─ūCō■(j©┤)Ż¼╦Ų║§ÅŖ(qi©óng)╚╦╦∙ļyĪŻ▒╚ššé∙äš(w©┤)╝m╝ŖŻ¼é∙ÖÓ(qu©ón)╚╦ų„Åłé∙äš(w©┤)╚╦ø]ėą░┤Ų┌āö▀ĆŪĘ┐ŅŻ¼Č°é∙äš(w©┤)╚╦ų„ÅłęčĮø(j©®ng)āö▀ĆŻ¼Ę©į║╩Ūę¬Ū¾é∙ÖÓ(qu©ón)╚╦│ąō·(d©Īn)šfĘ■ž¤(z©”)╚╬▀Ć╩Ūę¬Ū¾é∙äš(w©┤)╚╦│ąō·(d©Īn)Ż┐ę╗░ŃŪķørŽ┬Ż¼┤░Ė║▄┐╔─▄āAŽ“ė┌é∙äš(w©┤)╚╦Ż¼ę“?y©żn)ķ╦¹┐╔ęį╠ß╣®ģR┐Ņå╬ĪóŃyąą▐D(zhu©Żn)ÄżūC├„Ą╚ĪŻį┘▒╚ššąąš■┴P┐ŅĪóŠą┴¶Ą╚░Ė╝■Ż¼įŁĖµ▒žĒÜūC├„Š▀¾wąąš■ąą×ķĄ─┤µį┌║═▀`Ę©ąįŻ║ī”Š▀¾wąąš■ąą×ķ╩Ūʱ┤µį┌▀@ę╗å¢Ņ}Ż¼æ¬(y©®ng)įōė╔įŁĖµžō(f©┤)ž¤(z©”)šfĘ■Ę©╣┘Ż¼[19]╝┘╚ń▒╗ĖµĖ∙▒Šø]ėąū„│÷┴P┐Ņ╗“Šą┴¶Ż¼Č°įŁĖµģsų„ÅłėąŻ¼[20] ę¬Ū¾▒╗Ėµžō(f©┤)ō·(d©Īn)šfĘ■ž¤(z©”)╚╬Ż¼╦Ų║§ėąŃŻ│Ż└ĒŻ╗Č°ī”Š▀¾wąąš■ąą×ķ╩Ūʱ▀`Ę©å¢Ņ}Ż¼įŁĖµ│ąō·(d©Īn)╠ßūCž¤(z©”)╚╬▓óļSĢr(sh©¬)┐╔└¹ė├ę╗Č©ūCō■(j©┤)īóž¤(z©”)╚╬▐D(zhu©Żn)ęŲĮoī”ĘĮŻ¼Č°▒╗Ėµ│ąō·(d©Īn)šfĘ■ž¤(z©”)╚╬Ż¼▀@╝╚Ę¹║Ž│╔╬─Ę©ęÄ(gu©®)Č©Ż¼ėų▓╗╩¦╣½š²ĪŻ╦∙ęįŻ¼į┌▒Š░ĖųąŻ¼╝╚╚╗įŁĖµ╠ß│÷╣½░▓ÖC(j©®)ĻP(gu©Īn)ėą▀`Ę©ąą×ķ┤µį┌Ż¼Č°▒╗Ėµ╣½░▓▓┐ķT╩Ė┐┌ʱšJ(r©©n)ėą┤╦╩┬īŹ(sh©¬)Ż¼─Ū├┤Ż¼įŁĖµæ¬(y©®ng)įōŠ═╣½░▓▀`Ę©ąą×ķ┤_īŹ(sh©¬)┤µį┌▀@ę╗╩┬īŹ(sh©¬)ų„Åłžō(f©┤)ō·(d©Īn)šfĘ■ž¤(z©”)╚╬ĪŻ ĪĪĪĪ╩Ū▓╗╩ŪįŁĖµŠ═▀@éĆ(g©©)ĀÄūh³c(di©Żn)│ąō·(d©Īn)šfĘ■ž¤(z©”)╚╬Ż¼Š═Ģ■(hu©¼)╠Äė┌śO×ķ▓╗└¹Ą─Š│Ąž─žŻ┐[21] ▓óĘŪ╚ń┤╦ĪŻ▒Š░ĖįŁĖµįćłDęį£½╦└Ū░Ą─░YĀŅüĒšfĘ■Ę©╣┘Ż¼Ą½Å─Ę©╣┘Ą─═Ų└Ēųą(Ī░▓╗─▄å╬æ{£½╦└Ū░Ą─ĘNĘN░YĀŅĪ▒)Ż¼┐╔ęį┐┤│÷▀@éĆ(g©©)ūCō■(j©┤)¤oĘ©ØMūŃĮŌ│²šfĘ■ž¤(z©”)╚╬Ą─ś╦(bi©Īo)£╩(zh©│n)ĪŻ▓╗▀^Ż¼╝┘įO(sh©©)įŁĖµį┌═źīÅųą╠ß│÷Ż║Ī░ę¬▓ķŪÕ▒╗Ėµėąø]ėą▀`Ę©ąą×ķŻ¼╬©ę╗═ŠÅĮ╩Ū▀M(j©¼n)ąą╩¼ÖzĪŻČ°▒╗Ėµ¤oęĢ╬ęéāĄ─ę╗į┘ę¬Ū¾╝░ŲõĘ©Č©Ą─╩¼Öz┬Üž¤(z©”)Ż¼▓╗▀M(j©¼n)ąą╩¼ÖzŠ═ž¤(z©”)┴Ņ╬ęéāīó╩¼¾w╗╗»ĪŻ▀@ļyĄ└▓╗─▄▒Ē├„▒╗Ėµ║”┼┬╩¼ÖzĪó║”┼┬╩¼ÖzĮY(ji©”)╣¹Įę┬ČŲõ▀`Ę©╩┬īŹ(sh©¬)Ż┐ļyĄ└╬ęéā▓╗─▄ė╔┤╦═ŲČ©Ųõėą▀`Ę©ąą×ķå߯┐Ī▒▀@Š═╠ß│÷┴╦╩┬īŹ(sh©¬)═ŲČ©å¢Ņ}(▓óĘŪĘ©┬╔═ŲČ©Ż¼ę“?y©żn)ķ╗∙ė┌Į?j©®ng)“×(y©żn)Īó│ŻūR(sh©¬))ĪŻī”ė┌ę╗éĆ(g©©)ėą└ĒąįĄ─╚╦Č°čįŻ¼▀@éĆ(g©©)╩┬īŹ(sh©¬)═ŲČ©Ą─╔w╚╗ąį╦Ų║§▀h(yu©Żn)▀h(yu©Żn)│¼│÷50%Ż¼╔§ų┴┐╔ęį▀_(d©ó)ĄĮ80Ī½90%ĪŻ─Ū├┤Ż¼Ę©╣┘═Ļ╚½┐╔ęįšJ(r©©n)Č©įŁĖµĄ─šfĘ■ž¤(z©”)╚╬ęčĮø(j©®ng)▀_(d©ó)ĄĮĮŌ│²ś╦(bi©Īo)£╩(zh©│n)Ż¼▓óŪęŻ¼šfĘ■ž¤(z©”)╚╬ė╔┤╦▐D(zhu©Żn)ęŲĄĮ▒╗Ėµ╔Ē╔ŽĪŻ▓╗▀^Ż¼┤╦Ģr(sh©¬)▒╗Ėµ▓╗╩Ū꬚fĘ■Ę©╣┘Ųõø]ėą▀`Ę©ąą×ķŻ¼Č°╩Ūꬎ“Ę©╣┘ūC├„Ųõ▓╗▀M(j©¼n)ąą╩¼ÖzŠ═ž¤(z©”)┴Ņ╗╗»Ą─ąą×ķ╩ŪėąŽÓ«ö(d©Īng)│õūŃų«└Ēė╔Ą─ĪŻ╚ń╣¹▒╗Ėµ▓╗─▄║▄║├┬─ąąšfĘ■ž¤(z©”)╚╬Ż¼Š═Ųõ×ķ╩▓├┤▓╗▀M(j©¼n)ąą╩¼Öz╠ß│÷ėąšfĘ■┴”Ą─Ę┤±gūCō■(j©┤)Ż¼Ę©╣┘Š═Ģ■(hu©¼)ū„│÷ėą└¹ė┌įŁĖµĄ─ę╗ĘN╩┬īŹ(sh©¬)šJ(r©©n)Č©(┤_ŪąĄžšf╩Ū═ŲČ©)Ż¼╝┤▀`Ę©ąą×ķ┤µį┌ĪŻ ▀`Ę©ąą×ķ╩Ūʱī¦(d©Żo)ų┬£½╦└═÷Ą─įŁę“ ╝╚╚╗įŁĖµ┐╔ęį═©▀^╩┬īŹ(sh©¬)═ŲČ©ĮŌ│²šfĘ■ž¤(z©”)╚╬Ż¼┤┘╩╣Ę©╣┘šJ(r©©n)Č©▀`Ę©ąą×ķ┤µį┌Ż¼ĮėŽ┬üĒĄ─ĀÄūh³c(di©Żn)Š═į┌ė┌═ŲČ©Ą─▀`Ę©ąą×ķ(¤ošō╩Ū║╬ĘNąą×ķ)┼c£½╦└═÷╩┬īŹ(sh©¬)Ą─ę“╣¹ĻP(gu©Īn)ŽĄĪŻŠ═▀@éĆ(g©©)ĀÄūh³c(di©Żn)Ż¼ėųįōė╔šl│ąō·(d©Īn)šfĘ■ž¤(z©”)╚╬─žŻ┐Ė∙ō■(j©┤)▒Š░ĖĄ─╠žČ©Ūķą╬Ż¼╚ń═¼ę¬▓ķ├„▀`Ę©ąą×ķ╩Ūʱ┤µį┌ę└┘ćė┌╩¼Özę╗śėŻ¼▀`Ę©ąą×ķ┼c£½╦└═÷╩┬īŹ(sh©¬)Ą─ę“╣¹ĻP(gu©Īn)ŽĄę▓╚ĪøQė┌╩¼ÖzĪŻ▀@└’Š═╔µ╝░«ö(d©Īng)╩┬╚╦Ą─┼eūC─▄┴”ĪŻī”ė┌įŁĖµČ°čįŻ¼╦¹▓ó▓╗Š▀éõ▀M(j©¼n)ąą╩¼ÖzĄ─īŻķT╝╝ąg(sh©┤)║═ų¬ūR(sh©¬)Ż¼╩¼Özėų╩Ū╣½░▓ÖC(j©®)ĻP(gu©Īn)Ą─Ę©Č©┬Üž¤(z©”)Ż╗│²ĘŪ▒╗Ėµū„│÷╩¼Özł¾(b©żo)ĖµŻ¼įŁĖµÄū║§ø]ėą─▄┴”▓ķŪÕ£½╦└═÷Ą─ų▒ĮėįŁę“Š═╩Ū▒╗ĖµĄ─▀`Ę©ąą×ķĪŻė╔ė┌▀@ę╗ę“╦ž╦∙Š▀ėąĄ─øQČ©ąįū„ė├Ż¼į┌ōp║”╩┬īŹ(sh©¬)┼c▀`Ę©ąą×ķę“╣¹ĻP(gu©Īn)ŽĄ▀@éĆ(g©©)ĀÄūh³c(di©Żn)╔ŽŻ¼æ¬(y©®ng)«ö(d©Īng)ė╔▒╗Ėµ│ąō·(d©Īn)šfĘ■ž¤(z©”)╚╬ĪŻ ę▓įSĢ■(hu©¼)ėą▀@śėĄ─ę╔å¢Ż║╝╚╚╗ā╔éĆ(g©©)ĀÄūh³c(di©Żn)Č╝╚ĪøQė┌╩¼ÖzŻ¼×ķ╩▓├┤į┌šfĘ■ž¤(z©”)╚╬Ą─Ęų┼õĘĮ├µėą▓Ņ«É─žŻ┐æ¬(y©®ng)įō┐┤ĄĮŻ¼┼cŪ░ę╗éĆ(g©©)ĀÄūh³c(di©Żn)▓╗═¼ų«╠Äį┌ė┌Ż¼╚ń╣¹▒╗Ėµų„Åł£½Ą─╦└═÷┼c▀`Ę©ąą×ķ¤oĻP(gu©Īn)Ż¼[22]─Ū├┤Ż¼▒╗Ėµ┐╔ęį═©▀^╩¼Öz▓ķ│÷ī¦(d©Żo)ų┬£½╦└═÷Ą─šµš²įŁę“(─│ĘN═╗░l(f©Ī)ąį╝▓▓Ī)ĪŻę▓Š═╩ŪšfŻ¼─│ĘN═╗░l(f©Ī)ąį╝▓▓Ī╩Ū┐╔─▄░l(f©Ī)╔·Ą─╩┬īŹ(sh©¬)Ż¼æ{ĮĶī”Ųõ┴¶Ž┬Ą─║██E▀M(j©¼n)ąąÖz“×(y©żn)Ż¼▒╗Ėµ┐╔ęį╠ß│÷ūCō■(j©┤)šf├„įō╩┬īŹ(sh©¬)░l(f©Ī)╔·Ą─╔w╚╗ąįśO┤¾Ż¼Å─Č°ĮŌ│²šfĘ■ž¤(z©”)╚╬ĪŻČ°į┌Ū░ę╗éĆ(g©©)ĀÄūh³c(di©Żn)╔ŽŻ¼▒╗Ėµų„ÅłĄ─╩Ūø]ėąīŹ(sh©¬)╩®▀`Ę©ąą×ķĪŻ¤ošōī”ė┌──ę╗ĘĮ«ö(d©Īng)╩┬╚╦Č°čįŻ¼ļyęįŽļŽ¾ąĶę¬╩▓├┤śėĄ─ūCō■(j©┤)üĒšfĘ■Ę©╣┘┤_ą┼ę╗éĆ(g©©)╩┬īŹ(sh©¬)ø]ėą░l(f©Ī)╔·Ą─╔w╚╗ąįśO┤¾ĪŻ ĪĪĪĪė╔ė┌▒Š░Ėųą▒╗Ėµø]ėąęįā×(y©Łu)ä▌ūCō■(j©┤)╗“├„’@║═┴Ņ╚╦ą┼Ę■Ą─ūCō■(j©┤)Ż¼šfĘ■Ę©╣┘ŽÓą┼£½╦└═÷ŽĄŲõ╦¹įŁę“Č°ĘŪ▀`Ę©ąą×ķ╦∙ų┬Ż¼╦∙ęįŻ¼Ųõ▒ž╚╗ę¬│ąō·(d©Īn)öĪįV║¾╣¹ĪŻ▓╗▀^Ż¼į┌Ą┌ę╗éĆ(g©©)ĀÄūh³c(di©Żn)╔ŽŻ¼╩┬īŹ(sh©¬)═ŲČ©Ą─╔w╚╗ąįśO┤¾(ę▓ę“┤╦ĮŌ│²įŁĖµšfĘ■ž¤(z©”)╚╬)Ż¼Ą½╚ń╣¹ęį▒╗Ėµ╬┤▀M(j©¼n)ąą╩¼Öz×ķė╔üĒ═ŲČ©▀`Ę©ąą×ķ╩Ūī¦(d©Żo)ų┬£½╦└═÷Ą─ų▒ĮėįŁę“Ż¼Ųõ╔w╚╗ąįätę¬┤¾┤“š█┐█ĪŻę“?y©żn)ķŻ¼š\╚ńĘ©╣┘╦∙═Ų└ĒĄ─Ż¼═╗░l(f©Ī)ąį╝▓▓ĪĄ─╔w╚╗ąįę▓┤µį┌ĪŻė┌╩ŪŻ¼Ę©╣┘į┌┼ąČ©▒╗Ėµ▒žĒÜ│ąō·(d©Īn)┘rāöž¤(z©”)╚╬Ą─═¼Ģr(sh©¬)Ż¼ėųū├Ūķ£p╔┘┴╦┘rāööĄ(sh©┤)Ņ~Ż¼▀@éĆ(g©©)▓├┼ą╩Ū║Ž║§└ĒąįĄ─ĪŻ ęį╔ŽĄ─įć“×(y©żn)┐╔ęįį┌─│ĘN│╠Č╚╔ŽĘ┤ė││÷Ż¼▒M╣▄Ęų╬÷Ą─ĮY(ji©”)šō┼c▒Š░ĖĘ©╣┘Ą─ĮY(ji©”)šōĮėĮ³ę╗ų┬Ż¼Ą½═Ų└Ē▀^│╠ė╚Ųõ╩Ūį┌Ęų┼õ┼eūCž¤(z©”)╚╬ĘĮ├µĄ─═Ų└Ēėąų°▌^┤¾ģ^(q©▒)äeĪŻÖzėæĄ─╗∙▒Šę¬┴xį┌ė┌šf├„Ż¼┼eūCž¤(z©”)╚╬Ą─Ęų┼õąĶę¬Ę©╣┘ßśī”Š▀¾wĀÄūh³c(di©Żn)Īó┐╝┴┐ČÓĘNę“╦žüĒ═Ļ│╔Ż¼Ūą▓╗┐╔═©▀^ĮŌßī│╔╬─Ę©ęÄ(gu©®)Č©üĒäō(chu©żng)įO(sh©©)å╬ę╗╣╠Č©─Ż╩Į▓óŠą─Óė┌ŲõųąŻ¼ę▓äš(w©┤)▒ž▒▄├Ō╩▄─│ĘNČ©╬╗ė┌å╬ę╗╣╠Č©─Ż╩ĮĄ─īW(xu©”)└ĒĮŌßīĄ─Į¹ÕdĪŻĶbė┌╬ęć°ęį│╔╬─Ę©×ķų„ę¬╠žš„Ż¼Ę©╣┘ėųŅHČÓĘ©Ślų„┴xāAŽ“Ż¼╦∙ęįŻ¼Ė³×ķžSĖ╗Ą─Özėæī”ė┌┴óĘ©ę▓ėą┤┘▀M(j©¼n)ū„ė├ĪŻ[23] ĪĪĪĪąąš■įVįA┼eūCž¤(z©”)╚╬Ż║šlų„Åłšl┼eūCåß ĪĪĪĪ«ö(d©Īng)Ū░Ż¼į┌īW(xu©”)└ĒŅI(l©½ng)ė“ā╚(n©©i)Ż¼ĻP(gu©Īn)ė┌ąąš■įVįA┼eūCž¤(z©”)╚╬┼cĪ░šlų„ÅłŻ¼šl┼eūCĪ▒įŁätų«ķgĻP(gu©Īn)ŽĄĄ─│ķŽ¾ėæšōŻ¼┐╔─▄Ģ■(hu©¼)│╔×ķūĶĄK╬ęéā░l(f©Ī)š╣┼eūCęÄ(gu©®)ät╝░└ĒšōĄ─ę╗éĆ(g©©)ųžę¬ę“╦žĪŻėąīW(xu©”)š▀ųĖ│÷Ż¼į┌▀@éĆ(g©©)å¢Ņ}╔ŽŻ¼ų„ę¬ėą╚²ĘNė^³c(di©Żn)ĪŻĄ┌ę╗ĘNė^³c(di©Żn)╩Ūų„ī¦(d©Żo)ė^³c(di©Żn)Ż¼╝┤į┌ąąš■įVįAųąĪ░▒╗Ėµžō(f©┤)┼eūCž¤(z©”)╚╬Ī▒Ż╗Ą┌Č■ĘNė^³c(di©Żn)šJ(r©©n)×ķ▒╗Ėµų╗ī”Ųõū„│÷Ą─Š▀¾wąąš■ąą×ķ║ŽĘ©ąįžō(f©┤)┼eūCž¤(z©”)╚╬Ż¼Ųõ╦¹å¢Ņ}╚į▓╔╚ĪĪ░šlų„ÅłŻ¼šl┼eūCĪ▒įŁätŻ╗Ą┌╚²ĘNė^³c(di©Żn)ätšJ(r©©n)Č©ąąš■įVįA┼eūCž¤(z©”)╚╬╩ŪĪ░šlų„ÅłŻ¼šl┼eūCĪ▒ę╗░ŃįŁätį┌ąąš■įVįAųąĄ─¾w¼F(xi©żn)ĪŻ[24] į┌┤╦ī”Ą┌╚²ĘNė^³c(di©Żn)ū„ę╗įuār(ji©ż)Ż¼ęį▀M(j©¼n)ę╗▓ĮĻU├„▒Š╬─Ą─ų„ų╝ĪŻ ĪĪĪĪ×ķ╩▓├┤╩ŪĪ░šlų„ÅłŻ¼šl┼eūCĪ▒ Ą┌╚²ĘNė^³c(di©Żn)╩ūŽ╚┼·įuĪ░ąąš■įVįAųą▒╗Ėµžō(f©┤)┼eūCž¤(z©”)╚╬Ī▒Ą─ė^³c(di©Żn)╩ŪŲ¼├µĄ─Ż¼Ųõ└Ēė╔╚ńŽ┬Ż║1.ĪČąąš■įVįAĘ©ĪĘ▓ó╬┤ęÄ(gu©®)Č©ąąš■ÖC(j©®)ĻP(gu©Īn)æ¬(y©®ng)ī”Ųõ▓╗ū„×ķžō(f©┤)┼eūCž¤(z©”)╚╬Ż╗2.▒╗Ėµ×ķŲõŠ▀¾wąąš■ąą×ķ┼eūC▀_(d©ó)ĄĮę╗Č©│╠Č╚ų«║¾Ż¼įŁĖµ▀Ć╩Ū꬞ō(f©┤)┼eūCž¤(z©”)╚╬Ż¼Ę±ätų╗─▄╩ŪöĪįVŻ¼įVįAųą┼eūCž¤(z©”)╚╬į┌ļpĘĮ«ö(d©Īng)╩┬╚╦ų«ķgĄ─▐D(zhu©Żn)ęŲ▓╗╚▌ʱȩŻ╗3.ąąš■░Ė╝■┴ó░Ėų«Ū░Ż¼ąąš■ŽÓī”╚╦▒žĒÜžō(f©┤)ūC├„ŲõĘ¹║Žę╗Č©│╠ą“ę¬╝■ų«┼eūCž¤(z©”)╚╬Ż¼Ę±ätŻ¼įŁĖµ▒ž╚╗▒╗▓├Č©±g╗žŲįV╗“┼ąøQ±g╗žįVįAšłŪ¾Ż╗4.ąąš■┘rāöįVįAųąŻ¼įŁĖµ╚ń▓╗┼eūCŻ¼ų╗─▄╩ŪöĪįVĪŻ ĪĪĪĪ─Ū├┤Ż¼╩Ūʱ┐╔ęį░čĪČąąš■įVįAĘ©ĪĘĄ─ęÄ(gu©®)Č©ĮŌßī×ķŻ║▒╗Ėµī”Š▀¾wąąš■ąą×ķ║ŽĘ©ąįžō(f©┤)┼eūCž¤(z©”)╚╬╩ŪĪ░šlų„ÅłŻ¼šl┼eūCĪ▒Ą─Ą╣ų├Ż¼Č°Ųõ╦¹å¢Ņ}╚įū±čŁ▀@ę╗įŁät─žŻ┐Ą┌╚²ĘNė^³c(di©Żn)Ą─┤░Ė╩ŪʱȩĄ─ĪŻę“?y©żn)ķŻ¼Ī░į┌ī”▒╗Ėµū„│÷Ą─Š▀¾wąąš■ąą×ķ╠ßŲąąš■įVįA░Ė╝■ųąŻ¼ŲįVļm╚╗ė╔ąąš■ŽÓī”╚╦╠ßŲŻ¼Ą½Ę©į║ę¬īÅ▓ķĄ─ģs▓╗╩Ūąąš■ŽÓī”╚╦ąą×ķĄ─║ŽĘ©ąįŻ¼Č°╩ŪŠ▀¾wąąš■ąą×ķĄ─║ŽĘ©ąįĪŻČ°Š▀¾wąąš■ąą×ķ╩Ūė╔▒╗Ėµū„│÷Ą─Ż¼╩Ū▒╗ĖµĪ«ų„ÅłĪ»Ą─═Ōį┌▒Ē¼F(xi©żn)ą╬╩ĮŻ¼ė╔▒╗Ėµ×ķų«┼eūCš²╩ŪĪ«šlų„ÅłŻ¼šl┼eūCĪ»Ą─ę╗░Ń┼eūCįŁätĄ─¾w¼F(xi©żn)ĪŻĪ▒ąąš■ĀÄūh┼c├±╩┬ĀÄūh▓╗═¼ĪŻ├±╩┬ĀÄūhųąŻ¼ų„ÅłīŹ(sh©¬)¾wšłŪ¾Ą─ę╗ĘĮ╚¶▒╗ī”ĘĮŠ▄Į^Ż¼ų╗─▄╠ßŲ├±╩┬įVįAŻ╗į┌įVįAųąŻ¼┼eūCž¤(z©”)╚╬ūŅ│§æ¬(y©®ng)ė╔īŹ(sh©¬)¾wšłŪ¾Ą─ų„ÅłĘĮ│ąō·(d©Īn)Ż¼▒╗ų„ÅłĘĮ╠ß│÷Ą─╩Ūī”ų„ÅłĘĮīŹ(sh©¬)¾wšłŪ¾Ą─┐╣▐qŻ¼┤╦Ģr(sh©¬)▓╗│ąō·(d©Īn)┼eūCž¤(z©”)╚╬ĪŻąąš■ĀÄūhųąŻ¼╚¶īŹ(sh©¬)¾wšłŪ¾ė╔ąąš■ŽÓī”╚╦╠ßŲ(░³└©╔Ļšłąąš■ÖC(j©®)ĻP(gu©Īn)ū„×ķ║═ę¬Ū¾ąąš■┘rāö)Ż¼ätŪķør═¼ė┌├±╩┬įVįAŻ╗╚¶īŹ(sh©¬)¾wšłŪ¾ė╔ąąš■ÖC(j©®)ĻP(gu©Īn)╠ßŲŻ¼ąąš■ÖC(j©®)ĻP(gu©Īn)┐╔ūįąąīŹ(sh©¬)¼F(xi©żn)ŲõīŹ(sh©¬)¾wų„ÅłĪŻį┌ąąš■įVįAųąŻ¼įŁĖµīŹ(sh©¬)┘|(zh©¼)╔Ž╩Ūī”▒╗Ėµį┌ąąš■ĀÄūhųą╠ß│÷Ą─īŹ(sh©¬)¾wšłŪ¾Ą─┐╣▐qŻ¼▒╗Ėµæ¬(y©®ng)╩ūŽ╚×ķŲõīŹ(sh©¬)¾wšłŪ¾┼eūCŻ¼Š▀¾wąąš■ąą×ķ▒ŠüĒŠ═╩Ūąąš■ÖC(j©®)ĻP(gu©Īn)Ą─ų„ÅłĪŻ[25] ĪĪĪĪ╩Ūʱ┐╔ęį│¼įĮ║åå╬╗»Ą─Č©ąįėæšō ęį╔Ž└ĒšōĮĶĶb╝░╝┘įO(sh©©)Ą─▀mė├ęčĮø(j©®ng)▒Ē├„Ż¼Ī░ąąš■įVįAųą▒╗Ėµžō(f©┤)┼eūCž¤(z©”)╚╬Ī▒Ą─ė^³c(di©Żn)┤_īŹ(sh©¬)╩ŪŲ¼├µĄ─Ż¼Ą½┼c╔Ž╩÷Ą┌╚²ĘNė^³c(di©Żn)Ą─šōūC▀^│╠▓╗═¼Ż¼▒Š╬─Ė³āAŽ“ė┌ßśī”Š▀¾wĀÄūh³c(di©Żn)Ą─Š▀¾wĘų╬÷ĪŻ╚ń╣¹ł╠(zh©¬)ų°ė┌║åå╬╗»Ą─Č©ąįėæšōŻ¼Š═┐╔─▄║÷ęĢīŹ(sh©¬)äš(w©┤)Įń╦∙├µ┼RĄ─ųT░ŃéĆ(g©©)ąį╗»Ą─Š▀¾wŪķŠ│ĪŻ└²╚ńŻ¼Ą┌╚²ĘNė^³c(di©Żn)ęįąąš■┘rāöįVįAųąįŁĖµžō(f©┤)┼eūCž¤(z©”)╚╬×ķė╔Ż¼┼·įuå╬ę╗Ą─▒╗Ėµžō(f©┤)┼eūCž¤(z©”)╚╬─Ż╩ĮĪŻ┐╔╩ŪŻ¼š²╚ńŪ░╬─Š▀¾wĘų╬÷╦∙╩ŠŻ¼ąąš■┘rāöįVįAųąįŁĖµ║═▒╗ĖµČ╝┐╔─▄žō(f©┤)ō·(d©Īn)šfĘ■ž¤(z©”)╚╬ĪŻ ĪĪĪĪĄ┌╚²ĘNė^³c(di©Żn)░čąąš■╣▄└Ē▀^│╠║═ąąš■įVįA▀^│╠┬ō(li©ón)ŽĄŲüĒŻ¼ū„×ķĘų┼õąąš■įVįA┼eūCž¤(z©”)╚╬Ą─╗∙ĄA(ch©│)Ż¼Ą─┤_ėąŲõ¬Ü(d©▓)ĄĮĄ─ęŌ┴xĪŻ▓╗▀^Ż¼ęį×ķį┌ąąš■╣▄└Ē▀^│╠ųą╩Ūąąš■ÖC(j©®)ĻP(gu©Īn)ų„Åł▓óūįąąīŹ(sh©¬)¼F(xi©żn)Š▀¾wąąš■ąą×ķŻ¼ąąš■ÖC(j©®)ĻP(gu©Īn)į┌ū„│÷Š▀¾wąąš■ąą×ķĢr(sh©¬)žō(f©┤)ž¤(z©”)┼eūCŻ¼ę“Č°į┌ąąš■įVįAųąĄ─ų„ÅłĘĮ║═┼eūCĘĮŠ═╩Ūąąš■ÖC(j©®)ĻP(gu©Īn)Ż¼▀@śėĄ─šōūCę▓ėą║åå╬╗»Ą─āAŽ“ĪŻ ĪĪĪĪ╩ūŽ╚Ż¼į┌ąąš■│╠ą“ųąŻ¼▓óĘŪ│²┴╦╔Ļšłąąš■ÖC(j©®)ĻP(gu©Īn)ū„×ķ║═ę¬Ū¾ąąš■┘rāöų«═ŌĄ─Ūķą╬Č╝╩Ūė╔ąąš■ÖC(j©®)ĻP(gu©Īn)žō(f©┤)ō·(d©Īn)šfĘ■ž¤(z©”)╚╬ĪŻ▀@┐╔ęįģó┐╝ę╗Ž┬├└ć°Ę©į║Ą─┼ą└²ĪŻĪ░═¼śėŻ¼į┌ę╗éĆ(g©©)Ā┐╔µā╚(n©©i)ĻæĄVł÷▀\(y©┤n)ĀI╔ĻįV╬»åTĢ■(hu©¼)Ą─░Ė╝■ųąŻ¼įōąąš■ÖC(j©®)ĻP(gu©Īn)žō(f©┤)ž¤(z©”)╠ß╣®▒Ē├µ╔Ž┤_ĶÅĄ─ūCō■(j©┤)Ż¼üĒūC├„ęį▓╗░▓╚½▀\(y©┤n)ĀI×ķė╔Ž┬┴Ņę╗╝ę├║ĄV═ŻśI(y©©)╩Ū║Ž└ĒĄ─Ż¼Ą½╩ŪŻ¼ūC├„├║ĄV▀\(y©┤n)ĀI╩Ū░▓╚½Ą─ž¤(z©”)╚╬ätė╔śI(y©©)ų„│ąō·(d©Īn)ĪŻį┌┤╦░ĖųąŻ¼Ę©į║Ą─▓┐Ęų═Ų└Ē╩ŪŻ║įō├║ĄVśI(y©©)ų„ūŅ╩ņŽż├║ĄVĄ─▀\(y©┤n)ĀIĀŅørŻ¼į┌Ž±▀@śėĄ─░Ė╝■ųąŻ¼ī”╩┬īŹ(sh©¬)ėą╠ž╩Ō┴╦ĮŌĄ─╚╦žō(f©┤)ō·(d©Īn)┼eūCž¤(z©”)╚╬╩Ū▀m«ö(d©Īng)?sh©┤)─ĪŻĪ▒[26] ĪĪĪĪŲõ┤╬Ż¼ąąš■╣▄└Ē▀^│╠║═ąąš■įVįA▀^│╠į┌ŽÓ«ö(d©Īng)│╠Č╚╔Ž╩Ū▒╦┤╦¬Ü(d©▓)┴óĄ─ĪŻĮø(j©®ng)Üvąąš■│╠ą“ų«║¾Ż¼ąąš■įVįA│╠ą“═Ļ╚½╩Ūė╔įŁĖµšJ(r©©n)×ķŠ▀¾wąąš■ąą×ķ▀`Ę©ŪųĘĖŲõ║ŽĘ©ÖÓ(qu©ón)ęµ╦∙ę²ŲĄ─ĪŻįŁĖµį┌╠ßŲįVįAšłŪ¾Ģr(sh©¬)ę¬Ū¾Ę©╣┘šJ(r©©n)Č©Š▀¾wąąš■ąą×ķ▀`Ę©Ż¼ļyĄ└▀@▓╗╩Ūę╗ĘNų„Åłå߯┐į┌ąąš■│╠ą“ųąŻ¼ąąš■ŽÓī”╚╦Ę┤±gąąš■ÖC(j©®)ĻP(gu©Īn)ū„│÷─│éĆ(g©©)Š▀¾wąąš■ąą×ķĄ─└Ēė╔Ż¼╠ß│÷ūį╝║Ą─ūCō■(j©┤)ę¬Ū¾ąąš■ÖC(j©®)ĻP(gu©Īn)┐╝æ]Ż¼┤╦Ģr(sh©¬)╦¹╠Äė┌┐╣▐qĘĮĄ─Š│ĄžŻ╗▀M(j©¼n)╚ļąąš■įVįA│╠ą“ų«║¾Ż¼╦¹ęčĮø(j©®ng)▐D(zhu©Żn)Č°╠Äė┌šłŪ¾ĘĮĄ─Ąž╬╗Ż¼ąąš■ÖC(j©®)ĻP(gu©Īn)ät│╔×ķ┐╣▐qĘĮĪŻ╚ń╣¹Ę±šJ(r©©n)▀@ę╗³c(di©Żn)Ż¼įŁĖµ┼c▒╗Ėµų«ĘųžM▓╗╚½╚╗╗ņŽ²┴╦Ż┐╝╚╚╗▓╗─▄ʱšJ(r©©n)ąąš■įVįAįŁĖµ╩ŪšłŪ¾ĘĮŻ¼Ųõę▓╩Ūį┌ų„Åłī”ūį╝║ėą└¹Ą─╩┬īŹ(sh©¬)Ż¼╝┘╚ńį┘║åå╬Ąž╠ūė├Ī░šlų„ÅłŻ¼šl┼eūCĪ▒įŁätŻ¼╬ęéāžMĘŪę▓┐╔ęįĄ├│÷įŁĖµę¬│ąō·(d©Īn)┼eūCž¤(z©”)╚╬Ą─ĮY(ji©”)šōŻ┐ ĪĪĪĪūŅ║¾Ż¼¤ošō╩ŪįŁĖµ▀Ć╩Ū▒╗ĖµŻ¼×ķ┴╦½@Ą├ä┘įVŻ¼Č╝Ģ■(hu©¼)į┌įVįA▀^│╠ųąų„Åłī”ūį╝║ėą└¹Ą─╩┬īŹ(sh©¬)Ż¼Č╝▒žĒÜŠ═┤╦žō(f©┤)ō·(d©Īn)┼eūCž¤(z©”)╚╬ĪŻų╗╩ŪŻ¼į┌▓╗═¼Ą─╠žČ©ĀÄūh³c(di©Żn)╔ŽŻ¼╗∙ė┌š■▓▀║═╣½š²Ą─┐╝┴┐(Ųõųą░³└©įSČÓ┐╝æ]ę“╦ž)Ż¼ā╔įņ«ö(d©Īng)╩┬╚╦Ą─┼eūCžō(f©┤)ō·(d©Īn)▌pųž▓╗═¼ĪŻ×ķ▒Ńė┌▒Ē▀_(d©ó)▓Ņ«Éų«╠ÄŻ¼╠ßūCž¤(z©”)╚╬┼cšfĘ■ž¤(z©”)╚╬Ą─Ė┼─ŅĘųŅÉæ¬(y©®ng)▀\(y©┤n)Č°╔·ĪŻ╚╬║╬ę╗ĘĮ«ö(d©Īng)╩┬╚╦Ż¼ų╗ę¬╠ß│÷ę╗ĘN╩┬īŹ(sh©¬)ų„ÅłŻ¼Č╝ų┴╔┘▒žĒÜ│ąō·(d©Īn)╠ßūCž¤(z©”)╚╬Ż¼Ę±ätŻ¼Ųõų„Åł▒╗Ę©╣┘╗“╚╬║╬ėą└ĒąįĄ─╚╦│ąšJ(r©©n)Ą─┐╔─▄ąįĮėĮ³ė┌┴ŃĪŻČ°ŪęŻ¼┐éėąę╗ĘĮ«ö(d©Īng)╩┬╚╦ę¬×ķŲõų„Åł│ąō·(d©Īn)šfĘ■ž¤(z©”)╚╬ĪŻ╚ń╣¹Å─▀@éĆ(g©©)ęŌ┴x╔ŽČ°čįŻ¼Ī░šlų„ÅłŻ¼šl┼eūCĪ▒įŁätÄū║§╩ŪĮ^ī”Ą─ĪŻĄ½╩ŪŻ¼╚ń┤╦ÅŖ(qi©óng)š{(di©żo)Ī░šlų„ÅłŻ¼šl┼eūCĪ▒įŁätŻ¼ī”ė┌└Ēšō░l(f©Ī)š╣║═Ę©┬╔īŹ(sh©¬)äš(w©┤)Č╝ø]ėą╩▓├┤ųžę¬ār(ji©ż)ųĄ┐╔čįŻ¼ę“?y©żn)ķ╬ęéā▀Ć╩Ū¤oĘ©┼¬ŪÕŻ║į┌─│éĆ(g©©)╠žČ©ĀÄūh³c(di©Żn)╔ŽŻ¼──ę╗ĘĮ«ö(d©Īng)╩┬╚╦ų╗ąĶ×ķŲõų„ÅłĄ─╩┬īŹ(sh©¬)│ąō·(d©Īn)╠ßūCž¤(z©”)╚╬Ż¼Č°──ę╗ĘĮ«ö(d©Īng)╩┬╚╦▒žĒÜ×ķŲõų„ÅłĄ─╩┬īŹ(sh©¬)│ąō·(d©Īn)šfĘ■ž¤(z©”)╚╬Ż┐ ĪĪĪĪĖ∙ō■(j©┤)╬ęć°Ą─Ę©┬╔ęÄ(gu©®)Č©╝░īŹ(sh©¬)█`Ż¼ęį▓ó▓╗ć└(y©ón)ųö(j©½n)?sh©┤)─öóšfšōų«Ż¼├±╩┬įVįA║═ąąš■įVįAę▓įSėą▀@śėĄ─ģ^(q©▒)äeŻ║╝┤į┌├±╩┬įVįAųąŻ¼═©│ŻŪķą╬╩ŪįŁĖµ│ąō·(d©Īn)šfĘ■ž¤(z©”)╚╬Ż¼į┌éĆ(g©©)äe└²═ŌŪķą╬ųą▒╗Ėµžō(f©┤)šfĘ■ž¤(z©”)╚╬Ż╗Č°į┌ąąš■įVįAųąŻ¼▒╗Ėµ×ķŲõū„│÷Ą─Š▀¾wąąš■ąą×ķĄ─║ŽĘ©ąį│ąō·(d©Īn)šfĘ■ž¤(z©”)╚╬╩Ū═©│ŻŪķą╬Ż¼į┌éĆ(g©©)äe└²═ŌŪķą╬ųąįŁĖµžō(f©┤)šfĘ■ž¤(z©”)╚╬ĪŻė╔ė┌į┌įVįA│╠ą“ųąŻ¼įŁĖµ┐é╩ŪūŅŽ╚╠ßŲ─│éĆ(g©©)ų„ÅłĄ─ę╗ĘĮŻ¼╦∙ęįŻ¼╚ń╣¹╬ęéā░čĪ░šlų„ÅłĪ▒└ĒĮŌ×ķĪ░šlūŅŽ╚╠ß│÷ų„ÅłĪ▒Ż¼░čĪ░šl┼eūCĪ▒└ĒĮŌ×ķĪ░šlžō(f©┤)šfĘ■ž¤(z©”)╚╬Ī▒Ż¼─Ū├┤Ż¼├±╩┬įVįAĄ─ę╗░ŃįŁät╩ŪĪ░šlų„ÅłŻ¼šl┼eūCĪ▒Ż¼Č°ąąš■įVįAĄ─ę╗░ŃįŁät╩ŪĪ░šlų„ÅłŻ¼šl┼eūCĪ▒Ą─Ą╣ų├ĪŻ▓╗▀^Ż¼▀@ĘN║åå╬╗»Ą─Č©ąį▒Ē╩÷ę└╚╗¤oĘ©ĮŌøQę└┘ćŠ▀¾wŪķŠ│Ą─ĪóéĆ(g©©)ąį╗»Ą─┼eūCž¤(z©”)╚╬Ęų┼õå¢Ņ}ĪŻ[27] ĪĪĪĪąĪĮY(ji©”)Ż║ąĶę¬ę╗ĘNéĆ(g©©)ąį╗»Ą─蹊┐ ĪĪĪĪ¼F(xi©żn)īŹ(sh©¬)╩└ĮńÜŌŽ¾╚fŪ¦Ż¼įSČÓĘ©┬╔å¢Ņ}▒╦┤╦ų«ķg╝╚┐╔─▄┤µį┌ę╗░Ń╣▓ąįų«╠ÄŻ¼ę▓╠N(y©┤n)║Łą╬ą╬╔½╔½ĪóŽÓ╗źÕ─«ÉĄ─éĆ(g©©)ąįĪŻ▀@ą®Ę©┬╔å¢Ņ}Ą─╠Ä└Ē▓╗═Ō║§ā╔éĆ(g©©)īė├µŻ║Ųõę╗Ż¼┴óĘ©š▀(ŽÓī”ęŌ┴x╔Ž░³└©┬─ąą▓┐Ęų┴óĘ©┬Üž¤(z©”)Ą─ąąš■ÖC(j©®)ĻP(gu©Īn)║═ū„│÷ŅÉ╦Ų┴óĘ©ęÄ(gu©®)Č©Ą─╦ŠĘ©ĮŌßīĄ─╬ęć°ūŅĖ▀Ę©į║)Ųš▒ķ│ķŽ¾╗»Ą─┼¼┴”Ż╗ŲõČ■Ż¼ł╠(zh©¬)Ę©š▀╠Ä└ĒŠ▀¾wå¢Ņ}Ą─éĆ(g©©)ąį╗»┼¼┴”ĪŻŪ░š▀įćłDśŗ(g©░u)Į©Ųš▒ķš²┴xĄ─ų╚ą“─Ż╩ĮŻ¼║¾š▀į┌Š▀¾wéĆ(g©©)░ĖųąīŹ(sh©¬)¼F(xi©żn)š²┴x─Ż╩ĮĪŻė╔ė┌īW(xu©”)└Ē╔ŽĮø(j©®ng)│ŻėĶęįėæšōĄ─ę╗ą®įŁę“Ż¼Ū░š▀Ą─┼¼┴”¤oĘ©║Ł╔wį┌║¾š▀├µ┼RĄ─å¢Ņ}ųą│÷¼F(xi©żn)Ą─╦∙ėąéĆ(g©©)ąįŻ¼║¾š▀ę╗Ą®Šą─Óė┌╗“ų╣▓Įė┌Ū░š▀ęÄ(gu©®)Č©Ą──Ż╩ĮŻ¼éĆ(g©©)¾wš²┴xĄ─īŹ(sh©¬)¼F(xi©żn)Š═Ģ■(hu©¼)Ž±į┌─ÓšėųąĄ°Ą°ĮOĮOĪŻ│÷ė┌ī”Ę©┬╔łDŠ░▀@ę╗ĮŪĄ─┐╝æ]Ż¼▒Š╬─ćLįćį┌ąąš■įVįA┼eūCž¤(z©”)╚╬Ņ}ė“ā╚(n©©i)╠Į╦„ę╗ŚléĆ(g©©)ąį╗»čąŠ┐┬ĘÅĮĪŻę▓įSŻ¼×ķ▀M(j©¼n)ę╗▓Įķ_░l(f©Ī)▒ŠŅ}ė“Ż¼╬ęéāį┌└Ēšō蹊┐╔Ž╦∙ąĶꬥ─š²╩Ūę╗ĘNéĆ(g©©)ąį╗»Ą─┼¼┴”ĪŻ▀@śė┼¼┴”Ą─ĮY(ji©”)╣¹īóėąų·ė┌╬ęéāį┌Ė³Ė▀īė├µ╔Ž▀M(j©¼n)ąą│ķŽ¾╗»Ż¼Å─Č°čžų°┬▌ą²╩Į▐D(zhu©Żn)╠▌▓╗öÓŽ“╔ŽĪŻ |
| ą┬└╦╩ūĒō > žö(c©ói)Įø(j©®ng)┐vÖM > Įø(j©®ng)Ø·(j©¼)Ģr(sh©¬)įu > ╔“Äh > š²╬─ |
|
| ||||
 |
| |||||||||||||||||||||||||||||
|
|
ą┬└╦ŠW(w©Żng)žö(c©ói)Įø(j©®ng)┐vÖMŠW(w©Żng)ėčęŌęŖ┴¶čį░Õ ļŖįÆŻ║010-82628888-5173ĪĪĪĪĪĪÜgėŁ┼·įuųĖš² ą┬└╦║åĮķ | About Sina | ÅVĖµĘ■äš(w©┤) | ┬ō(li©ón)ŽĄ╬ęéā | šąŲĖą┼Žó | ŠW(w©Żng)šŠ┬╔Ĥ | SINA English | Ģ■(hu©¼)åTūóāį | «a(ch©Żn)ŲĘ┤ę╔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