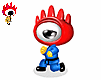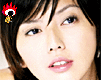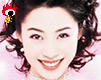| SARS拷打之下的"各自為政"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03日 16:10 中評網 | |||||||||
|
SARS是一種生物形態的刑具,無影無形、隨處可至、定時潛伏、瞬間株連、廣泛波及、乏藥可治,加上其對人類生命的摧毀力以及不可預見的肆虐周期,這些令人恐懼的品性結合一身的它,正在不斷地拷打著我們的人性與制度。 防治SARS的“各自為政”
共和國總理溫家寶在曼谷出席東盟關于防治SARS的會議之后,有香港記者提問,內地多個省市要求到當地的港人接受隔離14日,是否不歡迎港人到內地,溫家寶總理連說“不會的”,并且表示,“如果說出于保護香港同胞的健康,我們采取一些預防措施就行了……如果有這樣各地各自為政的政策,我們會讓他們糾正的”。 其實,在防治SARS過程中的“各自為政”已經不是如果而是現實。 據《京華時報》報道,4月28日上午,北京至塘沽的103國道,有兩處被人動用大型挖掘機挖斷,造成嚴重的交通堵塞。到了下午,兩處國道又被神秘地回填,方才恢復通車。而在比鄰北京的河北香河縣,有一條活動路障橫亙在縣城路口,上掛一紅條幅,“嚴緊外埠車輛通行”。路障前的一塊牌子上還貼有一張告示:“根據上級指示,為防止非典傳播,本縣大小車輛禁止通行……”。落款是“香河縣公安局”。聯想起交通部近日發出的關于不得通過任何方式中止交通運輸的緊急通知,顯然,此類事件并非偶發的個例。 以防止疫情擴散為由進行交通限制,只是“各自為政”的一個方面。而《財經》雜志關于SARS入侵山西的紀實,則折射出另外一個令人關注和擔憂的情景。 迄今為止,山西是全國僅次于廣東和北京的重災區,在其10個地級市和1個地區中,只有晉城一地尚未發現SARS,其余地市均已發現確診或疑似病例。而相對于嚴峻疫情,山西省防疫救治的醫院和專業醫護人員極為少見,診治SARS的專業培訓都是臨陣磨槍式的,而醫療設備和資金更是緊缺。省財政廳副廳長粗算,山西的防治經費缺口至少在1.5億元。而疫情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蔓延到煤礦,就會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能源供應。《財經》雜志在這份報告的最后,如宣誓般地道出,“SARS陰影重重之中,山西正在奮爭。現在還不是勝算在握,但這是一場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戰爭!” 可是,山西作為一個經濟和醫療條件相對落后的省份,單靠自己的力量,能盡快擺脫困境、防止更大規模的疫情爆發嗎? “地方自衛”的人性 當災難和死亡的威脅降臨之時,我們作為人類的表現會是怎樣的? 古希臘偉大的歷史家修西底德的記錄,揭開了人性中深埋著的脆弱。公元前430年,古希臘文明城邦雅典爆發大規模可怖的瘟疫,因看護病人而染病的人像羊群一樣成群死去,流動在城里的鄉下人在炎熱的初夏擁擠在空氣不流通的茅屋里,像蒼蠅一樣地死去。在這場災變之中,人們害怕去看護病人;有的人在埋葬親人時,發現另一個火葬堆正在燃燒,就把他們親人的尸體扔在別人的尸體上,然后匆匆跑開。 相隔2400余年的時間長河,望著在雅典城突然隆起的一座座新墳,望著一處處正在燃燒的火堆,望著驚恐萬狀、手足無措的人群,我們體味人性,內心中會有怎樣的復雜情感?反觀當前國內挖掘國道、阻斷交通、隔離疫情發生地與未發生地的交往、乃至部分村落劃地而治、禁止外人入內的大大小小“地方性策略”,撫摸身心深處掩藏的怯懦,我們不免會生發一絲凄涼和一聲悲鳴。 當然,我們作為人的存在,對堅忍、勇毅、無私、同情、互助、奉獻等人性的另一面,始終有著一種內在的、無法阻擋的渴望與追求。在SARS的陰影之下,白衣戰士的勇敢與堅強、醫護人員親屬的無私支持、志愿者的積極加入、捐獻者的付出、記者冒險的現場報道、部分患者、疑似患者或接觸者的主動隔離,以及一串串紅色“中國結”展示的民心,無一不昭示和弘揚著人性中的美與善。 只是,既然人性之脆弱不可根除地深植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那么,除了在道義上頌揚美善之德、接受其對我們心靈的凈化和提升、盡可能幫助每個人克服軟弱以外,我們又可以在制度上做些什么呢? 地方治理的制度透析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有這么一段描述,“假如公路上發生故障,車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會自動組織起來研究解決辦法。這些臨時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選出一個執行機構,在沒有人去向有關主管當局報告事故之前,這個機構就開始排除故障了。”托克維爾意在說明美國人的結社習慣,但是,這也恰好點出,人類在面臨生活苦難時,有一種組織起來、凝聚集體力量、共保自由與安全的自覺性。 這樣的組織行為,最小規模的形式就是兩個人的聯合,村落、鄉鎮、城市、地區、省份、國家乃至國際共同體,則是范圍逐級擴大的形式。一旦如SARS這樣極具傳染性、危及人群的病種威脅一個共同體(無論大小),那么,地方的聯合抵抗本來就會自然形成。加之SARS是一個有著最長兩周潛伏期的定時炸彈,地方上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也無可厚非。截至5月6日,全球200個左右的獨立主權國家,有100個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旅行者實施入境限制措施,這也映證了地區性防范的合理性。 若從政治原理著眼,即便現實運作并不完全如此,但至少在形式上,任何一級政府皆由當地選民選舉產生。政府在性質上等同于或類似于民眾自愿組成的一個社團,其存在的宗旨就是維系所在地方的和平、安寧和繁榮,政府的政治責任就是對投票人負責。在SARS威脅本地民眾生命安全之際,地方政府當然必須予以積極的回應。 而我國實際運作的防治SARS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也為地方治理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我國地方政府官員并不完全由人民選舉產生,中央政府對其有著直接或間接的控制。北京市長孟學農的被罷免,就是首先從中共中央免去其北京市黨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開始的。但是,在一個幅員如此遼闊的國度進行任何一項系統的任務,無論是執行某個法律或者政策,還是實施像防治SARS這樣一個巨大項目,中央政府勢必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地方各級政府的努力。北京市長的罷免,在程序上,可以表明中央政府對各地進行控制的能力。可是,其透露出來的“在地方防治不力,將受罷官處分”的實質信息,可能在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員看來,意味著當前最為首要的任務是盡量讓SARS在本地少出現。因為,防治不力的表象體現,就是SARS在地方的爆發和流行。 另一方面,我國現行的《傳染病防治法》第4條原則性地規定,“各級政府領導傳染病防治工作,制定傳染病防治規劃,并組織實施。”第25條規定,“傳染病暴發、流行時,當地政府當立即組織力量進行防治,切斷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必要時,報經上一級地方政府決定,可以采取限制人群聚集的活動、停工、停業、停課、臨時征用房屋、交通工具、封閉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公共飲用水源等緊急措施。第26條規定,“甲類、乙類傳染病暴發、流行時,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報經上一級地方政府決定,可以宣布疫區,在疫區內采取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的緊急措施,并可以對出入疫區的人員、物資和交通工具實施衛生檢疫。”我們姑且不論當前各地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或者《傳染病防治法》是否在此次事件中顯露出缺陷,但法律將主要的防治傳染病工作授權給地方政府進行,是毫無疑問的。 “各自為政”的去與留 或許有人質問:如此說來,難道挖掘國道、阻斷交通是合理的?難道就這樣讓一個經濟落后的山西省獨自對抗嚴重疫情,而不顧傾其“家當”都有1.5億元防治經費缺口的事實?難道我們就輕易放棄團結、互助、奉獻之精神,而永遠在人性脆弱中為趨利避害尋找藉口,讓中華民族跌入泯滅美善德性的、萬劫不復的深淵? 承認“地方治理、各自為政”在一般意義上的合理性,并不意味著對在此名義下進行的各種具體措施,一概持肯定的態度。其實,SARS拷打之下出現的各自為政現象,再次牽引出兩個互有關聯的難題: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劃分問題;法治問題。 與法治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現行憲法條款,盡管規定了劃分原則(第3條,“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以及中央和地方各個國家機關的權限,但是,疏于結合具體管轄事項來確定中央和地方的分工合作問題。這一課題,遂更多地交付各個針對具體事項的單行法律予以完成。 《傳染病防治法》確實也有這方面的規定。例如,根據第26條,宣布疫區、在疫區內采取法定的緊急措施、對出入疫區的人員、物資和交通工具實施衛生檢疫,是縣級以上地方政府享有的權力(宣布疫區需經上一級地方政府決定);決定對甲類傳染病疫區進行封鎖的權力,歸省級政府;而封鎖大中城市或者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疫區,以及封鎖疫區導致中斷干線交通或者封鎖國境的,歸國務院決定。 然而,結合該法律文本與當前的防治形勢進行分析,在防治傳染病事項上,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配置仍然存在諸多模糊之處,以至于中央和地方權力在實際運作中都可能出現既過大又過小的問題。以交通部的緊急通知為例。該通知要求“任何地方、部門、單位和個人不得通過任何方式中止交通運輸,以保障廣大身體健康的旅客的正常運行,保障防治‘非典’的藥品、醫療設備、醫療原材料以及社會生產生活物資的運輸順暢。”交通部的動機顯然是良好的,旅客運行和物資運輸的順暢,即便在抗SARS的嚴峻形勢下,也應予以適當的保障。但是,且不論在此一律禁止“單位和個人”以“任何方式中止交通運輸”,已經因為用語不當而有越權和禁令過寬之嫌,單就完全杜絕地方中止交通運輸的可能性而言,難免導致地方政府不能根據疫情發展的具體情況而作出適當的中止部分交通運輸的決定。設若某縣突發大規模SARS疫情,難道要讓省級政府聽之任之,仍然允許縣際客運暢通無阻? 由此事例,已可窺見一斑。為日后立法計,當將中央與地方在應對緊急事態方面的權力劃分,予以相對明確的厘定。雖不能在此代立法者言或草擬詳細規則,但建議考慮以下原則: (1)【中央保留】凡全國性或者涉及省際關系的緊急或者救援措施,或者在大、中城市的重大緊急或者救援措施,當由中央進行決策(當然,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國務院及其部門之間,仍然需要一定的權力劃分)。 (2)【地方保留】除上述措施以外的緊急或救援措施,若非限制人身自由的緊急措施(現行《立法法》要求必須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才能規定),授權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以地方性法規或決議、省級政府以地方政府規章或決定規定之。在中央或者省級地方規定的措施以外的緊急或救援措施,省級以下地方確實需要實施的,當報經省級地方批準、并報中央備案。 (3)【排除妨礙】凡地方出現任何妨礙緊急或者救援措施順利實施的情形,中央和省級地方都有權作出決策或者采取必要的、適當的措施予以排除。 (4)【請求幫助】省級地方確實需要資金、設備、醫藥、人員等方面援助的,有權向中央提出請求。省級以下地方確實需要的,也有權向省級地方請求幫助。 依照這些原則去重構防治傳染病的法律制度,或許可以既保留必要的地方治理(尤其賦予省級地方相當的自主權),又防止出現散沙式的、混亂的地方割據,亦可防止個別經濟落后的地區苦苦支撐防治工作的局面。 此外,現時的SARS防治工作,已經在一些方面突破了法律的規定,從而向近年來倡導的法治提出了挑戰。例如,上海市政府發布防治“非典”的第二個通告,要求從“非典”病例發生地返滬的上海市市民,即便未發熱和體征無異常者,也應當在其居住地或者社區的指定地點接受醫學觀察兩周。從SARS的潛伏特性著眼,這一措施本有其合理一面。但是,它不僅在《傳染病防治法》上找不到依據(該法規定,對疑似甲類傳染病病人,在明確診斷前,在指定場所進行醫學觀察),而且,到“指定地點”接受醫學觀察,與《立法法》關于此類措施必須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的法律加以規定的要求相悖。 即便我們循從上述原則重構法律制度,授予省級地方更大的自主權,也會致使上海市政府遭受“違法行政”的詬病。因此,為了在我國建立成熟的、豐富的法治,應當在《傳染病防治法》和其他相關法律中,引進法學理論上所謂的“應急性原則”。大致內含: (1)【緊急創制】授權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和省級政府,在出現明確無誤的緊急狀態下,以地方性法規或決議、地方政府規章或決定的方式,規定與現有法律或國務院行政法規相抵觸的非常緊急措施。省級以下地方確實需要實施與法律或國務院行政法規相抵觸的非常緊急措施時,應當請求省級地方作出規定。 (2)【合乎比例】首先,以上采用的非常緊急措施,必須能夠實現防治傳染病緊急目標的實現或至少有助于其實現;其次,以上采用的非常緊急措施,與其他可供選擇的具有相同效應的措施相比,必須對公民自由權利的侵害最少;最后,以上采用的非常緊急措施,對公民自由權利侵害的程度,必須與所要實現的公共利益的大小相對應。 (3)【特別程序】省級地方在規定了與法律或國務院行政法規相抵觸的非常緊急措施以后,應當在一定期限內,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或國務院請求確認有效。 若能在相關法律文本中設計若干條款,體現學理主張的“應急性原則”,那么,省級地方的緊急創制權,就不會與法治相悖了,因為,該權力本身獲得了法律上的依據。 堅忍、勇毅、團結、互助、奉獻等美善人性,讓我們感動,為我們所追求,但是,人性之脆弱絕不應該因此遭到冷漠的白眼。一個良好的制度,當助我們盡力克服自身的弱懦。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沈巋 > 正文 |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