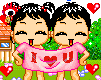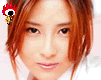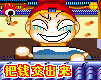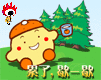| 從傳統民間公益組織到現代“第三部門”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29日 12:11 中評網 | |||||||||
|
A、公益事業發展史的西方模式
兩種“第三部門”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維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義,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國家機構也不是私營企業的第三類組織,那末它就應該是個古已有之的現象。因為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區,國家(政府)與企業之外的人們組織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種類繁多的。而且嚴格說來,“民族國家”在西方被認為是近代現象,在中國固然“國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見的官僚機構,但其組織的發達也不能與現代國家相比。而“私營企業”的嚴格定義幾乎只適用于資本主義時代,其廣義的所指盡管可見于古今中外,畢竟也以近代為繁榮。所以從邏輯上講,如上定義的“第三部門”應當是時代越古、社會越“傳統”它就越興盛才對。我們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樣)活動在“衙門與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組織──宗族、部落、村社、教會、幫伙、行會等等──中的時候,實比如今的人們為多。就是在加上附加條件(如必須是提供“公共產品”的組織等)之后也如此:畢竟那個時代如果有“公共產品”的話,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門與公司來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們都是把“第三部門”作為一種現代(近代)現象,乃至“后現代”現象來描述的。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門”的成長與國家干預、國家控制的退縮和公民自治、社會自治的擴張聯系起來,因而非常強調它的“現代性”意義或“市民社會”意義──這兩個詞在這種語境中一般都是與被稱為資本主義的西方現存社會相聯系的。這種觀點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門”之發展與“私有化”進程的關系、與福利國家的消亡之關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計劃的(個人志愿)合作”與“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則主要強調“第三部門”的成長是對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私人企業等“市民社會”古典原則的否定,把“第三部門”的興起與社群主義、合作主義、“新社會主義”、“現代性批判”或“后現代趨向”聯系起來。這種觀點往往把非私有(當然,也非官辦)經濟當作“第三部門”的主要構成,從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業、西班牙的蒙德拉貢、英國的工合運動與費邊主義經濟直到以色列的基布茲公社,都被視為“第三部門”的事例。有人還歸納出了“第三部門”的三種類型:“合作經濟”、“混合經濟中的合作成份”和“與利潤分配相結合的參與制中的合作利益”。(Clayre,1980)
顯然,這兩種“第三部門觀”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立的。它不僅導致了價值判斷的差異,而且也導致了事實判斷、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門”這一判斷的差異。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業”、西班牙的蒙德拉貢與以色列的基布茲這類雖非私有但仍是“企業”、雖未必追求利潤極大化但絕對具有法人經濟效益目的的“部門”,在克萊爾眼中是第三部門的典型,但在克萊默看來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門范疇的。我們可以把它們分別稱為新左派的第三部門觀與新右派的第三部門觀,或者“非個人主義”的第三部門觀與“非國家主義”的第三部門觀。按瑪利琳.泰勒的說法,這是兩種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產品的途徑: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書中稱為“福利多元主義”)期待于“志愿部門”,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門社會保障網絡的贏利部門”。在財政來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來源。在規則方面,前者主張按政府與作為“中介結構”的志愿部門的規矩,后者則主張按市場規則通過個人交易來進行。當然,有別于這二者的是傳統的福利國家模式,它在所有這三個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Gidron [et al],1992:150)
可見,如今人們講的“第三部門”具有時代之根(現代的或“后現代”的)和結構之根(政府和企業之間,或更本質地說,是國家與個人之間)。它是現代化過程中人們生活日益形成國家與公民社會(即個人主義的或個人本位的社會)二元格局的結果。也正是作為這種二元格局中的一種“中介”組織和對二元緊張的現代社會癥狀的一種治療嘗試,“第三部門”中才會存在“非國家主義”與“非個人主義”、“現代性”與“后現代”這樣兩種方向。
從“共同體”公益到“國家+市場”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傳統西方,這種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德國現代社會學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體”與“社會”是人類群體生活的兩種結合類型。前近代的傳統文明中沒有“社會”而只有“共同體”,共同體是一種自然形成的、以習慣性強制力為基礎的血緣、地緣或宗教緣集體紐帶,它不是其成員個人意志的總和,而是有機地渾然生長在一起的整體,是一種“人們意志的統一體”。只是到了近代化過程中,一方面交往的發達突破了共同體的狹隘界限,發育了大范圍的(地區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個性與個人權利發達起來,于是形成了“社會”。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自然習俗的產物,而社會則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礎上結成的“有目的的聯合體”。共同體是整體本位的,而社會則是個人本位的,“社會的基礎是個人、個人的思想和意志”。共同體是相對狹小的群體,而社會則大至與民族國家相當,并由此形成“社會”與“國家”的二元結構。“共同體是古老的,而社會是新的”。(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這種分析,我以為是大體符合西方社會史的實際的。在這一進程中既然國家與“社會”(個人本位的公民社會)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現代)化的產物,那么這二元之外(或之間)的“第三”部門也只能是近現代的產物。而在傳統的“共同體”時代既然沒有民族國家與公民社會這“二”元,當然也就不會有“第三”部門。因此盡管西方傳統時代也存在著“衙門與公司之外”的組織(即“共同體”),存在著由它提供的“公共產品”即傳統的公益、慈善事業,但現代第三部門并不是它的后繼。而“第三部門史”的研究者在論述當代第三部門發育的時代、社會根源的同時,也很少要涉及它的“歷史根源”。
當代史學對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國)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業或“社會工作”事業的歷史已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如J.B.施尼溫德等對西方博愛與救濟意識演進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麥坎茨對17-18世紀荷蘭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組織與孤兒救助事業的論述(McCants,1997)、M.道頓等的英國公益慈善史探討(Dauton,1996)、W.K.約爾丹的1480-1660年間倫敦慈善團體研究(Jordan,1960)、S.卡瓦羅對1541-1789年意大利都靈地區慈善醫院文獻的考證(Cavallo,1995)、T.M.薩弗利關于德國奧格斯堡地區濟貧撫孤公益事業歷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維特關于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貧兒、棄兒與孤兒養濟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從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傳統時代慈善、公益事業除技術上的落后特征(活動領域狹小,主要限于救濟孤兒、施舍醫藥等等)外,在觀念形態與社會組織層面更有明顯的特點:在觀念上慈善過份依賴于宗教意識,被看作是一種單方向的“賜與”(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Schneewind,1996)活動局限于狹小的群體,而且往往被納入傳統共同體的束縛──保護關系中,施舍者與被施舍者間形成一種人身依附紐帶。如16世紀都靈地區“慈善與權力”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捐助者建立免費醫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為通往統治者地位的橋梁。而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最著名的慈善機構英諾森養濟會,則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它雖然也由教會募捐來支持,但那時的認捐屬于對教會盡義務,并無“志愿”性質。
西歐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傳統公益活動,也帶有明顯的“共同體”性質,束縛──保護紐帶而非志愿合作紐帶成為這些活動的基礎。如俄國傳統的米爾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勞動組合、連環保等經濟職能外,還有十分發達的社區公益職能。米爾專門預留有“共耕地”,其收獲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當于公益捐助),諸如老弱病殘、意外災難的補助、公醫、公匠、公牧的雇請、節慶典儀的開支等,均可承擔(Figes,1986)。日本傳統時代的町與印度的村社,也有類似的公益職能。(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進入近代化過程后,傳統共同體趨于解體,人們在擺脫了傳統的束縛的同時,也失去了傳統的保護──包括相當一部分原由傳統共同體提供的“公共物品”。于是許多國家的人們在由“共同體的附屬物”變成自由公民的同時便“享受”到了兩種自由:擺脫束縛的自由與失去保護的自由。傳統共同體的公益職能一部分由新興的國家機器來承擔,一部分則成了市場交易物而改由贏利部門來提供。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車”問題在這個時期是不會引起太大注意的。原因很簡單:在由共同體本位的傳統時代向個人本位的市民社會過渡時由于舊的身份、等級、特權、共同體等壁壘的存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車”而造成的“失靈”因而易于被掩蓋。只有到舊時羈絆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發展、社會經濟機制最大限度地趨近于“完全市場”的狀態下,那些不是因為非市場力量的干擾,而是由于市場邏輯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靈”才會凸顯。同樣道理,在“民族國家”職能初具、政府干預力量還未充分施展之時,“政府失靈”的問題也是難以凸顯的。直至“二戰”以前的情形的確如此。那時“國家主義”和市場主義一樣處在上升期。從19世紀英國的迪斯累里、德國的俾斯麥分別建立福利國家的雛形(即“皇帝──國王的國家社會主義”、“保守的福利國家”和“父權式的托利黨社會主義”)、20世紀的美國新政、北歐社會黨福利體制、英國勞合喬治與麥克唐納的“工黨社會主義”、德意法西斯的“法團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直到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歐美的左派(社會黨)、右派(保守黨)、極左派(共產黨)與極右派(法西斯)都出臺了由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制度設計。另一方面,傳統的共同體公益日漸衰落,如17世紀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傳統社區捐贈基金與教會慈善基金尚處在“黃金時代”,但18世紀后因“資本主義的興起”,市民社會出現了“財政上的保守與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與金錢”的關系日顯,傳統慈善基金制度隨即衰落了。(Mccants,1997)在英國,原由教會主持的慈濟診所與藥房在18世紀大都世俗化,轉由世俗政府及企業支持,當時在約克、利茲、赫爾、設菲爾德等地的這類醫療公益還帶有行會性,到19世紀這種行會性也趨于消除。如在哈德菲爾德的紡織業慈濟診所中,1841年還有57%的病人是紡織業雇員,到1871年這一比例降至22%;但診所超越行會性而向社會開放的同時,慈善性也逐漸為商業性所取代了。(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紀法國的傳統社區互助協會在擺脫村社、行會、教會的色彩后也發展迅速,其數從1852年的2488個發展到1902年的13673個,會員由23.9萬增至207.4萬。但同時其慈善色彩也大為減退。到1910年,這類協會總預算收入達6298萬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萬,即18.8%來自捐贈、遺產贈與及成員的自愿奉獻;另有1172萬(18。6%)來自政府資助,3936萬(62.5%)來自帶有自惠性的入會費或會金──而這部分取之會員,用之會員的資金作為入會條件實際上是一種交易。(同上,172-186)。
總之在歐美社會“走入現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業的共同體基礎逐漸為國家+市場(或政府+“社會”、國家+個人)基礎所取代。正如研究者所指出:這一時期公益組織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數組織處于政府的監督下”。法國在1882-1902年間“經批準的”公益會社成員增加了100萬,而“自由的”公益組織成員只增加10萬。解釋很簡單:國家的資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而若無國家支持,極少有組織可以達到收支平衡。因此從國家與私人(市場)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這一時期“互助主義”(mutualism)公益的實踐實際上是戰后福利國家體制的序幕,“它使人們不由自主地選擇了一條介乎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之間的道路”。(同上:184-185)
對于西方歷史上從傳統公益向現代公益的演變,以往學者有多種表述,如“從教會慈善向世俗控制轉變”(Weaver,1967:14),“從父愛主義的福利形式向職業化管理與保險──融資體制過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從“救助個人的慈善”到“作為社會責任的慈善”和“作為道德責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國家中的慈善”的演變(Alvey,1995),以及從“近似原則”向“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發展(同上;26)等等。但從根本上講,筆者認為這種轉變的本質在于“共同體失靈”所導致的對國家與對市場的二元崇拜。西方的現代公益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形成的。
從“國家+市場”公益到第三部門:否定的否定?
現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帶來了一系列變化:
首先是傳統慈善觀念的變革。西語中“慈善(Charity)”一詞現在的辭書中都釋為“仁愛”、“基督之愛”、“為上帝而普愛眾生”等,帶有濃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但實際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時代已經流行,在早期拉丁語(caritas)及希臘語(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著一種珍貴的情懷與高尚行為,它與恩惠及感恩相聯系,但無論在古希臘還是古羅馬,這個詞都從不用來表達一個家庭(家族)內的施惠關系,而只是用以表達一個人對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為。可見,這時的慈善雖然含有受者對施主的依附性含義,但也反映了一種突破共同體中自然形成的人際關系的局限之意圖。(Weaver:6)這時也已經出現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則”(cy-pres doctrine):這一原則認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標不能達到時,有勢力的組織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Alvey;8)這就為慈善信托基金的發展開了路。但到19世紀,與感恩相聯系的慈善觀念已越來越為兩個方面所排拒:對弱者而言,他們“對于受惠的民主化預期”已使“慈善”變得像是“對貧窮階層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對于強者而言,“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也造成了一種對所謂不爭氣者的一種“維多利亞式的厭惡”;而傾向于“對受惠者更具選擇性的博愛”。正如英國學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幫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蕩子、二流子或純粹的貧民,土地法已經為他們提供了足夠的東西。它只打算幫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們與其他人一樣,沒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發災難擋住他們的路”。新的博愛要幫助的是這樣的人:“他們不能乞討,因為他們習慣于工作,他們拒絕成為窮人,因為他們已經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獨立性”。(Alvey,1995:26)
由于這種“福音主義”拒絕救助所謂“自已弄窮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窮”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殘疾人、孤棄兒等)的救助又被認為應當是當時職能日趨發達的國家的責任,因而19世紀興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漸退出傳統慈善領域即對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轉向了對公共生活的關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則是20世紀興起的環保等領域。
現代公益的特點在與宗教的關系上表現尤為明顯。如前所述,中世紀西方慈善事業的最大施主是教會,“教會資助社會事業”是那時的傳統。但英國在16世紀、荷蘭在18世紀、其他西歐國家大致也在此期間都出現了來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減少的趨勢。由大筆私人遺產(資本主義積累的產物)捐贈而設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濟事業的支柱。(Alvey:1995:12,19)但隨著“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興起,濟貧施藥養老育孤這類事業逐漸轉由國家主辦,民間世俗基金便更多地關心公眾的精神需求,同時現代化要求的政教分離趨勢也使國家不便支持教會,民間世俗基金便成為宗教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資者。基督教博愛思想、救世情懷與利他主義雖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為的精神動力之一,但教會本身已由施助者變成了主要是受助者。“教會資助社會事業”遂為“社會事業資助教會”所取代而成為現代公益的一大特征。在美國這一點尤為明顯,20世紀60年代前期美國全國公益來源有80%來自個人捐贈,而在公益開支中宗教占了將近一半(49%),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Weaver,1967:62-65)
在傳統慈善的重要領域醫療事業中,“父愛主義”的施醫舍藥也逐漸變成了“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醫學研究資助。1888年法國出現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視為“20世紀醫療慈善事業所繼承的模范”。這個私人投資、吸納志愿捐助的非贏利機構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聞名于世外,還開展了預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會公益活動并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費醫療。但它的主辦者始終認為科學是“消除貧困與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則是次要的。它開創了此后一大批類似機構之先河,如法蘭克福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保羅.埃里克研究所等。與此類似,傳統的施舍濟貧也發展成以民間公益組織擴大就業機會的努力,工合運動的發展便是一個典型。(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現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動領域是教育。隨著公民社會──民族國家二元結構的形成,以市場規則運作的“教育產業”和國家主辦的“教育事業”同時勃興并排擠了傳統時代以教會、村社為主角的共同體教育。但“教育產業”與官辦“教育事業”之間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種力量來填補,這是工業化時代教育成為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之一的結果,因此也正是在這一領域較早興起了新的公益組織形式。19世紀前期,英國出現了擁有數千捐助人的“要求關心窮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員會”、布羅哈姆委員會等組織,從事對學校與對學生的教育資助。當時一份調查顯示,英國有4100多所學校受到資助,這些學校共有學生16.5萬。在另外約14300個未受資助的學校中,則有31萬交費生與16.8萬慈善資助生。受資助學校的學生與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計33.4萬人,已經超過了交費生人數。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統之外的非英國國教徒中還有許多受資助的初級學校,分別由戰?教徒、猶太人與胡格諾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領域的這些情況表明,即使在“國家+市場”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進現代化”時期西方也存在著國家與市場之外的民間公益力量。它無疑是當代第三部門的先驅。無疑,就西方文化的繼承性而言它與前近代傳統文化并不是毫無瓜葛,正如保爾.魏德林所說:基督教人道主義遺產與更早時代商業主義的大眾參與到工業時代“與其說被拒絕了,不如說是在更現代的指導下被改造了”。(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實踐的指導思想、組織資源、動員方式與行為規則等方面看,父愛主義與理性福音主義、共同體慈善組織與公民公益組織、“教會資助社會”與“社會資助教會”等區別的斷裂性還是很明顯的。正因為如此,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西方一直有所謂“慈善終結論”、“慈善失敗論”之說。正如英國討論公益問題的拿旦(Nathan)委員會在20世紀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們歷史中最悲壯的失敗之一,就是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尤其是在18世紀后期及19世紀,由私人努力來提供學校、醫院、施藥所、濟貧院、孤兒院的普遍服務、發放養老年金、以及救濟其他范疇的‘應當貧窮者’(deserving poors)”。而歷史證明民間的這些努力終結了,“如今國家的法定服務──新的或舊的──現在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個人福利,……(于是)困擾委員會的基本問題是:慈善者還有什么事可做?”
但委員會主席、英國著名律師與議會法學家拿但認為舊慈善的終結恰恰意味著新型志愿行動的興起。有趣的是:他在論證這一點時并未強調“市場失靈”與“國家失靈”,而恰恰論述了志愿行動與這二者的契合。他認為志愿服務與國家服務相互排斥的觀點已經過時,這兩者并無明顯界限:“歷史上(民主)國家行為就是志愿行為的結晶與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沒有志愿服務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國家很難有效地發揮職能”。福利國家制度應當由志愿努力來補充,這不僅由于作為民間力量的志愿組織可以作為壓力團體對國家構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幫國家的忙:“志愿部門不像政府衙門,它有自由去進行實驗,能成為開創性的先鋒,而國家可以接著干──如果這種開創被證明有益的話”。與之相比,贏利部門雖然也有“實驗的自由”,但其實驗的目的是產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實驗成功,國家也無法“接著干”。反過來講,志愿部門因其不具強制性,其實驗如果失敗,也不致造成嚴重后果,而國家如果胡亂搞“實驗”,那就要釀成災難了。
換言之,志愿部門再不濟,頂多成為“有益無害的烏托邦”,而國家若搞烏托邦就可怕了──有過這種經歷的中國人對此應當比拿但更有體會──這是從“消極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門。若從“積極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動當然就更值得肯定。因為這種自由觀不僅講“有權做什么”,而且更講“應當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務公眾顯然是“應當做”的。
可見,拿但委員會眼中的志愿部門是建立在自由主義(在“積極自由”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基礎上的,它以(民主)國家有效、市場有效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國家主義、個人主義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層次上體現其非國家主義、非個人主義的色彩,發揮其彌補“國家失靈”、“市場失靈”缺陷的功能。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社會才能“找到一種方法,使過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務于現時變化了的新需求”。(Alver,1995:38)
因此,現代西方的志愿部門或第三部門是在公民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無論它的創新實驗是成功打開了“后現代”的大門,還是流為“有益無害的烏托邦”,它與前公民社會的傳統慈善都已判然為兩。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邏輯下,傳統慈善的若干特點有時會“復歸”,如“近似原則”如今已成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準則。依靠這一原則,分散的捐助者的個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這些捐贈整合為統一的資助意向并服務于更大的社會目標。古羅馬時代已經出現的這一原則在“理性福音主義”時代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因為那時更強調遺囑自由和對捐贈者特定選擇的尊重。但在戰后,第三部門與公益事業的發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贈者個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則”也就日益擴大了適用性。如美國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蘭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組織之一“富蘭克林基金”(正式名稱為美國仁愛協會),以富蘭克林捐贈的遺產為本金,富氏原定的資助對象是:波士頓、費城兩地“有優良聲譽的已婚青年發明家”。但到1962年,富蘭克林基金會終獲法律許可,在cy pres的原則下把最初專為青年發明家而設的這筆錢用于資助醫學院學生及醫院職員,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開辦富蘭克林學院。(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則”賦予民間組織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條件下有效動員志愿捐贈資源用于事前并未設想的各種公益目標的權利,明顯地擴大了志愿部門的能量。可以說沒有這一原則就沒有今天的第三部門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拿但委員會曾主張:如果志愿的公益應受到鼓勵的話,則公益信托基金必須被賦予“它們的古代特權”(指cy pres等)。(Alvey,1995:38)但這種“古代特權”已經是公民社會條件下經過二次創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結果,已不是“傳統的”簡單延續了。
B.公益事業發展史的中國模式
共同體.社會.大共同體
如上所述,共同體——(個人本位)社會的縱向二分法與民族國家——公民社會的橫向二分法是解釋西方社會變遷的有效模式。因而從傳統共同體公益向近現代國家+社會(個人、市場等)公益轉變,再從國家與市場之外發展出第三部門便成了西方公益事業發展的主線。然而中國的情形則全然不同。正如筆者曾論證的(秦暉,1998-9),秦漢以來的傳統中國社會并非滕尼斯所講的那種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但地緣、血緣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體也并無西方中世紀那樣發達。在古代中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下無數小農的個體家庭直接作為“編戶齊民”而隸屬于皇權及其下延權力組織(吏權)。在這種結構中,小共同體無法取得本位地位,但這并非意味著個性自由與公民個人權利的成長,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權國家作為一個大共同體的強控制使小共同體權利的成長都成為不可能,就更談不上個人權利的成長了。于是在微觀層面,傳統中國因缺乏強固的小共同體紐帶而呈現出與西方近代化過程以個人本位消解了傳統共同體之后的狀況具有某種表面相似的“偽個人主義”狀態,“編戶齊民”之間無法發生廣泛的橫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紀在村社、采邑、教區、行會與宗族等類群體中所見的那種依附),因而彼此間顯得很“自由”,中國也因此很早就產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過程開始后才習見的許多現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但這種一盤散沙式的“自由”卻以宏觀層面上的某種“普遍奴隸制”為前提。(杜正勝,1990)
換言之,傳統中國社會(此“社會”乃廣義言之,不同于滕尼斯所言的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既非小共同體本位又非個人本位,因此不能納入滕尼斯乃至許多西方論者所習用的那種二分法分析框架。但中國人與人類其他民族一樣,在過去的時代是以群的狀態整體地存在的,而個人——不是生物意義上的單個人,而是每個人的自由個性、獨立人格與個人權利——只是近代化造成的公民社會的產物。馬克思的名言:“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就越顯得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群體”,盧梭的名言“臣民關心整體和諧,公民關心個人自由”,以及滕尼斯關于從共同體到個人本位的分析,都包含了同樣的意思。區別在于滕尼斯講的共同體只是“自然形成的”小整體,而馬克思講的古代個人“從屬于整體”是個很寬泛的概念:“首先是家庭,然后是擴大的家庭——氏族以及氏族發展而來的國家”。(見馬克思“巴黎手稿”)在馬克思看來,這些都屬于“自然形成的(按:顯然指氏族之類)或政治性的(顯然指“國家”)”“共同體”,因此馬克思的“共同體”概念要比滕尼斯講的大,而且它可能具有人為的目的性或“非自然”性。所謂“亞細亞國家”就具有這樣的性質:它與滕尼斯的“社會”一樣具有非自然的建構性,而且在建構中對自然形成的共同體造成破壞,但它卻絕無“社會”的個人主義基礎,因而也不可能形成“國家—社會”二元結構中的一元即所謂公民的公共生活空間。我們把這種超出了滕尼斯二分法的傳統結構稱為大共同體。
“編戶齊民”的古代中國就是個典型的大共同體。秦時的法家政治便強調以人為的“閭里什伍”來取代自然的血緣族群,甚至用強制分異、不許“族居”和鼓勵“告親”來瓦解小共同體,以建立專制皇權對臣民個人的人身控制。這樣的結構既非滕尼斯的“共同體”,亦非他講的“社會”,而且勿寧說正是它使得“共同體”與“社會”都難以成長,以至于到了市場經濟、市民社會與近代化過程啟動時,出現的不是一個“社會”取代“共同體”的過程,而是小共同體與“社會”同時突破強控制下的一元化體制的過程。—我國近代以來越是沿海發達農村,宗族組織越發達的狀況就是例子。
在中國文化中一直存在典章層面“獨尊儒術”、維護血緣宗法倫理而制度層面“漢承秦制”、實行法、術、勢治國的“儒表法里”傳統。在這一傳統下民間血緣共同體遠沒有像書面倫理宣稱的那樣受尊重,而地緣共同體更不發達,加之沒有可與政治權力抗衡的教區、采邑、行會、自治城鎮等組織,而大共同體—專制國家的組織能力則堪稱奇觀。從缺乏血緣、地緣公社對個人產權的約束這一角度看,中國“私有制”出奇地早熟,但正因為沒有小共同體自治的阻隔,“利出一孔”的大共同體統制色彩也十分突出。秦漢時代書中為我們展現了如下景觀:
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鄉有庠。……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后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織,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漢書.食貨志》)。
這段話給人的印象簡直是個紀律森嚴的軍事化農場,干活則“令民畢出”,里胥、鄰長分別把著里門左右點名;連收工時帶回柴火“輕重相分”,農閑時婦人夜織“必相從”都有規定。而從僅管五家的“下士”級鄰長,直到掌管12500戶的“卿”級鄉長,科層分明。這與人所共知的秦漢“五口之家”的小農經濟圖景似有矛盾。但實際上“偽個人主義”與大一統朝廷的強控制恰恰是互為因果的,小農的“一盤散沙”正是其得以為官府“編戶”的條件。若像歐洲中世紀那樣到處是村社、采邑、或者像魏晉南北朝那樣盛行“百室合戶,千丁共籍,”王朝的“閭里什伍”之制也就無法維持了。在缺乏小共同體紐帶的情況下,王朝正可以壟斷組織資源,達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同上)的效果。因此,“五口之家”的獨立小農是相對于小共同體的松散而言,“閭里什伍”的國家管制是相對于沒有小共同體自治而言,二者各反映了現實的一個維度。
就上面那幅圖景而言,里有兩塾,里胥監門之制,里胥受上命為吏而不為草根長老等等,都是多有佐證的事實。①至于集體出工、集體收工、那大概在多數情況下是理論上可能而實際上并不如此操作,尤其是一般農事作業大約是各家自己進行的。然而這種“令民畢出”的能力并非虛構,一旦朝廷興役,下令征調,從郡縣直到鄉里的大共同體組織系統是可以令民“畢出”應役的。人口僅2000萬、統一僅十余年的秦王朝能夠筑長城、戌五嶺、治馳道、組織龐大的徐福船隊,興建始皇陵、阿房宮這類今人亦驚其浩大的工程,正是靠的這種大共同體對編戶齊民的控制力,而這是中世紀西方不能設想的。
大共同體的束縛必然要伴以大共同體的“保護”,由此出現了古代中國的“國家福利”觀。《漢書.食貨志》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師古注:令習事也。);……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為了“編”戶,必須“齊”民,因此國家要“令貧者富,富者貧”(《商君書.說民》),實行“摧制兼并,均濟貧乏”的“抑兼并”政策,提供平均主義這種“公共產品”。極而言之,甚至出現王安石那種設想:“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洙,勢亦無自來。”(王安石:《兼并》詩)
當然,正如現實中大共同體的束縛并沒有達到天天集體上下工的程度一樣,現實中大共同體的保護也是打折和的。“七十以上上所養,十歲以下上所長”的圖景并非現實,但專制朝廷的確也有一套“社會措施”。俞偉超先生論述過的漢代里—社—單體制是一套行政主導(以“里”為本)的基層控制體制,其中的“單”就具有許多民政、社會職能(俞偉超,1988),單設有維持治安的“尉”,掌管單倉的“谷史”、管理買賣的“司平”,辦理社供的“廚護”乃至管理薪樵的“集”。他們如能各司其職,當時社會所需的“公共產品”便有了著落。
受抑制的小共同體福利
但大共同體本位并不會導致“古代福利國家”,今天的福利國家是建立在公民社會之上的,即使是俾斯麥、迪斯累里式的保守主義(非社會民主主義)福利體制,也是公民社會壓力的結果。而古代中國并無此種壓力,由此造成大共同體本位的束縛與保護職能是不相稱的。專制帝王“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結果,是許多“社會福利”反而辦成了社會禍害。標榜“右貧抑富”的抑兼并政策成了借國家壟斷而搜刮民財的“國家自為兼并”之舉;“均田制”并未保證耕者有其田,卻為有權者擴張等級占田制開路;以國家提供廉價金融服務為名的“青苗法”變成了官府勒索民間的大弊政;就是賈魯治河這樣的“善舉”也激成了“挑動黃河天下反”的元末民變。事實上歷代的民間造反,大都不是在朝廷放任無為的條件下、而是在朝廷大抑“兼并”的情況下激發的:從“利出一孔”的秦末,到“五均六管”的王莽,從以抑兼并始而以“西城刮田”終的北宋末“新政”,到宣稱“弗以累貧,素封是誅”的明末加派。而“莊主”帶領“莊客”造“官家”的反這樣一種景觀,更是對“大共同體保護”的一大諷刺。
總之,與提供社會保障但決不壓抑人權的現代“福利國家”相反,缺乏公民社會基礎的大共同體本位,是一種束縛有余而保護不足的體制。為了尋求國家吝于提供的保護,傳統中國民間便在國家不吝施加的束縛下仍然形成了一些公益機制與公益組織:
一是宗族公益組織,這是以往史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家提及最多的傳統公益形式。發達的宗族組織常有跨社區聯宗活動,它以建祠修譜、聯宗祭祖提供精神“產品”,以族規族法、宗族審判與宗族調解提供秩序“產品”,以族學、科舉資助基金與族人文集、族人叢書來提供文化“產品”,以族田族產及其收入舉辦的種種福利(義倉、族墓等等)來提供物質“產品”,等等。但必須指出,過去因種種原因而形成的關于傳統中國“宗族社會”的神話在嚴重夸大了宗族的能量。實際上中國歷史上宗族(含擬宗族)勢力強大到足以“自治”的情況主要是兩個:一是東漢末至北朝元宏改革前的宗主督護時代,那時大一統帝國解體,塢壁林立、強宗巨族稱雄,是我國歷史上一段罕見的小共同體活躍時期;一是近古乃至近現代我國某些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如東南沿海出現的宗族興盛,如下文所言,這種興盛已不能簡單歸之為“傳統”。除此以外,我國歷史上多數時空、尤其是更封閉更少受外來影響的時空,宗族的存在與能量都極為有限。而專制國家對“宗族自治”傾向也是打擊(而不是支持)的。“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官吏)多”之類的民謠遠比有文化的士大夫設想的桃花源式長老自治圖景更實在,“廢宗主,立三長”式的法家基層控制也遠比褒獎累世同居大家族的儒家說教更真實,而閭里保甲、什伍連坐的國家基層組織更比宗支流派的血緣系統要有效。
二是宗教寺院系統的公益組織。盡管“中國文化”的研究者常把“有宗族而無宗教”作為中國特色,但從社會公益角度看,宗教組織的作用實比宗族組織更大。(道端良秀,1967)尤其是佛教僧團組織在中國古代屢屢擁有很大勢力,它不僅在教義上如西方基督教一樣提供了倡導慈善、普渡眾生的救世倫理,而且創造了一套很有特色的寺院金融與信托制度,能進行有效的募捐、融資、基金運營與公益信托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有似于西方的教會慈善基金(楊聯升,1984:289)。唐以前僧侶遺產歸官,寺院積累所為有限,宋代建立了僧團遺產繼承制,宗教公益事業因而大有發展,研究者認為當時的寺院已成為“社會上最有規模及組織的民間慈善公益團體”,它提供了種種福利產品,“使幼有所養,病有所醫,饑有所食,老有所歸,死有所葬,行者得橋道而行,渴者得甘泉而飲”。(張志義,1990)
當時寺院所辦的公益設施,不僅有純屬慈善救濟性質的悲田院、養病坊、居養院、漏澤園、安濟坊、嬰兒局、慈幼局、舉子莊,有調節經濟作用的平糶倉,還有橋梁、道路、堤防、渠堰、燈塔、旅亭館舍等“地方建設”,甚至興辦學校,推行不以宗教為限的世俗教育。據著名宗教史家方豪統計,在《古今圖書集成》及各地方志所載的橋梁中,寺院募建者在福建占到橋梁總數的54%,江西、江蘇均占27%,浙江、廣東占到15%。又據錢穆先生稱,在南宋書院興起前,寺院“實擔當了社會教育之職責,”“陶鑄圣凡,養育才器,……教化之所從出”,如范仲俺,呂蒙正、韓億、李若谷、王安石等名儒,都曾寓于寺而苦讀。即使在書院教育盛行后,寺院仍占教育一席之地。
然而中國寺院的地位畢竟不能與西方的教會相提并論,其在公益上的作用也難于類比。西方中世紀教權與政權不僅分庭抗禮而且有時還居優勢,教會構成強大的“非政府組織”,而中國教權歷來依附于皇權,寺院獨立性有限。以上所述的宗教公益,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官督寺辦”的。唐代僧產繼承問題尚為懸案,寺院公益難以大興,宋代雖解決了此問題,但當時的“官督寺辦”公益本身就帶有政府借此耗散寺院之財的動機,到了明清時代,此種政府動機減弱,寺院公益的勢頭也就不及宋元了。(梁其姿,1997)合法宗教之外,中國民間非法宗教結社如漢之太平道、唐宋之摩尼教、明清之白蓮教、天地會等組織也有一定的公益職能,但其非法狀態既造成了它們的封閉性又使它們具有邪教的副作用,其公益性能否抵銷其“公害性”尚屬問題。
三是宗族、宗教之外的民間公益組織。這包括城市中的行會、同鄉會,以及象敦煌文書中的“社邑”之類民間互助團體。但中國的行會與西方的基爾特相比,亦如中國寺院與西方的教會相比一樣存在著缺乏獨立性問題。中國的同鄉會只是城里商人或士子中的小團體,而且是近代才興盛的,而真正的鄉域地緣共同體,如西歐之馬爾克,東歐之米爾,日本之町,在中國傳統中并不存在,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中國“自然村”并非村社,除了官府分劃“編戶”而形成的里甲、保甲和血緣性的宗族(并非必有)外,“自然村”沒有什么共同體色彩,自然也少有所謂公益。
但中國仍有非宗族的公益活動,在敦煌文書中反映的“社邑”,包括家居佛教徒組成的社團、百姓自愿結成的互助性民間組織和既從事祭社、互助活動也從事佛教活動的民間團體等三種組織。這些組織立有“社條”(章程),設有社長、社官、社老及錄事等職,有入社、退社手續,有“社歷”即財務帳目與“義聚”即公共積累,每逢活動則向社人發出“社司轉帖”通知其參加。社人多屬同一地域,但不同宗族,社人通過捐助與納贈籌集財力,用于一家一戶難以應付的喪葬、社交儀式、宗教儀典、水利建設與維護,以及民間的信貸合作等等。這類社團大多規模很小,如唐大中年間的儒風坊西巷社有社人34人(內有12俗姓,3僧戶)、景福年間某社社人13名(9個姓)、后周顯德六年女人社社人15名等等(寧可、郝春文,1997:1-25),有的還是因事立社,活動水平低,公益性較弱。顯然,我國傳統時代純民間非族性公益活動是不發達的。
總之,與西方前近代傳統共同體公益組織相比,我國傳統時代在國家組織早熟、控制嚴密的同時,民間公共生活并不活躍,“共同體公益”不發達,這是與傳統中國大共同體本位壓抑下的“偽個人主義”狀態有關的。
近代西方公益的東漸與傳統共同體公益的興起
1840年后中國在外部刺激與內部要求的雙重推動下走上了近代化的坎坷道路,現代民族國家與現代企業開始興起。“衙門與公司之外”的現代化也因而起步。但這一過程與西方現代公益的興起過程大有不同,這種不同除了所謂后發展國家外生型現代化與西方的內生型現代化之異外,更重要的還在于中西現代化賴以發生的傳統社會不同。西方的現代化是個從共同體(小共同體)到(個體本位的)社會的過程。這個過程以采邑、村社、行會、宗族等小共同體的解體為要件,而且初期曾經歷過“公民與王權的聯盟”,即初生的公民個人權利與(哪怕暫時還是傳統的)國家權力聯合起來首先擺脫小共同體的桎梏之過程。隨后才是發展了的公民權利與王權發生沖突。但在中國,傳統的大共同體本位使個人權利與小共同體權利都受壓抑,因而現代化過程起初便表現為“(小)共同體”與“社會”的同時覺醒,并且事實上形成了“公民與小共同體聯盟”首先擺脫大共同體桎梏的趨勢。只是在擺脫了王權的整體主義控制后,公民權利才可能進而拋開小共同體謀求自由發展。反映在公益事業的發展上,西方出現的是共同體公益與“父愛主義”的衰落,“國家十市場”公益的興起,而在中國,傳統時代受到大共同體壓抑的小共同體公益卻是在近代化中大有發展,并與西方傳入的公民社會公益形式并行乃至交融式地成長,形成了奇特的公益景觀。
西方式社會公益首先在香港、大陸通商口岸城市的租界乃至東北的俄羅斯人社區中發展起來,并擴展到所謂“華界”。到20世紀初,這些公益組織大都趨于本土化,同時使口岸城市的一些傳統社團也發生了現代化轉型,如上海的“廣東旅滬同鄉會”等外埠人傳統組織,在二三十年代大都從旅滬外僑社團那里學來了一套組織、活動、籌款、選舉等模式。尤其在抗戰初期的上海“孤島”中,非政府民間社團的作用一時大為凸顯,其在維持“孤島”社會秩序、展開善后救濟、發展市民公共生活等方面的能力不亞于租界當局。(廣東旅滬同鄉會,1938;上海國際救濟會,1937-1938)當時人稱民間社團是孤島的“第二政府”。實際上,這是在外敵入侵、民族危機深重的困難時期,在常規政府管理已失效的情況下由民間非政府組織從事市民自治的一次可貴的實踐,它證明了覺醒的中國人是有高度自治能力的。
在香港,現代公共生活與民間公益社團早期主要在西方人中流行,英國殖民當局并不提倡中國人的現代公民自治意識,而寧可維持華人的“傳統秩序”。但到抗戰以后,在現代潮流與民族覺醒的背景下中國居民的現代公共生活與社團意識也高度活躍,出現了大量全港的及區域性的社會組織。一些贏利部門與政府部門也捐資建立非贏利信托基金(典型的如1959年建立的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從事自主公益活動。(香港賽馬會,1989,1995;鐘聲慈善社,1950,香港公益金,1969),1967年反英運動過后,香港居民公共生活的熱情從政治領域轉向社會領域,使70年代民間基金會活動形成高潮,港府為此出臺了一系列法制安排促其發展。(香港布政司署社會事務科,1976)
在東北地區,20世紀初俄僑社區中出現大量自治組織,1917年十月革命后東北俄僑驟增,這些不認同蘇俄的僑民失去祖國的支持后只能自助自救,因而更促使俄僑公益團體發展,這期間先后成立了古魯金僑民救助會,阿爾緬僑民公會,謝拉菲莫夫卡食堂、猶太養老院、波蘭慈善會、索菲亞教堂貧民救助會、俄羅斯殘廢軍人聯合會、俄僑公會等組織。在東北的西方人也推進了此潮,截至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共建立了176個歐美人社團,其中有關教育的103個,醫療保健的38個,社會保障31個,其他4個。東北中國人的新式社團更從無到有,九一八前已有195個,其中半數以上是醫療救護類公益組織,其次依次為社會教化,兒童保護、經濟保障、失業保障。這些社團中1/4是“公立社團”,其余3/4都是“私立”即民間的。(沈潔,1996:178-179,191,294)
“西風東漸”影響下出現的新式社團對中國的醫療保健,農業、科學與教育、促進學術研究乃至提高公民權利一義務意識,參與意識,公共生活意識與自治意識都起了很大作用。(Hewa and Hove,1997:3-38)但對于廣大的中國內地與占有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來說,近古到近代的最大發展卻是“傳統”的共同體公益之發展。如前所述,儒家倫理雖然一直傾向于“敬宗收族”,但由于“儒表法里”條件下大共同體本位結構的壓抑,我國古代多數時空中農民微觀上是一盤散沙的“偽個人主義”,宏觀上是國家的“編戶”,小共同體組織并不發達。但明清時代隨著商品經的發展,南方尤其是東南沿海諸省宗族共同體發達起來,到近代這一趨勢更加發展。許多宗族已經從純精神上的一般認同與儀典上的聯誼組織發展成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發揮多種社會組織作用的民間共同體。以族田族產為例,到本世紀初廣州府屬各縣耕地中已有50%——80%以上是族田,廣東其他諸府這一比例也在30——50%左右。浙江浦江縣族廟公產占全縣地產的1/3,永康縣占42%,義烏縣一些村莊竟占到80%,閩,贛兩省也有類似情況。而長江流域族田則少得多:湖南省長沙府,湖北省漢陽府這兩個最發達的地區,各縣族廟公產占15—20%,而且其中族田比重僅為一半左右,至于北方各省,包括號稱中國文化之根所在的關中,河南等地,族產的比重都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秦暉,1998-1999)。從時間看,沿海許多地方的族產擴張是清代乃至近代現象,以廣東珠江三角洲為例。這里的沙田開發明前期是以官府為主導的,到明中葉沙田開發開始轉向民間主導,清乾隆時發明石圍技術,民間投資大增,一些大姓組織族人合股開發,宗族勢力于是膨脹起來,逐步排擠了官府的影響。清同治后朝廷財政危機,在廣東出售屯田,宗族公社因而控制了整塊沙坦,規劃大圍,到光緒時出現了具有濃厚商業因素的圍館與包佃,成為筑圍的投資方。
顯然,珠三角的“宗族公社”是在官府控制削弱與民間商業性沙田開發的背景下發展的。簡單地把它歸諸“傳統”是不合適的。勿寧說它正是大共同體本位傳統在商業化與近化化過程中被削弱的結果。實際上從乾隆年間起,廣東官府就已感到宗族勢大威脅到朝廷對地方的控制,曾幾次企圖強行分解祠產,搞族田私有化,但并無成效。擁有雄厚經濟資源的宗族(有些實際上是異姓人為公共目的聯合成的“擬宗族”)成為當地公共生活的組織者,在鄉治、教育、社會調解、公益福利方面都有很大影響。
這樣的宗族當然仍以傳統倫理為基本紐帶,并非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的新式社團。但如果說西方近代化初期傳統王權能與公民權利聯盟以瓦解小共同體本位,那末中國在類似階段中“傳統”宗族與公民權利的成長也未必就是矛盾的:它們至少都在消解著大共同體本位這一阻礙中國現代化與公民社會成長的主要桎梏。事實上,在清末廣東立憲派的地方自治運動中,就有宗族勢力的參與。當時聯合成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的38個集體成員中,就有5個“家族自治研究社(所)”。反過來,近代化的背景也影響到這些“傳統”宗族的內部結構。許多“宗族”已有異姓聯宗現象,族內實行公議制,族人參與程度高,與族長專制模式已有所不同。
反映在公益事業的發展上,便形成了近代中國“西化”的新式公益與“傳統的”(所謂傳統的是相對于“西方個人主義”而言,實際上如前所述,相對于中國的大共同體本位而言它也可視為反傳統的)小共同體公益的融合與互補。當代一些研究慈善問題的西方學者曾談到西方慈善觀念在東方得到佛教、儒教等“亞洲文化”慈善觀回應的現象(Heva and Hove,1997:185-230)。其實這除了人性相通之外,就中國而言恐怕還是與“公民和小共同體的聯盟”有關,并不僅僅是個“文化現象”。西式公益與“傳統”共同體公益的融合,產生了受到西方現代民間基金運作方式影響的“佛教慈濟基金會”(丘秀芷,1996)和傳統村落宗族公益與西化的基督教公益相結合的新式公益組織,這些組織有許多現在仍活躍于香港新界一帶的前鄉村地區。(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1985-86)。
“有公民意識的組織”與“非政府組織”:
中國第三部門與公民社會的走向
“公民與小共同體聯盟”的邏輯上的可能變成實際進程是要有條件的。近代中國嚴重的民族危機刺激起來的國家主義使這些條件消失。1949年以后中國進入了高度一元化的“計劃社會”(不僅僅是計劃經濟),嚴格意義上的企業即所謂第二部門也消失了,當然也就不可能有所謂“第三”部門的問題。但現代化的邏輯仍在頑強地為自己創造條件。70年代末中國走上改革之路,開始向市場經濟邁進,企業或“贏利部門”應運而顯,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的問題也再度浮出水面。
但是中西社會的發展路徑是如此不同,中西傳統社會與以此為起點的現代化進程是如此不同,中西公益事業的發展道路因之差異巨大,中西“第三部門”的生存、發展環境、面臨的問題與任務,就更是不同了。
西方的近代化是個共同體解體,共同體公益衰落的過程,然而中國的現代化初期卻存在著小共同體興盛的相當合理性,這就有個怎樣對待它的問題。相應地中國不存在“理性福音主義”歧視“應當受窮者”的合理性,以原始積累時期的冷酷對待不幸者,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應成為時尚。這是以愛心為幟的第三部門和志愿行動者在西方的“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并不時興,而在我們的“初級階段”卻必不可少的理由。
西方的第三部門是在已成現實的公民社會內部產生與發展的,它并不需要為實現公民社會而奮斗。相反,現代第三部門在“否定之否定”前的傳統對應物(如與現代行業協會對應的傳統行會,與現代志愿者對應的傳統教會)還曾經是通往公民社會之路上的障礙。在西方,建立公民社會的力量是擺脫共同體束縛的人們的經濟參與(其結果是“第一部門”即市場中的企業)與政治參與(其結果是第二部門即民主國家),而第三部門是作為這二者的結果自然產生的。如今人們或者希望它能捍衛公民社會的古典價值(即“新右派的第三部門觀”),或者希望它們能克服公民社會的弊病(即“新左派的第三部門觀”),但似乎沒有人把建立公民社會的責任寄望于她。然而,中國的第三部門卻需要為建立公民社會而奮斗,而且她的許多同仁也是以此為抱負的。因此,如果說西方第三部門的意義不限于一般的慈善與公益,它還意味著對公民權利與公民義務的新的理解,那么中國第三部門發展的意義就更是如此,因為它實際上要從爭取最起碼的公民參與空間做起。在某種意義上,西方第三部門所從事的是一項宏大的實驗,成功了西方的“后現代”文明可以更上一層樓,即或不幸流為“有益無害的烏托邦”,也不會影響西方公民社會已取得的基本成就。而中國的第三部門則背負著沉重的使命,它實際上與另兩個“部門”的現代化,即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建設同命運。如果它失敗了,中國將沒有任何現代化可言。
西方的第三部門是要克服現代社會中的“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具體地講,就是“民主制福利國家失靈”與“規范競爭的市場失靈”。而中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第三部門面臨的“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則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質。中國歷史上就存在著大共同體本位下束縛功能有余而保護功能不足的問題,改革前的舊體制雖號稱“大鍋飯”,但實際上社會保障的水平是非常低下的,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在受到舊體制嚴重束縛的同時卻沒有享受到任何保障,這是中國農民之所以能主動發起改革(而中國工人與東歐農民則不能)的唯一原因。換言之,中國的“政府失靈”并不是“福利國家失靈”。而是“大共同體本位失靈”。同樣,中國的“市場失靈”也不是市場機制本身的邏輯缺陷之凸顯,而是權力扭曲市場的結果。因此中西第三部門面臨的問題是明顯不同的。即以同樣對國家行為的批判而論,在發達國家,國家干預問題是個公平與效率兩難選擇問題,左派(社會民主派)要求國家干預以維護公平,而右派(保守主義者)認為國家干預會妨礙效率,但他們不會指責國家干預為權貴聚斂。這與例如緬甸的昂山素季指責國家干預為腐敗之源是全然不同的。市場問題也同樣如此,西方國家是“福利國家”太多了,“自由市場”太多了,所以人們要尋找“既非福利國家,又非自由放任”的第三條道路。而在中國問題也許在于“福利國家”還不夠,“自由市場”還不夠,因此,中國的第三部門一方面當然要認識到市場邏輯與政府邏輯本身的局限性,并有針對性地克服我們特定的“政府失靈”及“市場失靈”,但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政府有效”與“市場有效”,并積極地配合第一、第二部門中爭取有效政府與有效市場的努力——而這,是西方的第三部門完全不必操心的。
與此相應地,西方第三部門發展方向中的“非國家主義”與“非個人主義”之分或自由主義方向與社會民主方向之爭,對我們也是很少意義的。中國面臨的并不是“要福利國家,還是要自由放任”的問題,中國需要宏揚的實際上是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者都贊成的價值,需要否定的則是這二者都反對的價值。因此在現今的中國凸顯“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之爭”,實在是有些無的放矢。
中國第三部門無所謂“非國家主義”與“非個人主義”之分,但卻有它自己特有的兩分法:在現階段邏輯上存在“公民與小共同體聯盟”的狀態下,中國人是從兩個方向進入“衙門與公司之外”的領域的:一方面在城市中公民文化、公民意識的發展推動人們從事第三部門活動,但在現存體制的制約下,這些活動很少能以完全“非政府組織”的形式進行,而不能不帶有某些“政府部門”的痕跡。另一方面,主要在鄉村中,改革在走出“大共同體本位”桎梏的進程中出現了無數純粹的“非政府組織”,但它們未必都建立在明確的公民意識基礎上,其中不少還帶有明顯的“傳統”小共同體色彩。這樣,在中國現階段便出現了“有公民意識的(但未必是非政府的)組織”與“(未必有公民意識的)非政府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分離的現象。具體在公益領域,一方面出現了像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那樣具有現代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的“半民間半官方”公益組織,并且成功地組織了希望工程等一系列公益活動。(康曉光,1997(a)、(b))另一方面在農村出現了許多草根共同體、民間互助組織乃至“宗族復興”現象,它們的活動雖未必符合所謂“東方文化優勢”論或“新集體主義”的標簽,但的確提供了目前農村社區的相當一部分公益產品(秦暉,1995)。
這樣一種狀況是西方第三部門或公益事業發展史上所沒有的。它給兩者都造成了問題:前者的體制約束與后者的文化缺陷都有可能使它們受到局限,但另一方面,前者擺脫體制約束與后者擺脫文化缺陷的過程如能夠形成良性互動,則會給它們各自都開辟更廣泛的前景,中國第三部門的前途也許取決于這種互動,而如我們前面所述,歷史上并不是沒有這方面的借鑒的。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秦暉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