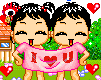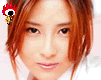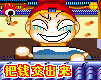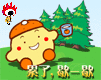| 誰,面向哪個東方?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29日 11:52 中評網 | |||||||||
|
A.G.弗蘭克的《重新面向東方:亞洲時代的全球經濟》[1](中譯本名為《白銀資本》[2])一書最近在中國引起爭議。從形式上看這是一本經濟史著作,但弗蘭克本人并非職業經濟史專家,中國的爭議雙方也不是。這本身就很耐人尋味。 以沙.柏林有所謂狐貍與刺猬之說,按他的比喻,學問家是狐貍,思想家是刺猬。這本書是一本典型的刺猬之作,思想犀利、批判鋒芒明確、視野開闊,的確提出了針對兩方面
弗蘭克以前曾經提倡依附理論,但現在這本書與依附理論顯然大相徑庭。依附理論的核心觀點之一是認為第三世界的落后是西方剝削造成的,但本書則強調東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興起。既然這樣,衰落的主要原因就很難歸咎于西方了。因此我不認為這本書的論點有利于所謂新左派,同時這本書當然是反駁了所謂現代性理論(據說自由主義是崇拜現代性的, 雖然這一點本身就有待證明),然而它主要不是說現代性不好,而是說現代性這個東西根本就不存在。既然不存在也就無所謂批判。因此也很難說這本書就不利于“自由主義”。于是這本書雖是刺猬之作,卻很難說到底刺了誰,它雖然思想新異,但很難說對當今各種思想對峙的格局能有什么影響。它在今日國內居然成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戰”的前沿,實在是件古怪的事。 因此我以為對這本書最好是先把刺猬當作狐貍評,從經濟史的角度看看它說的是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再考慮它的思想價值。 一 但從經濟史專業角度講,本書是缺乏說服力的。徐友漁與劉禾在本書資料是否扎實的問題上爭論很大,其實關鍵問題不在這里。從考證的角度講,專業漢學家之外談論中國的西方人,包括從馬克思、韋伯到布羅代爾這些大家,都不免粗疏的。像布羅代爾的書,談歐洲自然很有功力,一涉及中國,常識性問題一大堆,大至“中國人口增減節奏與西方類同”這樣的判斷,小至把甘肅而非新疆稱為“中國的突厥斯坦”、以及說華北農民用鋤頭而不用鐮刀來收割小麥(資訊 論壇)等等[3]。這些都不奇怪,何況弗蘭克這樣一個非專業學者。劉禾說他在資料上下過很大功夫,這是可以相信的。問題在于弗蘭克動用大量資料證明的只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中國在1400—1800年間的對外貿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銀作為貿易順差流入中國。但是弗蘭克從這樣一個老生常談的事實中推出了一個獨創性的新穎結論,即中國是當時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而這個推論恰恰既沒有什么實證基礎也沒有邏輯依據。鴉片之禍以前中國有大量外銀流入,中外學界不僅早有專家論及(如民國時期就寫成的彭信威《中國貨幣史》),而且我們的中學課本就一直以此來反襯西人輸入鴉片之害。但在弗蘭克之前的確誰也沒想到以此證明中國是“全球經濟中心”而西方只是“邊緣”地區。 評論界早有人指出這種以外貿盈余來證明經濟發達的“貿易主義”是弗蘭克此書的一大硬傷。所以說是硬傷,蓋因其不是個資料多少的問題,而是個不合邏輯的問題。眾所周知,我國現在就是世界外貿順差最大的國家之一(僅次于日本),而美國則是世界頭號外貿逆差國。這能說明我國如今是“世界經濟中心”而美國則是比非洲還要慘的最“邊緣”之地么? 如果延伸到中國歷史,問題就更大了。在中國古代外貿史上,外幣與貴金屬的流入主要在明清。而我們以往引以為榮的秦漢唐宋輝煌文明都是本國貨幣(包括貴金屬)流出時期,亦即外貿(如果可以把那時的各種中外經濟來往形式都稱為“外貿”的話)大量逆差的時期。 在流通黃金的漢代,中國的對外貿易就是長期逆差,黃金是比絲綢更重要的對外支付手段。[4]今人把當時的中外商道稱為“絲綢之路”,實際上史籍中漢的輸出通常都是黃金與絹帛并列,而以黃金居首。如《漢書.張騫傳》:“赍金幣帛直數十巨萬”;《漢書.地理志》:“赍黃金雜繒而往”;《鹽鐵論.力耕篇》:“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等等。當時在西北陸上“絲路”以黃金易“宛馬”[5]、在西南海上“絲路”以黃金易珠寶琉璃[6]的貿易極為活躍。而由于漢的貨幣經濟更為發達,漢方用作通貨支付的黃金在對方往往被視為一般商品:“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不知鑄錢,……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7]顯然,在這里如果有什么“經濟體系”的話,其“中心”只能是貿易逆差的漢帝國,而不是“順差”的對方。 唐宋時期中國的貿易逆差就更為明顯,這個時期中國貴金屬的極度稀缺據說就與此有關。貴金屬之外,當時中國一般通貨的大量外流更蔚為大觀,從“開元通寶”到宋代制錢,都曾廣行于周邊地區,幾成“國際通貨”,有似今日美國以美元支付逆差的結果。所謂“兩蕃南海貿易,(錢幣)有去無還”[8];“北界(契丹)別無錢幣,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銅(資訊 論壇)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矣”[9];“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10];“金銀銅錢之類,皆以充斥外國”[11];“泉州商人……載銅錢十余萬緡出洋”[12];等等、等等。有趣的是:當時的一般趨勢是中國經濟越繁榮,通貨輸出越明顯,而在經濟衰敗時期便會出現通貨回流。如宋金對峙時代南宋錢幣長期北流入金,但到南宋末的最后數十年間,卻出現了錢幣回流現象[13]。 實際上,農業時代世界史中相對發達地區貿易是逆差、通貨純流出的現象是大量的,相反的事例反而較少。在漢帝國黃金流向西域的同時,羅馬帝國的黃金也在向東流。早在共和晚期,為了與東方的交易等用途而流出的黃金便多得據說“可與19世紀加利福尼亞大淘金相比”,以至于引起金荒,一度使羅馬元老院下令實行黃金出口管制。[14]帝國時代與東方的奢侈品貿易耗費的金銀更多,據普林尼記載,當時流向東方的金銀總值達到每年一億塞斯退斯之多。[15]而當時作為羅馬最大富豪之一的普林尼全部年收入為一百萬塞斯退斯,一所科路美拉式莊園初始地價才7000 塞斯退斯,房價最貴的意大利地區60%的建筑價格都在2—20萬塞斯退斯之間。[16]相比之下每年一億的外貿逆差實足驚人。西亞、中亞和印度這片地區成了吸納羅馬和秦漢這東西兩大文明中心流出之貴金屬的貿易大“順差”地區,而穆罕默德之前六個世紀的不毛之地阿拉伯也是普林尼所說吸納羅馬黃金的主要地區之一。這難道可以證明這里當時的經濟是世界第一,而羅馬與秦漢兩大帝國反而是“邊緣”么? 在弗蘭克此書論述的16—18世紀,西歐不僅對印度、中國的貿易是逆差,對世界其余地區例如東歐、俄羅斯的貿易也是如此。用布羅代爾的話說: (西歐)貴金屬也經由波羅的海流向東歐。這些落后國家為西方提供小麥、木材、 黑麥、魚、皮革、毛皮,但很少購買西方的商品。實際上是西方逐漸促成這些國家的貨幣流通。16世紀與(俄羅斯)納爾瓦的貿易便是一例,……1553年英國人在(俄羅斯)白海港口阿爾漢格爾斯克開創的貿易是又一個例子。18世紀圣彼得堡的貿易也屬于這種情況。必須注入外國貨幣,才能指望俄國輸出西方期待的原料。荷蘭人執意用紡織品、布料和鯡魚支付貨款,結果他們失去了在俄國的優先地位。[17] 眾所周知,這個時期正是俄國彼得大帝大力倡導西化改革之時,而按弗蘭克書中的邏輯,俄國向西方大(資訊 行情 論壇)量輸出“但很少購買西方的商品”便證明它比西方先進很多,那彼得一世就可以說是“龍王”學習“乞丐”的曠古未聞之大傻帽、是使國家由“先進”變落后、由“中心”淪為“邊緣”的歷史大罪人了。 同樣按這個邏輯,明清有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因此她是世界第一。那么我們怎么評價秦漢唐宋?那可是大量通貨流出中國的時代,是大量外國商品傳入中國的時代,是“貿易”大量逆差的時代。如果用這種尺度評價,那兩千多年中華帝國歷史的大部分便成了大衰落的時代,一無可取的時代,龜縮于“世界體系之邊緣”的時代,只有到了明清間的這幾百年,才曇花一現,忽然崛起為“全球經濟中心”,爾后又莫名其妙地忽然衰落。[18]同樣根據這種尺度,全部產生于明以前的中國四大發明,以及恰恰出現在弗蘭克講的西方“邊緣”時代的產業革命前后科學技術的諸多突破都不知有何意義,而處于“世界體系中心”地位的明清王朝(也許還有明以前的西方中世紀?)又不知為什么在技術、制度與文化上都找不到什么突破——這樣的邏輯能讓人信服么? 應當看到,近年來在“重新發現東方”的時髦中經濟史學界除了“貿易主義”(應譯為重商主義)尺度外,也還有證明“東方”先進的其他研究成果。如從人口增長、勞動生產率推算等方面取得的的進展,王國斌、李伯重等的研究就是如此。然而弗蘭克在這方面汲取的東西很少,他的基本立論幾乎完全建立在外貿順差這一點上,此書中譯本取名《白銀資本》(據說這個書名征求了弗蘭克本人的意見)即因此而來。但是,即使考慮到重商主義之外的這些研究,是否就能得出“重新發現”者希望得出的結論,也是很可疑的。因為歷史上人口、土地、產量、生產率乃至生活水平的考證十分復雜、因而爭議極大,尤其涉及兩相比較時更是如此。許多“重新發現”都是有爭議的。倒是在外貿格局方面的確爭議不大——如前所說,明清白銀大量流入是誰都承認的常識。但從這一常識中能得出什么結論則是另一回事。正是在這一點上,弗蘭克豈止是激情有余而論證不足,他幾乎是只有激情而無論證的。 其實從情理與世界史上大多數事例而言,相反的結論恐怕要合理得多:農業時代的外貿需求一般主要是奢侈品需求,強大帝國的這種需求(可以貨幣支付的需求)往往高于衰弱國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初級工業化開始后大宗產品供給與大宗原材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與沒有投資需求的傳統農業國進行貿易,則它的大宗原材料需求會比大宗產品供給更易實現,從而也造成大量逆差。秦漢唐宋與羅馬屬于前一種情況,而18世紀前后的西歐屬于后一種情況。但兩者都不表明它們的經濟不如其貿易對象。勿寧說,在前重商主義條件下,明清時代中國對外貿易之從此前的歷史性逆差轉變為順差,倒更有可能是她開始逐漸轉為相對落后、相對“邊緣”化的體現。 二 以外貿順差的有無及多少作為經濟發達水平的核心尺度乃至唯一尺度,這是典型的重商主義標準。這樣的標準在某種經濟結構中可能是合理的,但在另外的背景下這種標準就會顯得荒誕。無論在農業時代的“前重商主義”條件下,還是在自由貿易的“后重商主義”條件下,前者如把明清的“順差”看成“世界體系中心”的證明,后者如把今日美國的“逆差”看成它的“邊緣”化。而“前重商主義”與“后重商主義”都還是就市場經濟本身的發展程度而言。如果放在根本非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比如說在J. 希克斯所說的“習俗—命令經濟”的背景下,這種標準就更成問題了。 然而許多人在進行“中外比較”或“古今比較”時,往往忽視這種背景的區別,從而導致許多隨意性極大的結論。這個毛病不僅弗蘭克為然,也不僅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為然,中國學者也常犯類似錯誤。 例如曾經有一種也是來自海外漢學而如今在國內流行的說法,認為古代中國具有比西方更發達的自由主義精神和自由貿易傳統。這樣說的唯一根據是:據說當時西方關稅稅率比中國為高。但且不說這里的稅率數字是否無可爭議,只需要指出:即使在關稅壁壘已成為自由貿易主要障礙的今天,僅僅以關稅稅率來衡量貿易的自由度也是有問題的。例如,波爾布特治下的柬埔寨根本就不征關稅,你能說它是貿易自由的典范么? 事實上,以稅率杠桿來調節經濟這一現象本身,比之直接以行政手段支配經濟來已是“自由”多多。在歷史上,關稅壁壘是重商主義的一種實踐,而沒有這種壁壘可能意味著“后重商主義”自由貿易時代,也可能意味著“前重商主義”命令經濟時代。在中國古代,政府對外貿最積極的時代是宋元而非明清。兩宋政府尤其是幅員縮小而軍費浩繁的南宋政府基于財政需要而鼓勵市舶貿易,市舶口岸多達20余個,還曾以抓壯丁式的方式強籍商人出海[19]。然而這種貿易并不“自由”。市舶司(類似海關)對進口貨“抽解”(征稅)10—40%,這一稅率比清代關稅要高許多。但關鍵問題并不在此:宋政府對外貿的最致命的控制實際上是在“抽解”后。納完關稅的貨物并不能直接進入市場,要先由市舶司統購統銷一大部分,號曰“博買”主要的舶貨如奢侈品、鑌鐵、藥材等全部收購,其他貨物也要由官府“博買”一半。“博買”后由官方編綱解運京師。“官市之余,聽市于民”[20],真正能“自由貿易”不過這些漏網之魚而已。 明清政府的外貿政策就更為保守。明代曾長期實行“片板不許入海,寸貨不許入蕃”海禁政策,完全取締民間外貿,以致于逼商為“寇”,造成了綿延不絕的“倭寇”問題。清代初年也曾厲行海禁,“片帆不準入口”。康熙中葉解除海禁后也只限四口(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通商,比宋元時代的口岸少得多。而且僅僅70年后又關閉了三口,只限廣州一口通商,實際上回到了半海禁狀態。在廣州一口又實行官府特許的行商壟斷制度,加上對越來越多的貨物實行禁止外貿(包括軍需品、糧食、鐵、絲綢、馬匹、書籍等)、對國民接觸外國人的嚴厲限制(如1759年《防夷五事》條規所規定的)等等,對“自由貿易”排拒豈是今日所謂的關稅壁壘或貿易保護主義所能比擬的? 清代的關稅稅則紊亂,黑幕重重,貪污勒索,若就國庫所得而言,其稅率確實不高,不僅低于英國。而且也低于兩宋。但這與自由貿易全不相干,只反映了當時以“農本”立國,以地丁錢糧為“正供”,當局視外貿為不正經,猶如偷雞摸狗,國家財政豈能寄望于此?有趣的是清代關稅稅率比更為看重市舶之利的兩宋為低,但卻比根本無所謂關稅、絕對禁止民間外貿而只搞破財換虛榮的“貢賜” 的明朝為高。可見在傳統帝國體制下關稅稅率(如果說可以按現代統計口徑稱之為稅率的話)的低下與其說與貿易的自由度成正比,不如說幾乎是成反比的。這無疑是典型的“前重商主義”特征。 在前重商主義體制下,官方不僅限制進口,尤其禁阻出口(這與重商主義只限制進口但支持出口正相反);限制的目的也不是保護國內產業,而是便于管制國民。清初海禁是為了對付鄭成功,弛禁后的外貿管制也是為了防止洋人“勾串內地奸民”[21]。因此如果說重商主義各國歧視外商是為了支持本國商民的話,傳統帝國在對外商有時的確“真是太寬容了”的同時,對本國商民卻極盡歧視、鎮壓乃至剿滅之能事,其手段一點也不“和平”。相應地作為“博弈”的另一方,當時的中國海商也常常以海盜的形式對祖國處在戰爭狀態,從明代作為所謂“倭寇”主體的中國民間海商武裝,到明清兩代的林鳳、林道乾、劉香、鄭芝龍鄭成功父子以至蔡牽、郭惟太等莫不如此,這其間哪有什么“用和平方式解決沖突”的文明規則!尤有甚者,明清當局與擴張到東方的西洋殖民勢力聯手剿滅本國海商的事也屢見不鮮,堪稱“規則”。明萬歷時“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菲律賓,西班牙人“助討有功”[22]。清康熙時官軍又與荷蘭人聯合進攻鄭成功在金門、廈門的基地。有人對中、西在菲律賓的“殖民”作比較后大為感慨,引為傳統“中國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和平更自由的證據。其實那時的帝國官府何止“沒有派兵去保護中國僑民”而已,他們還派兵去追殺過“中國僑民”呢!在當時的官方眼里這些“僑民”根本就是“盲流”或“叛逃”之類,巴不得借洋人之手除了他們,這里哪有什么和平與自由,有的不過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而已。 可見以關稅稅率高低來衡量自由程度,猶如用外貿順差大小來衡量經濟發達程度一樣,有時會產生怎樣的謬誤。 再一個例子是如今關于“第三部門自主性”的討論。西方所謂第三部門的自主性,是在公民社會的背景下針對這些部門對政府資助和交易性收入的依賴而言。然而在另外的背景下用這樣的尺度來比較,就會出現非常可疑的結果。例如北歐國家的第三部門經費依靠國家資助的程度常常高達90%,有論者批評這危及了第三部門的獨立,他們并指出某些發展中國家第三部門從國家得到的資助極少。但人們不禁要問:這是否能說明這些國家第三部門的獨立性比北歐第三部門大得多? 事實上,由于“慈善不足”導致“志愿失靈”的現象,在現代化早期的西方就曾引起過討論。如在1882—1902年間,法國依賴政府資助的公益會社成員增加了100萬,而“自由的”公益組織成員只增加10萬人。1910年法國社區互助協會收入中只有18.6%來自捐助,其余都是國家資助與交易性收入。[23]如今志愿提供公益的部門即第三部門仍然要依賴于以強制提供公益的部門(第一部門)和以志愿提供私益的機制(第二部門),其獨立性十分有限。對于發達國家而言這確實是個尖銳的現實問題。無法擺脫“強制產生公益”和“志愿產生私益”的局限性,的確關系到第三部門的存在價值。 但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第三部門面臨的最重要的還根本不是這種問題。例如:在這些國家假如第三部門對政府的依附只是由于政府資助了它們,那就已經是很大的進步。(這正如假使紅色高棉學會了只是運用關稅來調節貿易而不是公行滅商,那已經算是很“自由化”了)因為事實上在這里政府根本不資助第三部門,而第三部門仍然依附于政府。這與北歐國家政府大力資助民間公益組織但并不對之發號施令,完全是相反的。 當然,雖不對之發號施令,但如果財政上依賴國家太甚,國家對其的影響力肯定比完全靠民間自愿捐款與志愿服務的組織所受到的國家影響更大,推而廣之,帶有福利國家色彩的北歐第三部門組織的自主性不如公民志愿行動及自由捐款更發達的美國第三部門,也是可以想見的。換言之,以對政府財政資助的依賴程度來衡量第三部門自主性受到的束縛,這樣的論證在公民社會是可以成立的[24]。但放到其他社會類型就不行了。北歐第三部門的自主性無疑高于某些發展中國家第三部門,哪怕后者的政府完全不為NGO或NPO掏一個子兒。亦即上述那種衡量標準對這些國家根本是不適用的 可見,一種評價體系都是在一定前提下才能存在,而這種前提取決于給定的制度背景。弗蘭克的這本書沒有考慮這一點,而這并不是僅他如此。在漢學與中國學領域,這種問題是很多的。照我看,如果要說什么“西方中心論”的話,這種以西方背景下產生的問題(順差多少,關稅稅率多少和國家資助多少)作為衡量標準用之于其他背景的做法倒真正是不折不扣之“西方中心論”的。 三 并非職業經濟史家的弗蘭克寫作此書,不是出于考據的愛好而是出于歷史觀的沖動。而他的歷史觀之最大特點,我姑且歸納為“非‘進步’的全球或全人類整體史觀”。它一方面與“文化類型史觀”相對立,另一方面又與“進步的整體史觀”相對立。 對中國人來說,這種歷史觀最大的啟示還不是他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拒絕,而是他對“文化類型史觀”的否定。眾所周知,80年代以來的“文化熱”中這種史觀的影響是多么大。 大致而言,傳統時代流行的是強調宿命、神意、正統價值觀的傳統史觀,啟蒙時代以后,理性主義潮流下“進步的整體史觀”逐漸興起,它強調人類歷史的統一性、可解釋與可理解性,乃至可預期性,其說包括價值理性的善(“進步”)惡(“反動”或“落后”)判斷,以及工具理性的“客觀規律”論或“科學歷史觀”。唯物主義的社會形態演進史觀是典型的兩者結合:它既有“進步”優于“落后”的強烈價值取向,又相信“進步”取代“落后”是一種物理學式的客觀進程。但理性史觀也可以不采取這種二合一的形式:它可以不承認有“歷史規律”但堅持人文主義的“進步”價值觀,也可以擯棄人文主義價值而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冷酷“規律”。 如今這種史觀在中國與西方都在衰落——在西方是由于“后現代”的理性主義退潮,在我們這里則是由于以這種史觀為牌號的行為失去了信譽。于是韋伯、施賓格勒與湯因比式的“文化類型史觀”流行一時。它否定統一的人類歷史發展而代之以共時態的各種“文化”(或“文明”)大陳列,強調各種文化價值的不可通約性而淡化了普世人文價值的信念。這種史觀在文化是否有優劣之分的問題上存在兩種態度:承認文化有優劣之分,即以播化論取代進化論,這在把文化定義為民族性的情況下,有由文化優劣論演變為民族優劣論的危險。而徹底的文化相對論(文化無優劣)不但有無視普世價值的危險,而且它等于既拒絕進化又拒絕播化,至少對于不發達國家而言它決不是好主張。 尤其在中國,80年代以后文化類型史觀的流行一方面固然有脫離社會形態演進史觀窠臼的啟蒙意義,另一方面又有一種“荊柯刺孔子”的怪誕。90年代這種史觀的主流發生褒貶倒易(由推崇西化變為提倡傳統化),啟蒙意義也基本消失。“文化決定論的貧困”要求歷史觀的突破。弗蘭克此書是可供借鑒的。 《重新面向東方》開篇便打出“整體主義”、“全球學”的旗號。弗蘭克宣稱“不必考慮生產方式”,(61頁)又頗為自得地引別人批評自己的話說:“你對文化視而不見”。(73頁)他主張(不無武斷地)自古以來就有一個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其中的各個地區既無所謂“生產方式”的區別,“文化差異”好像也不起什么作用,唯一存在的似乎只有處于“康德拉季耶夫經濟長波周期”中不同位置、因而或者“上升”或者“下降”的不同經濟單元。他對韋伯、湯因比的文化史觀嗤之以鼻,對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強烈抨擊,既否定了從強調希臘羅馬傳統到強調新教倫理的各種“歐洲特殊論”,也反對“新非洲中心論、舊伊斯蘭中心論、甚至更古老的中國中心論、俄國特殊論等等”。他對那些熱衷于為“我的人民”建立特殊理論的政治家和那些“主張進行文化、宗教、民族、種族等等分析的學者”都極不以為然。(73頁)他宣布奉行“全人類的價值”,或曰“生態的價值”,以此來改寫世界歷史,至少是改寫世界經濟史。 這種既不同于傳統人類社會發展史,又堅決反對文化類型史觀的“新世界(資訊 行情 論壇)史觀”來源于以沃勒斯坦等人為代表的新左派“世界體系”理論。但沃勒斯坦的理論是批判資本主義的,而弗蘭克則干脆取消了“資本主義”這個問題,只以“西方中心論”作為批判對象。這雖然很武斷,但文化類型史觀的確是站不住腳。這不僅是價值判斷,而且首先是形式邏輯判斷。筆者曾提到一種悖論:設若某甲性喜吃米飯、喝老白干,某乙性喜吃面包、喝威士忌,我們就說二人各自屬于一種“文化”,如果有一人群A都象某甲那樣飲食,另一人群B都象某乙那樣飲食,我們就名之曰文化A和文化B。 但如果某一人群C實行飲食自由之制(即其成員可以自由選擇吃米飯或面包等等),而另一人群D則厲行飲食管制,只許吃某一種食品(許食面包而禁米飯,或者相反),那么這兩者是否也構成了不同的“文化”(姑且稱之為文化C與文化D)呢? 當然不是!C與D決不是文化之分。 這首先是因為A與B、C與D這兩種“文化劃分”是互悖的:在前一種劃分里分屬兩種“文化”的人,在后一種劃分里完全可以同屬一種文化:吃米飯者A與吃面包者B都屬于后一劃分中的“文化”C。反過來說,前一種劃分里同屬于一種“文化”的人,在后一種劃分中也會分屬兩種“文化”——比方說同為吃米飯者,如果他并不禁止別人吃面包,那他就屬于“文化”C,如果他禁止,則屬于“文化”D。這樣一來,在邏輯上“文化識別”就成為不可能。——請注意這是在邏輯上不可能,不是說的經驗邊界模糊問題。如果一個人既喜歡吃米飯也喜歡吃面包,你可以說他既有文化A、也有文化B的成分,因此很難識別。但這只是個經驗邊界模糊問題,你不能因此說文化識別這件事本身是沒有道理的,因為的確存在著只喜歡吃面包和只喜歡吃米飯的人,亦即文化A和文化B的確可分,盡管亦A亦B或非A非B的情況也不能排除。但如果只吃米飯者自己就可以既屬于此文化也屬于彼文化,而只吃米飯者和只吃面包者又都可以屬于同一文化,那這種“文化識別”還有什么道理可言、還有什么意義可講! 文化識別都不可能,更談何“捍衛文化”?豈止“捍衛”,一切關于“文化”的討論都將成為不可能。因為這種討論將出現更滑稽的悖論:在前一種劃分的意義上提倡文化寬容、文化多元或文化相對論,就意味著在后一劃分意義上只能認同“文化C”而不能容忍“文化D”,即在這一劃分中“文化寬容”之類命題是無意義的。而如果在后一劃分中主張文化寬容(即認可文化D的不寬容原則)或文化相對(肯定D與C各有價值,不可比優劣),那在前一劃分中的寬容、相對云云就全成了廢話。為了使“文化討論”有意義,在邏輯上就必須排除后一種劃分。這與討論者的價值偏好無關。你可以喜歡飲食管制,你可以說這種“制度”很好,或者說這種“規定”很好,但不能說這種“文化”很好,否則就沒法跟你對話了。 換言之,“文化”不可比,但“制度”有優劣。這本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如果你是個文化決定論者,你可以把一切差異都看成各有其價值的“文化”之別(即上述A與B之別),當然就無所謂孰優孰劣,——但你也就不要講什么“跨文化的全人類價值”了。反之,如果你不贊成文化決定論而想從“跨文化的全人類價值”出發,那你就拿了一把“普世性”的標尺,就有義務用這把標尺找出C與D之別,并以此普遍價值為標準論其優劣。當然由于“主義”不同,即對此普遍價值的認識不同,到底是C優D劣還是D優C劣可以有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判斷。“進步理論”斥責明清的專制制度造成了中國的“落后”,“世界體系理論”則抨擊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剝削了第三世界并造成后者的不發達,當然也可以兩者并用,讓中國專制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為中國的衰落共負罪責。但不管怎樣,放棄了文化類型史觀和文化決定論,那就難免要討論制度問題。 而弗蘭克卻想另辟蹊徑,既回避文化差異又回避制度差異,既要弘揚超越東西方的全人類普世價值又想解釋西方與東方的不同命運,而這種解釋又要避開“文化”與“制度”,這就使自己陷入了邏輯困境之中。評論者都指出弗蘭克大講了一通東方的光榮之后,卻未能成功地解東方衰落西方興起的原因(老實說,僅此一點就使他的這部著作意義大減,因為東方昔日的光榮誰都知道,人們想弄明白的不就是光榮失去的原因么?)。其實這不能怪他搜集的資料不足,而是他理論的邏輯困境使他無法解釋。他不能不求助于那不是解釋的解釋即所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25] ,以及痛罵西方人(不是“西方文化”,也不是“資本主義制度”,而就是——殺千刀的西方人!)搶劫了美洲土著后用贓款“買了東方快車的末等客票”。然而人們不禁要問:如果“西方人”不作惡,東方就能永遠光榮而西方只會永遠衰敗下去么?如果是這樣,那還有什么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可言?[26]如果不是這樣,光罵罵西方人作惡又能解決什么問題? 顯然,這已經不是弗蘭克個人的理論困境,而是這一類“非‘進步’的全球或全人類整體史觀”面臨的困境,它的背后反映的是當代西方新左派歷史理論的不成熟。這是不能只苛責于弗蘭克的。 四 其實對于西方新左派而言,從制度解釋退到“文化”解釋本是一種無奈,[27]而由“文化”解釋退到“不是解釋的解釋”就是更大的無奈。[28]從批判作為現存制度的資本主義,到鉆進形而上的象牙塔里從事解構理性的“文化分析”,再到把抽去了“制度”與“文化”內涵、沒有確定的價值取向、從馬克思到哈耶克、從沃勒斯坦到亨廷頓、連弗蘭克自己也無所逃于其間[29]的“西方中心論”作為批判對象,這種無奈是人們應當理解的。 當然如今批判“西方中心論”的并不只是弗蘭克這樣的新左派。從薩依德、阿明、伯納爾以下,許多亞非裔西方學者以批判此論表達了“非西方”人自我意識的覺醒,許多歐裔學者也以與此論劃清界限來表達西方人的歷史反省。這種自我意識和歷史反省無疑是極可貴的。但我以為“西方中心”之為“論”,實在是不知所云。 在西方學術界猶如社會上一樣,肯定有些人是存心歧視非西方人,抱有民族乃至種族偏見的,這是道德問題(或利益問題)而不是學術問題。比如有些當官的蔑視百姓,城里人歧視農民工,你可以罵他沒心沒肺不是東西,但說他是學術上的“職務中心論”或“戶口中心論”,我以為是高抬他了。 至于如果限于資料、見聞之囿作出了錯誤的事實判斷,那最好就事論事,在事實面前人人平等,在邏輯面前人人平等。無論過分高抬或貶低哪一“方”都同樣錯誤。有什么必要戴一頂“中心論”的帽子?以馬克思而論,以人類大同為理想的他大約不會存心蔑視中國人,他根據那時的資料對“東方”所做的論述有錯誤,今人糾正就是了,難道他對“西方”的黑暗就沒有批判?就沒有罵錯了或罵得過分之處?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看法姑且不論,對“西方”中世紀傳統、尤其是對被認作西方文明標志的基督教之抨擊亦可謂極端。難道人們就可以因此說他是“東方中心論”? 還有一種情況是人們從自己面臨的“問題情結”出發,借題發揮,借談論“東方”來說西方的事,或者借“西方”話題來說東方的事,尤其對于并非為考據而考據的刺猬們來說這太正常了。這種借題發揮無論褒貶,都是從“自己的問題”出發的,或者說都是“自己所處場境中心論”者。伏爾泰借褒獎“東方理性”在西方鼓吹啟蒙,馬克思借抨擊“東方專制”在西方鼓吹民主,包括這次弗蘭克借大捧“亞洲時代”來進行西方新左派自己的社會批判,在這一點上并沒有任何區別。為什么貶低了“東方”就是什么“中心論”者,而高抬了“東方”就不是?至于這些褒貶對還是不對,如上所述,可以就事論事。人家本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又何必把醉翁與酒混為一談? 總之無論哪一種情況,“西方中心論”都是個沒有意義的假問題。在前兩種情況下誰都不是什么“中心論”者,因而批判“中心論”猶如唐吉柯德戰風車,在后一種情況下誰都是“中心論”者,因而指責某人是“中心論者”實為最無須智力的“智力游戲”。 近20年來,西方文化批判很重要的一個趨勢即把視線轉向“東方”,這當然和西方本身的“問題情結”有很重要的聯系。實際上“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尤其刺猬們更是如此,狐貍們也不能完全擺脫,——刺猬和狐貍的區別也是相對的,沒有什么純粹的刺猬和狐貍。之所以近20年來人們“重新面向東方”,與自由主義的危機和左派思潮的危機同時存在大有關系。以前人們對西方主流體制的批判寄托于傳統社會主義(包括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由于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這個資源也產生問題了。后冷戰時代“自由主義的勝利”似乎也為時很短,無論是西方本身、轉軌中的東歐還是“南北關系”都又出現了許多問題。既然西方的主流話語和非主流話語、批判性話語和鞏固性話語都產生了問題,那么大家就都覺得好像東方是新資源的所在。這不光左派如此,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也有這個趨勢。用“東方(自然包括中國)經驗”來證明自由主義、尤其是保守主義理論,現在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前些年在中國很熱了一陣子的奈斯比特的《亞洲大趨勢》就是把亞洲當作自由主義的典范、并教訓西方人應該向“東方”學習的[30]。 的確,如今弘揚“東方”的不光是左派,甚至連休克療法的發明者J. 薩克斯也很推崇“東方”(與弗蘭克一樣主要也指中國),正是他向東歐介紹亞洲經驗、四小龍的經驗、尤其是中國改革的經驗。他分析東歐轉軌為什么失敗,就因為東歐社會福利太多了,工會太強大了。他向捷克總理克勞斯建議學習中國、學習東亞,它們不搞社會福利,它們把所有的社會負擔都推給家庭,于是它們成功了。中國更了不起,那里根本不許搞工會,怪不得資本家都爭相去投資!你們東歐能比么?[31] 于是在經濟轉軌問題上,左派、右派似乎都成了“東方中心論”者,都在以“中國的經驗”教訓歐洲人應當如何干。薩克斯教訓歐洲人應當學習中國禁止民間工會,崔之元教訓歐洲人應當學習中國搞“鞍鋼憲法”,——人們能把他們在“東方中心論”的名義下一鍋煮么? 顯然,盡管由于某種原因左右派都稱道“東方”,“東方”好像既是社會主義的希望所在,又是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希望所在,但我們沒有理由去忽視“主義”本身所給出的真問題,而沉迷于所謂“東方”還是“西方”這樣的假問題,并以那種所謂薩克斯和崔之元都是“東方中心論者”的昏話把人搞糊涂。 同樣,那種所謂馬克思與哈耶克等等都是“西方中心論者”這樣似是而非意義可疑的話也未必能給我們帶來多少新知。西方中心也好,東方中心也好,也許我們討論的都是偽問題。捧“西方”的人和捧“東方”的人各自內部之間的區別遠遠大于這兩種所謂的“中心論”之間的區別。而某些褒“西”貶“東”者和另一些褒“東”貶“西”者之間卻可能比什么“中心論”內部有更大的一致性。中國人和西方人對話,總有一個他是西方人,我是中國人的情結,更有一種自以為代表“東方”去與整個“西方”對陣的愛好,殊不知這種代表權是極為可疑的。假定中國人是一種立場,西方人是另一種立場,其實遠不是這么回事。討論西方中心論,要小心別把真問題掩蓋了。說馬克思和自由主義者都是西方中心論,其實兩者間最大的問題,如自由與平等的緊張關系問題,其實質化程度,遠遠超過了什么東方、西方論以及什么哪一段時間是東方、哪一段是西方的說法。不能把它一鍋煮,說這都是西方立場,而不去探討實質性的問題。現實社會主義衰敗了,自由主義也面臨很多問題,究竟人類的道路在哪里,這只能從普世的角度,而不是什么西方或東方的角度來研究。 記得前幾年《東方》雜志上有句話:誰是“東方”?小心地球是圓的,向東,向東,沒準兒又回到了原地。愿人們在“重新面向東方”時想想這句話。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秦暉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