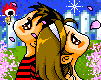| 《雍正王朝》是歷史正劇嗎?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29日 10:33 中評網(wǎng) | |||||||||
|
我并不認(rèn)同“文革”對“帝王將相文藝”的“左”傾討伐,但如果“帝王戲”越過了多元化的合理背景而畸形“繁榮”,恐怕也不正常。 今非昔比。但有趣的是從80年代起,史學(xué)界與文藝界都一反民國以來對“滿清”的貶斥,競相掀起歌頌清代帝王的浪潮。從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爾袞、孝莊文皇后,個個雄才大略,人人奮發(fā)有為,圣明君主之多開歷朝未有之盛。這種
但近來帝王劇出現(xiàn)了新景觀,這就是號稱“歷史正劇”的《雍正王朝》,它以大投資、高檔次、權(quán)威參與、 “大片”派頭、輿論宣傳加上市場炒作,掀起了空前的“雍正熱”。面對這個滿口現(xiàn)代話語的有為之君大紅大紫,一些史學(xué)家乃至愛新覺羅后人紛紛作證說雍正的“政績與人品”的確偉大,該劇從“大的氛圍”、“歷史事件”直到“器物層面”的細(xì)節(jié)都很“真實”云云。倒是據(jù)說改編所自的小說原作者二月河委婉地表達(dá)了他對這個“高大全” 的雍正難以認(rèn)同,對電視劇“把雍正塑成無私無畏的、一點缺點也沒有的人”頗有微詞。 的確,電視劇中的雍正與二月河小說中的形象已判若兩人,而與歷史上的雍正更是相差萬里。應(yīng)當(dāng)說這部片子在藝術(shù)上還是比較精彩的,要求創(chuàng)作的作品完全真實而不虛構(gòu)更無必要。問題在于該劇編導(dǎo)打著“歷史正劇”的旗號,否認(rèn)是在“戲說”雍正。該劇也確實是按照極鮮明的價值取向來編排的,并非消閑性的“戲說”可比。然而該劇不僅遠(yuǎn)離歷史的真實,而且這一遠(yuǎn)離所體現(xiàn)的取向更屬落伍。從“戲說”乾隆到“歪說”雍正,標(biāo)志著近年來帝王劇景觀的一個新發(fā)展,而如果說遁世的“戲說”本無害,欺世的“歪說”就更無益了。予以辯正,誠屬必要。 雍正是不是無私的“道德皇帝”? 歷史上的雍正政績雖無劇中夸張的那樣顯赫,但應(yīng)當(dāng)說還是個有為之君。傳統(tǒng)史觀因其殘暴而抹殺其政績的確不公,近年來史學(xué)界在這一點上是幾成共識的。然而在專制的“家天下”,有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奇。如唐太宗的殺兄誅弟、霸占弟媳、逼父奪位,武則天的連殺親子乃至親手掐死自己的女兒,明成祖的叔奪侄位、株連“十族”,隋文帝的謀殺小外孫而篡其國,等等,就反映了絕對權(quán)力導(dǎo)致絕對之惡的規(guī)律和專制極權(quán)具有的“道德淘汰機(jī)制”。歷史上九重之內(nèi)的宮廷陰謀、厚黑者勝,是不勝枚舉的。今天的歷史觀沒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國能力與其“得國之正”混為一談。過去人們以雍正“得國不正”而漠視其治國之績;如今的電視劇為張揚其治國之績而把他的“得國”說得高尚無比,其實都是基于同一種陳腐觀念。 當(dāng)然更重要的不在于觀念而在于事實。與歷史上的其他“得國” 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點在于他的“得國”不僅在后世常受譴責(zé),而且在他在位時就有“流言”頂著嚴(yán)刑峻法而四處播散。 為了平息指責(zé),雍正挖空心思寫了《大義覺迷錄》一書以自辯,我們今天看到的電視劇就是以這本奇書中的雍正自道為基礎(chǔ)而進(jìn)一步拔高的。 根據(jù)這種說法,雍正本無心于大寶,只是目睹時艱,“為社稷百姓著想”,又受了父皇囑其改革除弊之重托,才勉承大任,做了這“有國無家”、嘗盡“人間萬苦”的社會公仆。而他的政敵則個個陰險惡毒,以私害國害民,大搞鬼魅之伎,與他不僅有“改革”和“保守”的路線斗爭,而且有善與惡、光明正大與陰謀詭計的人品較量。他們不顧雍正的寬宏大量,怙惡不悛,死不改悔,不僅在雍正繼位前妄圖篡國,而且在整個雍正年間都猖狂作亂,從煽動社會風(fēng)潮、策劃宮廷陰謀直到發(fā)動軍事政變,為破壞“新政”、謀害雍正而無所不用其極。而雍正在忍無可忍時才發(fā)動正義的反擊,但依然寬宏待敵,仁至義盡。通過雍正自己粗茶淡飯,卻給大逆犯曾靜享用豐盛御膳、自己大義滅親殺愛子,卻對主要政敵“阿其那(狗)”不忍加誅等“感人場面”,電視劇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愛民第一、勤政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之浩蕩皇恩! 這樣的歪說也未免太離譜了。封建時代的宮廷陰謀往往成為千古之謎,說法眾多難以統(tǒng)一并不奇怪,可是在雍正問題上無論怎樣眾說紛紜,嚴(yán)肅的史學(xué)家沒有一個會相信《大義覺迷錄》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評價雍正政績的人在內(nèi)。因為該書的拙劣編造早在當(dāng)時就已是欲蓋彌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為禁書。正如我國一流清史專家集體編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簡史》(多卷本《清代全史》簡編本)所說:“由于胤?與隆科多合謀取得帝位,事出倉猝,密謀不周,以致漏洞很多。雍正即位后,花了很大氣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義覺迷錄》就是其中一個典型。”對這樣一種連雍正的兒子和指定繼承人都羞于示人的編造,這部“歷史正劇”的編導(dǎo)卻不僅全盤接受,還錦上添花,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馮爾康先生是國內(nèi)史學(xué)界倡導(dǎo)給雍正翻案的代表,曾譽(yù)雍正為“中國歷史上為數(shù)不多的比較杰出的帝王之一”。但馮先生對雍正偽造歷史的劣行也深有體會。中國素有標(biāo)榜直筆的“史官文化”,雖然實際上歷代帝王都干預(yù)修史,造成“實錄”不實,但像雍正那樣不僅偽造歷史,而且涂改檔案,偽造史料,則還是罕見的。在對照了雍正“加工”過的《朱批諭旨》、《上諭內(nèi)閣》等檔案與故宮中幸存的原件后,馮先生也感嘆曰:雍正“愛改史料,實是一個大毛病。”(馮著:《雍正傳》522頁)宮中檔案尚要改,何況《大義覺迷錄》這樣的宣傳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種愛好當(dāng)然不是閑得無聊,實在是他虧心事做得太多了。 就以雍正“得國”而言,雖然九重之內(nèi)的許多細(xì)節(jié)已成千古之謎,民間種種流言也未必可信(如改康熙遺詔“傳位十四子”為“傳位于四子”之說顯然不實),但今天已能確證的事實是: 第一,康熙暴卒于暢春園時,胤?與負(fù)責(zé)警衛(wèi)的隆科多控制著局勢,真情如何只有他們二人清楚。而《大義覺迷錄》所講的“八人受諭”(即雍正到暢春園以前康熙已向隆科多及七位皇子下達(dá)了傳位詔諭)之說純屬編造。他為何要編造呢? 第二,所謂“康熙遺詔”的漢文原件現(xiàn)仍存故宮內(nèi)第一歷史檔案館,它之為雍正偽造是鐵證如山的,馮爾康先生也指出:“毫無疑問,這個詔書是胤?搞的,不是康熙的親筆,也不是他在世時完成的。”(同上書62頁)當(dāng)然,馮先生并不認(rèn)同雍正“篡位”說,但他沒有解釋:不篡位為什么要矯詔? 第三,康熙末年諸皇子在朝臣中聲望最高的是皇八子胤,康熙本人最器重的是皇十四子胤,而胤?(后來的雍正)并無任何特殊地位。因而其繼位大出人們意料。這一背景是明擺著的。 第四,雍正即位后立即把康熙晚年的近侍、常傳達(dá)康熙旨令的趙昌誅殺,當(dāng)時在京的外國傳教士馬國賢稱此舉“使全國震驚”。接著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發(fā)的朱批諭旨全部上繳,嚴(yán)禁“抄寫、存留、隱匿”。這顯然有殺人滅口與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 第五,隆科多與年羹堯是雍正繼位的關(guān)鍵人物。隆掌宮禁,傳“遺詔”,而年則為雍正派往西北監(jiān)控爭位主要對手胤的親信。即位后雍正一時不顧君臣之禮地大捧他們,稱自己不識隆才,“真正大錯了”,說隆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dāng)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對年更稱為“恩人”:“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還檢討說“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聞。然而大位一穩(wěn),雍正很快翻臉殺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殺隆科多時還特別宣稱先帝臨終時“隆科多并未在御前”。(《東華錄》雍正五年十月)當(dāng)年被視為“遺詔”傳人的人如今竟被認(rèn)為根本不在場!如非殺人滅口而是僅僅因為其他罪過,這話從何說起呢? 此外,雍正即位后似乎害怕康熙亡靈,棄康熙常住的暢春園、避暑山莊而不往,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創(chuàng)建西陵作為自己的歸宿,等等,都是后人斷定雍正“得國不正”的根據(jù),這一切決不是“雍正的政敵造謠”所能解釋的。 顯然,雍正謀位成功只是“厚黑學(xué)”的成就,何嘗有絲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馮爾康先生所言,他“結(jié)黨謀位”至少在康熙五十二年(即康熙死前九年)已開始,“追求儲位已發(fā)展到不顧罹罪的程度”(同上書48頁)。當(dāng)然,專制時代宮廷斗爭無道德可言,“誰上臺手腳都不干凈”,雍正的政敵也未見得比他好。但無論胤還是胤,其治國思想都于史無征,他們之間的爭奪既談不上是道德之爭,也談不上是政見、路線之爭。 如果說雍正奪位問題尚有疑云的話,劇中其他地方對雍正的美化就更是“歪說”了。曾靜一案,雍正的處理即使從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殘忍地將只有思想異端的呂嚴(yán)沈三族株連慘殺,卻留下“現(xiàn)行犯”曾靜為他宣講《大義覺迷錄》,電視劇居然把這描繪成仁慈之舉!雍正的最后四年一直“安適如常”,他的突然猝死雖史無確證,但包括推崇雍正之治的楊啟樵、馮爾康等在內(nèi)的海內(nèi)外清史界多認(rèn)為是妄求長生迷信丹藥中毒而亡。電視劇卻描繪雍正長期抱病操勞,為治國而“活活累死”。雍正的政敵胤、胤被他囚禁后不久幾乎同時死去,死前被貶稱豬、狗,受盡虐待,一般都認(rèn)為是被雍正授意虐殺。而電視劇不僅將二人被鎮(zhèn)壓的時間由雍正初年移到雍正末年(以顯示二人一直搞破壞,而雍正一直忍讓),還描寫雍正寧誅己子也要謹(jǐn)守父訓(xùn),決不肯殺弟弟!如此等等。為塑造這個高大全的道德偶像,真是不遺余力了。 “天下讀書人”挑釁皇帝之說是否成立? 如果僅僅出于道德宣傳而抬高雍正倒也罷了。這部“正劇”的特點恰恰是按鮮明的觀念來剪裁、組裝的。這一觀念就是:“天下讀書人”清流誤國,結(jié)黨亂政,而雍正皇帝依靠家奴治國,推行“新政”,為民作主,兩條路線的斗爭貫穿“新政”始終。 為了表達(dá)這一主題,該劇精心編造,把歷史上本在雍正初年便被囚遇害,而且據(jù)乾隆說也“未有顯然悖逆之跡”(《清史稿.允傳》)的“八王”胤說成雍正一朝反對派勢力的總首腦,讓他猖狂活動直到雍正十二年(即雍正死前一年)虛構(gòu)的陰謀兵變被粉碎后才失去自由。在這個臆造出來的總司令麾下,聚集了編者想象得出來的一切惡勢力:從貪官污吏、關(guān)外滿洲八旗守舊貴族直到舉著孔孟牌位上街游行的“天下讀書人”。 也真虧他想得出來!極端反漢化的關(guān)外八旗守舊貴族與代表漢文化正統(tǒng)的儒家士人居然成了一條戰(zhàn)壕中的戰(zhàn)友,團(tuán)結(jié)起來與皇上作對! 片中屢屢出現(xiàn)關(guān)于“清流”乃萬惡之淵的現(xiàn)代話語,突出表現(xiàn)雍正敢于殺言官、誅諫臣、懲治“科甲朋黨”、為得罪“天下讀書人”而不惜“身后罵名滾滾來”的種種豪舉。 應(yīng)當(dāng)說歷史上的雍正的確有此傾向,他對科舉出身的文臣有看法,寧用家奴不用名儒,尤其對直言敢諫、特立獨行、以道義自負(fù)而“妄談國是”的古代士大夫清議傳統(tǒng)尤為厭惡。作為一個公然標(biāo)榜“以一人治天下”(《朱批諭旨.朱綱奏折》)的獨夫,雍正最不能容忍那種自許清廉而對君主保持某種獨立的“海瑞罷官”式行為,在他看來這種“潔己沽譽(yù)”的“巧宦”比那種唯君命是從的貪官更壞,也因此懲處了一大批“操守雖清”而奴性不夠的儒臣,如李紱、楊名時等。雖然喜歡奴才而討厭“海瑞”是歷代皇帝的通病,但傳統(tǒng)儒家意識形態(tài)還是要肯定“海瑞”的道德意義的。而雍正不但在行為上更不能容忍獨立人格、在理論上更是突破儒家道德觀,公開批判“潔己沽譽(yù)”的清流傳統(tǒng),因此他的確有典型性。 今天看來,傳統(tǒng)士人的確有諸多劣根性:在意識形態(tài)上,道學(xué)虛偽的一面造成言行不一之弊;在體制上,科舉入仕之途造成知識人與官吏身份合一;作為依附于皇權(quán)的權(quán)貴層,他們不僅難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獨立人格,甚至也缺乏西方傳統(tǒng)中那種抗衡皇權(quán)的貴族精神。而在某種情況下,儒生的迂腐確實不如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因此雍正排斥儒臣任用奴才,對雷厲風(fēng)行地貫徹其治國主張是有一定作用的,放在當(dāng)時背景下確也無可厚非。但從根本上說,雍正的“反儒”與現(xiàn)代意識對傳統(tǒng)儒家知識分子的反思是截然相反的:它反對的不是“天下讀書人”對皇權(quán)的依附性,而恰恰是對皇權(quán)的相對獨立性。 雍正這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電視劇作者對此的贊賞。豈止贊賞,電視劇實際上是青勝于藍(lán)地強(qiáng)化了這種“雍正思想”。它不僅把知識分子勇于講真話的一面視為大惡之尤,而且對連在傳統(tǒng)文化中也作為正面價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顏直諫的精神都加以嘲弄與攻擊,而把目不識丁的皇家奴才塑造為蓋世英雄。這樣的價值觀真叫人目瞪口呆! 如今人們常對“宮廷戲”、“辮子戲”充斥熒屏嘖有煩言,對清官、忠臣形象滿天飛而公民、人權(quán)意識萎靡不振多有批評。但老實說,像《雍正王朝》這樣連東林、海瑞式的書生意氣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揚家奴意識的作品還真少見。 《雍正王朝》在編造“歷史”上走得多遠(yuǎn),以下可見一斑: 雍正一朝的三大“模范總督”是鄂爾泰、田文鏡與李衛(wèi)。鄂爾泰通常都列三人之首,其治績與影響(包括雍正的評價)更勝田、李一籌。但電視劇卻突出田、李而隱去鄂氏,為什么?因為鄂是科舉入仕,而田只是監(jiān)生,李更非“讀書人”。但李雖讀書甚少,卻是個大財主,他是康熙末年“入貲(捐錢買官)為員外郎”而進(jìn)入官場的(《清史稿.李衛(wèi)傳》)。而電視劇為了突出“清流誤國、奴才救國”的主題,把這個李員外“變”成了“要飯的叫化子”出身、被胤?收為家奴后才苦盡甜來! 田文鏡、李衛(wèi)的確是忠心事君、政績卓著的名臣,但奴性太重也有消極一面。尤其是田文鏡習(xí)慣于報喜不報憂,他治理的河南年年以錢糧超額受表揚,但雍正八年大水災(zāi),田匿災(zāi)不報,還謊稱“民間家給人足”并嚴(yán)催錢糧,弄得豫民大量逃亡鄰省。鄰省告發(fā),雍正查明是實,卻為田開脫說:田“多病,精神不及,為屬員之所欺瞞耳”(雍正《上諭內(nèi)閣》,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類似情形發(fā)生多次。田后來留下罵名,固然有他為皇上辦事敢于得罪地頭蛇的因素,但老百姓也罵他同樣是不可否認(rèn)的。 總之,雍正厭“清流”而用奴才是實,但程度沒有那么甚,效果更沒有那么好。而電視劇在這兩點上是夸張得太離譜了。 雍正年間有過嚴(yán)懲李紱、謝濟(jì)世、陸生楠“科甲朋黨”一案。這其實是個大冤案。李、謝分別于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月各自上疏參劾田文鏡,據(jù)說是因“天下讀書人”受壓制而不滿。陸生楠并未參與劾田,只因是謝的同鄉(xiāng)而受株連,三年后又有人告發(fā)他有“抗憤不平之語”,遂罹文字獄之難。這三人的確都有“讀書人”的牢騷,但只是各自行事,何來“結(jié)黨”之說?更何況李、謝之劾田文鏡也不是沒有田的過錯。因此后人多稱三人之冤,就連今日推崇雍正的史學(xué)家如馮爾康等也認(rèn)為此案“未免冤抑”(馮著《雍正傳》219頁)。然而到了電視劇里,卻變成了三人帶領(lǐng)大批“讀書人”出身的官員,策劃于密室,點火于基層,發(fā)難于朝堂。李、謝相隔數(shù)月的各自上疏也變成了三人領(lǐng)銜的大批人一再集體上疏請愿鬧事。 循著“天子圣明,為民作主,奴才忠誠,書生可惡”的思路,電視劇幾乎把從清初以來的一切壞事乃至作者認(rèn)為壞而其實未必壞的事,都算到了“讀書人自私”的賬上。呂留良的反清復(fù)明思想本在雍正以前,且與清初的民族矛盾和抗清斗爭一脈相承,而電視劇卻把它說成是一些因“科舉不順”而心懷怨望的自私“讀書人”的反社會行為。曾靜的反清直接受呂留良影響,也是民族矛盾的體現(xiàn),而在電視劇里它卻成了“讀書人”反對“新政”的小丑行徑,其原因是“新政”使“我們讀書人都沒有了好處”! 科舉制度造成了“儒的吏化”,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皇權(quán)操縱下形成的“縉紳”階層,具有知識分子與專制官僚、“讀書人”與皇家奴才的雙重身份,也因此享有了皇權(quán)賦予的種種特權(quán)。在“官民一體當(dāng)差”與攤丁入畝這類改革中,某些縉紳出于私利而百般阻擾,但他們正是以專制官僚與皇家奴才的身份,而不是以知識分子和“讀書人”的身份這樣做的。電視劇對專制皇權(quán)大加歌頌,卻把一切罪惡歸咎于“天下讀書人”的清流、清議與知識分子的敢講真話(當(dāng)然是相對而言),這不是顛倒黑白么? 雍正的“有為”應(yīng)該怎么評價? 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他治國有方,在清前期“康乾盛世”中是個承前啟后的人。就個性而言,他的勤政與果敢也是比較突出的。但電視劇為弘揚“雍正思想”而把他神化成千古一帝,甚至以丑化康熙時代來突出雍正之治,則很成問題。實際上雍正的許多治績都有前人奠基、后人續(xù)力,其成就也不那么輝煌。 雍正打擊縉紳勢力,推行“一體當(dāng)差”,這實際上是清初順治時借“奏銷案”壓抑縉紳并從制度上縮小其特權(quán)之舉的繼續(xù)。至于“攤丁入畝”,作為“并稅式改革”在我國歷史上只是許多實踐中的一次,作為由人丁稅向土地稅的轉(zhuǎn)變也有上千年的歷史,就政策本身而言它起源于明后期“量地計丁并為一條”的一條鞭法,因此史家又有把攤丁入畝稱為“清代一條鞭法”者。而雍正時期攤丁入畝只是繼康熙時在廣東、四川等地的試行而逐漸推廣,其普行于全國已在乾、嘉乃至道光初,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人丁負(fù)擔(dān)問題也并未完全解決,像陜西關(guān)中的一些縣就仍然是“地丁屬地,差徭屬人”。更不用說“并稅式改革”本身就有一個“鞭(編)外有編”、簡而復(fù)繁的循環(huán)律,雍正的實踐并未打破這一循環(huán)。 電視劇在雍正“平定西北”問題上大加渲染。而實際上雍正時期恰恰是清前期西北邊政大失敗的時期,馮爾康的《雍正傳》曾以《調(diào)度乖方,西北兩路用兵的失敗》為標(biāo)題專節(jié)詳述,明確指出西北大敗“應(yīng)當(dāng)歸咎于雍正調(diào)度乖方”。事實上,清朝對西北用兵起于康熙,畢功于乾隆,雍正一朝雖有青海之捷,總的看來是敗多于勝,無足稱道的。 雍正設(shè)軍機(jī)處強(qiáng)化皇權(quán),也是電視劇闡釋雍正思想的濃重之筆。但姑且不論這種強(qiáng)化在今天看來是否值得歌頌,就算值得,我國歷史上專制帝王不相信朝臣而用身邊親信班子來架空“外朝”的動作在歷史上也不知重復(fù)過多少次,雍正的這一次又算得上什么大手筆?關(guān)鍵在于獨夫們既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只好借助親信,但親信地位一高也就轉(zhuǎn)化為新的“外朝”,下一位獨夫只好又物色一個新的親信機(jī)構(gòu)來架空之了。 本劇對雍正的頌揚到劇末出現(xiàn)一個“數(shù)字化”高潮:據(jù)說康熙末年留下的國庫存銀僅700萬兩,而經(jīng)雍正大治之后,他留下的國庫存銀已達(dá)5000萬兩矣!這數(shù)字其實是個巧妙的游戲:康熙末年國庫存銀是800萬而非700萬兩(見《清經(jīng)世文編》卷26),但這是康熙年間的低潮而非最高數(shù)字。而雍正末年國庫存銀,一說是三千余萬,一說有2400 萬兩(見同上,又見《嘯亭雜錄》卷一),只是在雍正五年一度達(dá)到過5000萬兩的最高額。編導(dǎo)妙筆生花,把康熙年間的最低數(shù)字(還有誤)與雍正年間的最高數(shù)字變成了“康熙末”與“雍正末”,一下就把三倍之增擴(kuò)大成了七倍多! 當(dāng)然,即使從800萬增至2400萬,也堪稱偉大成就。問題在于“國庫”之富不等于國民之富,朝廷之富也不就是國家之福。在中央集權(quán)專制主義的古代中國,國富民窮的狀況十分常見,國窮民富的情形也間或有之。兩宋朝廷長期困于財政拮據(jù),號稱“積貧積弱”,但宋朝民間的富庶與社會經(jīng)濟(jì)的繁榮實遠(yuǎn)超于盛唐。而明末李自成進(jìn)京時發(fā)現(xiàn)宮中藏銀達(dá)七千萬兩之巨,比雍正時的國庫要多多了;西漢末新莽朝廷滅亡時,僅集中于王莽宮中的黃金就達(dá)七十萬斤之多,其數(shù)據(jù)說與當(dāng)時西方整個羅馬帝國的黃金擁有量相當(dāng)!而明王朝與新莽王朝都是在餓殍盈野的社會危機(jī)中爆發(fā)民變而滅亡的。按編導(dǎo)的邏輯,崇禎帝與王莽這兩個亡國之君不是比雍正更偉大么?雍正時的民間與康熙時相比總體上如何,史無明證,但從前引雍正最欣賞的總督田文鏡在河南的“政績”看,是很難樂觀的。 雍正的確果敢有為,但“有為”并不一定就有進(jìn)步意義。某種變化是否能看作進(jìn)步,取決于一定的價值立場。從一個立場看來是進(jìn)步的事情,在另一個立場看來就可能是“反動”。 從全球論,雍正的時代英、荷早已完成資產(chǎn)階級革命,美、法的革命也已在醞釀中;從中國論,明清之際中國已出現(xiàn)所謂“啟蒙思想”,即真正的改革思想,黃宗羲的“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的“凡為帝王者皆賊也”,顧炎武提出以“眾治”代“獨治”,王夫之要求“不以天下私一人”。而雍正那種連傳統(tǒng)儒家規(guī)范他都嫌專制得不夠、而赤裸裸要求“以一人治天下”的獨夫言行,在這樣一個歷史進(jìn)步的背景下,就顯得非常刺目。 同樣是在一個世界范圍的歷史背景中,雍正重農(nóng)抑商和統(tǒng)制經(jīng)濟(jì)傾向,也不具有進(jìn)步性。在農(nóng)業(yè)政策上雍正只重糧食,經(jīng)濟(jì)作物只準(zhǔn)種在“不可以種植五谷之處”,結(jié)果導(dǎo)致一些地方官府強(qiáng)行毀掉已種的經(jīng)濟(jì)作物令農(nóng)民改種糧,致使因失農(nóng)時而絕收。雍正使政府干預(yù)強(qiáng)行進(jìn)入傳統(tǒng)時代一般不進(jìn)入的農(nóng)戶經(jīng)營中,導(dǎo)致了破壞性結(jié)果。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雍正認(rèn)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五月初四),他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yán)禁之外,無二議也”。(《朱批諭旨.孔毓?、焦祈年奏折》這樣摧殘工商、禁錮市場、統(tǒng)制農(nóng)業(yè)的強(qiáng)硬政策,在有清一代也屬最保守的,而且效果也極壞。 而電視劇對雍正的這些作為是避而不談的。 總之,《雍正王朝》為了塑造一個有為皇帝的高大形象,在對待史料上缺乏嚴(yán)肅性,在歷史觀和價值取向上更缺乏進(jìn)步性。這樣一部戲在學(xué)術(shù)進(jìn)步、思想進(jìn)步的今天居然創(chuàng)造了這樣的轟動效應(yīng),令人感到愕然! 無疑,《雍正王朝》的收視是相當(dāng)火爆的。考其原因,除了聲勢、頻道、時段上的優(yōu)勢外,我以為主要有兩條: 首先是人們已經(jīng)厭煩了泛濫已久的“戲說”式宮廷劇,因而對于風(fēng)格迥異的“正劇”有耳目一新之感。而這部片子也的確拍得很精心,可看性強(qiáng),有相當(dāng)?shù)乃囆g(shù)水平。 其次,經(jīng)歷20年后我們的改革已進(jìn)入微妙階段,利益調(diào)整劇烈,公正問題凸顯,社會矛盾增加,不確定因素增多,人們心理易于失衡,加上某種文化積淀的作用,人們隱約產(chǎn)生了某種期待:有人能以鐵腕掃清積弊,賜予社會以公平與安寧。而電視劇迎合了有些人的這種心理。僅就這一點而論,“雍正現(xiàn)象”便令人擔(dān)憂:人們難道真能指望一個雍正式的人物嗎?
|
| 新浪首頁 > 財經(jīng)縱橫 > 經(jīng)濟(jì)時評 > 秦暉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新浪網(wǎng)財經(jīng)縱橫網(wǎng)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wù) | 聯(lián)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wǎng)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chǎn)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