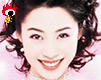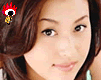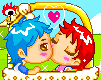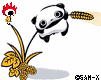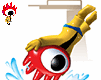盡快建立一套完整的投資基金法律制度安排
文中觀點僅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看法,并不代表作者所在機構的觀點;
對話者:
夏斌研究員: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司司長
巴曙松博士: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展戰略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后
巴曙松:
據報道,一度以統一立法為出發點的投資基金法,近期已經明確定為證券投資基金法,內容僅涉及證券投資基金、風險管理等,不包括產業投資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全國人大財經委透露,近期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對《證券投資基金法》草案的初次審議過程中,并未出現重大原則性分歧,因此,預計該法很有希望在年內出臺。
我的印象中,您一直是主張針對投資基金進行統一立法的。目前看來,為了盡快推出針對證券投資基金的證券投資基金法,統一立法原則出現了明顯的調整。這種調整的理由基本上可以歸結為:自國務院頒布《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以來,證券投資基金已有4年的實踐,現在出臺《證券投資基金法》的條件已基本成熟。與此形成對照是,風險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則依然處于探索階段,盡管各地大概已經有100多家風險投資公司和產業投資公司,但是規模都比較小。因此,針對風險投資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等的法規只能推后進行。
夏斌:
我之所以反復強調堅持統一立法,是基于我作為一名金融業研究者對當前中國基金業發展現狀和趨勢的判斷,其目的也是為了盡快建立一套針對整個基金業的完整的法律制度安排。首先針對證券基金進行立法當然有簡便易行等益處,但是,從整個基金業的健康發展來看,《投資基金法》還是應當盡可能不要退回到《證券投資基金法》。
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也證明,法律規范遲遲落后于經濟活動,不僅不利于有效配置資源這一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影響經濟成長的質量,而且易滋生不必要的金融風險,為日后的經濟活動帶來麻煩。因此,在目前這個階段針對投資基金立法,就必須要瞻前顧后,給市場發展留下空間。要參照有關市場經濟發展較成熟國家的立法經驗及曾經歷的教訓,在立法之初就應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對明天可能出現的經濟活動,對今天仍是萌芽、尚未成為主流的經濟活動,要提出規范發展的約束要求。例如資產管理中的有限合伙形式,盡管在《投資基金法》討論中涉及不多,但這恰恰是美國風險投資基金、對沖基金所采取的一項重要組織形式。
巴曙松:針對投資基金的立法當然要借鑒參考國際的發展趨勢和通常的慣例,同時也不得不考慮當前中國金融市場和法律體系發展的總體狀況和水平。實際上,目前看來促使立法機構放棄統一立法思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當前中國的市場發展狀況,那末,您認為統一立法原則與中國的國情之間有聯系嗎?
夏斌:當然,我們希望制定的《投資基金法》既要考慮市場經濟發展趨勢,也要符合當前中國的國情,這需要具體表現在法律條文上,也就是說,針對不同發展程度的市場,或者是我們目前的認識和把握程度不同的領域,在具體的法律條款內容的起草上可粗細結合。例如,看準的內容,法律條款應詳細的,則詳細羅列;當前看不準的,部門間分歧較大的,條款內容可粗略些。但“粗略”不等于“省略”。對一些已經出現或可能出現的資產管理中的一切相關問題,《投資基金法》都應以嚴謹的法律語言,作出本質性的、原則性的約束。具體的實施細則,可交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另行制定。
巴曙松:
2001年7月,您發表的一篇關于中國“私募基金”的報告引起海內外金融界的廣泛關注,我當時在香港金融界工作,就聽到不少對于中國金融市場躍躍欲試的投資銀行界人士討論您的這篇報告。從去年到現在,由于股市行情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應當說全國私募基金的規模在縮小。但是,私募基金作為一種資產管理活動形式仍存在。那末,您認為在當前或者未來的基金立法中,對于私募基金應當采取怎樣的立法取向?
夏斌:
一個比較完整的《投資基金法》,必須對私募基金活動作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法律制度安排。私募基金在中國存在并且正在不斷發展,已是不容爭辯的事實,絕對予以取締,已不可能,且違反市場原則;放任不管、不作出法律制度安排,易生事端,不利于市場秩序的穩定。因此,《投資基金法》不能因為個別人對此有不同的理解、監督管理制度安排上涉及部門間難以協調,而因小失大,回避對其作出比較完整的法律制度安排。
巴曙松:
如果我們從比較廣泛的角度來考察資產管理業務,從法律制度安排層面觀察,規范資產管理活動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四種:首先是代理形式,也就是投資者和管理者簽署委托合同,投資者不轉移資產的占有,受托管理者代表投資者,以投資者的名義進行資產管理,管理后果由投資者承擔。其次是信托形式,投資者和管理者簽署信托合同,投資者轉移資產的占有,受托管理者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資產管理,管理后果歸屬投資者或者指定的受益人。第三是公司形式,由投資者作為出資人按照公司法組建以投資管理為目標的公司,然后由公司董事會決議,將公司財產委托給專業化的資產管理者進行管理(其間簽署信托合同),投資管理后的損益由公司投資者按出資比例分享,投資管理者向公司收取受托管理手續費。第四是有限合伙形式,投資者作為有限合伙人,管理者作為普通合伙人共同簽署合伙協議,管理者以投資入伙的資產對管理活動承擔無限責任,投資者按出資比例分享投資收益并僅以出資額為限承擔有限責任。
這樣看來,一個完整的針對資產管理的相對完整的法律體系應當考慮到上述不同的資產管理形式。
夏斌:
確實如此。同時,在具體的立法中,一方面要根據不同資產管理形式及其具體的運行特點,另外,也必須要關注我國目前資產管理實踐活動中所遇到的矛盾、困惑與問題。例如,《投資基金法》應對公司型、有限合伙型資產管理業務要有明確界定和約束。上述資產管理中的代理形式,在《合同法》中已有約束,信托形式在《信托法》中已有約束。有限合伙形式,經濟生活中較少見,《合伙企業法》又從根本上限制采取有限合伙形式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公司型資產管理業務,經濟生活中已是不少見,但現有的《公司法》有關條款又限制、阻礙了其業務的發展。因此,準備頒布的《投資基金法》應做好與其他已頒布法律的銜接,對公司型、有限合伙型資產管理業務一定要有法律制度的安排。至于公司型基金的公司與《公司法》中界定的公司之間的運行差異,可通過《投資基金法》從立法技巧予以明確、銜接。另外,《投資基金法》應對市場中同一經濟活動作出同一的、不可隨意解釋的律制度安排。例如,對于證券投資信托,同一個投資者委托他人資產管理,中國人民銀行的有關規定,將依據《信托法》,是信托行為;中國證監會的有關規定,是依據《合同法》,是代理行為。同一投資者極有可能委托不同的機構進行同一的資產委托活動,若產生糾紛、訴諸法律,將是不同的結果,這在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不成熟期,似乎不太合適。 還需要強調的是,一個完整的《投資基金法》的出臺,要力求對現有法規不完善并應完善之處加以彌補。例如,基于當時的某些原因,對信托行為要轉移財產所有權這一本質特征,恰恰《信托法》未予以明確;公司型資產管理業務,其資金主要用于投資,但《公司法》對一公司投資比例又有限制;資產管理中委托資產雖由管理人管理,但資產的收益實際由委托人(收益人)享有,管理人只收取手續費。根據國際上稅法習慣,只對實際受益人征稅,不采取重復征稅制度。我國目前的稅制如何適應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等等。這一切,要求《投資基金法》的出臺,盡可能對推動我國資產管理業務發展的方方面面作出明確的法律制度安排,避免法律公布后在執行中的種種扯皮與困難。
巴曙松:現實地看,各種不同形式的資產管理活動,已構成我國經濟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不僅有其存在的需要,也有其發展的空間。但是對于這項市場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迄今為止,我國僅在已公布的《合同法》和《信托法》中有所涉及,中國證監會、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務院有關部門,對相關的業務活動作出了具體的規章。那,從總體上說,您認為已頒布的有關法律、規章還有哪些地方需要進一步完善的?
夏斌:
我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已有的法律規范不能涵蓋全社會各種形式的資產管理活動。制度建設落后于生動的經濟實踐。第二,已有的法律規范不能反映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對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中下一步可能或者說必然會出現的經濟活動,對其尚未留出予以規范的發展空間。第三,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目前對同一內容的經濟活動,有關部門間在對其的規章約束上存在不協調現象。這些不足,我認為有必要在針對基金的立法中積極予以彌補。
從當前的情況看,我認為全國人大和國務院有關部之間、國務院各有關門之間,應抓緊時間,講究效率,存大同求小異,瞻前顧后,粗細相宜,盡快結束對《投資基金法》歷經幾年的低效率討論,提交人大通過、頒布能涵蓋各種形式資產管理活動的《投資基金法》,以整頓我國的市場秩序,基本規范各種形式的資產管理活動,在擔心我國內需不足的宏觀憂慮下,促進和發展市場性投資活動。
巴曙松:目前看來,基于各個方面的原因,新的投資基金法草案去掉了原草案包含的產業投資基金等內容。法律名稱也由《投資基金法》改為《證券投資基金法》,將該法界定為專門明確證券投資基金的法律地位和規范其行為的法律;至于其他類型的投資基金將在條件成熟時,另行立法或修訂相關法律。這也許可以視為放棄了針對投資基金的統一立法的思路,并且形成基金立法中的一些缺憾。但是,換一個角度看,對于當前發展勢頭還不明朗的基金形式暫時不納入立法范疇,是不是也可以視為為未來的新的立法預留了空間呢?
夏斌:無論如何,一個完整的針對投資基金的法律制度體系,絕不能僅僅覆蓋證券投資基金。如果說產業投資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已經被決定不屬于此次草案的調整范圍,但我還是建議,應當對產業投資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要抓緊立法。既然已經開始制定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的法律,那么,對基金的基本運行原則也要有一些原則性的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