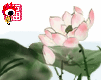| 地理環境、社會制度和李約瑟之迷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22日 18:23 中評網 | |||||||||
|
姚洋 一五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剛在內戰中取勝的印加帝國皇帝阿塔瓦爾帕帶領八萬士兵,在現今秘魯的高地小鎮卡加馬卡(Cajamaca)迎戰由文盲佛朗西斯科·皮薩羅帶領的168名西班牙入侵者。然而,這場看似力量對比懸殊的戰役的結果,卻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當望見印加人華麗的宿營帳篷和浩大的軍隊的時候,就連西班牙人自己也覺得是自投羅網。但是
很顯然,決定這場戰役的關鍵因素是西班牙人手中的長槍和鋼刀,而此次戰役也不是西班牙征服者以少勝多的唯一一場戰役,類似的戰役還發生過幾次。這些戰役對于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卻沒有消滅印加帝國的人口。真正使南、北美洲幾千萬印第安人幾乎滅絕的因素,是歐洲人所帶來的細菌和病毒。例如,麻疹于1520年由一個西班牙人的奴隸帶入墨西哥,在以后的一百年間,墨西哥境內的印第安人由大約2千萬銳減到160萬。病菌的殺傷力遠遠大于刀槍的殺傷力。 那么,為什么是歐洲人、而不是印第安人首先使用刀槍呢?為什么是歐洲人把病菌傳染給了印第安人、而不是反過來呢?這是杰瑞德·戴爾蒙德(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和鋼鐵:人類諸社會的命運》一書中所要回答的問題。事實上,戴爾蒙德的問題比上述問題更寬泛,他試圖解釋人類文明的地域差異:為什么人類文明起源于歐亞大陸而不是別的地方?為什么太平洋一些島嶼上的居民至今仍然過著刀耕火種的生活,而歐亞大陸的文明已經達到了無與倫比的高度? 戴爾蒙德對此的回答既傳統又新穎:所有這些差異都來自于各地區地理環境的不同。此說如何新穎,留待后面再說;它之所以傳統,是因為地理環境決定論在十九世紀就產生了。記得八十年代初剛上北大地理系的時候,胡兆量教授在《經濟地理概論》中首先講到的就是地理環境決定論,并對這一理論進行了批判。從此之后,凡是有地理環境決定論之嫌的言論,我都避而遠之,甚至持批判態度。在經濟學界,有一些人非常強調地理環境對一國一地經濟增長的作用。比如,原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等人對中國各省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現進行了數量分析,得到的一個結論是,省會城市離運河越近的省,其經濟表現越好。可是,運河是人所修造的,因此會不會有意往經濟發達的地區修呢?如此這樣的問題,讓我對地理環境的解釋力持懷疑態度。因此,當我看到戴爾蒙德又提地理環境時,心中不免生疑,同時也心生好奇,開始讀這部洋洋四百多頁的厚書。沒想到,此書的語言和敘事像磁力一般把我吸引住了,讓我在短短一周內讀完了全書。戴爾蒙德在書中并沒有提供新的史實,他的過人之處在于以新的視角把人類過去1萬年的歷史重新梳理了一遍。他的貢獻得到了應有的承認,此書獲得了普利策獎。 戴爾蒙德的本行是生物學,他對人類社會的興趣起源于他在新幾內亞的長期的田野工作。在和當地人的長期交往過程中,他發現,當地的許多人其實非常聰明,而新幾內亞人口的整體智力水平絕不低于歐洲人。但是,正如一位當地政治領袖亞力在三十年前問戴爾蒙德的:“為什么我們就是不如你們白人?”正是為了解答亞力的問題,戴爾蒙德才把注意力轉向了對人類歷史的研究。對于歷史學家或經濟史學家而言,歷史只從人類建立了社會組織開始;而戴爾蒙德的自然科學背景引領他把歷史的起點向前推進了一步,去研究人類脫離自然界的過程。 人類脫離自然界的起點是定居農業的產生。在此之前,人類過著采集和狩獵的生活,在本質上和動物無異。定居農業為人類提供了可以儲存的剩余,使得一些人可以從生產中解放出來,專門從事文化、藝術、管理和宗教等事務。與此同時,剩余的產生還導致了對制度的需求。一方面,人類需要一套所有權制度來界定剩余的歸屬;另一方面,人類還需要一個公共機構來實施對所有權的保護。同時,定居生活增加了人們之間的相互交往,因此也產生了對國家結構的需求。因此,定居農業是人類諸社會走向分岔的起點。在這方面,歐亞大陸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世界上有五個無可爭議的農業起源中心:美索不達美亞平原、中國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地區、中美洲地區、南美安第斯地區和美國東部地區。但是,位于歐亞大陸的美索不達美亞和中國所馴化的植物遠較其它地區多,并且,這兩個地區的作物的營養價值更高。比如,美索不達美亞馴化了小麥,中國馴化了水稻和小米。與此同時,這兩個地區也馴化了更多的今天仍然在飼養的大型家畜:美索不達美亞馴化了綿羊和山羊,中國馴化了豬,而其它地區要么沒有馴化任何家畜,要么只馴化了小型動物。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差距呢?戴爾蒙德認為,這是因為美索不達美亞和中國擁有更多的適合于馴化的野生作物和動物。非洲的動、植物資源也非常豐富,但適合于馴化的卻不多。比如,斑馬是非洲非常普遍的動物,但它的性情暴躁,經常咬人致傷;因此,盡管人們也嘗試馴化斑馬,但最后都不得不放棄了。另外,可馴化的動物還必須以草為主食、生長期較短、且體型較大,以便人類在較短的時間內以低廉的飼料換取他們的肉。在這方面,歐亞大陸具有絕對的優勢,它擁有72種符合條件的野生動物,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51種,美洲只有24種,澳洲僅有1種。在迄今為止人類飼養的14種家畜中,歐亞大陸就馴化了13種。 歐亞大陸不僅有利于動植物的原始馴化,而且有利于動植物的傳播。事實上,在人類文明的發育過程中,傳播比原生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歐亞大陸的傳播優勢來源于它的東西向的地理主軸,地球的氣候一般是以緯度來區分的,同緯度的地區基本屬于同一種氣候。歐亞大陸的東西向地理主軸因此使得作物和動物的傳播變得較為容易。相反,非洲和南北美洲的地理主軸是南北向的,它們的氣候在南北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因此阻礙了馴化動、植物的傳播。比如,公元前7000年左右在美索不達美亞發源的作物,到了公元前3800年就傳播到了北歐和英國;相反,在南、北美洲分別馴化的作物和動物,要經過5000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到達對方同樣的氣候地區,因為兩者之間的熱帶地區阻斷了動、植物的傳播。 然而,定居農業的后果并不總是好的,一個隨定居農業而產生的重大問題是病菌的傳播。對人類具有殺傷力的病菌都來源于動物,因此,馴化動物較多、人口密度較大的歐亞大陸成為病菌的發祥地就不足為奇了,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是歐洲人向美洲印第安人傳播了疾病,而不是印第安人向歐洲人傳播了疾病。 解決了農業和病菌的起源問題,這以后的事情便順理成章了:農業發達的地區首先產生了文字,隨后向周邊地區擴散;同時,技術在這些地區發展起來,人們學會制造刀槍等殺人武器;最后,社會組織也變得日益復雜,君主制度等集權體制代替了較為平等的部族首領制。這些文明的分岔現象因此可以看作是定居農業的副產品,進而又是各文明所處地理環境的產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戴爾蒙德對待地理環境的態度和十九世紀地理環境決定論者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在后者那里,地理環境起作用,是因為它改變人的性格:生活在溫帶的人更勤勞,而生活在熱帶的人更懶惰。戴爾蒙德所反對的,正是這種種族主義的觀點。他的書的起點是,人類社會不分種族,生來具備同樣的平均智力水平。人類諸社會之所以形成今天這樣巨大的差別,是因為各個社會所處的地理環境限制或鼓勵了它們的發展。戴爾蒙德將人類社會分岔的起點上溯至農業的起源,在那個起點上,人類無疑受到地理環境的巨大約束,由此而產生他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戴爾蒙德沒有解釋的,是各大洲內部的差異。定居農業是人類諸社會分岔的起點,在此之后,分岔非但沒有停止,而且日益加劇。以今天的眼光觀之,解釋這些導致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的文明分岔也許更為重要。這其中,最令人著迷的莫過于李約瑟之迷:中國在古代領先世界一千多年,但到近代為什么卻落后了呢?近代世界的分水嶺是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發生在歐洲的工業革命,因此,李約瑟之迷也可以表述為: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 關于這個謎,有許多解釋。戴爾蒙德的書主要討論人類社會脫離自然界時的分岔,但在書的結尾處,他也給出了對李約瑟之迷的一個解釋。他的出發點仍然是地理環境。如果我們隨意地查看一下歐洲和中國的海岸線,馬上就會發現,歐洲的海岸線犬牙交錯,且近海島嶼眾多,而中國的海岸線平滑有序,近海幾乎沒有大的島嶼。前者有利于形成眾多競爭的小國,而后者則有利于形成大一統的帝國,從而也決定了兩個區域不同的發展軌跡。戴爾蒙德以航海為例來說明他的觀點。發現美洲大陸的哥倫布生于意大利,為了他的偉大的航海計劃,先后投靠了三、四位歐洲君主,最后才得到西班牙皇室的支持。如果歐洲統一在任何拒絕了哥倫布的君主之下,則歐洲對美洲的殖民可能永遠不會發生。相比之下,中國明朝的鄭和的命運就要壞得多了。鄭和七下西洋,其艦隊規模之大,遠不是哥倫布所能及的。但是,在大一統的皇權之下,宦官一旦失勢,鄭和的遠洋航行也就終止了。因此,戴爾蒙德將中國的落伍歸咎于其完整的地理環境所造成的大統一的國家體制。 但是,這個解釋雖然對中國在近代的落伍有一定的解釋力,但無法解釋中國在此之前為什么能夠領先世界一千多年。與戴爾蒙德的解釋相類似的是中央集權的稅收假說。1998年夏天,我到美國巴爾的摩市參加留美經濟學會的夏季年會,同室的是一位明尼蘇達大學的博士生。這位美國仁兄高高大大,研究的卻是中國經濟史。他的博士論文是關于中國南宋時期的稅收制度的,其基本觀點是,在南宋時期中國已經有了工廠化工業的萌芽,但卻被高度集權的中央稅收所扼殺了。南宋時期,江南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是,外患頻仍的南宋王朝為了戰爭而大肆向工商業課稅,而且,稅收高度集中,地方政府沒有任何稅收留成。由此一來,地方官員無心扶持當地工商業的發展,相反卻加強稅收力度,以向朝廷交差了事,工商業因此在重賦之下凋敝了。2001年夏天,我到廈門參加留美經濟學會在國內召開的年會,恰巧又與這位老兄同住一室。原來,他已經在臺北中研院下屬的經濟所做了兩年的博士后,并剛剛娶了一位臺灣太太;同時,他的研究工作也有了進展,真是雙喜臨門。他告訴我,為了更好地理解宋代財政,他不得不了解宋代以前的中國歷史,為此,他已經回溯到春秋戰國時代了。雖然我們用英語交談,但我相信,他的古文閱讀能力肯定大大地超過了我的。幾年的研究更堅定了他當初的看法,即南宋時期高度集權的稅收體制是打開李約瑟之迷的鑰匙。 然而,這個解釋也存在一定的困難。如果南宋時期因為戰爭而不得不把稅收全部收歸中央,明、清兩代經歷了幾百年的和平時期,難道各位皇帝就沒有學會“放水養魚”的道理?更一般化的解釋來自于黃仁宇。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書中,黃仁宇引用諾斯等人的觀點,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在于財產所有權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比如,明末清官海瑞的斷案方針是:“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平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海瑞是封建官吏的典范,他的思想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黃仁宇認為,這種思想不顧“內在的公平”,而只意在維持由血緣關系、社會身份和道德品質所支撐的社會等級制度,從而扼殺了社會的商業動機,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也就不足為奇了。 黃仁宇從產權保護方面所做出的解釋具有相當強的說服力。一方面,他對中國古代社會以德治代替法治所造成的后果有深刻的洞察(讀一下他的《萬歷十五年》,感受一下萬歷皇帝在群臣的道德圍攻下的無能為力,我們就會意識到這一點);另一方面,他對諾斯的理論的引用也貼切到位。但是,問題在于,所有權的建立是否真如諾斯所說的那樣,是資本主義起飛(更確切地說,是工業革命)的充分條件嗎?如果真是這樣,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理論,乃至大部分經濟學都可以廢棄了,而這些領域的發展恰恰說明,所有權不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因此,要解開李約瑟之迷,我們還需要新的理論。 尹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陷阱假說就是這樣的一個理論。在于1973年發表的《中國歷史的式樣》一書中,尹懋可認為,中國之所以在工業革命之前一千多年里領先世界,而后又被歐洲所趕超,是因為中國受到人口眾多、而資源匱乏的限制。由于中國人口眾多,她就必須全力發展農業技術,以至于到歐洲工業革命時,中國的農耕技術遠遠領先歐洲,這包括復種、灌溉、密植、耕種工具的改良等等。但是,農業技術的改進所帶來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輪的人口增長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長又進一步帶動農業技術的改進。如此往復,中國在較高的農業水平上維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國工業的發展卻受到了有限的資源的約束。尹懋可列舉了許多史實,試圖證明中國在明末和清朝已經遭遇到了資源約束的瓶頸,從而無法在舊有的技術條件下取得進一步的發展。由此中國便進入了一個“高農業水平、高人口增長和低工業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尹懋可關于中國農業的論述具有相當的真理成分,但他關于中國工業的解釋卻缺乏說服力,甚至有邏輯錯誤。所謂的資源約束都是相對的,不存在絕對的資源約束。如果我們相信中國在明清時期就遭遇了無法克服的資源約束瓶頸,則我們今天就可以躺倒睡覺了,因為任何努力都不會有回報。尹懋可大概也認為資源約束是相對的,中國在明清時期的資源瓶頸是相對于當時的技術而言的。但是,這里有一個邏輯問題:尹懋可想解釋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新的工業技術,卻又把新技術當作緩解資源約束的前提條件了。 但是,只要稍做經濟學的修改,尹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假說仍然可以解釋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近代工業。我們可以回到中國人多地少的事實,考察由此而帶來的工農業回報的差距。直到現代時期,中國的農業資本回報一直高于工業的資本回報,這可以從南方大量存在的不在村地主現象得到證明。這些地主因為在城鎮擁有工商業才離開農村(或者他們原本就居住在城鎮),但又無一例外地在鄉下購置土地。如果這樣的人只是少數,我們還可以說,這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脫掉土財主的習氣;但是,大量不在村地主的存在就不能簡單地以個人偏好來解釋了,而只能是因為農業的資本平均回報高于工業的資本平均回報的緣故。據葛劍雄在《中國人口簡史》中的估計,在清代以前,中國的人口一直在6千萬到1億之間徘徊;但是,經過清代的“人口奇跡”,中國的人口在十九世紀中葉已經達到4.5億。可想而知,在相對狹小的可耕地上要承載如此眾多的人口,土地的價值必然增加。高額的土地回報誘使人們投資農業,工業因此缺少資金,無法發展起來。相反,歐洲由于人口密度低,較低的農業水平也足以支撐人口的增長,工業回報因此高于農業回報,資金向工業集中,歐洲因此向一個高水平的均衡發展。 因此,經過修改之后,尹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假說可以解釋西歐和中國正反兩方面的事實,而且,這是一個基于地理環境的經濟學理論。我在這里還想補充一些細節。依我看來,尹懋可的理論有賴于兩個基本前提:一個是人口的增長符合馬爾薩斯原理,即當人均收入超過長期均衡工資時人口有的正的增長,相反,人口出現負增長;另一個是工業具有規模經濟。第一個假設保證農業技術提高所帶來的剩余被人口的增長所吞沒;在十九世紀及以前,這個假設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第二個假設也具有現實性,因為任何工業生產都涉及一定的起始成本,而起始成本帶來規模經濟(比如,電信業就是這樣)。如果工業中不存在規模經濟,則即使工業品的價格較低也會有人去生產,因為贏利總是可能的。這顯然會破壞尹懋可的理論。反過來,如果工業具有規模經濟,則只有當規模超過一定限度之后,投資工業才會開始贏利(如電信業,只有客戶群達到一定規模之后才會贏利)。此時,尹懋可的理論預測才會成立。 以上這些理論都是在經濟學范疇內提出來的。在此之外,還存在其它一些非經濟學的解釋。第一個這種解釋是戴爾蒙德所說的“英雄理論”:技術創新是少數“英雄”的活動,而“英雄”的數量—以及創新的數量—取決于人口的大小和技術創新的難易程度。林毅夫教授持這種觀點。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在歷史上能夠領先世界,是因為當時的技術比較簡單,可以靠經驗積累來完成,所以,中國較大的人口更容易產生技術創新。但是,現代技術不是建立在經驗、而是建立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的,人多因此并不能保證更多的技術創新。但是,這個解釋所忽視的,是工業革命并不是以現代科學為前提的,如同諾斯所指出的,工業革命(公認的時期為1750年-1850年)比現代科學和技術的結合(公認為十九世紀后半葉)早了近百年。事實上,工業革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身處其高潮的亞當·斯密沒有注意到它,而與他同時代的馬爾薩斯更是對人類前景持悲觀態度。工業革命中的許多技術是經過許多人長時間的經驗積累而成熟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但事實是,瓦特只是在前人的發明上做了重大的改進,以使得它更為實用。蒸汽機的雛形是英國人托馬斯·薩瓦瑞(Thomas Savery)于1688年發明的,真正實用的蒸汽機是由另一個英國人托馬斯·紐可曼(Thomas Newcomen)在1705年發明的。但是,這種蒸汽機極其浪費能源,因為它不使用壓縮空氣。直到1768年,瓦特才發明了更加實用的蒸汽機,但人類還要等到15年之后,才能看到它被用來驅動車輪。 李約瑟本人也給出他自己所提出的謎語的解答。他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產生現代科學,是因為中國人重實用,而輕分析。這種說法有多大合理性,還有待于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去評判,我在這里想指出的是,即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確和歐洲人有差別,這種差別也無法解釋工業革命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發生,因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工業革命并沒有依賴于科學的幫助。 也有人從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特別是科舉制度來尋找李約瑟之迷的答案。科舉制度不僅扼殺了青年人的創造性,而且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激勵結構,誘使人們都去爭過科舉的獨木橋,唯讀書、做官是尊,而輕視發明創造和商業活動。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過于寬泛,容易讓我們忽視一些具體的東西。同時,一個好的激勵結構也未必是產生工業革命的充分條件。如果尹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假說成立的話,一個好的激勵結構也就只能激勵更多的農業創新,工業革命照樣不能發生。 看來,以上關于李約瑟之迷的任何解答都不可能單獨解釋中國在近代的落伍。最近,有人向我推薦一本新書《國富國窮:為什么一些國家如此之富,而另一些國家如此之窮》,說這本書提供了一些新的觀點。于是,我趁在日本講課之際,從亞馬遜書店郵購了這本書。誰知,讀后大失所望,作者戴維·蘭德斯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東西,至少對于我們解釋中國的衰落是如此。誠實地講,豈只是大失所望,我甚至產生了憤怒。這位哈佛大學的經濟史教授是一個大膽的、毫不掩飾的種族主義者(也許,這本書之所以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也是因為作者道出了美國右翼勢力一直想說而又不敢說的心理話?),不僅堂而皇之地鼓吹歐洲特殊論,而且對其它地區極盡其蔑視之能事。他雖然意識到研究中國的重要性,卻對中國歷史要么不甚了解,要么帶著深度的有色眼鏡去了解。 比如,他認為歐洲人在中世紀發明了鐘表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順便提一句,蘭德斯認為中世紀歐洲有許多偉大的發明和進步,因此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是一個黑暗的時代),而中國人把時間看作是皇權的特權,“在城市,鼓和其它噪聲發生器(noise makers)被用來報時;而且,皇室的日歷在所有地方規定了季節和其中的活動。日歷也不是統一和確定的,每個皇帝都有自己的日歷,將他們的封印刻在時間之河上。私人對日歷的計算因此變得毫無意義。”(第50頁,著重號為筆者后加)這種無知和傲慢竟會出自一個身處現代的大學教授,讓人吃驚。不僅如此,蘭德斯對中國的蔑視更是讓人無法忍受。比如,他認為中國人口多的原因是因為中國人喜歡大家庭(這種觀點已經被中國學者的歷史研究所否定),人多“消耗更多的食物,而食物又導致更多的人。Treadmill.”這最后的一個單詞,我是查了字典之后才確定了它的意思的,意為“人力脫粒機”,或“單調而討厭的、周而復始的動作”,不管是哪種意思,都是侮辱性的。蘭德斯教授這種無知的勇猛和傲慢,讓我聯想起一種動物,那就是……森林里跑出來的野豬。你可以把這種動物的所有品行特征和蘭德斯教授聯系起來。 作者都是美國人,但《槍炮、病菌和鋼鐵》和《國富國窮》兩本書給人的感覺完全相反,一個開放、生動,另一個傲慢、狹隘;說到底,是因為兩位作者所代表的觀念和勢力不同。戴爾蒙德反對種族主義,而蘭德斯則宣揚一種披著學術外衣的種族主義。關于這一點,讀者在讀了這兩本書之后自然會有所體會。至于李約瑟之迷的答案,還需要進一步的綜合研究。正當我們跨入紀元之后的第三個千年的時候,中國已經開始顯示出了重新崛起的趨勢,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了湯比因的文明周期理論。也許,相對于文明的周期波動,前面所介紹的所有理論都不過是對文明的短期擾動的解釋?也許,在中國文明于唐代達到頂峰之后,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擋它滑入明清時期的低谷?迄今為止,我們只經歷了一次歷史長波,因此也不可能對這些問題做出一般性的回答。或許,只有等到下一個千年來臨的時候,我們的子孫后代們才能給出一個圓滿的答案。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and London, 1999. David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and London, 1999.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姚洋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