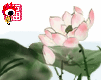| 道德的兩個層次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22日 18:22 中評網 | |||||||||
|
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讀書筆記 姚洋 倡導人類的自利行為可以通過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達到人類整體最大福利的亞當·斯密在寫作《國富論》的同時也寫了一本《道德情操論》,贊美人類的同情心和道德,
我們現在還在討論市場經濟運作的規則基礎,但這個問題斯密在二百年前就解決了:在他看來,這個規則基礎就是正義。雖然斯密沒有對正義下一個明顯的定義,但從他的行文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所謂的正義,就是把自已放到他人的位置上,考察自己對別人所做的事情,并認定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可以接受的,即孔夫子所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者也。為什么要將自己放到他人的位置上去考察自己的行為呢?因為每個人生來都是平等的,不比另一個人多一點兒或少一點兒,而且只有自己才能了解自己的感覺。在這里,斯密要求的是人與之間的對等性。但與他在《國富論》中對人性的假設相一致,這種對等性是建立在個人的自利基礎上的:你用不著去相信他人的感覺,正義只是建立在把你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你自己認定你的行為合理的基礎之上。當然,這種正義的一個前提是每個人都具備隨時進行冷靜思考的能力。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不說那些總是被偏見所左右的人,即使是一般人,也難免有被情緒所支配的時候。但是,對于斯密的理性人來說,這不會成為一個問題。讓我們權且接受這個假設,繼續對正義的討論。 斯密沒有說清楚、我們也無法說清楚,基于對等性的正義到底包含了哪些具體的內容;但是,它排除了許多我們所認為不正義的事情,如偷盜、殺人、占他人便宜、限制他人自由等等。顯然,這種意義上的正義是市場經濟所必需的游戲規則,是市場達到其效率不可或缺的東西。斯密將正義和基于仁慈的道德進行了區分。斯密說:“與其說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還不如說正義是這種基礎。沒有仁慈之心,社會也可以存在于一種不很令人愉快的狀態之中,但是不義行為的盛行卻肯定會徹底毀掉它。”又說:“行善猶如美化建筑物的裝飾品,而不是支撐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勸戒已經足夠,沒有必要強加于人。相反,正義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柱子松動的話,那么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巨大的建筑必然會在傾刻之間土崩瓦解。”(第106頁)。斯密之所以強調正義的重要地位,我以為,是因為正義是令自利行為在看不見的手控制下達到人類最大福祉所需要的最起碼條件。如果沒有這個最起碼的條件,人類的利已行為就會將人類帶入霍布斯的野獸世界。對于一個文明社會來說,一個人的利已行為止于不對他人構成直接的傷害。“在追求名譽、財富和顯赫地位的競爭中,為了超過一切對手,他可盡其所能地全力以赴,但是,如果他要擠掉或打倒對手,旁觀者對他的遷就就會完全停止。”(第103頁)人們不允許一個人“做出不光明正大的行為”,也不允許他把自己看得比別人高出一等。 換一個角度看,正義允許人們對不是由自己行動所造成的后果表示出漠不關心。我努力地工作,試圖超出我的競爭對手,只要手段光明正大,符合正義的要求,競爭對手的破產則不應由我來負責,因為是市場,而不是我直接導致了他的破產。再者,我們也無須對與己無關的不義行為進行譴責或糾正。一個看到小偷而不去追趕的人可能是不道德的,卻沒有違反正義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正義是一種被動的約束,它只要求人們保持對他人的尊重,但不要求人們去主動為他人的福祉盡力。由此可見,斯密的正義原則和古典自由主義原則是一致的。 在很大程度上,斯密的正義與法律對個人自由的保護是重合的,因為兩者均將人看作平等的個體,都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存在而設定的規則,都不帶感情色彩,而懲治不義行為又都是兩者的責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和以牙還牙似乎是造物主指令我們實行的主要規則。”(第101頁)但是,如果法律僅僅停留在為受害者伸冤這個層次上則遠遠不夠。當我們要求對施害者進行懲罰時,“與其說是對那個受到傷害的人的關心,不如說是對社會總的利益的關心。”(第111頁)這里體現的仍然是斯密的中心思想:正義是支撐人類社會的主要支柱,伸張正義理所當然地要以社會的整體福祉為目標。在這里,斯密更像一個功利主義者,而不像一個蘇格蘭傳統的自由主義者。以當代法律經濟學的眼光來看,他的思想無疑是非常深刻和具有前瞻性的。傳統法學以道德為基礎,現代法律經濟學則強調社會福利分析的重要性,而斯密的思想則是這種分析范式的開先河者。 當我們將正義和法律聯系在一起時,我們就發現,市場經濟的規則基礎就是一國的法治。但是,法律制度是冷冰冰的,為的僅僅是人們可以在我們稱之為“社會”的無形空間里和睦相處。如果僅僅有正義和支撐它的法律,人類大概會過著一種類似機器人所過的生活。人類還需要同情。誰能毫不羞愧地宣稱,他在一片反對聲中從不期待一丁點兒贊同的表示?但是,正義的行為不需要同情。比如,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公共汽車的座位上看著一位孕婦站著,因為正義不要求我給她讓位子:我的行為根本與她無直接關系!但是,同情心要求我感受她正在忍受的痛苦,也就是說,我必須接受她的感覺;這樣一來,同情心就會驅使我讓出自己的位子。正義允許我從自己的角度看別人,同情則要求我從別人的角度看別人。 再者,正義需要法律來表達,而法律從來就不可能是完備的。因此,在正義的名義下可能發生對社會不利的結果。辛普森案便是一個例子。在那里,正義完全被法律文本和程序所左右,而真正意義上的“正義”,即辛普森殺人這一事實,卻被擱置在一邊。 另一方面,只有正義,一個經濟系統是否就可以達到最高效率呢?換言之,是否存在能夠增加社會效率的補充機制呢?首先,只有正義的社會可能是一個交易成本高昂的社會。比如,就囚徒困境而言,參與者可能需長時間的重復過程才能找到對群體來說最優的結果。如果存在道德約束,則群體進行的就是阿瑪蒂亞·森所說的信任博弈 --- 一個每個人都信任每個其他人會采用一個有益于社會的策略的博弈,社會最優從一開始就可以達到,因此也就不會出現類似公共地悲劇的事情了。其次,只有正義而無道德的社會可能使得經濟活動無法進行。讓我們來看看合同的執行問題。哈特的一個貢獻是發現了合同的不完備性是產生所有權的重要因素。為了解決合同的不完備性所帶來的重新談判問題,且當對方資產與自己的資產互補時,廠家會將對方收購下來。也就是說,所有權是解決合同不完備性的手段。但是,所有權本身也是一種合同,一種個人通過國家與其他所有的人簽訂的合同,因此它本身就是不完備的。巴澤爾強調所有權中的公共領域,正是這個意思。一個企業主可以擁有他的企業的法律所有權,從而對他的雇員的工資和工作量有決定權。但是,雇員總是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如怠工、降低工作質量等等,來蠶食企業主的所有權。法律只能賦予企業主一個抽象的名義所有權,具體的所有權取決于企業主對維護其所有權的成本-效益分析。維護所有權是要付出代價的,比如必須對雇員進行監督,而最優的監督很少會是完備的,因為監督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這正是所有權不可能完備的原因。于是,我們便有了“哈特悖論”:既然所有權本身是一個不完備的合同,它如何能解決其它合同的不完備性呢?答案在于,人們利用其它非經濟的手段來解決合同(包括所有權)的不完備性問題。 道德就是這些手段之一。在斯密那里,道德的實質是同情心,是一個人對他的同胞的愛和對自我利益的克制。他將道德描述為我們“心中的那個居民”的判斷。他熱情地嘔歌,道德是出自“一種對光榮而又崇高的東西的愛,一種對偉大和尊嚴的愛,一種對自己品質中優點的愛。”(第166頁)道德是一種不受個人經濟利益支配的命令。怠工可以獲得個人利益,但是,一個有道德的人會受到“心中的那個居民”的譴責,因為怠工是不道德的。和正義相比,道德是主動的。它要求一個人對哪怕是發生在遙遠的地方的不幸表示同情;它要求一個人在看到不義的行為時挺身而出,對其進行譴責和制止;它要求一個人在自己的行為哪怕是間接地影響到他人的福祉的時候克制自己;……因為有了道德,人類社會才變得豐富多彩;因為有了道德,人類社會才運轉得有序、和諧;也正因為有了道德,我們的經濟系統才在不知不覺中節省了大量的成本。道德為社會中的個人提供了一個可以信賴的共同期望。有了它,我就可以肯定,當我行善的時候,別人會以同樣的善心對待我,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善心都是發自我們“心中的那個居民”的命令。法律卻無法給我這樣的信心。雖然一個司機闖紅燈是違法行為,但我無法肯定每個司機都會在遇到紅燈的時候停下來,因為在沒有警察在場的情況下,闖紅燈是不會受到懲罰的。因此,即使是綠燈亮時,我在過馬路的時候也會小心慢行,以免被闖紅燈的車撞倒。如果遵紀守法已經溶入了每個社會成員的血液,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文化的一部分,我大概會在過馬路時大膽一些。道德的喪失正在使我們的經濟蒙受巨大的損失,因為我們的企業家們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對付不道德者。貨到付款是天經地義的事,但許多企業即使有錢也不按時付款,或干脆永遠抵賴下去。由此一來,現金交易量大增,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一些企業怕上當受騙干脆少接單,其中不可避免地要失去一些值得做的生意。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很多。嚴格的執法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述現象的發生頻率,但法律是最昂貴的社會組織工具,如果每個人都具備道德,從而降低法律的使用頻率,豈不是更好?道德雖然可能是景上添花,但是,缺了這朵花,我們的社會不知會頹敗到什么程度! 道德的形成固然有自發的演化過程,但是,這個過程更多的時候可能是形成一種游戲規則,而不是包含著同情和自我克制的道德。出于社會個體的自發博弈從來不可能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但在部分社會群體內所達到的博弈均衡卻往往不能達到對全社會來說的最優結果。比如,在美國,職業道德可以看作一種自發形成的同一職業內部的人所遵守的行為準則。在律師這一行里,這個準則的基本要求是,在法律的框架內為自己的當事人盡力打贏一場官司。在辛普森一案中,科庫倫為辛普森贏得官司的做法,以一個律師的職業道德來衡量是完美無缺的,但這種道德顯然不是我們所認定的那種,因為我們所認定的道德要求我們對認定的不義行為采取負責的態度。 既然道德的要求超乎于人類利已之心之上、而又不可能是自發博弈的結果,道德的實施只能通過個人內心的強制。法律不能成為強制道德的手段,因為它不能逾越正義所允許的范疇,要求人們主動地對他人施于同情或為他人利益克制自己的較小利益。然而,要達到個人內心的強制,對于追求私利的個人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過去,這種強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外部懲罰達到的。一種懲罰是通過組織進行的。這些組織包括家庭、家族、教會等。但是,這種懲罰到了現代就變得不適宜了,對正義的要求迫使社會放棄這種懲罰。另一種懲罰是社會群體對違反道德的個人的指責乃至唾棄。當我們想做違背道德的事情時,“內心那個人馬上提醒我們:太看重自己而過分輕視別人,這樣做會把自己變成同胞們蔑視和憤慨的合宜對象。”(第166頁)然而,群體壓力只有當群體相對穩定時才能發揮作用,在社會流動性極大的今天,它的作用已經大大地弱化了。要想使道德成為“心中那個居民”的呼喚,必須內化對不道德行為的懲罰。在這一點上,宗教大概是做得最好的。“在每一種宗教和世人見過的每一種迷信中,都有一個地獄和一個天堂,前者是為懲罰邪惡者而提供的地方,后者是為報答正義者而提供的地方。”(第113頁)地獄和天堂都是未知世界里的東西,描述的是人死后的景象,因而既無法被證實,也無法被證偽;同時,對死亡的恐懼是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的。這種恐懼和天堂、地獄的不可證偽性使得人們寧愿相信死后懲罰和報答的真實性。同時,宗教通過一系列的儀式來強化行善的崇高感和作惡的罪惡感。比如,基督教創立了原罪說,以證明人生來就是為了贖罪,同時使得再次作惡變得逾加得不可饒恕。另一方面,基督教通過講道與講道場所的設計傳遞一種崇高感,從而使信教者從行善的行為中得到一種自我獎償。對信教者個體來說,宗教首先是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替代不可知世界的精神樂園;對社會來說,宗教則首先是一種足以內化道德懲罰的社會組織。 有人會說,教育可以起到與宗教相同的作用。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首先,要想使人們相信教育對道德的推崇,首先必須建立一套自恰和具有說服力的理論,來論證道德的合理性。但是,由于道德的命令性質,要建立這樣的一種理論是不可能的。道德好比數學里的公理,永遠無法在同一個系統中得到證明。其次,教育沒有一個可以伴隨一個人終生的組織來支撐,因而其功能遠不如宗教那樣強大。我在這里將宗教和教育進行對比,是想說明組織在傳輸和實施道德方面的重要性。現代社會不再容忍通過組織的強制,但是,組織、還有與其相一致的儀式,可以造就一種道德氛圍,內化人們的道德懲罰。 回到對“斯密問題”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在斯密看來,正義本身足以支撐人類社會的運行。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不需要道德。但是,一個沒有道德的社會如同一篇符合語法卻毫無生氣的文章,枯燥乏味;同時,一個沒有道德的經濟系統如同一架沒有潤滑過的機器,費時費力。斯密雖然沒有意識到道德對市場經濟的運作可以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對人類社會豐富多彩的追求促使他寫下《道德情操論》這本書。這與他對看不見的手掌握之下的利已之心的肯定毫不矛盾:雖然利己之心能將人類社會送上財富的頂峰,提倡道德,為人類社會景上添花又有何妨?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八日初稿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二稿 二000年九月十三日三稿 二00一年四月九日四稿 二00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五稿 《道德情操論》, 亞當·斯密著,蔣自強等譯,胡企林校,商務印書館,1998年,北京。 * 原文發表于以《道德情操》的篇名發表于《讀書》2001年第10期。收錄進本書時略有改動。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姚洋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