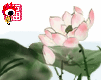| 穿行于現實和書齋之間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22日 18:20 中評網 | |||||||||
|
姚洋 約翰·里德(John Reed)是美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在此之前,他是左翼雜志《群眾》(The Masses)的一名記者。一九一七年,他和他未來的妻子路易絲·波南特(Louise Bryant)一道來到俄國,親眼目睹了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他們為俄國的巨變而感到振奮,向美國發回了許多熱情洋溢的稿件。回到美國后,他出版了影響巨大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
以上是電影《約翰·里德》的主要內容。今年夏天,在位于日本新瀉鄉下的一所大學的教師宿舍里,我在深夜看完了這部電影,感慨良多。有人說:“一個人在三十歲之前如果不激進,那么他的心智有問題;但如果他在三十歲之后還激進,他的頭腦就有問題。”當一個人年輕的時候,他意氣風發,疾惡如仇,恨不得在一夜之間改變世上的所有不公。隨著年紀的增長,他到處碰壁,這才意識到:“我不是振臂一呼而應者云集的英雄。”(魯迅語)所以,他開始不那么左傾,而轉而注重理智地“思考”,從離經叛道的青年變成忠實地捍衛主流社會的一分子。 里德的同志、《群眾》的主編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就是這樣的一個極端的例子。在三十年代之前,伊斯特曼是蘇聯和工人階級事業的最忠實的支持者之一。他認為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之間的一場不義之戰,因此堅決反對美國參戰。當美國最終于1917年對軸心國宣戰之后,《群眾》雜志對美國政府提出了強烈批評。此時,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高昂,左翼勢力迅速上升。威爾遜政府的司法部長米切爾·帕爾瑪(Mitchell Palmer)和他的特別助手、后來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乘機向美國公眾渲染“紅色恐懼”(the Red Scare),并對美國的左翼勢力進行了無情的鎮壓。于1917年通過的《反諜法》是他們手中的一件有力的武器,《群眾》雜志以違反《反諜法》為由遭到當局的起訴。雖然對《群眾》的指控兩次都被陪審團以證據不足為由判定為無效,但是雜志不得不關閉。伊斯特曼又和幾個同志一起創辦《解放者》(The Liberator)雜志,繼續左翼宣傳。但是,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迫害使得伊斯特曼對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開始產生了懷疑。他先是變成托洛茨基的忠實支持者,在托洛茨基被暗殺之后,又變成社會主義的強烈批評者。他因此被美國主流雜志《讀者文摘》聘請為主編,并在該雜志上發表批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章。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伊斯特曼更是變成了麥卡錫的忠實支持者,他的文章對麥卡錫主義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伊斯特曼還是極端的例子的話,經歷過六、七十年代狂風驟雨的許多美國人的轉變則是普遍現象。我的導師便是其中一個。七十年代初,美國的所有高中生都必須抓鬮決定是否要上越南戰場。輪到我的導師一屆時,正好越戰結束,他因此逃過一劫。他的本科是在喬治城大學學外交,畢業時到美國國務院應聘,得到的評價是:“此人愛思考,不適合做外交工作。他應該去搞研究。”由此他便決定到威斯康星大學學發展經濟學。七十年代末,他以研究拉美土地問題開始學術生涯。拉美社會的一個特點是土地占有的極度不均,少數的大莊園主和多數的無地農民形成鮮明的反差。因此,幾乎所有的拉美知識分子的思想都左傾。導師也不例外。他在書架上擺放的一本他自己用西班牙文寫的書可以證明這一點:我雖然不懂西班牙文,但從封面上高舉拳頭的憤怒的農民我也能看出,這是一本關于拉美土地斗爭的書。他的太太是律師,是那種天性開朗和豁達的美國人。倆人結婚近二十幾年一直都只有一輛車,導師無論雨雪,上、下班一律騎自行車。他也從來不打高爾夫球,認為那是小資產階級的愛好。然而,最近他來中國,告訴我說,他們新買了一輛BMW,第一次擁有了兩輛車;同時,他也開始和太太一起去打高爾夫球了,并發現這是一項很好的運動。盡管他的學術取向仍然左傾,他的生活卻已經逐漸中產階級化了。 如同波斯納所言,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美國知識分子,在多數情況下只是把自己關在學術的象牙塔中,無非偶爾露一下面,做一回公共知識分子而已。他們并不真正參與公共事物,他們的公共討論只是他們偶爾從象牙塔中的探頭張望;很快,他們就會把頭縮回去,繼續和社會保持距離。蘇力很有勇氣地自我認同波斯納的觀點(《讀書》2002年7月號),認為自己每次超出專業范圍的活動也不過是從象牙塔中探一次頭而已。曹錦清懷著一個都市知識分子渴望了解黃河邊上的中國的心情到河南采風,希望以客觀的學者的眼光洞悉中原腹地的文化嬗變。然而,《黃河邊的中國》與其說是一部學術著作,毋寧說是一部注解頗多的游記,字里行間流露著作者經世濟民的理想。曹錦清并沒有信守學者不參與的規范,而是在多個場合參與了當地的政治生活。當他慷慨激昂地在黃河北岸的小村莊里發表演說的時候,他已經脫離了學者的角色,而擔當起啟蒙者的任務。他的激情得到了當地農民的回報,在他臨走的時候,村民紛紛前來送行。然而,參與的激情也只能在那種特定的場合下才能釋放;回到上海之后,曹錦清仍然是一個學者。 我也一樣。一九九九年我到廣東東莞一個村莊調查外來移民的情況。村里有許多外資工廠,打工者幾乎都來自內地省份。一天,我在一個工廠里召集工人填調查表。來的工人大部分是十幾歲的女工,許多人小學都沒有讀完,根本無法填寫,只能讓他人代勞。但其中一個女孩填表的速度極快,原來她已經讀完高二了,因為家里沒錢而輟學。填完表之后,她就對我訴說起自己的遭遇來。她家在河南,喜歡唱歌,唱得很好,但父親就是要讓她輟學,因為家里沒有錢供養她。沒有辦法,她于一年前帶著200元錢和朋友一起來廣東打工。她說著便哭了起來:“我就是想上學,想唱歌。你幫幫我吧!”我能幫她什么呢,除了心痛?領班過來大聲地呵斥她,要她回去干活,她只好抹著淚去了。我無法忘記她轉身看我的眼神,那是一種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而稻草又迅速斷掉了的絕望。 我到村里的聯防隊去聯系采訪,發現廳里跪著一個光著腳的外地年輕人。聯防隊長告訴我,他是小偷,昨天夜里被抓住的。年輕人面容佼好,如果生活在城里的富足人家,一定是許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可此時,他跪在地上,淚流滿面,只會說:“我不是小偷。”聯防隊長是一個極負責任的人,他撿起年輕人的一只鞋,開車帶著我去看昨夜抓到他的地方。原來,一個工廠宿舍連續發生盜竊案,昨夜又發生了一起,但聯防隊趕到時,小偷剛跑掉,還掉了一只鞋。隊長認為小偷沒有跑遠,便埋伏下來等著。到深夜3點左右,小偷覺得安全了,從躲藏的草叢里出來,被抓了個正著。隊長帶我去看小偷留下的鞋印,把那個年輕人的鞋一放,果然對上了。 除了夸獎聯防隊長工作認真、為民鋤害,我還能對他說什么呢?我能告訴他,體罰犯人是違法的嗎?我能建議他給年輕人一點尊嚴,因為他偷竊可能是出于生活所迫嗎?都不能,因為我是一個需要聯防隊長帶領進入這個村莊社會的旁觀者。 一位社會學家在評論完我的一次學術演講之后對我說:“經濟學家真厲害,對什么事都那么冷靜。”的確如此。十幾年前我和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妻子一起游三峽,船過一處碼頭時,恰逢一艘運煤船在卸貨,一隊搬運工扛著沉重的煤袋爬幾十級的臺階把煤從船上卸到高高的岸上去。站在我們旁邊的一個人說:“怎么這么落后?為什么不用傳輸帶?”我回答說:“用了傳輸帶這些工人不就沒活干了嗎?扛包掙錢總比失業好。”不是我沒有憐憫心,而是事實就是如此。現在,在面試研究生的時候,我還時常以這個例子做為一個問題,看學生是否了解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在不知不覺之中,我在要求學生放棄道德考量,而專注于經濟學的“冷靜”思考。 盡管心中有無限的正義沖動和經世濟民的抱負,作為學者的社會科學工作者,說到底應該還是社會的旁觀者,因為社會分工要求學者對社會進行公正、冷靜和深入的分析。十幾年前在北大做研究生的時候,北大校報上登了一篇學生來稿,說北大學生在社會實踐方面不如清華學生,作者因此呼吁學校多給學生提供實踐機會。當時我就對這篇文章的觀點不以為然,認為北大就是應該培養思想家。近年來,北大步清華后塵,在學生中間開展創業競賽,團委還撥專款資助那些有希望的項目。看來,在社會實踐方面趕超清華仍然是北大的理想之一。但是,時至今日,我仍然認為,北大是沒有必要和清華在培養實用型人材方面一比高低的,北大應該培養學者(思想家是培養不出來的,但學者中間可以出思想家),因此,北大不妨和社會保持一種必要的距離。這當然不是要求北大培養“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書生。一個學者可以不參與社會,但必須關注社會,洞察社會變化后面的力量。 中國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的氛圍中生活得太久了,許多人的學術研究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對“主義”的詮釋和主張式的吶喊。參加國內的學術會議,聽到最多的是:“我的觀點是……”“我的主張是……”可是,你的分析在哪里呢?說實在的,要談主張,學者大概不會比地方干部強多少。最近到南方一個城市調查國有企業的改制情況,發現當地經貿委主任的主張比我們許多教授的主張更開放、更符合實際。他給我舉例說,在一次會議上,他辯倒了一位教授。那位教授主張,像公用事業這種行業還是國家經營好。經貿委主任反問:“為什么?香港把公共汽車線路租給私人經營不是很好嗎?我看象水電、煤氣這樣的公用事業也可以照此辦理。”我們的教授無話可說。我想,這位教授大概只會談主張,不會分析,否則,他至少可以說出幾條過硬的理由吧?當主張代替了分析的時候,學問就變成偽學問了。這樣的學問,不如不做的好。 保守的意識形態容易被識別,也容易在分析面前敗下陣了,比較難識別的是隱藏在分析之下的意識形態。在目前的中國,價值中立是學者們所追求的理想目標,一些人更是愿意以價值中立自居。表現在經濟學界,就是濫用經濟理性的推理,而忽視社會的其它價值。比如,江西發生了巨大的鞭炮廠爆炸事件,可死難工人的家屬卻勸政府要繼續允許辦鞭炮廠。于是,有人就會說,工人是理性的;言下之意,鞭炮廠惡劣的作業環境并不需要改變。但是,對工人來說,他們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在家里等著沒飯吃,另一種是到危險的鞭炮廠工作。在前一種選擇下,他們可能只能等著餓死,在后一種選擇下,他們還有活下去的希望;兩相權衡,選擇后者當然是理性的。然而,我們應該看到的是,工人的選擇實際上是在沒有選擇下的“選擇”,這種選擇是理性的,但導致這種選擇的外在制度安排及其實施過程卻是不人道的。人不是只會搬運牛糞的屎殼郎,經濟追求只是他的所有追求的一部分。一個社會的制度安排必須認同這一點,保護和鼓勵人的崇高的一面,而不應該把公民降低為在極低的水平上為生存而奔波的昆蟲。事實上,就目前的技術條件而言,做好工廠的安全防護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國家也有較完備的安全生產法規,問題出在地方政府的管理和企業主的執行上。不可否認,在工人和企業主之間,地方政府往往偏向于后者的利益,因為后者為地方帶來就業和稅收。在這種偏向于資本的權力格局下,工人的利益經常被忽視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很多情況下,許多人強調經濟理性不過是在給他們偏向資本的意識形態穿上一件價值中立的外衣。要知道,完備的理性和經濟學定理只出現在教科書里,而并不完全反映真實世界。但是,這一點很容易被人所忽視,以為書本里的定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就好比弗里德曼的名言所說的:“如果數據沒有支持理論,則肯定是數據錯了。”對書本知識的盲從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會使書本上的定理變成一些人的信念,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基于理性的分析因此也變成了對自己意識形態的辯護。 所以,無論是保守還是激進,學術如果被意識形態所左右,學者就和政治鼓動家沒有什么兩樣了。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斷言,意識形態和學術研究根本不相容。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人阿瑪蒂亞·森是主流經濟學家中極少數公開表示自己在政治上是左派的人。最近,趁他來北京開會的機會,我問他是如何處理他的政治立場和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的。他回答說:“我的政治立場當然對我的學術研究有影響,我之所以選擇研究饑荒問題,就是因為我的左傾的政治立場。但是,一旦問題選定,我們就必須用客觀的態度來進行分析。我在對饑荒的研究中采用的完全是主流的新古典方法。”森的這段回答,為學者和知識分子之間搭起了橋梁:作為知識分子,一個人要擁有、并積極捍衛自己的意識形態,因此他是入世的;作為學者,一個人則要擱置自己的意識形態,以客觀的態度來對社會現實做出分析,因此他是一個旁觀者。一個想成為知識分子的學者總是處在入世與旁觀的張力之中。這種張力是一種痛苦,也是一種美。一幅好的藝術作品需要張力,一個好的理論也需要張力,豐富的人生本身就體現張力。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邊界的穿越者,是入世者和旁觀者的統一。 然而,這樣的要求可能對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苛求。成就彰著的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說,他過去二十年的學術生涯是在理論研究和現實政策討論中交替度過的,而八十年代中期參加里根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使他受益非淺。中國沒有這種條件,官與學之間的聯系永遠是單線的,要么由學而官,要么由官而學,決不會出現象克魯格曼那樣官學交替的情況。一個學者如果想實現自己的想法,就必須向官靠攏,或干脆自己做官。那些不想在現實社會中有所作為的人,則成了書齋里的隱士。歐洲大陸的思想家們不僅可以在報刊上和廣播電視上發表他們的主張,在必要的時候,他們也可以參加街頭群眾運動。中國沒有容納這種參與的空間。學者們也上電視,但談的是經濟形勢、房產信息以及股市行情,而不是思想。這決不是電視臺的商業化傾向所能完全解釋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的誕生還有待時日。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姚洋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