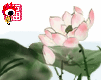| 昨日的理想與今日的創新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22日 18:18 中評網 | |||||||||
|
姚洋 四十一年前的八月六日,隨著毛澤東在河南新鄉七里營一聲“人民公社好”的號召,人民公社幾乎在一夜之間在中華大地上遍地開花。共產黨人的偉大理想與傳統農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交織在一起,全國上下,從黨的理論權威到普通百姓,無不為之歡欣鼓舞。然而,隨之而來的饑荒猶如一瓢冷水,澆醒了無數人美好的夢想。塵埃落定,理想還歸于理想的
人民公社是實施“主義”的結果。在今天的中國談論“主義”,一定會引來旁人的竊笑。然而,“主義”這東西卻為中國1949至1978這三十年間上至意識形態、下至普通百姓生活的一切活動提供了無可爭辯的準則,沒有人敢用不嚴肅的態度來對待它。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無疑是非常透徹和深刻的,他的許多結論在今天仍然成立;共產主義作為理想也將繼續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但是,任何理論都是對現實的有條件的再現。馬克思本人并沒有對共產主義實踐提出任何具體的建議,后來的社會主義實踐完全是后人從理論推演出來的。當然,如果邏輯縝密的話,這種推演本身并不構成任何問題。但是,人們在實施過程中,卻很容易忘掉理論后面的條件,把對現實有條件再現的理論當成是無條件成立的真理,從而在實踐中犯錯誤。或者,實踐本身便會遇到始料不及、但卻是致命的問題。比如,信息問題是任何社會主義的實踐者所沒有預料到的,但卻構成了后來計劃經濟難以為續的主要原因。在這一點上,自然科學比社會科學占有明顯的優勢。和社會科學的理論一樣,自然科學的理論也是對自然有條件的再現。比如,牛頓第一定律說,物體在沒有外力作用下保持靜止或勻速運動狀態。“沒有外力作用”便是這一定律成立的條件。但是,自然科學的優點在于,它的理論符合波普所謂的證偽標準,即人們可以用可控實驗來對它們進行檢驗,看是否可以發現反例;如果發現反例,則理論被證偽;否則,理論被接受。理論被接受不等于說理論就是對的,因為將來可能會發現反例。社會科學則不然。就連號稱社會科學中最具科學性的經濟學,離證偽的標準也相差甚遠。從根本上來說,經濟學的計量檢驗受制于數據的不精確性。自然科學也用統計方法,但它們可以通過嚴格的可控實驗來產生必要的數據,從而達到對理論進行精確檢驗的目的。經濟學的實驗則是社會的歷史,不但談不上可控性的問題,多數情況下甚至連準確的觀察也是一種奢望。數據的不準確和不完備導致了檢驗的不可靠性。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個經濟學的理論可以同時被證實和證偽。這種粘著狀態養成了人們對社會科學的容忍態度,并激發了無數社會科學理論的產生和實踐。人民公社便是基于一個無法進行事前驗證的理論推論而產生的;其結果是,它本身變成了一個殘酷的實驗。可惜,這個實驗不可能象自然科學那樣,在可控的條件下進行,而其結果更是不可逆轉的。 人民公社這個實驗忽略了一個關鍵因素,那便是人的利己本性。如果人生來是利他的,人民公社大概不至于以失敗而告終。畢竟,公社也有個體農戶所無法比擬的優點,如對風險的抵御能力、對勞動力的協調運用以及對公平的關懷等等。張樂天在《告別理想--人民公社研究》一書中對七十年代浙北農村的記述和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對華北農村解放前后產量的比較都證明了這一點。可惜的是,上帝在制造亞當和夏娃時忘了在他們的大腦中植入利他的基因,以致于人欲橫流至今。人民公社的實驗從一開始就陷入了與農民利己之心爭斗的泥潭。如同張樂天所記載的,生產隊內部的報酬機制不可謂不精確,監督不可謂不嚴密,但農業的天然性質注定了它的生產組織不可能象工廠的流水線那樣,人人都被機器所控制,從而無法偷懶。既然農業的監督如此困難,搭便車現象便不可避免。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是通過某種機制使監督成為農民的自覺行動;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使農民內化公社生產組織所無法消化的監督成本。 在公社時代,教育被選擇作為這種機制。那個時代聽到最多、運用最廣的口號大概要數“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閃念”之類。有一個文革笑話,說的是一個光棍成了村里的造反派,因此有機會得到地主寡婦。他第一次上寡婦的床,還沒行事,卻突然跳將下來。原來,寡婦的枕頭上繡著“狠斗私心一閃念”幾個字!光棍大概知道自己的地位來之不易,所以事事以口號為準繩。但是,要使普通農民做得和他一樣,教育起碼要做到以下兩點之一。一是正面的,即讓農民從自我約束與教育的一致性中得到一種滿足感;另一是負面的,即讓他們看到對偷懶有足夠嚴厲的懲罰。然而,在生存都頻頻受到威脅的年代,教育所提倡的東西對農民來說是與他們不相干的官樣文章,只有基于生存而生的傳統行為準則才是實實在在、值得尊重的東西。這種脫節大大降低了教育的正面功效。同時,在鄉土的村莊里,懲罰別人是傷面子的事情,所有人都想極力避免,更何況偷懶或占集體便宜是人人都想做、或已經做過的事情。七十年代,筆者在江西農村時,村里一家男主人涂改了工分本,生產隊對他的處理不過是改正他的工分而已。張樂天在他的書中也記載了在監督和懲罰不嚴厲的情況下所產生的人人爭先恐后謀私利的“負攀比”現象。教育既不能給予農民有價值的獎勵,也不能提供足以令他們信服的懲罰,因而無法達到內化監督的目的。這正是人民公社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人民公社的二十六年間,特別是饑荒和文革之間的短暫空隙和七十年代較為穩定的時期,中國農業的增長與當時世界的平均水平相比并不差;如果不是因為執行以重工業為主的趕超戰略,中國農村的增長會更快一些。在七十年代,由于放松了對社隊企業的限制,鄉村工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其總體速度并不亞于八十年代的水平。但是,經濟的增長并沒有降低農民對自己的所得斤斤計較的傾向,更何況他們從增長中得到的收益微乎其微。農民的斤斤計較甚至可以達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小崗村的農民在包產到戶之前還以討飯為生,包產到戶的當年卻生產了人民公社二十六年間糧食產量的總和!私如水,無所不至。導之可灌萬畝良田,堵之則可潰千里江堤。這一正一反的結果自然讓以大公無私為修身要義的理想主義者大惑不解。從小崗的包產到戶到公社的正式解體,用了六年的時間,也正說明了這個問題。凌志軍的《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對這段歷史做了精彩的描述。 人民公社解散至今,已有十五年了。對城里人來說,它已是一個過去的故事;而對農村人來說,它仍然以各種形式存在于他們的生活之中。比如,“社員”一詞早已被正式媒體所摒棄,而代之以“村民”這一稱呼。但是,我們經常看到,農民們自己卻仍然用“社員”來相互指稱同村的村民。在更深層次上,如同張樂天在他的書中所指出的,人民公社徹底地改變了中國農村制度變遷的軌跡。兩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度被人民公社的建立所打破。今天實行的家庭承包制并沒有觸動作為人民公社本質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公社后的土地制度變遷只能沿著公社遺留下來的軌跡發展。所不同的是,制度的確定已由原來單一的國家壟斷變成了國家、農戶以及村干部之間的博弈。 國家在農村制度建設中仍然保留著角色,原因在于它承擔著穩定全國、特別是城市糧食供應的責任。國家的這種責任在人口眾多、且以稻米為主食的東亞國家中是普遍存在的。世界稻米市場非常狹小,價格波動劇烈,使得以稻米為主食的國家怯于依賴國際市場來滿足國內消費。中國亦不例外。正如周其仁教授所指出的,責任制本身便注定了中國農村產權的殘缺,因為它的內涵便是農民通過向國家讓渡部分權利以換取對土地的剩余索取權。從根本上說,國家對地權進行干預,是因為它不相信農民在完整的地權條件下通過市場所進行的資源配置可以達到保證足夠糧食供給的目的。由于國家的壟斷地位,它可以在它的利益脆弱到它所認為不能容忍的時候中止對農民產權的讓渡。這在發達地區表現尤為突出。發達地區非農就業機會多、收入高,務農自然不是農民的首選職業。事實上,這些地方的許多農民已不是經濟意義上的農民了,只是因為他們身份的關系,要求他們種好土地才似乎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政府一直要求他們完成一定數量的糧食播種面積,從而干擾了他們對土地的自由使用權。但是,把土地沒有種好的責任歸咎于農民是不公允的,真正應該歸罪的應該是土地市場的缺失或不完善。近幾年來,大批內地農民到沿海地區承包土地,土地市場活起來了,沿海地區的種田問題也隨之解決。 農村制度建設中更為重要的力量是農民自己和基層干部。這兩個新角色往往擁有和國家不同的利益。對農民來說,地權的完整性似乎應該是他們的首選。但是,我們往往看到土地因人口變動而在村民之間進行不定期的調整。這種調整自然損害了單個農戶地權的完整性,同時也損害了他們對土地進行長期投資的積極性,從而降低了經濟效率。然而,土地調整卻照顧了村民對公平的追求,因此可能是村民在權衡利弊之后在土地集體所有制范疇內所做的理性選擇(應該注意的是,村民的這種選擇是在不能選擇土地私有的前提下做出的。如果土地完全或準私有(如永佃制)可以成為他們的選項之一的話,我們就很難斷定他們不會選擇更加個人化的土地所有制,因為土地私有確定了單個農戶作為某塊土地未來收益流唯一擁有者的地位,從而增加了該塊土地對這個農戶的價值)。村干部這個角色比較特殊。一方面,作為國家政權的一部分,他們必須執行上級的指示;另一方面,作為民選的地方官員,他們又必須照顧村民的利益。由于國家利益的不可談判性,村干部在事關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完全是一邊倒的(這也是國家能夠繼續在村級土地制度建設中保持影響的必不可少的條件)。相反,當國家利益不是那么明顯時,他們會聽由村民進行決策。因此我們看到,在土地使用方面,村干部維護國家利益,對農民的違規行為進行嚴厲的懲罰;但在土地調整方面,他們則被動地接受村民的意愿。當然,這里也不排除村干部利用對地權的干預謀取私利的現象。但是,隨著村級民主的推廣和深入,相信這種現象會逐漸減少。 公社后多個行為主體的參與,使得現階段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具有明顯的誘導型特征。誘導型制度變遷的概念是日本學者速水佑次郎和美國學者佛農·拉坦首先提出來的,指的是制度變遷的方向受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引導。諾斯進一步提出了制度變遷的效率假說:制度總是朝著有利于提高社會效率的方向發展。具體到土地所有權上,這個假說意味著,隨著土地相對稀缺性的提高,地權的個人化程度將加深。但是,這個假說所適用的范圍是有限制的。筆者認為,它只適用于制度變遷是由單個行為主體實施或推動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該行為主體理性的經濟行為使得制度變遷也沿著經濟理性所指示的方向發展。中國農村制度變遷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決定過程是國家、村干部和村民多個行為主體之間的博弈,其結果不一定符合經濟理性。但是,作為社會選擇的結果,中國農村的制度變遷仍然具有誘導性的痕跡,只是其結果不一定和速水等人的效率假說相符。比如,在人均土地很少的地方,每個農戶可能因調整所得到的土地量也較少。由于土地調整需要每個農戶付出必要的交易成本,較少的所得可能會使他們放棄對土地進行調整的要求。另一個極端是,當人均土地非常多時,對土地調整的呼聲也可能較低,因為當其它生產要素不能增加或增加有限時,土地邊際收益隨土地量的增加而遞減。因此,我們看到,在人均耕地非常少的貴州和福建以及人均耕地較多的東北地區,土地調整的現象比較少見;而在耕地資源中等、非農就業機會匱乏的中部省份,如江西和河南,土地的調整卻相當頻繁。 在所有土地制度創新中,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村民集體選擇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折曉葉在《村莊的再造--一個“超級村莊”的社會變遷》一書中從社會學的角度對此有詳細的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村工業化進程是由三來一補企業帶動起來的。在這些企業建立之初,各個村子都面臨著如何向村民征集土地的問題。廣東人以其獨有的商業頭腦,創造了土地股份合作制,在不打破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收益在村民之間進行了合理的分配。筆者對社會學家執著的田野工作方法始終心懷敬意。折曉葉以一個社會學家對細節的特有關注,對土地股份合作制這一制度創新的優點做了深入細致的討論。我這里只想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對他的討論做一點補充。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優點在于降低了外商在本地辦廠或外地農民到本地租耕土地的交易費用。如果土地由分散的農戶掌握,一個外商必須和眾多的農戶簽訂土地租賃合同,他和其中任何一個農戶之間發生糾紛,都可能導致他的工廠關門。在土地股份合作制下,外商只需和村委會一方簽訂合同,從而節省了談判費用。同時,由于村委會是一級政府組織,在某些方面外商也覺得利于合同執行過程中的監督。這樣一來,外商愿意來開廠了,地方經濟也隨之發展起來。因此,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村莊內部在集體所有制前提下的一次帕累托改進式的制度創新,即在無人受損的情況下改善了社區整體的福利。建立人民公社的初衷之一是要解決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化大生產與土地私有制之間的矛盾,但人民公社的實踐不僅沒有解決這一矛盾,反而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現在,廣東農民卻利用過去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合作制解決了這一問題。張樂天在他的書中提問,如果沒有人民公社,中國農村能夠如此之快地擺脫傳統村落文化的“循環陷阱”嗎?以廣東股份合作制來反觀這個問題,我們不難發現,答案至少是部分肯定的。我說“部分肯定”,是因為廣東的實踐只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特定環境下的一種可能方案,至于這個方案是否可以推廣到其它地方還是個問號。 事實上,并不是每一個自發的制度變遷都是一次帕累托改進。首先,信息的不完善可能使人們無法確定帕累托改進的存在或實施改進的路徑。其次,即使各方均知道帕累托改進的存在和路徑,由于參與主體之間存在利益的沖突,類似于囚徒困境的問題也可以阻擋這個改進的發生。以土地的調整為例。一個可能的情況是,每個村民都知道土地調整意味著效率的損失,因為調整降低了每個人投資土地的積極性,從而降低了產量。但是,每戶人家在人口增加時又都想多要土地,因為土地調整的收益是這戶人家的,成本卻由全村的農戶共同承擔。這種收益與成本的不對稱,如果沒有其它再分配機制與之相抵銷的話,一定會導致過多的土地調整。 人民公社是實施理想的產物,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這種制度變遷,如果具有足夠的彈性、從而能夠包容經濟主體的理性行為的話,也許能夠生存。但是,凌志軍和張樂天的著作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展示了人民公社的理想與農民的理性之間的沖突以及公社最終的悲壯結局。折曉葉的著作則向我們敘述了公社后自發性制度變遷的一個成功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盡管舊日公社理想的印跡仍然依稀可見,但經濟理性已經成為左右制度變遷的擔綱者。 經過近二十年的變革,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不受理想約束的時代。喜乎?悲乎?喜的是我們再也不用去為無法證實的理論進行代價昂貴的社會實驗了,悲的是我們可能又走入了一種由無目的的經濟理性所主導的宿命。由于交易成本和各種市場缺陷的存在,經濟理性的自發行動往往不能達到社會最優(我在寫下這句話時頗有些躊躇,因為它極易被人用來合理化中國目前過多的政府干預)。如果這就是我們的宿命,我們便沒有理由聽之任之。更廣義地講,一個社會在失去了理想所確定的標尺之后,如果沒有其它現實的替代物來填補因此而留下的空缺的話,難免會陷入信仰和道德的雙重危機。中國社會是一個入世的社會,歷史上的中國是由孔孟的綱常五倫所維系的。革命徹底地打破了舊有的道德體系,代之以共產主義的理想以及相應的道德準則。如今,兩種道德體系似乎都不起作用了。這正是許多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有識之士所憂慮的。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四日改定于北京大學朗潤園 《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張樂天著,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1月第一版,28.00元。 《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凌志軍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16.00元。 《村莊的再造--一個“超級村莊”的社會變遷》,折曉葉著,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23.50元。 * 原文發表于《讀書》,1999年第10期,發表時有刪節。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姚洋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