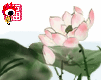| 地方性創新和泛利性執政黨的成功結合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22日 18:13 中評網 | |||||||||
|
對改革開放以來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的一個解釋 姚洋 自1978以來的二十五年間,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每年增長了8%。在世界范圍內,一個人口大國能夠維持如此長期的高速增長,絕無僅有,稱之為“奇跡”當不過分。在1970年代
僅僅在經濟層面尋求對這個課題的解答是遠遠不夠的。誠如阿瑪蒂亞·森所指出的,中國在1970年代末的經濟起飛準備 ― 教育水平和健康狀況 - 遠遠優于像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森,2002);也誠如統計數字所顯示的,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投資積累率從未低于30%;或如林毅夫等人所展示的,遵循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是中國成功地參與國際分工的關鍵所在;但是,中國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內發生了巨大的制度變遷,它們與經濟增長之間必定存在一定的關系,而且,這些關系可能比經濟邏輯更具根本意義。正如諾斯和托馬斯在《西方世界的崛起》前言中所指出的,諸如投資等因素是增長的本身,而不是增長的原因,良好的制度才是增長的原因。中國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內的經濟增長恰恰驗證了這一判斷。中國經濟的恢復起始于農村改革,農戶經濟的恢復以及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大大激勵了農民的積極性,中國因此在短短幾年間解決了糧食問題。隨之進行的城市改革雖然舉步維艱,但價格雙軌制的實行為農村工業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空間,使之成為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半壁河山。進入1990年代,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開放、私營經濟的勃興以及國營企業的改制又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的動力。一句話,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體制變革所釋放的能量。不同于蘇東國家的振蕩療法,中國的體制轉型變革幾乎總是自下而上,先在少數地方試行,成功之后在全國推廣。以價格雙軌制為典型,中國的體制轉型又幾乎總是一點一滴逐步積累完善的,而少有一夜之間的劇烈變革。這種漸進改革不僅有利于獲得多數人的支持,而且有利于經濟效率,因為它避免了因體制震蕩所帶來的經濟失衡;而且,體制轉型的能量逐步釋放,有利于保持經濟的增長勢頭。 回顧過去二十五年的路程,我們發現,中國的經濟轉型基本上是沿著有利于經濟效率的軌跡向前推進的。在純理論的層面上,有效的制度變遷不可能在一個意見分散的社會中通過純粹的民主政治過程而實現;在現實中,當今的民主國家無不為利益集團的大肆活動所困擾,一些國家甚至陷入奧爾森所說的“不可治理”的局面。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威權國家都順利地過渡到了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威權治理在東亞取得了成功,卻在拉美和非洲慘敗。因此,探討有效的制度變遷是如何在中國實現的,就是一個同時具有世界意義和現實指導作用的課題。 本文將回顧中國體制變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考察體制變革的特征,著重強調體制變革的漸進性和有效性,并為此提供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解釋。這個解釋由兩個核心組成,即體制創新的分散性和中國共產黨的泛利性。前者保證了新體制的有效性,后者保證了新體制在全國的推廣。中國共產黨作為全體人民利益的代表,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內將經濟發展作為其首要目標,從而能夠接受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新體制,哪怕后者與舊有的意識形態相沖突。 一、 體制釋放和經濟增長 導致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資本積累和對資本積累的有效利用,用更通俗的話來說,是將更多的今天的錢有效地投入到生產明天的消費的活動中去。因此,研究經濟增長就是研究如何增加人們的投資動機以及如何引導人們進行有效的投資。主流經濟學家關注導致積累的直接原因,如教育投入、科研投入等等,制度經濟學家則退一步,研究導致或妨礙人們進行有效投資的制度機制。對于像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而言,制度的建立尤為重要。本節所要論證的命題是,制度釋放是中國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經濟增長的源泉。 農村改革是支持這一命題最明顯的證據。在1980年代初重新建立的家庭農業制度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短時期內便解決了一直困擾中國的糧食問題。根據林毅夫的一篇影響很大的論文的結論,1980年代前期農業增長的60%來自制度變遷(Lin, 1992)。盡管有人指出,這一結論是在沒有考慮農產品價格上漲因素的前提下得到的,然而,沒有人懷疑1980年代初的農業增長極大地得益于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革這一根本結論。 農村改革的成功使得改革者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困難的城市改革上來,城市改革的兩個核心是價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前者的目標是將計劃定價轉變為市場競爭定價,后者的目標是加強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所有制改革在1980年代雖有突破,但是,因為沒有觸及公有制這個根本問題,圍繞它進行的各種試驗都沒有產生實質性的進展。相反,價格改革在雙軌制下推進了一大步,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雙軌制既保護了像國營企業這樣的既得利益者,又為不受計劃保護的非國營成分提供了原材料和產品市場;最為顯著的是,它為鄉鎮企業的崛起提供了先決條件。鄉鎮企業早在1970年代就出現了,但它在當時的定位僅僅是對農業的補充。農村改革之后雖然沒有鼓勵農村工業發展的政策,但是農村剩余的增加引導農民在非農領域尋求更大的發展。如果市場仍然完全受制于國家計劃,農村工業就不可能自由地獲得原材料和自由地在市場上銷售產品,它的規模也就不可能達到我們所見的樣子。在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短短十年間,農村工業從無足輕重的補充地位一躍而成為中國工業的半壁河山,價格雙軌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沒。 雙軌制不是沒有代價的。市場定價和計劃定價的同時存在導致了巨大的尋租空間,“官倒”成為1980年代下半期全國上下深惡痛絕的對象。然而,由此而引發的價格“闖關”卻以失敗而告終,改革也因此被迫停頓。價格改革最終是在雙軌制下不知不覺地完成的。伴隨著1990年代初期較為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價格管制快速開放,以取消城市糧食定量和外匯并軌為標志,價格改革在1990年代中期就基本結束了。隨之而來地是鄉鎮企業中公私混合所有制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私營經濟的蓬勃發展。九十年代的私營經濟由三部分成份構成。第一部分是由地下變成地上的私營企業,這些企業在過去就是由私人經營,只是帶了一頂集體經濟的紅帽子。第二部分是九十年代新建的私營企業,第三部分則是由集體或國營企業改制而成的。九十年代后期以來,這一部分企業越來越多。和1996年相比,2001年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個數已經下降了40%;在多數城市,多數剩余的國營企業也計劃在二至三年內全部改制(Garnaut, Song, Tenev, and Yao, forthcoming)。九十年代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私營部門的發展。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教育水平、外資比例、出口比例和私營部門投資份額等因素當中,私營部門投資份額是唯一對中國省區經濟增長速度具有解釋能力的因素(盧峰、姚洋, 待刊)。可以鮮明對照的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國營企業全面虧損的狀況下,中國經濟仍然維持了高速增長,其原因就在于私營部門的快速發展。 九十年代見證的另一巨變是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的涌入。盡管農村移民仍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們畢竟已經邁出了一大步,這就是獲得了身份的自由。限制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戶口制度將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面,既不人道,也不利于人力資源的有效利用。是農民自己打碎了束縛他們身份的枷鎖,農村工業的勃興使他們原地轉換了身份,進城務工讓他們直接經歷了現代文明所帶來的解放(和痛苦),盡管爭取和城市居民同等地位還需相當長的時間。 任何到過珠江三角洲的人都不會再否認農村移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源源不斷的移民壓低了工業工資,加上珠三角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環境,港澳臺資金大量涌入,把當地最偏僻的村莊都變成了盡管嘈雜、但充滿了活力的工業集鎮。如果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工廠,則農村移民就是支持這個巨大工廠的基石。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是中國的負擔,而是中國經濟在世界上保持競爭力的有效資源。農村勞動力幾乎無限制的供應為中國經濟的增長積蓄了長期的“勢能”,如何合理地利用這一勢能并在它釋放之后如何使農村移民很好地溶入城市社會,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必須解決的大問題。 時至今日,中國的體制轉型以近尾聲。在價格領域,國家調控的價格的比例已接近、甚至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所有制領域,民營企業在數量、就業和產值方面已經遠遠高于國營企業,在三到五年之內,除少數大型企業之外,人們將很難找到國營企業了。這兩個領域的成功轉型已經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促進了其它領域的轉型。城市社會保障制度正趨于合理,農村社會保障已經納入議事日程,一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正在形成。金融業的轉型稍慢一些,但是,銀行的商業化已經取得了可觀的進步。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由體制釋放所支持的那一部分經濟增長將逐步消失,中國將更多地面對一個成長的市場經濟所必須面對的問題,目前的匯率問題就是這樣的問題之一。如何應對這些新問題將是對中國經濟政策的新的挑戰。 二、 漸進改革與經濟效率 中國制度-經濟轉型的主要特征是它的漸進性。漸進性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在時間上的循序漸進,二是在空間上的試驗和推廣。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現已公認為中國的一次帕累托式的制度改進,但是,它的完成仍然用了六年的時間。包產到戶、包產到組始于安徽小崗,而后由萬里推廣到安徽全省,經過反復的爭論才最終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認,即使是當時最為激進的改革者也曾經對包產到戶持懷疑態度。價格雙軌制雖然沒有經過地方性的試驗(也無法進行這種試驗),但它卻是中國漸進改革的典型例子。如果說農村改革的漸進性還是來自于決策者對改革最終目標的不確定性的話,價格雙軌制則是決策者在確定的目標下而有意設計的過渡制度。發生于1990年代的企業改制則重復了農村改革的路徑,始于少數地方的試驗性且往往不徹底的改革,而終于中央政府的統一政策。此次改革所經歷的時間更長,摸索的成份更多。當順德和諸城在1990年代的初期開始改制的時候,職工股份合作制是主要的改制形式,而改制之后的企業也仍然被認為是集體企業。這種改制形式在1990年代中期被許多地方所仿效,而順德和諸城則發現了它的弱點,從而開始了二次、甚至三次改制,其主要目的是將股份集中到管理層手中。這樣,改制便成了真正意義的私有化。盡管私有化沒有成為官方用語,中央政府的“抓大放小”政策早已給中小國營企業的私有化開了綠燈。 二十五年來的實踐表明,漸進改革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增長。總結起來,這是因為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漸進改革有利于獲得各方的政治支持。除了農村改革,其它改革無不觸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為了獲得這些人的支持,改革者有必要進行妥協。價格雙軌制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早在1980年代初期,建立市場化價格體系就是城市改革的首要目標。但是,市場化價格體系必然要損害國營企業的利益,因為它們將失去以往計劃所賦予它們的特權。為了爭取國營企業職工的支持,雙軌制成為一個折衷的過渡選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劉遵義、錢潁一和羅蘭才認為,雙軌制是“沒有失敗者的改革”(liu, Qian and Roland, 2000)。 漸進改革不僅通過補償潛在的失敗者而獲得政治支持,而且通過提供學習和思考的時間讓反對者轉變思想,讓改革者認清改革的方向。在農村改革和國有企業改制之初,改革者并沒有改革的終極目標,而反對者更是懼怕改革可能帶來的對意識形態的沖擊。地方性試驗為改革者提供了試錯的機會,也讓反對者看到了改革的正面效果,并為中央政府最終形成統一的政策提供了準備時間。 其次,漸進改革有利于企業和個人調整行為,使整個經濟快速達到新的均衡。制度變革通過改變制度規則和財產關系迫使經濟由一個均衡過渡到另一個均衡。但是,這個過渡不可能在瞬間完成,因為個人和企業需要時間來調整他們的合約和生產計劃。調整是需要成本的,這其中主要使搜尋成本,即個人和企業在放棄舊的合約和尋找新的合約伙伴中所承擔的成本;一些企業可能在調整過程中因為失去競爭力而倒閉,這也是調整成本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制度變遷是“破壞性的建設”。但是,劇烈的制度變革可能只有破壞而沒有建設。這是因為,當制度變革過于全面和急迫的時候,個人和企業可能無法完成他們的調整,從而使經濟長期處于失衡狀態。前蘇聯的劇烈政治和經濟變革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經濟學家認為,這場變革造成了前蘇聯社會的無組織化,后者是劇變之后十年前蘇聯國家經濟滑坡的主要原因(秦暉,2003)。在蘇聯時期,任何物品的生產都是在嚴密的計劃指導下進行的,各個工廠無需擔憂原材料的供應和產品的銷路,整個經濟維持著一種雖然低效但卻有序的狀態。市場化巨變打破了這種平衡,工廠無法買到原材料,也不知道買主在何方;更重要的是,它們不知道如何為市場需求進行生產。由此而產生的混亂,再加上國外產品的競爭,讓前蘇聯各國的經濟滑坡在所難免。中國的漸進改革卻產生了相反的結果,它實現了破壞性的建設,為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條件。漸進改革在規模和時間兩方面為個人和企業的調整創造方便。在規模上,漸進改革每次只前進一小步,個人和企業容易適應;在時間上,漸進改革推進緩慢,給個人和企業留下足夠的時間去認識和調整到新的均衡上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企業可能無法生存下去,一些個人也難免在調整中失利,但漸進改革將這樣的破壞降到了最小限度,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了社會生產力,實現經濟增長。 第三,體制釋放帶來經濟增長,體制的逐步釋放帶來地持續增長。每個經濟體都存在一個穩態增長速度,它的高低取決于諸如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率和制度環境等因素。和本文論題相關的是制度因素。對于轉型經濟而言,每一次的制度變革都釋放一定的能量,推動經濟的增長;當所有制度變革都完成時,由制度變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也就停止了,經濟達到穩態增長水平。于是,我們可以借助圖一來分析漸進改革和激進改革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含義。圖中的橫軸代表時間,縱軸代表人均國民收入。假設無論漸進改革還是激進改革都不存在上文所說的破壞性,即個人和企業可以瞬間找到新的均衡;同時假設兩種改革都達到同樣的完美狀態。即便如此,激進改革下的經濟增長路徑也顯著有別于漸進改革下的增長路徑。假設兩種改革均起始于t-----0時刻。激進改革將所有制度潛能在短時間內迅速釋放,經濟增長速度也相應提高。但是,當制度變遷在t1點結束時,經濟快速地收斂到完美制度環境下的穩態增長速度ge,從此經濟以此速度穩定地增長。漸進改革將制度釋放的時間拉長,直至t2點才結束。在t0和t2之間的改革時期,漸進改革下的經濟增長速度低于激進改革在t0和t1之間的增長速度,但當改革在t2時刻結束時,它也收斂到穩態增長速度ge,因為兩種改革最終達到同樣的制度安排。從圖中可以看出,只要漸進改革在t0和t2之間的改革期間的增長速度高于穩態增長速度ge,且這個期間足夠長,則漸進改革的增長路徑就和激進改革的增長路徑相交,并且交點t*在t1之后,因此漸進改革所達到的長期穩態收入水平將持續高于激進改革所能達到的水平。 圖一、激進改革和漸進改革的比較 在現實中,激進改革具有破壞性,像蘇東經驗所顯示的,收入水平在短期內不升反降,由此可能出現圖二所示的增長路徑。一個可能結果是,漸進改革下的收入水平從t0時刻起就高于激進改革下的收入水平。“欲速則不達”,這句古諺在此得到了很好的印證。 圖二、破壞性的激進改革 以上分析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漸進改革可以到達和激進改革相同的制度安排,因此兩者具有同樣的穩態增長速度ge. 然而,二十五年的實踐表明,中國的漸進改革并沒有發生止步不前的跡象,相反,中國的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了一條有利于經濟效率的路徑,符合諾斯所謂的制度變遷的效率假說。因此,我們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是,有效的制度變遷在中國是如何實現的? 三、 地方性創新:有效制度變遷的政治基礎之一 在諾斯的古典國家理論里,無效制度可能因為兩個原因而持續存在,第一個原因是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阻止了有效制度的產生。諾斯早期將意識形態看作是外生的,后來則認為意識形態內生于人對周圍世界的闡釋。人通過對周圍世界的觀察和詮釋形成一個關于理想世界的圖景,并照此設計和改造制度環境。當周圍世界因此而發生變化的時候,人通過比較現實和理想圖景來修正自己的認知模型。由此周而復始,制度和經濟環境發生螺旋式的交替變化。在這個過程中,人的認知模型,或意識形態可能不利于有效制度的獲得。比如,如果統治者認為收入不均是不可接受的,則他不可能接受私有財產制度。即使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沒有問題,諾斯認為,交易成本也會成為阻礙有效制度變遷的第二個原因。比如,西班牙王室之所以不實行土地私有制,是因為向小土地私有者收稅比向大牧羊主收稅更困難(以上討論詳見姚洋,2002)。 在現代民主社會中,制度變遷幾乎總是通過競爭政治發生的,諾斯的古典國家理論因此失去了意義。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中的經典研究告訴我們,民主制度會因為利益集團的左右而無法對變化的現實世界做出正確的反應,有些國家會因此陷入“不可治理”的泥潭;比如,英國的衰落就和利益集團的持續有很大的關系。筆者本人的一項研究表明,在一個意見充分分散的社會里,有效的制度變遷不可能通過降多數原則這樣的政治過程而實現(姚洋,2003a)。道理在于,有效的制度變遷要求制度對經濟環境的變化做出線性的反應(比如,當一種要素的相對價格上升時,這種要素的所有權就應該更加個人化),而政治過程因為要接受所有人的偏好而失去了對經濟環境的敏感度,從而無法對環境的變化做出有效的反應。 既然有效的制度變遷在古典國家和現代民主的框架下都可能無法實現,那么,它為什么能夠在中國發生呢?筆者認為,原因有三,即制度創新的分散性、市場化改革的自我加強性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泛利性。 如前所述,中國漸進改革的一大特征是它幾乎總是源于地方性的試驗。地方與中央的關系,一直是建國以來糾纏不清的問題。中國雖然是單一制的國家,但巨大的地域差距又迫使歷代領導人不得不關注地方積極性。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早已對此進行了論述。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幾收幾放,搖擺不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向地方分權占據了主導地位。在整個八十年代,財政包干制度賦予了地方極大的財政自主權;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則將財政分權規范化。在這種背景下,地方積極性成為推動中國漸進式改革的重要力量。 地方創新之所以優于中央的統一命令,首先是因為地方政府具有中央政府所不具備的信息優勢。他們接近企業、接近市場,容易知道哪些制度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在意識形態尚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這種信息優勢的價值就更加顯著。中央政府由于不了解企業和市場的確切信息,它對自己的意識形態的更新就會比較慢,制度變遷的步伐自然會小一些。相反,地方政府會較快地更新意識形態,因此也更容易接受新的有利于經濟效率的制度安排。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官員的意識形態色彩隨官員地位的下降而逐漸減退;許多地方官員的意識形態色彩比一些學者還輕,這和兩者距離現實的遠近關系極大。 地方積極性導致有效制度變遷的第二個原因來自于地方政府所面對的挑戰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在近代之所以落后于西歐,是因為中國大一統的皇權沒有適當的競爭壓力,使得中國疏于變革而勤于守成。戴爾蒙德認為,西歐德海岸線凹凸不平,有利于形成許多相互競爭的小國,而中國的海岸線非常光滑,有利于形成統一的帝國(Diamond,1999)。在統一的帝國下,地方積極性受到打擊甚至扼殺,地方官員不關心和支持私人的創新活動,經濟自然停滯不前。這種觀點對于解釋中國當代的制度創新也是適用的。在財政分權的體制下,每個地方政府都面臨其它地方政府的競爭壓力,人員和資本的流動迫使每個地方政府挖掘自身的制度潛力,盡力吸引更多的經濟資源流入本地。這里當然會產生浪費性的競爭,也可能產生地方保護主義,但競爭更多地導致了各地制度環境的改善。這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表現尤為明顯。在中國投資辦廠曾經是非常艱難的事情,各種審批和手續無謂地增加了企業的財務和時間成本。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各地為爭奪投資開始了白熱化的競爭,簡化企業注冊手續成為各地的競爭手段之一。從“一條龍”辦公到“十天沉默許可”和變前置審批為后置審批,各地已經開始突破現有的國家統一注冊法規。可以預見,這些地方性的措施會在不遠的將來成為全國性的政策。 分權的制度創新優于統一命令的另一個原因是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強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國債的方式彌補財政赤字,也可以通過行政命令要求地方政府上繳更多的收入,而地方政府卻不能這樣做。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越是底層的政府越是面臨更大的財政壓力,因為它們所掌握的收入更少而負擔的支出卻更多(參見姚洋、楊雷,2003)。這就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更加關注地方性的稅收收入,而后者又和地方經濟密切相關,從而要求地方官員關注影響地方經濟的制度因素。殺雞取卵的事當然有,在不發達地區可能還很普遍;但是,制度的變革仍然可能成為地方官員的選擇之一,因為制度的改變未必會影響他們對企業的攫取,卻可能會帶來更多的收入。 導致地方政府預算硬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銀行系統的商業化。在過去,地方政府可以隨意為地方企業的借款提供擔保,銀行資金因而通過企業而變成地方政府的稅收和其它收入。經過1994年和1998年兩次的銀行改革,銀行信貸變得日益商業化,地方政府已經不能為企業擔保,而銀行貸款的70%必須有抵押和第三方擔保。盡管目前的銀行體制仍然有諸多的不如意之處,但其商業化已成定局,銀行再不是地方政府的私家錢莊了。九十年代遍及全國的企業改制浪潮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既然企業已經不再是地方政府攫取銀行資金的管道,國有制的弊端就日益成為地方政府關注的焦點。改制既可以提高企業的效率,也可以甩掉一些包袱,因此它成為地方政府的當然選擇。 以上分散性制度創新的成果具有自我加強的性質。變革的閘門一旦打開,涓涓細流就會匯成滾滾江河。小崗村民簽下血書之時,農村改革就注定沒有回頭路了。盡管就連中國共產黨內一些最開明的人士也對包產到戶持懷疑態度,小崗的示范效應已經足以讓全國各地紛紛起而效尤。家庭經濟的重新確定不僅僅提高了勞動生產力率,對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而言,它的意義更在于解放了農村勞動力。農民又一次能夠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了。他們先是大量地投入農業生產,當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又將目光投向了非農產業。家庭經濟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現狀明朗化,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出路這一要求構成了對農民身份認定的挑戰。“農民可以不種田” - 這一觀念性的轉變不是學者和官員的號召帶來的,而是經濟力量使然。發達地區的農民就地變成了非農民,不發達地區的農民則紛紛進城打工,形成一浪接一浪的民工潮。農村移民對城市經濟的巨大貢獻迫使政府政策由初期的限制和歧視轉變為現在的包容和接納,而農村移民在城市的沉淀則要求政府采取進一步的行動,促使他們盡快溶入城市社會。 制度變遷自我加強的內在機制是清楚的。對于轉型社會而言,舊有的制度幾乎總是意味著對個人自由和市場力量的約束。當一種制度約束被解除之后,個人自由和市場力量就得到一次伸張,它們的發展壯大必然達到剩余的約束所能容忍的極限,從而對舊制度再一次構成挑戰。制度變遷的分散性大大地增加了這種挑戰的成功機會。中國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如果制度變革由中央政府發起,則為了平衡各地的不同要求,激進的制度創新就幾乎不可能發生;相反,分散性的制度創新可以讓制度在沖擊最強烈的地方首先取得突破。 然而,分權改革的自我加強作用也不能過分夸大。一種觀點認為,分權是中央政府的一種承諾機制,即分權一旦發生,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收回權力。但是,中國過去五十年的實踐表明,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掌握分權與收權的節奏,分權并不意味著剝奪了中央政府收權的能力。中國的分權改革之所以能夠持續有效地進行下來,和我們所說地第三點原因,即中國共產黨的泛利性有很大關系。也許是因為官方話語地過分渲染所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制度變革中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應有重視。在下一節里,我們將著重討論這個問題。 四、 泛利性執政黨:有效制度變遷的政治基礎之二 在《國家的興衰》一書中,奧爾森強調了泛利集團對于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所謂泛利集團,即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集團。與此相對的是分利集團,即那些只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集團。由于只代表少數人的利益,分利集團傾向于要求消費性的分配,而忽視整個社會的財富積累。當分利集團個數很多,且利益又足夠分散時,一個民主的社會就極可能陷入“不可治理”的狀態,無法對經濟的變化做出快速有效的反應。民主的過度發達足以使它走向反面,成為利益集團謀取私利的工具。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法瑞德·扎卡內爾在《自由的未來》一書中對此進行了歷史性和比較性的分析(Zakaria,2003)。他將民主社會分成兩類,一類使不自由的民主,另一類是自由的民主。自由的民主是在憲政支持下的民主,它對個人的自由表達施以某些限制,在很多情況下,它甚至忽視群眾的集體要求,但正因為此,它使個人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不自由的民主表面上完全伸張個人自由,但個人自由的泛濫卻往往導致集體的暴力,最終反過來侵害個人自由。自由的民主需要一種社會中堅力量來維持。扎卡內爾極力推崇一定程度上的貴族統治。貴族無需考慮他們的衣食,也無需考慮他們自己的子女的未來,因此可以轉而關注整個社會的前途。扎卡內爾認為,美國的潛在危險是精英的自我消失。比爾·蓋茨富可敵國,卻堅持認為自己不過是中產階級的一分子而已。精英的自我消失帶來的是責任感的喪失,美國社會因此正在走向不自由的民主。 扎卡內爾沒有討論的,是如何為自由的民主提供制度保障。他極力推崇尼赫魯領導下的印度。尼赫魯自稱是印度的“最后一位英國紳士”,他領導下的印度繼承了英國的憲政自由原則。然而,尼赫魯之后的印度則逐步退化成不自由的民主社會,種族沖突不斷,一些邦甚至完全被流氓和罪犯所統治。扎卡內爾將這種變化歸咎于尼赫魯式的貴族傳統的消失。但我們不得不問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這種傳統會消失?或者,印度的民主是否缺少一種制度的保障?對于一個轉型社會而言,回答類似的問題就更為緊迫。 放眼世界,我們發現,盡管民主的發展中國家也有經濟成功的例子,但是,絕大多數實現了趕超的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政府都或多或少帶有威權特征;而且,這些國家(地區)又集中在東亞。因此,我們不得不問這樣的問題:威權政府、特別是東亞的威權政府和經濟發展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系?對世界現存的威權政府進行一下分類將有利于我們回答這個問題,同時也為我們對中國的討論奠定基礎。 在現代世界里,存在著四種威權政體。第一種是少數人的獨裁體制。在這種體制下,獨裁者只顧個人利益,視人民為魚肉,動輒以武力鎮壓人民的反抗;那里沒有法律,而只有暴政。獨裁者往往有意挑起民族和種族仇恨,由此來鞏固自己的地位;與此相呼應,反對者也利用民族仇恨來反對獨裁者的統治,其結果是國家陷入怨怨相報的惡性循環之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和1990年代初中期的南斯拉夫是這樣的國家的典型例子。 第二種威權政體是民粹主義的威權政府。庀隆統治下的阿根廷是這種政府的最好例子。它迎合民眾的要求,因此常常受到民眾的擁戴。但是,民眾的要求幾乎總是分利性而非建設性的,因此要以犧牲整個社會的長期利益為代價。這不是說民眾缺乏道德水準,而是集體行動的邏輯使然:每個人從政府那里分得的利益是實實在在的,而每個人可以占有的社會福利的增加部分卻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每個人都會注重政府的直接分配,而不會去考慮全社會福利的提高。由于無法長期滿足民眾的要求,民粹主義政府會因為失去政治基礎而很快垮臺。 第三種威權政體是泛利性的威權政府。東亞地區的威權政體屬于這一類。泛利性威權政府的特點是以社會的長遠利益為目標,為此經常抵制民眾的要求,哪怕這種要求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當政府能夠以社會的長遠利益為目標的時候,它就會制定出有利于長期經濟增長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東亞經濟的迅速趕超與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關系很大。 那么,為什么東亞的威權政體是泛利性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東亞的歷史和文化中尋找答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東亞在近現代都經歷了一段屈辱的歷史。日本在歷史上長期是中國的小學生,在近代又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這樣的歷史讓極其自尊的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之后發奮圖強,很快在甲午海戰中擊敗中國,繼而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俄國。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戰敗的恥辱更是增強了日本人的凝聚力,在短短三十年間便趕上了占領者美國。韓國長期是中國的附屬國,近代又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這樣的歷史和獨特的地理環境造就了韓國發奮甚至褊狹的民族性,后者有利于形成國家的凝聚力和經濟的發展。韓國民眾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紛紛變賣金銀首飾以供國家還債,由此可見韓國的國家凝聚力有多強。臺灣的經濟發展和國民黨與大陸共產黨的競爭不無關系。1960年代初期之后,反攻大陸已經沒有了希望,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可能競爭領域就只剩下經濟發展了。蔣介石去世之后,蔣經國正式放棄反攻大陸,頃全力發展臺灣經濟,他執政的十年成為臺灣經濟發展最輝煌的時期。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儒家文化的忠、孝、廉、勤的品質為東亞各國(地區)提供了社會的黏合劑。其它發展中國家也曾經歷過屈辱的歷史,但它們沒有東亞的獨特文化。一位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的美國朋友的概括最能說明問題。他說:“新加坡的神奇之處在于,它有一個精于治理的政府和一群愿意被治理的民眾。” 第四種威權政體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蘇式社會主義國家具有很強的泛利性,但是,意識形態和對經濟規律的錯誤認識妨礙了它采納有效的市場制度安排。計劃經濟在一定時期內可以取得很高的經濟成就,但長期卻會使國家陷入停滯。同時,計劃體制造就了一個官僚階層,它阻礙社會的創新。 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屬于第四種威權政體,同時也具有在政治動員基礎上的民粹主義特征。在革命時期,共產黨以下層民眾為其基礎;革命成功之后的社會主義改造繼續了這一傳統,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這些變化創造了社會的民主化;但在另一方面,社會的層級結構被破壞,群眾性的破壞力量時而得到空前的釋放,在沒有民主制度框架的條件下,中國具有了許多不自由的民主的特征。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民眾的破壞力量幾乎總是在執政者或好或壞的意志的鼓動下聚積和釋放的。大躍進是執政者出于好意發動的集體趕超運動,但是,錯誤的政策導致了巨大的災難。文化大革命則是由少數人出于個人目的發動的群眾運動,其結果不僅是使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且也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的社會結構,破壞了人與人之間最起碼的信任和尊重。經濟的損失可以在短時期內補救回來,而社會秩序的損失可能需要幾代人之后才能恢復。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歷了一個由蘇式社會主義向泛利性威權政體轉變的過程。中國在近現代也經歷了外敵入侵、國土淪喪的屈辱歷史,又是儒家文化的發祥地,因此具有走向泛利性政體的歷史和文化基礎。除了經濟制度方面的轉型,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最顯著的轉變是在意識形態和具體政策上的非群眾化。這個轉變不為人所注意,但卻對中國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濟和社會轉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給共產黨的一個慘痛的教訓是,在沒有真正的敵人的情況下,哪怕其初衷再好,群眾運動也會演變為對制度和秩序極具破壞性的力量。大鳴大放式的民主是沒有責任的民主,它很容易變成用來進行匿名攻擊的工具,對自由的民主不但毫無貢獻,而是只會破壞之。同時,正如種族和民族仇恨經常被獨裁者用來撈取個人利益一樣,群眾運動也極容易被一些人用來達到他們的個人目的,國家因此陷入派性斗爭的泥潭。群眾運動表面上是賦予群眾以最大的自由和民主權利,其結果卻是極大的不自由和反民主。因此,改革開放之后放棄以群眾動員為主要形式的經濟和制度建設方式,無疑是一個明智之舉。這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變化,而且也是工作方式的變化。過去,走群眾路線是共產黨的一項基本工作方針;隨著意識形態的改變,這項方針已經被部分地放棄了,只是在某些情況下才得到有選擇的執行。 在具體政策上,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首開非群眾化的先河。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意味著放棄對平民化社會結構的追求,也意味著對群眾分化的承認。于1992年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始了全面非群眾化的進程。市場經濟意味著大部分的資源配置將由市場來完成,同時也意味著經濟決策的分散化;因此,群眾動員失去了基礎,群眾的同質性無法維持,群眾更應該在市場上獲得報酬而不是找國家尋求幫助。在劇烈的體制變革過程中,有受益者,也有受損者。如果改革者不能抵制受損者的利益要求,改革就無法推進。如果說農村改革是順應了群眾的要求的話,過去二十五年發生的其它所有其它改革都多多少少地損害了一部分群眾的利益。這些改革之所以能夠實行,恰恰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能夠抵制受損者的利益要求,在某些條件下,這些受損者甚至可能是作為共產黨傳統階級基礎的工人階級。這在1990年代表現得尤為顯著。在這個時期,大量的國營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瀕于倒閉,職工紛紛下崗失業,其源頭可以追溯到于1990年代初完成的價格改革以及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的確立。正是由于市場化改革的推進,1990年代才見證了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和外資的大量涌入,它們擠壓了國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導致了大量的下崗和失業。可以想象,在一個完全的民主社會里,由此而引起的社會不滿會迅速地通過利益集團和政黨政治傳遞到國家決策中去,市場化改革因此可能胎死腹中。民主是一把雙刃劍,民意的表達既可以防止執政者的一意孤行,也可以顛覆有利于國家長遠利益的經濟政策。由于它的獨特地位,中國共產黨可以不考慮部分民眾的利益要求,而專注于國家的長遠利益。一方面,國家抓緊了對下崗失業人員的社會救濟和培訓;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向縱深方向發展,改制和民營化成為最后解決國營企業問題的措施。中國的私有化的速度和程度都不低于蘇東國家,且也以內部人控制為主要形式,腐敗和不公因此在所難免。盡管國家也強調要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但這種強調的口頭意義大于其實際意義,地方政府為早日完成改制,對新的企業所有者(主要是企業內部人員)做出了很大的讓步。在建立市場經濟的大目標下,腐敗和不公在很大程度上作為不可避免的副產品而被容忍了。 十六大所確定的黨的新的代表方針進一步強化了黨的泛利性,對于一個以經濟趕超、民族復興為第一要務的黨來說,這種代表性的轉變是必要的。由于它的泛利性,中國共產黨不僅僅是一個執政黨,而且也為中國的社會轉型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礎。這樣說當然不排除由此而引起的副作用。黨對經濟效率的追求極有可能導致意識形態的喪失,從而使黨乃至國家失去應有的粘合劑。在泛利化的過程中,黨有必要重塑意識形態。這是一個有別于本文主旨的話題,具體討論參見筆者的另一篇文章(姚洋,2003b)。 五、 結束語 回顧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二十五年制度變遷的歷史,我們發現,它的軌跡基本上反映了對經濟效率的追求;而且,制度的釋放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中國獨特的政治體制是支持有效制度變遷的關鍵。這個體制的特點是地方性創新和一個統一的泛利性執政黨的結合;前者保證了制度創新的有效性,而后者則保證了有效的制度在全國的推廣和執行。 總結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有利于我們對中國民主之路的思考。民主具有無可否認的規范價值,同時也具有積極的實證意義,其中最為重要的,依我所見,是它會讓我們這個本不寬容的民族學會寬容。但是,民主僅僅是我們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之一,當對民主的追求和更基本的需求相矛盾的時候,我們可能不得不弱化前者而專攻后者。同時,民主的形式不止一種,達到民主的途徑也不止一條;選擇何種民主,采取哪條途徑,已經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問題。中國經濟制度的平穩轉型為中國政治的平穩轉型提供了思路。從某種意義上講,政治轉型已經開始模仿經濟轉型的道路。一方面,基層民主已經在城鄉推廣,民眾在這個過程中將學習民主,民主也將由此得到錘煉;另一方面,法治在更高層面得到加強,人大的地位有了提高。一種新的共識正在形成,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以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分離和制衡為特征的憲政是可能的。在這個憲政框架中,中國共產黨所扮演的,是國家利益的看護者的角色;相應地,立法、司法和行政扮演的是執行者的角色。由于公共機構天然的官僚傾向,讓立法、司法和行政之中的任何一個擁有過大的權力都會妨礙國家整體利益的獲得。因此,它們之間的分權和制衡是獲取國家利益的有效制度安排;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不僅不會弱化共產黨的領導,而是只會加強之。如果以上共識能夠更加明朗化并得以實施,中國就可以盡快地確立自由的民主的制度基礎,從而使未來的民主變成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說沒有通往市場的市場化道路,則必定也沒有通往民主的民主化道路。中國經濟的漸進轉型或許也是中國民主的轉型之路。 參考文獻: Diamond, Jare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and London: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Garnaut, Ross, Ligang Song, Stoyan Tenev, and Yang Yao. Firm Restructuring in China. World Bank, forthcoming. Lau, Lawrence, Yingyi Qian, and Gerard Roland. “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08(1): 120-43. Lin, Justin Yifu.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1): 34-51. 盧峰、姚洋:《金融壓抑下的法治、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中國社會科學》待刊。 秦暉:《中國的經濟轉軌、社會公正與民主化問題》,載姚洋主編:《審視中國-轉型時期的社會公正和平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阿瑪蒂亞·森:《評估不平等和貧困的概念性挑戰》,《經濟學季刊》,2003年,第2卷第2期:257-270。 姚洋:《制度與效率:和諾斯對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姚洋:《政治過程和有效制度變遷》, 《制度經濟學研究》,2003a,第1卷第1期: 1-16。 姚洋:《務實而不放棄理想》,《中國改革》,2003b, 2003年第3期。 姚洋、楊雷:《制度供給失衡和中國財政分權的后果》,《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3期,第27-33頁。 Zakaria, Fareed,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 感謝丁利、張宇燕以及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高級研討會與會者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姚洋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