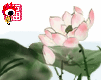| ūįė╔┐╔ęį▀@śėüĒūĘŪ¾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Ļ07į┬22╚š 18:10 ųąįuŠW(w©Żng) | |||||||||
|
ĪĪĪĪ░ó¼ö?sh©┤)┘üåĪż╔Łą┬ų°ĪČū„×ķūįė╔Ą─░l(f©Ī)š╣ĪĘįuĮķĪĪĪĪ ĪĪĪĪę”č¾ ĪĪĪĪĪĪ
ĪĪĪĪī”ė┌Įø(j©®ng)Ø·īW╝ęüĒšfŻ¼║Ō┴┐Įø(j©®ng)Ø·░l(f©Ī)š╣Ą─ųĖś╦▓╗═Ō║§╚²éĆŻ║╚╦Š∙╩š╚ļĄ─╠ßĖ▀Īó╣żśI(y©©)╗»╦«ŲĮ║═│Ū╩ą╗»╦«ŲĮĪŻļm╚╗▀@ą®ųĖś╦ŅlŅlįŌĄĮĘŪĮø(j©®ng)Ø·īW╝ęĄ─┼·įuŻ¼Ą½ę╗░ŃĮø(j©®ng)Ø·īW╝ęī”▀@ą®┼·įu▓ó▓╗▓╔╚ĪšJšµī”┤²Ą─æB(t©żi)Č╚ĪŻ░ó¼ö?sh©┤)┘üåĪż╔Ł╩ŪĮ?j©®ng)Ø·īW╝ęųąĄ─┴ĒŅÉŻ¼╦¹╩Ū×ķöĄ(sh©┤)▓╗ČÓĄ─╝╚į┌ų„┴„Įø(j©®ng)Ø·īWĮńųąŽĒėą║▄Ė▀┬Ģ═¹Ż¼═¼Ģrėų─▄│¼║§Įø(j©®ng)Ø·īWų«═Ō┼cŲõ╦¹╔ńĢ■┐ŲīW╝ę╝░╚╦╬─īWš▀ī”įÆĄ─Įø(j©®ng)Ø·īW╝ęĪŻį┌Ųõą┬ų°ĪČū„×ķūįė╔Ą─░l(f©Ī)š╣ĪĘ(Development As Freedom)ę╗Ģ°ųąŻ¼╔Łī”Įø(j©®ng)Ø·░l(f©Ī)š╣▀Mąą┴╦╚½├µĄ─Ę┤╦╝Ż¼▓óęį╦¹Ą─ūįė╔ė^×ķ║╦ą─ī”░l(f©Ī)š╣▀Mąą┴╦ųžą┬Č©┴xĪŻ╦¹ęį┴„Ģ│Ą─╣Pė|║═ą█▐qĄ─▀ē▌ŗŽ“╚╦éāš╣╩Š┴╦ę╗éĆų„Ņ}Ż¼▀@Š═╩ŪŻ¼░l(f©Ī)š╣╩Ūī”╚╦Ą─╚½├µūįė╔Ą─ūĘŪ¾ĪŻ▀@śėĄ─ę╗éĆų„Ņ}ūóČ©┴╦▀@▒ŠĢ°Ą─ė░Ēæīó▀h▀h│¼│÷Įø(j©®ng)Ø·īWĄ─ĘČ«ĀŻ¼╩╣Ą├╦³│╔×ķ░l(f©Ī)š╣蹊┐ųąĄ─ę╗▓┐└’│╠▒«╦ŲĄ─ų°ū„ĪŻ ĪĪĪĪ╚╗Č°Ż¼«ö╔Ł│┴õŽė┌ī”░l(f©Ī)š╣Ą─š▄īW╦╝┐╝Ą─Ģr║“Ż¼╦¹ī”Ųõ└Ēšōį┌īŹ╩®īė├µĄ─ęŌ┴x┐╝æ]śO╔┘Ż╗═¼ĢrŻ¼į┌ęįūįė╔▀@ę╗éĆĖ┼─ŅĮy(t©»ng)ę╗Ųõ░l(f©Ī)š╣ė^Ą─Ģr║“Ż¼╦¹ę▓▓╗┐╔▒▄├ŌĄžę¬ė÷ĄĮę╗ą®└ĒšōļyŅ}Ż¼│÷¼F(xi©żn)ę╗ą®▀ē▌ŗ╔ŽĄ─├¼Č▄ĪŻ▒Š╬─īó╩ūŽ╚ĮķĮB╔ŁĄ─ų„ę¬ė^³cŻ¼╚╗║¾ī”Ųõ└ĒšōĮo│÷ę╗ą®įušōĪŻ╬─š┬Ęų│╔╚²╣Ø(ji©”)ĪŻĄ┌ę╗╣Ø(ji©”)ĮķĮB╔Łęįūįė╔×ķ║╦ą─Ą─░l(f©Ī)š╣ė^Ż¼Ą┌Č■╣Ø(ji©”)ĮķĮB╦¹╦∙ėæšōĄ─ÄūéĆīŻŅ}Ż¼Ą┌╚²╣Ø(ji©”)╩ŪÄūéĆīŻŅ}įušōĪŻ ĪĪĪĪę╗Īó ░l(f©Ī)š╣┼cūįė╔ ĪĪĪĪ░l(f©Ī)š╣▓╗āHāH╩Ū╚╦Š∙╩š╚ļĄ─╠ßĖ▀ĪŻ╔Ł┼eŅAŲ┌ē█├³Ą─└²ūėęįšf├„ų«ĪŻųąć°Ą─╚╦Š∙ć°├±╩š╚ļ×ķ815├└į¬Ż¼ŅAŲ┌ē█├³×ķ71Üq(Ą┌╬Õ┤╬╚╦┐┌Ųš▓ķöĄ(sh©┤)ō■(j©┤))Ż╗╦╣└’╠m┐©Ą─╚╦Š∙╩š╚ļ┼cųąć°ŽÓ«öŻ¼ŅAŲ┌ē█├³×ķ73ÜqŻ╗░═╬„Ą─╚╦Š∙╩š╚ļ×ķ2800├└į¬Ż¼ŅAŲ┌ē█├³ģsų╗ėą65ÜqŻ╗─ŽĘŪĄ─╚╦Š∙╩š╚ļĖ▀▀_3000├└į¬Ż¼ŅAŲ┌ē█├³ę▓ų╗ėą65ÜqĪŻį┘š▀Ż¼├└ć°║┌╚╦Ą─╩š╚ļļm╚╗į┌├└ć°ŽÓī”▌^Ą═Ż¼Ą½┐ŽČ©│¼▀^┤¾▓┐Ęųųąć°╚╦║═ėĪČ╚╚╦Ą─╩š╚ļŻ¼Ą½╩ŪŻ¼├└ć°║┌╚╦─ąąįį┌Ė„éĆ─Ļ²gĮMĄ─╦└═÷Ė┼┬╩Č╝│¼▀^ųąć°║═ėĪČ╚┐╦└Ł└Ł(Kerala)░Ņ═¼─Ļ²gĮM─ąąįĄ─╦└═÷Ė┼┬╩ĪŻÅ─╚╦Š∙╩š╚ļüĒ┐┤Ż¼ųąć°ĪóėĪČ╚║═╦╣└’╠m┐©¤oę╔ī┘╩└Įń╔ŽūŅ▓╗░l(f©Ī)▀_ć°╝ęų«┴ąĪŻĄ½╩ŪŻ¼╚╦▓╗╩Ūå╬├µĄ─Įø(j©®ng)Ø·╚╦Ż¼Č°╩ŪŠ▀ėąČÓųžūĘŪ¾Ą─╔ńĢ■╚╦ĪŻĮø(j©®ng)Ø·─┐ś╦ų╗╩Ū╦¹Ą─ūĘŪ¾ų«ę╗Ż¼Č°ĮĪ┐ĄĪóĮ╠ė²Īó▓╗╩▄╦¹╚╦ē║Ų╚Īóūįė╔▀wßŃĪóūįė╔▒Ē▀_ęį╝░ūį╬ęīŹ¼F(xi©żn)Ą╚Ą╚ę▓╩Ū╦¹╦∙ūĘŪ¾Ą──┐ś╦ĪŻ╔Łīó╚╦Ą─╚½├µūĘŪ¾Įy(t©»ng)ę╗į┌ūįė╔▀@ę╗Ė┼─Ņų«Ž┬ĪŻ ĪĪĪĪī”ūįė╔Ą─Č©┴x╩ŪČÓ├µĄ─ĪŻūŅ▒Ż╩žĄ─ūįė╔ė^╩Ū╣┼Ąõūįė╔ų„┴xš▀Ą─ūįė╔ė^Ż¼Ųõ«ö┤·┤·▒Ē╚╦╬’╩Ū±TĪż╣■ę«┐╦ĪŻį┌╦¹─Ū└’Ż¼ūįė╔╩ŪĪ░ę╗éĆ╚╦▓╗╩▄ųŲė┌┴Ēę╗éĆ╚╦╗“┴Ēę╗ą®╚╦ę“?q©▒)ŻöÓęŌųŠČ°«a(ch©Żn)╔·Ą─ÅŖųŲĄ─ĀŅæB(t©żi)ĪŻĪ▒(╣■ę«┐╦Ż¼1997Ż║Ą┌4Ēō)ūįė╔Ą─Ę┤├µ╩Ūę╗ĘNÅŖųŲŻ¼ę“┤╦╩Ūę╗ĘNÉ║ĪŻūįė╔ęŌ╬Čų°ę╗éĆ╚╦▓╗╩▄▀@ĘNÉ║Ą─ÅŖųŲŻ╗ø]ėą▀@ĘNÉ║Ą─┤“ö_Ż¼ę╗éĆ╚╦Š═╩Ūūįė╔Ą─ĪŻę“┤╦Ż¼ę╗éĆ┴„└╦Øh╩Ūūįė╔Ą─Ż¼ę╗éĆć╗─ųąĄ─ļy├±╩Ūūįė╔Ą─Ż¼│÷┘u┼«ā║ęįĄųé∙Ą─ŚŅ░ūä┌ę▓╩Ūūįė╔Ą─Ż¼Č°ŪęŻ¼╦¹éāĄ─ūįė╔║═▒╚Ā¢Īż╔w┤─Ą─ūįė╔▓ó¤oČ■ų┬ĪŻĄ½╩ŪŻ¼ę╗éĆć├±Ą─ūįė╔ęŌ╬Čų°╩▓├┤Ż┐ļyĄ└╩ŪĪ░ūįė╔Ąž╚ź▀xō±╦└═÷Ī▒å߯┐’@╚╗Ż¼╣■ę«┐╦ī”ūįė╔Ą─Č©┴x╩Ū▀^ĘųĄž¬MšŁ┴╦ĪŻ░ž┴ųģ^(q©▒)Ęų┴╦ā╔ĘNūįė╔Ż¼ę╗ĘN╩Ū▒╗äėūįė╔Ż¼ę╗ĘN╩Ūų„äėūįė╔ĪŻ▒╗äėūįė╔╝┤╩Ū╣┼Ąõūįė╔Ż¼Ą└│÷┴╦ūįė╔╩╣╚╦├Ōė┌╦¹╚╦Ūų║”Ą─ę╗├µĪŻų„äėūįė╔ųĖĄ─╩Ū╚╦Ą──▄äėĄ─ę╗├µŻ¼╝┤ę╗éĆ╚╦─▄ū÷╩▓├┤(Berlin, 1969)ĪŻ’@╚╗Ż¼ć├±╦∙ŽĒėąĄ─āHāH╩Ū▒╗äėūįė╔Ż¼Č°ø]ėąų„äėūįė╔ĪŻ ĪĪĪĪ╔Łī”ūįė╔Ą─└ĒĮŌ║═░ž┴ųę╗ų┬Ż¼╦¹īó▒╗äėūįė╔║═ų„äėūįė╔ĘųäeĘQ×ķūįė╔Ą─▀^│╠ĘĮ├µ║═ūįė╔Ą──▄┴”ĘĮ├µŻ¼▓ó╠žäeĻP(gu©Īn)ūóūįė╔Ą──▄┴”ĘĮ├µĪŻĪ░─▄┴”Ī▒(capability)▀@éĆĖ┼─Ņį┌╔ŁĄ─└Ēšōųąš╝ō■(j©┤)ų°ųžę¬Ą─Ąž╬╗ĪŻ╦³▓╗╩Ūį┌ĪČū„×ķūįė╔Ą─░l(f©Ī)š╣ĪĘ▀@▒ŠĢ°└’╠ß│÷üĒĄ─Ż¼Č°╩Ū╔Łį┌▌^įńĄ─Ģr║“×ķ┴╦īżšę╠µ┤·╣”└¹ų„┴xĪó╣┼Ąõūįė╔ų„┴x║═┴_Ā¢╦╣ų„┴xĄ─ą┬Ą─╣½š²└ĒšōČ°╠ß│÷Ą─ę╗éĆ║╦ą─Ė┼─ŅĪŻĪ░ę╗éĆ╚╦Ą─Ī«─▄┴”Ī»ųĖĄ─╩Ū┐╔╣®ę╗éĆ╚╦½@╚ĪĄ─▓╗═¼Ą─╣”─▄ĮM║ŽĪŻ─▄┴”═¼Ģr╩Ūę╗ĘNūįė╔Ż║ę╗ĘN▀_ĄĮ▓╗═¼╣”─▄ĮM║ŽĄ─ųžę¬ūįė╔(╗“ė├▓╗╠½š²╩ĮĄ─šZčįüĒšfŻ¼╩ŪūĘŪ¾▓╗═¼╔·╗ŅĘĮ╩ĮĄ─ūįė╔)ĪŻĪ▒(Sen, 1999:Ą┌75Ēō)[1] ╔Ł┼e└²šfŻ¼Å─▒Ē├µ╔Ž┐┤Ż¼ę╗éĆĖ╗ėąĄ─╚╦Ą─ūįįĖ╣Ø(ji©”)╩│║═ę╗éĆĖF╚╦Ą─▒╗Ų╚▐▀Iį┌╦∙▀_ĄĮĄ─╣”─▄╔Ž╩Ūę╗śėĄ─Ż¼Ą½╩ŪŻ¼Ū░š▀═Ļ╚½ėą─▄┴”▀xō±ČÓ│įę╗ą®Ż¼ę“┤╦Ż¼╦¹▒╚║¾š▀ōĒėąę╗éĆĖ³┤¾Ą─Ī░─▄┴”╝»Ī▒ĪŻ ĪĪĪĪ╔Ł╠ß│÷─▄┴”▀@éĆĖ┼─Ņėąā╔ĘĮ├µĄ─ęŌ┴xĪŻę╗ĘĮ├µŻ¼╦³▒▄├Ō┴╦╣”└¹ų„┴xš▀Ą─ą¦ė├╦∙ę²ŲĄ─Ųń┴xĪŻą¦ė├═Ļ╚½╩Ūę╗ĘNą─└ĒĀŅæB(t©żi)Ż¼╚ń╣¹╬ęéāīó╣½š²└ĒšōĮ©┴óį┌ą¦ė├▒╚▌^Ą─╗∙ĄA(ch©│)╔ŽŠ═Ģ■│÷¼F(xi©żn)å¢Ņ}ĪŻ▒╚╚ńę╗éĆ╗©╗©╣½ūė─▄ē“═µ│÷įSČÓ╗©śėŻ¼╦¹Å─▀ģļH╔ŽĄ─ę╗į¬ÕX╔Ž╦∙Ą├ĄĮĄ─ą¦ė├▒╚ę╗éĆÜł╝▓╚╦Ė▀Ż¼╣”└¹ų„┴xę“┤╦ę¬Ū¾╔ńĢ■░č▒ŠįōĮoėĶÜł╝▓╚╦Ą─▀@ę╗į¬ÕXĮo╗©╗©╣½ūėĪŻ─▄┴”▓╗╩Ūę╗ĘNėõÉéŻ¼Č°╩ŪĻP(gu©Īn)ė┌ę╗éĆ╚╦▀xō±╝»Ą─Č╚┴┐Ż¼ę“┤╦▒▄├Ō┴╦ą¦ė├▒╚▌^Ą─å¢Ņ}ĪŻ[2] ┴Ēę╗ĘĮ├µŻ¼─▄┴”ę▓▓╗═¼ė┌┴_Ā¢╦╣Ą─╗∙▒Š╬’ŲĘĪŻį┌ĪČš²┴xšōĪĘę╗Ģ°ųą(┴_Ā¢╦╣Ż¼1991)Ż¼┴_Ā¢╦╣įćłDį┌ūŅ┤¾ūŅąĪįŁätĄ─╗∙ĄA(ch©│)╔Žśŗ(g©░u)įņę╗éĆą┬Ą─╔ńĢ■╣½š²└ĒšōĪŻĄ½╩ŪŻ¼▒Ŗ╦∙ų▄ų¬Ż¼▀@éĆįŁätĄ─║¾╣¹╩Ū═Ļ╚½ŲĮŠ∙ų„┴xĪŻ×ķ┴╦Åøča▀@éĆ▓╗ūŃŻ¼┴_Ā¢╦╣╠ß│÷┴╦╗∙▒Š╬’ŲĘĄ─Ė┼─ŅĪŻ░┤šš┴_Ā¢╦╣Ą─Č©┴xŻ¼╗∙▒Š╬’ŲĘ░³└©╗∙▒ŠĄ─š■ų╬ÖÓ(qu©ón)└¹║═ę╗ą®╗∙▒ŠĄ─╬’┘|(zh©¼)«a(ch©Żn)ŲĘĪŻ┴_Ā¢╦╣░čūŅ┤¾ūŅąĪįŁätĄ─▀mė├ĘČć·Ž▐Č©į┌╗∙▒Š╬’ŲĘĄ─ĘČć·ų«ā╚(n©©i)ĪŻ╗∙▒Š╬’ŲĘĄ─Č©┴xŽ¹│²┴╦éĆ╚╦ķgą¦ė├Ą─▒╚▌^Ż¼Ą½═¼Ģrę▓Ę┼Śē┴╦ī”╚╦éā└¹ė├▀@ą®╗∙▒Š╬’ŲĘĄ──▄┴”▓Ņ«ÉĄ─ĻP(gu©Īn)ūóĪŻ╔ŁįćłD╚§ča▀@ę╗³cĪŻ╦¹Ą──▄┴”Ė┼─Ņ▓╗āH░³└©ę╗éĆ╚╦╦∙ōĒėąĄ─ÖÓ(qu©ón)└¹║═╬’ŲĘŻ¼Č°Ūę░³└©▀@éĆ╚╦╩╣ė├▀@ą®ÖÓ(qu©ón)└¹║═╬’ŲĘĄ──▄┴”ĪŻ▒╚╚ńŻ¼ę╗éĆļp═╚Üł╝▓Ą─╚╦¤ošōČÓ├┤ėąÕXę▓¤oĘ©ūį╚ńĄžį┌ø]ėą▌åę╬Ų┬Ą└Ą─Įų╔ŽęŲ äėŻ╗╦¹ļm╚╗ōĒėą┴╦╬’ŲĘŻ¼Ą½ģsø]ėąōĒėą╩╣ė├▀@ą®╬’ŲĘĄ──▄┴”ĪŻųĄĄ├ūóęŌĄ─╩ŪŻ¼╔ŁĄ──▄┴”▓╗ę╗Č©╩ŪāHųĖéĆ╚╦─▄┴”Ż¼į┌╔Ž╩÷└²ūėųąŻ¼╦¹Ą──▄┴”╚ĪøQė┌╔ńĢ■╦∙╠ß╣®Ą─Ä═ų·Ą─ČÓ╣čĪŻ ĪĪĪĪ╔Łī”╣”└¹ų„┴xĪó┴_Ā¢╦╣ų„┴xęį╝░ęįųZ²R┐╦×ķ┤·▒ĒĄ─╣┼Ąõų„┴x▀Mąą┴╦┼·┼ąĪŻ╦¹ī”╣”└¹ų„┴xĄ─┼·┼ą▓╗═¼ė┌╬ęéāę╗░Ń╦∙ęŖĄ─Ż¼╦¹šJ×ķŻ¼╣”└¹ų„┴xĄ─å¢Ņ}▓╗į┌ė┌ą¦ė├Ą─┐╔▒╚ąįŻ¼Č°į┌ė┌╦³Ą─ą┼Žó╗∙(information base)╠½šŁĪŻ╣”└¹ų„┴xų╗ĻP(gu©Īn)ūóĖŻ└¹ę╗ĒŚųĖś╦Ż¼Č°║÷┬į┴╦Ųõ╦³ųĖś╦Ż¼╚ńūįė╔ĪóŲĮĄ╚║═ÖÓ(qu©ón)└¹Ą╚Ą╚ĪŻī”ė┌┴_Ā¢╦╣ų„┴xŻ¼╔Łī”ūįė╔ā×(y©Łu)Ž╚įŁät╠ß│÷┴╦╠¶æ(zh©żn)ĪŻ╦¹Ą─ų„ę¬å¢Ņ}╩ŪŻ¼▀@éĆįŁät─▄ʱ▀_ĄĮéĆ¾wūįė╔Ż┐├µī”ę╗éĆć─c▐A▐AĄ─┴„└╦ØhŻ¼╬ęéā─▄ę¬Ū¾╦¹į┌ūįįĖ×ķ┼½ęįĄ├ĄĮę╗▓═’¢’ł║═I╦└ų«ķg▀xō±║¾š▀å߯┐ųZ²R┐╦(1974)šJ×ķŻ¼─│ą®ÖÓ(qu©ón)└¹ęį╝░ė╔┤╦Č°č▄╔·Ą─Ī░æ¬(y©®ng)Ą├ų«╬’Ī▒(entitlements)╩Ū╔±╩ź▓╗┐╔ŪųĘĖĄ─ĪŻ▒╚╚ńŻ¼žö«a(ch©Żn)ÖÓ(qu©ón)ęį╝░ė╔┤╦ȰĦüĒĄ─╩šęµ(░³└©└^│ą╦∙Ą├ĄĮĄ─╩šęµ)╩Ū▓╗┐╔ŪųĘĖĄ─ĪŻųZ²R┐╦▀Mę╗▓ĮųĖ│÷Ż¼╝┤╩╣ī”▀@ą®ÖÓ(qu©ón)└¹Ą─▒ŻūoĢ■įņ│╔ę╗Č©Ą─éĆ╚╦ōp╩¦Ż¼ć°╝ęę▓▒žĒÜ▀@śėū÷ĪŻĄ½╩ŪŻ¼Ī░╬ęéā║▄ļy┘Ø═¼▀@ĘN▓╗ŅÖ║¾╣¹Ą─║åå╬Ą─▀^│╠ūįė╔įŁätĪŻĪŁĪŁŽÓĘ┤Ż¼į┌▓╗║÷ęĢŲõ╦³┐╝æ]Ī¬Ī¬░³└©Ė„ĘN▀^│╠ī”╚╦éāīŹļH╦∙ōĒėąĄ─ūįė╔Ą─īŹļHė░ĒæĪ¬Ī¬Ą─ŪķørŽ┬Ż¼ĻP(gu©Īn)ūóĮY(ji©”)╣¹┐╔ęį┘xėĶūįė╔Ą─īŹ¼F(xi©żn)╗“▀`▒│ęį║▄Ė▀Ą─ųžę¬ąį(▓óŪę┐╔─▄Įo║¾š▀ęį╠žäeĄ─ėH▓A)ĪŻĪ▒(Sen,1999:Ą┌66Ēō)╔ŁšJ×ķŻ¼ųZ²R┐╦Ą─Į^ī”ÖÓ(qu©ón)└¹ė^║▄ļy×ķ░l(f©Ī)š╣ųąć°╝ę╦∙Įė╩▄ĪŻ ĪĪĪĪ╔Ł▒Š╚╦Ą──▄┴”įŁätį┌║▄┤¾│╠Č╚╔Ž║═╬„ĘĮ┼dŲĄ─ą┬ū¾┼╔Ą─ų„Åłę╗ų┬ĪŻėóć°╣ż³hĄ─└Ēšō╝ę╝¬ĄŪ╦╣į┌ĪČĄ┌╚²ŚlĄ└┬ĘŻ║╔ńĢ■├±ų„ų„┴xĄ─Å═┼dĪĘę╗Ģ°ųąšJ×ķ(╝¬ĄŪ╦╣Ż¼2000)Ż¼╣ż³hĄ──┐ś╦╩ŪĮ©┴óę╗éĆĪ░═Č┘Yą═Ī▒Ą─╔ńĢ■ĪŻį┌╦¹┐┤üĒŻ¼ĖŻ└¹ųŲČ╚Ą──┐ś╦▓╗╩ŪŠ╚ų·ĖF╚╦Ż¼Č°╩Ūųž╦▄╦¹éāģó╝ė╔ńĢ■╔·«a(ch©Żn)╦∙▒žąĶĄ─╝╝─▄ĪŻ▀@║═╔Łīó╣½š²└ĒšōĮ©┴óį┌éĆ╚╦─▄┴”Ą─▒╚▌^╗∙ĄA(ch©│)╔ŽĄ─ų„Åł▓╗ų\Č°║ŽĪŻį┌╔Ł─Ū└’Ż¼├┐éĆ╚╦Ą─│§╩╝ĘA┘x╩Ū▓╗═¼Ą─Ż¼Ą½└ŁŲĮĘA┘xĘų┼õ▓╗╩Ū╣½š²Ą──┐ś╦Ż¼Č°įņŠ═éĆ╚╦└¹ė├ĘA┘xĄ─ŲĮĄ╚─▄┴”▓┼╩Ū─┐ś╦ĪŻ╔Ł▓╗╩Ūū¾┼╔Įø(j©®ng)Ø·īW╝ęŻ¼Ą½ī”╚§ä▌╚║¾wĄ─ĻP(gu©Īn)ūó╩╣╦¹Ą─ų„Åłūį╚╗Č°╚╗Ąž║═ū¾┼╔ū▀ĄĮ┴╦ę╗ŲĪŻ ĪĪĪĪČ■Īó ÄūéĆīŻŅ}ėæšō ĪĪĪĪ╔Łį┌│╬ŪÕ┴╦─▄┴”▀@ę╗║╦ą─Ė┼─Ņų«║¾ė├Äūš┬Ą─Ų¬Ę∙ėæšō┴╦ÄūéĆīŻķTå¢Ņ}Ż¼╚ńĖF└¦Īóć╗─Īó╩ął÷║═ć°╝ęĪó├±ų„ĪóŗD┼«Ąž╬╗Īó╚╦┐┌║═ėŗäØ╔·ė²Īó╬─╗»║═╚╦ÖÓ(qu©ón)ęį╝░╔ńĢ■Ą─│ąųZĄ╚ĪŻį┌▒Š╣Ø(ji©”)└’Ż¼╬ęų°ųžĮķĮB╦─éĆīŻŅ}Ż║ć╗─ĪóžÜ└¦║═─▄┴”Ą─äāŖZŻ¼╩ął÷║═ūįė╔Ż¼╬─╗»▓Ņ«ÉĄ─ęŌ┴xęį╝░╔ńĢ■Ą─│ąųZĪŻ ĪĪĪĪć╗─ĪóžÜ└¦║═ī”─▄┴”Ą─äāŖZ ĪĪĪĪī”ė┌ć╗─Ą─蹊┐╩Ū╔ŁĄ├ęį½@Ą├ųZžÉĀ¢Įø(j©®ng)Ø·īW¬äĄ─žĢ½Ių«ę╗ĪŻ[3] į┌ĪČžÜ└¦┼cć╗─ĪĘę╗Ģ°ųą(╔Ł,2001)Ż¼╔Ł╠ß│÷┴╦ĻP(gu©Īn)ė┌ć╗─Ą─╦„╚ĪÖÓ(qu©ón)└Ēšō(entitlement theory)ĪŻĖ∙ō■(j©┤)▀@éĆ└ĒšōŻ¼ć╗─▓╗āHāHį┌╝Z╩│╣®Įo┴┐╝▒äĪŽ┬ĮĄĢr▓┼Ģ■│÷¼F(xi©żn)Ż¼╝┤╩╣«ö╝Z╩│╚╦Š∙╣®Įo┴┐ø]ėąūā╗»Ą─Ģr║“Ż¼╚╦┐┌ųąĄ──│ę╗▓┐Ęųę▓Ģ■ę“╩š╚ļĄ─╝▒äĪŽ┬ĮĄ╗“ć°╝ęĄ─ÅŖ┴”Ė╔ŅAČ°╩¦╚źī”╩│╬’Ą─ūŃē“╦„╚ĪÖÓ(qu©ón)Ż¼Å─Č°«a(ch©Żn)╔·ć╗─ĪŻ╔ŁęįČ■╩«╩└╝o╦─╩«─Ļ┤·╦¹╦∙ėHÜvĄ─įŁėĪČ╚├Ž╝ė└Ł░Ņć╗─║═Ų▀╩«─Ļ┤·├Ž╝ė└Łć╗─×ķ└²Ż¼ūC├„╦³éāĄ─«a(ch©Żn)╔·▓╗╩Ūę“×ķ╩│╬’Č╠╚▒įņ│╔Ą─Ż¼Č°╩Ūę“×ķęį│÷┘uä┌äė┴”×ķ╔·Ą─Ąūīė╣ż╚╦Ą─╣ż┘Y┤¾Ę∙Č╚Ž┬ĮĄįņ│╔Ą─ĪŻ ĪĪĪĪć╗─╩Ūī”╚╦Ą──▄┴”Ą─═Ļ╚½äāŖZŻ¼Č°žÜ└¦╩Ūī”╚╦Ą──▄┴”Ą─┬²ąįäāŖZĪŻ╔ŁšJ×ķŻ¼ęį╩š╚ļųĖś╦║Ō┴┐Ą─žÜ└¦╩Ū╣żŠ▀ąįĄ─žÜ└¦Ż¼ī”žÜ└¦Ą─īŹ┘|(zh©¼)ąį║Ō┴┐▒žĒÜ╩╣ė├ĻP(gu©Īn)ė┌─▄┴”Ą─ųĖś╦ĪŻ▀@╩Ūę“×ķŻ¼─▄┴”▓┼╩Ū░l(f©Ī)š╣╦∙ūĘŪ¾Ą──┐ś╦Ż¼Č°╩š╚ļ┼c─▄┴”ų«ķg═∙═∙┤µį┌▌^┤¾Ą─▓Ņ«ÉĪŻįŁę“ėą╦─ĪŻĄ┌ę╗Ż¼╩š╚ļ┼c─▄┴”ų«ķgĄ─ĻP(gu©Īn)ŽĄŻ¼╩▄éĆ╚╦Ą──Ļ²gĪóąįäeĪó╔ńĢ■ĮŪ╔½Īó╦∙╠Ä╔ńģ^(q©▒)ĪóĄž└ĒŁh(hu©ón)Š│ęį╝░Ųõ╦³ŽÓĻP(gu©Īn)Śl╝■Ą─ė░ĒæĪŻĄ┌Č■Ż¼ėąą®─▄┴”Ą─å╩╩¦▓╗āHęŌ╬Čų°ę╗éĆ╚╦╩¦╚ź½@╚Ī╩š╚ļĄ──▄┴”Ż¼Č°ŪęęŌ╬Čų°╦¹īó╩š╚ļ▐D(zhu©Żn)╗»×ķ╣”─▄Ą──▄┴”Ą─å╩╩¦ĪŻ╚ńę╗éĆÜł╝▓╚╦▓╗āH╩¦╚ź┴╦Ųõ▓┐Ęų½@╚Ī╩š╚ļĄ──▄┴”Ż¼Č°Ūę╩¦╚ź┴╦ŽĒ╩▄╩š╚ļĄ─▓┐Ęų─▄┴”ĪŻĄ┌╚²Ż¼╝ę═źā╚(n©©i)▓┐Ą─╩š╚ļĘų┼õ▓╗Š∙Īóė╚Ųõ╩Ūī”┼«ąįĄ─ŲńęĢ╩╣Ą├╚╦Š∙╩š╚ļ▀@ę╗ųĖś╦Ė³╝ė╩¦╚ź┴╦ęŌ┴xĪŻĄ┌╦─Ż¼╩š╚ļĄ─ŽÓī”äāŖZ┐╔─▄ęŌ╬Čų°─▄┴”Ą─Į^ī”äāŖZĪŻī”ė┌ę╗éĆ╔·╗Ņį┌Ė╗ėÓć°╝ęĄ─ĖF╚╦Č°čįŻ¼╦¹┐╔─▄ę“×ķ¤oĘ©▀M╚ļų„┴„╔ńĢ■Č°╩¦╚źģó┼c╔ńĢ■Ą──▄┴”ĪŻ ĪĪĪĪ╔ŁįćłDīóžÜ└¦čąŠ┐ę²ī¦ĄĮĖ³Ė▀Ą─īė┤╬Ż¼▀@▒Ē¼F(xi©żn)į┌╦¹ī”╩¦śI(y©©)Ą─ėæšōųąĪŻ╩¦śI(y©©)╦∙įņ│╔Ą─╩š╚ļōp╩¦į┌░l(f©Ī)▀_ć°╝ę╩Ū▌^╚▌ęūčaāö?sh©┤)─Ż¼Ą½╩ŪŻ¼╩¦śI(y©©)▓╗āHāH╩Ū╩š╚ļĄ─å╩╩¦Ż¼Č°ŪęęŌ╬Čų°Š½╔±š█─źĪó╣żū„¤ßŪķĄ─å╩╩¦Īóūį▒░ęį╝░╝▓▓Ī─╦ų┴╦└═÷┬╩Ą─╔Ž╔²Ą╚Ą╚ĪŻÜWų▐Ą─ĖŻ└¹ć°╝ę╦Ų║§āHāHĻP(gu©Īn)ūó╩¦śI(y©©)Ą─╩š╚ļę╗├µŻ¼Č°║÷ęĢ┴╦Ųõ╦³ĘĮ├µŻ¼ŲõĮY(ji©”)╣¹╩Ū▌^ŲĮĄ╚Ą─╩š╚ļČ°▌^Ė▀Ą─╩¦śI(y©©)┬╩ĪŻ├└ć°ŪĪŪĪŽÓĘ┤Ż¼╦²ī”╩¦śI(y©©)┬╩▓╗─▄╚▌╚╠Ż¼Ą½ģs─▄╚▌╚╠▌^Ė▀Ą─╩š╚ļ▓╗ŲĮĄ╚ĪŻ▀@ĘN╬─╗»╔ŽĄ─▓Ņ«É«a(ch©Żn)╔·┴╦Š▐┤¾Ą─Įø(j©®ng)Ø·║═╔ńĢ■▓Ņ«ÉŻ¼▓óŪęī”Ė„ć°Ą─Ę┤žÜ└¦▓▀┬įŠ▀ėą╔Ņ▀hĄ─ęŌ┴xĪŻ ĪĪĪĪ╩ął÷┼cūįė╔ ĪĪĪĪĮø(j©®ng)▀^╠K¢|Ą─Š▐ūāŻ¼╚╦éāę╗ų┬šJūRĄĮŻ¼╩ął÷╩ŪĮø(j©®ng)Ø·▀\ąą▒ž▓╗┐╔╔┘Ą─╣żŠ▀Ż¼Ą½╩ŪŻ¼ę╗░Ń╚╦ī”╩ął÷Ą─ōĒūoüĒūįī”╩ął÷ĮY(ji©”)╣¹Ą─įuārŻ¼▒╚╚ńŻ¼╩ął÷į┌┼õų├┘Yį┤ĘĮ├µėąą¦┬╩Ż¼ę“┤╦╬ęéāąĶę¬╩ął÷ĪŻ╔Ł═¼ęŌ▀@śėĄ─ė^³cŻ¼Ą½═¼Ģrę▓ųĖ│÷╦³Ą─▓╗ūŃĪŻ╦¹šJ×ķŻ¼╬ęéāąĶę¬╩ął÷Ż¼▓╗āH╩Ūę“×ķ╦³«a(ch©Żn)╔·║├Ą─ĮY(ji©”)╣¹Ż¼Č°Ūę╩Ūę“×ķ╩ął÷×ķ╬ęéā╠ß╣®┴╦▀xō±Ą─ÖCĢ■Ż¼╠žäe╩Ūūįė╔ō±śI(y©©)Ą─ÖCĢ■ĪŻĪ░╝┤╩╣╩Ū─Ū╬╗┘Y▒Šų„┴xĄ─éź┤¾┼·įuš▀┐©Ā¢Īż±R┐╦╦╝ę▓░čŠ═śI(y©©)ūįė╔Ą─«a(ch©Żn)╔·┐┤ū„╩Ūę╗ĒŚŠ▐┤¾Ą─▀M▓ĮĪŻĪ▒(Sen, 1999Ż║Ą┌113Ēō)╔ŁšJ×ķŻ¼äāŖZ╚╦éāĄ─┘I┘uĪóĮ╗ęū║═īżŪ¾ąęĖŻ╔·╗ŅĄ─ūįė╔▒Š╔ĒŠ═╩Ūę╗éĆ╔ńĢ■Ą─Š▐┤¾╩¦öĪĪŻĪ░▀@ę╗╗∙▒ŠšJų¬Ž╚ė┌╬ęéā─▄ē“╗“▓╗─▄ē“ūC├„Ą─╚╬║╬ėąĻP(gu©Īn)╩ął÷į┌╩š╚ļĪóą¦ė├Ą╚Ą╚ĘĮ├µĄ─ūŅĮKĮY(ji©”)╣¹Ą─Č©└ĒĪŻĪ▒(Sen, 1999Ż║Ą┌112Ēō)ėŗäØĮø(j©®ng)Ø·Ą─╩¦öĪ▓╗ų„ę¬▒Ē¼F(xi©żn)į┌Įø(j©®ng)Ø·║═╔·╗Ņ╦«ŲĮ╔ŽĪŻČĒ┴_╦╣─┐Ū░Ą─ŅAŲ┌ē█├³Ž┬ĮĄĄĮų╗ėą╬Õ╩«░╦ÜqŻ¼Ą═ė┌ėĪČ╚║═├Ž╝ė└Łć°Ż╗Ą½╩ŪŻ¼╝┤╩╣╩Ūį┌▀@ĘNŪķørŽ┬Ż¼ČĒ┴_╦╣╚╦├±ę▓ø]ėą▀xō±╗žĄĮ┼f¾wųŲ╚źŻ¼╩«Äū─ĻüĒĄ─▀x┼eĮY(ji©”)╣¹ęčĮø(j©®ng)šf├„┴╦▀@ę╗³cĪŻėŗäØĮø(j©®ng)Ø·Ą─╩¦öĪĖ³ČÓĄž¾w¼F(xi©żn)į┌ī”╚╦├±╗∙▒Šūįė╔Ą─äāŖZ╔ŽĪŻ ĪĪĪĪī”ė┌╩ął÷Ą─ĮY(ji©”)╣¹Ż¼╔ŁšJ×ķ╬ęéā▓╗āH┐╔ęįÅ─ą¦ė├Ą─ĮŪČ╚üĒ┐╝▓ņŻ¼Č°Ūę┐╔ęįĪóę▓æ¬(y©®ng)įōÅ─ūįė╔Ą─ĮŪČ╚üĒ┐╝▓ņĪŻ╩ął÷ī”ūįė╔▀xō±Ą─▒ŻūoęčĮø(j©®ng)×ķ╬ęéā▒ŻūC┴╦▀^│╠Ą─ūįė╔Ż¼Č°╩ął÷Ą─▀\ū„ĮY(ji©”)╣¹īóĮo╬ęéāĦüĒéĆ╚╦─▄┴”ĘĮ├µĄ─ą¦┬╩ĪŻį┌ę╗Ų¬╬─š┬ųą(SenŻ¼1993)Ż¼╔ŁūC├„Ż¼į┌░ó┴_-Ą┬▓╝¶ö?sh©┤)─ę╗░ŃŠ∙║Ō┐“╝▄ā?n©©i)Ż¼╩ął÷┐╔ęį▀_ĄĮéĆ╚╦į┌ūįė╔(─▄┴”)ĘĮ├µĄ─┼┴└█═ąūŅā×(y©Łu)Š│ĮńĪŻ’@╚╗Ż¼«ö╬ęéāī”ūįė╔▀Mąą▀m«ö?sh©┤)─Č©┴xų«║¾Ż¼╔ŁĄ─▀@éĆĮY(ji©”)šō╩Ūø]ėą╩▓├┤ą┬Ųµų«╠ÄĄ─ĪŻ╚╗Č°Ż¼š²╚ń▓╝┴_─Ę└¹(1996)║═Åł╬Õ│Ż(Chueng, 1974)╦∙ųĖ│÷Ą─Ż¼┼┴└█═ąūŅā×(y©Łu)▓╗╩Ūę╗éĆ║Ō┴┐Įø(j©®ng)Ø·ųŲČ╚║├ē─Ą─ųĖś╦Ż¼ę“×ķ╚╬║╬Įø(j©®ng)Ø·ųŲČ╚Ī¬Ī¬┘Y▒Šų„┴xę▓║├Ż¼╔ńĢ■ų„┴xę▓║├Ī¬Ī¬Č╝┐╔ęį▀_ĄĮ┼┴└█═ąūŅā×(y©Łu)ĪŻĖ³Š▀¾wĄžŻ¼╩ął÷Įø(j©®ng)Ø·Ą─┼┴└█═ąūŅā×(y©Łu)Ą─ĮY(ji©”)╣¹╚ĪøQė┌ĘA┘xĘų┼õĄ─Ų╩╝ĀŅæB(t©żi)Ż¼ŲõĮY(ji©”)╣¹┐╔─▄╩Ū║▄▓╗ŲĮĄ╚Ą─ĪŻ╔Łę▓ūóęŌĄĮ▀@éĆå¢Ņ}Ż¼▓óī”┤╦╝ėęį┴╦šō╩÷Ż¼šJ×ķ╬ęéāæ¬(y©®ng)įōī”╩ął÷Ą─ĮY(ji©”)╣¹▀Mąąūą╝ÜĄ─┐╝▓ņĪŻėąęŌ╦╝Ą─╩ŪŻ¼╦¹┼eüå«öĪż╦╣├▄ī”Ė▀└¹┘JĄ─Ę┤ĖąüĒū„×ķ└²ūėĪŻ╦╣├▄ļm╚╗šJ×ķéĆ╚╦Ą─ūį└¹ąą×ķ┐╔ęį▀_ĄĮ╔ńĢ■žöĖ╗Ą─ūŅ┤¾╗»Ż¼Ą½╦¹ę▓ę¬Ū¾ć°╝ęī”ūŅĖ▀└¹┬╩▀MąąŽ▐ųŲŻ¼ę“×ķʱätĄ─įÆ╔ńĢ■┘YĮŠ═Ģ■┴„╚ļō]╗¶š▀ų«╩ųŻ¼«a(ch©Żn)╔·└╦┘MĪŻŠ▀ėąųS┤╠ęŌ╬ČĄ─╩ŪŻ¼╣”└¹ų„┴xĄ─▒Ūūµ▀ģŪ▀×ķ┤╦īŻķTĮo╦╣├▄īæ┴╦ę╗ĘŌķLą┼Ż¼ä±ī¦╦¹ŽÓą┼╩ął÷Ą──▄┴”ĪŻ╔ŁšJ×ķŻ¼╬ęéā«ö╚╗▓╗▒ž┘Ø═¼╦╣├▄Ą─ė^³cŻ¼Ą½æ¬(y©®ng)įōÅ─╦¹─Ū└’īWĄĮę╗ą®¢|╬„Ż¼▒▄├Ō╩ął÷Ęų┼õųą╦∙«a(ch©Żn)╔·Ą─╔ńĢ■┘Yį┤Ą─└╦┘MĪŻę╗éĆŽÓą┼╩ął÷╚▒Ž▌Ą─╚╦╩Ū▓╗Ģ■ī”╩ął÷┼õų├ę▓«a(ch©Żn)╔·¤oą¦┬╩▀@ę╗┼ąöÓ«a(ch©Żn)╔·æčę╔Ą─ĪŻ▒╚╚ńŻ¼į┌┤µį┌═Ō▓┐ąįĄ─ŪķørŽ┬Ż¼éĆ¾w│÷ė┌╦Į└¹Ą─▀xō±Š══∙═∙«a(ch©Żn)╔·¤oą¦Ą─┘Yį┤┼õų├(Łh(hu©ón)Š│╬█╚Š╩Ūę╗éĆ║▄║├Ą─└²ūė)ĪŻ╔ŁĄ─ĖµĮõ╩ŪŻ¼╬ęéāį┌ōĒūo╩ął÷Ą─═¼Ģræ¬(y©®ng)įōī”Ųõ║¾╣¹▀Mąąūą╝ÜĄ─┐╝▓ņĪŻį┌▀@└’Ż¼╣½▒ŖĄ─ģó┼c║═ėæšō╩ŪĘŪ│Żųžę¬Ą─Ż¼ę“×ķ╩ął÷┼õų├Ą─ĮY(ji©”)╣¹ī”▓╗═¼Ą─╚╦«a(ch©Żn)╔·▓╗═¼Ą─ė░ĒæŻ¼š■Ė«Ą─╣½╣▓š■▓▀æ¬(y©®ng)įō┐╝æ]╚½¾w╣½├±Ą─└¹ęµĪŻ ĪĪĪĪ╬─╗»▓Ņ«ÉĄ─ęŌ┴x ĪĪĪĪęį└Ņ╣Ōę½║═±R╣■Ą┘Ā¢×ķ┤·▒ĒĄ─ę╗ą®üåų▐š■ų╬╝ęÅŖš{(di©żo)╬─╗»▓Ņ«ÉĄ─ū„ė├Ż¼▓óīóüåų▐ārųĄū„×ķėąäeė┌╬„ĘĮārųĄĄ─Ą└Ą┬║═╬─╗»¾wŽĄŻ¼ęį┤╦×ķüåų▐▓╗═¼ė┌╬„ĘĮĄ─š■ų╬ųŲČ╚▐qūoĪŻ║═įSČÓ╚╦ę╗śėŻ¼╔Ł▓╗šJ×ķ┤µį┌Įy(t©»ng)ę╗Ą─üåų▐ārųĄŻ¼Ė³ųžę¬Ą─╩ŪŻ¼╦¹įćłDūC├„üåų▐║═╬„ĘĮų«ķgĄ─╬─╗»▓Ņ«É▓óø]ėą╚╦éā╦∙ŽļŽ¾Ą──Ū├┤┤¾ĪŻ╦¹╩ūŽ╚šf├„Ż¼╬„ĘĮ¬Ü╠žšō╩ŪĪ░ė╔Į±╝░╣┼Ī▒Ą─Õeš`šōöÓĪŻ╬„ĘĮ«ö┤·Ą─╗∙▒ŠārųĄė^╩Ūį┌åó├╔▀\äėų«║¾ą╬│╔Ą─Ż¼į┌┤╦ų«Ū░Ż¼ÜWų▐┼cüåų▐į┌╦╝ŽļĘĮ├µĄ─▓Ņäe▓ó▓╗╩Ū─Ū├┤┤¾ĪŻ▒╚╚ńŻ¼╬ęéā┐╔ęįÅ─ā╔ĘĮ├µüĒėæšōéĆ╚╦ūįė╔Ż¼ę╗ĘĮ├µ╩ŪéĆ╚╦ūįė╔Ą─ārųĄŻ¼┴Ēę╗ĘĮ├µ╩ŪéĆ╚╦ūįė╔Ą─ŲĮĄ╚ĪŻüå└’╩┐ČÓĄ┬═Ų│ńŪ░š▀Ż¼Ą½╦¹ī”ŗD┼«║═┼½ļ`Ą─┼┼│Ō╩╣Ą├╦¹ī”║¾š▀ø]ėą╚╬║╬žĢ½IĪŻŽÓĘ┤Ż¼üåų▐Ą─╣┼┤·╦╝Žļ╝ęéāę▓▓╗Č╝┼┼│ŌéĆ╚╦ūįė╔ĪŻĘĮ╠ĮoėĶ║▄┤¾Ą─ūįė╔╦╝┐╝Ą─┐šķgĪŻųąć°ļm╚╗ęį╚Õ╝ę╦╝Žļ×ķų„ī¦Ż¼Ą½Ųõ╦¹│½ī¦ūįė╔╦╝┐╝Ą─╦╝Žļ╝ę╚ńŪfūėĄ╚╚╦Ą─ė░Ēæę▓▓╗┐╔║÷ęĢŻ¼╝┤╩╣╩Ūį┌╚Õ╝ę╦╝ŽļųąŻ¼╬ęéāę▓▓╗ļy░l(f©Ī)¼F(xi©żn)ūįė╔╦╝┐╝Ą─ėÓĄžĪŻ«öūė┬Ęå¢┐ūūė╚ń║╬╦┼ĘŅŠ²ų„ĢrŻ¼┐ūūė╗ž┤šfŻ║Ī░╬Ų█ę▓Ż¼Č°ĘĖų«ĪŻĪ▒[4] Ą─┤_Ż¼╚Õ╝ę╦∙═Ų│ńĄ─ųęŠ²╦╝Žļ▓╗╩Ūė▐ųęŻ¼Č°╩Ūų▒čįŽÓųGĪŻ╔ŁĖµįV╬ęéāŻ¼«ö╬ęéāį┌ū÷¢|╬„ĘĮ╬─╗»▒╚▌^Ą─Ģr║“Ż¼Ī░šµš²Ą─å¢Ņ}▓╗╩Ūüåų▐é„Įy(t©»ng)ųą╩Ūʱ░³║¼▓╗ūįė╔Ą─│╔Ę▌Ż¼Č°╩Ūūįė╔╚ĪŽ“Ą─│╔Ę▌╩Ūʱ▓╗┤µį┌ė┌üåų▐é„Įy(t©»ng)ų«ųąĪŻĪ▒(Sen,1999: Ą┌234Ēō)Š═▓╗ūįė╔Ą─│╔Ę▌Č°čįŻ¼┐ūūėĄ─╦╝Žļ┤¾Ė┼▓╗Ģ■│¼▀^░ž└ŁłDĄ─╦╝ŽļĪŻ ĪĪĪĪ╔Łī”─ŪĘNīó├±ų„ū„×ķĮø(j©®ng)Ø·░l(f©Ī)š╣Ą─č▄╔·╬’Ą─ė^³c▀Mąą┴╦┼·┼ąĪŻ╝┤╩╣╩Ū║▄ĖFĄ─╚╦ę▓Č«Ą├šõŽ¦╦¹Ą─š■ų╬ÖÓ(qu©ón)└¹Ż¼ėĪČ╚Š═╩Ūę╗éĆ║▄║├Ą─└²ūėĪŻįSČÓ蹊┐(░³└©╔Ł▒Š╚╦Ą─蹊┐)Č╝▒Ē├„Ż¼├±ų„┼cĮø(j©®ng)Ø·░l(f©Ī)š╣╦«ŲĮęį╝░Įø(j©®ng)Ø·į÷ķLų«ķg▓╗┤µį┌ę╗Č©Ą─ę“╣¹ĻP(gu©Īn)ŽĄĪŻ├±ų„Ą─ārųĄ▓╗āHāH╩ŪĮø(j©®ng)Ø·Ą─ĪŻ│²┴╦├±ų„Ą─ęÄ(gu©®)ĘČārųĄŻ¼╔ŁÅŖš{(di©żo)├±ų„Ą─╣żŠ▀ārųĄ║═Į©įO(sh©©)ĮŪ╔½ĪŻ├±ų„Ą─╣żŠ▀ārųĄį┌ė┌Ę└ų╣ę“š■Ė«š■▓▀╩¦š`Č°ī¦ų┬Ą─×─ļyąį║¾╣¹ĪŻ╔Łį┌įSČÓł÷║ŽšäĄĮī”ųąć°1959-1962─Ļć╗─Ą─įuārŻ¼šJ×ķą┼ŽóĮ╗┴„▓╗Ģ│╩Ūī¦ų┬─Ūł÷ć╗─Ą─ųžę¬įŁę“ĪŻĄ─┤_Ż¼╠╚╚¶├½Ø╔¢|į┌Å]╔Į╔Ž┬Ā┴╦┼ĒĄ┬æčĄ─┼·įuŻ¼Ūķør┐╔─▄┤¾▓╗ę╗śėĪŻ├±ų„Ą─Į©įO(sh©©)ąįĮŪ╔½į┌ė┌Ż¼╣½ķ_Ą─ėæšōėą└¹ė┌╔ńĢ■Š═╣½╣▓š■▓▀▀_│╔╣▓ūRŻ¼Å─Č°ę▓ėą└¹ė┌╣½╣▓š■▓▀Ą─īŹ╩®ĪŻ╔Ł┼e┴╦ėĪČ╚┐╦└Ł└Ł░ŅĄ─└²ūėüĒšf├„▀@éĆå¢Ņ}ĪŻ▀@éĆ░ŅĄ─╔·ė²┬╩ų╗ėą1.7Ż¼Ą═ė┌ųąć°1.9Ą─╦«ŲĮŻ¼Ą½▀@éĆ░Ņ▀_ĄĮ╚ń┤╦Ą═Ą─╔·ė²┬╩▓╗╩Ū═©▀^ÅŖųŲŻ¼Č°╩Ū═©▀^ą¹é„Į╠ė²▀MČ°ą╬│╔ą┬Ą─╔ńĢ■ārųĄ▀_ĄĮĄ─ĪŻš■Ė«┼c├±▒Ŗų«ķgĄ─Į╗┴„▓╗āHāH╩Ūī”├±▒ŖĄ─ūųžŻ¼Č°Ūę╩Ūī”š■Ė«š■▓▀ą╬│╔║═īŹ╩®Ą─Ä═ų·ĪŻ ĪĪĪĪ╔ńĢ■│ąųZ ĪĪĪĪīóéĆ¾wūįė╔ū„×ķ░l(f©Ī)š╣Ą──┐ś╦ąĶę¬╔ńĢ■Ą─│ąųZĪŻ╚ń╣¹ø]ėą▒žę¬Ą─╣½╣▓įO(sh©©)╩®╝ėęį▌oų·Ż¼ę╗éĆÜł╝▓╚╦╩Ū▓╗┐╔─▄Ž¾š²│Ż╚╦─Ūśė╔·╗ŅĄ─Ż╗ę╗éĆ×lė┌╦└═÷Ą─ć├±╚ń╣¹ø]ėą╩│ŲĘį«ų·Š═ų╗─▄ū▀Ž“╦└═÷Ż╗ę╗éĆ╔Įģ^(q©▒)Ą─╩¦īWā║═»ø]ėą╔ńĢ■Ą─Ä═ų·Š═ė└▀hę▓─Ņ▓╗═ĻąĪīWŻ╗Ą╚Ą╚ĪŻĄ½╩ŪŻ¼ę╗éĆå¢Ņ}ūį╚╗«a(ch©Żn)╔·┴╦Ż║ļyĄ└ę╗éĆ╚╦▓╗æ¬(y©®ng)įō×ķ╦¹ūį╝║žōž¤å߯┐Ą─┤_Ż¼╚ń╣¹ę╗éĆ╚╦═Ļ╚½▒╗╔ńĢ■╦∙ššŅÖŲüĒŻ¼╦¹▒Š╚╦┐╔─▄Ģ■╩¦╚źįSČÓ¢|╬„Ż¼╚ńäō(chu©żng)įņ╝żŪķĪóūįūĄ╚Ą╚ĪŻ╚╗Č°Ż¼ę╗éĆ╩¦╚ź┴╦─▄┴”Ą─╚╦╩Ū¤oĘ©│ąō·ž¤╚╬Ą─ĪŻę╗éĆ╩¦īWā║═»▓╗āHāH╩Ū╩¦╚ź┴╦Š═īWĄ─ÖÓ(qu©ón)└¹Ż¼Č°Ūę╩¦╚ź┴╦▀Mąąėą┘ćė┌ūxīæ─▄┴”Ą─øQ▓▀Ą──▄┴”Ż╗ę╗éĆø]ėąßt(y©®)»¤▒ŻļUĄ─│╔─Ļ╚╦¤oĘ©▒▄├Ō╝▓▓ĪĄ─š█─źŻ¼ę“┤╦ę▓╩¦╚ź┴╦×ķ╦¹ūį╝║║═äe╚╦ū÷╩┬Ą─ūįė╔ĪŻÅ─▀@éĆęŌ┴x╔ŽšfŻ¼Ī░ž¤╚╬ąĶę¬ūįė╔ĪŻ╦∙ęįŻ¼ę¬Ū¾╔ńĢ■ų¦│ųęįöUš╣╚╦éāĄ─ūįė╔Ą─└Ēė╔┐╔ęį┐┤ū„╩Ūę¬Ū¾Č°▓╗╩ŪĘ┤ī”éĆ╚╦ž¤╚╬Ą─└Ēė╔ĪŻĪ▒(Sen,1999:Ą┌284Ēō) ĪĪĪĪ╝╚╚╗╬ęéāę¬Ū¾╔ńĢ■Ą─│ąųZŻ¼ę╗éĆ▓╗┐╔▒▄├ŌĄ─å¢Ņ}┐╔─▄╩Ū╔ńĢ■╚ń║╬Ęų┼õéĆ¾wūįė╔Ż¼«ģŠ╣Ż¼ę╗éĆ╚╦ūįė╔Ą─į÷╝ėŠ═┐╔─▄ęŌ╬Čų°┴Ēę╗éĆ╚╦ūįė╔Ą─£p╔┘ĪŻę“┤╦Ż¼ę╗éĆĻP(gu©Īn)ė┌╔ńĢ■╣½š²Ą─└Ēšō╩Ū▒žę¬Ą─ĪŻĻP(gu©Īn)ė┌▀@ę╗³cŻ¼╔Ł┐éĮY(ji©”)┴╦╦─³cęŌęŖĪŻĄ┌ę╗Ż¼éĆ¾wūįė╔╩Ū║Ō┴┐╔ńĢ■│╔Š═Ą─ų„ę¬ųĖś╦Ż¼▀@╩Ū╦¹į┌▒ŠĢ°╦∙▒Ē▀_Ą─ų„ę¬ė^³cĪŻĄ┌Č■Ż¼éĆ¾wūįė╔ė^³c╩ŪŠ▀ėąÅŚąįĄ─Ż¼Č°Ūęėąę╗ą®─┐ś╦ų«ķg╩Ūėąø_═╗Ą─ĪŻ▒╚╚ńŻ¼Ė³ŲĮĄ╚Ą─ūįė╔║═╠ßĖ▀╦∙ėą╚╦Ą─ūįė╔ų«ķgŠ═┐╔─▄╩Ū▓╗ŽÓ╚▌Ą─ĪŻĄ½╩ŪŻ¼▓╗═¼ė┌Ųõ╦¹└Ēšō╝ęŻ¼╔Ł▓ó▓╗Žļ×ķ┤╦╠ß╣®ę╗éĆå╬ę╗Ą─įu┼ąįŁätŻ¼▒╚╚ńŽ¾╣”└¹ų„┴x─ŪśėūŅ┤¾╗»╦∙ėą╔ńĢ■│╔åTĄ─ą¦ė├ĪŻĄ┌╚²Ż¼ĻP(gu©Īn)ė┌ę╗éĆ╔ńĢ■Ą─╣½š²Ą─ś╦£╩ąĶę¬╚½╔ńĢ■ĘČć·ā╚(n©©i)Ą─╣½ķ_ėæšōŻ¼ę“┤╦Ż¼▒ŻūC╣½ķ_ėæšōĄ─╗∙▒Šš■ų╬ÖÓ(qu©ón)└¹š╝ō■(j©┤)ų°▓╗┐╔╠µ┤·Ą─Ąž╬╗ĪŻūŅ║¾Ż¼ęį╗∙▒Šūįė╔×ķ─┐ś╦Ą─░l(f©Ī)š╣ė^▓╗┐╔▒▄├ŌĄž░čūóęŌ┴”╝»ųąį┌╚╦Ą──▄äėĄ─ę╗├µŻ¼Č°▓╗╩ŪāHāH░č╚╦┐┤ū„╩Ū░l(f©Ī)š╣Ą─│╔╣¹Ą─▒╗äėĮė╩▄š▀ĪŻ╔Łį┌ĪČéÉ└ĒīW┼cĮø(j©®ng)Ø·īWĪĘ(╔Ł,2000)ę╗Ģ°ųą╠ß│÷╚╦Ą─Ī░─▄äėĪ▒(agency)Ą─ę╗├µŻ¼▓óį┌▒ŠĢ°ųą└^└m(x©┤)╩╣ė├▀@éĆį~ĪŻ╔Ł╩Ūį┌agency▀@éĆį~Ą─╣┼┴x╔Ž╩╣ė├╦³Ą─Ż¼ęŌųĖ╚╦╩Ūę╗éĆ─▄ē“╦╝┐╝║═ģó┼cĄ─ų„¾wŻ¼Č°▓╗╩Ū▒╗äėĮė╩šĄ─┐═¾wĪŻ░l(f©Ī)š╣Ą─ūįė╔ė^ÅŖš{(di©żo)ī”╚╦Ą──▄┴”Ą─┼ÓB(y©Żng)Ż¼ęŌ┴xį┌ė┌╠ßĖ▀╚╦▀Mąąų„äėģó┼cĄ──▄äėąįĪŻ╔Łį┌▀@└’╠ßąč╬ęéāŻ¼▒M╣▄į÷╝ėéĆ¾wūįė╔╩Ū╔ńĢ■ž¤╚╬Ą─ę╗▓┐ĘųŻ¼Ą½▀@▓ó▓╗ęŌ╬Čų°ć°╝ę┐╔ęįīóī”ę╗▓┐Ęų╚╦Ą─Ä═ų·┐┤ū„╩Ūī”╦¹éāĄ─╩®╔߯¼╗“š▀Ė³ų▒ĮėĄžīó╦¹éā┐┤ū„╩Ū¤oąą×ķ─▄┴”Ą─▒╗äėĮė╩▄š▀Ż¼×ķ╦¹éā░▓┼┼╦¹éāĄ─╔·╗Ņ▀xō±ĪŻĪ░Š▄Į^ę╗éĆ║óūėĮė╩▄╗∙▒ŠĮ╠ė²╗“ę╗éĆ▓Ī╚╦Įė╩▄╗∙▒Šßt(y©®)»¤Ą─ÖCĢ■╩Ū╔ńĢ■ž¤╚╬Ą─╩¦š`Ż¼Ą½╩ŪŻ¼╚ń║╬└¹ė├Į╠ė²║═ĮĪ┐Ąätų╗─▄╩Ūė╔éĆ╚╦ūį╝║üĒøQČ©ĪŻĪ▒(Sen,1999:Ą┌288Ēō)’@╚╗Ż¼╔Łį┌▀@└’╝╚▓╗┘Ø│╔ųZ²R┐╦Ą─▒Ż╩žų„┴xĄ─ūŅąĪć°╝ęė^³cŻ¼ę▓▓╗┘Ø│╔äāŖZéĆ╚╦▀xō±ūįė╔Ą─é„Įy(t©»ng)╔ńĢ■ų„┴xŻ¼▀@╩╣Ą├╦¹į┘┤╬║═ų„ÅłĄ┌╚²ŚlĄ└┬ĘĄ─ą┬╔ńĢ■├±ų„ų„┴xš▀(╚ń╝¬ĄŪ╦╣)šŠį┌┴╦ę╗ŲĪŻ ĪĪĪĪ╚²Īó Äū³cįušō ĪĪĪĪ╔Łį┌▒ŠĢ°ųąĄ─žĢ½I▓╗į┌ė┌╦¹ī”¼F(xi©żn)┤µĄ─░l(f©Ī)š╣ė^╦∙ū÷Ą─┼·┼ąŻ¼ę“×ķ▀@ĘN┼·┼ąį┌Įø(j©®ng)Ø·īWų«═Ō▒╚▒╚Įį╩ŪĪŻ╦¹Ą─žĢ½Iį┌ė┌į┌ęį─▄┴”▀@ę╗Ė┼─Ņ×ķ║╦ą─Ą─ūįė╔ė^ų«Ž┬īó░l(f©Ī)š╣Ą─▓╗═¼é╚(c©©)├µĪ¬Ī¬Įø(j©®ng)Ø·Ą─Īó╔ńĢ■Ą─ęį╝░š■ų╬Ą─Ī¬Ī¬Įy(t©»ng)ę╗į┌ę╗éĆ═Ļš¹Ą─└Ēšō┐“╝▄ų«ųąĪŻ«ö░l(f©Ī)š╣Ą──┐ś╦▒╗┤_Č©×ķī”╚╦Ą─ūįė╔Ą─öUš╣Ą─Ģr║“Ż¼╬ęéāŠ═▓╗┐╔─▄ų╗ĻP(gu©Īn)ūóĮø(j©®ng)Ø·į÷ķLŻ¼Č°▒žĒÜ═¼ĢrĻP(gu©Īn)ūó╔ńĢ■║═š■ų╬Ą─▀M▓ĮĪŻ▀@╩Ū╔Łį┌▒ŠĢ°Įo╬ęéāūŅ┤¾Ą─åó╩ŠĪŻ ĪĪĪĪĄ½╩ŪŻ¼╔ŁĄ─└Ēšōę▓▓╗╩Ūø]ėą╝ä┬®Ą─ĪŻŽ┬├µ╬ęīóÅ─╦─éĆĘĮ├µüĒī”┤╦▀MąąėæšōĪŻ╦³éā╩ŪÅV┴xūįė╔┼c¬M┴xūįė╔å¢Ņ}Īó─▄┴”Ą─▒╚▌^å¢Ņ}Īóūįė╔Ą─īė┤╬å¢Ņ}ęį╝░ūįė╔Ęų┼õĄ─╣½š²å¢Ņ}ĪŻ ĪĪĪĪ¬M┴xūįė╔┼cÅV┴xūįė╔ ĪĪĪĪūįė╔╩Ūę╗éĆ╚▌ęūę²ŲŲń┴xĄ─Ė┼─ŅĪŻ¬M┴xūįė╔╩Ū║══Ōį┌Ą─Ž▐ųŲĪó╠žäe╩Ū╚╦╔ĒŽ▐ųŲŽÓī”┴óĄ─ĪŻį┌▀@└’Ż¼Ī░═Ōį┌Ą─Ī▒▀@ę╗Ž▐Č©į~╩Ū║▄ųžę¬Ą─Ż¼╦³┼┼│²┴╦ė╔ė┌éĆ╚╦ūį╔ĒĄ─įŁę“╦∙«a(ch©Żn)╔·Ą─Ī░▓╗ūįė╔Ī▒Ą─ĖąėXĪŻ▒╚╚ńŻ¼ę╗╬╗╩¦æ┘Ą─ŪÓ─ĻĢ■ĖąĄĮĘŪ│ŻĄ├▓╗ūįė╔Ż¼ę“×ķ╦¹¤oĘ©Ą├ĄĮ╦¹ą──┐ųąĄ─┼«║óĄ─ŪÓ▓AŻ╗═¼śėŻ¼ę╗╬╗Š½╔±╩¦│Żš▀į┌╦¹╚╦┐┤üĒę▓╩Ū▓╗ūįė╔Ą─Ż¼ę“×ķ╦¹Ą─╦╝┐╝─▄┴”ę“╝▓▓ĪĄ─įŁę“Č°╩▄ĄĮŽ▐ųŲĪŻĄ½╩ŪŻ¼ęį¬M┴xĄ─ūįė╔ė^ų«Ż¼▀@śėĄ─▓╗ūįė╔š▀īŹļH╔Ž╩Ūūįė╔Ą─Ż¼ę“×ķ╦¹éāø]ėą╩▄ĄĮ═Ōį┌Ą─Ž▐ųŲĪŻĄ½╩ŪŻ¼ÅŖš{(di©żo)═Ōį┌Ą─Ž▐ųŲ¤oąĶ╗žĄĮ╣■ę«┐╦Ą─▒╗äėūįė╔ė^Ż¼Č°╩Ū┐╔ęį░³└©ūįė╔Ą─▒╗äė║═ų„äėā╔éĆĘĮ├µĪŻĮy(t©»ng)ę╗▀@ā╔ĘĮ├µĄ─║╦ą─Ė┼─Ņ╩ŪéĆ╚╦Ą─▀xō±╝»Ż¼╝┤┐╔╣®éĆ╚╦▀xō±Ą─ÖÓ(qu©ón)└¹Īó╬’ŲĘ╝░ŲõĮM║ŽĄ─ČÓśėąįĪŻ░┤šš▒╗äėūįė╔Ą─▀ē▌ŗŻ¼ų╗ę¬ę╗éĆ╚╦Ą─▀xō±╝»ø]ėą▒╗╦¹╚╦╦∙Ž▐ųŲŻ¼ätę╗éĆ╚╦Š═╩Ūūįė╔Ą─Ż╗«ö╬ęéā╝ė╔Žų„äėūįė╔Ą─Ģr║“Ż¼╝┤╩╣╩Ūø]ėą╦¹╚╦Ą─Ž▐ųŲ╬ęéāę▓┐╔ęįšä?w©┤)ōę╗éĆ╚╦ūįė╔Ą─ČÓ╣čŻ║ę╗éĆōĒėąĖ³ČÓÖÓ(qu©ón)└¹║═▀xō±ÖCĢ■Ą─╚╦▒╚┴Ēę╗éĆōĒėą▌^╔┘ÖÓ(qu©ón)└¹║═▀xō±ÖCĢ■Ą─╚╦ōĒėąĖ³ČÓĄ─ūįė╔ĪŻ ĪĪĪĪ╔Łø]ėą▓╔╝{╔Ž╩÷¬M┴xūįė╔Ą─Č©┴xŻ¼Č°╩Ū▓╔╝{┴╦ę╗éĆÅV┴xūįė╔Ą─Č©┴xĪŻį┌╦¹┐┤üĒŻ¼ūįė╔▓╗āHę“éĆ╚╦▀xō±╝»Ą─┤¾ąĪČ°«ÉŻ¼Č°Ūęę“éĆ╚╦īó▀xō±▐D(zhu©Żn)ōQ×ķėąęŌ┴xĄ─╣”─▄Ą──▄┴”Č°«ÉĪŻ▒╚╚ńŻ¼ę╗éĆ╚╦Ą─ūįė╔▓╗āH╚ĪøQė┌╦¹╦∙ōĒėąĄ─╩š╚ļĄ─öĄ(sh©┤)┴┐Ż¼Č°Ūę╚ĪøQė┌╦¹īó╩š╚ļ▐D(zhu©Żn)╗»×ķėąęŌ┴xĄ──┐Ą─Ī¬Ī¬╚ńĮė╩▄Į╠ė²Ī¬Ī¬Ą──▄┴”ĪŻ╚╗Č°Ż¼▀@śėę╗éĆÅV┴xĄ─ūįė╔Č©┴xĢ■«a(ch©Żn)╔·ę╗Č©Ą─å¢Ņ}ĪŻ▒╚╚ńŻ¼į┌═¼Ą╚Śl╝■Ž┬Ī¬Ī¬═¼śėĄ─īWąŻĪó═¼śėĄ─└ŽÄ¤Īó═¼śėĄ─╝ę═ź▒│Š░Ż¼ę╗éĆ║óūė┐╔─▄Š═╩Ū▒╚┴Ēę╗éĆ║óūėīW┴Ģ│╔┐ā▓ŅŻ¼Å─Č°║¾š▀Š═─▄╔Ž║├┤¾īWČ°Ū░š▀Š═╩Ū╔Ž▓╗┴╦┤¾īWŻ¼ę“×ķ╚╦Ą─ųŪ┴”Š▀ėą╠ņ╚╗Ą─▓Ņ«ÉąįĪŻĄ½╩ŪŻ¼╬ęéā─▄ę“┤╦šfŪ░š▀▒╚║¾š▀Ė³▓╗ūįė╔å߯┐░┤šš╔ŁĄ─ūįė╔ė^Ż¼╬ęéā▒žĒÜĮo▀@éĆå¢Ņ}ę╗éĆ┐ŽČ©Ą─╗ž┤ĪŻ╚╗Č°Ż¼▀@śėĄ─╗ž┤ėąā╔éĆå¢Ņ}ĪŻ╩ūŽ╚Ż¼╦³▓╗Ę¹║Ž╬ęéā═©│Żī”ūįė╔Ą─šJūRŻ¼ę“┤╦╚▌ęūę²ŲšZ┴xĄ─╗ņüyĪŻŲõ┤╬Ż¼Ė³ųžę¬Ą─╩ŪŻ¼│ąšJŪ░ę╗éĆ║óūėĄ─▓╗ūįė╔▓ó▓╗─▄×ķ╣½╣▓š■▓▀╠ß╣®ę╗éĆ┴╝║├Ą─ųĖ─ŽĪŻ╚ń╣¹╬ęéāę¬╠ßĖ▀▀@éĆ║óūėĄ─ūįė╔Ą─╦«ŲĮŻ¼╬ęéāŠ═▒žĒÜĮ©Ė³ČÓĄ─┤¾īWĪŻĄ½╩ŪŻ¼▀@śėĄ─ę╗ĘNš■▓▀╚ĪŽ“?q©▒)ŹļH╔Ž╩Ūį┌─©Üó╔ńĢ■Ęų╣ż╦∙ĦüĒĄ─║├╠ÄŻ║ī”ė┌▀@éĆ▌^▒┐Ą─║óūėüĒšfŻ¼ī”╦¹║═ī”╔ńĢ■üĒšfČ╝ūŅ║├Ą─▐kĘ©┐╔─▄╩Ūūī╦¹Įė╩▄ųąĄ╚╝╝ąg(sh©┤)Į╠ė²Ż¼│╔×ķę╗éĆ╩ņŠÜ╣ż╚╦Č°▓╗╩Ū╝╝ąg(sh©┤)åT╗“╣ż│╠ĤĪŻ ĪĪĪĪę“┤╦Ż¼ÅV┴xĄ─ūįė╔ė^į┌šZ┴x║═š■▓▀ā╔éĆīė├µČ╝┤µį┌å¢Ņ}ĪŻ×ķ┴╦▒▄├Ō▀@ą®å¢Ņ}Ż¼ī”ūįė╔Ą─Č©┴x▒žĒÜų╣ė┌éĆ╚╦Ą─ūį╬ęĖąėX╗“ąą×ķŻ¼Č°ų╗ĻP(gu©Īn)ūóī”éĆ╚╦Ą─═Ōį┌Ž▐ųŲĪŻ═¼ĢrŻ¼ī”─│ą®ūį╚╗╦∙╩®ė┌éĆ╚╦Ą─Ž▐ųŲę▓æ¬(y©®ng)┼┼│²į┌╬ęéāĄ─ėæšōų«═ŌŻ║╬ęéā¤oĘ©ĄĮ╠½┐š╚ź┬├ąąŻ¼┐╔╩ŪŻ¼│ąšJ▀@śėĄ─▓╗ūįė╔ī”╬ęéāį┌ĄžŪ“╔ŽĄ─╔·╗Ņėą╩▓├┤ęŌ┴x─žŻ┐╔Łīó─▄┴”ų├ė┌ūįė╔Ą─ųąą─╬╗ų├Ą─ū÷Ę©ŪĪŪĪ╩Ūø_ŲŲ┴╦Ą┌ę╗éĆŽ▐ųŲŻ¼▀@śėū÷▓╗āHę²Ų┴╦ī”▀@éĆĖ┼─Ņ▒Š╔ĒĄ─šJūR╗ņüyŻ¼Č°Ūęę▓ī”╦¹Ą─╣½š²└Ēšō«a(ch©Żn)╔·┴╦▓╗└¹ė░ĒæĪŻ ĪĪĪĪ─▄┴”Ą─▒╚▌^å¢Ņ} ĪĪĪĪ╚ńŪ░╬─╦∙ųĖ│÷Ą─Ż¼╔Łų«╦∙ęį╠ß│÷─▄┴”▀@éĆĖ┼─ŅŻ¼╩Ūę“×ķ╦¹▓╗ØMė┌ęįą¦ė├×ķ╗∙ĄA(ch©│)Ą─╣”└¹ų„┴x║═ęį╗∙▒Š╬’ŲĘ×ķ╗∙ĄA(ch©│)Ą─┴_Ā¢╦╣ų„┴xĪŻ─▄┴”▀@éĆĖ┼─Ņļm╚╗┐╦Ę■┴╦╣”└¹ų„┴x║═┴_Ā¢╦╣ų„┴x¬M░»Ą─ą┼Žó╗∙Ą─å¢Ņ}Ż¼Ą½╦³ø]ėą▒▄├Ō┴_Ā¢╦╣Ą─╗∙▒Š╬’ŲĘĄ─╝ė┐éå¢Ņ}Ż¼ę▓ø]ėą▒▄├Ō╣”└¹ų„┴xĄ─ą¦ė├▒╚▌^å¢Ņ}ĪŻš²╚ń╔Łūį╝║╦∙ųĖ│÷Ą─Ż¼─▄┴”ųĖĄ─╩Ūę╗╩°─▄┴”Ż¼ę“┤╦▒ž╚╗┤µį┌╚ń║╬Įo▓╗═¼─▄┴”Ęų┼õÖÓ(qu©ón)ųžęį«a(ch©Żn)╔·ę╗éĆå╬ę╗Ą─įu┼ąųĖś╦Ą─å¢Ņ}ĪŻ«ö╚╗Ż¼▒╚ŲéĆ╚╦ķgĄ─▒╚▌^üĒŻ¼╝ė┐éå¢Ņ}╩Ūę╗éĆąĪå¢Ņ}ĪŻė╔ė┌─▄┴”▓╗āH░³└©éĆ╚╦Ą─▀xō±╝»Ż¼Č°Ūę░³└©éĆ╚╦īó▀xō±▐D(zhu©Żn)╗»×ķ─┐Ą─Ą──▄┴”Ż¼─▄┴”ų«ķgĄ─▒╚▌^Š═Ģ■│÷¼F(xi©żn)å¢Ņ}ĪŻį┌┴_Ā¢╦╣Ą─╗∙▒Š╬’ŲĘ─Ū└’Ż¼╔ńĢ■┐╔ęį─«ęĢéĆ╚╦└¹ė├▀@ą®╬’ŲĘĄ──▄┴”Ż¼╔Ł╠ß│÷─▄┴”▀@éĆĖ┼─Ņ╩ŪŽļŽ¹│²▀@ĘN─«ęĢĪŻĄ½╩ŪŻ¼▐D(zhu©Żn)╗»║═└¹ė├╬’ŲĘĄ──▄┴”ę“╚╦Č°«ÉŻ¼╔ńĢ■Š┐Š╣æ¬(y©®ng)įōęįšlĄ──▄┴”×ķįu┼ąś╦£╩─žŻ┐į┌▀@└’Ż¼╔ŁĄ──▄┴”▓ó▓╗▒╚╣”└¹ų„┴xĄ─ą¦ė├Ė³╚▌ęū╠Ä└ĒĪŻ╩┬īŹ╔ŽŻ¼╔Łī”╣”└¹ų„┴x▀^šŁĄ─ą┼Žó╗∙Ą─┼·įu▒Š╔ĒŠ═ėą▀^╗ų«╠ÄĪŻį┌¼F(xi©żn)┤·Įø(j©®ng)Ø·īWųąŻ¼ą¦ė├▓ó▓╗╠žųĖ╚╦Ą─Ėą╣┘ėõÉéŻ¼Č°╩ŪéĆ╚╦ī”ę╗ĮM╬’ŲĘĄ─ėąė├ąįĄ─╝ė┐é┼┼ą“ĪŻ╣”└¹ų„┴xĄ─ą┼Žó╗∙ęčĮø(j©®ng)¾w¼F(xi©żn)į┌╬’ŲĘĪ¬Ī¬╝╚┐╔ęį╩Ū╬’└Ē┤µį┌Ż¼ę▓┐╔ęį╩ŪĘŪ╬’└Ē┤µį┌Ż¼╚ńÖÓ(qu©ón)└¹Ī¬Ī¬Ą─ČÓśėąį╔Ž┴╦ĪŻ╬ęéā▓╗─▄ę“×ķ╣”└¹ų„┴x╩╣ė├┴╦éĆ╚╦ī”▀@ą®╬’ŲĘĄ─╝ė┐é┼┼ą“Ȱʱȩ╦³ī”ČÓśėąįĄ─┐ŽČ©ĪŻę“┤╦Ż¼╔Łęį─▄┴”┤·╠µą¦ė├║═╗∙▒Š╬’ŲĘĄ─┼¼┴”▓óø]ėą×ķ╬ęéāĮŌøQ╣½š²å¢Ņ}╠ß╣®īŹ┘|(zh©¼)ąįĄ─▀M▓ĮĪŻ ĪĪĪĪĄ½╩ŪŻ¼▀@▓╗Ą╚ė┌šf─▄┴”▀@éĆĖ┼─Ņ╩Ūø]ėąęŌ┴xĄ─ĪŻū„×ķ╣½╣▓║═░l(f©Ī)š╣š■▓▀Ą─ę╗éĆųĖī¦╦╝ŽļŻ¼─▄┴”▀@éĆĖ┼─ŅĄ─ęŌ┴x╩Ū’@ų°Ą─ĪŻÅ─░l(f©Ī)š╣Ą─ĮŪČ╚üĒ┐┤Ż¼╦³īóĮø(j©®ng)Ø·Īó╔ńĢ■║═š■ų╬Ą─▀M▓Į╝{╚ļĄĮę╗éĆĮy(t©»ng)ę╗Ą─┐“╝▄ųąŻ¼▀@╩Ū▒Š╬─ČÓ┤╬╠ߥĮĄ─ĪŻÅ─╣½╣▓š■▓▀Ą─ĮŪČ╚üĒ┐┤Ż¼╦³īóš■Ė«Ą─ūóęŌ┴”ę²ī¦ĄĮī”╣½├±─▄┴”Ą─┼ÓB(y©Żng)╔ŽüĒĪŻ▒╚╚ńŻ¼Ę÷žÜĄ──┐ś╦▓╗æ¬(y©®ng)įō╩ŪāHāH╠ßĖ▀žÜ└¦╚╦┐┌Ą─╩š╚ļŻ¼Č°╩Ūę¬╠ßĖ▀╦¹éāäō(chu©żng)įņ╩š╚ļĄ──▄┴”Ż¼──┼┬▀@śėū÷┐╔─▄Ģ║Ģr£pŠÅžÜ└¦╚╦┐┌╩š╚ļĄ─╠ßĖ▀ĪŻÅ─▀@éĆĮŪČ╚üĒ┐┤Ż¼╠ßĖ▀žÜ└¦Ąžģ^(q©▒)Ą─Į╠ė²╦«ŲĮ▀h▌^╠ßĖ▀─Ū└’Ą─Š═śI(y©©)╦«ŲĮėąą¦ĪŻį┘▒╚╚ńŻ¼ī”ė┌Ž┬ŹÅ╣ż╚╦Ą─Š╚ų·▓╗╩Ūī”╦¹éāĄ─╩®╔߯¼Č°╩Ū▒Ż┤µ╦¹éāęį╝░╦¹éāĄ─ūė┼«Ą─╔·«a(ch©Żn)─▄┴”ĪŻę“┤╦Ż¼╔ŁĄ──▄┴”Ė┼─Ņī”«öĮ±ųąć°Š▀ėą╔Ņ┐╠Ą─¼F(xi©żn)īŹęŌ┴xĪŻ ĪĪĪĪūįė╔Ą─īė┤╬ ĪĪĪĪ╔Łī”ųZ²R┐╦Ą─Į^ī”ÖÓ(qu©ón)└¹║═┴_Ā¢╦╣Ą─ÖÓ(qu©ón)└¹ā×(y©Łu)Ž╚ė^Č╝▀Mąą┴╦┼·┼ąŻ¼į┌╦¹ūį╝║Ą──▄┴”┐“╝▄ā╚(n©©i)Ż¼╦∙ėąūįė╔ĒŚČ╝Š▀ėą═¼Ą╚Ą─Ąž╬╗ĪŻĄ½╩ŪŻ¼į┌ąą╬─ųąŻ¼╔ŁĢrČ°▓╗Ą├▓╗│ąšJŻ¼ę╗ą®ūįė╔ĒŚĄ─Ąž╬╗ā×(y©Łu)Ž╚ė┌Ųõ╦³ūįė╔ĒŚĪŻ▒╚╚ńŻ¼╦¹ÅŖš{(di©żo)╣½ķ_ėæšōį┌ą╬│╔╣½š²Ą─╔ńĢ■įu┼ąś╦£╩ĘĮ├µĄ─ųžę¬ąįŻ¼ę“┤╦īó╣½├±Ą─├±ų„ÖÓ(qu©ón)└¹ö[į┌┴╦ā×(y©Łu)Ž╚Ąž╬╗ĪŻ╩┬īŹ╔ŽŻ¼īó╦∙ėąūįė╔ĒŚö[į┌═¼Ą╚Ąž╬╗¤ošō╩Ūį┌└Ēšō╔Ž▀Ć╩Ūį┌īŹ█`ųąČ╝Š▀ėąā╚(n©©i)į┌Ą─├¼Č▄ĪŻ ĪĪĪĪŠ═└ĒšōČ°čįŻ¼ę╗ą®ūįė╔ĒŚ╩Ūęį┴Ēę╗ą®ūįė╔ĒŚĄ─īŹ¼F(xi©żn)×ķŪ░╠ߥ─ĪŻ▒╚╚ńŻ¼ę╗éĆ╚╦─▄ē“ūįė╔Ąž▀xō±╔·╗ŅĘĮ╩Įį┌║▄┤¾│╠Č╚╔Ž╩ŪĮ©┴óį┌ę┬╩│¤oænĄ─Ū░╠ßų«╔ŽĄ─Ż¼ī”ė┌ę╗éƤoĘ©ŠS│ų╝ę═ź╗∙▒Š╔·╗ŅĄ─ę╗╝ęų«ų„Č°čįŻ¼│¼║§║²┐┌Ą─▀xō±▓╗▀^╩Ūē¶ŽļČ°ęčĪŻŲõ╦³└²ūėĖ®╩░Įį╩ŪŻ¼ę╗éĆūŅ┘NĮ³ųąć°¼F(xi©żn)īŹĄ─└²ūė╩ŪŻ¼▀^╚źČ■╩«─ĻüĒ╚╦├±╔·╗Ņ╦«ŲĮĄ─╠ßĖ▀╩Ūęį╦¹éā▀xō±┐šķgĄ─öU┤¾×ķŪ░╠ߥ─ĪŻ▀@╩Ū╬ęéā┐╔ęįÅ─Č■╩«─ĻĖ─Ė’Üv│╠ųąĄ├ĄĮĄ─╔┘öĄ(sh©┤)ÄūéĆ╣▓ūRų«ę╗ĪŻę“┤╦Ż¼īó╦∙ėąūįė╔ĒŚö[į┌═¼Ą╚Ąž╬╗Ģ■╩╣╬ęéā╩¦╚ź┐éĮY(ji©”)║═╠Įėæę“╣¹ĻP(gu©Īn)ŽĄĄ──▄┴”Ż╗═¼ĢrŻ¼▀@śėū÷ę▓č┌╔w┴╦▓╗═¼ūįė╔ĒŚų«ķgĄ─ø_═╗å¢Ņ}ĪŻ╔Ł«ö╚╗ę▓ūóęŌĄĮūįė╔ĒŚų«ķgĄ─ø_═╗å¢Ņ}Ż¼Ą½ø]ėąī”┤╦▀Mąą╔Ņ╚ļĄ─ėæšōĪŻ▀@éĆå¢Ņ}╔µ╝░ĄĮ╚ń║╬įuārę╗éĆ╔ńĢ■Ą─╣½š²│╠Č╚Ą─å¢Ņ}Ż¼╬ęį┌Ž┬ę╗ąĪ╣Ø(ji©”)īóīŻķTėĶęįėæšōĪŻį┌┤╦ŽļųĖ│÷Ą─╩ŪŻ¼ī”ūįė╔ĒŚų«ķgø_═╗Ą─║÷ęĢŽ„╚§┴╦╔ŁĄ─└Ēšōī”ė┌īŹ█`Ą─ųĖī¦ęŌ┴xŻ¼ę“×ķ╦³ø]ėąĖµįV╬ęéā?n©©i)ń║╬į┌▓╗═¼ūįė╔ĒŚų«ķg▀Mąą╚Ī╔ßĪŻŽÓĘ┤Ż¼īó╦∙ėąūįė╔ĒŚö[į┌═¼Ą╚Ąž╬╗śO┐╔─▄▒╗äeėąė├ą─Ą─Įy(t©»ng)ų╬š▀╦∙└¹ė├Ż¼Å─Č°ī¦ų┬╣┼Ąõūįė╔ų„┴xš▀╚ń╣■ę«┐╦╦∙ō·ą─Ą─┼½ę█╝┘ūĘŪ¾ūįė╔ų«├¹Č°ĄŪ╠├╚ļ╩ęĄ─Š░Ž¾ĪŻė╔ė┌Ė„ūįė╔ĒŚ▓ó¤oŽ╚║¾ų«ĘųŻ¼Ą½╦³éāų«ķgėų▒žĒÜėą╦∙╚Ī╔߯¼Įy(t©»ng)ų╬š▀Š═┐╔ęį╝┘ūĘŪ¾─│ą®éĆ╚╦ūįė╔Ī¬Ī¬╚ń▀^╔ŽĖ╗ūŃĄ─╔·╗ŅĪ¬Ī¬ų«├¹Č°ē║ųŲéĆ╚╦Ą─Ųõ╦³ūįė╔ĪŻ╦╣┤¾┴ųĮy(t©»ng)ų╬ų«Ž┬Ą─╠K┬ō(li©ón)▓╗Š═╩Ūę╗éĆ└²ūėå߯┐Š═▀B╚š▒Š▄Ŗć°ų„┴xš▀į┌┤¾╦┴╚ļŪųüåų▐Ė„ć°Ą─Ģr║“ę▓▓╗═³┬ĢĘQūį╝║╩Ūį┌░čüåų▐╚╦├±Å─╬„ĘĮ┴ąÅŖĄ─┼½ę█ų«Ž┬ĮŌĘ┼│÷üĒĪŻ ĪĪĪĪ×ķ┴╦▒▄├Ōęį╔ŽļyŅ}Ż¼╬ęéāėą▒žę¬Š═ć°╝ęī”éĆ╚╦ūįė╔Ą─▒Żūoģ^(q©▒)Ęųā╔ĘNūįė╔Ż║┐╔▒ŻūoĄ─ūįė╔║═┐╔Į╗ōQĄ─ūįė╔ĪŻ┐╔▒ŻūoĄ─ūįė╔╩Ūę╗éĆ╚╦ū„×ķ╔ńĢ■ę╗åT╦∙▒žĒÜŠ▀ėąĄ─ūįė╔Ż¼╦³Ą─īŹ╩®▓╗Ģ■ė░ĒæŲõ╦¹╚╦Ą─ūįė╔Ż¼═¼ĢrŻ¼ę╗éĆ╚╦ōĒėąĄ─ūįė╔▒žĒÜę▓╩Ū╦¹╚╦┐╔ęį═¼ĢrōĒėąĄ─Ż¼ę“┤╦╦³į┌╚╦╚║ųąĄ─Ęų┼õ▒žĒÜ╩ŪŲĮĄ╚Ą─ĪŻī”ė┌▀@ĘNūįė╔Ż¼ć°╝ę▒žĒÜ╝ėęį▒ŻūoŻ¼ę“×ķʱätĄ─įÆŠ═Ģ■«a(ch©Żn)╔·╚╦┼c╚╦ų«ķg┼c╔·ŠŃüĒĄ─▓╗ŲĮĄ╚ĪŻÅ─┴Ēę╗ĘĮ├µüĒšfŻ¼ć°╝ęī”ūįė╔Ą─▒Żūoę▓ų╣ė┌▀@ĘNūįė╔Ż¼ę“×ķć°╝ę│¼║§ŲĮĄ╚Č°ī”─│ą®╚╦Ą─ūįė╔Ą─▒Żūo▒žČ©Ģ■é¹║”Ųõ╦¹ę╗ą®╚╦Ą─ūįė╔ĪŻę“┤╦Ż¼┐╔▒ŻūoĄ─ūįė╔į┌║▄┤¾│╠Č╚╔Ž┼c╣■ę«┐╦║═░ž┴ųĄ─▒╗äėūįė╔╩Ūę╗ų┬Ą─ĪŻ┐╔Į╗ōQĄ─ūįė╔╩Ū│²┐╔▒Żūoūįė╔ų«═ŌĄ─╦∙ėąūįė╔ĒŚŻ¼ī”ė┌▀@ą®ūįė╔ĒŚČ°čįŻ¼ę╗ą®╚╦Ą─╦∙Ą├Š═ęŌ╬Čų°┴Ēę╗ą®╚╦Ą─╦∙╩¦Ż¼ę“┤╦╦³éā┐╔ęįį┌éĆ╚╦ų«ķg▀Mąą▐D(zhu©Żn)ōQŻ¼▒M╣▄├┐éĆ╚╦ī”ę╗éĆūįė╔ĒŚĄ─įuār┐╔─▄╩Ū▓╗═¼Ą─ĪŻć°╝ę¤oĘ©▒ŻūC├┐éĆ╚╦ŽĒėą═¼śėČÓĄ─┐╔Į╗ōQūįė╔Ż¼ī”ė┌╦³éāĄ─Ęų┼õąĶę¬ę╗éĆĻP(gu©Īn)ė┌╣½š²Ą─└ĒšōŻ¼▀@╩ŪŽ┬ę╗ąĪ╣Ø(ji©”)╦∙ę¬ėæšōĄ─ā╚(n©©i)╚▌ĪŻ ĪĪĪĪūįė╔Ęų┼õųąĄ─╣½š²å¢Ņ} ĪĪĪĪ╔Łļm╚╗ūóęŌĄĮūįė╔Ęų┼õųąĄ─╣½š²å¢Ņ}Ż¼Ą½Š▄Į^╠ß╣®ę╗éĆĻP(gu©Īn)ė┌╣½š²Ą─└ĒšōŻ¼Č°ŪķįĖīó▀@éĆå¢Ņ}Į╗ė╔╣½├±Ą─╣½ķ_ėæšōüĒĮŌøQĪŻĄ½╩ŪŻ¼╣½├±Ą─ėæšō─▄ʱ«a(ch©Żn)╔·ę╗éĆĻP(gu©Īn)ė┌╣½š²Ą─ś╦£╩╩Ūę╗éĆć└ųžĄ─å¢Ņ}ĪŻė╔ė┌├┐éĆ╚╦Č╝╩Ū└ĒąįĄ─Ż¼├┐éĆ╚╦╦∙░l(f©Ī)▒ĒĄ─ė^³cų╗─▄┤·▒Ē╦¹ūį╝║╗“ų┴ČÓ╦¹╦∙Å─ī┘Ą─ĮM┐Ś╗“ļAīėŻ¼▀@śėę╗üĒŻ¼╬ęéāŠ═▒žĒÜę└┘ćę╗éĆ╔ńĢ■▀xō±ÖCųŲüĒī”éĆ╚╦Ų½║├▀Mąą╝ė┐éŻ¼ęįą╬│╔ę╗éĆ╔ńĢ■Ų½║├ĪŻ╝┤╩╣▀@śėĄ─ę╗éĆ╔ńĢ■▀xō±ÖCųŲ┤_īŹŽ±╔Ł╦∙šJ×ķĄ──Ūśė┤µį┌ė┌¼F(xi©żn)īŹ«öųą(╝┤░ó┴_▓╗┐╔─▄Č©└Ē╩¦ą¦)Ż¼╬ęéāę▓║▄ļy▒ŻūCė╔┤╦Č°ą╬│╔Ą─╔ńĢ■Ų½║├Ģ■ėą└¹ė┌╔ńĢ■ųąĄ─ūŅ▓╗└¹š▀ĪŻ▒╚╚ńŻ¼ī”ė┌ČÓöĄ(sh©┤)įŁätĄ─ę╗éĆĮø(j©®ng)Ąõ┼·įu╩ŪŻ¼ā╔éĆĖ╗╚╦┬ō(li©ón)║ŽŲüĒŠ═┐╔ęįäāŖZę╗éĆĖF╚╦Ą─žöĖ╗ĪŻ▀@śėĄ─ĮY(ji©”)╣¹’@╚╗ėąŃŻ╔ŁĄ─│§ųįŻ¼╔Ł▒Š╚╦ę▓ī”┤╦▀Mąą┴╦┼·┼ą(╔Ł,2000)ĪŻ ĪĪĪĪ╩┬īŹ╔ŽŻ¼╚╬║╬╔ńĢ■▀xō±▀^│╠Č╝▓╗╩Ūė╔éĆ¾wŲ½║├ų▒ĮėŽ“╔ńĢ■Ų½║├▐D(zhu©Żn)╗»Ą─▀^│╠Ż¼Č°╩Ūę¬Įø(j©®ng)▀^š■³hš■ų╬Ą─õų╚Š║═▀^×VĪŻī”ė┌ČÓöĄ(sh©┤)╚╦Č°čįŻ¼ĻP(gu©Īn)ė┌╩└Įń║├ē─Ą─įu┼ą▓╗═Ļ╚½╩Ūūį░l(f©Ī)Ą─Ż¼Č°╩Ū╩▄Ųõ╦¹╚╦Īóš■³h╗“├Į¾wĄ─šTī¦Č°ą╬│╔Ą─ĪŻĄ½╩ŪŻ¼š■³h║═├Į¾w▓╗╩Ū├żäėĄ─Ż¼Č°╩Ūėą├„┤_Ą─ų„Åł╗“āAŽ“ĪŻ┤╦ĢrŻ¼ę╗éĆĻP(gu©Īn)ė┌╣½š²Ą─└ĒšōĄ─ārųĄŠ═¾w¼F(xi©żn)│÷üĒ┴╦ĪŻ ĪĪĪĪųąć°š²į┌Įø(j©®ng)Üvę╗éĆ╝▒äĪĘų╗»Ą─▀^│╠Ż¼╩š╚ļ▓ŅŠÓį┌▓╗öÓ└Ł┤¾Ż¼Ė„ĘN╔ńĢ■├¼Č▄╚šęµ═╗¼F(xi©żn)Ż¼į┌▀@ĘNŪķørŽ┬Ż¼ę╗éĆĻP(gu©Īn)ė┌╔ńĢ■╣½š²Ą─└Ēšō╩Ūš¹║Ž╔ńĢ■ø_═╗╦∙▒ž▓╗┐╔╔┘Ą─ĪŻ╔ŁĄ─ą┬Ģ°ī”╬ęéāįO(sh©©)ėŗųąć°╬┤üĒ░l(f©Ī)š╣Ą─ĘĮŽ“śOĖ╗ģó┐╝ārųĄŻ¼Ą½ø]ėą×ķ╬ęéāį┌░l(f©Ī)š╣▀^│╠ųą╚ń║╬š¹║Ž└¹ęµø_═╗╠ß╣®Į©įO(sh©©)ąįĄ─ęŌęŖĪŻ▀@╩Ū▀@▒ŠĢ°Ą─▓╗ūŃų«╠ÄĪŻ ĪĪĪĪ░ó¼ö?sh©┤)┘üåĪż╔ŁŻ║ĪČū„×ķūįė╔Ą─░l(f©Ī)š╣ĪĘŻ¼ųąć°╚╦├±┤¾īW│÷░µ╔ń╝┤īó│÷░µĪŻ ĪĪĪĪ* įŁ╬─░l(f©Ī)▒Ēė┌ĪČĮø(j©®ng)Ø·īW╝Š┐»ĪĘ2001─ĻĄ┌1Ų┌Ż¼▒ŠĢ°╩šõøĢrėąäh╣Ø(ji©”)ĪŻ ĪĪĪĪ[1] ė╔ė┌ųą╬─░µ╔ą╬┤│÷░µŻ¼▒Š╬─ī”ĪČū„×ķūįė╔Ą─░l(f©Ī)š╣ĪĘĄ─ę²╬─ę╗┬╔üĒūįŲõėó╬─░µĪŻ ĪĪĪĪ[2] ĻP(gu©Īn)ė┌ą¦ė├▒╚▌^å¢Ņ}Ż¼ģóķåSen and Williams (1982)ĪŻ ĪĪĪĪ[3] ī”╔ŁĄ─īWąg(sh©┤)žĢ½IĄ─╗žŅÖŻ¼ģóķå▒ŠĢ°Ą─┴Ēę╗Ų¬╬─š┬ĪČĻP(gu©Īn)ūó╔ńĢ■ĄūīėĄ─Įø(j©®ng)Ø·īW╝ęĪĘĪŻ ĪĪĪĪ[4] ęŖĪČšōšZĪżæŚå¢Ų¬ĪĘĪŻ |
| ą┬└╦╩ūĒō > žöĮø(j©®ng)┐vÖM > Įø(j©®ng)Ø·Ģrįu > ę”č¾ > š²╬─ |
|
| ||||
| ¤ß ³c īŻ Ņ} | ||||
| ||||
|
ą┬└╦ŠW(w©Żng)žöĮø(j©®ng)┐vÖMŠW(w©Żng)ėčęŌęŖ┴¶čį░Õ ļŖįÆŻ║010-82628888-5173ĪĪĪĪĪĪÜgėŁ┼·įuųĖš² ą┬└╦║åĮķ | About Sina | ÅVĖµĘ■äš(w©┤) | ┬ō(li©ón)ŽĄ╬ęéā | šąŲĖą┼Žó | ŠW(w©Żng)šŠ┬╔Ĥ | SINA English | Ģ■åTūóāį | «a(ch©Żn)ŲĘ┤ę╔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