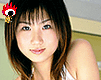我認識的費孝通先生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4月25日 21:59 文匯報 | |||||||||
|
我為費孝通先生整理“訪談實錄”,回味著費先生的談話,一些曾經親歷的場景又回到眼前。 1997年春,費先生在專題調查太湖水資源的污染、治理和開發問題的行程中,訪問了江蘇宜興。他走進紫砂村村民顧秀娟家,坐在工作臺一側,饒有興趣地觀看紫砂壺的手工成型過程,眼光隨著壺的旋轉,流露出由衷的羨慕。現場很靜,費先生輕聲問道:“你收不收
1998年冬,在深圳迎賓館,費先生拿出新出版的《行行重行行》(續集),送給前去看望他的深圳市長。市長翻閱片刻,問:“費老,您書里的這些例子和數據都是從哪兒來的?”費先生說:“都是我走到實地一點一點問出來的。我的老師遍天下啊。” 在費先生外出作實地調查的一次次座談會上,許多地方領導和基層干部都聽他說過類似的話——我現在老了,沒有學校肯收我這個學生了。我只好出門找老師,找農民,找做實際工作的同志。很多新事情,我不知道,他們知道,我只有向他們請教。 費先生的請教,讓農民覺得親近可敬,也曾使不夠深入的干部陷于尷尬。一次,一位縣委書記對費先生講起當地用地窖儲藏、實現水果保鮮的事。費先生問:這辦法是誰最先想到的?是怎么想到的?這個事是誰最先做起來的?是怎么做起來的?要投入多少錢?錢是自家的還是借的?借錢都有什么渠道?私下借錢要不要保人?保人要有什么資格?……一連串問題,書記一個也答不上來,只好表示“我們一定會了解清楚”。事實上,也許書記還沒來得及布置,費先生當天下午已經為此走進了農戶。 提出類似的問題,費先生是在求教,以增進自己的知識;也是在點撥,以促進基層干部的務實精神。同時,也在影響著身邊的工作人員。求知之舉本身,就有“誨人”之益。 在外出作實地調查的旅途中,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在縱筆揮灑的字里行間,在私下閑談時,費先生時常會有富于詩意的妙語或痛定思痛的心緒,帶著深切的生命感受,意境動人,味道十足。若能有所會意,自不乏接引之緣。 1986年,費先生當年的學術奠基之作《江村經濟》的漢譯本終得問世。他面對隔著近半個世紀時光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愧赧對舊作,無心論短長。路遙知馬力,坎坷出文章。毀譽在人口,浮沉意自揚。涓滴鄉土水,匯歸大海洋。歲月春水逝,老來羨夕陽。闔卷尋舊夢,江村蠶事忙。” 1990年,費先生訪問過莫斯科后,在《紅場小記》一文中寫道:“擺弄了我一生的風暴,不就是從這里起源的嗎?……紅場的坡道,對我來說是相當陡的,因此也相當費力……氣喘如牛,勉力前進,最后總算踏進了紅場,望見了列寧的陵墓……一路思緒如潮,花開花落,逝者如斯,但恨年邁我來遲。” 話題回到太湖。在那次考察活動的最后一站,費先生對家鄉父母官說:“我想為家鄉再做點事情,做一篇‘小’文章。中間的一豎是長江,左右兩點是太湖和洪澤湖。‘小’文章是要以水興蘇(江蘇)。我已經把太湖跑了一圈,有了一個點。打算再去洪澤湖,不能讓‘小’字少一點,少一點就成‘卜’了,就前途未卜了。我這些年一直在做‘小’文章。小商品,小城鎮,都是‘小’。現在做水的文章,還是個‘小’字。老小老小,老了又變小了。這次圍著太湖轉了一圈,就是當小學生,一路請教,知道了很多新知識。” 結束環太湖考察活動后,在回北京的火車上,費先生說:“我在想‘太湖精神’,想了八個字:匯納百川,潤澤萬民。我想多懂一點水。匯納百川,滋潤人家,并不一定要人家感激你。讓別人都懂得你,哪里可能啊?太湖就是這樣。過去水多好啊,潤澤萬民,沒有去想讓人感激。有時候,不光沒有感激,還要污染它。可是太湖并沒有因為被污染而停止潤澤萬民。”這段話,讓我受到震撼,即希望費先生寫成文章。 費先生又談到了寫文章和教書,他說:“寫了文章拿到課堂上去念,不算希奇。要用旁白把正文里沒有講出來的東西烘托出來,提高一步。旁白比正文好,正文的寫作常受拘束。光有正文,傳達不出旁白的東西。有的教授只能上課念講義,有的連講義也不是自己的,那成什么教授啊!教授的本領在旁白。” …… 費先生類似的談話,很多很多。說到要緊處,他有句口頭禪:“明白我的意思嗎?”說者有意,也希望聽者有心,能聽懂那些不宜說破、不想說破、不能說破的話頭中藏著的正文乃至旁白。有機會常聽費先生談話,總覺得當下即是課堂。正文精彩,旁白更是絕妙。 至今仍記得,隨費先生考察太湖途中,看過他隨身攜帶的一個小筆記本。上面寫有他準備做文章的題目,分為兩類,一類是:做人之道,有人緣、涵養功夫、性格素質、抑制沖動、規矩與出格、為別人著想、調適自己的感情、感受別人的感受……另一類是:新城加舊城、運河新貌、生態循環、效應交織、垃圾處理、農民要有書讀、現代化的負效應……新的正文、新的旁白在費先生大腦中醞釀著。他仍繼續著田野調查,仍在認真“補課”。 最近,費先生又增新課,他正讀《解碼生命——人類基因組計劃和后基因組計劃》。厚厚一本大書,讀得專心致志。他很可能想起自己早年專修體質人類學的事了。從當年測量人體骨骼數據,到今天的人類基因組計劃,近七十年間,是一場人類研究領域的驚世之變。費先生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對他感興趣的事情跟著看,看出變化,看到過程,看出道理,講出意義。終生致力于人類學研究、親身經歷這場人類研究巨變的費先生,寫出過《人不知而不慍》,寫了史祿國。他還打算寫《有朋自遠方來》,寫寫錢穆。作為私愿,我曾希望費先生再寫一篇《學而時習之》。現在想想,自己是多嘴了。已經九十一歲的費先生,如今還在一趟趟出門找老師,一門接一門補課,這情景不就是一篇魅力十足的《學而時習之》?與其落筆紙上,何如寫在天地之間!(作者 張冠生 原文來源于《文匯報》2002年1月23日)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學者隨筆 > 社會學家--費孝通 > 正文 |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票:今日黑馬 |
| 怎樣迅速挖掘網絡財富 |
| 短線最大黑馬股票預報 |
| 海順咨詢 安全獲利 |
| 開園藝花卉店年利50萬 |
| 首家名牌時裝折扣店 |
| 如何加盟創業賺大錢? |
| 05年最具潛力好項目 |
| 開麥當勞式美式快餐店 |
| 05年最賺錢的投資項目 |
| 開冰淇淋店賺得瘋狂 |
| 美味--抵擋不住的誘惑 |
| 新行業 新技術 狂賺! |
| 點!----億萬商機 |
| 05年投資賺錢好項目!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