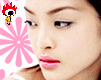|
樊樹志
作者:復(fù)旦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
博士生導(dǎo)師
歷史給人以深邃的眼光去看待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它可以洞察世事,入木三分。這種眼光對于全球化時代的人們,尤其是那些為爭名逐利而奔忙,愈來愈心浮氣躁,局限于眼前方寸之地難以自拔的人們更為必要。在下愿意借報紙一角,談古論今,知往鑒來。
“公社”這個事物,在二十世紀(jì)中期曾經(jīng)喧鬧了一陣,因為不合時宜,早已土崩瓦解,消失得無影無蹤。也許,如今的青年人已經(jīng)不知“公社”為何物了。然而,忘記并不解決問題。在我看來,它的出現(xiàn),比它的消失更值得注意。社會學(xué)家、經(jīng)濟學(xué)家已經(jīng)在進(jìn)行研究。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從歷史根源來探討一下。
“公社”這個詞匯,并非新名詞,卡爾·馬克思的著作經(jīng)常提到“公社”。中國歷史上也有“公社”的存在,它是一種共同體,以地域為紐帶的農(nóng)村公社取代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公社,是歷史的進(jìn)步。農(nóng)村公社的消失,更是歷史的進(jìn)步。然而久已從歷史舞臺上消失的農(nóng)舍公社,給中國傳統(tǒng)社會留下了深遠(yuǎn)的影響,它的幽靈始終縈繞著人們。
農(nóng)村公社的特點,就是土地公有,共同生產(chǎn),共同消費,沒有貧富的兩極分化。根據(jù)民族學(xué)家的調(diào)查,二十世紀(jì)初的西雙版納傣族中還保留著農(nóng)村公社的遺存,與遠(yuǎn)古時期的情況極為相似。從《夏小正》、《管子》等典籍中,可以依稀看到它的影子。西周的井田制度,根據(jù)后人的追述,農(nóng)村公社的氣息是相當(dāng)濃厚的。由儒家倫理培育出來的政治家、思想家,對它推崇備至,奉為理想主義的土地制度和政治模式。
亞圣孟子生活的時代,農(nóng)村公社、井田制度已經(jīng)分崩離析,這使他感到耿耿于懷。所以當(dāng)一些國君向他征求治國方略時,他總是說,要施仁政,而“仁政必自經(jīng)界始”,也就是說,仁政的第一步就是恢復(fù)農(nóng)村公社的井田制度。孟子關(guān)于井田制度有這樣的描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yǎng)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農(nóng)田劃分成為棋盤狀,每家農(nóng)民必須優(yōu)先共同耕種“公田”,然后才可以耕種自家的自留地——“私田”。由于每家農(nóng)民擁有同等數(shù)量的“私田”,所以過著沒有貧富分化的和諧生活。
后世儒家學(xué)者鑒于土地私有造成的貧富分化,對已經(jīng)消失的農(nóng)村公社充滿向往和羨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傳何氏解詁》、韓嬰《韓詩外傳》對公社有許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組織生產(chǎn)之外,還保留著“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體主義互助習(xí)尚,“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于儒家學(xué)者對農(nóng)村公社與井田制度的理想主義虛構(gòu)。
它與秦漢以來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形成鮮明的對照。小農(nóng)經(jīng)濟是以土地私有為前提的,必然伴隨土地買賣、兼并,以及貧富兩極分化。首先發(fā)難的是儒家公羊?qū)W大師董仲舒。他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深為不滿,認(rèn)為這是商鞅廢除井田制度所留下的后遺癥。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藥方,就是恢復(fù)井田制度。鑒于井田制度一時難以恢復(fù),他提出一個折中主義的方案——“限田”,目的在于“塞兼并之路”,使得富有者占田不能超過一定數(shù)量,貧者不至于沒有土地。他的這個方案不過是儒家的平均主義理想而已,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莽的農(nóng)業(yè)改革,重彈董仲舒的老調(diào),再次顯示了儒家那種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政治的致命傷。他頒布的“王田令”,是以贊美早已退出歷史舞臺的公社與井田為出發(fā)點的,主張取消土地私有制,把私有土地收歸國有,然后按照《周禮》的井田制度模式,實行“均田”——平均分配土地。這種看似很“革命”的主張,其實是歷史的倒退。把私有土地收歸國有,禁止土地買賣,是企圖以國家行政手段向經(jīng)濟發(fā)號施令,違背了經(jīng)濟發(fā)展規(guī)律。因此遭到全社會的一致反對。甚至連農(nóng)民也不買賬,這是為什么?因為農(nóng)民是小私有者,他們不愿意自己的私有田產(chǎn)成為“國有”。王莽的“托古改制”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卻并未使后世的政治家引以為戒。
有宋一代,小農(nóng)經(jīng)濟獲得了長足發(fā)展,伴隨而來的兼并盛行,貧富分化加劇。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以為是“田制不立”的結(jié)果。于是乎,恢復(fù)井田制度的議論如沉渣泛起,幾乎連綿不斷。即使被譽為“十一世紀(jì)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對井田制度也百般美化,他在與宋神宗議政時,建議模仿王莽的“王田令”,“令如古井田”。他的“方田均稅法”,似乎是這一主張的第一步。看來,王安石與王莽是頗有一些共鳴之處的。新儒學(xué)大師朱熹也不見得高明,也主張恢復(fù)井田制度,他說:“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而今要行井田,索性火急做”。
到了近代,“三農(nóng)”問題尖銳化,上述思路再一次重現(xiàn)。1853年洪秀全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頗令后世政治家、思想家贊賞,為他來不及實施而惋惜。其實惋惜大可不必。冷靜加以透視,它不過是王莽的“王田令”的高水平重現(xiàn)罷了。其田畝制度規(guī)定,耕地按照農(nóng)戶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以實現(xiàn)“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這并非新發(fā)明,而是共同生產(chǎn)共同消費的農(nóng)村公社模式的翻版。在這種社會中,小農(nóng)的個體家庭變得無足輕重,公有制的共同體是至高無上的。這種烏托邦主義,無視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發(fā)展規(guī)律,如果付諸實施,勢必對經(jīng)濟造成極大的破壞。值得慶幸的是,它沒有實施,甚至以后的太平天國官方文書中再也沒有提及。這個地上天國的締造者不得不面對現(xiàn)實,還是比較明智的。
令人尊敬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針對“三農(nóng)”問題的癥結(jié)——地權(quán)不均,提出“平均地權(quán)”、“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如果不為尊者諱,實事求是細(xì)細(xì)分析的話,其中頗有一些問題。孫中山的“平均地權(quán)”是以土地國有代替土地私有為前提的。簡而言之,在孫中山思想中,平均地權(quán)和土地國有是合二為一的。孫中山曾多次從不同角度闡述他的平均地權(quán)思想,對井田制度及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給予高度評價。他說:“平均地權(quán)者,即井田之遺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滯而不可復(fù)用,則唯有師其意而已”;“中國古時最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權(quán)的用意是一樣的”;“諸君或者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么東西。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以前,便老早有過這項主義了。像周朝所實行的井田制度,漢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對公社與井田的贊美與懷戀,公社與井田,以及恢復(fù)公社與井田的嘗試,竟然成為了其“平均地權(quán)”的出發(fā)點,實在是耐人尋味的。
為什么人們的改革思路始終離不開井田制度,公社的幽靈如此難以擺脫、始終揮之不去?實在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