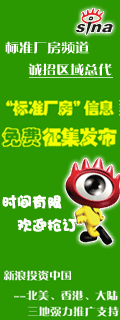|
劉文瑞 景濤
馬克斯·韋伯是一個天才式的人物,也是一個讓人難以完全理解的人物。對他的學術貢獻,至今仍然眾說紛紜。
韋伯之于社會學,正如牛頓之于物理學。社會學家柯塞(Lewis A. Coser)評價說:韋
伯以永不停息的斗爭為代價,獲得了對社會清晰透徹的認識,很少有人達到他那樣的深度。他帶來的是對人類和社會的深刻理解。他對社會行動中的磨難、悲劇以及成功的冷眼關注,使他成為社會分析方面至今無人能及的大師。他的學術領域,首先立足于對當時德國經濟社會問題的經驗研究,其次是擴展為對西方社會轉變的歷史研究,再次是引申到對西方與非西方社會的比較研究。這種研究,幾乎體現了一種要把人類社會的所有奧秘都揭示開來的勇氣,相應的研究成果,統統被后人視為理論經典。韋伯所討論的問題,并非抽象的理論,而是對社會轉變的因果詮釋。韋伯的價值,其實不在于抽象理論的建構,而在于啟發人們對社會現實的關懷、思考與理解。
韋伯其人與韋伯其學
韋伯實際上十分關注現實,熱愛生活。他的興趣極其廣泛,愛好音樂,又懂一些建筑,還對股票市場有極大興趣。他一生積極準備著參與政治,非常關懷德國的命運,思考如何促使德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他出于對德意志民族國家的使命感和對歷史的責任感,自稱在國家利益上是“民族主義者”,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許“以政治為志業”。所以,韋伯常常在公眾場所亮相,有點像我們今日那種在媒體上開壇講說的學者。但是,政治卻不期許韋伯,他始終未能在現實政治中顯露頭角,這或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說起韋伯的學問,人們多以社會學家看待,但這是不完整的韋伯。在韋伯的時代,社會學尚處于草創時期。拿韋伯自己的話來說,“在海德堡,盡管已經以社會學為出發點來考慮許多問題,但作為研究社會的科學尚未在學院體系中出現。”社會學的前身,在日耳曼地區被稱為國家學,用現在的學科分類標準來看,包括了歷史學、法理學、社會學和經濟學。韋伯在大學里,也一直以經濟學家或歷史學家身份出現,一直到1909年海德堡學會成立時,他還是以歷史學家的資格入選的。即使以1910年德國社會學學會的建立為標志,韋伯從事社會學研究也僅有短短的十年。他在此前的研究,無疑帶有國家學的色彩。或許,正是這種綜合性的國家學,才使韋伯能夠成為橫跨多個學科的社會科學大師,尤其是歷史學的積淀,使韋伯的研究成果有了一種洞穿時空的深邃。約翰·洛夫曾指出:“韋伯的學術生涯開始于古代史研究,只是在精神崩潰后的中期才轉向當代課題的研究。”在韋伯步入學術領域的前期,他主要運用歷史學的思考方法,后來,才逐漸采用了比較社會學的分析方法。隨著韋伯由歷史學向社會學的轉化,他開始更深入地探討整個人類社會的理性化問題,進而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理性化歷史進程及其變遷進行思考,最終落腳于東西方文明的比較研究。
韋伯的“專注”和“博大”
韋伯關注的研究對象,一直在不斷變化,在他的論著中,研究領域由德意志一直擴展到全世界,研究范圍由經濟史一直擴展到政治、宗教、社會、文化諸史。但是,這種領域和范圍的變化又包含著主題的不變化,他的不變的主題,就是人類社會的理性。有人指出,韋伯畢生的論題,就是“何為理性”。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韋伯重點研究了西方社會的理性化過程。在韋伯的筆下,這一歷史過程的核心就是“祛魅”。所謂“祛魅”,實際上就是運用科學的方法剝去迷罩在人類社會現象上的神化或魔化的種種光環,也被稱為“去巫”、“去昧”。后來,韋伯注意到,理性化并不只有西方式一種形態,在中國、印度等非西方地區,同樣存在理性化形態。但是,近代西方形態的理性化在韋伯的筆下具有“獨特性”。也就是說,只有西方式的理性,才能發育出資本主義。這種“獨特性”反過來又具有普遍歷史的意義,在韋伯眼里,它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方向。但在強調理性的同時,韋伯又十分重視文化領域和精神領域的情感、信仰等因素,通過對新教倫理與西方世界的關系分析,韋伯指出,西方理性化的動力,來自于社會理性化與人的自由化之間的復雜張力。韋伯孜孜不倦所要追求的,就是尋求社會秩序與個性發展之間的恰當尺度。也許,正是這種理性和情感的糾結,科學和人文的交錯,歷史和現實的重疊,使韋伯的精神處于一種高度緊張狀態之中。
韋伯的價值,不僅在于他在社會科學各個領域都提出了具有獨創性的觀點,而且在于他以理性和超然的態度分析了世界的理性化進程,除去了社會研究中的“神性”和“魔性”,用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的方法,給人們還原了一個邏輯的和經驗的社會。同時,他又在以科學冷靜的方式剖析社會時,對人生的意義和精神的追求形成了超常的理解能力與同情心理。所以,在不同的人眼里,就有了不同的韋伯。美國有一位神學家,在讀了韋伯的著作之后說,即使是神學家,也很少有人能像韋伯那樣對宗教有如此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心。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則認為,韋伯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科學家、哲學家。而在管理學家那里,往往強調韋伯官僚組織理論在社會管理中的價值和作用。作為歐洲文明之子,韋伯是一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思想可謂博大精深,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在那么多的領域做出那么大的貢獻。到西方去讀書,不管你學習社會科學的哪門學科,似乎都與韋伯有關,政治學要讀韋伯,社會學要讀韋伯,經濟史更要讀韋伯,法律社會學則非讀韋伯不可,歷史學方法論也離不開韋伯。
韋伯研究的“兩極”
韋伯最有代表性的兩部著作,一部是《宗教社會學》,人們最為熟悉的就是其中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另一部是《經濟與社會》,包括他的博士論文以及經濟史,也屬于這一部分。這兩部分構成了完全不同又互相關聯的兩個領域,一個領域是文化,一個領域是制度。這種“兩極”狀態導致對韋伯的研究也分為兩派。在文化領域,韋伯強調,思想、觀念和精神因素,對人的行動具有決定作用。而在制度領域,韋伯又強調,人的行動背后,是更具有決定作用的制度約束。后學在研究韋伯中眾說紛紜,往往同韋伯在不同著作中對兩個領域的不同側重有關。在前一個領域,人們往往把韋伯看做文化決定論者,而在后一個領域,人們又往往把韋伯看做制度決定論者甚至唯物論者。這種把一個完整的韋伯解析為兩個相互對立部分的看法,從韋伯思想脈絡的局部上說,似乎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據,但整體看來卻有以偏概全的失誤。韋伯在他的研究中,采用的是“理想型”方法,既把社會現象的某一部分抽取出來進行類似化學實驗的“純粹”研究。而在現實社會中,純粹的“理想型”是不存在的。比如,化學實驗用的食鹽,是按純粹的氯化鈉分子式來操作的,而現實中的食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雜質。因此,說韋伯的研究中同時注重文化和制度兩個方面,似乎要更恰當一些。
韋伯的制度主題
韋伯的制度研究,主要關注點在西方的領主式封建制度和基督教制度上。他力圖從西方的制度演化中尋找出資本主義興起的奧秘,進而探求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在韋伯眼里,封建制度具有為資本主義誕生提供前提的功能。這種功能建立在它的契約性上面。在韋伯的筆下,前資本主義社會比較穩定的社會組織都是建立在傳統權威基礎上,即家長制。這種家長制在東方和西方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西方就是領主封建制,東方則是世襲官僚制(家產制)。封建制下的領主與附庸,由契約來規定權利和義務,這就誕生了憲政的萌芽。韋伯把這種萌芽稱為“準憲政主義”。而東方式的世襲官僚制,缺乏契約和權力限制,所以,不可能產生出近代憲政。他的官僚組織理論,就是在這一基礎上提出來的。
韋伯的這些思想不屬于管理學。如果我們只是打算解決管理活動中遇到的眼前問題,那么,讀韋伯的書就沒有多大意思。但是,如果我們打算從本質上深度發掘中國式社會與西方式社會的內在差異,韋伯的書就極具啟發意義。比如,我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搬來了西方式的公司治理結構,股東會、董事會、總經理、監事會,應有盡有,但實際運作卻充滿了中國色彩,潛在的規則和顯現的規則往往不吻合。如果用韋伯的方式去探究,會對我們在制度規則體系的形成演變機制上的探討有許多啟迪。韋伯的研究,在一定意義上開了制度經濟學的先河。對韋伯研究頗有深度的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李強教授甚至認為,韋伯和現在流行的新制度經濟學相比,會使人感到學術上的今不如昔,前者是高山,后者只是簡簡單單的丘陵。
韋伯的文化主題
韋伯的文化研究,主要關注點在宗教問題上。不過,韋伯的宗教,不像我們通常意義上理解的宗教,而是更為廣闊的文化意義上的宗教。宗教在人類社會中具有特殊意義,它借助彼岸世界和終極價值的追求,使人類社會有了道德倫理,有了精神秩序。在韋伯看來,只有首先以宗教規范精神秩序,才會形成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有了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人類才能具備社會生活的常態。即宗教和文化決定制度,制度決定經濟和社會。
韋伯在宗教文化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比較方法。他致力于解釋不同宗教中所包含的經濟倫理與政治倫理,進而解釋不同宗教的理性化程度。韋伯的比較宗教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各種宗教理性化程度的強弱上面。比如,韋伯把中國的儒學和道家學說也看做宗教,他認為中國的宗教(即儒學和老學)過于關注現實,缺乏對彼岸世界的追求,所以理性化程度不高。而印度的佛教則只追求彼岸世界的解脫,不關注現實世界,理性化的程度也不高。只有歐洲新教中的加爾文教,處于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緊張狀態之中,做上帝選民的使命和對現實社會的責任交織在一起,孕育并催生出了資本主義。
對于我們來說,讀一點韋伯的宗教社會學著作,有助于廓清文化研究中的迷霧。比如,在企業文化建設中,文化到底是什么?企業的價值觀念應該如何確立?現實中的價值觀念又是通過什么方式和途徑形成的?這些問題往往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困惑。在有些企業家那里,文化建設僅僅是一種提高效率的手段,好一些的,則把文化建設當作維系人心和凝固力量的工具,從人的本質角度探究文化底蘊,從超越功利出發進行文化建設,對不起,則往往十分遙遠。韋伯的研究,可以使我們對文化的認識產生質的飛躍。
科學與宗教的溝通——現代社會的困境
仔細觀察不難發現,韋伯的制度主題和文化主題,在更高的層次上,通過互補和鑲嵌融為一體,這就是科學和宗教的溝通。科學產生技術理性,宗教產生救贖倫理;科學尋求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案,宗教尋求理想世界的最后歸宿。二者之間的對立,使現代人處于非此即彼的焦慮之中。至今我們經常看到的科學主義和人文關懷之爭,實際上是這種科學與宗教對立的邏輯延伸。韋伯小心翼翼地溝通二者,尋求二者的統一。也許,這才是韋伯對社會科學的最大貢獻。
當代研究韋伯的專家施盧赫特曾對韋伯的這一貢獻有著學術性的說明:“韋伯的論點讓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現實狀況的診斷,而在他的診斷中,韋伯對兩種看法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我們終會找到最后真理的信仰,另一種是認為我們可以創造人類幸福的信仰。 今天,似乎逃避現世與適應現世的心態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環不已,韋伯的這番診斷因此重新顯出其重要性。他的診斷指出了我們在現代社會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卻也讓我們明白為什么我們對于這種不適意、不痛快卻甘之如飴,而不輕言放棄。”(《理性化與官僚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
國內研究韋伯的專家蘇國勛則從另一個角度——現代社會的形式理性和實質非理性的沖突來解讀韋伯的意義。他說:“在韋伯的思想中,現代社會的矛盾即從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相互關系和張力中解讀的:形式上的合理性與實質上的非理性是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征。換言之,突顯功能效率精神是現代社會的合理之處,而不合理之處在于把功能效率這一本來屬于手段的東西當作目的來追求。理性化造成現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方面受賜良多;另一方面他們又身不由己地陷于理性化所造設的‘鐵籠’,飽受喪失目的追求(價值)、喪失精神家園的痛苦。韋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見深刻揭示了現代人的這種尷尬處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現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強調作為現代人的命運,現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現代性的悖論。這也許是不同國度和地區的人對他共同感興趣的原因。”(《中華讀書報》1998年4月15日)
不管從那個角度,韋伯都能給我們帶來新的思考,尤其是學理上的思考。在喧囂的社會中,在忙忙碌碌的工作與生活中,我們已經很少認真冷靜地思考人類命運了,學術也越來越功利化了,韋伯可以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學術的厚重和虔誠。有人曾經用諷刺的口吻說:“誰掌握了對韋伯的闡釋權,誰也就有望執學術研究的牛耳。”我倒覺得,把這句話中的揶揄語氣去掉,可能更符合實際。面對像韋伯這樣的大師,我們有什么理由不以為然!
馬克斯·韋伯其人其事:
馬克斯·韋伯:最后的博學者
馬克斯·韋伯:圈外大師 德國的亞當·斯密
馬克斯·韋伯:融合中的創造
馬克斯·韋伯對關于報酬的兩個神話的終結
韋伯過時了嗎
生活中的韋伯
韋伯大事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