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融合中的創(chuàng)造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4月03日 13:51 《管理學(xué)家》 | |||||||||
|
楊蕾 劉文瑞 一般來說,只有那些具有世界級(jí)影響的名人,才會(huì)引起“過時(shí)了嗎”的討論。小人物是沒有這種殊榮的。然而,韋伯在生前,恰恰是一個(gè)小人物。 想當(dāng)年,馬克斯·韋伯的命運(yùn)也充滿了坎坷。他立志于政治,命運(yùn)卻把他拋入學(xué)術(shù)
幸運(yùn)的是,韋伯“墻里開花墻外紅”,美國人帕森斯發(fā)現(xiàn)了他,向世界宣傳了他。這真應(yīng)了“距離產(chǎn)生美”那句名言。從40年代起,韋伯走紅了整個(gè)世界。而且歷時(shí)愈久,似乎愈能顯示出他的老辣。60年代,德國人開始“重新發(fā)現(xiàn)”韋伯,慕尼黑市還命名了一個(gè)廣場(chǎng)為“馬克斯·韋伯廣場(chǎng)”。到了80年代,世界各國關(guān)于韋伯的研究成果車載斗量,汗牛充棟。人到了這個(gè)份上,當(dāng)然就同平頭百姓不一樣,就有了是否過時(shí)的憂慮。 韋伯的學(xué)術(shù),從褒義上說是博大精深,從貶義上說是龐雜凌亂。見仁見智,自有后人評(píng)說。一般都認(rèn)為,韋伯在社會(huì)學(xué)、歷史學(xué)以及社會(huì)科學(xué)方法論等方面的貢獻(xiàn),時(shí)至今日仍然有其價(jià)值,惟獨(dú)在他提出的官僚組織理論上,有著較大爭論。談?wù)擁f伯過時(shí)與否,往往集中在官僚制問題上。 韋伯以其非人格化的、效率取向的、程序優(yōu)先的官僚制理論著稱于世。他的“官僚制”伴隨著機(jī)器大工業(yè)的轟鳴聲誕生,為西方工業(yè)時(shí)代的輝煌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當(dāng)代西方發(fā)達(dá)國家已進(jìn)入后工業(yè)社會(huì),官僚制在“內(nèi)適應(yīng)”和“外適應(yīng)”上都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弊病。因此,20世紀(jì)60年代起,就有對(duì)官僚制的不斷質(zhì)疑,尤其是本尼斯,在1966年斷然宣布,從當(dāng)時(shí)算起,25年到50年內(nèi)就要為官僚制送葬。蓬勃興起的民權(quán)運(yùn)動(dòng),對(duì)西方的政治沖擊不亞于30年代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官僚制受到嚴(yán)峻的挑戰(zhàn)。80年代以來,在官僚制最為典型的公共管理領(lǐng)域,從英國到美國,從澳大利亞到新西蘭,幾乎展開了一場(chǎng)全球化的改革運(yùn)動(dòng)—新公共管理運(yùn)動(dòng)。在企業(yè)界,人性化管理、網(wǎng)絡(luò)組織、虛擬組織、學(xué)習(xí)型組織等等新的管理模式不斷出現(xiàn)。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yè),都有一個(gè)強(qiáng)大的聲音在呼喊著—拋棄官僚制!甚至有人私下認(rèn)為,韋伯還是安安生生回歸他的社會(huì)學(xué)吧,管理學(xué)已經(jīng)不需要韋伯了。 這就給我們帶來了一個(gè)不得不回答的疑問:韋伯真的過時(shí)了嗎? 恐怕事實(shí)并非如此。如果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地觀察和研究,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一個(gè)有趣的事實(shí)—那些所謂的替代官僚制的東西,不管是新型理論也好,還是實(shí)用模式也好,不但沒有拋棄掉官僚制,反而是在完善修補(bǔ)著官僚制。倒是那些沒有同官僚制發(fā)生正面沖突的學(xué)術(shù)理論,在不動(dòng)聲色地消蝕著官僚制的基礎(chǔ)。 在管理實(shí)踐上,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政府領(lǐng)域的改革,“經(jīng)理革命”在企業(yè)管理上的沖擊,都沒有上根本上動(dòng)搖官僚制。恰恰相反,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著眼于提高績效,降低成本,所采用的方法都屬于理性方法。沒有一項(xiàng)改革是否定層級(jí)分工、減少理性因素、反對(duì)專業(yè)技能的。如果韋伯地下有知,肯定會(huì)說:感謝你們,你們?cè)趻仐壒倭胖频钠焯?hào)下,正是采用了官僚制的精髓。改革官僚制的嘗試,正好驗(yàn)證了韋伯的斷言:“官僚制本身純粹是一種精密儀器”,“由于它內(nèi)部的徹底理性化結(jié)構(gòu),使對(duì)它的‘革命’愈來愈不可能”。官僚制也有它的生命,伴隨著它的運(yùn)行,肯定會(huì)積累一些非官僚制的因素。天長日久,就好像一臺(tái)機(jī)器被灰塵蒙住了光輝。20世紀(jì)60年代以后針對(duì)官僚制的各項(xiàng)改革,恰如給這臺(tái)顯得老態(tài)的機(jī)器擦洗污垢,清除雜物,拋光上油,緊固部件,反而使它煥發(fā)了活力。 在管理理論上,那些對(duì)官僚制提出挑戰(zhàn)的觀點(diǎn),最后也落入了官僚制的窠臼。比較典型的,如西蒙的組織行為理論。西蒙對(duì)整個(gè)古典管理理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píng)。當(dāng)然,他是主要沖著泰羅和法約爾等人去的,但是,古典管理理論中的理性和效率,把韋伯與泰羅、法約爾綁在了一條船上。所以,批評(píng)泰羅、法約爾,也就捎上了韋伯。按照西蒙的觀點(diǎn),古典組織理論的致命弊端在于它是機(jī)械的,過于理性化的,人變成了組織機(jī)器和的齒輪和螺絲釘。但是,西蒙自己對(duì)決策程式的研究,對(duì)人工智能的熱衷,對(duì)計(jì)算機(jī)在管理中運(yùn)用的探討,使他自己也帶上了“機(jī)器化”的色彩。厄威克正是在這一點(diǎn)上,不無挖苦地說道:“西蒙教授是這樣熱衷于電子計(jì)算機(jī),但其他著作家有哪一個(gè)批評(píng)他采用了一個(gè)‘行為科學(xué)的機(jī)械模式’呢?”最要命的是,西蒙雖然在《管理行為》中用“有限理性”否定了“完全理性”,但他仍然立足于理性,而且在論述組織的作用時(shí),特別強(qiáng)調(diào)組織能夠克服理性限制,提高人們的理性水平。這樣,西蒙繞了一個(gè)大圈,在重視理性的問題上與韋伯殊途同歸。 科學(xué)哲學(xué)家?guī)於鳎岢隽恕胺妒健?pardigm)的概念。時(shí)至今日,范式作為一種科學(xué)研究中的分析模型,已經(jīng)被學(xué)術(shù)界廣泛接受。在《必要的張力》一文中,庫恩認(rèn)為,科學(xué)的發(fā)展,可以分為建立完善范式和打破范式兩個(gè)階段。學(xué)術(shù)研究首先是建立一個(gè)范式(如經(jīng)典物理學(xué)中的牛頓體系),然后是不斷完善范式,當(dāng)新的東西在舊范式里容納不下時(shí),就提出了打破范式的任務(wù)。科學(xué)的發(fā)展既可以表現(xiàn)為對(duì)范式的補(bǔ)充和完善,又可以表現(xiàn)為對(duì)范式的打破和重建。把范式這一概念借用過來評(píng)價(jià)官僚制,我們就不難看出,正是韋伯的官僚制,建立了一個(gè)研究組織與管理的前所未有的范式。韋伯以后的管理學(xué),實(shí)際上一直在不斷完善、豐富、發(fā)展著這個(gè)范式。迄今為止的組織理論,雖然有了一些突破官僚制范式的星星點(diǎn)點(diǎn),但仍不具備一個(gè)替代韋伯的新范式雛形。所以,那些試圖拋棄官僚制的改革實(shí)踐,到頭來只是在這個(gè)范式上添磚加瓦;而那些對(duì)官僚制的理論批判,多數(shù)都在崇尚理性這一點(diǎn)上補(bǔ)充著韋伯的理論。韋伯的官僚制范式,迄今還在主宰著世界。 當(dāng)然,官僚制理論不可能永葆青春。但就目前的管理理論和實(shí)踐而言,說官僚制已經(jīng)過時(shí)為時(shí)尚早。后工業(yè)化社會(huì)的發(fā)展,確實(shí)有可能拋棄官僚制。筆者以為,在當(dāng)前的社會(huì)科學(xué)理論中,真正能夠?qū)倭胖菩纬商魬?zhàn)的理論還是來自德國人,這就是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在語言哲學(xué)中屬于“獨(dú)白”,交往理性所強(qiáng)調(diào)的“對(duì)話”,有可能突破官僚制的層級(jí)結(jié)構(gòu)。而一旦層級(jí)結(jié)構(gòu)不復(fù)存在,就會(huì)對(duì)官僚制范式形成解構(gòu)。不過,這是今后的事了。一個(gè)時(shí)代只能解決一個(gè)時(shí)代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我們眼下最為欠缺的,正是韋伯倡導(dǎo)的理性精神。 退一萬步說,即使官僚制過時(shí)了,也不等于韋伯的過時(shí)。人類歷史上有許多彌久彌新的思想,值得我們永久敬仰和尊重。例如,雅典城邦早已成為歷史的遺跡,但我們誰也不能說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已經(jīng)被歷史淘汰;春秋時(shí)代是遙遠(yuǎn)的過去,但中國不會(huì)忘記孔子與老子。如果官僚制有進(jìn)入歷史博物館的一天,那也就是韋伯永遠(yuǎn)被人紀(jì)念的新開端。 馬克斯·韋伯其人其事: 馬克斯·韋伯對(duì)關(guān)于報(bào)酬的兩個(gè)神話的終結(jié) |
| 新浪首頁 > 財(cái)經(jīng)縱橫 > 經(jīng)濟(jì)學(xué)人 > 正文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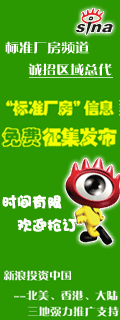 |
| 熱 點(diǎn) 專 題 | ||||
| ||||
| 企 業(yè) 服 務(wù) |
| 股市黑馬:今日牛股! |
| 1.28萬辦廠年利100萬 |
| 名人代言親子裝賺錢快 |
| 小女子開店50天賺30萬 |
| 女人錢,怎么賺 (圖) |
| 06年賺錢項(xiàng)目排行榜! |
| 介入教育事業(yè)年賺百萬 |
| 100萬年薪招醫(yī)藥代理 |
| 品牌折扣店!月賺30萬 |
| 泌尿頑疾——大解放! |
| 拒絕結(jié)腸炎!! 圖 |
| 從此改變哮喘氣管炎!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糖尿病——重大發(fā)現(xiàn)! |
| 高血壓!有了新發(fā)現(xiàn)! |
|
|
|
| |||||||||||||||||||||||||||||||||||||||||||||||||||||||||||||||||||
|
新浪網(wǎng)財(cái)經(jīng)縱橫網(wǎng)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píng)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wù) | 聯(lián)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wǎng)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huì)員注冊(cè) | 產(chǎn)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