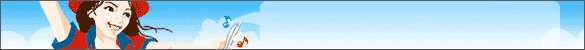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秦暉/演講
商業時代的社會公正,首先就是商業的公正問題。商業公正其實非常簡單,第一,不能搶,在市場經濟中不能用權利謀利益;第二,不能騙,不能搞信息欺詐。商業社會是一個強調競爭的社會,但競爭也要有一個限度,不能“贏家通吃”。我們承認競爭必然有輸贏,在這個問題上要反對平均主義,但不能輸家就輸掉一切。
所以,所謂公正就是:競爭過程是公正的;對競爭過程的后果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控制。簡單來說,商業時代的不公正實際上就是:一,全家通贏;二,贏家通吃。其中,全家通贏可能是不公正最重要的一點。
怎么解決“贏家通吃”的情況呢?這當然需要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來加以解決。現在,有很多人寫文章說福利國家有很多壞處,福利國家普遍處于危機之中。實際上,中國的福利不必達到瑞典的水平,達到美國的水平就不錯了。美國的福利水平在其左派看來很糟糕,在他們眼里,美國被認為是自由放任的社會,是強調自由而不顧平等的社會。但與我們相比,美國的保障水平已經高出很多,這是事實。
底線的迷失
社會公正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底線問題,但即使這樣簡單的底線問題,往往被人為地用理論游戲把它給復雜化。而一經復雜化后,底線就容易迷失。底線的失守當然是權利不受制約而造成的,但在語言形態上,它的迷失的確跟有些人不恰當地把簡單問題復雜化有很大關系。
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的經濟學界存在對交易成本理論的誤用。實際上在亞當·斯密時代,西方經濟學和整個西方經濟社會主要面臨的問題是交易權利的正當性問題,只有在這個問題得到解決時,才有可能提出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問題。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科斯在講到農人和牧人的交易費用時說,只要產權是確定的或者說產權是明晰的,交易費用最小就可以達到效率最優化。科斯講這句話顯然有一個無需說明的前提,不管權利是屬于農人還是牧人的,至少權利是合法的。他沒有假設農人把牧人殺了,或者牧人把農人搶了之類的情況。
但是,交易費用在引進中國時有了很大的變形。
第一,交易權利的合理設立,變成一個用人為剝奪交易權利或者人為膨脹交易權利,來為某些人降低代價的命題。有一些學者說,這種做法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降低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當然可以降低了,因為只準我交易不準你交易,交易費用就極大地降低了。
可這里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以交易成本最低化為由來剝奪一些人的權利,這是不是交易成本本來的意義呢?或者,把不是屬于一些人的東西,不經所有者的認可拿去任意交易,問題的本質是不是交易費用的問題呢?交易費用理論到底應該處理什么問題呢?
打一個比方,假如某甲和某乙在市場上討價還價,吵了半天,交易費用很大而達不成交易,結果某甲把某乙搶了,交易費用當然就下降了,因為不用交易了。
第二,科斯所說的交易費用,實際上是講整個社會維持一個交易系統所要付出的組織成本,決不是指交易某一方所出的價格是不是最低。但我們現在很多人在談交易費用時,實際上講的都是交易的某一方,尤其是強勢一方怎么樣降低費用。
比如,有一位學者曾經用交易費用最小化來證明過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說國家和一家一戶的小農打交道,交易費用太大,因此合作化、人民公社是勢在必行的。但他到印度考察以后得出一個相反結論,說印度經濟之所以搞不過中國,是因為印度的農會、工會太厲害,印度的工人、農民都組織起來以后,統治者和他們打交道的交易費用就大大增加,尤其印度的企業沒有中國有效率,因為印度的工會很強大,資本家和工人打交道的交易費用大幅度增加。
如果說,一家一戶與農民交易,費用很大,而農民組織起來后的交易費用就更大,是不是可以推理出,最好的辦法是把他們都抓起來,放到強制性農莊里去,這樣交易費用就最小了呢?這個推理肯定是不對的。因為現在很多情況下我們討論交易費用,實際上只考慮了一方面出價最低。把農民抓到集體農莊的思路,并沒有考慮到農民為此付出了很大費用,比如,幾千萬人的自由算不算交易費用。
交易費用被解釋到這種地步,問題確實太大了。這把很多交易權利的不正當設定乃至不正當剝奪,都在所謂交易費用最小化這樣一個似乎學術化的話題之下給合法化了。
首要問題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確存在這樣的現象,利益各方的權利被剝奪,由一個權利中心或者說由一些不受制約的權利來配制利益。的確,在一定情況下,這給社會提供了一個穩定的表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一個時期的經濟發展。恰恰這一點,可以解釋中國在前一時期很大一部分的經濟增長,不僅在中國與東歐的經濟改革比較中可以看出這種差異,在中國和印度的經濟比較中也可以看出。
用這種辦法來節約交易費用,交易費用是真正降低了,而這是否變成一筆將來需要用高利償還的高利貸,還很難說。在中國這樣一種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經濟轉軌過程的本質就是交易權利的設定過程。只有在這個過程設定以后,在交易權利設定以后,我們才能談得上所謂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在交易權利的設定過程中,我們現在需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交易權利設定的合法性問題,實際上就是交易權利的公平設定問題。只有在這個問題解決完以后,我們才能進入到科斯他們所討論的那一個層次。
由于中國現階段的社會公正問題是太過程式化的或太過底線化的,因此它還和我們現在所講的很多理論,甚至可以說和所謂公有化和私有化的爭論也沒有多大關系。
實際上,在現代公民社會中,產權問題只有一個原則,就是尊重所有者,不管是在私有化還有公有化的過程里。在美國這樣的私有制國家,很多私有財產通過捐助變成公益基金,從來沒有人說這種行為侵犯了私有化;同時,在很多搞私有化的國家里,私有化都要遵循一定的規定。一位網民說,“私有資產變成公有不是不可以,但要經得私人同意。公有資產變成私有不是不可以,但要經得公眾同意。”
如果私有財產變公有不征得私人同意,公有財產變私有也不征得公眾同意,不管是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者,都會覺得這個社會出了問題,社會主義者會覺得公共財產受到侵犯,自由主義者會覺得私有權利受到侵犯。
其實,在中國爭論公有好還是私有好,私有快點好還是慢點好,往往不得要領。中國現實中存在的最主要的不公正,其實并不是公有還是私有的不公正,而是不管是公有還是私有過程中,不管搞計劃還是市場,總是一部分人吃虧,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我們不必過多強調“左”或者“右”,因為在一個現代社會中,這兩種取向都是存在的,而且這兩種取向在一個現代社會中是可以達成互補的。實際上,現代社會中應該有一種天平效應。在自由競爭過分發展時,就有服務于社會保障的力量——會站出來,在社會保障、福利上拿出較多的舉措。但如果這樣的政策施行到一定程度,人們認為它妨礙了經濟活力、阻礙了投資,那么比較傾向自由放任的人出來——政策就會朝更多的自由去傾斜。這樣一種政策調整,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中都是不斷進行的。
一個好的現代社會,都需要一種利益的正常調整,而且通常來講都是有利于整個社會的。而一個缺少公正的社會,利益總集中于某一個群體,而且這些利益群體通常都和權利有太多聯系。
如果我們不解決這樣的社會公正的問題,所謂的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家這樣的爭論,在中國將成為很奢侈的話題。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在西方中世紀就是效率與平等的問題,這個問題應該說并不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是競爭本身的公正與否的問題,而不是競爭結果到什么程度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首先要做制度性的改進,在這個過程中知識界也應該有一個自省,不能使得一些常識問題經過理論包裝后,不公正被掩蓋了。
(未經演講人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