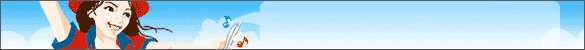ÃÏòƒú║ÖÓ(qu¿ón)¢þ┐╔ÊÈË╬Êã ╚║╝║▓╗─▄¯ìÁ╣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6─Û03È┬18╚ı 15:29 ¢ø(j¿®ng)Ø·(j¿¼)Ë^▓ýê¾(b¿ño) | |||||||||
|
ííííÃÏòƒ/ÃÕ╚A┤¾îW(xu¿ª)Üv╩À¤Á¢╠╩┌ÖÓ(qu¿ón)└¹Í¸¾wÊÔÍ¥▒ÏÝÜ╩▄Á¢ÎÍÏ íííí╬ÊÅ─ýû½I(xi¿ñn)╠´¤╚╔·îªíÂ╬´ÖÓ(qu¿ón)À¿íÀÁ─┼·Èuıfãíú ííííç°Ëð┘Y«a(ch¿ún)(ãõîì(sh¿¬)▓╗âH╩Ãç°Ëðú¼Ê▓░³└¿╔þà^(q¿▒)Á╚ãõ╦¹¯Éð═╣½╣▓┘Y«a(ch¿ún))▒╗─│ð®╚╦Êðı╠╠ÏÖÓ(qu¿ón)ı╝×Ú╝║Ëðú¼▀@éÇ(g¿¿)¼F(xi¿ñn)¤¾║┴ƒoÊ╔åû╩Ã┤µÈ┌Á─ú¼Â°ÃÊ╬Ê10ÂÓ─ÛÚgÊ▓ÂÓ┤╬Ív▀^▀@éÇ(g¿¿)åû¯}ú¼ÍvÁ├øQ▓╗▒╚└╔
íííí╦¨ÊÈ╬ÊËXÁ├ú¼îª«a(ch¿ún)ÖÓ(qu¿ón)Á─ÎÍÏãõîì(sh¿¬)Å─üÝ¥═ø]Ëð╣½╦¢Í«ÀÍíú╩└¢þ╔¤Í╗Ëð├³┴¯¢ø(j¿®ng)Ø·(j¿¼)ç°╝Ê¢¹Í╣╦¢ËðÍãú¼Å─üÝÊ▓ø]Ëð╩ðê÷¢ø(j¿®ng)Ø·(j¿¼)ç°╝Ê¢¹Í╣╣½ËðÍãÁ─íú═¼ÿËú¼╩└¢þ╔¤Í╗Ëð├³┴¯¢ø(j¿®ng)Ø·(j¿¼)ç°╝Ê─▄ë‗╚╬ÊÔäâèZ╦¢╚╦Ïö(c¿ói)«a(ch¿ún)ú¼Å─üÝÊ▓ø]Ëð├±Í¸╩ðê÷¢ø(j¿®ng)Ø·(j¿¼)ç°╝Ê─▄ë‗ÎîÖÓ(qu¿ón)┘F╚╬ÊÔ═Á▒I░Èı╝╣½╣▓┘Y«a(ch¿ún)Á─íú╬ÊéâÁ─é¸├¢È°ê¾(b¿ño)Á└▀^ú¼ÜWÍÌ─│ç°▓┐ÚLâHÊ‗╣½äı(w¿┤)│÷ÈLΰ├±║¢(▓╗╩ÃîúÖC(j¿®)╗‗░³ÖC(j¿®))┼ô╬╗ËÔÁ╚ú¼¥═▒╗ÎÀ¥┐°Ìo┬ÜÁ─╩┬ú¼╚þ┤╦ç└(y¿ón)©±Á─╣½╣▓└¹Êµ▒úÎo(h¿┤)ú¼È┌ýû½I(xi¿ñn)╠´╦¨Í^Á─í░╠KÂÝ├±À¿é¸¢y(t¿»ng)í▒¤┬─▄ë‗ÈO(sh¿¿)¤Ùåßú┐╚þ╣¹╬Êéâ¼F(xi¿ñn)È┌Ëð╚╦ıµı²ÛP(gu¿ín)ð─Ïö(c¿ói)«a(ch¿ún)▒╗ÃÍÀ©Á─åû¯}ú¼░³└¿╣½╣▓┘Y«a(ch¿ún)▒╗ÃÍÀ©Á─åû¯}ú¼Ê▓░³└¿╦¢╚╦┘Y«a(ch¿ún)▒╗ÃÍÀ©Á─åû¯}ú¼─Ã├┤╬ÊéâÁ─«a(ch¿ún)ÖÓ(qu¿ón)▒úÎo(h¿┤)ú¼░³└¿«a(ch¿ún)ÖÓ(qu¿ón)┴óÀ¿Á─╣ñθ¥═æ¬(y¿®ng)Èô┬õîì(sh¿¬)íú°ÃÊ╦³Á─È¡ät¥═æ¬(y¿®ng)Èô╩Ãã¢Á╚▒úÎo(h¿┤)©¸ÀNÏö(c¿ói)«a(ch¿ún)íú╝╚êÈ(ji¿ín)øQ▒úÎo(h¿┤)╣½▒è╣▓ËðÏö(c¿ói)«a(ch¿ún)├ÔÈÔ▓╗╩▄╣½▒èÍã╝sÁ─éÇ(g¿¿)╚╦╗‗ðí╝»êF(tu¿ón)╦¢ÎÈÃÍ═╠ú¼Ê▓êÈ(ji¿ín)øQ▒úÎo(h¿┤)╦¢╚╦Ïö(c¿ói)«a(ch¿ún)├ÔÈÔÊÈ╣½╣▓└¹Êµ×Ú├¹Á─▓╗╩▄Íã╝sÖÓ(qu¿ón)┴ªÁ─ÃÍÀ©íú ííííîì(sh¿¬)ÙH╔¤ú¼È┌Ã░─ÛÁ─«a(ch¿ún)ÖÓ(qu¿ón)ËæıôÍðú¼¥W(w¿úng)╔¤ËðÊ╗éÇ(g¿¿)╠¹ÎË╬ÊËXÁ├ÍvÁ─╩Ã┤¾îì(sh¿¬)ÈÆú¼░Ðåû¯}Ív═©┴╦íúÈô┘Nıfú¼▀@éÇ(g¿¿)åû¯}ÍvãüÝ║▄║åå╬ú║╦¢ËðÏö(c¿ói)«a(ch¿ún)▓╗╩Ã▓╗─▄╣½Ëð╗»ú¼▒╚╚þıf╚╬║╬╬¸À¢ç°╝ÊÂ╝╩Ã╣─ä¯(l¿¼)¥ÞÍ·Á─ú¼Â°ÃÊ¥ÞÍ·╣½ÊµÜvüÝ¥═╩▄Á¢ı■▓▀ͺ│Íú¼Á½╩Ã─ÒÁ├╦¢╚╦═¼ÊÔú╗╣½╣▓┘Y«a(ch¿ún)Ê▓▓╗╩Ã▓╗─▄╦¢Ëð╗»ú¼Á½╩Ã─ÒÁ├╣½▒è═¼ÊÔú¼Á├Ëð├±Í¸│╠ð‗ú¼Îî╣½▒è╬»═ðíó▒O(ji¿ín)¢íóÍã╝s║═àó┼cíúÁ½╩ÃÈ┌╬Êéâ▀@â║ú¼╩Τ╚╠ÄÍ├╦¢ËðÏö(c¿ói)«a(ch¿ún)┐╔─▄▓╗╠½¯Ö╦¢╚╦ÊÔÍ¥í¬í¬▒╚╚þıfı¸ÁÏ▓▀wú¼╣┘åT¤Ù─├▀^üÝ¥═─├▀^üÝíú°╠ÄÍ├╣½╣▓Ïö(c¿ói)«a(ch¿ún)ËÍ╩ä٢oıl¥═¢oılú¼╝╚ƒo├±Í¸┴óÀ¿ú¼ËÍ╚▒╣½▒è▒O(ji¿ín)¢ú¼«ö(d¿íng)╚╗¥═ò■Èý│╔ÍTÂÓ▒Î▓ííú¼F(xi¿ñn)È┌Ëðð®╚╦╩┐║▄▓╗ØMÊÔ╣½╣▓┘Y«a(ch¿ún)▒╗ÃÍÀ©ú¼Â°┴ÝÊ╗ð®╚╦▓╗ØMÊÔ╦¢ËðÏö(c¿ói)«a(ch¿ún)▒╗ÃÍÀ©ú¼ãõîì(sh¿¬)▀@Ëð╩▓├┤├¼Â▄─Ïú┐â╔ı▀Á─╣▓═¼©¨È┤¥═╩ÃÖÓ(qu¿ón)┴ª▓╗╩▄Íã╝síú╚þ╣¹╗Ï▒▄▀@éÇ(g¿¿)îì(sh¿¬)┘|(zh¿¼)ú¼└¤╩ÃÊ╗ð®╚╦×ÚÃÍÀ©╦¢«a(ch¿ún)ÌqÎo(h¿┤)ú¼┴ÝÊ╗ð®╚╦×ÚÃÍÀ©╣½«a(ch¿ún)ÌqÎo(h¿┤)ú¼─Ã¥═▓╗╣▄╩▓├┤Ïö(c¿ói)«a(ch¿ún)Â╝│╔┴╦ÖÓ(qu¿ón)┴ªÁÂ┘̤┬Á─¶~╚Ô┴╦íú íííí╬ÊÈ°▒╚˸ú¼▓╗╩▄Íã╝sÁ─ÖÓ(qu¿ón)┴ª╩ÃË├ξ╩Í░Ð░┘ðıÁ─╦¢«a(ch¿ún)─├▀M(j¿¼n)ç°Äýú¼ËÍË├ËÊ╩Í░Ðç°ÄýÁ─û|╬¸┼¬▀M(j¿¼n)ÖÓ(qu¿ón)┘FÁ─╦¢─Êíú╬ÊËXÁ├╬ÊéâÍvÀ¿Í╬ú¼Íví░║├Á─╩ðê÷¢ø(j¿®ng)Ø·(j¿¼)í▒ú¼¥═╩Ãʬ░Ð▀@â╔Í╗╩Í└ªÎíú¼Â°▓╗─▄Í╗ÂóÊ╗▀à╝┘ÈO(sh¿¿)╦³╩ÃéÇ(g¿¿)¬Ü(d¿▓)▒█Üê╝▓ú¼©³▓╗─▄í░ξËÊ┼╔í▒©¸×ÚÊ╗▒█╦╔¢ëú¼À±ät▀@éÇ(g¿¿)åû¯}¥═▓╗┐╔─▄¢ÔøQíú°ÃÊ▀@â╔ı▀Ê▓▓╗ÿï(g¿░u)│╔├¼Â▄íúø]Ëð╚╬║╬Ê╗éÇ(g¿¿)╩ðê÷¢ø(j¿®ng)Ø·(j¿¼)ç°╝Êú¼▓╗╣▄╩Ã┤¾ÛæÀ¿¤ÁÁ─▀Ç╩ÃËó├└À¿¤ÁÁ─ú¼╦³Á─Ïö(c¿ói)«a(ch¿ún)▒úÎo(h¿┤)À¿ò■═¼ÊÔ╣½╣▓Ïö(c¿ói)«a(ch¿ún)┐╔ÊÈÎî┐┤╩Ïı▀×E═Áú¼©¨▒¥¥═ø]Ëð▀@ÿËÁ─åû¯}íú╦¨ÊÈú¼╚þ╣¹ıf╬ÊéâÁ─╣½╣▓Ïö(c¿ói)«a(ch¿ún)├µ┼RÍ°┴¸╩ºÁ─åû¯}ú¼─â^▓╗╩ÃÊ‗?y¿ñn)Ú╬ÊéâîªÀÃ╣½Ï?c¿ói)«a(ch¿ún)▒úÎo(h¿┤)▀^ÀÍ┴╦ú¼Â°╩Ã╬ÊéâÁ─ÖÓ(qu¿ón)┴ª▓╗╩▄Íã╝s▀^ÀÍ┴╦íú íííí▀@└´¥═╠ß│÷┴╦Ê╗éÇ(g¿¿)åû¯}ú¼È┌Ê╗éÇ(g¿¿)À¿Í╬╔þò■ú¼ƒoıô╣½«a(ch¿ún)╦¢«a(ch¿ún)ú¼ç°╝ÊÂ╝▒ÏÝÜÎÍÏÖÓ(qu¿ón)└¹Í¸¾wÁ─ÊÔÍ¥ú║θ×Ú╦¢ËðÏö(c¿ói)«a(ch¿ún)ãõÖÓ(qu¿ón)└¹Í¸¾w¥═╩ÃéÇ(g¿¿)╚╦ú¼╣½╣▓Ïö(c¿ói)«a(ch¿ún)Á─ÖÓ(qu¿ón)└¹Í¸¾w¥═╩Ã╣½▒è╗‗╣½▒è┤·└Ý╚╦íú«ö(d¿íng)╚╗▀@éÇ(g¿¿)╣½▒è▓╗╩Ã├±┤ÔÊÔ┴x╔¤Á─╣½▒èú¼Â°╩ÃʬËð├±Í¸┴óÀ¿│╠ð‗Á─╣½▒èíú íííí╚║╝║ÖÓ(qu¿ón)¢þʬÀÍÃÕ íííí┤¾╝ÊÂ╝ͬÁ└ú¼░l(f¿í)▀_(d¿ó)╩ðê÷¢ø(j¿®ng)Ø·(j¿¼)ç°╝ÊÁ─┴óÀ¿╗¨▒¥╔¤╩ÃË╔Îhò■▀M(j¿¼n)ððÁ─ú¼▀@éÇ(g¿¿)Îhò■¥═╩Ã┤·▒Ý╣½▒èÁ─┴óÀ¿ÖC(j¿®)ÿï(g¿░u)ú¼Á½╩Ã╦³▓ó▓╗╩ä¹£þéÇ(g¿¿)ðÈÁ─í░ÅVê÷┐±Ügí▒ú¼┐┐ılÁ─╔ñÎË┤¾ú¼║░│÷üÝ¥═╩ÃÀ¿íú íííí▀@└´¥═╠ßÁ¢Ê╗éÇ(g¿¿)╩▓├┤¢ðí░À¿Í╬í▒Á─åû¯}ú┐Íðç°ËðÊ╗éÇ(g¿¿)鸢y(t¿»ng)¥═╩âø(j¿®ng)│úıäÀ¿Í╬ú¼Á½╩ÃÊ╗ıäÀ¿¥═ıäÁ¢À¿╝Êú¼Â°▓╗╩ÃıäÀ¿Í╬íúÀ¿╝ÊÁ─Ê╗ð®ÈÆ╝┤╩╣╩ÃÈ┌╬─╗»┤¾©´├³─Ã├┤╗ýüyÁ─á¯æB(t¿ñi)¤┬ú¼Ê▓╚È╚╗È┌îì(sh¿¬)ððú¼¥═╩Ã╬─©´òr(sh¿¬)¢ø(j¿®ng)│úÍvÁ─ú║í░Í╗ÈS─ÒéâÊÄ(gu¿®)ÊÄ(gu¿®)¥Ï¥Ïú¼▓╗ÈS─ÒéâüyıfüyäËí▒íú▀@éÇ(g¿¿)╦¨Í^Á─í░ÊÄ(gu¿®)ÊÄ(gu¿®)¥Ï¥ÏíóüyıfüyäËí▒ú¼îì(sh¿¬)ÙH╔¤╩Ãí░Í╗ÈSͦ╣┘À┼╗íó▓╗ÈS░┘ðı³c(di¿ún)ƒ¶í▒íú ííííÈ┌«a(ch¿ún)ÖÓ(qu¿ón)┴óÀ¿╔¤ú¼À¿Í╬▀Ç╩ÃÀ¿╝Êú¼à^(q¿▒)äeÈ┌──└´─Ïú┐╬ÊËXÁ├ú¼ãõîì(sh¿¬)Íðç°╚╦äéäé¢ËË|¢³┤·åó├╔╦╝│▒Á─òr(sh¿¬)║‗ú¼Ëðð®▒╚¦^┬ö├¸Á─Íðç°╚╦¥═ÊТø(j¿®ng)ÍvÁ├║▄═©ÅÏ┴╦ú¼▀@¥═╩Ãç└(y¿ón)Å═(f¿┤)È┌À¡ÎgíÂOn LibertyíÀÁ─òr(sh¿¬)║‗äô(chu¿ñng)ÈýÁ──ÃéÇ(g¿¿)├¹È~í¬í¬í░╚║╝║ÖÓ(qu¿ón)¢þí▒íú ííííîì(sh¿¬)ÙH╔¤╚þ¢±ÈSÂÓıfÀ¿Â╝╦ã╩ðÀÃÁ─ú¼▒╚╚þıfËð╚╦Íví░╬¸À¢í▒╬─╗»ÎÈ╣┼¥═╠ÏäeÍÏÊòéÇ(g¿¿)¾w͸┴xú¼║├¤±í░û|À¢í▒╬─╗»¥═╠ÏäeÍÏÊò╝»¾w͸┴xíúÁ½╩Ã╬ÊéâͬÁ└ú¼ãõîì(sh¿¬)╔þò■͸┴xíó╣▓«a(ch¿ún)͸┴x▒¥╔ÝÊ▓╩Ã╬¸À¢üÝÁ─û|╬¸ú¼╦¨ÊÈËÍËð╚╦ıf╬¸À¢╬─╗»ÍðÊ▓Ëð╝»¾w͸┴xÁ─Ê╗ͺíú«ö(d¿íng)─Û╬Êéâç°╝Ê©Òí░Ê╗┤¾Â■╣½í▒Á─òr(sh¿¬)║‗ú¼║ú═Ô©█┼_Á─ÈSÂÓð┬╚Õ╝Ê▓╗¥═Åè(qi¿óng)ı{(di¿ño)╚Õ╝Ê͸ÅêÎÈË╔¢ø(j¿®ng)Ø·(j¿¼)ú¼▓óÊÈ┤╦üÝ┼·Èuç°â╚(n¿¿i)Á─▀@ÀNá¯æB(t¿ñi)åßú┐Ë┌╩üF(xi¿ñn)È┌ËÍËð╚╦ıfç°═ÔÁ─ÎÈË╔͸┴x╠½Åè(qi¿óng)ı{(di¿ño)éÇ(g¿¿)╚╦͸┴xú¼Â°╔þò■͸┴xËÍ╠½Åè(qi¿óng)ı{(di¿ño)╝»¾w͸┴xú¼╬Êéâ?n¿¿i)Õ╝Ê¥═╠ÏäeÍðË╣ú¼╣½╦¢╝µ¯Öíú╬ÊËXÁ├▀@éÇ(g¿¿)ıfÀ¿Ê▓║▄│╔åû¯}íúãõîì(sh¿¬)╬¸À¢Å─üÝ¥═▓╗╚▒Àª¢ø(j¿®ng)Áõ╔þò■͸┴x║═¢ø(j¿®ng)ÁõÎÈË╔͸┴xÍ«ÚgÁ─©¸ÀN┴¸┼╔ú¼░³└¿Íðξ┼╔íóÍðËÊ┼╔║═ÍðÍð┼╔íú╬ÊéâÊ▓ͬÁ└ú¼│²┴╦í░©´├³í▒╗‗í░À┤©´├³í▒Á─╠Ï╩Ôòr(sh¿¬)ã┌ú¼È┌Ê╗░Òı²│úÃÚør¤┬ú¼Å─üÝÁ├ä¦Á─Â╝╩ÃÍðË╣┴¸┼╔ú¼Íðξ┼╔║═ÍðËÊ┼╔íúË╚ãõ╩Ã╬Êéâ═¿│úÍví░╬¸À¢í▒ίÁõð═Á─ÄÎéÇ(g¿¿)ç°╝Êú¼¤±Ëó├└ú¼Ëóç°Á─▒ú╩ϳhíó╣ñ³h¤ÓîªË┌ÈSÂÓÜWÛæç°╝ÊÁ─ξËÊ┼╔üÝıfú¼¥═╩ÃÍðËÊú¼Íðξú╗°├└ç°Á─╣▓║═³h▓╗¤±Ëóç°▒ú╩ϳh─Ã├┤ËÊú¼├±Í¸³hÊ▓▓╗╚þ╣ñ³h─Ã├┤ξú¼â╔³h¢ÈÈ┌▒ú╩ϳh║═╣ñ³hÍ«Úgú¼┐╔ÊÈ¢ðÍðÍð┼╔┴╦íú─Ã├┤╦¹éâÙyÁ└¥═─Ã├┤ÿOÂ╦╝»¾w͸┴x╗‗ÿOÂ╦éÇ(g¿¿)╚╦͸┴xú┐╦¹éâ¥═▓╗╣½╦¢╝µ¯Öú┐ íííí╦¨ÊÈ╬ÊËXÁ├ú¼ãõîì(sh¿¬)ÛP(gu¿ín)µI▓╗È┌Ë┌╩▓├┤éÇ(g¿¿)╚╦͸┴x╗‗╝»¾w͸┴x╗‗â╔ı▀Á─ı█Íðú¼Â°È┌Ë┌ç└(y¿ón)Å═(f¿┤)ÍvÁ──Ã¥õÈÆú¼¥═╩Ãí░╚║╝║ÖÓ(qu¿ón)¢þí▒ʬÀÍÃÕíú╣½╣▓¯I(l¿½ng)Ë‗Üw╣½╣▓¯I(l¿½ng)Ë‗ú¼╦¢╚╦¯I(l¿½ng)Ë‗Üw╦¢╚╦¯I(l¿½ng)Ë‗ú¼Ã░ı▀═¿ðð├±Í¸ÊÄ(gu¿®)ätú¼║¾ı▀═¿ððÎÈË╔ÊÄ(gu¿®)ätú¼▀@éÇ(g¿¿)ÖÓ(qu¿ón)¢þ╩ÃÊ╗¿ʬÀÍÃÕÁ─íúÍ┴Ë┌ÀÍÁ─¢Y(ji¿ª)╣¹ã½¤‗Ë┌í░┤¾╝║ðí╚║í▒Ê╗ð®ú¼▀Ç╩Ãí░┤¾╚║ðí╝║í▒Ê╗ð®ú¼Á╣╩Ã┤╬ʬåû¯}íú°╬Êéâ¼F(xi¿ñn)È┌ί┤¾Á─åû¯}╩Ã▀@â╔ı▀┼¬│╔Ê╗ÕüÍÓú¼╚║╝║╗ý¤²íó╚║╝║▓╗ÀÍú¼╔§Í┴╚║╝║¯ìÁ╣ú¼í░╣½ÖÓ(qu¿ón)í▒╚╬ÊÔÃÍÀ©╦¢╚╦¯I(l¿½ng)Ë‗ú¼Â°╣½╣▓¯I(l¿½ng)Ë‗ËÍ▒╗éÇ(g¿¿)╚╦íó▒╗ðí╝»êF(tu¿ón)íó▒╗Ê╗ð®▓╗╩▄Íã╝sÁ─╚╦╦¨░Ð│Ííú╣½╣▓¯I(l¿½ng)Ë‗ø]Ëð╣½╣▓ðÈú¼╦¢╚╦¯I(l¿½ng)Ë‗ø]Ëð╦¢╚╦ðÈú¼╚║Ë‗ƒo├±Í¸ú¼╝║Ë‗ƒoÎÈË╔ú¼▀@╩Ãί┤¾Á─åû¯}íú íííí«ö(d¿íng)╚╗ú¼Ê¬?ji¿úng)ØÀÍ╚║╝║Ö?qu¿ón)¢þú¼▀@éÇ(g¿¿)ÖÓ(qu¿ón)¢þÊ▓╩ÃäËæB(t¿ñi)Á─íúÊ‗?y¿ñn)Ú╚╦¯É╔·╗¯Á─À¢À¢├µ├µÍðú¼Á¢ÁÎ──ð®î┘Ë┌╦¢╚╦¯I(l¿½ng)Ë‗íóʬÏ×ÅÏÎÈË╔È¡ätú¼──ð®î┘Ë┌╣½╣▓¯I(l¿½ng)Ë‗ú¼Ê¬Ï×ÅÏ├±Í¸íó╝┤╣½╣▓▀xô±È¡ätú¼æ¬(y¿®ng)ÈôıfÈ┌║▄ÂÓÀ¢├µ╚╦éâÊТø(j¿®ng)╚íÁ├┴╦╣▓ÎRú¼¥═Íväé▓┼ıfÁ─Ïö(c¿ói)«a(ch¿ún)åû¯}░╔ú¼Ùm╚╗Ëð╚╦ıfξ┼╔ð└┘p╣½ËðÍãú¼ËÊ┼╔ð└┘p╦¢ËðÍãí¬í¬¼F(xi¿ñn)È┌▓╗Ê╗¿╩Ã▀@ÿË┴╦ú¼Á½╩ÃÊÈÃ░╩ÃËðÁ─ú¼▒╚╚þËóç°╣ñ³h║▄ÚLÊ╗Â╬òr(sh¿¬)ã┌ú¼░³└¿ê╠(zh¿¬)ı■Á─¹£┐╦╠ã╝{òr(sh¿¬)ã┌Ê╗Í▒╩Ã͸ÅêöU(ku¿░)┤¾ç°Ëð╗»Á─(¼F(xi¿ñn)È┌╦¹éâÊТø(j¿®ng)▓╗È┘▀@ÿË͸Åê┴╦)ú¼Á½╝┤╩╣╣ñ³hÊ▓▓╗ò■͸ÅêÊÈ╬Êéâ▀@ÀNı¸ÁÏ▓▀wÁ─À¢╩¢üÝÃÍı╝└¤░┘ðıÁ─╦¢ËðÏö(c¿ói)«a(ch¿ún)ú╗À┤▀^üÝıfú¼▒ú╩ϳh«ö(d¿íng)╚╗╩Ã͸Åê╦¢Ëð╗»ú¼▀@╩Ãø]Ëðåû¯}Á─ú¼Á½╝┤╩╣╩Ã▒ú╩ϳhÊ▓▓╗ò■┘Ø│╔í░ıã╔Îı▀╦¢ı╝┤¾´êÕüí▒╩¢Á─ðð×Úíú¥═╩Ãıfú║╠ÄÍ├╦¢«a(ch¿ún)ʬ╦¢╚╦═¼ÊÔú¼╠ÄÍ├╣½«a(ch¿ún)ʬ╣½▒è═¼ÊÔú¼È┌ÎÍÏÖÓ(qu¿ón)└¹Í¸¾wÁ─ÊÔÍ¥À¢├µú¼╦³éâ╩ÃÊ╗Í┬Á─íú ííííÁ½╩Ãú¼¢³┤·╩ðê÷¢ø(j¿®ng)Ø·(j¿¼)ÐË└m(x¿┤)Á¢¼F(xi¿ñn)È┌ÊТø(j¿®ng)â╔íó╚²░┘─Ûú¼╚╦¯Éðð×ÚÍðÁ─┤_ËðÊ╗ð®¯I(l¿½ng)Ë‗Á¢ÁÎ╩Ã╦¨Í^Á─╝║Ë‗▀Ç╩Ã╚║Ë‗ú¼╗‗ı▀╣½╣▓¯I(l¿½ng)Ë‗▀Ç╩ÃéÇ(g¿¿)╚╦¯I(l¿½ng)Ë‗ú¼╚È╚╗╩Ã▒╚¦^─ú║²Á─ú¼╗‗ı▀ıf╩Ã╗Ê╔½Á─íú▒╚╚þıfÄ═Í·╚§ı▀Á─åû¯}ú¼Î¯¢³╚╦éâ─©´Á─Í├Ê╔ú¼║▄ÍÏʬÁ─¥═╩ÃÛP(gu¿ín)Ë┌╣½╣▓À■äı(w¿┤)ú¼ÛP(gu¿ín)Ë┌╔þò■▒úı¤Á─åû¯}íú╚Ñ─Ûú¼║▄ÂÓ╚╦Â╝ͩσ(z¿ª)╬ÊéâÁ─¢╠˲║═ðl(w¿¿i)╔·╣½╣▓À■äı(w¿┤)╗¼ã┬ú¼Ê²ã┴╦ç└(y¿ón)ÍÏÁ─åû¯}íúί¢³àÃ¥┤¡I¤╚╔·È┌â╔ò■Íð¥═╠ß│÷ú¼ıf¢╠˲║═ðl(w¿¿i)╔·╩Ã▓╗╩ÃÂ╝î┘Ë┌╣½╣▓À■äı(w¿┤)¯I(l¿½ng)Ë‗ú¼╩Ã▒ÏÝÜʬ╝Ü(x¿¼)ÀÍÁ─ú¼¢^▓╗─▄╗\¢y(t¿»ng)▒ÝæB(t¿ñi)ú¼ıf╦¨Ëð¢╠˲¥═╩Ã╣½╣▓¯I(l¿½ng)Ë‗ú¼╦¨Ëððl(w¿¿i)╔·¥═╩Ã╣½╣▓¯I(l¿½ng)Ë‗íúîì(sh¿¬)ÙH╔¤ðl(w¿¿i)╔·Ê▓║├íó¢╠˲Ê▓║├ú¼─╦Í┴ãõ╦¹Á─Ê╗ð®À■äı(w¿┤)Ê▓║├ú¼═¨═¨╩ÃÀÍîË┤╬Á─íú▒╚╚þ╬Êéâ┤¾¾wÂ╝│ðıJ(r¿¿n)╗¨ÁA(ch¿│)¢╠˲æ¬(y¿®ng)Èô╩Ã╣½╣▓¯I(l¿½ng)Ë‗ú¼Á½╩é▀Á╚¢╠˲╩Ã▓╗╩Ã╣½╣▓¯I(l¿½ng)Ë‗ú¼▀@¥═╩ÃËðáÄÎhÁ─íúÍT╚þ┤╦¯ÉÁ─áÄıôò■║▄ÂÓú¼╚þ╣¹╬Êéâ¥▀¾wËæıôåû¯}ú¼░³└¿ðl(w¿¿i)╔·ú¼╦³Ê▓Ëð╗¨ÁA(ch¿│)ßt(y¿®)»ƒ║═╦¨Í^â×(y¿¡u)┘|(zh¿¼)ßt(y¿®)»ƒÁ─à^(q¿▒)äeú¼▀ÇËð─Ãð®©▀║─┘M(f¿¿i)Á─¥S│ÍðÈÍ╬»ƒåû¯}Á╚Á╚íú▀@ð®À■äı(w¿┤)╩Ã╚║Ë‗▀Ç╩Ã╝║Ë‗ú¼Â╝╩ÃðÞʬËæıôÁ─íú íííí°ÃÊÈ┌▀@ÀNËæıôÍðîì(sh¿¬)ÙH╔¤ıµı²Á─ÀÍãþ╬┤▒Ï¥═╩ÃÁ└┴xÀ¢├µÁ─ÀÍãþú¼╚ÈÊÈ▒úÎo(h¿┤)╚§ı▀×Ú└²ú¼È┌░l(f¿í)▀_(d¿ó)ç°╝Êί╗¨▒¥Á─▒úı¤æ¬(y¿®ng)Èô╩Ã╣▓ÎR┴╦ú¼Á½╩Ã╦«ã¢©▀Ê╗³c(di¿ún)Á─ú¼▒╚╚þıf─▄ë‗▀^╔¤ËðÎç└(y¿ón)Á─╔·╗¯ú¼▀@éÇ(g¿¿)í░ËðÎç└(y¿ón)Á─╔·╗¯í▒Á¢ÁÎ╩Ã╩▓├┤ÿ╦(bi¿ío)£╩(zh¿│n)ú¼«ö(d¿íng)╚╗¥═ò■Ëð▓╗═¼Á─ÊÔÊèíúÈ┌─Ãð®ç°╝Êú¼¤±╬Êç°▀^╚ÑÁ─À¿╝Ê─ÃÿË▓╗âHÀ┤îª▒úÎo(h¿┤)©F╚╦ú¼Â°ÃÊ╣½╚╗͸Åêôî¢┘íóæ═┴P©F╚╦Á─͸Åê╗¨▒¥ÊТø(j¿®ng)¤¹╩ºú¼▒úÎo(h¿┤)╚§ı▀θ×ÚÊ╗éÇ(g¿¿)Á└Á┬├³¯}╚þ¢±╩Ã║▄╔┘╚╦ò■À┤îªÁ─ú¼à^(q¿▒)äeÈ┌Ë┌Ëðð®╚╦ıJ(r¿¿n)×Ú▀@╩Ã╚║Ë‗ú¼æ¬(y¿®ng)ÈôË╔├±Í¸ç°╝ÊË├©▀ÂÉ╩ıíó©▀©ú└¹Á─À¢╩¢ú¼¥═╩ÃË├╣½╣▓▀xô±Á─À¢╩¢üÝ¢ÔøQ▀@ð®åû¯}ú╗°┴ÝÊ╗ð®╚╦¥═͸Åê▀@æ¬(y¿®ng)Èô╩Ã╝║Ë‗ú¼╩ÃéÇ(g¿¿)╚╦ÎÈÈ©íó╣½Êµ┤╚╔ãíó╝┤╦¨Í^ÀÃı■©«ÀÃáI└¹¢M┐ùíóÁ┌╚²▓┐ÚT╗‗ͥȩ▓┐ÚTÁ─╩┬íúÈ┌╦¹éâ─Ã└´ú¼─│éÇ(g¿¿)í░ËÊ┼╔í▒È┌À┤îªöU(ku¿░)Åê╣½╣▓¯I(l¿½ng)Ë‗Á─═¼òr(sh¿¬)ú¼╦¹▒¥╚╦Ê▓ÈS¥═╩ÃéÇ(g¿¿)┤╚╔ã╝Êú¼È┌Á└Á┬╔¤─Ò▓╗─▄ıf╦¹╩ÃéÇ(g¿¿)└õ┐ßÁ─╚╦íúÁ½╩ÃÈ┌îW(xu¿ª)└Ý╔¤Á─┤_Ëð╚║╝║ÖÓ(qu¿ón)¢þÁ─í░¢þí▒ȧ├┤äØÁ─åû¯}íú íííí╬ÊıJ(r¿¿n)×Úú¼Ëðð®¯I(l¿½ng)Ë‗Á─┤_║▄Ùy¢^îªıfÃÕ╚þ║╬äØÀÍíú╬ÊÈ°¢ø(j¿®ng)┼e▀^▀@├┤Ê╗éÇ(g¿¿)═¿╦Î└²ÎËú¼╚þ╣¹Ëð╚╦È┌─Ò·▀àÀ┼▒Ì┼┌ú¼╬ʤÙ╚╬║╬Ê╗éÇ(g¿¿)Ëð└ÝÍÃËðÎç└(y¿ón)Á─╚╦Â╝ò■æì┼¡íú▀@¥═╩Ãıfú¼├┐éÇ(g¿¿)╚╦æ¬(y¿®ng)ÈôôÝËð·Âõ▀àÊ╗¿ÀÂç·â╚(n¿¿i)Á─í░░▓ýoÖÓ(qu¿ón)í▒ú¼Àâø(j¿®ng)È╩ÈS─Ò▓╗─▄╚╬ÊÔüÝ‗}ö_╬Êú╗Á½╩Ã╚þ╣¹È┌¥ÓÙx╬ÊÊ╗ú├ÎÊÈ═ÔÁ─Ê╗éÇ(g¿¿)╣½╣▓ê÷╦¨─▄▓╗─▄À┼▒Ì┼┌ú¼▀@╬Ê¥═╣▄▓╗┴╦ú¼▒ÏÝÜ╩Ã╣½▒è▀xô±Á─╚║Ë‗┴╦íúÁ½╩Ãâ╔ı▀Á─¢þ¤ÌÁ¢ÁÎäØÈ┌──└´©³║¤▀mú┐5├Îú¼10├Î▀Ç╩Ã20├Îú┐┐Í┼┬║▄ÙyËðÿ╦(bi¿ío)£╩(zh¿│n)┤░©íú íííí╝┤▒Òã¢òr(sh¿¬)ÃÕ│■Á─¢þ¤Ìú¼ÀÃ│úÃÚ¥│Ê▓┐╔─▄╩╣Í«©─Îâú¼└²╚þí░╠®╠╣─ß┐╦╣╩╩┬í▒Íðú¼░┤│ú└Ý╠Ë╔·▒¥╩Ã├┐éÇ(g¿¿)╚╦Â╝ËðÁ─ÖÓ(qu¿ón)└¹ú¼Á½╩ÃÈ┌─ÃÀNÃÚør¤┬¥═Ëð╚╦╠ß│÷ú¼Â°ÃÊ╣½▒è═¼ÊÔ┴╦í░ïD╚µâ×(y¿¡u)¤╚í▒Á─ÀÍ┼õÍãú¼îì(sh¿¬)ÙH╔¤╩Ã░Ð╠Ë╔·Îâ│╔í░╣½╣▓▀xô±í▒Á─╚║Ë‗┴╦íú▀@Ê▓ÈS▓óÀÃí░͸┴xí▒°╝âî┘ÃÚ¥│╦¨Í┬ú¼▓╗─▄┼┼│²▀@ð®╚╦▒¥╔ÝÊ▓╩ÃÎÈË╔͸┴xı▀ú¼Á¢┴╦░Â╔¤╦¹éâ═Û╚½┐╔─▄͸ÅêÎÈË╔©éáÄú¼Á½╩ÃÈ┌╬ú┤¼╔¤╦¹éâàsÀ┼ùë┴╦©éáÄ╠Ë╔·ÖC(j¿®)ò■íú ííííÁ½ƒoıô╚þ║╬ú¼ËðÊ╗³c(di¿ún)ÀÃ│ú├¸┤_ú║▒M╣▄í░ÖÓ(qu¿ón)¢þí▒┐╔ÊÈË╬Êãú¼Á½í░╚║╝║í▒▓╗─▄¯ìÁ╣íú°ÃÊäØ×Ú╚║Ë‗Á─╩┬¥═ʬÎ÷Á¢├±Í¸ú¼äØ×Ú╝║Ë‗Á─╩┬¥═ʬÎÍÏÎÈË╔ú¼â╔ı▀▒ÏÝÜÀÍÃÕ│■íú¥═¤±╬Êäé▓┼ÍvÁ─ú¼È┌Ä═Í·╚§ı▀Á─åû¯}╔¤╬¸À¢ËÊ┼╔░Ð╦³┐┤θ╝║Ë‗ú¼Î¾┼╔┐┤θ╚║Ë‗ú¼Í¸ÅêÊÈ©ú└¹ç°╝ÊüÝöU(ku¿░)┤¾╣½╣▓▒úı¤ú¼Á½Î¾┼╔Á─Ã░╠ß╩Ã▀@éÇ(g¿¿)©ú└¹ç°╝Ê╩Τ╚▒ÏÝÜ╩ÃÊ╗éÇ(g¿¿)æùı■├±Í¸ç°╝Êú¼╬¸À¢Á─ξ┼╔Å─üÝ▓╗ò■ͺ│ͤ±┘┬╦╣¹£─ÃÿËÊÈ©ú└¹×Ú├¹üÝ©ÒîúÍãÁ─ç°╝ÊíúÊ▓¥═╩Ãıf─Ò┐╔ÊÈöU(ku¿░)┤¾╚║Ë‗ú¼Á½╩Ã▀@éÇ(g¿¿)╚║Ë‗▒ÏÝÜıµı²¥▀Ëðí░╣½╣▓ðÈí▒ú¼▓╗─▄Ë╔ılüÝ╚╬ÊÔ░Ð│Ííú ííííí░╠®╠╣─ß┐╦╣╩╩┬í▒Ê▓╩Ã▀@ÿËú║È┌╬ú┤¼╔¤┤¼ÚL░Ð╠Ë╔·ÖÓ(qu¿ón)äØ▀M(j¿¼n)┴╦╚║Ë‗°▓╗È╩ÈSí░ÎÈË╔©éáÄí▒ú¼╣½▒è×Ú╩▓├┤─▄ͺ│Í╦¹ú┐╩Τ╚«ö(d¿íng)╚╗╩ÃÃÚ¥│╬ú╝▒╩╣┤¾╝ÊËXÁ├└Ý«ö(d¿íng)╚þ┤╦ú¼Á½©³ÍÏʬÁ─ú¼▀Ç╩ÃÊ‗?y¿ñn)Ú╦¹▒¥╚╦Ê▓░Ð╠Ë╔·Ö?qu¿ón)ÎîÂ╔¢o╚║Ë‗ú¼ÎÈ╝║Ê▓áÌ╔³Á¶┴╦ú╗╚þ╣¹╦¹äâèZ┴╦äe╚╦Á─ÖÓ(qu¿ón)└¹ÎÈ╝║àsí░ÎÈË╔í▒ÁÏ?f¿┤)îı╝¥╚╔·═º╠ËÎ▀ú¼─Ã╣½▒è▀Ç▓╗░Ð╦¹Îß▒Ô┴╦úí íííí╦¨ÊÈ╬Êıfí░╚║╝║ÖÓ(qu¿ón)¢þí▒È┌Ê╗¿ÀÂç·â╚(n¿¿i)╩Ã┐╔ÊÈË╬Êãíó°ÃÊÙy├ÔË╬Êãíú╚╗°▀@¥═│÷¼F(xi¿ñn)┴╦Òúıôú║ÖÓ(qu¿ón)¢þ▓╗äØÃÕ¥═Ùy├Ô╚║╝║╗ý¤²¯ìÁ╣ú¼Á½Ê╗┤╬äØ╦└Ë̓oÀ¿┼còr(sh¿¬)¥Ò▀M(j¿¼n)ú¼È§├┤Ìkú┐ ííííãõîì(sh¿¬)¼F(xi¿ñn)┤·æùı■ÍãÂ╚ÊТø(j¿®ng)╗¨▒¥¢ÔøQ┴╦▀@éÇ(g¿¿)åû¯}ú¼─Ã¥═╩ÿã┌ÍÏäØíú░l(f¿í)▀_(d¿ó)╩ðê÷¢ø(j¿®ng)Ø·(j¿¼)ç°╝ÊÍ«╦¨ÊÈËðâ╔³hÍãú¼Å─╚║╝║ÖÓ(qu¿ón)¢þÁ─¢ÃÂ╚üÝÍvú¼¥═╩ÃÈ┌ÖÓ(qu¿ón)¢þ▒╚¦^─ú║²íóËðáÄÎhÁ─¯I(l¿½ng)Ë‗ú¼├┐©¶ÄÎ─ÛÎî┤¾╝ÊÍÏäØÊ╗┤╬íú└²╚þÈ┌¢ø(j¿®ng)Ø·(j¿¼)À¢├µú¼▀@┤╬┤¾╝Ê▀xô±╔þò■³hú¼Îî╦³öU(ku¿░)┤¾╚║Ë‗ú¼È÷╝Ë╣½╣▓À■äı(w¿┤)ú¼╚þ╣¹│÷¼F(xi¿ñn)▒Î▓íú¼¤┬┤╬È┘▀x▒ú╩ϳhú¼Îî╦³öU(ku¿░)┤¾╝║Ë‗ú¼┤┘▀M(j¿¼n)╣½ã¢©éáÄíú▓╗╣▄ȧÿËú¼├┐┤╬¢þÀÍ╝╚¿ú¼─Ã╚║Ë‗¥═▒ÏÝÜ▒úÎC╩Ã├±Í¸Á─ú¼╝║Ë‗¥═▒ÏÝÜ╩ÃÎÈË╔Á─ú¼▀@¥═¢ðÁÎ¥Çú¼╩Ã▓╗ÀÍξËÊÁ─íóã┤aÁ─╣▓ÎRíú╬Êéâç°╝Ê▓╗©Òâ╔³hÍãú¼Á½Å─▀@┤╬╬´ÖÓ(qu¿ón)À¿ıôáÄíó©─©´À┤╦╝ıôáÄ┐┤üÝú¼─│ÀNð╬╩¢Á─â╔┼╔─╦Í┴ÂÓ┼╔ÊÔÊè╩Ã├¸´@┤µÈ┌íóƒoÀ¿╗Ï▒▄Á─ú¼─▄▓╗─▄▀_(d¿ó)│╔╣▓ÎR─Ïú┐░l(f¿í)▀_(d¿ó)╩ðê÷¢ø(j¿®ng)Ø·(j¿¼)ç°╝ÊÁ─Üv╩À©µÈV╬Êéâú¼═Û╚½Á─╣▓ÎR╩Ã▓╗┐╔─▄Á─ú¼├ÒÅè(qi¿óng)þͫÊ▓╩Ã╠ô╝┘Á─ú¼Á½ÁÎ¥ÇÁ─╣▓ÎR╚þ╣¹Ê▓ø]Ëðú¼─ÃÀ¿Í╬┼c╩ðê÷Á─╗¨ÁA(ch¿│)¥═│╔åû¯}┴╦íú íííí╩ðê÷¢ø(j¿®ng)Ø·(j¿¼)╩à ííííÍv¥┐║¤À¿ðÈÁ─¢ø(j¿®ng)Ø·(j¿¼) íííí°¼F(xi¿ñn)È┌╬Êéâί┤¾Á─åû¯}ÃíÃí╩Ãú║Ëðð®╚╦ÊÈ╣½╣▓¯I(l¿½ng)Ë‗ú¼╗‗ÊÈ╦¨Í^╣½╣▓└¹Êµ×Ú└ÝË╔äâèZ┴╦╚╦éâÁ─ÎÈË╔▀xô±ú¼ë║┐s┴╦╚╦éâÁ─╝║Ë‗ú¼Á½╩Ã═¼òr(sh¿¬)às░Ð┼‗├øãüÝÁ─▀@éÇ(g¿¿)í░╚║Ë‗í▒Í├Ë┌╦¹ÎÈ╝║Á─éÇ(g¿¿)╚╦ÊÔÍ¥¤┬ú¼Â°═Û╚½ããë─┴╦ãõ╣½╣▓ðÈíú▀@¥═╩ÃÀ¿╝Êı■Í╬鸢y(t¿»ng)Èý│╔Á─ίç└(y¿ón)ÍÏÁ─▒Î▓ííú«ö(d¿íng)─Û╬ÊéâÁ─Ê╗ð®¤╚ı▄¥═îª┤╦═┤╝ËßÿÝ¥íú¤±├¸─®³SÎ┌¶╦¥═ıf▀^ú║▀@ð®╚╦¥═╩Ãʬí░╩╣╠ý¤┬╚╦▓╗Á├ÎÈ╦¢íó▓╗Á├ÎÈ└¹ú¼Â°ÊÈ╬ÊÍ«┤¾╦¢×Ú╠ý¤┬Í«┤¾╣½íúí▒äâèZ╦¨Ëð╚╦Á─╝║Ë‗ú¼╩╣╦¹éâí░▓╗Á├ÎÈ╦¢ú¼▓╗Á├ÎÈ└¹í▒ú¼È¡üÝ▓╗▀^╩âÞí░╠ý¤┬Í«┤¾╣½í▒üÝÍ\í░╬ÊÍ«┤¾╦¢í▒°ÊÐíú▀@▀Ç▓╗ë‗┐╔Éuíó┐╔É║íó┐╔▒»åßú┐ íííí▀@¥═╩Ã╣½Ë‗╦¢Ë‗Á─¯ìÁ╣ú¼╚║Ë‗╝║Ë‗Á─¯ìÁ╣ú¼╚║Ë‗ƒo├±Í¸ú¼╝║Ë‗ƒoÎÈË╔íúÊ╗Á®│÷¼F(xi¿ñn)▀@ÀNá¯æB(t¿ñi)ú¼éÇ(g¿¿)╚╦ÖÓ(qu¿ón)└¹║═╣½╣▓À■äı(w¿┤)Â╝ò■å╩╩ºú¼╬Êéâ¥═ò■├µ┼R╝╚ø]ËðÎÈË╔íóÊ▓ø]Ëð©ú└¹Á─á¯æB(t¿ñi)ú¼Â°ÃÊ▀@ÀNá¯æB(t¿ñi)ò■▒ݼF(xi¿ñn)×ÚÊ╗ÀNС¡h(hu¿ón)íú▒╚╚þıfÊ╗òr(sh¿¬)ı■▓▀ã½Î¾ú¼┤¾╝ÊÁ─ÎÈË╔£p╔┘┴╦ú¼Á½╩éú└¹▓óø]ËðÈ÷╝Ëú╗Ê╗òr(sh¿¬)ı■▓▀ËÍã½ËÊú¼┤¾╝ÊÁ─©ú└¹£p╔┘┴╦ú¼Á½╩ÃÎÈË╔▓óø]ËðÈ÷╝Ëíúξòr(sh¿¬)ÖÓ(qu¿ón)┤¾Ïƒ(z¿ª)▓╗┤¾ú¼öU(ku¿░)ÖÓ(qu¿ón)╚¦ÊÎåûσ(z¿ª)Ùyú¼ËÊòr(sh¿¬)σ(z¿ª)ðíÖÓ(qu¿ón)▓╗ðíú¼ðÂσ(z¿ª)╚¦ÊΤÌÖÓ(qu¿ón)Ùyíú▀@ÿËÁ─í░│▀¾ÂС¡h(hu¿ón)í▒Íð╬Êéâ¥═║▄ÙyËðı²│úÁ─À¿Í╬íúÊ‗?y¿ñn)ÚÀ¿Í╬╔þò■┐╔ÊÈ╩ÃÎÈË╔╩ðê÷ú¼Ê▓┐╔ÊÈ╩éú└¹ç°╝Êú¼Á½â╔ı▀Â╝▒ÏÝÜÖ?qu¿ón)σ(z¿ª)îªæ¬(y¿®ng)ú¼ÖÓ(qu¿ón)╩▄¤Ì°σ(z¿ª)┐╔åûíúËðÖÓ(qu¿ón)ƒoσ(z¿ª)▀Çıä╩▓├┤À¿Í╬ú┐ íííí╬ÊéâÍví░╩ðê÷¢ø(j¿®ng)Ø·(j¿¼)╩ÃÀ¿Í╬¢ø(j¿®ng)Ø·(j¿¼)í▒ú¼îì(sh¿¬)ÙHÊÔ┴x¥═╩ÃÍ©╩ðê÷¢ø(j¿®ng)Ø·(j¿¼)╩ÃÍv¥┐║¤À¿ðÈÁ─¢ø(j¿®ng)Ø·(j¿¼)ú¼Â°▀@éÇ(g¿¿)║¤À¿ðÈú¼▓╗âH╩Ã│╔╬─À¿ÊÔ┴x╔¤Á─║¤À¿ðÈú¼©³ÍÏʬÁ─╩Τ╚╩ÃÎÈ╚╗À¿ÊÔ┴x╔¤Á─║¤À¿ðÈú¼Ê▓¥═╩ÃıfʬÍv╣½└Ýíó╣½ı²íú¼F(xi¿ñn)È┌Ëð║▄ÂÓ╚╦░Ðí░À¿Í╬í▒└Ý¢Ô×Ú¥═╩Ã╝t¯^╬─╝■ú¼░┤ıı╝t¯^╬─╝■ê╠(zh¿¬)ðð¥═╩ÃÀ¿Í╬ú¼Á½╩Ã║▄ÂÓ╝t¯^╬─╝■▒¥╔Ý¥═╩Ã▀`À¿Á─ú¼▓╗âHÈ┌│╠ð‗╔¤▀`À¿ú¼Â°ÃÊÈ┌ÎÈ╚╗À¿ÊÔ┴x╔¤Ê▓╩Ã▀`▒│╣½ı²Á─íú▀@ÀN╝t¯^╬─╝■È¢ÂÓú¼┐╔─▄╬ÊéâÙxÀ¿Í╬▓╗╩ÃÈ¢¢³ú¼Â°╩ÃÈ¢▀h(yu¿ún)íú íííí╬ÊËXÁ├¤±ç└(y¿ón)Å═(f¿┤)ÈþÈ┌100ÂÓ─ÛÊÈÃ░¥═Ív▀^Á─ú¼Í╗ʬıµı²─▄ë‗¢ÔøQ╚║¾wÖÓ(qu¿ón)¢þÁ─åû¯}ú¼Á¢ÁÎ╩Ã╚║Ë‗┤¾Ê╗³c(di¿ún)▀Ç╩Ã╝║Ë‗┤¾Ê╗³c(di¿ún)ú¼Ê▓ÈS▓╗╩Ãıµı²Á─åû¯}íú°ÃÊÈ┌▀@ÿËÁ─©±¥Í¤┬ú¼©¸ÀN└¹Êµ╚║¾wú¼©¸ÀNâr(ji¿ñ)ÍÁ╚í¤‗ú¼░³└¿ƒoıôξ┼╔▀Ç╩ÃËÊ┼╔ú¼Â╝ò■©¸Á├ãõ╦¨íú ííííί¢³┴─╠ýú¼Ëð╬╗ξ┼╔┼¾ËÐıfú¼╬¸À¢Ê▓▓╗ÊèÁ├¤±╬Êéâ╦¨ÍvÁ──ÃÿË▒úÎo(h¿┤)╦¢ËðÏö(c¿ói)«a(ch¿ún)ú¼▒╚╚þıf©▀ÂÉ╩ı©▀©ú└¹ÍãÂ╚ú¼╚þ╣¹ÂÉ┬╩ı¸Á¢80%ú¼─Ã║═í░╣▓«a(ch¿ún)í▒ËÍ▓¯ÂÓ╔┘ú┐╬Êıf╦¹ÍvÁ─Ê▓▓╗╩Ãø]ËðÊ╗³c(di¿ún)Á└└Ýú¼Á½╩Ã▀@Á├ËðÄÎéÇ(g¿¿)Ã░╠ßú║╚╦╝ÊÁ─͸Åê▓╗╩ÃÊ╗ȬÁ─ú¼▀xô±Ê▓▓╗╩ÃÊ╗┤╬ðÈÁ─íúÁ┌Ê╗ÂÉ┬╩ȧ├┤¿ú¼▀@î┘Ë┌╚║Ë‗ú¼╩Ã╣½╣▓▀xô±Á─ÀÂç·ú¼▓╗╩ÃË╔─│éÇ(g¿¿)╗‗ÄÎéÇ(g¿¿)¢y(t¿»ng)Í╬ı▀┼──X┤³¥═─▄øQ¿Á─íúÂÉ╩ıı▀╠ý¤┬Í«╣½ã¸ú¼┤¾╝ÊÂ╝ͬÁ└ËðÊ╗¥õÈÆ¢ðí░ƒo┤·▒Ý▓╗╝{ÂÉí▒ú¼▓╗¢ø(j¿®ng)╣½├±éâÁ─═¼ÊÔú¼ø]Ëð╝{ÂÉ╚╦Á─Ëæıôú¼─Ò─▄ËðÖÓ(qu¿ón)ı¸ÂÉåßú┐Á┌Â■╝┤╩╣îì(sh¿¬)ðð©▀ÂÉ┬╩ú¼îªÂÉ║¾Á─▀@▓┐ÀÍ┘Y«a(ch¿ún)ÖÓ(qu¿ón)Ê▓ʬ┤_îì(sh¿¬)▒úÎCú¼╝║Ë‗¥═ÈôÎÈË╔┬´íúı¸ÂÉ╩ÃÊ╗╗Ï╩┬ú¼Á½îªÂÉ║¾Á─Ïö(c¿ói)«a(ch¿ún)ú¼©ú└¹ç°╝ÊÊ▓ʬ┤_îì(sh¿¬)▒úı¤┬´íúÁ┌╚²ú¼┤¾╝Ê╩┌─Òı¸ÂÉÍ«ÖÓ(qu¿ón)¥═ʬ─▄ë‗?q¿▒)ª─ÒåûÏ?z¿ª)ú¼ÊÈ▒úÎC─Ò▓╗ò■í░ÊÈ╬ÊÍ«┤¾╦¢×Ú╠ý¤┬Í«┤¾╣½í▒íú©³ÍÏʬÁ─╩ÃÁ┌╦─ú¼îªÂÉ┬╩▀M(j¿¼n)ððÎhıôÊ▓╩Ã╝║Ë‗ú¼╩Ã╣½├±ÐÈıôÎÈË╔Á─ÖÓ(qu¿ón)└¹ú¼╝┤╩╣═¿▀^┴╦©▀ÂÉ┬╩┴óÀ¿╗‗ı▀ıf©ú└¹ç°╝Ê┴óÀ¿ú¼▓╗═¼ÊÔ▀@ÀNÎ÷À¿Á─╚╦▓╗─▄┐╣ÂÉú¼Á½╦¹╚È╚╗┐╔ÊÈð¹é¸╦¹Á─͸ÅêíúÁ¢┴╦¤┬Ê╗┤╬ú¼╬Ê╩ÃıfÁ¢┴╦¿ã┌ÍÏäØí░ÖÓ(qu¿ón)¢þí▒Á─òr(sh¿¬)║‗ú¼┤¾╝ÊÊ▓ÈSËÍò■▀x┼eÁ═ÂÉ┬╩ıôı▀┴╦─Ïíú ííííÊ‗┤╦╬Êıf╚þ╣¹│ðıJ(r¿¿n)▀@ÄÎùlú¼─Ã├┤ƒoıô─Ò╩Ã͸Åê░┘ÀÍÍ«░┘©▀ÂÉ┬╩Á─ÿOÂ╦╝»¾w͸┴xı▀ú¼▀Ç╩Ã͸Åê┴ÒÂÉ┬╩Á─ÅÏÁÎéÇ(g¿¿)╚╦͸┴xı▀ú¼▀Ç╩Ã͸Åê░┘ÀÍÍ«╬Õ╩«Á─ÍðË╣Í«Á└͸Åêı▀ú¼Â╝╩üF(xi¿ñn)┤·╗»ÂÓȬ╔þò■Íðı²│úÁ─íóÀeÿOÁ─Ê╗ȬíúÁ½╩Ã─Ã╬╗┼¾ËÐıf▀@▓╗ððú¼©¶ÄÎ─ÛäØÊ╗┤╬ú¼▀ÇËðø]ËðéÇ(g¿¿)£╩(zh¿│n)Тú┐©▀ÂÉ┬╩║├¥═©╔┤Ó¿┴╦ú¼╬Êéâ¥═Ë└▀h(yu¿ún)▀@├┤¤┬╚Ñíú╬Êıf─Ã¥══Û┴╦ú¼╚þ╣¹▀@ÿËÁ─ÈÆú¼▓╗╣▄─Ò╩Ã͸Åê░┘ÀÍÍ«░┘Á─ÂÉ┬╩ú¼▀Ç╩Ã͸Åê░┘ÀÍÍ«┴ÒÁ─ÂÉ┬╩ú¼▀Ç╩Ã͸Åê░┘ÀÍÍ«╬Õ╩«Á─ÂÉ┬╩ú¼┤¾╝ÊÂ╝ø]Ëð║├╣¹ÎË│Èíú íííí╦¨ÊÈ╬ÊËXÁ├ÛP(gu¿ín)µI▓╗È┌Ë┌╚║Ë‗┤¾Ê╗³c(di¿ún)▀Ç╩Ã╝║Ë‗┤¾Ê╗³c(di¿ún)ú¼ÛP(gu¿ín)µI¥═È┌Ë┌╬Êäé▓┼ÍvÁ─▀@ÄÎéÇ(g¿¿)È¡ätú║Á┌Ê╗╩Ã╚║╝║ÖÓ(qu¿ón)¢þʬ?ji¿úng)ØÃÕú¼▓╗─▄╚║╝║▓╗ÀÍ╔§Í┴╚║╝║¯ìÁ╣ú╗Á┌Â■╝║Ë‗ʬÎÈË╔ú¼╚║Ë‗ʬ├±Í¸ú¼▓╗─▄Á╣▀^üÝú¼╣½╣▓ÖÓ(qu¿ón)┴ªÙSÊÔÃÍÀ©╦¢╚╦¯I(l¿½ng)Ë‗ú¼éÇ(g¿¿)╚╦║═ðí╝»êF(tu¿ón)ËÍë┼öÓ╣½╣▓¯I(l¿½ng)Ë‗ú╗Á┌╚²ú¼¥═╩â^┤¾▓┐ÀÍÁ─╚║Ë‗║═╝║Ë‗Ëð╣▓ÎRú¼Â°îªË┌─Ãð®▓╗─▄ð╬│╔╣▓ÎRÁ──ú║²¯I(l¿½ng)Ë‗ú¼┐╔ÊÈÎî┤¾╝Ê¿ã┌ÍÏäØíúÍ╗ʬ▀@ÿËú¼╬ÊéâÁ─╩ðê÷¢ø(j¿®ng)Ø·(j¿¼)¥═Ëð┴╦Ê╗éÇ(g¿¿)║├Á─╗¨ÁA(ch¿│)íúÈ┌▀@éÇ(g¿¿)╗¨ÁA(ch¿│)╔¤ú¼▓╗╣▄╩Ã͸Åê©ú└¹ç°╝ÊÁ─╚╦ú¼▀Ç╩Ã͸ÅêÎÈË╔À┼╚╬Á─╚╦ú¼Â╝┐╔ÊÈ©¸Á├ãõ╦¨ú¼Â╝┐╔ÊÈÈ┌╔þò■Á─▀M(j¿¼n)▓¢║═░l(f¿í)ı╣ÍðãÀeÿOθË├íúÁ½╩Ã╚þ╣¹ø]Ëð▀@ÿËÊ╗éÇ(g¿¿)╗¨ÁA(ch¿│)ú¼║▄┐╔─▄▀@â╔ô▄╚╦Á─¤ú═¹Â╝ò■┬õ┐ıú¼╬Êéâ¥═╠°▓╗│÷í░│▀¾ÂС¡h(hu¿ón)í▒ú¼╠°▓╗│÷├±┤Ô͸┴x║═╣Я^͸┴xíóí░ë─╩ðê÷í▒║═í░ë─Ëï(j¿¼)äØí▒Á─╣Í╚ªíú |
| ð┬└╦╩ÎÝô > Ïö(c¿ói)¢ø(j¿®ng)┐vÖM > ¢ø(j¿®ng)Ø·(j¿¼)îW(xu¿ª)╚╦ > ¢ø(j¿®ng)Ø·(j¿¼)îW(xu¿ª)╚╦--ÃÏòƒ > ı²╬─ |
|
 |
| ƒß ³c(di¿ún) îú ¯} | ||||
| ||||
|
| ||||||||||||||||||||||||||||||||||||||||||||||||||||||||||||||||||
|
ð┬└╦¥W(w¿úng)Ïö(c¿ói)¢ø(j¿®ng)┐vÖM¥W(w¿úng)ËÐÊÔÊè┴¶ÐÈ░Õ ÙèÈÆú║010-82628888-5174ííííííÜgË¡┼·ÈuÍ©ı² ð┬└╦║å¢Ú | About Sina | ÅV©µÀ■äı(w¿┤) | ┬ô(li¿ón)¤Á╬Êéâ | ıðã©ð┼¤ó | ¥W(w¿úng)ı¥┬╔ă | SINA English | ò■åTÎóâÈ | «a(ch¿ún)ãÀ┤Ê╔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